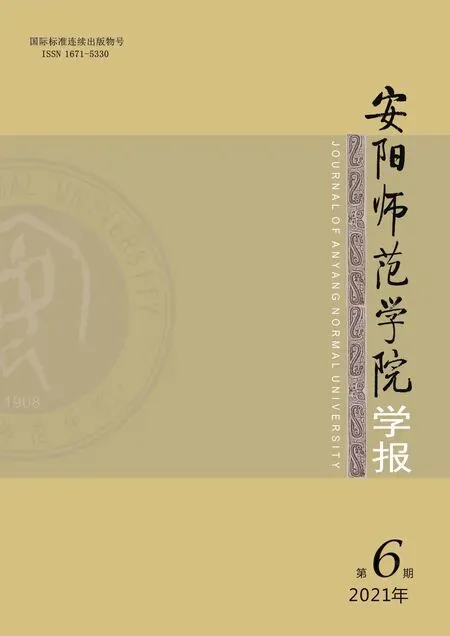中美新冠疫情治理的差异及其根源分析
2021-11-28李庆四
李 倩,李庆四
(1.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现代社会发展增强了现实生活诸要素各环节多领域的关联性,公共危机逐渐从单一向复合型演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全方位嵌入社会整体运行发展之中,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因素。新冠病毒自身的高度变异性及快速传播性导致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公共卫生事件突破行政区域及时空边界影响,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民众焦虑情绪,破坏了社会力量凝聚,挑战了国家治理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指出,新冠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和冲突[1]。约翰霍普金斯流行病学教授詹妮弗·纳佐(Jennifer Nuzzo)坦言,由于全球环境正变得越来越适合病毒传播,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太可能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甚至可能不是最糟糕的[2]。
一、中美新冠疫情治理效能的差异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不仅严重冲击了各国医疗卫生系统,更将根源于不同政治制度的应对机制和治理效能聚焦于公共危机治理这一共同场域。虽然国内外学界对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人类历史转折点这一议题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传播不受国家制度限制,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维侵害,公共危机应对成为考验各国治理效能和制度根源的共同标准。
从疫情治理效能角度出发,中美两国客观而言差异较大。由于病毒自身的高传染性和不确定性,巨大的人口基数叠加流动因素的影响,在爆发初期中国的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遭受巨大冲击[3]。疫情暴露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的不足和短板。中国将“生命至上”即对生命权的维护置于治理效能转化目标首位,认为疫情面前没什么比挽救生命健康更重要,所以“必须以人权为基础,其中也包括健康权。”(1)世卫组织总干事2020年12月11日在2019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媒体通报会上的开幕词。https://www.who.int/zh/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december-2020.登录时间:2021年2月12日。中国在危机时刻采取严厉隔离措施,付出艰苦努力和巨大代价之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与此同时统筹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国家。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因资本力量进入并主宰了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导致资源分布不均,医院设备配备缺位,暴露了国家卫生体系的不足。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冲击之下濒临崩溃,造成很多病患丧生,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超过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以及海湾战争战斗死亡总人数(2)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战争和军事行动的伤亡:名单和统计》统计得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战斗死亡人数分别为53402人、291557人、33739人、47434人以及148人。参见American War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Casualties:Lists and Statistics,July 29,2020,https://fas.org/sgp/crs/natsec/RL32492.pdf.登录时间:2021年5月1日。,成了事实上的疫情风暴中心,遭到美国学者的激烈批评[4-6]。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卫生安全指数居全球首位,拥有最雄厚的经济实力、最先进的医疗水平及最强大的医疗力量,而且是在中国为世界争取了疫情防控“窗口期”之后爆发,拥有完整且有效抗疫经验,本应准备充分到位。但由于病毒爆发初期远离美国本土或其他原因,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认真应对,外加检测试剂盒的制造缺陷严重、防护装置匮乏等原因,疫情逐步走向失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9月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本国对新冠病毒爆发反应不足,对政府应对能力评价较低[7]。拜登政府将战胜新冠疫情视作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困难挑战之一,执政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出台全国性疫情防控政策。2021年1月发布了一份长达200页的《COVID-19病毒应对和大流行防范国家战略》,公布了包括疫苗接种、疫情检测、佩戴口罩、扩大救济、开放学校以及促进公平等相关的多项行政措施[8]。拜登政府执政之初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迫近42万人[9],“百日抗疫”后死亡病例增加16万,平均每天新增死亡病例约1600例,同比特朗普执政后期百日内平均每日新增死亡病例约1900例,(3)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特朗普政治执政末期的100日内(2020年10月12日-2021年1月19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计算得出。参见COVID-19 Dashboard by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SSE)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拜登政府确有抗疫成效但并不显著,美国依然是目前世界上确诊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新冠疫情以来美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美国2000万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在流感大流行中失去了工作,而约有650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万亿美元以上,它们现在的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10]。中美面对同样棘手的疫情困境,治理效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新冠疫情暴露美国的威权转向》中将美国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行政结构决策能力匮乏[11]。福山(Francis Fukuyama)明确回避了唯体制论二分法,聚焦于“国家能力”议题[5](P26-32)。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撰文直指“美国国家能力之死”[12]。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13]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毫不讳言地指出,新冠疫情颠倒了中美两个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和提供国际援助方面的角色[14]。可见各方学界对美国疫情防治低效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
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与危机相伴随,现代社会已然进入了公共危机集中的风险全球化时代。“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5]。当代公共危机不仅表现出意外性、突发性和公共性等经典特征,也日益凸显出跨域性、复合性和未知性等新特性。人类囿于自身认知水平有限性与事物发展多变性的矛盾,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公共危机进行精准判断,故而难以准确预测结果的严重性。人类社会本质上是需要合作的群体[16]。面对风险社会日益增多的公共危机,探讨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危机应对机制、分析政治制度根源及由此造成的治理效能的差异,对于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中美疫情治理机制的差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指出:“整个社会都关心的问题是负责公共事务的政治机构所采取的确切形式,以及旨在指导人类行动的制度,因为每个成员都渴望有意义的生活。”[17]中美两国面对疫情冲击时在理念认知、决策机制以及运行效果三个层次的差异,凸显了政治与科学、权威与制衡及国家动员能力的三重差异。
(一)政治与科学的张力突出理念认识差异
如何平衡政治立场和科学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各国政府应对疫情时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侧重从分析病毒自身特征入手,机制构筑和决策实施都建立在专业认知和系统分析基础之上。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评估结果,修订并发布了多项疫情防控、诊疗技术和心理疏导方案,科学规范并规模化地开展病例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18]。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个人,从公共卫生到后勤保障,系统各部在行政权力领导下科学有效运行。
美国应对疫情的认知理念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后差异较大,经历了由政治向科学转变的过程,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政治化导向)将对美国的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产生持久的影响[19]。美国存在政治泛化倾向,政治与科学的较量使得国内对待疫情的立场和观点分裂明显。特朗普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反应不足且过度乐观,漠视病毒对公众健康及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将党派政治忠诚凌驾于专业知识之上,干预科学界的预防措施[20],甚至莫名其妙地公开表示没有什么理由担心(病毒影响)[21]。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病毒防控措施迎合了支持严格移民控制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以反华为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持续发酵,日益凸显出狭隘性、狂热性和暴力性等特征,甚至演化为非理性的排他行为,实际上形成了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主义逻辑。“特朗普将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中国……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他灾难性的疫情处理方式的注意力。”[22]事实上这并不是偶发事件,历史上美国也曾将1347年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大流感归咎于中国[23]。拜登政府视新冠疫情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造成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内战以来对美国民主最严重的一次攻击(4)拜登总统在国会联系会议上发表讲话。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ddress-to-a-joint-session-of-congress/.,重新确立了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不受政治干扰且共同推动疫情防控的政策,积极推动疫苗接种。拜登签署了庞大的COVID—19救援计划,承诺将在100天内接种2亿支疫苗[24]。事实上美国在应对疫情时,政治与科学在理念认识层面产生的纠葛,对防控结果造成了深远影响。
(二)权威与制衡的分歧扩大决策机制差异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令许多决策者和大部分民众措手不及。公共危机决策机制的现代化构建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安全服务,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职能权威性决定其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中国金字塔形的行政体系向来重视强调政治权威,协调统一各级各部以形成合力。政府在决策时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和丰富的社会资源,通过中央权威意志表达以整合多元主体,进而协调各级力量。危机来临时供给公共产品,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同时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责任边界,科学配置管理分工。地方政府在中央的行政框架内发挥有限主动性,客观上缩短了防控链条长度,提升了疫情治理效率。
美国立宪制不创设绝对权威,甚至视其为暴政之源而千方百计予以防范。疫情爆发迄今,美国困顿于分权制衡体制因而始终未能建立系统化的抗疫机制,整个国家对统一的防控政策施政乏力。同时,联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在“隔离政策”上产生分歧,再加两党制衡掣肘,疫情救助计划迟迟难以生效。疫情初期数据矛盾混乱,更新速度滞后且不全面,难以实时反映疫情扩散的最新情况。由于技术缺陷、监管障碍以及领导不力等原因,抑或由于特朗普政府担心医疗体系被疫情击穿,所以未能或者不愿进行规模化检测,故而无法开展必要的流行病学调查。
由于政治上横向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纵向上州与联邦相对独立并分权,行政权力在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被广泛分配,使诸如怎样应对疫情等日常决策变得非常困难。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型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更多时间关注有效治理的保障。
(三)国家动员能力不同凸显运行效果差异
动员能力考验一国面对重大公共危机的应变能力,强调人员物资必要时的迅速集中、统筹协调以满足效率需求。国家动员能力是政治绩效的直接表现,不仅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程度,更强调对机构控制的有效性,回应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强调,世界各地抗疫形势表明,只要发挥强大的领导动员能力,实行清晰全面的应对战略,保持沟通的连贯性和人员的参与度,仍可扭转抗疫的不利趋势[25]。面对公共危机的冲击,民主集中制更善于发挥自身优势,强有力的中央领导能快速动员和集中各方力量,指挥与决策都发生在制度框架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联合防疫,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疫情爆发之后果断关闭离汉通道、限制人员流动、完善基层网格化管理、推迟复工复产,与此同时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支援行动,全力驰援湖北。尽管初期也曾引起一些争议,但这的确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
由于美国在冷战后的20至25年中,未能将国家动员能力置于主要国防规划问题之列[26],行政体系内部权力过分分散,程序正确成为权力合法性唯一标准。美国社会分裂加剧,政治极化严重,种族多元化和亚文化多样化等产生的文化认同张力早已存在,由此而生的观念冲突频发,导致社会动荡撕裂,催生暴力犯罪,严重阻滞了国家动员能力的发挥,进一步加剧了疫情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国家动员能力还涉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时至今日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只是政府“编造”出来控制民众的谎言。凡此种种均严重制约了美国应对疫情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早在拜登就职当日,美国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都是世界遥遥领先,疫苗接种工作更是刻不容缓。然而尽管美国疫苗接种进展速度名列世界各国前列,但并未明显遏制新冠肺炎蔓延势头,美国社会曾经对疫苗研发成就的自豪感,也被困惑、指责、沮丧和焦虑情绪所取代。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不同价值观念下的不同治理机制是造成治理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但其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
三、中美疫情治理差异的制度根源分析
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使用最广泛的公共产品,兼具稳定性和根本性,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范式。制度本质决定了各国在面对共同危机时的巨大差异,这势必会导致应对结果的迥然不同。中国坚持人民立场、民主集中、一党执政、中央集权,迅速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同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暴露出的资本至上、分权制衡、党派对立、联邦分权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日益明显的政党极化现实和制约中央权威的联邦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局限与低效,暴露出美国治理体系的结构缺陷与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
(一)人民立场与资本至上凸显两国政策立场不同
政治制度的立场取决于其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捍卫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一定程度讲,新冠疫情危机应对可以视为对各国政治制度效能的集中检验,而决定政治绩效的终极因素是政治体制的人民性程度[27]。
人民民主专政扩大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专政主体范围,无论从理论维度抑或现实实践均鲜明有力地夯实了国家政治基础,民众在制度理念价值层面更倾向于建立对政府和政党的信任。近代以来中国在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代表皇权的制度改良以及代表资本的政治改革始终都无法弥合当时的社会分裂,未能形成合力以实现民族独立,更遑论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当代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架构原则体现了新型代议制民主集中,无论从政治制度原点抑或政权组织形式,均实现了人民立场的确立,以及对西方国家资本至上制度品格的超越。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资本立场为制度逻辑起点,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资本,操控政治、主宰权力,凌驾于国家力量建构之上。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疯狂掠夺触发全球金融、债务和财政危机,私有制逐渐显现出无法克服的矛盾。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调和当前的政治分裂与社会矛盾,资本垄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利益集团全面统治着美国经济和政治,决定着国家决策和行动。金钱政治、政治献金、资本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大肆渗透,美国70%以上的公众认为美国公共政策受到权势集团过大的影响[28],政治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自己的公民[29]。资本逻辑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平等本质[30],因为“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31],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事实上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教皇方济各在起草并签署新通谕谈到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时出人意料地指出:“世界体系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暴露出的脆弱性证明,市场自由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疫情大流行证明市场资本主义‘神奇理论’已失败。”[32]
(二)民主集中和分权制衡体现两国政治体制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横向看,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机关不是同行并列、相互制衡关系,而是产生与负责、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确保国家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持久有序,形成国家治理合力,在维护人民至上的同时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性。纵向看,各级人大代表来源具有在不同阶层民众中的广泛代表性,集体议事充分发扬民主,使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表达和落实,同时整体合力的集中提升了总体效率。“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最大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连。”[33]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体制,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做出决策。各级国家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合理划分职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中央集中领导,地方适度分权,由此使得国家机关在组织结构和职权构成上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
美国制度体系中权力分立的观点无疑是受到了古老的混合宪法思想影响,这些思想在柏拉图、西塞罗、阿奎那和洛克的著作中都有体现[34]。麦迪逊极力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原则,他坚持好的政治制度必须实现,“没有一种权力能超出其合法限度而不被其他权力有效地加以制止和限制。”[35]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大量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通过分权与制衡可以协调内部利益矛盾和冲突。首先,总统共和实质是一种否决型政体,分权制衡已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理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达成的妥协。在多种平行权力的现实制衡中,不同的权力机关相互倾轧,降低了国家权力的运行效率,削弱了国家机构的整体功能。其次,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间接选举制度,严格讲,美国公民并没有直接选举总统的政治权利。在寡头政治和金钱选举双重作用下产生的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有赖于政治与资本的相互制衡。在这样的逻辑体系中,美国部分民众将抗疫失败归咎于总统领导不力,但未从根本上对政治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如果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真的是“历史的终结”,那为什么会产生饱受诟病的抗疫机制和领导人呢?这实际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最后,美国民主化模式维系的是一种体制机制和操作层面的形式民主,过分强调政治参与度的提升和竞争性指标的达成,策略性的程序平等掩盖了社会分配的非正义实质。西方制度程序与目标本身,以及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混淆的潜意识陷阱将部分民众带入误区,对民主形式的崇拜,很容易丧失对实质性内涵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困惑不仅在于民主与善治谁居首位,更在于民主理性本体和现实之间的张力。
(三)一党执政和两党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不同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近代总体性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同时构建了新的国家秩序。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权威—秩序—发展”理论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权威对于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同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3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尽管多党并存,但必然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体现了整体权威理念下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良序合作。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与政治学说认为不同政党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各党派没有共同价值的目标引领,强调的是竞争而非合作[37],故而很难在国家利益最大化上达成共识,政策具有较强短视性和狭隘性,容易受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绑架[38]。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两次移民潮演化里,逐步变成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各自资本利益的代言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美国两党竞争、交替执政的政治生态不仅没有显示出制度最初设定时的优越性,反而日益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角斗工具,屡屡上演政治争斗闹剧,互相对峙、拆台、扯皮成为常态,限制了政府履行职责的范围和效率,导致政策实施效率低下,暴露了与生俱来的制度缺陷。党派竞争背景下,美国各党对疫情爆发的态度大相径庭,从疫情严重程度、核酸检测率、抗疫措施到复工进程等都因两党相互牵制而差异较大。两党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无法团结民众,一些州的分裂和独立情绪上升。新冠疫情危机加剧了两党在国内议题上的长期分野。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两党分歧在于经济和疫情防控何者优先,特朗普坚持经济为先、疫情防控要配合经济重启,而拜登则坚持疫情控制为先、经济重启应让步于疫情防控(5)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举行就任总统65天来的首场记者会,他表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经济仍是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设立的专职负责疫情防控的全球卫生安全小组在2018年被特朗普解散,无疑加剧了疫情失控。拜登政府上任签署了至少50项行政命令,其中大约一半推翻了特朗普的政策,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移民政策、修建边境墙和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39],并承诺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提供资金接种疫苗(6)外交政策杂志咨询了25位专家为拜登新团队在外交政策上的开局打分。Foreign Policy,SPRING 2021,pp.23-31.。甚至2020年总统大选出现因党派斗争而发生的“国会山暴动”,正常的行政系统运转受阻。
(四)中央集权与联邦分权显示两国制度协调能力不同
古今中外多数国家的央地关系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制度范式的嬗变以维护央地关系动态平衡为基础,本质上蕴含着政治架构理想化与国家治理实效性两大主题。对共同体内的行为进行协调的方式只有两种,即全体一致或建立权威,此外再无其他可能性[40]。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在权威体制、有效治理与民主参与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中国由若干行政区域单位组成单一主权国家,制度设计确保了强大国家力量的凝聚,确保了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府的行政效率,为制度权威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坚实架构基础。故而自上而下的信息指令可以迅速下达执行,各方资源力量得以全力调动,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变成现实。
联邦制的美国,中央和地方共享权利、分而治之且相互制衡,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难以形成整体行动力。联邦政府不对地方治理负责,地方无法协调全国资源,难以形成国家合力。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二者权力划分“是建立在集权与分权这对矛盾的基础上的”[41]。美国联邦体制和两党竞争制造的政治张力对于处理疫情的负面作用明显,再加之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诱导,联邦主体和中央政府间往往因为利益冲突扯皮、拆台和掣肘。由于没有整体计划,导致了各州疫情物资的严重短缺,并且在未来疫苗工作上也极有可能出现同样失调情况。联邦与各州不同的关系模式决定了各州公共卫生机构在基本运作、资金来源、活动安排、人事任免等方面亦有所差别。在两党政治极化大背景下,联邦与州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出现诸多矛盾。
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制度设计是整体主义理念下的分工合作,更强调合力的形成,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制度形态克服了资本为核心带来的生产高度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制度合力更适合应对公共风险,尤其重大公共危机。美国以资本私有制和利润最大化为核心,政治制度框架主要基于资本统治下的权力分立原则形成,在实际行使共有权力过程中,政府活动持久的有效性更依赖各部门密切合作。私有制基础上的分权制衡制度在应对国内问题时,政党竞争变成攻讦与倾轧,国家永远处于实际分裂状态。正如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分析当今世界疫情形势时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失败的,难以理解的失败[22](P6)。
四、结语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0全球风险报告》显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各类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共振,全球风险复杂且多样。无论是大流行病、气候变化还是恐怖主义,都是全球性问题,唯有通过各国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并缓解风险。新冠病毒大流行及其在一些国家的剧烈反弹标志着全球发展议程的根本性转折,疫情凸显了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裂痕,加剧了此前人类面临的多项重大挑战,而我们尚处于后疫情时代的早期阶段[42]。疫情未能触动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协调行动,目前的多边治理机制缺乏陷入困境时立即采取行动的自主调节性[43],在最需要全球共同努力的阶段,国际合作仍然严重缺失。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加剧富裕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在获得疫苗方面正在出现的不平等[44]。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再次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理念,全人类共赢的逻辑应超越某个国家单赢的逻辑。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够仅凭本国之力战胜病毒,应对当前形势必须有全球合作的眼光和行动。中美可在疫苗研发、临床试验、财政刺激、信息共享、防控设施生产以及共同援助等方面合作,惠及全世界。从马克思唯物史观审视和观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走向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尽管两国之间存在根本制度差异,但从公共危机治理前景看,中美仍拥有应对全球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两国在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面对各种全球性公共危机,各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需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来审视未来发展的新格局、新特征和新趋势,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发展机遇、未来目标和历史走向,各国应当成为互帮互助、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放弃制度差异的羁绊,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更多全球公共治理危机与挑战,人类才能赢得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