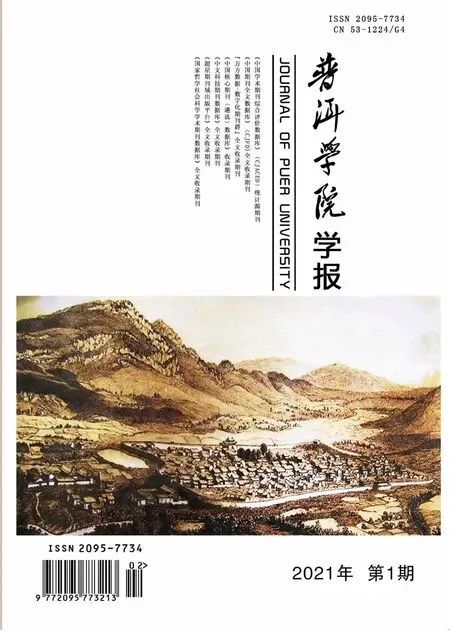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2021-11-27李雪
李 雪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0935
悲剧性是中国美学范畴中的重要内容,使艺术创作能够将作家对历史、自然、社会的悲剧属性有机地融入到美学创作的过程中,引发读者对艺术作品的思索。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美学”中界定了戏剧的概念,并指出悲剧是戏剧的核心,能够将哲学拷问融入到人们的审美体验中,使其深入地理解社会、历史及自然对人类的冲击,体现出人类在物质世界中的渺小与悲哀。而女性悲剧性是一种对“理性思考”和“自觉意识”的主观把握,能够借助艺术作品独有的审美理念完成对其自身的内在审视。萧红在很多作品中体现和阐述了这种女性悲剧意识,并将其对旧社会的忧伤和悲悯,以及受情感经历、人生经历、家庭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融入到对底层女性的描绘中。
一、《呼兰河传》中女性悲剧意识的形成渊源
20世纪30年代,我国正处于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抗战时期,萧红这个柔弱瘦削、面色苍白的女作家以其独有的艺术笔触,创造出《呼兰河传》。虽然这部长篇小说以散文化的笔致,诗化的句子,为人们展示了北方社会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并从中探索到浓郁的女性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是浅层的、是无意识的,却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角色的精神理念和情节发展。在揭示和描绘旧社会过程中,表达了萧红对世界、历史及社会的思考,体现出萧红独有的哲学理念。一般而言,解读一部文学作品,要将时代、创作背景、作家经历及读者联系起来,不能将作品解读局限在作品所呈现的角色塑造、情节编织、主题呈现、场景描写等层面上,要以整体意识来挖掘作品所隐含的哲学理念和文化思想。萧红在她极为短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情感和生活的磨难,使其对社会、人生及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见解。这种“见解”在她的家庭悲剧中得到体现,她曾在回忆录中说过:“家是无比温暖的‘居所’,当家不再温暖时,这世界将变得寒冷。寒冷得犹如冰雪般,将人的灵魂、血肉及肌肤冰封住,不见天日,不见光明”。家庭悲剧让萧红对世界形成了全新的认知,但她个性倔强、积极、总是以乐观的姿态迎接这个冰冷的“世界”。萧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女人,她的忧伤和痛苦来自男性,也来自社会,所以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是多元性的,涉及萧红个人、社会及历史,但更确切地说,这种悲剧意识是对萧红家庭悲剧、情感悲剧及社会悲剧的投射,是主观化的悲剧意识。而《呼兰河传》中体现萧红对女性被压迫、被侵害时的怜悯,及对男人施加给女人创痛时的敌意,便是萧红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鲜明投影。她在创作《呼兰河传》时,身患重病,在家庭生活上又面临挫折,因此在诵读《呼兰河传》时,读者能够感受到她在颠沛流离时的无奈,在生产的痛苦、情感的压抑及家庭变故下,她对社会、世界及人生的无奈。
二、《呼兰河传》的情节及思想
《呼兰河传》描绘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北方的普通小城及其居民的普通生活,它不仅是为萧红的个人经历“作传”,更是为这座偏僻的、蕴含浓厚民俗特色的小城作传。在角色刻画中,无不能感受到小城在历史的“车轮”下对作者的影响和冲击,鲜明地呈现出作者主观化中的小城民俗及个人的“悲剧意识”。《呼兰河传》第一二章以宏观视角,勾勒北方小城的格局,将呼兰河的荒凉和寒冷描绘得淋漓尽致,将北方小城的萧索与蒙昧衬托得分外鲜明。第三四章以“我”视角勾勒“我”的童年时光,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将萧红的个人体验融入其中,并加强了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文化底蕴。而第五六七章,却从“场景描写”过渡到“角色刻画”上,以此展现出二伯、冯歪嘴子、团圆媳妇的悲剧命运。将时代的悲伤烙印在呼兰小城上,使“我”的命运与“呼兰河”的命运紧紧地衔接在一起。小说结尾处,二伯因“绝后”而痛苦的场景,鲜明地揭示出小说的悲剧性主题。在文学创作上,萧红将个人自传与小城自传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小城的历史成长与个人的成长蜕变相融合,通过宏观的视角“呼兰河”-“呼兰城”向微观视角“我”-“呼兰居民”过渡,使小城的兴衰荣辱与“我”的悲剧性意识相重叠。人们通过诵读小说全部章节,能够发现“我”对“呼兰河”的“认知”是从寒冷得“大地满地裂着口”逐渐演变成悲凉得“所有的河与人、人与狗、那些不幸与万幸的,侥幸而迷惘的,都陷入了沉默……”的。悲剧意识逐渐取代童年的幸福感,成为“我”成长的烙印。虽然《呼兰河传》以氛围营造和故事叙事为主,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然而萧红却以王大姑娘和团圆媳妇的悲剧命运,揭示出社会黑暗对底层女性的侵害,为读者营造出一幅无奈、痛苦、悲哀及沉重的小城画卷。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而强烈地呈现,能够将萧红的情感悲剧、家庭悲剧及社会悲剧以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视角体现出来,使人物成为小说主题的呈现载体,也成为个人体验得以抒发的平台。鲁迅曾说过,萧红在文学上的才华,得益于她的“陌生化”视角,能够以人物的情感、阅历、年龄及思想为契机,呈现出“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事物。这种“陌生化”手法,能够为读者接触单纯性或混沌性的真相提供帮助,可以让读者以全新的视角,探索那些被隐藏、被遮挡的情感细节和生活细节,以及萧红所特有的女性悲剧意识。而在《呼兰河传》的叙述浅层,则以作者的视角批判呼兰城的封建与麻木,通过时叙时议的方式,将呼兰河居民的麻木、蒙昧及落后的思想呈现得一览无余。但作者本人却将叙事视野置于国家、民族、文化及社会的视角上,以鲁迅式的口吻,对旧中国、旧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以此表达出作者对底层女性悲剧性结局的无奈与感伤。尤其在萧红散文化的叙事结构和诗化的笔触下,这种情感和意识能够得到更充分地彰显和呈现。
三、《呼兰河传》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呼兰河传》中,团圆媳妇的出场总是处于“受虐”或“痛苦”的状态,她本是活泼的姑娘,然而婚姻却让她变得麻木。萧红在情节编织和角色刻画中,阐述了女人之所以要“成家”,是迫于“传宗接代”思想和“三从四德”理念下的无奈。团圆媳妇才12岁便被迫嫁给了现任的丈夫,过早地肩负起“家庭”的重任,她本想寻找自己的爱情,但跳大神的那句“大仙家说吧”,却彻底地将她推进了无穷无尽的噩梦中。在她刚出嫁的第二天,婆婆便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将她毒打了整整1个月,最后在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下她病倒了。而婆家的人又太过迷信,凡事都要问“大仙”,用滚烫的开水帮她祛病,就这样,团圆媳妇被烫了3次,昏了3次,皮开肉绽的不成人形,还没到嫁到团圆家2个月,笑呵呵的媳妇就死了。在这里萧红将“婚姻是女人的噩梦”,“婚姻是扼杀少女的笼子”等抽象思想阐释得淋漓尽致。用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揭示出封建社会对底层女性的压迫与剥削,使萧红独有的女性悲剧意识得以彰显和呈现。这种女性悲剧意识是以婚姻为媒介得以抒发与彰显的,能够传达出萧红对婚姻的恐惧与憎恶,揭示出女性的渺小与脆弱,传达出“在婚姻中女性永远都是处于被动的,永远都是男人的附属品,以及‘同性相残’的可悲现实”。封建的思想和落后的家庭观念让类似“团圆媳妇”的女人遭受巨大的人生磨难,并将她们的痛苦经历,以“封建”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使其在无尽的轮回中得以“永生”。
而在叙述王大姑娘时,萧红则用间接描写、场面烘托、象征暗喻的手法,将王大姑娘的“勤劳朴实”“多子多福”“秀外慧中”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团圆媳妇不同,王大姑娘极富反抗精神和开放思想,能够冲破封建的束缚,嫁给冯歪嘴子,这严重违背了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致使邻居们将王大姑娘描绘成不知廉耻、有悖纲常的贱姑娘和恶媳妇。虽然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巴生活贫苦,但能够相互帮扶、相互体贴、相互照顾,有幸福和快乐的婚姻。然而在封建舆论的影响下,王大姑娘还是死了,死于难产。也许那些善良乡民的“白眼”和“舌头”,并没有直接地杀死“王大姑娘”,然而他们的“话”却深深地折磨着她的灵魂与肉体,吞噬她的精神和思想,使她脱离了社会,成为封建社会的另类。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萧红并没有将恶人作为“恶事”的媒介,只是将善心的乡民当做了“刽子手”,使人性中的“恶意”更加鲜明,更加“清晰”起来,使呼兰城的“封建本质”直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因为这种剥削和压迫,使得王大姑娘饱受精神的折磨,难以寻得“生”的意义,最后沦为封建观念的“牺牲品”。通过深化萧红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嘲讽,深切地表达出萧红对底层女性的关切、无奈及惋惜,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而从《呼兰河传》的女性悲剧中,人们不仅能够看出萧红在情感和婚姻中所承担的痛苦和磨难,还能感受到她极为细腻敏感的情感,能够发掘她所潜藏的、无法鸣咏的苦楚。而正是这点,才让《呼兰河传》的女性悲剧意识变得深远、变得深沉、变得富有批判价值。
《呼兰河传》不仅是小城的传记,同时也是萧红个人的传记,是社会动荡不安下,萧红对自身、对民族、对历史、对社会、对自然的审视。这种审视拥有较强的虚拟性、美学性及批判性,它有萧红对呼兰城的儿时幻想,有对婚姻生活的失望和绝望,有对封建制度的痛恨与批判,有对底层女性的怜悯与关爱。它承载了太多,揭示了太多,但它终究是呼兰河的自传、萧红的自传以及无数底层女性的自传。正因为《呼兰河传》的叙事重心是“城”与“人”,所以在女性悲剧意识抒发上,更加多样、多变和多元,更加富有时代特性和历史特征,能够将呼兰女性的倔强与执拗、封建制度的残忍与疯狂、萧红对婚姻的幻想与希望勾勒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虽然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是通过情节编织、事件描绘呈现的,但在主题刻画和呈现中,人们能够感受到气息鲜明的“悲凉感”和“绝望感”。而这种欲抑先扬式的开头,却在景观描写与自然刻画中,为悲剧性的结局奠定了基调,使女性悲剧意识成为自然。
四、结语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萧红以呼兰城女性为视角,探寻和抒发自身“生命体验”的佳作。在思想和主题上,呼兰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技法,将人的命运与旧社会的麻木及苍凉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更富时代、社会及历史色彩,进而使女性悲剧上升到民族、社会及国家的层面上,深化了小说主题,揭示出萧红对人、社会、自然及历史的个人体验及悲剧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