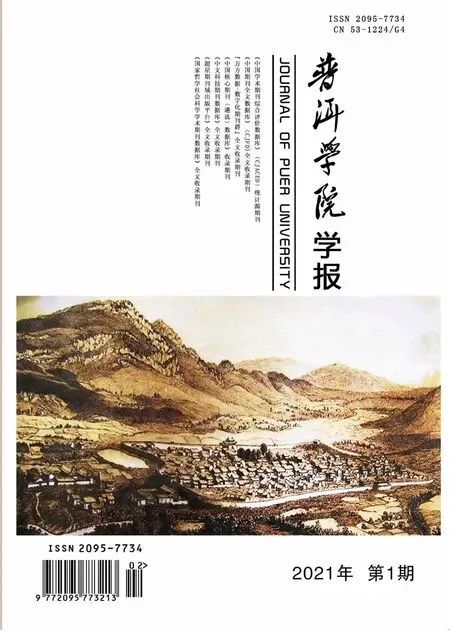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原型内涵对小说《母枪》的影响
2021-11-27旃小桐
旃小桐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650504
《牡帕密帕》作为拉祜族的创世史诗,2006年被纳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涉及到拉祜族的民间信仰、自然观念、婚育习俗、生产劳动、饮食习惯等拉祜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牡帕密帕》也被称为拉祜族的百科全书。《母枪》是拉祜族第一位女作家娜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新世纪以来拉祜族作家的创作。小说讲述了拉祜族先民在迁徙中的故事,其中穿插了拉祜族的创世神话、民间故事,歌颂了拉祜族的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
一、史诗《牡帕密帕》与小说《母枪》
(一)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的研究现状
从文献研究来看,目前对《牡帕密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承方面,以传承为圆心,辐射到传承人研究、传承方式研究、传承意识研究等,而涉及到《牡帕密帕》作为民间文学在非遗中的处境是比较少的。就文学角度而言,目前学者研究的也仅涉及到叙事结构等,忽视了民族创世史诗与当代民族作家创作的关系;忽视了作为创世史诗的《牡帕密帕》本身所包涵的原型意蕴以及它对当代拉祜族作家创作的影响;忽视了非遗文学是民族文化符号的表现,是民族心灵的呈现。《母枪》是拉祜族第一位女作家娜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新世纪以来的拉祜族作家的创作,其内容反映了拉祜族的迁徙历程、民俗习惯、民族品格。本文从文学角度切入,以《牡帕密帕》为支点,从民间原型内涵的角度出发,运用“神话——原型”的理论方法,分别从原型结构、原型主题、原型想象三方面,对娜朵的长篇小说《母枪》进行分析。
(二)小说《母枪》及作者娜朵
娜朵是拉祜族第一位女作家,1964年出生于云南澜沧,从小便有创作的梦想,后来求学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期间接受系统的文学创作教育,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疯兰》《绿梦》;纪实文学《绿满拉祜山》《边地民族花》;报告文学《民族热土》等。《母枪》是娜朵发表于2003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拉祜族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几个家庭为切入点,描写了拉祜族的迁徙历程。
二、《牡帕密帕》的原型内涵对小说《母枪》的影响
《牡帕密帕》是拉祜族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硕果,于时间而言具有历时纵向的延续性,从空间上来看具有横向传播过程的延续性。小说《母枪》的创作反映拉祜族社会、历史、文化和风俗。通过对小说的细读,不难发现,一个在城市中浮沉的拉祜族人对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吸集,其背后的的内涵是真正的文化自信,立足于民族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
(一)原型结构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原型结构中,有“两兄弟”和“两姐妹”模式,展现男性友谊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的是手足相亲相爱或者手足相残。其中展现男性兄弟之情破裂的原因是为了钱财、名利、权势。表现女性之间的情谊的则多是姐妹间为情反目。在结构上还有一个宽广、一个狭隘;一个无私、一个自私;一个低调,一个炫耀。一个是有情有义,道德美好的象征,一个是趋利避义,贪恋声名的丑陋的象征。
使用结构上二元对立的方式表现人物的特点,在《牡帕密帕》中,造天造地的两位助手,一个比较勤奋,时刻不敢停歇,一个爱偷懒,消极怠工,最终造成了天地的不协调,天小了,地大了。这样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小说《母枪》中也保留了下来。小说中的扎多和扎儿,同为一个部落里面的兄弟,两人都为猎人。一方面是扎多不仅倾囊相授狩猎技术,而且还处处保护扎儿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在猎杀老虎之后事事低调,不炫耀不显摆,把老虎皮放在家中让妻子娜米好好保管。
实际上,老虎并不是扎儿所杀,但是扎多并没有拆穿扎儿的“谎言”,反而帮扎儿在部落中宣传,树立了扎儿打虎的形象。在老头人将头人位置传给扎多的时候,扎儿表现的极其不服气,以至于后来在外人小山的挑唆下离开了拉祜部落,自己另立山头。在结构上往往出现二元对立的特点,扎多所代表的道德化人格和扎儿所代表的功利化人格。二元对立的原型结构,在史诗《牡帕密帕》和小说《母枪》中表现为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具体情节。
(二)原型主题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主题原型是指在民间故事、传说中反复出现的、较为稳定的核心思想,与作为情节单元的“母题”有所区别[1]。主题原型有报恩主题、忠义主题、善恶相报主题、忠于爱情主题、长生不老主题、生死轮回主题,具有浓烈的伦理道德色彩的特点。《牡帕密帕》所记载厄莎是掌管一切事物的神,不仅造天造地、造人造物,而且最主要的功能是守护着拉祜族。所以厄莎是拉祜族“具有无穷智慧和力量的守护神。拉祜族视厄莎为天神和衣食父母”[2]。孙浩然《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认为:拉祜族主要信仰神灵“厄莎”,是“厄莎”创造了人类。“厄莎”种下了葫芦籽后,细心照料,待果实成熟,由小米雀和老鼠共同啄开葫芦,诞生了一男一女,男为“扎笛”,女为“娜笛”;二人成年之后,结为夫妇,衍生了拉祜族群。所以,拉祜族的最早祖先即为“扎笛”与“娜笛”,拉祜族又称为“从葫芦里走出来的民族”[3]
《牡帕密帕》中所表现出的主题原型以“善恶奖惩”居多,首先是厄莎寻找葫芦。厄莎撒下一颗葫芦籽,造人的过程中,在葫芦籽长大结果快要成熟的时候,“树上果子掉下来,打在麂子鼻子上,麂子受惊便乱跑,吓得野牛踩断葫芦藤”[4]。葫芦藤倒了以后,葫芦就滚到了各个地方,厄莎四处找寻,去芭蕉林寻找,芭蕉回答没看到,厄莎就责罚芭蕉“等到人出世,让那串串果儿把你压弯腰”[4]。厄莎去到泡竹林,竹子也回答没看见,厄莎责罚竹子“等到人出世,砍下茅草盖房子”[4]。厄莎去到金竹林,金竹子也回答没看到,厄莎责罚“等到人出世,砍下金竹做响篾”[4]。厄莎去到松树林,松树回答看到了,但并没有出手去帮厄莎留住葫芦,厄莎赠予松树红缎子,并奖赏松树“等到人出世,把你砍来做明子”[4]。厄莎去到靛园,蓝靛表示没有看到葫芦的去向,厄莎表现出很生气,给蓝靛的惩罚是“等到人出世,用你把布染”[4]。厄莎去到蒿树林,蒿树看到了葫芦的去向,厄莎很高兴,准许蒿树可以开花结果,还可以用来做甑子。后来厄莎接连去了茨竹林、黄栗林,他们都没有看到葫芦的去向,厄莎也给予了惩罚,用茨竹编箩筐,用黄栗树做锄头、斧子的把。可见,在《牡帕密帕》中的善恶奖惩观是十分显著的。
这样的主题原型,在当代女作家娜朵的《母枪》中也得到很好的继承,并有了新的取向和扩展。拉祜族是一个狩猎的民族,拉祜族男性都以猎取更多动物为荣。要是能猎虎在族群中的地位会得到迅速提升,不仅让家族沾光,还能因此向心仪的姑娘表明心意。拉祜族女性在择偶的时候也会把男性获得的动物头骨数量作为重要参考条件。小说中扎儿是在猎到一种麂子之后才去娜哩家提亲,扎俄也是如此,在猎杀自己人生中第一只猎物之后,心上人方才同自己住进新建的小屋。奖赏的模式,和《牡帕密帕》中厄莎的原则一样,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三)原型想象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王光东在《民间原型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1976年至2009年文学与民间文化关系研究》中,将与神话有关的民间故事传说中的想象原型概括为:1.“万物有灵论”的宇宙观念,相信万物有生命和思想情感,常常把自然物神化或者人格化,人兽易形、人兽通婚等等;2.在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人、神、鬼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人可以变为神、人可以变成鬼。鬼、神也可以有人的情感和思想[1]。这样就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提供了两个空间,现实世界和神灵的世界可以相互转化,可以改变想象的空间,为创作想象力的产生增加一种可能性。让“日常的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之外的虚拟空间,共存于一个世界中[1]。
民间文学之所以历经千年还得以延续流传,历久弥新,想象力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信仰又是想象力的来源之一。苏童认为“我理解的民间想象的最大特点是跳出现实,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它们有实用主义的目的。强烈的情感色彩是这种想象力的靠山,首先它是以一种情感安慰另一种情感,目的在于排遣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适感。所谓的民间生活不需要思考,却极其需要发泄”[5]。所以,作为想象的来源之一,信仰给想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关于民间想象的当下意义,王光东是这样认为的,“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经验日益趋同的时候,挖掘和发现这种民族思维深处的想象力,有可能带来当前文学中新的审美因素,抗拒物化交往过程中人们想象力的贫乏,复苏生命中的潜能和力量。”因此,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于原型想象的运用,一方面这是作者的“无意识”活动所致——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拉祜族,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民族文化已经融入了作者的骨骼;另一方面体现在小说的丰富性上,原型想象极大的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三、民族史诗与民族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荣格在研究人类共同心理时提出原型理论,原型理论是构成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是“人类远古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6]。各民族的优秀史诗,是人类童年时期最早和最重要的作品,它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跨越时间和空间相遇,沟通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创作。民族史诗以描写人类起源或者民族形成过程中包括迁徙、灾难等主题严肃的事件,赞扬民族形成过程中为氏族、部落、民族的集体利益而做出牺牲的英雄,歌颂祖先与自然做斗争不屈不折的精神。民族史诗可以反映出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可以反哺民族文学发展。
(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要做到文化自信,得先做到自我相信,对于自己民族、对于自己文化的信任。在研究中不难发现民族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有强烈的认同感,沉思于民族文化历史,才能走进文学创作,进而实现民族文化自觉和价值认同。正如社会学家林耀华在其著作《金翼》结尾处的言说“把种子埋在土里”也适用于此处,这代表着一种向内、向深处的延展。因此,坚持文化自信,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的民族文化内涵,可以转化为小说创作的动力,小说的创新发展又能促进文化自信的构建。
(三)为民族文学提供精神养分
朝戈金在2018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说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的合法性和特殊性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相关联。应当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反观各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地位、文化功能和审美特质,从而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意义。”《母枪》的创作,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发现史诗中包含的元素,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有汲取,有吸收,有发展。娜朵作为土生土长的拉祜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是熟悉的和热爱的,她从学科交叉的视野出发,让史诗研究走得更远。
四、结语
在整体观的认识中,把民族史诗研究当作一种文化研究,正如托马斯·尼克曼所提到的交互反射理论: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人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他对于自身个性与个体的认同,是需要通过与他者进行交往并不断进行反思的。文化也是如此,每一种文化样态并不是一种处于封闭状态之中,它需要积极地在与他者文化的对话之中进行交互反射,以他者文化这面镜子得到自我形象的反馈,在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观照中,来对自身的文化意义进行确立,为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