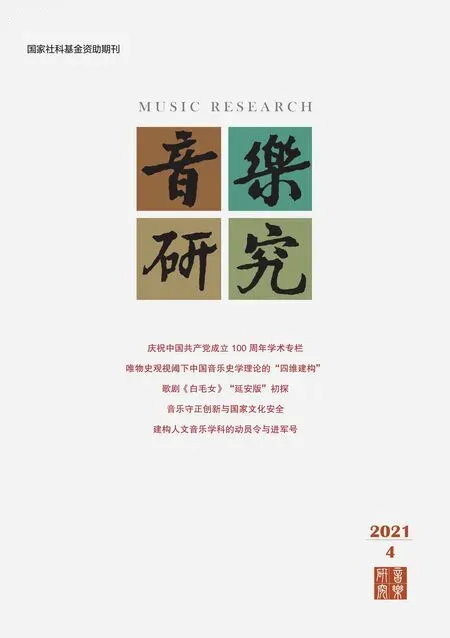歌剧《白毛女》“延安版”初探
2021-11-27李诗原
文◎李诗原
近年来,音乐理论界关于歌剧《白毛女》的研究,大多是就1962 年“中央实验歌剧院版”《白毛女》而言的,较少涉及其他更早期的版本。本文旨在对此做初步研究。
一、“延安版”与“上海黄河版”:歌剧《白毛女》早期版本寻踪
本文所论之歌剧《白毛女》“延安版”,指“鲁艺”歌剧《白毛女》创作班底1945年10 月赴张家口,并做出重大修改之前的版本。目前,关于“延安版”的存在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945 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年版(北京重印第1 版)歌剧《白毛女》;一说为1946年由陕甘宁新华书店出版,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歌剧《白毛女》。后者的“本书出版社说明”载:“1945 年5 月,《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并于同年发表剧本。1946 年,该剧由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正式出版。”此外,1945 年“鲁艺”刻印了一个油印本,①孟远《歌剧〈白毛女〉研究》附录1“歌剧《白毛女》的部分版本”,中国人民大学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4 页。其是否为1945 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白毛女》尚待核实。
歌剧《白毛女》1945 年延安新华书店初版、1946 年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版,笔者尚未得见原书,但发现了1947 年2 月黄河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的六幕歌剧《白毛女》(以下简称“上海黄河版”)。“上海黄河版”由郭沫若作序,并收有李楠发表于1946 年9 月26 日《新华日报》上的《白毛女——介绍一部解放军的歌剧》一文,全剧共六幕20 场93 曲。略有遗憾的是,这个版本没有“人物表”。
笔者认为,“上海黄河版”所依照的底本就是歌剧《白毛女》的“延安版”,理由有三。
第一,“上海黄河版”所载郭沫若“序”(1947 年2 月)说:“去年六月,陆定一北归之后,不久他便寄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吕梁英雄传》,一本就是《白毛女》。我如饿似渴地立刻把《白毛女》捧着读了一遍。故事实在感人。”②《白毛女》(六幕歌剧),黄河出版社1947 年版,第1 页。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北归”何处?无疑是延安,因为此后的陆定一,一直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工作,而未去华北和东北。这一事实说明:陆定一1946 年6 月(“去年六月”)后不久寄给郭沫若的歌剧《白毛女》,很有可能就是1945(或1946)年出版的“延安版”《白毛女》,而不可能是该剧班底到张家口改版演出后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版本(以下简称“张家口版”,1946 或1947 年版)。
第二,“上海黄河版”的署名情况(编剧:贺敬之、丁一、王斌,作曲:马可、张鲁、瞿维)符合贺敬之、张鲁、瞿维对“延安版”署名情况的描述:“在张家口正式出版之前,延安新华书店曾出版过未经作者集体审核的非正式本,作者署名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字样,具体人名也不准确。”③贺敬之《2000 年〈白毛女〉重版前言》,载《贺敬之文集》(五)“歌剧·歌词卷”,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页。该文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年版《白毛女》剧本“前言”。“上海黄河版”的署名,正好没有“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的字样,且“具体人名也不准确”。比如,编剧者中本不应有王滨(为延安首演导演组成员,只是指导了创作,并未直接参与创作);且将“王滨”讹写为“王斌”,将“丁毅”讹写为“丁一”。
第三,“上海黄河版”中没有体现“在张家口的修改”,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么,1945 年10 月该剧班底随鲁艺抵达张家口后对“延安版”做了哪些修改呢?关于“在张家口的修改”,可参见贺敬之1946 年3 月31 日在张家口东山坡所写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中的描述:
一、喜儿的性格在三幕以后加强一些;二、增强了农民在旧社会里的反抗性,添了王大春、大锁反抗狗腿子逼租出走,后来王参加八路军回来的一节;三、加一段赵大叔说红军故事,描出在旧社会里埋藏在农民心中的希望;四、根据观众意见第六幕(最后一幕)第一场话剧味道太重,重写,第二场也改写。④《白毛女》,晋察冀新华书店1946 年版,第7 页。
“上海黄河版”中没有赵大叔说红军故事和王大春出走、参加八路军后又回杨各庄的情节。这表明“上海黄河版”的底本不是“张家口版”,也非此后的其他版本(此后诸版都有“赵大叔说红军故事”和大春参军的情节)。
综上可以判断,“上海黄河版”的底本即“延安版”。2012 年6 月,“上海黄河版”作为“三联经典文库”(2010 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种,已由三联书店照搬出版(以下简称“北京三联版”)。因此,尽管尚未找到1945 年(或1946 年)延安出版的歌剧《白毛女》脚本和音乐,但关于“延安版”的分析就可依据以“上海黄河版”为底本的“北京三联版”。
二、“延安版”的音乐形态与艺术特征
“延安版”《白毛女》的音乐十分完整。全剧六幕20 场共93 曲,93 曲分配在不同的幕、场、景。作为一部1945 年在延安产生的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是成功的,不仅呈现出歌剧音乐的一般特征,还显露出为戏剧服务的艺术特点,因此体现出了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歌剧音乐创作原则。“延安版”《白毛女》也因有完整的音乐结构,一开始就有别于抗日战争后期的秧歌剧,也不同于20 世纪30 年代既有的“话剧加唱”形式。尽管它不及当时“正歌剧”的音乐规模和音乐表现,但其音乐还是该剧后来成为“经典”的基础。
具体而言,“延安版”《白毛女》的音乐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具有较为齐全的歌剧音乐元素。其中有声乐,也有器乐的序曲、伴奏、间奏和一般场景性配乐。开始的序曲(第1曲)尽管只有8 小节,实为第2 曲(《北风吹》)的前奏,但多少也有一点序曲的功能。伴奏是简陋的,其具体配器风格只能想象(因为“延安版”只留下单旋律谱)。置于第一幕第2 场开始处的开场曲(第17 曲),无疑有间奏的功能。场景性配乐则有第3、6、8、14、16、40、41、55 曲,其中一些还是人物上下场的配乐,具有人物形象塑造功能。该剧的声乐有独唱、对唱、合唱等不同形式,分别满足不同的艺术表现需要,其中合唱都出现在第六幕具有群众的场景中。
第二,具有塑造不同人物形象、性格的音乐主题设计。该剧尽管尚未充分凸显利用短小主题动机贯穿发展,以体现音乐材料统一性,预示不同人物或事件的歌剧音乐创作意识,但却用不同性格的音乐主题或主题性唱段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
第三,音乐材料较为集中,音乐风格较为统一。全曲的音乐素材可分为民歌和戏曲两大类。其中,民歌有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太平调》,山西民歌《捡麦根》《胡桃树开花》等;戏曲音乐素材有秦腔、山西梆子和河北梆子。此外还有民间器乐(第17 曲来自陕北唢呐曲《拜堂》)和佛曲(第41 曲来自佛教寺庙用曲《朝天子》)。全剧的音乐素材都来自山西、河北、陕北,由于三省属于大致相同的文化色彩区,因而全剧音乐素材较为集中,音乐风格也较统一。不仅如此,同一人物的唱段也多使用大致相同的音调,体现出一曲多用的主题材料发展手法(如杨白劳的唱段都来自《十里风雪》)。这种一曲多用的手法,无疑也是该剧音乐材料集中、音乐风格统一的重要前提。
从艺术特征看,该剧尚有两个涉及音乐形态的重要因素。
第一,关于河北民歌《小白菜》及其悲剧性因素。如前述,喜儿前两幕的音乐主题或主题性唱段,音乐素材都来自《小白菜》,成功塑造出喜儿的艺术形象和文化形象,且构建了喜儿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文化身份。毋庸置疑,这是该剧音乐创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可圈可点的手笔。当年的曲作者为什么选用河北民歌《小白菜》?这不仅仅是因为“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生在河北,或因为喜儿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选用《小白菜》这首诉说悲情的河北民歌,还在于喜儿这个人物的“身世”。这在该剧脚本中能够找到答案。在第一幕第1 场中,喜儿出场后的一段道白中就有“打三岁上就死了娘”的身世交代,《小白菜》中的那颗“小白菜”正是一个“没了娘”的小女孩。由此可见,选用《小白菜》作为喜儿主题或主题性唱段的音乐素材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小白菜》在该剧一开始就出现了,但并非直接引用,而是将其骨干音隐藏在《北风吹》(第2 曲)之中,并将其节拍(多为、交错节拍或拍)改为三拍子(),使之略带一丝春节的喜庆。在笔者看来,将民歌《小白菜》这个悲情音调隐藏在一个略带喜庆气氛的音调中,实乃神来之笔,似乎是“福兮祸所伏”的隐喻,预示着悲剧即将到来。果不其然,随着穆仁智前来讨租要债,喜庆的气氛很快化为灰烬,且发生了因还不起租金债务的一系列悲剧。很显然,这种将《小白菜》置于《北风吹》中的做法,更强调了歌剧的悲剧色彩。直到第二幕第3 场,喜儿怀孕7 个月且受尽欺辱、自叹命运多舛时才出现了《小白菜》的原型(第47 曲)。至此,基于《小白菜》的悲剧色彩才彻底释放出来。众所周知,《小白菜》作为一首“怨曲”,其6 段歌词讲述了一个失去亲娘后又受到后娘虐待的小女孩的悲惨命运,展现出封建时代后娘嫌弃继女、男尊女卑思想观念所带来的人间悲剧,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悲剧文化符号。在歌剧《白毛女》中,作曲家们正是用《小白菜》作为喜儿这个悲剧人物形象和性格的表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悲剧性。还不难发现,第三幕第2 场,喜儿怀孕后对黄世仁尚抱有幻想(第58 曲《自那以后七个月》中的“只有指望他,低头过日月”),张二婶则告诉喜儿“人家要的不是你”(第59 曲《叫声红喜傻孩子》)。张二婶这个唱段所用的音乐素材则是河北民歌《后娘打孩子》。这里对《后娘打孩子》的选用就进一步昭示出选用《小白菜》这首民歌的原因,使《小白菜》的悲剧性更进一步显现出来,并使歌剧的悲剧气氛得以增强。总之,《小白菜》是埋藏在歌剧《白毛女》中一个重要的悲剧性因素。
第二,关于戏曲音调特点、板腔体结构雏形与民族歌剧特征。无可否认的是,“延安版”《白毛女》具有较强的戏曲特点,不仅诉诸中国传统戏剧美学观念,还直接诉诸其戏曲音乐特点——不仅在于梆子腔的音调特点,还在于其中那些具有板腔体特点的唱段。正因为如此,“延安版”《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借鉴戏曲且以板腔体结构唱段为主要唱段的歌剧)的起点。在“延安版”《白毛女》中,戏曲音乐是作为一种戏剧性因素来运用的。这意味着,借助戏曲音乐潜在的戏剧张力满足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是运用戏曲音调和板腔体结构的契机。这种戏曲音调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幕第3 场的第36 曲(“杨白劳喝卤水”的配乐)中。这是一个二声部器乐段,其中上声部都运用秦腔音乐,与下声部作为杨白劳主题的《捡麦根》形成对位。接着第4 场的第37、38、39 曲,以及第44 曲“喜儿哭爹”的音乐,是秦腔“滚板”与《小白菜》的结合。其后第三幕第4 场中的第60、61、62、63 曲(《我要活》)则运用了河北梆子音乐。在后三幕(第四、五、六幕)的喜儿独唱唱段中,其河北梆子、山西梆子音调特点更显而易见。总之,其唱段中不失秦腔、山西梆子和河北梆子的音调特点。再看“延安版”中具有板腔体特点的唱段(例如,第26、35、44、54、60、63、66、67、71、72、73 曲),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板腔体特点,只不过大部分唱段尚无明显的板式变化,而只有速度、节拍的变化,可视为板腔体结构唱段的雏形。这意味着,大部分唱段并非由一定结构规模的结构段落所组成,而是由不同速度、节拍的短小片段组成。其中,板腔体特点较明显的有第67 曲《千重冤万重仇》、第73 曲《我是叫人糟蹋的喜儿》。前者有“慢板——快板——慢板”的板式变化:开始慢板是“千重冤万重仇,一件一件记心头,黄世仁哪黄世仁”一段;快板在“活活逼死我的爹……二婶把我救出黄家”;再接下去的慢板是“山洞受冷又受饿”至唱段结尾。后者也有“慢板——散板——快板——散板”的板式变化。尤其是前者(第67 曲),若将其与后面的第68 曲连在一起,其板腔体唱段的结构特点就更为明显。的确,在“延安版”《白毛女》中,一些不同速度的唱段往往被对白隔开,多少具有“话剧加唱”的特点,以致其中没有结构较长大的板腔体结构唱段。这也是许多早期民族歌剧中没有结构较为长大的板腔体唱段的原因。也正因为上述戏曲音调特点和板腔体结构雏形的客观存在,“延安版”《白毛女》具有了民族歌剧的体裁特征。
三、“延安版”的美中不足及内在冲突
毋庸置疑,“延安版”《白毛女》已是一部结构完整且不乏内在戏剧逻辑的歌剧,既有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又有充分的激烈矛盾冲突。尤其是就其可接受性而言,已相当成功和颇具艺术魅力,不仅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还饱含优良“基因”,作为一部向中共“七大”献礼的剧目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肯定。但作为革命文化中的第一部大型剧目,也有美中不足。
第一,此剧是以民间“白毛仙姑”传说为“本事”的,在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上保持着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和农民意识。该剧不仅选择了民间音调,也选择了民间戏曲,并依托戏曲而选择了中国古代戏剧的造剧模式、叙事方式,体现出寓于戏曲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由于该剧是一部农村斗争题材戏,所塑造的人物也主要是农民,故该剧的创作和审美一直被浓重的农民意识所统摄、笼罩。尽管“延安版”不乏破除迷信的意图,并将这一意图清晰地传递给了观众,但剧中人物(除第六幕中出现的区长、农会主任等干部及少数觉悟者之外)大多是宿命论者。他们信奉鬼神,并对其利害表示敬畏;笃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认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正因为如此,剧中塑造的农民(“杨白劳们”,也包括疾恶如仇的喜儿和大春)普遍缺乏反抗精神,更缺乏革命的自觉意识。他们任其命运主宰,甚至将命运的改变寄希望于“因果报应”和“神仙显灵”。更应看到的是,这种宿命观和迷信思想在剧中并未充分得以批判。
第二,“延安版”的革命叙事本身是不足的,尚未能充分表现和揭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二元对立,进而充分体现最早周扬等人作为“阶级斗争戏”的调子,因为地主还不够“恶”且未完全显露出其反动本质,农民太“善”而丧失其斗争精神。正因为如此,“延安版”为这部戏后来的不断改版和提高“预留”出了空间。当然,“延安版”中也不无批判农民阶级自身软弱、笃信宿命、信奉神灵的文化策略,并能被知识分子观众意识到。但对于当时大多数解放区的官兵和民众而言,这种批判意识和文化策略是不能参破的。试想,假如《白毛女》的受众均为知识分子,并将其思想主题从阶级斗争换成批判农民阶级的软弱,那就会像鲁迅《伤逝》等短篇小说对知识分子自身软弱的批判一样,显得更有批判的力度,因为那样更能反衬出封建制度的黑暗,更能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残酷性和隐蔽性,故其思想性或许要深刻得多,这个剧的艺术价值也许会更大。认识到剥削的隐蔽性,无疑比认识剥削本身更重要,如果真的将重心放在揭示剥削的隐蔽性上,或许后来就不会有“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本来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这类“现代经济法”角度的观点。⑤远江《故事新解》,《读书》1993 年第7 期,第102——104 页。显然,这种假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当时而言,这部剧必须面对陕甘宁解放区乃至整个解放区的广大军民,而不可能是少数知识分子,因此,其思想主题的表达也绝不可以采用这样一种“隐喻”方式和“晦涩”的戏剧语言。正因如此,后来的改版也只能是不断强调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二元对立。
上述这些都说明,“延安版”《白毛女》尚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本,一部成熟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目。一方面,该剧的民间文化色彩、传统文化心理和观念及狭隘的农民意识,因不完全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取向,降低了其革命性;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民间文化色彩、传统文化心理和观念及狭隘的农民意识及其相关叙事,满足了当时解放区军民(乃至国统区民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故而又成就了这部歌剧,使之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而具有大众性。这种“农民意识”像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其大众性而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接受和传播,又消解了其革命性而有悖于革命文化的特点和要求。
透过上述美中不足,也不难发现“延安版”《白毛女》的内在冲突。
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GC-MS)方法对样品的净化处理要求低,前处理方法更简单、快速,在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应用较多,应用GC-MS对环境污染物的监测分析依然是主流[9]。UV254检测可以反映出含有不饱和芳香环、碳碳共轭双键结构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有机污染物吸收紫外吸光强度会随着有机污染物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大而增大[10]。
第一,革命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内在冲突。作为一部产生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并充分吸取秧歌剧经验创作的“新歌剧”,“延安版”《白毛女》并不乏革命叙事,但这个革命叙事却是嫁接在民间“白毛仙姑”的传说之上。正是民间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内在冲突,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制约和冲淡了“延安版”的革命叙事,以致像过去革命文艺评论常说的那样:缺乏一条完整的“革命红线”。尽管有如张庚所认为:“它不是民间旧传说,而是抗战时期,在群众翻了身的解放区的传说”,“虽然也和一切其他民间传说一样,是浪漫的,富于想象的,而它的结局却是现实的,不仅是现实,而且也是光明的,这个光明,不是神仙,不是皇帝,又不是青天大老爷的恩赐,而是群众自己斗争所得的结果”,而不像“旧的传说,虽然所反映的也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生活现实,但是由于社会基本上是不公平的,所以结局总是没有出路,只好托为神仙鬼怪,年深月久,终于不免流于迷信”⑥贺敬之《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1946),载注③,第220 页。;但是,这个民间传说最终还是给歌剧《白毛女》涂抹上了一层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进而制约和冲淡其革命叙事。
应该承认,歌剧《白毛女》所依赖的“白毛仙姑”传说,来自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最终被证实为一个现实斗争故事,已是一个革命叙事。因为在剧中,这个“神仙”最终被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向剧中所有人(包括黄世仁和穆仁智)昭示:原来他们所敬畏的“白毛仙姑”并非神灵,而是那个肉体和精神都饱受摧残,且羞于见人、不得不上山隐居的喜儿,并从此将“鬼”(白毛仙姑)还原成了“人”。至此,对于剧中人而言,“白毛仙姑”传说中所有的“神秘”都被“揭”开了。就这个意义而言,“延安版”《白毛女》就已是一个革命叙事,因为它没有使这个“白毛仙姑”传说最终“流于迷信”。但也应看到,传说中的主角毕竟是“白毛仙姑”,其关键词也是“神仙显灵”,故在据此改编的歌剧《白毛女》中,几乎人人都信奉鬼神,认为“白毛仙姑”真的存在,在他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剧中人几乎都相信“白毛仙姑”能“显灵”,并认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中央军败退”、黄世仁“不减租”及“八路军来了”、黄世仁“被吓病了”,乃至人的贫贱富贵,都是她“显灵”的结果,他们还信奉“人鬼相通”“阴阳转世”等。总之,“延安版”《白毛女》的剧中人几乎都处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并共同营造了一种以信奉神灵为主体的民间传奇文化氛围。正是因为“白毛仙姑”传说中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使得1944 年“白毛仙姑”传说传到延安后,曾有将其编成一出“破除迷信”的戏的提议。然而,它毕竟不是一出“破除迷信”的戏,或者说相对于“阶级斗争”而言,“破除迷信”不是首要的。也因为如此,当时这种“破除迷信”的批判意识并不强烈。除干部外,剧中人似乎都不是觉悟者,并未充分意识到信奉“白毛仙姑”和“神仙显灵”的愚昧。剧中人虽然最终都知道所谓的“白毛仙姑”就是那个受苦受难的喜儿,但对自身笃信“神仙显灵”的愚昧并未根本反思。
从“延安版”的叙事结构看,全剧充分利用了“白毛仙姑”传说,可以说完全依赖了这个民间传说,不过是采取了一种“倒叙”的方式,将“神仙显灵”(喜儿在奶奶庙前装鬼吓唬黄世仁和穆仁智)作为关键性“桥段”,而成为全剧吸引人的一个亮点。此外,全剧叙事结合其思想主题,成为一个“人鬼互换”的结构。如果说此剧前半部分(前三幕)表现“人变(逼)成了鬼”,那么后半部分(后三幕)则旨在表现“鬼变成了人”。可见,“延安版”全剧似乎都在于帮助剧中人解开“白毛仙姑”的神秘面纱,而不是一个完整(前有铺垫、中有过程、后有结果)的革命叙事,只是一个依托“旧社会把人变(逼)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的思想主题,以及基于“人鬼互换”并有“阴阳转世”思想的传奇式叙事。整个“延安版”的革命叙事都放在第六幕,聚焦于其第3 场“斗地主·枪毙黄世仁”,甚至在第六幕第1 场还有围绕要不要“减租”的争论。此前五幕不见革命叙事的只言片语,只是在第五幕结束处提及“八路军”。
由于“延安版”过于遵循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传奇中那些有悖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剧中人所觉悟,也没有被观众所充分觉悟,最终使其革命叙事被“神仙显灵”“因果报应”“人鬼互换”的民间叙事所抵消。由于该剧过于忠实原民间传奇的叙事结构,故占用了革命叙事的空间,使整个“延安版”没有一个整体、有机的革命语境。这也是“张家口版”为什么要加上“赵大叔说红军故事”并让王大春出走、参加八路军等情节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而言之,“延安版”倚重民间传奇,与作为经典革命历史题材的“新歌剧”还有一段距离,这为后来的不断修改和提高“预留”了空间。
第二,揭示阶级矛盾与农民阶级自身软弱的内在矛盾。既然周扬等人从“白毛仙姑”故事中解读出的思想主题是“阶级斗争”,并将歌剧《白毛女》定位为“阶级斗争戏”,那么强调阶级斗争就自然而然。“延安版”的斗争精神尚不强烈,而这个不足正来自农民阶级的自身软弱。对于《白毛女》这出“阶级斗争戏”而言,如何强调其斗争精神,或揭示阶级矛盾?这需要加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而要加强其反抗精神,就必须加强其投身革命的自觉意识。
第三,显然,“延安版”《白毛女》的反抗精神是不足的。首先,剧中人笃信宿命,认为受苦受难都是命中注定故无须反抗。杨白劳认命,默认了那个“驴打滚”的不合理债务,并十分不情愿地按下了卖女儿的手印,最终在万般无奈和悔恨中选择了喝卤水自杀。喜儿认命,既然已被爹爹卖了,就只好到地主家做仆人,饱受凌辱后,躲进山洞,靠吃野果和寺庙里的“供献”为生而羞于下山。大春也认命,眼巴巴看着穆仁智抢走喜儿,面对其背后的强权和手中的武器,也只能挥挥拳,将愤怒诉诸一个在歌剧中都难以表现的面部表情(“眼睛发红,急欲追去,恨得牙齿发抖”)和几句没有台词的骂声。在他们看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无须奋斗,地主与佃户之间与生俱来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更是命中注定。⑦如第六幕中陈老汉对区长说:“谁不想少上交两颗,多吃上两口,不过自古以来贫富自有天定,你看白毛仙姑可灵应了,要不是黄家命里该富,白毛仙姑也不能让他,人家气数没尽嘛,咱们斗争有什么用!”总之,正是这种宿命观带来了农民阶级的自身软弱。其次,剧中人笃信“因果报应”,相信恶有恶报,无须主动去反抗。他们认为,一切善恶只能在“因果报应”中各食其果,在“惩恶扬善”中轮转,而无须“除霸安良”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日本鬼来占了县城”“中央军撤退”“八路从南山上下来了”,以及黄世仁被枪毙、自己当家作主人了,这一切都不是斗争的结果,而是一种“上天有眼”或“神仙显灵”的“因果报应”。这种对“因果报应”的笃信,也是农民阶级缺乏反抗精神而显得软弱的重要原因。
在“延安版”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难以构成作为阶级矛盾的二元对立。地主阶级是邪恶和凶残的,不仅表现在剥削和压迫,还表现在口蜜腹剑的“伪善”之中;农民阶级是软弱和无力的,甚至在敢怒不敢言的“愤怒”中还保留着善良。然而,正是这种地主阶级的“恶”与农民阶级的“善”,为此剧埋下了悲剧种子,成为其悲剧性的内在因素。
农民阶级的革命自觉意识和反抗意识的缺失,虽然使该剧作为革命文艺的斗争精神显得先天不足,但也使该剧具有作为悲剧的基本条件和潜在特征。笔者认为,斗争性与悲剧性有时是此消彼长的。就悲剧美学而言,作为二元对立的双方,己方斗争性越强,异己力量对己方的压迫就相对减弱,悲剧性也就相对减弱;己方斗争性越弱,异己力量对己方的压迫就相对增强,其悲剧性就得以增强。在“延安版”《白毛女》中,农民阶级的软弱削弱了该剧的斗争性,故增强了其悲剧性。这种软弱与喜儿“离母”“丧父”“失身”的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延安版”的悲剧性,使该剧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苦戏”和“怨曲”。当然,这种悲剧及其悲剧性也是《白毛女》受到解放区广大军民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剧首演后,陕甘宁广大军民要求“枪毙黄世仁”和中共中央也认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当枪毙”⑧1945 年4 月22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观看《白毛女》首演后的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向剧组传达了他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三点意见:第一,《白毛女》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参见张庚《回忆〈讲话〉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载戴淑娟编《文艺启示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2 页;张庚《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创作演出》,《新文化史料》1995 年第2 期,第6——7 页。,这是对剧中农民阶级软弱、缺乏斗争精神的一种“补益”,也成为悲剧中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的一种“最终解决”。
基于农民意识和农民阶级的美中不足和内在冲突,正是“延安版”《白毛女》的特点,是其作为悲剧的先决条件和优势,但也是斗争性不足并因此而不断改版的内在原因。
四、“延安版”的传播概况和香港首演
“延安版”《白毛女》的传播主要是纸质媒体的传播,其传播的范围也主要是“国统区”。该剧于1945 年4 月底在延安首演时的基本班底(“鲁艺”文艺工作者),随1945 年8 月底从延安迁往华北、东北的文艺大军,于同年10 月抵达河北张家口,并在那里对“延安版”进行了改版,进而确立了后来在各解放区广泛传播的“张家口版”《白毛女》。1946 年6 月,陆定一将“延安版”《白毛女》(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寄给了在“国统区”工作的郭沫若,由此,“张家口版”《白毛女》改成之后,“延安版”《白毛女》仍在南方传播。
从现有文献看,“延安版”《白毛女》最先是由郭沫若作序于1947 年2 月在上海黄河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不仅照搬了1946 年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的版本(六幕20 场93 曲版),还保留了延安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时所用的手写体乐谱。
郭沫若的序言(1947 年2 月22 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一切为了人民”的观念,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二是力图破除迷信,对“白毛”提出了质疑,即希望受众知道“白毛仙姑”并非真的存在,应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它,“不应该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非科学性或神秘性的阴影存在”⑨郭沫若“《白毛女》序”,载《白毛女》(六幕歌剧),黄河出版社1947 年版。。这也许是郭沫若强力推荐该剧出版的原因。
相比郭沫若的序言,该版本收录的李楠《白毛女——介绍一部解放军的歌剧》一文,似乎更接近周扬等人抓住歌剧《白毛女》一剧的旨意,并强调指出,该剧写的是“受难人民的苦遇和复仇”“劳动人民的大团圆;恶霸灭亡,好人重逢”,“这些描写人民从黑暗到团圆的作品,绝不是一般所谓‘光明的尾巴’可比,而是劳动人民生活中的真实”,“解放区有了《白毛女》这样的作品,表明了那里的中国人民已经在翻身,在大团圆了。”⑩同注②,第7 页。这里不难发现,当时上海黄河出版社在“国统区”出版歌剧《白毛女》的目的。
1947 年6 月,“上海黄河版”被苏中韬奋书店照搬出版,封面和版式基本相同,并保留郭沫若的序言、李楠的介绍文章,只是将原版的手写体乐谱改成了印刷体乐谱。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版本是由《江海导报》印刷厂印刷,而《江海导报》创办于1946 年9 月,隶属新华社苏中分社。由此可见,苏中韬奋书店出版的歌剧《白毛女》在苏中解放区得到了一定范围的传播。当时苏中是否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是否是按照这个“延安版”排演的,目前尚未查得相关资料予以证实。
1948 年5 月,六幕歌剧《白毛女》作为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3 辑之一种,由香港海洋书局出版。这个版本也来自“上海黄河版”,仍保留手写体乐谱、郭沫若的序言、李楠的介绍文章。正是这本由香港海洋书局出版的歌剧《白毛女》,使“延安版”《白毛女》在香港得到了排演。1948 年夏,李露玲在香港《华商报》资料室获得了歌剧《白毛女》的剧本,觉得剧本很好并希望能在香港上演。她将这个想法告诉王逸,并与王逸一起找到洪遒,由洪遒请示夏衍。夏衍同意并支持《白毛女》在香港演出,还建议由建国剧艺社与中原剧艺社、中华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演出。⑪李露玲《回忆歌剧〈白毛女〉在香港的一次演出》,《人民音乐》1981 年第5 期,第29 页。之后,1948 年5 月29 日至6 月19 日,在香港九龙弥敦道普庆大戏院,由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新音乐社联合演出了歌剧《白毛女》。
笔者认为,此次香港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应是“延安版”《白毛女》。据当时香港建国剧艺社社员巴鸿回忆:李露玲所发现的这个剧本,正是“《北方文丛》中刊登的解放区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全剧剧本”⑫巴鸿《忆1948 年〈白毛女〉在香港的演出》,《世纪》1999 年第6 期,第61 页。。尚存疑的是,海洋书局出版《白毛女》的时间是1948 年5 月,《白毛女》在香港首演的时间则是5 月29 日,时间上略显仓促。但是,即使李露玲所见到的不是香港海洋书局出版的《白毛女》,但只要是《北方文丛》中的《白毛女》则必定是“延安版”《白毛女》。笔者认为,尽管“延安版”《白毛女》在延安以外其他地区的演出情况,目前尚无更多的文字可以佐证,但1948 年在香港的演出,无疑显得弥足珍贵和具有历史意义。
此次歌剧《白毛女》在香港的演出,共演出4 场(从演出海报看)⑬时间为5 月29 日和6 月5、12、19 日;也有研究认为持续到7 月3 日,共演6 场。参见孟远《歌剧〈白毛女〉研究》,第115 页。,演出阵容十分强大。
演员主要由建国剧艺社担任;演出和舞台工作由中原剧艺社担任;音乐(包括指挥、配曲、乐队、合唱队)由新音乐社和中华音乐学院担任。很快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创作集体。
导演团:王逸(执行)、李凌、倪路;音乐指导:李凌;指挥:郭杰、严良堃;配曲:严良堃、胡均;演出委员会主任:庞岳;舞台监督:李门。
演员:喜儿——李露玲,杨白劳——方荧,穆仁智——蒋锐,黄世仁——兰谷,王大春——斯蒙,黄母——廖瑞群,区长——庞岳,大锁——李鸣,李嫂——王辛,陈老爹——陈新生。⑭同注⑫。
这个演出阵容可以说集聚了当时香港大部分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该剧获得香港“华民政务司”的演出许可证,送审时强调了“白毛仙姑”的情节,并将它说成是一出“神怪剧”。⑮同注⑪,第30 页。演出的宣传词中还有这样的提法:“剧情恐怖紧张,故事曲折离奇,包睇(看)到你哭,包睇到你笑”,“欲知白毛仙姑是人是鬼?欲知穷人怎样报仇?怎样翻身?就请你快来看《白毛女》。”⑯同注⑫,第62 页。其实这些也是徒劳的,因为一直对歌剧《白毛女》报以极大热情的郭沫若,在5 月23 日就在《华商报》撰写了《悲剧的解放》一文,对这部歌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进行了精当的阐释。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两千多年,随着这《白毛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到它最后的闭幕,“鬼变成了人”了。五更鼓响鸡在鸣,转瞬之间我们便可以听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齐声大合唱:报了千年的仇,伸了千年的冤,今天咱们翻了身,今天怎么见青天!⑰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编《纪念歌剧〈白毛女〉上演六十六周年暨庆祝歌剧〈白毛女〉复排上演学术研讨会文集》,作家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5——296 页。
显然,这部剧的思想主题是鲜明的,也不可能“瞒过”当时的香港“华民政务司”和国民党特务,因此最终也招致一些麻烦(剧场骚扰、报纸诟病)⑱同注⑪,第30——31 页。。但是,尽管如此,演出仍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产生了巨大反响。演出不仅吸引了当时香港的名流和政要,而且得到了香港《华商报》《南华早报》《德臣西报》《中国文摘》《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大公报》《正报》《星期报》《香港学生》《新生晚报》《华侨晚报》《伶星》等众多媒体的关注,可谓20 世纪中国一场重大的舞台演出事件。
结 语
在歌剧《白毛女》之前,中国就开始了歌剧民族化或民族歌剧的探索,出现了依托戏曲改良的歌剧,如歌剧《岳飞》(1936年山东省立剧院创作演出)和《苏武》(1943年山东省立剧院创作演出),但这些歌剧还较为接近戏曲,其歌剧的体裁特征和表现形式尚不明显。直到1945 年《白毛女》的诞生,中国才真正具有依托戏曲的民族歌剧。因此,“延安版”《白毛女》可谓中国民族歌剧的起点。
歌剧《白毛女》之所以深受解放区和新中国广大人民的青睐,不仅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直面农村、农民及土地问题,还在于它成功塑造出了一个类似古代悲剧人物形象的喜儿,并呈现出中国古代戏剧的表达方式。时至今日,“延安版”中的这种悲剧特征、传奇色彩及其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仍是该剧持续获得观众喜爱的魅力之源。作为一部不断改版而成为“红色经典”的中国民族歌剧,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