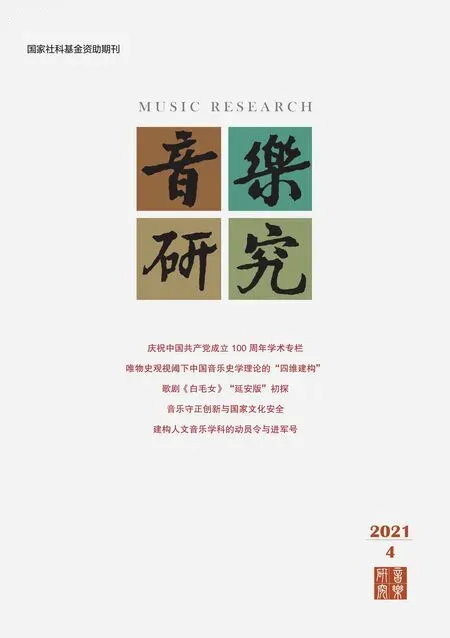建构人文音乐学科的动员令与进军号
——郭乃安先生《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再读有感之一
2021-11-27文◎秦序
文◎秦 序
音乐学前辈郭乃安先生(1920——2015),曾撰《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一文,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91 年第2 期。从1985 年创刊起,郭先生一直担任该刊主编,阅稿无数,此文系先生有感而发,针对性很强。先生强调:“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①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 年第2 期,第16 页。郭先生还列举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当下某些音乐学研究,见乐、见音乐形态、见律调谱器,也见物,但未能见人,未能深入关注人,难免片面、偏颇乃至失误。如单靠纯物理量的测试分析,不知必须与人相联系才能理解其本质,或忽略人耳听音的模糊性,以及听力范围局限等人的因素。又如,以指孔位置数据简单判断箫笛类管乐器的音律,不考虑具体演奏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忽视口风、岔口、半开口等技法指法影响,其结论当然“不怎么可靠”甚至“大错特错”。郭先生还指出,有些音乐学论著中常用一定篇幅叙述音乐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材料,但背景归背景、音乐归音乐,彼此挂不上钩,也看不出相互间的必然联系,正是“忽略了它们之间重要的中间环节,即人的积极作用”。
郭先生批评音乐学研究中的“就事论事”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聚焦透视于音乐的主体即人,忽略人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切中时弊。他登高而招发出的呼吁也极富启发性,引发广泛关注。发表迄今,已近三十年,学界仍不断有回馈反响遥相呼应。比如赵书锋不久前发表的《民族音乐学为何要研究人》,希望民族音乐学研究也要多多关注人、研究人;笔者两年前也“东施效颦”,模仿郭先生发出了《音乐学,请把目光也投向表演》②秦序《音乐学,请把目光也投向表演》,《中国音乐学》2019 年第2 期。的呼吁。
最近再次拜读先生大作,受益良多,引发许多思考。谈几点粗浅感想,与学界朋友们分享,并祈指正。
一、郭先生呼吁系向“音乐学”界朋友们发出
对郭先生“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呼吁,也有不同意见或不以为然者。有人认为无非老生常谈,不过是众人皆知的常识;也有人觉得普通听众或一般音乐爱好者,接触、欣赏音乐,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足矣。这些看法不无道理,我们先谈谈后一种看法。钱钟书先生幽默地反对别人去关注在大量作品和论著背后的他。钱先生说:“鸡蛋好吃就行,何必非要见到下蛋的鸡呢?”吴冠中先生大声疾呼,说中国当下“美盲”多于“文盲”!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辛苦劳作之余,愿意抽空聆听音乐或关注各类艺术作品,随性徜徉于艺术海洋,有所感受共鸣,已是音乐界、艺术界的幸事!若能喜欢或判断音乐之“蛋”新鲜与否、味道如何,或进一步关注作者及音乐本体等问题,对音乐家而言更是望外收获。这也是有关部门近来强调“加强学校审美教育”的重要缘由之一。
音乐属于时间艺术,诉诸听觉,自身无形无影又转瞬即逝。相比宗白华先生所说的“目所见的空间中表现”的建筑、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以及“同时在空间时间中表现的拟态艺术”,如戏曲、舞蹈等表演艺术,③参见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载《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8 页。当然音乐更为抽象、缥缈,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特性,④当然,音乐也不是“非物质”的存在,音乐同样离不开物质基础,离不开声波这种物质载体。也更难把握分析。一般人说自己“不懂音乐”“不是干这行的”,不足为怪。所以,周海宏等学者要反复解释“音乐何须懂”,请各界朋友放下心理负担,音乐欣赏的规律虽然独特,但音乐艺术本来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并不难体验感受!
不过请注意,郭先生“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呼吁,本向“音乐学”即音乐学家、音乐学人发出,专门投向研究音乐的同行们,并不针对普通大众和一般音乐爱好者。专门从事研究的音乐学家(或其他门类艺术的专门研究者)当然应有比一般听乐群众更高的要求。对某一具体作品,音乐学者不仅要“感其然”“体验其然”,还要“知其然”,以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既要相当深入地体验、了解,把握作品本体,探悉其创作过程,包括作曲家、演奏家创演该作品时的情感心态、思想精神及艺术创造的心路历程;还要了解艺术家个性、身世、经历、家庭、教育、艺术和风格追求等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不仅如此,还要能“知人论世”,即不仅分析了解“这一个”作品或作者,还要与其周围同人、朋友、社群、流派相联系,与同代文化艺术思想政治大背景相结合,掌握该艺术门类及体裁之由来和发展趋势,联系相关文化艺术传统的积淀(李泽厚语)等进行研究。
就体验观察和研究分析的方法而言,也有许多讲究,比如点面结合、多方面多层次甚至多学科有机综合;比如有针对性地结合运用音乐学的多学科(如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等)多方面,还可以拓展到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和经济学等邻近学科,广泛吸收、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以深化和拓展音乐学的研究。
李泽厚先生《走我自己的路》曾希望研究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多途径、多目标、多问题、多要求、多方法,互相互补,互相完善”,即走出单面思维、平面思维的局限,努力实现立体思维、多向度复合的全面综合的思维,这也是我们音乐研究的努力方向。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出发,结合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和风俗人情,深入分析研究艺术(美术),成就突出,影响很大。但后人仍有批评,说他虽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仍局限于“上层建筑”,“忽略了或是强调不够最基本的一面——经济生活”⑤〔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译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4 页。。而且,批评者也说丹纳的研究在目光投向人方面,尤其是关注具体的个人方面,也有不足。可见,艺术的研究存在非常广阔、深邃的空间,需要多方面、多学科、多层次展开,但也极不易达到完美。关键和核心之一,则需要把“目光投向人”,牢牢把握艺术主体、文化主体的“人”。
二、郭先生为何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
由此,不免想起音乐研究所的一段往事,与郭先生发出的呼吁或有某种联系。
20 世纪50 年代,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主任的古琴家查阜西先生(1895——1976),也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研究员。他主持整理、编辑《琴曲集成》和《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等重要琴乐文献,还与几位古琴音乐研究者一道,到全国各地实地采访、抢录大批极其珍贵的古琴音乐遗产。此外,还领导几位研究者广泛搜集资料编写了《历代琴人传》等诸多著述,为传统琴乐的继承发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对编写《历代琴人传》不理解,说我们应关注的事,是音乐,为什么去关注琴人呢?查先生的回答非常精辟,他说,“关注事当然应关注人呀,‘事在人为’嘛!”也就是说,没有人之为,哪来音乐的行为、事项和音乐艺术本身呢?
年轻人认为要关注事,不必关注人,也并非毫无道理。当时盛行读《居里夫人传》,里面有一段趣事: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元素镭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轰动世界。但居里夫妇极其低调,各国记者到处追踪,好不容易才在巴黎一个不知名的乡下,找到农妇打扮的居里夫人。不料这位女科学巨星不仅拒绝拍照、采访,反而谆谆告诫记者:“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⑥〔法〕艾芙·居里著,左明彻译《居里夫人传》,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219 页。
确实,科学上应该注意的是事,不必过多注意人。但在音乐艺术上和文学上,恐怕就大不一样。如前引郭先生文章所阐明,人在音乐艺术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作品的创作、表演,以及共同欣赏传播和共同再创造,都离不开人。
这个重要看法,当然不是郭先生首先提出,过去许许多多哲人和文学艺术大师,都曾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例如,席勒在18世纪末就明确提出“美育”概念,主张“审美游戏说”,主张艺术起源于“游戏”,并用“游戏冲动”指称“审美的创造形象的冲动”。他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它才完全是人。”席勒所说的“游戏”,即艺术。叶朗先生换用另一说法:“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审美;只有当人审美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叶先生还指出,柳宗元早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中,就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按,右军即王羲之,没有他(人)的关注,兰亭的清湍修竹,也不会成为审美对象,说明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美感是人的体验。“一个客体的价值正在于它以感性存在的特有呼唤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主体的审美体验”,所谓“主体”也就是人。⑦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404、405 页。有关席勒话语出自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叶先生采用的是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中的译文。而人这一主体的美感体验,是创造,也是沟通,是王阳明所说的“我的心灵”,是与“天地万物”的欣合欢畅、一气流通,也是王夫之所说的“吾心”与“大化”的“相值而相取”。⑧叶朗《美学原理》,第43 页。
尼采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是有意义的。”⑨〔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 年版,第105 页。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不在真理中,而在艺术中、在美之中。可见美感、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是人实现精神自由、实现人性完满的绝不可少的条件。没有人就没有文学艺术,也没有审美活动,人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与艺术的关系,对人对艺术都无比重要,所以,研究艺术、探讨审美,决不能忽略人,不能忽略人的相关思想与各种社会、文化艺术活动。
文学界早就高举“文学就是人学”的大旗。钱谷融先生说这句话含义极为深广,可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创作好,理论研究也好,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离开了这把钥匙,理论家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他还说,文学作为人类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如果撇开了“人”,何以安身立命?⑩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 月5 日。
因此,“文学是人学”早已深入人心,早已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常识。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据说是周作人在其著名文章《人的文学》中第一个提出“文学是人学”。笔者认为,艺术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学等,与文学一样,一刻离不开人这一主体,故毫无例外也都是“人学”,是人文之学。没有人,这些艺术和相关研究学科,也同样无法安身立命,故不能不关注人,既关注人的集体,也关注个人(个性及艺术风格各不相同的人)。
郭先生向音乐学界发出“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呼吁,是常识,也有“事在人为”的辩证前例。但今天回头看,笔者认为先生的呼吁不仅有重要的具体针对性,还有更深远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因为,“把目光投向人”,是郭先生向音乐学界发出校正现有航向偏差、回归人文学科广阔正道的呼吁;是建构包含科学音乐学在内的,更深、更广也更全面的人文学科音乐研究(或音乐学科研究)宏伟大厦的动员令和进军号!
兹事体大,也相当复杂,当专文深入论证,这里约略勾画几个要点。
三、科学的音乐学与人文学科的音乐之学
首先,要看到并承认音乐学、艺术学研究具有科学性,看到科学在这些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音乐学艺术学的基本立足点,是科学或科学的研究。可惜这一点不仅一般人不太了解,就连音乐学(及艺术学)领域众多师生,即所谓“局内人”,也不都十分清楚,予以高度重视。比如,归国应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著名画家陈丹青,几年后,却宣布辞去所有职务,并公开承认自己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美术学”。
为此,几年前笔者曾专门撰文探讨音乐学的学科性质,⑫秦序《音乐学学科性质再认识——读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劄记》,《中国音乐学》2015 年第2 期。并着力推介中央音乐学院俞人豪先生编著的《音乐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指出它是我国较早的且非常重要的音乐学基础教材。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指出,音乐学是“有关音乐的科学”,“音乐学”这个词在欧洲最早见于米茨勒1738 年在德国成立的团体名称“音乐学协会”(Socictact der musikalischen Wissenschaft),这个德文词的意思为“音乐的科学”。俞先生还说,确立这门学科的人应是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其1863 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不仅使用了“音乐学”这一名称,还明确指出,“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克里桑德还主张音乐学应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并且,“不应该逃避最严格的要求”。⑬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年版,第4 页。
要音乐学研究联系和学习的“实证科学”是什么呢?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1789——1857)首先提出“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各个部分都已进入实证状态,唯独人文科学仍游离于外,所以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实证科学体系,用自然科学来说明人类社会。英国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则是实证史学最重要的代表,将历史看作自然科学,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寻找历史规律。还说这个过程中,自然科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关键,强调“离开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也不成其为历史学了”⑭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孔德观点见第221、222 页,巴克尔观点见第224 页。。因此,一般所说的“音乐学”,应属近代科学体系中的艺术学分科之一。《概论》进一步说它应属“人文科学”或“精神学科”⑮“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系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其范围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参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0 页。范畴,还指出我国音乐学专业多设置于音乐、艺术院校,而在西方“音乐学系则普遍设置在综合大学的人文科学学院之内”⑯同注⑭,第11 页。。
但在拙文后面部分,对音乐学是科学的这一基本属性定位,已经有所修正和发展。强调音乐学与艺术学、历史学等学科一样,具有突出的人文特性及人文评判价值,显然不同于科学。所以,音乐学、艺术学等不全是科学,也不全是“人文科学”,应是人文学科。这是受何兆武先生《历史与历史学》等论著启发,而得到的一点新认知。
何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实证主义史学过分强调科学至上的观点,是片面的,它忽略了人文学科和科学(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何先生还指出,多年来存在“一切都要以科学性为唯一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唯一的归宿”,是一种“唯科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学理所当然应该是科学,完全地而又彻底,有如柏里(剑桥大学教授)声称“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一样。但何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不同于一般科学,因为“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无法进行可控的实验来证实它或者证伪它”⑰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载《历史与历史学》,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5 页。。
何先生还以历史学为例,多方面深入论证科学与人文学科两者的差异和不同。比如,历史学研究的是人文史而非自然史,人文史之所以成其为人文史,则端靠其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文思想。比如,“没有人的思想,也就没有人文史。都是人的思想赋给了历史以活的生命。假如没有理想、热望、感情、德行、思索乃至贪婪、野心、狂妄、愚昧和恶意等,也就无谓人的历史了。这一点是人文研究有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地方。”又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思想的生命;而其所研究的客体则是没有思想的乃至没有生命的自然界。而在人文研究中,研究的主体是人,研究的客体也是人,是人在研究他自己。所以它那研究的路数和方法就自然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再如,“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没有思想、感情和意志的,所以研究者对它的态度是价值中立的、超然物外的……历史归根到底乃是人的有意识的、有意志的(而非单纯自然的)产物。”
所以,历史的研究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或者说,它具有科学与非科学、自由与必然的两重性。⑱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2 页。所以,历史学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没有科学性,就没有学术纪律可言,历史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但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学。⑲同注⑰,第3 页。
何先生指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是科学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学的;又因为它是非科学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的,这两方面的合成,才成其为历史学。何先生还说,历史学不仅是一种科学,同时还是一种人文学科,这一点好像连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还不曾意识到。所以,“凡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或应该成为科学的人,于此都可以说是未达一间,正如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所表现的那样。”⑳同注⑰,第3 页。
受此启发,可以认为音乐学、艺术学与历史学等学科一样:一方面是科学(近代意义的科学),必须发扬科学精神、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和规范,相关研究成果要符合科学标准;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全是科学(不是反科学),而是有别于科学的、独具人文特质的“人文学科”。所以,常用的“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等概念,仅仅强调其科学的属性,是不能充分涵盖和指代音乐学、艺术学及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基本特性的。
何先生还就历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发出了非常重要的、富于建设性的呼吁。他说:
历史学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统一体。我们对外在世界(客观存在)的认识需要科学,我们对内在世界(主观存在)的认识还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这里的“某些东西”,即我们对认识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实质上有似于艺术的敏感性。我们对外界的认识要凭观察,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要凭人生的体验,否则就做不到真正地理解。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为避免与科学一词相混淆,我们姑称之为学科而不称为科学)的根本分野之一。[21]同注⑰,第4——5 页。
何先生提出,为了避免人文“与科学一词相混淆”,避免将历史学等学科统称“人文科学”,应将历史学(科学)改称“历史学科”,以示区别,即不再称“科学”而改用“学科”这一新称谓。这一称谓的改正,意义深远。虽然历史学,人文各学科各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但也容易发生同样“与科学一词相混淆”的问题,而遮蔽了、淡化了自己的最重要的人文特性。因此,人文学科各学科各方面研究,理应清楚、自觉地了解学科人文本质及归属,认真建构人文逻辑基础,认真构建自己人文学科的相关“元理论”,才能真正地将目光投向人,凸显自己学科人文特性和人文价值的依归,全面实现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目标。
四、20 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突出人文学科的价值与意义
明确人文学科、突出人文价值,也是20 世纪以来世界文化、思想发展的新潮流。工业文明占统治地位之后,随着科学技术高速进步,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旧貌,极大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犹如双刃剑:既造福世界,也能造成危害。人类的实际历史进程表明,科技腾飞的20 世纪并没有实现人性的真正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普遍异化、动乱不已。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理性,本是为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但人征服自然的结果,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破坏,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而在被技术理性完全统治的世界中,不但人与自然相异化,人与人也相异化;人还普遍物化,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相互冲突,甚至相互厮杀。[22]衣俊卿主编《文化哲学十五讲》“第九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84 页。
正如韦伯等学者所批评,在科学主义、理性至上思潮,尤其“技术理性”[23]韦伯提出“技术理性”概念,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背景下的一种新理性主义思潮,其立根于科学技术的无限潜力和无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西方现代理性文化危机,其根源离不开技术理性的异化。参见注[22],第180 页。统治的现代,科学、理性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先哲们预计的那样,不断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技术本身反而成为自律的、自我发展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成为扼杀人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成为一种比传统政治统治力量更强大的力量。同时出现了英国学者C.P.诺斯所说的“两种文化”,即“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与“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24]〔英〕C. 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3——4 页。,彼此渐行渐远,甚至发生日益尖锐的对立。所以,哲学家马尔库塞[2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誉为“新左派哲学家”。特别提醒人们,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背景的相对富裕的消费世界中,技术理性形成新的统治体制,让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存方式。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理应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却被技术理性所消解。人成为失去了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与现存认同的“单向度的人”或“单面人”,而“单向度的思维”或“单面思维”,则成了缺少否定维度的主导性的社会意识。[2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21——31 页;参见注[22],第184——186 页。
因此,鼓吹人文精神、人道精神和“人学”,反思科学主义、理性尤其是技术理性(也叫工具理性)的弊病,成为20 世纪以来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的重大核心问题。
旅美学者林毓生20 世纪80 年代回国,即强烈感到国内人文研究包括学科名称“呈现非常混乱的现象”。他在《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中批评很多人不清楚什么是“人文”,甚至把“人文学科”(humanities)叫作“人文科学”,“好像不加‘科学’两字就不觉得这种学问值得研究似的。”他强烈表示:“人文学科”绝对不能叫作“人文科学”,因为事实上“人文学科”与“科学”,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因为是“人”,所以有特别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是人,所以要肯定人的价值,找寻人的意义。[27]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载《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 页。该文原发表于台湾《联合月刊》第14 期,1982 年9 月。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文学、历史学,以及音乐研究、艺术研究的学科性质,也逐渐发生从“社会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变化,继又从“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分化出“人文科学”及“精神科学”等概念。更加突出人文特质的“人文学科”概念,正逐渐取代“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等称谓。比如,何兆武先生在早几年论著中,还常用“人文科学”概念,或与“人文学科”相混用,后来不仅明确改用“人文学科”一名,甚至提出上述以“历史学科”取代原有“历史学”的重大主张。
其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中就只有“人文学科”(humanities)条目,而没有“人文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词条。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外很早就加强和提升了对人文学科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的重视。[28]此《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根据美国1975 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编写的。
更早,20 世纪50 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唐君毅就连连著书,大声呼吁中西人文要返本开新,重建人文精神。他指出:“人是透过人文去看世界,从科学哲学去看世界的条理与秩序,从文学艺术去看世界之美,从道德去看世界之善,从宗教去看世界之无限的神圣庄严。但是,世界的迅猛进步,世界人文的巨大进化,反而出现巨大的混乱和矛盾。”这种矛盾,先是因西方近代人文中,科学一支特别发达,人们只依从已有的科学结论去看宇宙人生,以及科学技术运用得“不得其当”的影响。其次,是人们忘记了自己在人文世界;也就是说,科学之发达,竟致使人忘记了他们本来是在人文的世界,“而自以为处在一陌生世界、物质世界,而迷失了自己的道路”,不仅如此,还相反地“从事于人文之毁灭”[29]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 页。。
唐先生反复指出,科学只是人的学问中之一种,“它亦不能在人的学问世界中高居一至高的指导一切之地位,并由之以说明人的学问之全与其次序应当是什么,及人的学问与今日之人的存在问题之关系。”[30]唐君毅《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0 页。他还说,自己理想的世界是人文的世界,在这个理想之世界,其实科学亦自必需发达。我们反对的,只是以科学凌驾于一切人文之上。所以“要知道人文涵盖科学,科学不能凌驾人文。”[31]同注[29],第22 页。他希望提高科学以外的人文领域地位,并将人的生存置于科学态度、科学真理之上。因为科学之外的其他人文领域,“自具其真理、理想与价值。而人生存在自己,亦有超于科学之真理以上之理想与价值。”他还说,“我们固当讲人文世界的科学,但不必讲科学的人文主义”[32]同注[30],第63 页。,不是科学涵盖人文学科,而是人文学科应该涵盖科学,也就是说,不是科学文化高于、大于人文文化,而是因为人文学科本来就高于、大于科学,人文文化也应高于、大于科学文化(当然科学也需发达,也需重视)。[33]比唐君毅更早,与梁启超1918 年一起考察战后欧洲、后赴德国专攻哲学的张君劢,1923 年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指出西方文化,或称科学、物质文明,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解决世界乃至中国的问题。参见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 页。
人文学科努力摆脱“科学主义”、技术理性至上等束缚,走出“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等相对狭隘的定位,摆脱将人文艺术研究等同于纯科学研究的偏颇失误,已是20 世纪以来世界文化思想新的发展潮流和基本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反思,如何尽快实现我国现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入流”和“预流”(陈寅恪语),充分发扬人文学科独特品格和价值魅力,向绚丽灿烂的“人文学科”新天地迈进。开拓更为深广宏大的“人学”“人文研究”新疆域,应是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包括艺术研究、音乐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结 语
何兆武先生强调,一切人文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给定的事实和规律。他还说,展望现代思想文化前景,首先将是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统一性要求并且包括最大限度地发挥个性。其次,除了科学的进步,还必须努力保持人文学术的同步发展,没有人文学术的健全、发展,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一旦失控,不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很可能危害人类。[34]何兆武《历史两重性片论》,载《历史与历史学》,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3 页。唐君毅先生的理想的人文世界,与此相类似,也是强调人文和科学的共同携手共同进步的。
将郭乃安先生当年发出的呼吁,放到当今和未来音乐、艺术乃至世界人文学科发展的历史大潮流、大背景中重新审视,其深远内涵和意义,可以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受郭乃安、何兆武、唐君毅等先生启发,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艺术学、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本质属性,明确其“人学”品格。为厘清易与“科学”一词相混淆的“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等称谓,我们建议不妨改用“艺术学科”“音乐学科”(或略嫌烦琐啰唆的“人文学科艺术学”“人文学科音乐学”)这类新称谓,取代“艺术学”“音乐学”之类名称。这样的命名,可以同所谓科学的“艺术学”“音乐学”等相对狭隘的概念,能够泾渭分明,其人文学科的概念和定位,也更准确、更合理,其实也更科学。
为此,可以认为郭先生的呼吁,是校正现有音乐学、艺术学的航向偏差,回归人文学科研究广阔正道的动员令,也是建构包含科学的音乐学在内的人文学科音乐研究的进军号!我们要与时俱进,主动参与现代人文学科发展的澎湃新潮流,认真反思、明确音乐学的人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果断走出科学主义、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至上的束缚和困扰,坚持将目光投向人,坚持以人为本,高度肯定和凸显中国的人文音乐研究的民族个性与独特价值。
缘此,建构包括科学音乐学在内而具有真正人文特色的“中国的艺术学科”“中国的音乐学科”(或中国“人文学科艺术学”“人文学科音乐学”)的宏伟大厦,此其奠基之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