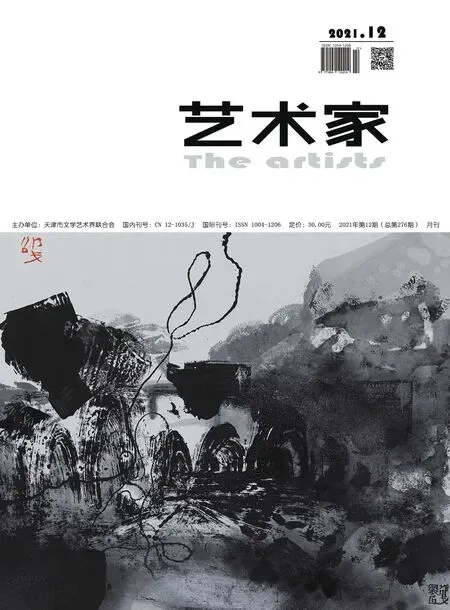门内与门外
——女性主义视域下《都督夫人董竹君》的人物形象分析
2021-11-27马露霏四川师范大学
□马露霏 四川师范大学
《都督夫人董竹君》一剧讲述了原本身处青楼的董竹君与都督夏之时之间的爱情故事。董竹君拒绝夏之时为其赎身的建议,反而选择逃出青楼与夏之时私奔,但是两人的爱情受到了封建家庭的阻拦,而董竹君最终选择离开夏之时,并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在剧中,董竹君同夏之时回到夏宅时,三次想要跨过夏宅的门槛都遭到夏母的刁难。夏母先让她易服,再束发,然后拿出小鞋让她穿。在舞台上,导演甚至设置了一道三叠平台构成的门。颇具象征意义的“门”不仅代表了封建家庭与新时代之间的隔阂,还象征着男权视域下女性自我认知的觉醒以及男性对性别公正的让步。
一、《都督夫人董竹君》中的女性形象
剧中共计出现了四名女性角色,分别是女主角董竹君、夏之时之母、夏国玲、柳彪所携的艳女。这四个女性角色总体上呈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阶段以及女性在以封建门第为界下内外的表现。
夏母作为封建规训的忠实维护者,坚守着门内的法则:“身为妇人,谨言慎行;三从四德,必守必遵”。当董竹君进门时,夏母要求她易服束发;面对失去丈夫的孙女夏国玲,夏母则要求她为亡夫守寡不可再婚。这种对妇人从外在的着装到内在的精神的禁锢,将女性捆绑在失语的他者地位上。
与夏母完全相对的则是看似身处门外,实则依旧深陷门中的“艳女”。艳女是在剧中跟随柳彪一起出场的歌女,也可能是柳彪的小妾之一。她没有名字,打扮妖艳,台词也不多。“艳女”从出场看到柳彪对董竹君的维护便酸溜溜地问柳彪是不是爱董竹君,柳彪说:“嘿,岂止是有点爱,简直是爱得很!爱得我害了几十年的单相思。只可惜,人家是云里飞的天鹅,我这个癞蛤蟆呀,只配得上你。哈哈哈……”柳彪在自嘲的同时,却也是在实打实地蔑视着艳女。“艳女”并非出身封建门阀家庭,思想上也并非被“三从四德”所束缚。她之所以为柳彪所蔑视,是因为她虽然身处门外,但是内心依旧对男性有着无法摆脱的“从属性”。这样的“艳女”虽然踏出了封建外在枷锁,突破了传统妇女所死守的妇容,但是在父权社会下男性的“天然威慑”下难以“出门”,因而思想被彻底拴在了门内。她迈出了封建的大门,却终究没有走出性别之门。
如果说夏母是完全的守门人,而艳女是“外在革命者”,那么董竹君从剧情一开始便在那扇象征着“性别之争”的大门处。她自幼沦落风尘,以卖唱为生,依靠自身魅力在男性中赢得追捧,在面对爱情时,毅然切断与以往生活的联系。为了能够在与夏之时的婚姻关系中获得平等而非从属地位,她没有接受夏之时赎出自己的提议,而是独自逃出青楼。由此可见,她的胆识并非寻常女子所有,并且她虽然身处青楼,却从未妄自菲薄。在她看来,卖唱女与总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决定选择爱情之后,她还能想到如果被夏之时赎出去,那么今后夏之时可能会说“董竹君,你是我花钱买来的!”董竹君逃离青楼的举动背后隐藏的内心想法是她渴望获得性别上的平等。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第二性在面对第一性时潜意识下的“献媚行为”。董竹君逃离青楼后,并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而此时的董竹君依旧处在他者地位。为实现创实业这一愿望,她请求丈夫认同的行为,就是在吸引丈夫的关注,因为希望得到他的赞同和帮助,也是“他者”的“他性”所在。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除了实现女性经济独立外,女性还要摆脱对爱情的过度依附。经济依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外在依附,而爱情依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内在化依附。对爱情的过度依附更容易让女性陷入内在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认识爱情,女性只有在自由平等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获取自由平等的爱情,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女性的内在性。在办厂后,董竹君自然实现了经济独立。然而,当她面对夏之时的爱情时,或者说是比爱情更为束缚人的婚姻关系,她选择对夏之时妥协,卖了厂房,独身前往上海寻夫。对于两性关系并不平等前提下所成就的婚姻关系,董竹君的妥协固然不可能扭转夏之时对女性的偏见,于是两人关系彻底破裂,董竹君进行了娜拉式的出走。这正是她所经历的“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娜拉出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提包里并没有钱。换言之,娜拉在剧中社会是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同样地,董竹君在彼时的社会也无法实现自立,固然她聪明,办厂的成功实例摆在眼前,但是工厂的启动资金却是夏之时提供的。当她当离开夏之时,落魄无路时,得到了李高的帮助,才能东山再起,同时柳彪也为她的饭店提供了保护。由此可见,董竹君的成功并没有脱离男性的支持。而董竹君在走投无路时也曾说“为什么世上男子千千万,支持我者无处寻?”由此可以看出,董竹君始终在寻求第一性的认可。
这样的董竹君一直游走在性别之门外,虽然具有了女性意识,但是依旧无法彻底摆脱父权话语下第一性对第二性的控制性影响。在剧中,她身为女性,要顾全丈夫,还要照顾孩子,并且不甘放弃自己的信念,同时又维护着妇道的尊严。一种角色,在多重限制下存在,即是剧中董竹君这一女性角色的“被限定的存在”。
如果说董竹君的成长是剧中的隐性存在,那么更为显性的便是夏国玲。夏国玲在剧中的身份是生长在封建家庭的寡妇,自幼接受传统礼教的管教,即便是丈夫死后回到娘家,也依旧被要求守寡,不能改嫁。二十岁的她便被要求余生都要在禁欲的强压下度过,而这样的事实无疑是残酷的。但是夏国玲始终身处门内,并没有办法接触太多的诱惑,因而在强压下也无法产生过多的心思。正如在剧中她说“在合江安心当寡妇,学烈女大门都不出。来成都才知守节苦,想李高想得我要哭”。这句话便很好地解释了她的心理,即接触“门外”世界后,对爱情的渴望使她从蒙昧的封建约束中逐渐抽离出来。她开始主动在意李高的动向,渴望与李高接触。然而,在得知李高并不会看上她这样的小脚女人后,她便大哭,哭着哭着却突然打住,以“算了,他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他哩”为由安慰自己。爱情的骤然离开使得她再次重回顺从的失语位置。得知夏之时要将自己嫁人,也并无表现。嫁给柳彪后生活并不顺遂,而她最终甚至被柳彪抛弃。
在剧中,与董竹君同为女性的夏国玲面对董竹君的作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赞赏,反而一直称她为“玉兰精”。从她对董竹君的态度,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嫉妒,而这个嫉妒究其原因,实则是她接触到门外世界,了解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后,却发现董竹君能为男性所接受,因而她从前所受到的妇德教育崩塌。她自己已经被打上了小脚的烙印,因而也并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新潮”的女人,于是面对无法顺应时势的悲哀,她对董竹君产生了嫉恨。最终,当她彻底失去了封建家庭的背景与管教后,选择“学”董竹君,“自己养活自己”,并且说“与其依靠男人,不如依靠盐茶鸡蛋!”这是她在明白了父权话语下第二性依附第一性失去经济独立的结局后,所选择的正确道路。
可以说,董竹君进不去的那道门,便是封建礼教之门。封建旧族死守禁欲的规训,将女性压制在礼教之下。门内的女子无法感知外面的世界,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排除异己,抵御外来者,并以此为责任度过一生。另外,剧中的门还是性别之门的象征,门的一边是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标志的世界;而另一边则代表着女性独立。董竹君为了爱情,为了家庭,不停地游走在性别之门处。而夏国玲则是逐步跨出大门,最终成就了一个能够说出“自己养活自己”的夏国玲。
二、父权中心下的男性形象
剧中总共出现了三个男性角色,分别是夏之时、李高、柳彪。作者以女性视角在对笔下男性角色进行描写时,并没有刻意丑化他们。他们三人代表了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三种态度。
夏之时、李高和柳彪三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情有义。自古流传的故事中有无数的才子同青楼女之事,然而结局多是“沉宝箱”“化鬼魂”,最圆满的结局也不过是青楼女最终成为妾。然而在剧中,夏之时不仅迎娶了董竹君,还将其立为正妻,也保证不会纳妾,而这个誓言直到剧终也未曾打破。李高辅佐身为总督的夏之时,在他势微之际也不曾离开,对青楼卖唱女出身的董竹君也从未看轻,并且对其心怀敬佩,在董竹君走投无路之际予以帮助。柳彪在剧中并非正面角色,但是他对董竹君表现得十分热情,并为董竹君提供了各种帮助。
无论夏之时对董竹君表现了多么忠诚的爱,都无法掩盖他依旧以费勒斯中心主义为人生准则的事实。他与董竹君有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儿,直到第五个孩子儿子的出生,他才停止让董竹君继续生育。他对夏国玲也曾说过“你二婶娘还是争气,总算给我生了个儿子”。而在与董竹君情感破裂后,他说道:“你要离婚,我四个女儿都不要。让她们四个都跟着你,看你如何养活她们!”这固然是在给董竹君的自立增加难度,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对他而言,女儿与儿子不同,是可以轻易舍弃的。
此外,他时时表现出第一性对第二性的控制。董竹君在日本上大学期间,他以“人家都说你长得漂亮,叫你‘西施’。许多男人看见你,眼珠子都不会转了”为由,禁止董竹君上大学。当后来董竹君办实业成功时,报纸舆论便大肆兴起,如夏国玲告诉夏之时那般,“说她好,便说二叔不能干,说二叔,垮杆都督只会玩。说她坏,便说二叔不顾脸,说二叔,不像阳刚七尺男。二婶娘每日里抛头露面,交游广有百姓也有达官。有了钱有了势她难服你管,有了势有了钱你管她也难。夫妻间失纲常必生祸乱,到那时再无有安乐家园”。于是,夏之时便开始禁止董竹君办实业,让她回归家庭。无论禁止董竹君上学还是禁止她创业,其实都是夏之时对自己的不自信。故而可以说,夏之时对董竹君的管制便来自他对于女性内在能力的恐惧。
而在结尾处,夏之时选择祈求董竹君的原谅,而这也是作者对男权社会下男性予以女性平等橄榄枝的美好期许。
剧中另一个角色——柳彪,始终以玩物来看待女性,不仅要求女性对自己要顺从,还要求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在已有五房姨太太的前提下,他依旧出入青楼等场所。而对于夏国玲,他虽然以正妻的身份娶了她,但是只将她看作“见董竹君”的工具。他在剧中说他所尊敬的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妈,另一个便是董竹君。可见对于他来说,女人始终只是玩物。因为董竹君的特别,他才另眼相看,不再将她同其他女人混为一谈。或者说,对于他而言,董竹君的优秀使他认可了她拥有进入男性中心的能力。
李高在剧中对任何一个女性都并未表现出轻视,甚至对董竹君的独立状态始终表示支持,并且予以帮助。但是细想之下可以发现,他同夏之时、柳彪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敬佩董竹君的同时其实也选择了忽视夏国玲,实则可以理解为,他同柳彪一样,只是认可了董竹君拥有进入男性社会的能力,从而忽视了她的性别。而对他来说,他并未对女性的整体产生更多的改观,就像他无视夏国玲对他的爱意一般。李高虽然帮助了董竹君,但在结尾处,他也向身为女性的董竹君求助。前文谈到,对于董竹君而言,她的目的是要在父权社会下取得男性的认可与支持,而从李高向董竹君求助看,若非他认可董竹君在男性社会中既得的地位,是不会向其寻求帮助的。
总的来说,作者以女性视角写实地描写了男权话语下的男性。无论这些男性的外表是儒雅还是轻狂,他们实则都依旧处于性别之门内。他们固然对个别女性予以尊重,但是轻视女性群体。他们的内心依旧坚信男性中心论。
诚然,无论是在门内生活的夏母还是夏国玲,实则依旧为了取悦男性,最终还是如菟丝花一般选择依附男性,抑或是同董竹君那样,即便是自身已然觉醒女性意识,但依旧心怀男性中心论,渴求在男性社会寻找立足之地。她们都是在社会的固态思维下所出生的女性,因而她们的思维模式便是社会的状态。在戏剧的结局处,女性处于男性中心所产生的恶意也通过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得到了消解。
在审视人类社会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模式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父权制话语依旧占据中心,但女性并未“败北”。在女性社会角色被预设之下,她们依旧可以活出自我。
门,代表着分隔,也表示着隔阂。而今封建之门似乎已经不在,但性别之门依旧存在,而门的存在必然给予现在以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