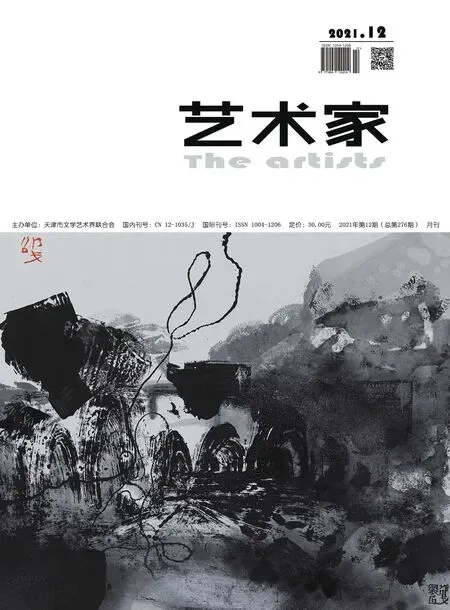以爱为名的伤害
——评大森立嗣电影《母亲》
2021-11-27南京传媒学院
□俞 阅 南京传媒学院
母爱是世界电影史的经典主题。在日本电影史上,有一系列反思母爱和剖析母亲形象的著名电影,比如今村昌平执导的《楢山节考》、山田洋次执导的《母亲》、成岛出执导的《第八日的蝉》、原田真人执导的《我的母亲手记》等。2021 年,大森立嗣执导的《母亲》,在第44 届日本电影学院奖和第63 届日本电影蓝丝带奖中荣获大奖。这部电影中放纵而堕落的母亲秋子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秋子的生命病态致使其无法成为传统的母亲,她与儿子周平的亲子关系也因此变得畸形而扭曲,以母爱为名的伤害直接导致了儿子的生命病态,致使其无法成长为拥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本文从母亲秋子的生命病态及其成因,秋子与儿子周平的内在关系这两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母亲秋子,反思了母爱的复杂性和精神伤害的隐蔽性。
一、母亲秋子的生命病态及其成因
精神分析学派奠基人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强调童年经历对人格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童年记忆有巨大力量,并与我们伴随相当长的时间”“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秋子的原生家庭及其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是导致其生命病态的根本原因,而成年后的几段情感经历是其生命病态的重要原因。秋子在成长过程中极度缺少爱,因为父母将更多的爱给予了比她“优秀”的妹妹三隅枫。电影开篇时,秋子带着儿子向父母和妹妹借钱时的对话,暗示了秋子在原生家庭里被遗忘的地位:秋子对母亲和妹妹说:“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你们从来没尊重过我。”又对母亲说:“我从小就被你当傻子对待,你只关心枫,我都没上过大学。”再对妹妹说:“他们单单在你身上就花了那么多钱。”而妹妹指责她说:“你从来都不认真学习,成绩也不好。”这些对话表明儿时的秋子缺少父母的认可与接纳、尊重与理解,这种爱的缺失的状态使其无法获得家庭归属感。此段借钱情节的镜头构图中,妹妹始终处于画面中央位置,暗示了妹妹在原生家庭里的核心地位。
秋子的原生家庭及其成长经历所引发的家庭归属感的缺失,导致她无法获得生命应有的存在感。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归属感产生存在感,归属感是存在感的载体。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伯特·纳伯格认为:“归属于一个人类群体,不论何种形式,都意味着一种相互的关系,归属意味着向投身的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做出一些承诺,从而为群体的运作甚至强大而贡献力量。作为交换,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对我们加入群体的认可,让我们产生一种基本归属感,进而滋生存在感。”因家庭归属感的缺失而导致存在感的缺失,显现为秋子的自尊和自信无法构建,其生命意义感无法实现,因而无法获得人生的希望、热情和力量。这也让秋子始终无法燃起养家的热情,沉溺在“小钢珠”赌博游戏中,以诱惑异性、出卖色相来维持生计,浑浑噩噩,好逸恶劳,更无力承担作为母亲的责任。
秋子成年后的几段情感经历,非但没有产生治愈和拯救的效用,反而一步步加剧了她因原生家庭所导致的生命病态。秋子对异性情感的态度存在矛盾性:一方面,她强烈依赖异性为其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其孱弱、自卑而放纵的人生极度需要寄生宿主;另一方面,她需要异性之爱作为其原生家庭所造成的爱的缺失的一种补偿和治愈。情感经历中多次出现秋子对性的渴求,这除了表现其以性换取经济来源之外,也暗示了她对爱的极度渴望。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E.弗兰克尔认为:“通常,性是爱的表达方式。”但成年后的这几段情感经历,都无法给予秋子足以治愈其心灵创伤的爱,反而带来了一层层伤害,加剧了她对生命的绝望和无力。第一段情感经历中,丈夫因厌弃秋子的懒惰嗜赌而放弃婚姻,丈夫没有足以拯救秋子的爱的能力。第二段情感经历中,为申请儿童抚养金以供挥霍,秋子诱惑市政办公室的公务员宇治田,而宇治田对秋子的感情中更多的是欲望而非爱的成分。第三段情感经历维系时间最长,也是秋子最渴望的一段感情,然而恋人川田辽的生命力如同秋子一样委顿。他以打零工、盗窃和借高利贷维持生计,无力承担家庭责任,也无力以爱救赎秋子。在秋子怀孕后,他为摆脱责任,殴打秋子,最后无情地抛弃了她。第四段情感经历中,宾馆经理赤川在占有秋子身体后,拒绝将空余房间给秋子母子居住,而仅提供简易帐篷,吝啬薄情之举可见其爱的稀薄。第五段情感经历中,工程公司老板松浦曾邀请秋子全家共进午餐,并宽恕他们的偷窃行为。但性事之后,松浦随即冷漠离去,如同交易,足见他对秋子并无真爱。
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拯救堕落的秋子。电影终篇时,社工高桥亚矢深情地将秋子的手放在自己脸颊上的动作,正暗示了这一点。但秋子始终无法获得足以拯救她的真正的爱,数次情感经历的悲惨结局使其对爱怀疑和绝望,同时原生家庭的伤害更是阻碍了自我救赎的能力,所以她无力挣脱毫无希望和未来的生命泥潭,而母亲和妹妹在其怀孕后的无情绝交又加速了其生命病态的恶化——最终秋子既无法获得家庭归属感,也无法获得社会归属感。她对社会充满排斥、疏离和抗拒心态,在救助站企图夺门而走时的极力挣扎就验证了这一点。她对原生家庭充满报复心理,因而发生了由她指使的弑父弑母血案。她的完整人格和独立自我亦无法建构,如同巨婴,处于自我迷失与人格残缺的状态。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卡伦·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为了不被分裂,必须做一些事情努力保持整合的状态,这就让他们变得更加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远离自己和别人。”
二、秋子与儿子周平的内在关系
上述所阐释的秋子的生命病态,是导致其与儿子周平内在关系逐渐变化的根本原因。这对母子间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控制与被控制的状态,儿子的话语权和自由意志基本被剥夺。秋子对儿子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方面,秋子为实现其病态生活而控制儿子,儿子成为她实现病态生活的手段和工具。比如,秋子与恋人川田辽合谋讹诈公务员宇治田十万日元以供挥霍时,就是以要求儿子谎称遭受宇治田侵犯为手段而达到目的的。在此事件中,儿子被母亲诱导而放弃诚信与纯真,公然说谎。秋子怀孕后向前夫、妹妹和母亲借钱以维系其病态的寄生生活,亦是以要求儿子向亲人说谎为手段,诱导儿子或谎称学校组织旅游而急需旅费,或谎称妈妈刚找到新工作而需要搬家费,从而骗取亲人钱财。儿子在工程公司打工后,秋子又要求儿子反复向老板松浦预支工资以供其赌博,在无法继续预支后,又要求儿子偷窃老板钱物以供其挥霍。在陷入绝境时,秋子竟指使儿子杀死外公外婆以获取钱财。秋子被捕后以其长期精神控制而产生的隐性控制力继续控制儿子,致使儿子对法官说谎,秋子因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由上述情节可见,秋子因为无力挣脱病态生活对自身的控制,所以无法终结对儿子的控制。因此,儿子的天性被扭曲,无法建构正确的道德观念。秋子的病态被强制成为儿子的常态,儿子成为秋子病态生活的牺牲品。秋子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爱,因而也缺乏为儿子付出爱的能力。爱的缺失使她无法成长为一个有爱的母亲。她固执地认为自己一直没抛弃儿子,这便是为儿子付出了最多的爱,但这样的不抛弃,其实只是控制和伤害的延续与泛滥。当秋子面对法官时,说她“给了他一个男孩子所能要求的所有爱”,可见秋子已将控制等同于爱,这是以爱为名的伤害。秋子既是生活的受害者,又是生活的施暴者。电影开篇时,秋子舔舐儿子膝部伤口的镜头,既有爱抚安慰,又有嗜血吸血的意味,暗示了秋子对儿子那以爱为名的伤害。当儿子试图抗拒这病态母爱的控制时,秋子则以抛弃他为威胁,儿子为留住母亲而不得不继续承受伤害。比如,当儿子拒绝向老板松浦再次预支工资以供秋子赌博时,秋子便说:“可能有一天,我就会消失了。”而儿子准备杀害外公外婆时,失魂落魄地行走于大桥上的长镜头,表面上呈现的是儿子的饥饿劳累,实际上呈现的是母爱对他造成的终极伤害。错误的母爱使他的尊严、自信和希望丧失殆尽,如同行尸走肉。
第二方面,因爱的缺失,秋子无法获得家庭归属感和社会归属感,其内心充满自卑、无力和绝望,对外部世界充满排斥、疏离和抗拒,无法有效建立安全感,所以她也担心并害怕儿子受到外部世界的侮辱、歧视和伤害,故而控制儿子迫使其远离外部世界,不让他上学,阻止他和外人交流,极力阻碍儿子与外部世界建立任何联系,将儿子囚禁在狭隘封闭的母子世界中。这种控制是秋子自身精神创伤后遗症的体现。秋子认为这是对儿子的爱,但这严重阻碍了儿子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归属感的构建,并阻碍儿子独立人格的形成。比如,社工高桥亚矢希望帮助周平融入社会,便问他:“你想去上学吗?有专为青少年开设的免费学校。”但秋子对高桥亚矢说:“没有我的允许,不要和他说话。”又对儿子说:“你在学校肯定会被人欺负。”高桥亚矢为周平送来大量书籍以供其阅读,而秋子暴怒地将书籍扔到门外。秋子无法挣脱对外部世界的畏惧,也阻挠了儿子人格的社会化。
渐渐地,儿子周平在高桥亚矢和学校师生的鼓励下,开始尝试挣脱这种错误母爱的控制。他渴望融入社会,建立自我,获得生命应有的自信、价值和希望,因而与以爱为名来控制他的秋子产生正面冲突。比如,当秋子和川田辽为躲避追债而准备逃亡异乡时,儿子勇敢说出自己不愿离开,而要留下来继续上学,可见儿子试图脱离秋子的控制,但秋子居然欺骗儿子说:“亚矢说她很讨厌你,她说你让人毛骨悚然……她还说你身上有臭味。”这番话将儿子刚刚建立的脆弱的自尊和自信破坏殆尽,同时也流露出秋子自身对外部世界的畏惧、怀疑和自卑。秋子对儿子的精神控制,致使儿子建立自我并融入社会的尝试最终失败。
秋子被捕后对法官说:“我想怎么养他都可以,我毕竟是他的妈妈,是我把他生下来的,他就是另一个我,你明白吗?我给了他一个男孩子所能要求的所有爱,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抚养我自己的孩子,这与你无关,不是吗?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亲生儿子。”这鲜明地表露出秋子无视儿子对独立人格和完整自我的渴望,以爱的名义将自己的生命病态强加给儿子。秋子的母爱只是病态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奠基人马斯洛提出了人的五个需求层次,最上层的需求就是“自我实现”。而秋子和儿子周平都无法获得“自我实现”。从未实现自我的秋子,也从未尊重儿子的自我;从未得到真正的爱的秋子,也从未让儿子得到真正的爱。
在童年阶段,周平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出于对母爱的强烈渴望,他一直以逆来顺受的方式取悦或迎合母亲,以换取母亲对他的接纳和不抛弃。但在其青少年时期,随着自我的觉醒,他逐渐感受到母爱对其自我与人格的束缚和扭曲,他尝试着突破,但无力挣脱。社工高桥亚矢的爱的付出,本足以给儿子带来精神力量去追寻自我,以挣脱母亲的控制,但高桥亚矢的爱最终也因母亲的欺骗而远去,让周平最终放弃对自我的追寻,不再质疑和抗拒这病态的母爱。他被捕后对高桥亚矢说:“自从我生下来,所有的事都不好,但爱我的妈妈也是一件坏事吗?”可见周平在成长过程中极度缺少爱,对爱的极度渴望以及对母亲的无力抗拒,导致他最终接受了母亲病态的爱,同时也以爱的名义自欺欺人地掩饰了这种爱对他的致命伤害。秋子因爱的缺失而无法成长为真正的母亲,儿子也因爱的缺失而无法成长为真正的男人。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所有好的关系都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秋子与儿子的病态亲子关系,使儿子的人格完善和自我成长都被中断,无法成为真实的自己,而沦为精神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