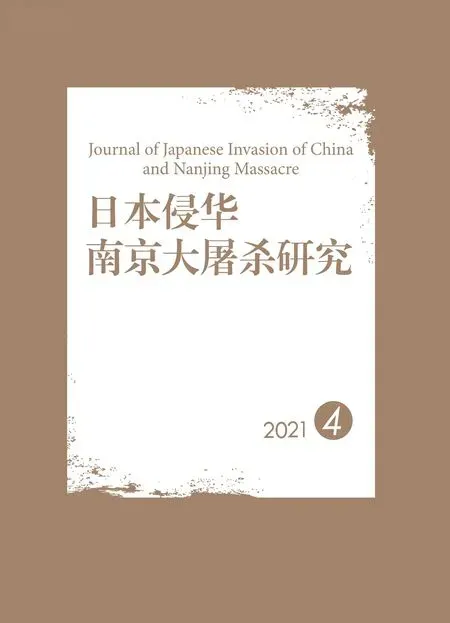国际主义抑或人道主义:一·二八事变中的上海扶轮社*
2021-11-27马建凯
马建凯
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是国际性民间社团,其成员多为各国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为世界商界及有专业之人之团体”。(1)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杨光编:《最后的名士:近代名人自传》,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68页。扶轮社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促进世界和平,实际上是一个兼具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性质的非政府国际组织。1905年,世界上第一个扶轮社成立于美国芝加哥,之后逐渐扩展至世界70多个国家。民国时期,扶轮社已遍布中国30多个城市。扶轮社极其注重社员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创立的目标之一是:“透过结合具有服务之理想之各种事业及专业人士,以世界性之联谊,增进国际间之了解、亲善与和平”。(2)国际扶轮社著,张运权译:《通向和平七条道路》,(台北)中华扶轮教育基金会,2009年,第2页。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国际扶轮社寄希望于各国社员以国际主义精神维系世界和平。一·二八事变爆发前,面对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国际扶轮社要求上海扶轮社的各国社员,“应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3)《邝富灼致国际扶轮社的信》,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
关于扶轮社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前人已梳理了基本史实,(4)江沛、耿科研:《民国时期天津租界外侨精英社团——扶轮社述论》,《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6期;管玉婷、陈蕴茜:《民国时期中国扶轮社发展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管玉婷:《近代中国的跨国社团——以中国扶轮社沪、宁分社为中心》,《近代中国》2010年;刘本森:《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民国研究》2013年第1期。或许是囿于当时有限的史料,未能深入探讨一·二八中日冲突期间扶轮社的应对问题。就研究视角而言,学界对国际人道组织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活动的研究,多侧重于人道救援,(5)如曹礼龙:《修行与慈善——上海的世界红卍字会研究(1927—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云波:《兵燹济难: 一二八抗战中世界红卍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丁泽丽、池子华:《“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民国研究》2015年第1期)、董根明:《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整建与救护工作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而对社会团体制止战争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在中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上海扶轮社采取了哪些维系和平的举措?各国社员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如何抉择?本文以中、日、美、英多方史料为基础,(6)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是本文参考较多的重要史料。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1883—1979),美国传教士,出生于中国苏州,后定居上海,他是国际扶轮社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扶轮社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上海扶轮社社长。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有大量涉及上海扶轮社,尤其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期上海扶轮社活动的记载,为探究上海扶轮社在中日两国冲突时的活动提供了核心史料。探讨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扶轮社的活动,尤其是该社在制止战争、维护国际和平方面的努力和成效等问题。
一、一·二八事变与上海扶轮社社员的态度
上海扶轮社成立于1919年,成员多是上海各界的上层人士,至1932年4月,社员共125人,来自约20个国家。(7)Seven Nationalities Among Rotary Club Officers, The Shanghai Times , April 2, 1932 :5;Shanghai Rota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 April 4, 1932 : 4.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上海扶轮社社长为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邝富灼,副社长为英国商人哈里斯(E.F.Harris)。一·二八事变前后,面对中日矛盾不断激化,上海扶轮社的中方、日方、第三方社员各有不同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社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行动。
邝富灼于1922年加入上海扶轮社,在任社长之前曾两次担任副社长。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邝富灼正在美国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国际会议,他亲身感受到海外华人华侨高涨的抗日热情,并为之震撼。(8)Manchuria Issue Stirs Chinese In U.S., The China Press, October 28, 1931:7.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邝富灼沦为难民,全家躲进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同时商务印书馆亦被日军炸毁,其事业也遭受沉重打击。
邝富灼十分认同扶轮社的宗旨,即使一·二八事变期间自身沦为难民,仍努力弥合中日社员之间的矛盾,以“维持上海扶轮社的国际形象”。他认为,中日冲突虽然使“扶轮社在上海受到严峻考验”,但也给上海扶轮社“提供了一个为和平服务的独特机会”。(9)Shanghai Rotary Club's Annual Meeting Dwells on Need of Friendship,The Shanghai Times,April 8, 1932:5.在他看来,由于国际联盟、《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及《九国公约》的存在,“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已经在维系和平方面取得了进步”。因此,对于中日冲突,他主张效仿甘地精神,依据国际公约进行和平、平等的谈判,用“温柔”的方式加以解决。(10)Rotary Xmas Though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 December 24, 1931: 14.同时,邝富灼也是一位爱国者,一·二八事变期间,他号召在沪的各国上层人士为上海难民捐助雨衣、衣服和毯子。(11)Local Aviator Tells of Experiences, The Shanghai Times , February 12, 1932 : 3.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虽未公开谴责日本,但含蓄地讽刺日本人“挥舞着他们的军刀”,正在推行所谓的“积极政策”。(12)Rotary Xmas Though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 December 24, 1931: 14.
陈立廷是上海扶轮社中国籍社员,但未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英语,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基督教青年会、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二八事变期间,他也因战事避难于基督教青年会。与邝富灼不同的是,陈立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鼓动民众进行抗日活动,主张对日强硬,积极备战,以战促和。早在九一八事变前,陈立廷即公开呼吁民众警惕日本对东北的野心,指出列强侵华者“尤以东邻之日本为最甚”,国人应当警惕日本“对于满洲之经营”。(13)陈立廷:《序言》,大岛与吉著,太平洋国际学会译:《满蒙铁路网》,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第1页。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帮助“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抗日救国十人团”等东北及上海的爱国团体,鼓动民众抵制日货并准备对日作战。(14)《东北民众请愿团抵沪》,《申报》1931年11月8日,第13版;《抗日十人团举行国难三周月纪念》,《申报》1931年12月20日,第18版。一·二八事变后,陈立廷深感民族危机,认为“我方愈表示怯弱,敌方愈益嚣”,“我国唯一对付方法,厥为武力抵抗,以促敌人之觉悟”。(15)曹云祥、陈立廷等:《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上海青年》第32卷第7期,1932年7月,第2-5页。陈立廷还前往广东,力劝广东方面与中央政府团结一致,准备对日作战。(1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版,第449页。他还在《大陆报》发表公开信,谴责部分日本上层人士公开支持日本侵华,无视中国主权。(17)An Open Letter to Dr.Nitobe, The China Press , March 12, 1932 :14.
虽然陈立廷主张以战促和,但面对中日冲突,他并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他表示,国人“一方面遭了日本的横暴,一方面感了国际联盟的懦怯”,不免认为国际组织是无用的,但不应因噎废食,而应“抱着大勇猛努力,不因一时的挫折而败志”。(18)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32年,“序言”。因此,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立廷一面主张对日强硬,以战促和,一面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并认为中方必须坚守底线。(19)曹云祥、陈立廷等:《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上海青年》第32卷第7期,1932年7月,第2-5页。
作为上海扶轮社的中方社员,邝富灼与陈立廷的心态有共同之处,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有爱国情怀,对通过扶轮社以和平方式化解中日冲突抱有一定的信心。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邝富灼更恪守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精神,不鼓动反日情绪,也未公开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而陈立廷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直接参与抗日活动,主张以战促和,并认为即使和平协商,也要有底线。
据时任中国政府对日谈判代表顾维钧观察,此时身处上海的中国上层人士“深受全国学生的所谓宣言和示威的影响”,纷纷主张对日强硬。(20)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4页。与陈立廷一样,上海扶轮社中方社员朱博泉、牛惠生、陈光甫等都加入了以支援前线、抗击日军为宗旨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21)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宣言》,出版者、出版时间不详,第6页。由此可见,陈立廷的态度在上海华人上层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海扶轮社还有一些日本籍社员,其中船津辰一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是在华日本商界的领袖,曾担任日本驻华领事,1926年起担任日本在华纺织会会长,“其一言一动,颇足以左右侨沪日本官民之势力”。(22)孔志澄:《日本现代人物传》(上),商务印书馆1940版,第236、237页。他与中国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认同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致力于维系中日和平。(23)佐野実「外交官·船津辰一郎と長崎」、http://nagasaki-bunkanet.jp/wp-content/uploads/2019/12/%E5%A4%96%E4%BA%A4%E5%AE%98%E3%83%BB%E8%88%B9%E6%B4%A5%E8%BE%B0%E4%B8%80%E9%83%8E%E3%81%A8%E9%95%B7%E5%B4%8E.pdf.2021年2月3日。然而船津同样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一·二八事变前后他的言行中有所体现。关于九一八事变,船津在致日本政府的呈文中表露了他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认同。船津认为,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一直不遵守“既有的条约”,“不具备现代国家的意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在为各国维护“既有的条约权利”,“拯救”东北人民。(24)「5 昭和7年7月16日から昭和7年7月2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280500、輿論啓発関係 第六巻/輿論並新聞論調/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1項 対支那国/1類 帝国外交/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沉重打击了上海的日商。作为日本在华纺织会会长,船津认为抵货运动“无疑是最邪恶的”,夹杂着“暴民”对日本商人的“酷刑、羞辱或其他形式的痛苦惩罚”(25)China and Japan,The Shanghai Times ,October 3, 1931:3.,“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不合理和不道德的”(26)The Psychology of the Boycot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October 9, 1931 :7.。为此,船津经常返回日本,向日本政府及民众反映中国抵货运动的严重性,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尽快制止这种暴力行为”。(27)「工人を挟んで工場閉鎖?罷業? 上海で日支睨合い 手出しすれば損 来阪した船津氏は語る」、『大阪毎日新聞』1931年10月11 日;「成行如何で一斉閉鎖を決意 暫くは形勢を観望 在華紡排日対策恊議」、『神戸又新日報』1931年10月13 日;「邦人在華紡は依然滞荷悩み 船津氏中心に関東側の懇談会」、『大阪毎日新聞』1932年1月8 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使船津产生通过战争即可迅速扑灭反日运动的错觉。在抵货民众的围困下,“一向稳健”的船津也强硬起来,与在沪日侨一起呼吁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排日运动,一扫从来的恶劣气氛”。(28)重光葵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浪潮,船津公开表示:“如果这种过分的反日宣传继续下去,没有人会惊讶在不远的一个晴朗早晨听到来自长江流域某个地方的另一个‘侵略’故事”。(29)China and Japan,The Shanghai Times,October 3, 1931:3.为了日本在华利益,船津不仅将扶轮社国际主义的理念抛之脑后,而且还与英美等国的侨民一起,试图将上海变成中方不设防的“自由港”。(30)「上海を自由港 十ケ国居留民委員で計画大綱を決定」、『大阪毎日新聞』1932年3月17日。
福岛喜三次服务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是日本在沪商界领袖,也是上海扶轮社的资深社员。他与船津的态度相似,但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二八事变前,福岛积极参与日本侨民的反华集会活动,“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迫使中国政府镇压中国人的一切反日抵货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福岛向上海的日本及欧美侨民鼓吹,日军“数小时即可尽占上海”,“解决沪局,固属轻而易举者也”。(31)《福岛末死》,《社会日报》1932 年 3 月 17 日,第2 版;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February 7,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船津、福岛等在沪日本上层人士,虽然是上海扶轮社社员,但其试图以战争手段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其民族主义的情绪逐渐遮蔽了自身曾高调奉行的国际主义理念。
横竹平太郎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商务参赞,也是上海扶轮社社员,面对中日冲突,他的心态与船津不同,更强调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作为日本驻沪领事馆官员,横竹向日本政府报告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情况,称“自满洲问题爆发以来,由于中国的民族运动,日本产品的销售渠道已被完全阻断”,但他并未呼吁日本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32)「上海(一)1昭和6年9月21日から昭和6年10月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313000、排日、排货关系第十一巻/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沟爆破ニ因ル日、支军冲突关系)/1类 帝国外交/1项 対支那国/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上海向け本邦綿布の危機 在上海横竹商務参事官公報」、『中外商業新報』1931年10月30 日;Mr.H.Yokotake, the Japanese Commercial Counsellor, Left Shanghai on Sunday for Japan,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November 3, 1931:8.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横竹一方面不断向东京报告上海抵制日货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参与扶轮社的工作,较之船津、福岛,其更乐于保持与各国社员的交流。(33)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January 28,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February 18,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乾精末是日本驻沪领事,曾任日本国际联盟促进会国际关系部委员,也是上海扶轮社社员。他与横竹态度相似,向来主张通过国际组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乾精末直言自己不认同日军的行动,但又无法干预,陷入“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34)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January 31,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上海扶轮社除了中、日两国的社员外,还有许多第三国社员。永明保险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英国人哈里斯作为第三国社员,为上海扶轮社的战时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二八事变前后,哈里斯担负起维护上海扶轮社国际形象,以及中、日社员间友好关系的责任。他坚信“做点事总比不做要好”,坚持在事变中遵循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希望通过扶轮社的努力来恢复上海的和平。(35)Rotarian's Trip to Manchuria,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Aug 10, 1932: 216.对于中日冲突双方,哈里斯试图保持中立,并认为中日两国都违背了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
但是,哈里斯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夹杂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因素。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在沪英侨大多希望借助战争以维护外人在沪特权,哈里斯即是其中一员。他公开表示,反对英国政府就治外法权问题向中国让步。他十分眷恋不平等条约赋予列强的在华特权,唯恐英国政府在中英治外法权谈判中同意废除英侨特权。(36)China Review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May 24, 1932: 317; Danger of Reticen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Nov 10, 1931: 200.在中日冲突问题上,他认为中日和解的基础是“条约必须得到遵守……直到双方同意修改或撤销为止”。(37)Rotarian's Trip to Manchuria,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Aug 10, 1932: 216.由此可以看出,一·二八事变期间,哈里斯主持扶轮社的工作,固然是为了恢复上海的和平,但其深层次的原因与船津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渴望列强在沪侨民能继续享受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和利益。
美国人费吴生在邝富灼之前曾担任上海扶轮社社长。他出生于苏州,自幼生活在中国,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费吴生认为,无论在东北还是上海,日军的行动“都是基于最赤裸裸的谎言”(38)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January 31,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日本人总是能够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制造借口”,中国虽然遭受日本侵略,但“在逆境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39)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January 29,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中国军队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40)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February 5,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对于中日冲突,费吴生明显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主张日本应无条件停止侵略,因为日本的侵略本身就违背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而中国的抗日具有正义性。在上海扶轮社的第三国社员中,不乏与费吴生想法相似的人,他们虽不像费吴生那样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曾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洛克伍德(W.W.Lockwood)积极参与了战时的难民救济活动,并认为在战争面前,中国人的应变能力“很有创造性”。(41)Sparse Attendance at Rotary Lunch,The Shanghai Times,February 19, 1932:5.再如曾任上海威廉氏制药公司经理的华尔夫(S.W.Wolfe),也十分同情中国民众的遭遇,感叹“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了如此可怕的伤害”。(42)Work Among Refugees: Jade Buddha Temple,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15 Mar,1932: 411.
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心态是复杂的。邝富灼、陈立廷、船津辰一郎、横竹平太郎、哈里斯作为上海扶轮社中、日、第三方的代表,参与了化解中日冲突的请愿活动。表面上,他们都表示遵循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愿意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而努力,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内心混杂着各自的民族主义情感及利益诉求。
二、上海扶轮社制止战争的努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扶轮社尚未直接面临战事的冲击,但作为以倡导国际主义、维系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9月25日,上海扶轮社仍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声明:
关于此次满洲所发之不幸事件,扶轮社全球社员,均应表示同情,且应注目此案将来发展。盖此次之暴举,不仅破坏远东之和平,且将引起全球人士之反感。其次,凡扶轮社社员,对该社组织宗旨第六条,有负使其实现之责任。此时正系促成目的实现之良机,故理应由上海扶轮社社员及其他各国社员,共同努力、促其实现。因以上原因,上海扶轮社应实时通过下列议案:上海扶轮社应即联络扶轮社国际同盟会,及其他相关团体,共同设法以全力促成和平,然近时间内解决满洲事件。(43)《扶轮社发表文件》,《申报》1931年9月25日,第14版。
11月16日,上海扶轮社前社长费吴生召集中外社员16人,召开主题为“满洲现状之根本原因”的研讨会。会上,陈立廷与福岛喜三次是中日双方的发言代表。陈立廷强烈呼吁中日友好合作,要求日本逐步放弃在华特权;福岛喜三次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日本必须在自身和苏联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并准备为此付出一切,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44)A Letter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to Mary,November 20,1931.File6-1,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与会的中日社员虽然能以“极大的勇气、自控力和理解力”友好磋商,但由于观点相对,未能形成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2月16日,“为进一步思考扶轮社在制止中日战争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上海扶轮社召开理事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其成员来自中、日、英、法、奥、美等国,包括上海政界、商界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经过磋商,扶轮社特别委员会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的信,发起“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请愿活动。请愿信写道:“鉴于中日两国政府都已接受设立一个中立区来确保上海地区的安全与防卫的提议,我们恭敬地请求两国政府立刻停火,以结束敌对状态。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进行关于上海地区安全防卫区域的谈判。”(45)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February 16,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之后,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推举中国社员邝富灼、陈立廷,日本社员横竹、船津,英国社员哈里斯组成代表团,负责将请愿信递交日本驻沪总领事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同意代表团所提的方案,但反复强调 “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之前撤退”是和谈的前提。2月17日,代表团又拜访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吴铁城“也同样相信,除非日本表现出足够的诚意,率先撤回到原来的驻防地,否则就不可能有公正的解决办法”。在日军率先撤军的前提下,吴铁城赞同设立中立区。(46)Rotary Unable to Prevent War, The China Press,February 26, 1932:9.由此可见,谁先撤兵是中日双方僵持不下的关键问题。
在请愿陷入困境之际,代表团又先后拜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顾维钧。重光葵与代表团成员讨论后,提出了和谈的基本条件:
中国军队应撤至20公里以外的特定区域,包括从吴淞撤离;当中国军队完成撤离后,日军将尽最快撤至1月28日晚之前驻防的位置,即沿四川北路至虹口公园一线;如果中国人需要,可组织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国际部队,对中国军队撤离的地区进行治安维护,但闸北除外,以确保其不受侵占;双方都应撤离吴淞,如果中国人愿意,应暂时将一支国际部队驻扎在那里;应当派遣中立的外国军事使团担任观察员,以监督双方履行约定;双方完成撤离后,应在上海召开圆桌会议,其他国家的代表及中日两国的代表应出席会议,以讨论和平解决上海事件的办法。(47)Ultimatum Rejected by Chines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February 23, 1932: 269.
重光葵提出的和谈条件较之村井苍松更为具体,但重点内容相差无几,都以中国军队先行撤离为和谈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重光葵对中国军队的撤退距离提出了具体且苛刻的要求,即中国军队放弃战略要地吴淞,这实际上无异于让中国军队放弃上海的防务。
代表团还面晤了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并将请愿信和重光葵的和谈条件交给了顾。然而在顾维钧回复之前的2月18日,日军司令部即发出最后通牒,这使代表团的和平希望彻底破灭。费吴生在日记中称,“我们一度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尽管有了重光葵的意见,但日军司令部今天发出了最后通牒,那是极具侮辱性的”。(48)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February 19,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由日军最后通牒引发的再次交火,使代表团的和平努力化为泡影。
事后不久,社长邝富灼在该社例行集会上总结、反思请愿一事时称,上海扶轮社“经受住了考验”,“日本和中国社员足够强大,没有让其民族主义精神遮蔽国际主义”。虽然上海扶轮社没有“成功地发挥和平缔造者的作用”,但表现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其已竭尽所能”。(49)Shanghai Rotary Club's Annual Meeting Dwells on Need of Friendship,The Shanghai Times,April 8, 1932:5.副社长哈里斯也对外宣称,中日社员,尤其是四位代表,在请愿活动中“工作得非常和谐”,表现出了真正的扶轮社精神。虽然他们制止战争的努力无果而终,但中日社员的友好合作“不可称之为失败”。(50)Efforts of Rotary for Peace,The Shanghai Times,February 26, 1932:6.事后,《字林西报》在报道请愿活动时,亦对上海扶轮社及相关社员的努力给予了肯定,称尽管相关社员未能达成制止战争的目标,但“他们不必感到羞愧”。(51)A Rotary Effor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 February 20, 1932:4.这些评价主要是基于相关社员的表现,认为他们超越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守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就参与和平请愿的动机而言,各方代表并未完全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及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陈立廷热衷于参与各种国际民间组织,目的是“增进世界对于吾人之观听,及吾国在国际上之地位”。(52)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东方杂志》第22卷第19期,1925年10月,第38-43页。同他参与第三、第四届太平洋会议的动机相类似,陈立廷参与扶轮社的和平请愿活动,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痛诉日军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军的侵略。(53)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32年,第46、47页。船津对反日运动深恶痛绝。与其他在沪日本上层人士一样,他虽不渴求侵略中国,但希望借助战争迅速扑灭中国的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54)高纲博文著,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他参与扶轮社的和平请愿活动,同样是为了迫使中方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目的。哈里斯则认为“中国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否定条约”。(55)Rotarian's Trip to Manchuria,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Aug 10, 1932: 216.如前文所述,他参与和平请愿一定程度上确系国际主义精神使然,但也夹杂着维护不平等条约,维护乃至扩大列强侨民在沪特权的目的。
就和平设想而言,各方代表多以本国家利益或自身利益为依归,置扶轮社国际主义精神于不顾。在与村井、吴铁城、重光葵的沟通中,上海扶轮社代表团逐渐接触到中日和谈的矛盾关键,即谁先撤兵和中立区问题。中方“以撤退可行,惟距离须最小限度,关键在此”(56)《宋子文电蒋中正本日三公使调停我方以撤退可行惟距离须最小限度关键在此正在磋商中》(1932年2月1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90200-00006-210。,而日方希图使上海成为中国之不设防城市,要求“以江海关为中心”,“10英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至此范围之华界区域,由警察维持地方,吴淞亦不驻军队”(57)《宋子文电蒋中正请核示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军密晤讨论双方撤兵等停战方案》(1932年2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90200-00005-174。,并以中方“先退为调停之先决问题”(58)《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本日在日本领事馆与日本第九师团参谋长并田代皖一郎会谈情形》(1932年2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110300-00002-020。。村井、吴铁城、重光葵为代表团开出的条件,与上述中日两国政府的和谈条件如出一辙。然而代表团接触到问题的关键时为时已晚,未等到代表团与双方进一步磋商,日军已发出最后通牒。实际上,即使代表团成员与双方进行了进一步磋商,和谈也难以达成,因为代表团各方成员的和平设想本就存在矛盾,这构成了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请愿活动的内在限界。呼吁和平的代表尚坚持互不相让的和平方案,未能放下个人立场,何谈说服两国政府实现和平。在中方代表陈立廷的设想中,中方“绝对不承认租界周围不许驻兵之议”,可暂时设立中立区,但“一俟日本军队撤至事变以前地点,仍由我军接防”,“绝端反对扩充租界”。(59)曹云祥、陈立廷等:《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上海青年》第32卷第7期,1932年7月,第2-5页。而在日方代表船津的设想中,中国军队须撤离上海,上海须设置永久中立区,最好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自由市”,方能使反日运动绝迹。(60)《日侨会议通宵》,《申报》1932年5月15日,第4版。显然两种设想具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撤兵问题、中立区问题上有明显对立。如上文所述,即使看似中立的第三方代表哈里斯,其深层次的设想也与船津相似,他十分渴望维持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既有格局,继续在上海“优越条件”下经商,希望扩大租界,甚至希望上海能够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表面看来,包括中日两国社员在内的多国社员坚持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为制止中日冲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相关社员实现了国际扶轮社在一·二八事变前的期许,即“我们身为扶轮社员,应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61)《邝富灼致国际扶轮社的信》,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但是,从深层次的参与动机与和平设想出发,多数成员未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反而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难以秉持国际主义理念去争取和平。
三、“求同存异”中的人道主义救助
与维系国际和平一样,“激发每个成员为他的同胞和整个社会服务的愿望”,“促进成员对社区公益事业的兴趣”,也是扶轮社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62)《上海扶轮社章程》(1919年),http://rotaryshanghai.org/wp-content/uploads/history/const/RCS-Constitution-1919.pdf.2021年2月3日。虽然上海扶轮社制止战争的请愿活动无果而终,相关社员亦未能将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但广大社员搁置分歧,一·二八事变期间为上海难民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在此过程中,上海扶轮社中、日及第三方社员求同存异,联合展开了救援行动,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紧急救援难民。在战事的影响下,上海扶轮社的部分社员及亲友不得不撤离家园,他们或被日军拘留,或将财产留在战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未带齐。(63)《邝富灼致国际扶轮社的信》,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此时,一些受日军侵扰较少的欧美、日本社员利用身份便利,积极开展援救活动,其中尤以欧美社员贡献最为突出,是一系列紧急救援行动的主导者,而日本社员在欧美及中国社员的请求下,也提供了必要帮助。费吴生称,“我几乎每天都被要求帮助朋友们撤离, 援救一些身陷后方的人士,以及找回他们在逃离时留下的私人物品”。(64)My 80 Years In China,File 21-1,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邝富灼的个人物品即是费吴生赴交战区带回的;社员朱博泉的好友叶元也是费吴生从日军的拘禁中解救出来的。在解救叶元时,哈里斯也应朱博泉的请求,给予了许多帮助。(65)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January 31,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上海扶轮社的一些日本社员也参与了难民救援行动。费吴生曾表示,为救援这些难民,“一些日本社员以真正的扶轮精神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帮助”。(66)《邝富灼致国际扶轮社的信》,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如进入日军控制区需要日方的“通行证”,在中国及欧美社员的请求下,日本社员利用身份之便,设法搞到了“通行证”。如在取回邝富灼、费吴生好友李清茂等人的个人物品时,横竹即为费吴生搞到了“通行证”,为他安全进入日军控制区提供了便利。(67)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February 2,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February 18,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乾精末也加入紧急救援难民的行列中。在解救叶元的过程中,费吴生、哈里斯联系了乾精末,希望通过乾精末的关系,敦促日军放人。作为日本驻沪领事的乾精末深知自己对日本军方的影响力有限,甚至自身都处在诚惶诚恐的状态中,但仍竭尽所能营救叶元。在美、英、日三国社员的配合下,叶元被成功解救。(68)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January 31,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第二,捐款救助难民。上海扶轮社社员费吴生、陈立廷、洛克伍德共同组织成立了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专门募捐救助沪战难民。(69)Diary of George Ashmore Fitch, February 1, February 3, 1932.File21-7,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该委员会虽然由欧美及中国社员发起,但大多数日本社员也参与捐款或从旁协助。据邝富灼所言,“该委员会在六个或更多的中心照顾着几千名难民”。(70)《邝富灼致国际扶轮社的信》,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上海扶轮社社员华尔夫发起募捐,救济、救治在上海玉佛寺避难的难民。他有感于玉佛寺“没有合适的手术台或其他合格的医疗设备”,登报呼吁民众为玉佛寺难民捐款。(71)Work Among Refugees: Jade Buddha Temple,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Mar 15,1932: 411.邝富灼也号召上海扶轮社各国社员为救济难民积极捐款。(72)Local Aviator Tells of Experiences, The Shanghai Times , February 12, 1932 : 3.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扶轮社向难民捐助了2145美元,其中日本社员也“为这项工作慷慨解囊”。(73)《邝富灼致国际扶轮社的信》,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扶轮社社员牛惠生的骨科医院是上海扶轮社的重点资助对象,日本社员也为该医院救治难民提供了一定资金。(74)Connie Fan,“The Rotary Club of Shanghai, The Events, Projects, and Personalities, from 1919 to 1949”.https://www.rghfhome.org/first100/global/asia/images/history_of_RC_Shanghai_1919.pdf.2021年2月3日。
一·二八事变期间,虽然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难以与民族主义相抗衡,各国社员大多无法超越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精神则在广大社员中得到认同,并共同为之努力。
四、结语
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扶轮社作为一个以维系世界和平为宗旨的人道主义组织,面对愈演愈烈的中日冲突,曾尝试以自身的力量制止战争、维系和平。中方社员陈立廷、邝富灼,日方社员船津辰一郎、横竹平太郎,第三方社员哈里斯、费吴生等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但由于日军悍然发出最后通牒,扶轮社制止战争的努力无果而终。在这一过程中,陈立廷、船津、哈里斯等各方代表看似超越了民族主义情感,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平,实现了国际扶轮社事变前的期许——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但实际上,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组织的请愿代表团成员大多未能坚持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反而受民族主义的支配。陈立廷是主张对日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参加扶轮社的请愿活动,是因为其视扶轮社为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侵略的平台;船津是战争的支持者,参与请愿的动机是实现扑灭中国民众抗日运动的目的;哈里斯参与请愿也抱有私心,即想维持不平等条约赋予外人的在华特权。此外,三方社员心目中理想的和平方案亦互相矛盾。由此观之,即使没有外部力量干扰扶轮社的请愿活动,各方代表也难以在和平方案上达成一致。
扶轮社维系国际和平的努力,在二次大战前后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是难以见效的。扶轮社试图培养各国社员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此来维系国际和平。但各国社员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高于国际主义理念,这成为上海扶轮社制止战争请愿行动的内在限界;另一方面,相较于维系和平的无力,在求同存异之下,上海扶轮社却能使各国上层人士在战争环境中共同秉持人道主义精神,推进人道主义事业。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虽大多未能将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但均认同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开展了人道救援活动。从一·二八事变期间扶轮社的活动可以看出,在二次大战前后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人道组织的国际主义理念,在民族主义面前不堪一击,难以切实维系和平,而其人道主义精神却能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战争中得以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