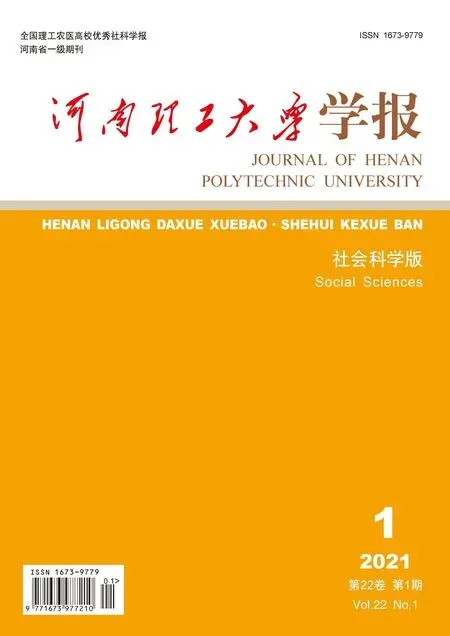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2021-11-26周伟
周 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有力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古文家苏洵,其对“文起八代之衰”、主导中唐古文运动的韩愈其人的评价与接受,是我们藉以审视北宋的韩愈接受实况乃至于唐宋古文运动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窗口。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散见于各类研究唐宋古文运动、韩愈、苏洵的专著及论文中,尚未形成系统的论述(1)相关研究著作有: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査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博士学位论文有:高光敏《北宋时期对韩愈接受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4年博士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主要在论述“三苏”的韩愈接受时对苏洵的韩愈接受作一笔带过式的叙述。期刊论文有:周楚汉《苏洵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陈新璋《宋代的韩愈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这些文章在论述中稍稍涉及了苏洵的韩愈接受。近年来关于韩愈的接受研究也不乏其人,比如查金萍《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张勇《论孤山智圆的韩愈观》,《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此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探讨。
一、治国之才:苏洵眼中的韩愈其人
苏洵流传下来的文章中涉及直接评价韩愈其人的文字几乎难以找到,大多都是有关韩愈文章的评述,不少时候甚至只是在行文中称引到了“韩文”这一笼统的词。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这些间接文字或是只言片语所出现的语境,我们也能总结出韩愈在苏洵眼中的人格特征。
在仁宗朝出现了一股“尊韩”思潮,并同时伴生了一股“非韩”思潮;前者的倡导者主要是精英士大夫,后者的倡导者主要是僧侣道流;两股思潮扭绞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关于韩愈及三王之道的学术讨论(2)详见刘成国《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文史哲》,2019年第3期。刘成国先生认为仁宗朝的这场关于“尊韩”与“非韩”的学术争锋具有深刻的学术史价值,认为这场交锋也是韩愈的《原道》一文走向经典的重要历练和鉴别过程。。苏洵身处这一学术语境,也不得不受到影响。很显然,苏洵站到了“尊韩”的阵营一方。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里面,模仿了韩愈《原道》一文建立道统的书写模式,将韩愈也放到了这一“为往圣继绝学”[1]376的王道统绪中:
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2]334?
其实,苏洵在列出了这个承传谱系之后,还说了“况夫四子(3)苏洵这里提到的“四子”指的是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认为他们继承了孔子以文明道的事业,对道统传承作出了极大贡献。者之文章,诚不敢冀其万一”[2]334的话,并没有直接提到他给出的这个谱系序列是道统中的还是文统中的,但宋人多认可“文以明(载)道”的观点,在他们那里道统与文统具有很大的重合度,苏洵也不例外,因此这个承传序列也不妨看作是苏洵道统框架中的重要一环。那么,我们就能知道,在苏洵看来,韩愈所以能够在后世名不朽、让后世对其“多称而屡书”[2]334的原因,就在于韩愈将这一千载不传的古圣王之道继承了下来。在古代,能够承传古圣王之道的人常常被认为是非圣即贤;古人认为这些人一旦被施用于世,将能够上辅君国、下护百姓、中致太平。苏洵对韩愈道统地位的认可,可视为是其认可韩愈治国才能的基础。
苏洵在他的好几篇干谒文里都提到了韩愈,除了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上欧阳内翰第二书》,还有《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上张侍郎第一书》等,在这些文章中,苏洵都有借重于韩愈等人来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的出发点,这正反映出了苏洵对韩愈其人治国才能的认可。
对韩愈政治才能的认同,应该说在宋代精英人士里面具有十分普遍的回响。宋代有一段记载值得注意:
韩魏公屡荐欧阳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复荐之曰: “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上从之[3]66。
韩琦在向仁宗推荐欧阳修的时候,竟然直接征引了韩愈未用于唐而导致后世非议的故事,并且将被荐者欧阳修呼之为“今之韩愈”。我们有理由相信,韩琦这里不仅仅是对二人才名相当的认同,更是对二人政治才能有补于世的认同:韩愈与欧阳修或许不具备宰相之才,但他们的政治才能绝对是万人之上的。
欧阳修在当时的声望,无论是文坛上还是朝堂上,都认为他与唐之韩愈可相提并论,所以他的弟子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里面对其当代地位予以了最终评定:“今之韩愈。”[4]978苏轼的这一评定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4)苏轼的原话是:“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经过苏轼的概括,成为后世认定的一个文化事实。苏洵自然对此不陌生,所以他在写给欧阳修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了韩愈。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2]327-330里面,苏洵还专门用了一大段文字评述了孟子、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的文章风格,其中对韩愈、欧阳修的评述堪称完善、形象、经典,多被后代研究者引用转述。苏洵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对韩愈文学才华的欣赏,一方面也是想借重韩愈的政治才能,引起欧阳修这位执政人员的注意。
从以上细琐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挖掘出苏洵对韩愈其人的基本评价态度是认可的,具体来说,就是对韩愈承传儒道、具备治国才能的认可。
二、经世与审美: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评价
文章要有用于世、关注现实,用古文家的说法就是文章要明道载道,这是苏洵文章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洵自己创作的文章就十分注重这一点,所以获得了欧阳修“有用之言”(5)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称道:“其(指苏洵)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舍,2007年版,第六册376-377页)明显指出了苏洵文章不仅语言精美,而且内容义旨合乎世用的特点。欧阳修还在《苏主簿挽歌》中说道:“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我独空斋挂尘榻,遗编时阅子云书。”(第一册第568页)将苏洵比作贾谊、扬雄,是对其文有用于世的认同,将其比作司马相如,是对其文精美性的认同。的赞誉。写作文章须从现实出发的创作理念,在苏洵的引领下俨然成为苏氏一族的创作家法。苏辙在《历代论一(并引)》中曾总结说:
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5]1212。
苏辙指出,其父苏洵与其兄苏轼的学问都是建立在以古为用、以今为的基础之上的,是对现实社会具有裨益的,而当他们的学问无法施用于世,他们就著之于篇章以期有闻于人,等待被别人践行的机会(6)苏辙的这段话与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一段文字在结构和旨义上相当类似:“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7版,第699页)韩愈认为自己所获得的“道”不应该被世俗当成器具一样的东西,用与不用完全付之于人,而应该用则施行之,不用则让它流传下去,以等待大用于世的时机。由此足以见出“三苏”对韩愈文章的融会贯通,并将其中的义理付诸了实践。。很显然,在苏洵的眼中,韩愈的文章不仅仅是艺术精致的文,更是载了道明了道的经世之至文。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以非常自负的态度表明自己怀抱有经国济世之才:“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叟不得夺诸舜。”苏洵认为自己拥有一份不传之绝才,还把这份绝才拿来与尧、舜之才并论,并由此引发一段关于怀才之人如何应付自己所怀之才与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的讨论:
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亵天。弃天,我之罪也;亵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亵,而人不我用,非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则弃天、亵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
这一看法显然是对传统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仕隐观的发明和延伸,只是态度上表现得更加刚介强硬,语言上表现得更加犀利夸张,其直指当政者的锋芒灼然可见。而苏洵借以展现自己值得施用于世的证明正是他相当自负的文章:
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用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2]317-319!
苏洵认为自己大肆其力后写作出来的文章,所以能够有补世用,原因就在于他退居山野之后广泛学习了周代《诗经》群作者的优柔,屈原等骚人的精深,孟子、韩愈的温淳,司马迁、班固的雄刚,孙子、吴起的简切等并能熟练运用之。显然,这里所谓的“优柔”“精深”“温淳”“雄刚”“简切”,不仅仅是指各家的风格所向,也包含有对各家义旨内容的概括和归纳。苏洵说他能在这些方面所向无不如意,显然不单单是说风格上的模仿,更是对文章义旨、结构、社会价值、伦理价值融会贯通之后的心有所得。苏洵通过透彻学习这些作品之后,能够轻松乐易地写出“有用之言”。那么,作为其学习对象之一的韩愈,自然所为之文也该是“有用之言”了。值得注意的是,苏洵拿来与韩愈同列比较的作家,《诗经》群作者、屈原、孟子、司马迁、班固、孙武、吴起、贾谊,都是写出“有用之言”的杰出代表;而苏洵相对地批判了董仲舒的迂阔(也即脱离现实)、晁错的诡诈(也即诡伪欺诈),反过来说就是认为韩愈等人的文章没有这种毛病,这正间接体现了韩愈文章的实用性和经世性。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无论是谈论道统还是谈论文统,苏洵多将孟子、韩愈并称,而孟、韩并称正是宋代古文运动中滋生出来的一种话语范式,可见苏洵的孟、韩并称是含有浓重的古文运动精神的。苏洵对韩愈文章经世性的认识,不仅是自我学习的结果,也是社会思潮濡染的结果。
对韩愈文章现实性的认识,使得苏洵以之作为教育后辈的一部重要教材。在给张方平所上的书信《上张侍郎第一书》中,苏洵详细地介绍了二子在家的学习经历: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
苏洵在这里提到,年少的苏轼兄弟从小就显露出优异的文学才华,而二人在掌握了声律属对的技能之后,就不满于这种雕虫小技了,他们期待更加雄伟壮观的学习对象,直到接触到孟子、韩愈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创作的真谛,进入了创作的大门,可望在这一领域登堂入室、大有所为。而值得留意的是,苏洵随后还提到,苏轼兄弟在学习了孟、韩文章之后,“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于是苏洵带领他们前往京师举进士的事情[2]345-346。换句话说,就是苏轼兄弟学习了孟子、韩愈的文章之后,认为自己可以写出有补于现实的文章出来,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为国效力了,于是自信地踏上了求仕之路。
从学习韩愈等人的古文而悟出为文之法,这一学习经验在苏洵的人生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烙印。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苏洵这样回顾道: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
苏洵一开始学习时文,因为身边的人都比不上自己,所以颇有自满之意,及至读到“古人之文”,才认识到自己的浅陋可笑,于是尽毁曩时所为之文,取韩愈等人的古文来深入学习。苏洵以细致简朴的语言将自己由最初的惊惶,到读得精深时候的豁然开朗,再到学至烂熟时候的轻松乐易的体悟过程叙述得真切动人,令读者颇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苏洵在深入掌握了韩愈等古人的为文之法并用之娴熟之后,不无得意地向欧阳修宣告道:“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途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2]329认为自己的“知道之心”已经炼就而成了,可以施之于世以辅邦国了。这正反映了苏洵对韩文经世性的清晰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自述其学习经历的这段文字,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自述其学习古文写作的那段文字颇有相似之处:
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6]699。
韩愈在孜孜不倦的古文阅读中培养出了十分高超的鉴赏能力,并在潜心钻研自己所筛选出来的古人文章中领悟到了创作古文的真谛,达到了文思泉涌、自然而出的创作境界。这种行文上的相似性,一方面反映出苏洵对韩愈文章的烂熟和模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二人共同地对所处时代的时文趋于形式、专讲声律辞藻、脱离现实的批判,以及二人在古文写作方面所持的古为今用、从现实出发的古文创作理念。韩愈这一理念的强烈竟然致使他产生“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6]699的感受。正是由于时人所持的评判标准是流行于俗的时文,所以韩愈宁愿听到别人对他文章的讥笑。由此可见,韩愈和苏洵都认为那些载有道、明以道的古人之文是一个志在写出“有用之言”的士子所应该努力效法的最佳对象。而苏洵作为晚辈,又多了一个堪称榜样的学习对象:韩愈这位先驱者的文章。
当然,经世之文的本质还是文,所以苏洵在讨论到韩愈的文章时,不仅仅从经世的角度去谈论它,也常常从艺术形式精美的角度去评论它(7)周楚汉在《苏洵文章论》中注意到了苏洵强调文章的文学性的论文特点:“苏洵论文重文不重道,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道文并重,道德文章并提不同,他只就文论文,或论‘遣言措意’的方法,或论文的风格,不涉及道的问题。”(第40页)其实古人(尤其苏洵所处的时代正值古文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论文多隐含着论道,更何况苏洵论文时所涉及的谈论对象还是历来被认为是道统上占据重要节点位置的古文家,而且他论文的目的多是借重于论古文家的文章来向执政者表明自己在学道上面的进步和成就。所以不能认为苏洵论文时不涉及道的问题,而应该承认他论文的同时包含有论道的成分在。,最有名的当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的那一大段鉴赏文字: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2]328。
苏洵在这里以蕴涵万怪的江河和深不见底的渊谷比喻韩愈的文章,既指出了韩愈文章艺术形式上不拘一格、不主故常、随势而变、应物多方的风格特点,也指出了韩愈文章义旨深厚、内涵浩大的现实功用性。而且苏洵似乎更看重文章的现实功用性(也即文章经世的特性),因为他自己就说过,在研读了韩愈等人的文章之后,他练就了自己的“知道之心”,这是他极为自豪的;显然,苏洵所谓的“知道之心”主要是针对经邦治国而言的。
三、“本末”论:苏洵对韩愈儒道观的接受与改造
苏洵在论文的时候就隐含有论道的成分在,这是我们上一节讨论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评价时得出的结论之一。“道”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实体,历来是古代文学及古代文论、古代哲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是我们借以审视古代社会乃至具体的某个作家的思想演变、文学表现、思潮涌动的重要中介。所以尽管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或多或少地涉及苏洵对韩愈之“道”的评价问题,但还是有必要将其拿出来单作讨论。
苏洵很少直接论及“道”的问题,不过,通过对其散落在各类诗文里的相关话语的整理,还是能够大致总结出其所谓“道”的主要内涵。正如苏洵自己所说,他的“知道之心”是在深入学习孔、孟、韩等圣人、贤人的文章之后炼成的。我们知道,由孔到韩,古人认为是有一个大致上的道统承传的,而就流传下来的作品的影响来说,韩愈的文章对苏洵时代的人们来说,不仅数量是最丰富的,流传也广泛得多。因此,韩愈的“道”,在道统序列中应该算得上是在北宋仁宗朝前后影响最为普遍和深刻的(8)刘成国在《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中说:“仁宗即位后,古文运动在历经真宗朝的萧条后重振,士人群体中的‘尊韩’思潮蔚然成风。”(第44页)刘成国先生认为这场“尊韩”思潮为北宋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儒学复兴的思想变革运动,并在文中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情况作了大量描述。。就苏洵而言,韩愈的“道”也确实得到了他根本上的接受和认同,只是苏洵从韩愈这里领悟的“道”,虽在本质上没有变,但在范围上却要更加广泛,在性质上更具有包容性;苏洵对韩愈“道”的接受与改造可以这样来概括:卫道而不排佛老。如此一来,韩愈的“道”由苏洵的眼光看来,不得不被附上狭隘的特点(9)周楚汉在《苏洵文章论》中说:“苏洵的道乃‘百家之说’,比韩愈、欧阳修主要是儒家之道进步,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比较近似。”(第40页)所谓“大中之道”,刘增光先生在《真心与皇极——北宋契嵩禅师三教论视域中的〈洪范〉学及其意义》中解释说,“皇,大。极,中也”,“皇极之道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是最为根本的、超越时空的本体”,这个“道”施用于天地则天地和顺、万物谐调,施用于人则思想无邪、性情淳厚,因此“大公中正即是圣人治理天下之根本原则”。(《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第44页)苏洵对《洪范》有深入的研究,自谓其论“大抵斥末而归本,授经而击传,刬磨瑕垢以见圣秘”(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可见苏洵的“道”确与大中之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接受问题
先来看苏洵对韩愈之“道”的接受问题。苏洵自谓其“知道之心”是从钻研韩愈等儒者的文章来的,那么其所获得的“道”是什么样的呢?前两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大量的苏洵论文论人的言行,从那些言行中我们已经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苏洵所认为的“道”,其本质就是韩愈在道统建构中所阐述的“道”,也即儒家之道,因此这里不再复述,不过这里还可以再给出一条证据。
苏洵在《权书叙》里面解释了自己写作《权书》这一篇政论文的原因: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
《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书》,为仁义之穷而作也[2]26。
苏洵首先批评了迂阔不实的腐儒“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的荒谬说辞,接着指出,自己所做的《权书》就是一部谈论军事的兵书,而该书与传统兵书的不同在于“用仁济义”的特点上。另外苏洵特别强调了自己与孙武这位兵家者流的区别,认为孙武的兵书是“常言”,也就是兵家者流的惯常之言,而他自己的这部《权书》则是仁义穷蹙后的“不得已而言之之书”。联系北宋时候军事上的薄弱,可以看出,苏洵所谓的“不得已”正是指由于北宋“仁义之兵”(10)所谓的“仁义之兵”,是古人对文明地区的官兵的称呼。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他这位儒者不得不学习兵法,站出来仿效兵家者流为国家的军事发展出谋划策。正是他所做的《几策》《权书》《衡论》这些“不得已而言之之书”获得了欧阳修“有用之言”的称赏,并使他获得了“士大夫争传之”[7]13093的崇高声名。值得注意的是,苏洵提到了:“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既言“本末”,则其以儒家思想为本,以兵家之法为护国之器的本意就明了了。另外,我们知道“仁义”所代表的就正是儒家思想,也即儒道的内涵范畴;苏洵这里频繁使用到的“仁义”一词自然与此有关,但恐怕还与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对儒道的阐发和溯源分不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6]1
(二)改造问题
再来看苏洵对韩愈之“道”的改造问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二人对待佛、老二家的态度问题上。
1.韩愈及宋初诸子的“排佛”“排老”论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以精简的笔法概括了韩愈的历史贡献,其中有两点是这样说的:“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8]。前一点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肯定了韩愈的反佛、反老观点,后一点则是从伦理的角度肯定了韩愈的排佛做法。韩愈在《进学解》中也借学生之口指出了自己卫道排佛、排老的人生行为:“(先生)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将当时隐微不显的儒道义理发诀出来,而将当时甚嚣尘上的佛老诸异端思想摈斥于外,并且将这一人生志趣贯彻到“恒矻矻以穷年”[6]147的程度。
韩愈所持的这种卫道反佛排老态度以及其所阐发的义理对宋初诸子影响甚大,他们上接韩愈的观点而打出复兴儒道、扫除异端的旗帜。如以“守道”为字的卫道者石介就在这方面对韩愈推崇备至,他专门写有《尊韩》一文,有云:
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
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9]7980!
石介认为韩愈是孔子之后对儒道传承最具有贡献的“贤人”。石介的辟佛排老态度及其理由与韩愈的也极近似:“夫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乱中国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乱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语乱中国之言语。”(《明四诛》)[9]71,不惜连华夏族人老子也斥之为“夷狄之人”。
欧阳修在《本论下》也有类似观点:
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传》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奚必曰“火其书”而“庐其居”哉[10]第二册63!
欧阳修认为,圣人治世之具尚在,只要上层人士能够“讲而修之”,使之传播于世、浸染于民,就能自然而然地“充行乎天下”,而致使异端思想“无所施”。他认为儒教优于佛、老诸教(11)欧阳修这里所反对的不只是佛一家,更包括儒家之外的诸异端,因为他引用的韩愈的“火其书”“庐其居”的说法,在韩愈所使用的语境下就是排斥佛、老诸异端思想的。,不必对事佛之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只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6]4,就能自然而然地收到预期效果,这体现了一种道德上和文化上的自信。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载了一件故事,说欧阳修是在石介的说服下才加入到卫道反佛辟老的阵营的: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11]281。
这则记载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宋初诸儒仅仅围绕传统的解经传注来研究儒家经典,有点类似汉唐诸儒的章句之学,直到孙复写作了《春秋发微》,才稍稍接触到了义理的阐发;二是石介与其师孙复率先站出来与佛、老之说抗衡;三是石介成功说服了欧阳修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一起援引韩愈之说以协力抗佛辟老。可以看出,辟佛反老在当时已经渐渐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变革深刻的思想潮流了,其后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股潮流所发挥出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正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说的那样:“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10]第四册406
2.苏洵对佛、老的宽容态度
在士大夫多言辟佛排老之说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苏洵并没有加入到这个阵营里面,在其诗文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排斥佛、老的思想倾向。他用一种可名之为“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来缓和韩愈等人的“辟佛”“辟老”论,这使得他在士大夫圈子中显得十分特立独行。其《彭州圆觉禅院记》说:
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者,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容于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而接之以礼。
苏洵这里指出了一个世风凉薄的扭曲现象:释老之徒自叛其师,而士大夫喜其来而优待之。这个现象反映出了当时儒、释、道三教之间竞争激烈的实况。接着苏洵提到了韩愈诗歌中的两个饮酒食肉、不守戒规的和尚的例子(12)韩愈在《送灵师》中有云“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黑白”,“六博在一掷,枭庐叱回旋”,“战诗谁与敌”,“饮酒尽百盏”,“寻胜不惮险”。(方世举笺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103-104页)在《送文畅师北游》中有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第239页)韩愈对和尚犯戒毁律持赞赏态度,恰与苏洵的批判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表明自己对这种不贞不诚、欺师灭祖之人的反感和痛斥:
灵师、文畅之徒,饮酒食肉以自绝其教。呜呼!归尔父子,复尔室家,而后吾许尔以叛尔师。父子之不归,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
也正因此,苏洵说他之所以愿意为该禅院作记的原因乃在于“予佳聪之不以叛其师悦予也”[2]399。僧保聪遇到的人是苏洵,所以他没有因为苏洵是一位习儒之人而故意曲迎其好的行为得到了苏洵的赞扬,并由此达成了求记的心愿;试想想,如果他遇到的是石介之类儒人,情况恐怕就得另作推测了吧。另外,苏洵在这段叙述中提到了一个假设:如果灵师、文畅之徒能够弃佛还俗,他就不反对他们叛师背道的行为。苏洵的这个假设反映出来了一种价值观:即对真、诚、贞、忠的肯定和向往。对那些处在这个价值观对立面的人,苏洵认为他们“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是非常痛切厌恶的。
苏洵的这一价值观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在《太玄论上》中谈及了立言的标准:
苏子曰:言无有善恶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辞不索而获[2]169。
这样一种自然发声论无疑是建立在正心诚意、忠实其人的修养之上的。再如《题张仙画像》中体现出来的那个倡言怪异的道教徒苏洵:
洵尝于天圣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观无碍子卦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乃云:“张仙也。有感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矣。故识其本末,使异时祈嗣者于此加敬云[2]416。
一个服勤于儒道的士子在面临祈祷应验、喜得贵子的幸运面前也不免产生“背道”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做法恐怕是孔子、韩愈这些“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者所切切于齿间的吧(13)其实在儒家、道家那里各有一套自己的神学系统,两者在性质上出入很大。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在于:儒家所信奉的神灵是以调和四季、规范风雨、中和万物、条畅天地、序列人伦、爙灾祈福、泽润万民为目的的,带有明显的伦理性特征;而道家所信奉的神灵则是以展现灵异、致人成仙、与人长生为目的的,带有明显的怪异性特征。。《老翁井铭》中那个亦仙亦儒的苏洵形象更是把苏洵“贵真务诚”的精神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因为作亭于其上,又甃石以御水潦之暴,而往往优游其间,酌泉而饮之,以庶几得见所谓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闵其老于荒榛岩石之间,千岁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后得传于无穷[2]407。
文章写于嘉祐二年卜葬亡妻之际,时作者求仕未遂,碌碌于世间,其心情与谪贬永州的柳宗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而文风也表现出了柳宗元《永州八记》那类山水记文的空虚幽独、寂寞入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篇散文熔儒、道于一炉,试看:缥缈不与人接的老翁不正如一名放逸人间的地仙么?而那离群索居、思老井边的幽人不正是一名怀抱儒术、期用于世而不得的伤心儒客么?这位儒客对自己不遇于世的遭遇的同情竟然也扩展到了对这位将要独“老于荒榛岩石之间,千岁而莫知也”的老人身上。这里的苏洵化身成了做梦的庄周,或者说是做梦的蝴蝶:老翁与苏洵,不是肉眼所见的那样分明可辨,而是水乳交融的浑然一体。苏洵不固守一端,而是“随物赋形”、以诚待物、自得其适。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苏洵随着所处环境、所接外物的不同而展现出来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内涵,但有一点是自始至终存在于他的意识中的,那就是对真和诚的持守。这份持守不涉及政治范畴,是纯粹的哲学理念的实现。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苏洵的“贵真务诚”理念不是建立在虚空之上的空中花园,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惯常认识到的所谓真诚、诚实;这一理念有它牢靠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他在《送吴侯职方赴阙引》中阐述的那一“自然”实体:
因天地万物有可以如此之势,而寓之于事,则其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穷万物而不可变[2]417。
苏洵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形而上的“自然”实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之间的那个“如此之势”,并且认为,只要世间之事建立在这一哲学实体之上履行,就会取得成之易而施之无所不可的神奇效果。而如何确认自己所行之事是否遵守了这个天地间的“如此之势”呢?其答案就是看我们是否按照了“真”和“诚”的原则办事。苏洵意在表明,一个正其心、诚其意的人所为之事,一定是符合天地间的这个“如此之势”的,其所取得的效果将是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也正因此,他很反对世人的违心做法:
有人焉,以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惊人也,乃曰:“杀吾身虽不能生人,吾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强之也。强不能以及远[2]417-418。
所谓“人心之所自有”,就是符合“如此之势”的事物;所谓“人心之所自无”,就是违背“如此之势”的事物,是需要依赖勉强才能存在的,而且其存在也必将是暂时且活动范围狭窄的。
值得一提的是,苏洵对佛、老的态度还体现在他对儒、释兼事的柳宗元的评价上。
在苏洵身边,欧阳修引起了一股不小的“批柳”思潮(14)孙昌武在《柳宗元传论》中说道:“从儒道的大本大原上攻击柳宗元,欧阳修是出言最苛的一个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0页)刘城在《欧阳修与“韩柳”“韩李”并称》中说到:“至北宋,‘韩柳’并称已极为普遍,但欧阳修却起而矫俗,欲以‘韩李’替代‘韩柳’。”(《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3页)“宋人论著中所出现的‘韩李’并称,几乎都源自欧阳修,可见欧阳修倡导‘韩李’并称的推广之功及影响之巨。”(第5期,第75页)他们都在文中对这股北宋时期的“批柳”思潮作了相当的描述。。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中欧阳修指出道: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10]第七册526。
对柳宗元杂糅有异端思想的“道”予以了批评。在《唐南岳弥陀和尚碑》中更是由批其“道”波及对其文章的评价: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10]第七册527。
而在苏洵的评价中,柳宗元离开了被批驳的位置,处在了被惋惜的位置。苏洵留下来的有关柳宗元评价的文字只存在一篇《上张益州书》,其中有云: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为天下之儒人,而一旦不幸,陷于不义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刘梦得、吕光化,皆才过人者,一为二王所污,终身不能洗其耻。虽欲刻骨刺心,求悔其过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为党人矣。洵每读其文章,则爱其才;至见其陷于党人,则悲其不幸[2]484。
苏洵写给张方平的这封书信本是为了感谢张氏的荐举而作的,所以他援引了柳宗元等人因择主不善、求进心切而留下“党人”的骂名的故事表白自己的行为操守。对柳宗元的批评,没有涉及柳氏信佛的一面,而只就其与“不义之徒”为伍的政治行为予以了指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洵不仅着重强调了柳宗元“儒人”的身份,而且对柳宗元的关注点也由批评转到了惋惜,并且后者的成分远远浓重于前者。当然,这是一篇关于政治品质的议论文,没有涉及柳宗元的三教观是很正常的,但至少从苏洵更加强调对柳宗元的同情和惋惜这一点来看,也能看出他对柳宗元的态度较之欧阳修等人是更为宽容和柔和的。
而清人平步青据“苏洵《上欧阳公书》,韩子后亦举习之”[12]卷七的做法认为苏洵与欧阳修一样也有排柳宗元而尊李翱的特点。平步青所举的例子是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评论诸家文章时,评论了李翱而没有评论柳宗元,但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其实苏洵在文中单独加以评论的只有孟子、韩愈、欧阳修三人,重点加以评论的只有韩愈、欧阳修二人,之所以评论涉及到了李翱,只不过是为了说明欧阳修的文章特点而已,况且苏洵还并举了陆贽一起形容说明,请看苏洵的原话:
执事之文……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2]329。
在苏洵的评价中,李翱只是体现出了欧阳修的某方面文风特点,难以与欧阳修相提并论。苏洵在文中只把孟子、韩愈、欧阳修放在一个水平上做了评论,由此可见,苏洵并不认为李翱可以代替柳宗元而获得与韩愈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那么平步青用这一个例子来证明苏洵想打破“千古足当韩豪者,惟柳州一人”[12]卷七,也即“韩柳”并称格局的说法就不妥当了。
总之,苏洵对韩愈之“道”既有所接受又有所改造。接受的内涵就是苏洵将韩愈的儒道观几乎全盘吸收了,承认韩愈对儒道的阐发,并自觉地承担起传承者和守卫者的角色;而改造的内涵就是苏洵在保证不危害到韩愈的儒道义理的基础上,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来修改韩愈对佛、老的批判态度,显得更加的包容。由于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苏洵的儒道观带上了“百家之说”(《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10]第二册602的特点,但正如苏洵自己强调的那样,其儒道观里面儒家之道与佛、老、申、韩诸道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二者形成了“本末”的相对关系。
四、结 语
苏洵生活的时代,文学思潮处在异常活跃的阶段。“尊韩”与“非韩”互相冲击;创作古文与写作时文论争激烈;儒道与异端针锋相对,口诛笔伐。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偏居巴蜀、自学成才的苏洵能够敏锐地嗅到当时的学术气息,并敢于挑战世俗风气,冲击陈旧的学术体系,倡导更符合时代发展的古文复兴,其眼光与气魄都是值得敬畏的。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就包含有这些时代共性,首先,苏洵“尊韩”,认可韩愈所倡言之“道”,以及其经邦治国才能;其次,苏洵热情称颂韩愈文章经世载道的特点;最后,苏洵从儒道传承方面肯定了韩愈的学术思想。这三点,都与当时的文学革新思潮相合拍。
当然,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除了上述社会共性方面的特点而外,更有苏洵自己个性方面的特点。苏洵好学好辩,对人生与历史多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但其学术来源多由自学,缺乏师友渊源,因此他所建构出来的韩愈形象,只是出于自己个性需要的韩愈形象。在人格方面,他对韩愈的评价局限在了治国才能上,不出当时古文家对韩愈评价的大局,这与他自负有经世之才的性格、积极进取的人材观相吻合;在文章方面,他不仅看到了韩文的经世性特征,还看到了韩文的美学价值,这与他在文学创作上追求水一样实用与精美共相焕发的创作观相合拍;在思想方面,他基本上接受了韩愈的儒道观,但对待其他思想种类,又不像韩愈那样严苛,而是采取了宽容处之的态度,这与其崇尚真诚、讲求容纳的人生信仰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