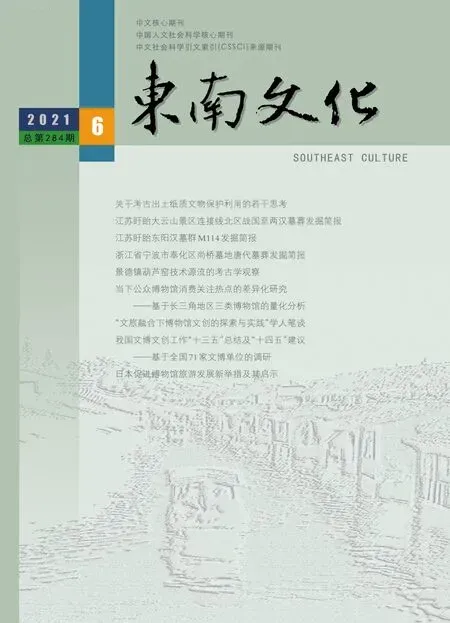博物馆公共事件题材展览中的情感体验
2021-11-26王旖旎
王旖旎
(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 浙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组织公共事件题材的展览是博物馆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可以让博物馆为社会利益的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更加直接和具体。突出公共事件的一个被忽视的特点,即事件中的情感因素,是进一步揭示情感动员在公共事件展览中核心作用的基础。将米哈利·巴赫金“移情”与“外位”结合的理论与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展示进行联系,有助于使观众对展示对象的理解从表象深入到精神内核。博物馆、观众及公共事件三重主体都将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意义的生长。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应该如何回应公共事件,又一次成为业界和学界的焦点话题。后疫情时代,在中国建立国家级防疫博物馆的提议也获得了很高的呼声。今天的博物馆正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在社会热点和变革的洪流中。博物馆化进程中“由经典向日常的拓展”和“由过往向现生的拓展”[1],呼唤博物馆的目光不仅观照精品,也观照物的“记忆载体”价值;不仅观照历史,也观照现在和未来。同时,从博物馆定义的不断演化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现代博物馆越发探求更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连接和社会参与,这实际上是理论界对博物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角色变化的反应。在新博物馆学思潮的影响下,博物馆保存、创造和传递社会记忆的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也驱动着博物馆从旁观者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形成更深入的逻辑思辨和更系统的行动策略。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展开,试图着眼于公共事件的“情感”维度,并提供一种更加开放的理念,希冀能为博物馆、观众及公共事件三者的关系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一、博物馆作为展示公共事件的行动者
公共事件是指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事故灾难(如煤矿塌方)、公共卫生事件(如传染病疫情)、社会安全事件(如恐怖袭击)。本文为了与博物馆展示建立强相关,故侧重于公共性和危害性两大基本特征。
公共事件凝结着社会的共同记忆,即使时隔久远或未曾亲身经历,一旦画面或声音再现,相关的记忆也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其底层逻辑正是基于公共事件能唤起人们普遍的情感联结。一般来说,一个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共事件,正是因为它普遍地调动起公众的情绪,可能是哀痛、愤怒、惋惜、悔恨,也可能是感激、爱国、自豪、荣誉感。唤起数量庞大的个体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是“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的内在动力。情感倾向主导着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判断,成为社会对公共事件记忆重中之重的环节。本文认为,公共事件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正是来自情感的传达。
近年来,博物馆关注公共事件的频度和维度都有所增加。公共事件的见证物被纳入收藏体系,展示公共事件成为展览叙事脉络的重要环节,甚至出现一些专门为纪念公共事件而设计的展览或博物馆。这些表现植根于博物馆所肩负的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博物馆社会服务意识的形成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博物馆大发展中产生的激烈竞争使其开始认真研究社会和观众的需要,从而逐渐形成了自觉的社会服务意识。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以下简称“国际博协”)第九届大会的主题是“为当代和未来公众服务的博物馆”(The Museum in the Service of Man,Today and Tomorrow),这是国际博物馆界第一次提出为社会服务的观念[2]。随后在1974年国际博协哥本哈根会议中,便把“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写入了博物馆定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学运动(Movement of New Museology)更将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推向高潮,强调“面向社会、介入社会、关注社会”[3],“把工作和关怀的重点放在社会上的人而不仅仅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藏品”[4]。
通过回应公共事件,博物馆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进化,也有潜力成为一支促进时代与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公共事件展览通过事实陈述见证、保存集体记忆,通过引发讨论创造集体记忆。透过事件之重构,在悲剧情绪中省思和激发责任感,或引发公众对英雄主义之认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包容。
二、公共事件展览中的情感关切
在公共事件题材的展览中,若仅仅依靠认知维度,既不能完整表达公共事件的丰富性,也难以打动观众。因此,博物馆应一改以往的认知本位,在公共事件展览中以“情”动人,把为观众创设情感体验放在核心位置。
情感是组织化了的情绪信息。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情感既是媒介又是信息:情感作为媒介时,能帮助观众与展览内容建立连接;情感作为信息时,具有内隐性的特点。这使得展览精神性的情感内核隐藏在展项之中,不易被直接解读,需通过策展人创设的体验来被观众领悟并成为观众的情感体验。
(一)情感体验的特点
1.相对自动化和无意识
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某些情况下情感判断在认知分析之前就已发生[5],感官体验引起的程序性的情境和情绪过程发生在潜意识中[6]。也就是说,观众情感的激发通常是身心自然发生的行为。
2.鲜活性和具体性
通过创设情感体验能引发观众高度的情绪介入,产生强烈震撼的心理活动和丰富活跃的联想。情感体验既可增强静态展品的感染力与表现力,也可避免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事件题材陷入抽象干瘪的、口号式的单一与僵化局面。
3.情境性
对符号化知识的学习可以脱离情境,但情感信息却总是需要与具体情境相联系。情感体验可能来源于文字和画面所描绘的情节,也可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但不变的是情感总是交织在情境中。这与公式、运算、规则、定义可以脱离与情境的互动而孤立存在有着根本不同。因此,博物馆创设情境成为了让观众获得情感体验的必然选择。
4.个性化和缄默性
一方面,情感体验总是因人而异,人们会对相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基于不同的“需要、价值取向、认知结构、情感结构、已有的经历等完整的自我去理解、去感受、去建构,从而生成自己对事物的独特的情感感受、领悟和意义”[7]。另一方面,情感体验进入内心深处,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的体验无法完全对“你”说,甚至主体本人对此也感到模糊。这样的特征为观众的情感体验预设了一种不确定性,期待着博物馆能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做出妥善的回应。
5.意义生成性
“我们对某物有深刻的体验,必会对其产生个性化涵义,即理解到它在我心目中的独特意义,或者形成某种联想和领悟、生成意义、获得启迪和升华,由此使人的心理获得调整、改造和发展。”[8]基于此,观众的情感体验可以被视为一种伴有情感反应的意义生成活动。
(二)情感体验的意义
情感体验既有认识论的意义,即观众通过情感体验实现认知与理解;又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情感体验深入到人的存在层面的观照。
1.有助于展览信息的全方位传达
情感是展览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少对情感维度的体验,会造成观众与展览信息沟通不畅,无法实现展览信息的全面传达。认知科学的大量实验已证明,“所有信息加工过程都含有情绪成分,情绪可以是信息加工的启动状态,也可以是信息加工的背景状态”[9]。观众在公共事件博物馆中参观学习,不仅是一个认知过程,更应该是一个情感过程。
2.通过情感的感染力打动人心
情感的感染力无可否认,尤其当博物馆展览涉及公共事件题材时。情感体验率先通过丰富性、互动性吸引观众的兴趣,然后通过深挖物和事件内部潜藏的价值与意义来传达深入人心、值得回味的情感信息,将相对艰涩枯燥的宏大叙事以更细腻的方式呈现出平易近人的效果。情感体验通过加强观众与信息的互动来打动观众,这种互动不仅指行为上的参与,更是指双方精神上的深度交流。
3.提升认知效果
情感因素直接影响着人对事物认知的效率、深度和结构,通过影响信息的吸引力和影响信息的处理过程来实现。在影响信息吸引力上表现为:人对信息的接收有选择性,“环境中的情绪事件比中性事件更容易进入意识”[10]。在影响信息处理过程上表现为:情感体验总是在情境中产生,通过具体的情绪唤醒事件来实现信息的编码。情感可以被视为认知过程中的有效标签,通过“特征捆绑—联想启动”为认知增添了一个线索性的新维度。
4.提升记忆效果
情绪对记忆具有加工优势,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记忆的增强效应”,在记忆的编码、巩固和提取阶段均存在。“相对于中性刺激,情绪信息使记忆在准确性和细节上都得到显著增强”[11]。其认知神经机制也已得到确认,“涉及的脑区主要包括双侧杏仁核、海马前部、海马回和前额叶皮层”[12]。“这种增强效应更多被认为是由情感对记忆初始阶段编码痕迹的影响所造成”[13],若情感因素加入记忆编码过程,当记忆网络中的情感节点被激活时,相应的记忆也就能被扩散性地激活。
三、情感体验视域下公共事件的展示策略
在作出事实与理论分析后,本文将在方法策略层面展开讨论,探索一座具体的博物馆如何通过理念创新来适应当前社会赋予的文化责任和使命担当。此处将借用米哈利·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移情”(empathizing)与“外位”(outsideness)结合的理论作为情感体验的方式,以此来启发博物馆在公共事件展览中的范式转变。
(一)移情与外位理论
“移情”首先在德国美学领域出现,西奥多·立普斯(Theodor Lipps)通常被视为创立者和主要代表,此后经过不断发展,建立起庞大而影响深刻的美学体系。此外,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产品设计学等学科均从不同的侧重点丰富了移情理论。
移情大致可被概括为:主体受到对象事物的感染,设身处地地将情感移置到对象身上,与对象产生共鸣。孩提时代人类便有了这种联想和模仿的能力,人的生理系统和认知反应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为移情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可能性。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则为我们理解移情的机制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支持依据,“大脑皮层的运动前区有一个镜像神经元系统,它负责监控运动行为,在看到他人的行动、表情时,它会激活我们自身相应的行动与情绪神经机制,而产生‘切身’参与的感受”[14]。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表情或经历时,脑岛中的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开始使用自身的心理机制模仿他人,想象自身也在经历同样的事件,由此体验到他人的感受,走进他人的情感世界。这种对他人行为的“内模仿”为移情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佐证。
巴赫金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批判了以立普斯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美学(Expressionistic Aesthetics)单纯地陷于移情,在移情的基础上提出“外位”理论,并将移情与外位相结合。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的第一个因素便是移情,即“我”应该去体验他人所体验的东西,站到他人的位置,由此深入他人内心,似乎同他融为一体。“内心充分的融合是否就是审美活动的最终目的”[15]?答案是否定的。移情是审美观照中重要却并非唯一的方面,只发挥前奏的作用,在移情之后接踵而来的应该是客观化的外位,“站到他的位置上,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16]。在移情之后,要能回到外位于他者的自我上。只有从这样的位置出发,用自己的意识丰富移情所得的材料,方能从伦理、认识或审美等方面把握移情材料[17]。如果不能返回自我,那就仅仅是感染他人情绪,“体验他人痛苦如自身痛苦的病态现象”[18]。我们还应注意到,“移情和外位这两种因素在时间上不是先后接续的关系。我们坚持认为它们在涵义上是不相同的,但在实际的体验过程中却是彼此紧密交织、相互融合的”[19]。
也就是说,外位是指移情之外,主体跳脱到区别于任何人的个体视角的理性反思。与人类在孩提时代便具有的移情能力不同,外位是更高水平的、更深化的心理加工过程。外位离不开人类的个体差异性,我与他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距离,“我所看到、了解到和掌握到的,总有一部分是超过任何他人的,这是由我在世界上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位置所决定的”[20]。但是这种外位性不是孤立地使自己超越于他人之外,而是总与他人发生联系。
(二)移情、外位理论与公共事件展览
设计以移情和外位心理为基础的表现手法尤其契合博物馆公共事件题材的展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基于情感因素在公共事件表达中的核心力量;二是基于博物馆和观众对展品的关注,已从单纯对物的外在物质形态的观赏演变为对物背后隐藏的事件的关注;三是基于人的移情与外位心理过程的产生,是来源于事件而非物本身。观众移情与外位心理的产生表面上看可能由物引发,但落脚点终会回到其作为见证物所具有的特殊内涵上。虽然例外情况是人会对奇珍异宝产生珍爱之情,但是公共事件展览中的展品通常并不起眼,甚至有时是破败不堪的,人们之所以会对它倾注情感、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正因为它是事件的见证或情感的寄托,具有“超越物质功能的精神内涵”。此外,公共事件展览的叙事基础很独特,甚至可以说与常见的展览类型相反。通常情况下,物是展览叙事逻辑展开的根本,有什么展品就讲什么故事,围绕物来铺陈展览线索似乎理所当然,虽然现今已不乏对物背后的事件的展示,但其仍将物推向台前,将事件隐身于幕后。而对公共事件展览来说,事件才是叙事逻辑的主干,物成为了旁证。
移情手法虽然适合博物馆公共事件展览,但在实际设计应用过程中也会面临不小的阻碍。首先,“负面性”使得公共事件无论对展览表达还是对观众接受来说都具有难度。博物馆在长期的圣地模式中已经习惯了寻找人类文明成就的一面,更偏向纯粹正面的解读,然而历史并不总是光鲜亮丽或令人愉悦的[21],负面历史可能因长久失声而变得隐晦[22]。因此,负面历史的再现对博物馆来说或许并不得心应手、轻车熟路。就观众而言,他们对负面情绪的接受和理解也有困难,负面事件所带来羞愧、恐怖、愤怒、悲哀、煽情和偷窥等情绪会造成观者的心理负担[23]。其次,公共事件展览的宗旨绝非是对灾难和暴行的描述,而是对事件中那些团结向上的正能量的发掘。所以对最终的呈现来说,需要我们探索出以博物馆化手段实现“过滤消毒”的方式,将血腥暴力之地转化为可供公开的体验对象,将恐怖惨烈转化为温情、敬畏和尊重。此外,如果观众与展览的“情境距离”远,也会对观众的接受造成难度。情境距离是指移情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同移情客体的距离,不能简单地用时间空间距离来判断。情境距离远近可以由观众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亲历过展览中的公共事件来判断。没有亲历或没有相似经历的观众,其移情过程或许不如其他人顺利。如果公共事件与当今时隔久远或面临地缘阻隔,或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也会造成观众与展览的情境距离远,从而干扰移情。
那么,公共事件展览应该如何弥合情境距离、发挥移情设计的效果?总体路径是,博物馆要为所有观众创造心理层面的“亲历”,即主体在心理上虚拟地亲身经历某件事。即使在实践层面没有亲历,也能通过博物馆与事件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在展览设计时,并不是根据相关史料进行机械的解读,而是将原始信息以具有情节性的方式组织加工,让观众被这种拟真的情境引导,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通过联想来感受他人。
具体可采用角色扮演、体验平凡人物故事的方式。例如在想象展览公司(Imagine Exhibitions,Inc)的全球巡展“泰坦尼克号:你就是乘客”(Titanic the Exhibition:Where You’re the Passenger)中,每位观众进入展厅后,先在电脑上输入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电脑会客观地匹配出与该观众身份痕迹最为“兼容”的一名沉船事故受害者。随后观众将领取到一个“登船牌”,上面印有受害者的身份信息和与本次旅程相关的介绍,如船舱位置、出发事由、同行旅伴等,以此为线索展开体验。每个卡片代表一个震撼的故事,邀约观者从集体受害者中找寻、辨识、理解、保存那个与自己身份相似者的经历,一同经历最初的梦幻旅程和最后的惊魂一夜,并在结尾的纪念墙上查询他遇难或幸存的信息。
博物馆公共事件展览涉及重大社会议题,有时宏观政策导向难免被异化为空泛的文字、抽象的口号、宏大的歌颂。单一的宏观视角在某种程度上稀释了公共事件中情感的浓度,让“表彰先进式的图片和物资展”[24]显得单调且乏味,不能体现“个体叙述”的细腻性、典型性、鲜活性,很难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这也是当前中国此类展览面临的普遍问题。尽管呈现手段有所丰富、视角更为多元、内容更加充实,但总体尚处在探索阶段,相当一部分展览缺乏整体性的移情设计、依赖文字展板且习惯说教,难以与观众建立关联。
对家国情怀的演绎未必只能采用宏大叙事,“可能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对普通人生活点滴的关照……不仅需要‘望远镜’,也需要‘显微镜’”[25]。“基于真实人物的情境演绎,以个体命运呼应宏观的历史事件,既补充了宏观视野所缺失的信息细节,更让原本模糊抽象的历史变得鲜活,再通过身份赋予激发观众的参观期望及代入感,从而能更积极地参与讨论[26]。
移情手法在电影、戏剧、小说中被广泛使用,巧妙地引导人们逐步深入参与到剧情中。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博物馆移情与上述媒体具有显著区别:(1)博物馆有实物作为见证。物的展示与事件的叙事相辅相成,有充分说服力的证物胜过千言万语,寻找二者之间相互补充的契合点、将实物完美融入事件的叙事脉络,将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震撼。(2)博物馆对事实的呈现必须真实准确。夸张和渲染对于电影等媒介来说是增强艺术表现力的基本手法,但在博物馆中并不适用。详实完备的事实陈述、清晰系统的数据罗列、典型恰当的实物佐证是博物馆移情设计的前提。(3)博物馆移情需适度。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教育机构,不能盲目追求戏剧性的情感效果,必须保持适当的情绪强度。博物馆移情最终是为实现传播效益而服务的,过度的情绪唤醒会使观众完全被情绪左右,降低学习效率,也会影响场馆内其他观众的参观学习。(4)移情后的外位尤为重要。教育可被视为博物馆的重要功能,相比之下其他媒介的教育目的并不凸显,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娱乐方式。外位强调观众独立思考判断的过程,因此它的重要性应在博物馆中得到彰显。
借鉴巴赫金将移情作为思路起点而提出的移情与外位结合的理论,我们也应注意到移情对于提供观众内省经验之不足。博物馆展览如果只能让观众沉溺于情感的旋涡,即使再栩栩如生、真切动人,也不能被称为一个高层次的展览。让观众脱离故事的激情冷静下来,以反思的心态审视整个事件,更是博物馆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在这一点上,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史诗剧理论(episches theater)的核心——“间离化”(alienation effect),从创作者角度为外位提供了进一步说明。“间离化”就是创作者有意识地在观众与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观众能跳出单纯的情景幻觉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的人物和事件,恢复理智思考和评判,防止在情感上与剧作认同而麻痹了判断的力量。他认为“体验型戏剧”(experiential theater)的弊端在于使观众在强烈的共鸣体验中放弃理性思考,处于不清醒、无力批判的入迷状态,无法发挥戏剧帮助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教育功能。戏剧不只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反省,以帮助人们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27]。
“当观众的情感终于被唤醒后,若缺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情感发酵升华,情感的容身之所不在,依然稍纵即逝”[28]。所以,博物馆公共事件展览的策划者也应有意识地通过设计督促观众在高情感卷入度的参观体验中,不仅能收获一种泛化的情感共鸣,而且能将情绪与感受转化为积极行动的力量。在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叙述在大部分观众眼中带有国家叙事的官方色彩。尽管从单纯的物的展示到通过物来进行宏大历史叙事已经是一种进步,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历史叙述无不透露着一元权威的特征[29],尚未能形成对社会重大和敏感问题的讨论氛围。
外位与间离化创作原则的引入能够改变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让博物馆在遵从主流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上,避免固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导向和任何程度的灌输,避免展览沦为说教,在展览事件与观众之间留出了使意义松动的阐释空间,开启了博物馆与观众平等理性对话的通道。
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在“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Space Shuttle Atlantis)展览中,以亚特兰蒂斯号串起美国长达30年的航天飞机时代,其中的“永远铭记”(Forever Remembered)单元系首次对“挑战者号”(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和“哥伦比亚号”(The Space Shuttle Columbia)航天飞机事故进行展示。展览的最后以开放式结尾引领观众思索美国的航天飞机时代究竟是代表着崇高和探索精神的人类科技之光,还是劳民伤财、酿成悲剧的错误战略。
从实践角度来看,博物馆还可以采用投票装置、当代艺术、留言空间、互动社区等多种方式引导观众外位于展览事件,产生自主性思考。比如,上海科技馆在“命运与共·携手抗疫”展的出入口设计了“病毒是永远的敌人吗?”投票门装置;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裂隙”造型建筑虽然不是高大的建筑,但通过隐喻性的设计,以抽象和象征的手法触发了观众对人与自然、生命与死亡的思考;美国“9·11”纪念博物馆(The 9/11 Memorial&Museum)的方形深坑水瀑通过水流的动态和声音在喧嚣都市中营造了宁静的冥思氛围,让观众在反思中满足内心诉求;英国亚姆村瘟疫博物馆(Eyam Plague Village Museum)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社群讨论亚姆村民与黑死病斗争这一故事如何在新冠时期引发共鸣。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展览在力求观众感同身受的同时,又突破了简单的一元权威逻辑,悬置了主观原则和价值判断,用客观的态度、温情的解读引领观众。这样的方式让展览不局限于直白的事件回顾和对历史观点的单薄描述,在展示公共事件时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冷眼审视的距离感以及自省的立场展望未来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说,博物馆成为了记忆的创造者。
总的来说,情感体验视域下博物馆公共事件展览的设计宗旨“不单是将记忆予以停泊,并在场于此时此地,让观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使他们对展览事件的再体验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需要将观众的情绪从强调历史观看的方式中抽离出来,唤醒他们对历史的感知和参与感,让他们更为积极地联系自身,培养个体批判性思考的能力”[30],“在自主联想和思考中达到对历史和社会认知更深层次的思考。观众从汇集知识再达到形成自身理解,从而调整自身经验,最终成为自身认识的一部分”[31]。
由此,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展示成为了一个持续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巴赫金也注意到,“如果我们与他人融合为一,那么事件靠什么丰富起来呢?可贵之处在于保持自己的外位性”[32],看到他人看不到的新问题,产生新应答。此时,无论是博物馆还是观众,抑或是公共事件本身,都通过这种“增补性”得到了丰富和充实。
四、结语
时代在塑造博物馆,博物馆也应通过对公共事件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建构承担社会角色、服务社会发展。在展示公共事件时,博物馆应以更具人文精神的姿态出现,以情动人,通过“可信可感的事实考辨、生动丰满的场景观察与鲜活有趣的细节体验”[33],实现更容易被观众接受的呈现效果。许多成功的展示设计案例都证明了蕴含丰富动人情感信息的展示能引起观众的关注和触动,情感因素对观众认同展览主题及展览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博物馆参观不只是一个让观众接收稳定、完整、确切的事实的知识性过程,也是一个提供情境让观众自己去理解、感悟的情感性过程,尤其对于公共事件这一特殊的展览主题,应在感性的移情与理性的外位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智识上、情感上、思想上建立一种与观众的内在契合。
本文或许只能提供一种思路,在真实的公共事件展览策划中,博物馆仍有大量具体的工作要做,而且任何方法都会存在缺点和盲区,这也要求我们继续探讨这一诠释工具的局限性与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