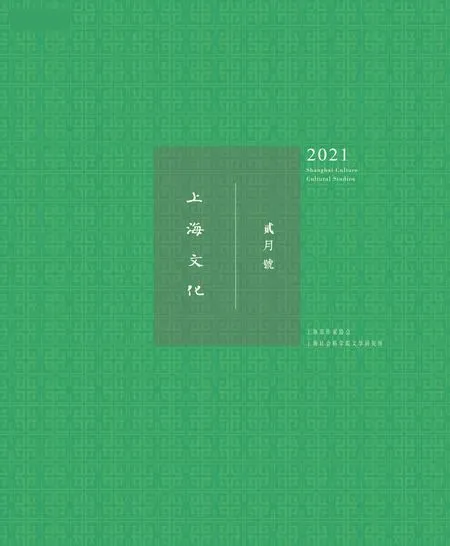踵事增华:沪上梨园竹枝词与风土诗歌的都市化转型
2021-11-25李碧
李 碧
竹枝词自盛唐文人听歌记闻或采歌入诗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与地域文化的传播有着不解之缘。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竹枝词已经跳脱了“棹歌”“舫歌”“渔唱”等乡土地域的定位,陌生化为描摹山川风物、百业民情、风流韵事等多方面社会内容的“竹枝体”,常被冠以“百咏”“杂咏”等称,其内容和表现手法均与传统竹枝词相同,但在诗境上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开拓。沪上梨园竹枝词的生成便是传统竹枝词迈向都市书写的典范,报刊等新媒体的推动、租界文化的包容、商业消费模式的构建,在带给戏曲更多可塑性空间的同时,也推动了以竹枝词为代表的风土诗歌的都市化转型。
一、新媒体的推动与梨园竹枝词的创作空间
清代中前期着意以竹枝词刻画戏曲的诗作并不多,笔者据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统计,其所收4000余首竹枝词中,直接以戏曲演出为主题创作的不足1%,另有散见于清人诗文集中的零星之作。这一时期竹枝词的创作涉及宫廷演剧,如康熙万寿有“千秋令节艳阳天,歌舞分班行殿前。此日球场开牧马,更无台阁立飞仙”。①陈金浩:《松江衢歌》,顾炳权编:《上海历代竹枝词》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12、13页。民间则流行“三里一台”的说法,如观玉仙演《葛衣记》有:“三里歌台未足奇,梨园只惜玉仙稀。垂帘择得乘龙婿,院本当场笑葛衣。”②陈金浩:《松江衢歌》,顾炳权编:《上海历代竹枝词》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12、13页。更多的民间演剧涉及节庆与祭祀,如春日搭台演戏(即春台戏)有:“春台好戏各争强,忽听新音韵绕梁。多少名班齐压倒,让他串客暂逢场。”①陈祁:《清风泾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历代竹枝词》上册,第102页。楼船戏有:“学士文佳碑石刻,院传仁济住黄冠。药王诞日楼船戏,即在高王庙畔看。”②沈蓉城:《枫溪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历代竹枝词》上册,第116页。还有文人雅集的演剧,如施绍萃工词曲,曾自制一舟,取名“随庵”,并邀好友与伶人共同载酒为乐,竹枝词有:“一天花影寻毵毵,峰泖云霞次第探。郎谱新词侬按拍,兴来携客上随庵。”③丁宜福:《申江棹歌》,顾炳权编:《上海历代竹枝词》上册,第185页。如此等等。梨园竹枝词的创作仍处于散点视角,既无戏曲发展的宏观把握,对演剧细节的关注也不够深入。随着晚清戏曲发展迎来又一高峰,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下,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为竹枝词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申报》在创办时便刊登了《申报馆条例》,其中明确了收稿标准:“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④《申报》1872年3月23日。因报纸面向的读者层面较广,传统文人诗只能与部分读者产生共鸣,竹枝词和长篇叙事诗在内容上更容易理解,创作要求也相对简单,展现的风物民俗还可开拓读者的视野,在创办之初便纳入了刊载视野。报纸上刊登文章往往要收取一定费用,而竹枝词类作品“概不取值”,即免费刊登,吸引了更多创作者纷纷投稿。几十年间,《申报》刊登的竹枝词作品涉及民俗民风的方方面面,成为此类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中以戏曲类竹枝词的创作为最盛,最早在《申报》见刊的有关戏曲的竹枝词为《沪北竹枝词》和《续沪北竹枝词》,以后者为例:
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
街头招贴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
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
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酒馆方阑戏馆招,才生弦索又笙箫。
无端忙煞闲身汉,礼拜刚逢第六宵。
案目朝朝送戏单,邀朋且尽一宵欢。
倌人请客微分别,两桌琉璃高脚盘。
戏园请客易调停,酒席包来满正厅。
座上何多征战士,纷纷五品戴花翎。⑤忏情生:《续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18日。
这组诗记载了海派京剧生成之前,京师梨园南下初期对上海梨园文化产生的冲击,以及观者对京剧的追捧和喜爱。《五彩舆》本属徽班传统剧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由春台班搬演,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道咸年间曾于宫廷演出此剧,《故宫珍本丛刊》收其脚本,光绪间由四喜班发扬光大,名角王九龄、孙菊仙、梅巧玲、王瑶卿、马连良均演过此剧,后福寿班、富连成班亦排演此剧。《五彩舆》是最早传入上海的京剧连台本戏之一,组诗第一首可推知此剧传入上海的时间约为同治十一年(1872年)前后。其所演海瑞到严嵩府上拜寿,因忤逆严世藩而被贬淳安事,是为大众所熟知的历史题材,涉及人物众多,非大型戏班不能承演,因而此剧制作相对精良,在上海掀起一阵热潮。据张红考证,传世的《五彩舆》版本有脚本两种、马连良藏十本戏版本及车王府藏十六本戏版本,①参见张红:《〈五彩舆〉连台本戏研究》,《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诗中提及的十本戏版本内容或与马连良藏本相近,但应不同于北京曾上演的徽腔版本,而是皮黄版本。组诗第二首中直言“一般京调非偏爱”,可知京剧在上海受到欢迎并非皆因声腔,除了如《五彩舆》般丰富多彩的连台大戏能够大开眼界之外,还有名伶的个人魅力。如隶属丹桂园的武生名角杨月楼,曾于上海梨园风靡一时,唱念讲究,仪表堂堂,有“天官”之誉。京剧的演出吸引了大量观众,有些伶人或戏班纷纷效仿,“好是吴中窈窕娘,春风一曲断人肠。只因听惯京班戏,近日兼能唱二黄”。②袁翔甫:《续上海竹枝词》,《申报》1872年4月12日。就连昆腔名剧《玉堂春》也可以京腔唱之,且愈加得以弘扬,正所谓“花样翻来局局新,京腔同唱《玉堂春》”。③浙西惜红生:《沪上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7日。组诗后三首可见京剧在上海流行初期观者甚众,且观者身份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无业游民,皆以看戏为日常休闲娱乐活动,竹枝词中亦有“第一开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姨娘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园”。④黄燮青:《洋泾竹枝词》,《申报》1874年10月17日。而戏园吸引观众的方法之一就是早早送上戏单,竹枝词还有“清早纷纷送戏单,新来角色大奎官。恰逢礼拜无闲事,好把京班仔细看”⑤梦兰仙史:《洋场杂咏》,《申报》1874年6月7日。等句,戏单可谓戏曲广告的雏形,其中受邀最勤的为妓馆,竹枝词云:“日日频将戏目分,偏于妓馆最殷勤。声声小姐来相请,今夜新灯好戏文。”⑥张春华:《洋场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12日。以丹桂茶园为代表的京班演剧获得了巨大成功,加之常邀三庆、四喜等京班名角至沪上演剧,京班对上海的昆班、徽班皆形成了冲击。大众审美趣味皆向京剧转变,“俏眼斜睃不自禁,先生也许订知音。为郎爱听京腔调,不弄琵琶换月琴”。⑦锄月轩居士:《申江竹枝词》,《申报》1872年11月11日。在此过程中昆腔式微,一度难以在梨园生存,“共说京徽色艺优,昆山旧部倩谁收。一枝冷落宫墙笛,白尽梨园弟子头”。⑧葛其龙:《前后洋泾竹枝词》,《申报》1881年5月8日。
《沪北竹枝词》和《续沪北竹枝词》中勾勒描绘了形形色色的都市文化生活,戏曲被视作其中一隅,仅仅经过两年时间,1874年2月5日《申报》便刊登了署名“松江养廉馆主”所作的《上海茶园竹枝词》,凡29首,再现了梨园演艺的繁盛景象,涉及戏曲文化的诸多面向。此后,竹枝词创作多以主题进行划分,如烟馆竹枝词、女弹词新咏、沪上青楼词、香国流民乞食词等,梨园竹枝词也走上了专题创作道路,甚至单独结集出版。以朱文炳的创作为例:
菊仙名角信非虚,声调悠扬气展舒。
一样内廷老供奉,叫天相较果何如。
灵芝草木有三人,昔日京华赏鉴真。
海上仅来崔氏子,擅场第一《玉堂春》。
大观名角紫金仙,小鸟依人亦可怜。
还有三花李百岁,戏迷传亦各完全。
当日春仙邱凤翔,戏中常供夜来香。
书生酸态描摹透,女子神情亦会装。
伶隐争夸汪笑侬,悔从宦海卜遭逢。
做官做戏何分别,下得场来孰改容。①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28、281页。
(1)重视手段忽视内在教学内容的改革。近年城乡规划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上更多的是强调教学手段的信息化,如微博信息平台互动教学的利用、微课教学形式的增加等,而对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对本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今后城乡规划职业的影响探讨较少。
除前文提及的杨月楼外,沪上梨园的名角名家如百花齐放,这组诗中勾勒出的梨园名家群像,每首诗均围绕一位伶人的技艺、样貌或擅长的剧作展开,兼及生与旦、文与武,未见创作者自身的审美趣味和观剧倾向,较为客观地展现了大众审美风尚。正是诗人将主体性抽离于作品,才使得竹枝词实现了诗史功能,将戏曲艺术的发展状态客观直接地记录和保存下来。
二、租界文化与戏曲艺术的可塑性
正如霍塞所言:“(上海)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②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纪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页。在纷纷涌现的娱乐行业中,戏曲也争相挤占市场。租界设立以后,因其有别于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在战乱中为文化传播营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19世纪60年代后,租界内的娱乐场所数量激增,茶馆、酒馆、烟馆、妓馆、戏馆、赌馆等大量开设,“昔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则曰:下有申江”。此时的戏曲演出也呈现出“书场唱晚,响闻宝善之街。京戏偷看,挤断百花之里”的繁盛景象,竹枝词中对此时戏曲演出的盛况有大量的描绘,正所谓“洋场处处是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处处似元宵”。③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
租界中开放的社会风气,改变了“男外女内”的传统社会观念,推动了女伶演剧及男女合台演出。尽管女伶演剧在戏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零星记载,但多出现在家班或被视作“官妓”,并未面向广大观众进行商业性演出,而真正的商业女戏班最先兴起于上海的租界之中。同光年间,租界出现了女伶演唱京戏,起初被称为“髦儿戏”。髦儿戏多为十二三岁女童登台表演,既方便女眷观剧,又不要求一定搭有较高的戏台,多盛行于堂会演出,后由满庭芳戏园名角桂芳将其带入商业演出的视野,竹枝词有载:“月中丹桂舞衣凉,坤角登台满庭芳。大戏亦教题桂字,取名应啖木犀香。”④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28、281页。坤角登台给观众带来了新鲜感,一时间形成了新的观剧热潮,“其时人心寂寞已久,忽然耳目一新,故开演之后,无日不车马骈阗,士女云集”。⑤佚名:《女伶将盛行于沪上说》,《申报》1899年12月9日。髦儿戏的演出内容丰富,演员风貌佳音,都成为吸引观众的看点,“髦儿戏俏听人多,一阵笙箫一曲歌。风貌又佳音又脆,几疑月窟降仙娥”⑥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二,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56-157页。“髦儿新戏更风流,也用刀枪与戟矛。女扮男装浑莫辨,人人尽说杏花楼”。⑦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可知髦儿戏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已在杏花楼进行比较成熟的商业演出,其中男性角色亦由女伶反串,且有武戏。“鸿福班头吴月琴,亏她色艺本双清。当场演出《天门雪》,试问梨园有几人。”⑧蒲郎:《上海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517页。吴月琴的《天门雪》演出一度问鼎梨园,达到髦儿戏演出的巅峰。继杏花楼之后,不同的髦儿戏馆之间竞争激烈,“髦儿戏馆各知名,丹凤群仙各竞争。漫道晓峰音调好,少娥亦是女中英”,①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29、229、194页。其中较为知名的为丹凤楼和群仙楼,各具特色,不相上下,观者趋之若鹜,一时风靡沪上。
作为典型的男女合台演出的花鼓戏,在民间演出过程中屡次遭禁,“花鼓戏传未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于乡野,继于镇市,始盛于村俗农氓,继沿于纨绔子弟”。②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第10页。早期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曾有“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③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第253-254页。之句,当花鼓戏由乡野走向都市,依然屡禁不止,租界也曾在清政府的照会下查禁花鼓戏,但始终网开一面,花鼓戏一度改称为“滩簧”以求存,竹枝词中对“花鼓戏”和“滩簧”均有记载,前者有“畅月楼中集女仙,娇官唱出小珠天。听来最是销魂处,笑唤冤家合枕眠”,④云间逸士:《洋场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58页。后者有“滩簧曲子自成腔,五凤楼中竟少双。编得淫词供俗赏,一班游女兴难降”。⑤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29、229、194页。由两首诗中的描述可知,花鼓戏不仅在都市文化中受到广泛认同,且在上海的禁戏力度并不大,给予了花鼓戏发展的空间,畅月楼和五凤楼更为花鼓戏的演出搭建了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坤伶登台,演技精湛的名角也受到追捧,竹枝词“女伶封王”有云:“寻常一辈少年郎,喜为坤伶去捧场。金字写来如斗大,崇衔唤作某亲王。”⑥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332页。而在清政府的严格禁令之下,北平梨园直至民国初年才开始有坤伶演戏,“民国初元,平市始有坤伶之发现……老俞之子俞五见有机可乘,遂尔招致坤伶,借以标新立异。当时递呈警厅,请解坤伶入京之禁。批准后,即在香庙建一戏棚,仿外埠男女合演之例”。⑦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戏剧月刊》1928年第1期。
沪上登台演出的另一新兴群体是串客和票友。所谓票友,即“不以优伶为职业,以道乐而学戏剧者,成为票友。南方名:清客串”。⑧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鹿原学人编译,上海:启智印务公司,1927年,第123页。“票房之创,肪于北直,风尚所趋,爰及上海。”⑨义华:《上海票房二十年记》,周剑云编:《菊部丛刊·歌台新史》,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年,第16页。光绪间,上海成立了专业的票房“盛世元音”,由盖叫天、赵小廉等名伶指导,成员皆为戏曲爱好者。此后还有市隐轩、雅歌集、遏云集等知名票房,玩票成为上海剧坛的另一片阵地。竹枝词诸如“残蜡人多串戏来,皖南野鹤亦登台。当场一出《胭脂虎》,喝彩声声震似雷”“逢场作剧便忘形,海上名流学老伶。优孟衣冠梁梦影,先生女生总明星”,⑩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29、229、194页。不论是富绅堂会还是专门的票房演出,每每有某先生或某女生之类的名流登台。民国时,雅歌集票房还成立了专刊《雅歌集特刊》,串客和玩票成为职业演出之外的演剧新风尚。
西风东渐的过程中,先进科技传入中国,上海的都市文化以其独有的包容性推进了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出中曾以真马、真虎等大型动物登台,以增强戏剧的真实性,当西方的马戏传入中国,为中国的表演艺术开拓了视野。1882年,号称“天下第一马师”的意大利马戏表演家车利尼到上海演出时,《点石斋画报》刊载竹枝词有:“绝技天然出化工,虽云戏术亦神通。可知事到随心欲,猛兽也将拜下风。”“海外名班车利尼,象狮熊虎舞翩跹。座中五等分层次,信是胡儿只爱钱。”①辰桥:《申江百咏》,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92页。其中将马戏也归为“戏术”,如“化工”“翩跹”等评点之语皆挪用中国传统艺术的评点语言。1908年,意大利人又在上海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继而美国人在上海创办亚细亚影片公司,电影以“影戏”的称呼定位,成为又一种流行“戏术”:“东西影戏到春申,活动非常宛似真。各式传奇堪扮演,一经入目尽称神。”②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二,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34、156页。影视文化的涌入给传统戏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眼球,也有一些伶人投入到戏曲题材的电影拍摄中。但毕竟电影的制作成本比较高,一些名伶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有选择转向灌制唱片,为近代戏曲艺术留下了珍贵的有声资料。竹枝词“留声机器行”条便对此进行了记述:“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关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箫锣鼓一齐鸣。”“买得传声器具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③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二,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34、156页。留声机在给受众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满足了足不出户即可听曲的需求。从演剧群体的扩大到全民参与,再到中西合璧,短短数十年间,戏曲以其极强的可塑性在租界文化的滋养下迅速发展。
三、商业驱动与梨园消费文化的建构
京师梨园南下之前,上海的演剧场地多为茶楼或戏棚,比较简陋,有的甚至为露天舞台,北京戏班将京城戏园的气派带到上海。红桂茶园为上海第一家较为气派的戏园,将“茶园”代指戏园亦源于北京,“据闻清代乾隆盛时,前门一带戏园林立,极歌舞升平之胜,而皇室贵胄八旗子弟征歌选舞毫无顾忌,致为纯庙所闻,赫然震怒。有旨八旗都统约束各旗并招五城察院勒停戏园……嗣以皇太后万寿御制戏曲,传集名伶进宫演唱,藉伸庆祝。由是禁令渐弛。前门一带昔时歌舞之场遂得重振旗鼓,开台再演。惟不敢显违功令,乃改头换面,避旧日戏园之名,易其市招为茶园。并称戏价曰茶资,世世相沿,即上海戏园亦援京师成例”。④《戏杂志》1923年第9期。此后名称各异的茶园在上海滩上纷纷建立,据统计,从同治初年到宣统年间,上海的职业戏园约120家,其中最著名的丹桂、金桂、天仙、大观合称为“清末四大京班戏园”。
飞座:青鸟何曾一柬通,酒坛蓦地集飞鸿。深心不肯多留恋,恐有新人在意中。
留条:人来不速静无哗,莫道疯狂错认衙。拼却十千沽美醉,樽前添得一枝花。⑦艺兰生:《宣南杂俎》,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第514、514、514-515页。
酒席间如有伶人为他人所召,客人便隔座相问,名曰“飞座”;为避免伶人错认座席,便在官座上留有便条,便于辨认,由此生成“留条”之规;此外还有“挑眼”,即指客人别有所属,伶人间相互妒忌的情状,等等,此类行话中充斥着浓重的商业色彩。伶人侑酒的商业利润丰厚,导致一时间童伶之风兴起,年仅12至16岁间的伶人纷纷站台,流连于商贾豪客之间,成为商人阶层炫耀财富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雏伶正处于学艺的起步阶段,便沦为戏班老板谋求戏外之财的工具,极大地影响其演艺水平,声音细弱,不识音律,舞台功底逊色,台上功夫的欠缺都靠台下侑酒来弥补。
大型戏园一般单独设置“官厅”“包厢”,若普通观众多付戏价,想得到更舒适的待遇,戏园又有“楼厅”“边厅”,可以“包定房间两侧厢,倚花傍柳大猖狂。有时点出风流戏,不惜囊中几个洋”。⑧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可见观者为得欢愉,包厢观剧是比较普遍的。观剧往往携妓侑酒,谓之“叫局”,“一阵花香香扑鼻,回头行过丽人来。吴娘唤到淡妆同,醉脸霏微浅露红。隔座忽传鸳牒下,花香钗影去匆匆”。①花川悔多情生:《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9月9日。从竹枝词的描绘可知,邀妓观剧的场景频繁出现,即便同时同地观演同一部剧,同一位妓女也可能收到不同的邀请,于是在演剧时奔波于不同包厢之间,如台上伶人换场一般,俨然已经成为戏园的另一道风景,人们争先光顾观演的热闹场面被概括为:“丹桂园兼一美园,笙歌从不问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断魂。”②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18日。也有携妓观剧避人耳目选择包厢就座的,“茶园丹桂满庭芳,到底京班戏更强。出局叫来终不雅,避人最好是包厢”。并注:“包厢,在台之两旁,有门可避人,伴妓共肩者,都掩饰于此。”③洛如花馆主人:《春申浦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64-65、65页。妓女伴座时还提供水烟,“偶闻新戏便伤哉,怕向园中看一回。只恐尊亲人在座,娘姨装过水烟来”④洛如花馆主人:《春申浦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64-65、65页。“锣鼓声喧戏上场,阿侬最喜坐包厢。装烟大姐直忙煞,才罢张郎又李郎”。⑤苕溪醉墨生:《青楼竹枝词》,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91页。在陪同看戏的过程中,如果客人不熟悉戏情,妓女还为其详细讲解剧情,竹枝词有:“邀同看剧包厢楼,促膝殷殷体态柔。节拍新掐浑未识,娇声为我说从头。”⑥辰桥:《申江百咏》,顾柄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05页。此时的戏曲演出作为商业运营的一部分,其利润来源不仅是一张戏票的价格,更多来自于叫局、侑酒等,用丰厚的盈利再对戏曲演出进行反哺和包装,台上之戏得以不断精进,使得戏曲文化产业走向良性循环。
四、风土诗歌在都市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张力
《文选·序》有云:“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页。竹枝词本由巴蜀民歌发展而来,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常在描摹世态民情中呈现出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自《申报》公开征求竹枝词与长篇纪事诗相关稿件以来,大量描绘上海都市生活的竹枝词创作涌现出来,客观上促使竹枝词脱离了乡土气息,转向都市书写,在都市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竹枝词中大量记载了近代上海戏曲的变革,包括京师梨园南下、伶人技艺与舞台生涯、戏曲评论等,客观反映出沪上梨园的发展变化状况,以及都市社会文化对戏曲发展进程的影响。在海派京剧诞生之前,京师梨园南下为海派京戏的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传统戏曲近代化的先声,但在戏曲史研究中因其处于过渡性阶段而较少受到关注。《申报》创刊之初便有多首竹枝词围绕京戏南下而撰写,其中涉及最早由北京传入上海的京戏连台本戏、京戏名角到上海演出情况,以及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等等,这些都为海派京戏的生成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竹枝词的书写还伴随了海派京戏的发展、昆曲徽班的衰落等,种种戏曲变革尽收眼底,连缀起来可形成一部小型的晚清民国上海戏曲史。
其次,竹枝词中描绘勾勒出梨园都市化、商业化的共享文化空间。清代中前期的观剧活动多为家班演出,后逐渐演变为堂会演出,甚至是私寓性质的演出,观者数量均控制在较小规模,几乎未见大规模的商业性演出。上海的满庭芳、丹桂茶园等大型娱乐场所的开设,以及租界对大众娱乐的跨文化包容,开创了观看戏曲演出的新范式。戏园设计宏大奢华,观众席的设置可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剧场中相应提供各种服务,观众和演员亦可近距离接触,戏园逐渐成为综合性娱乐消费的场所,既可满足观剧听曲的审美需要,还成为商人、仕宦炫耀财富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新平台。竹枝词中记录了这一共享文化空间生成的细节过程,生动再现了沪上梨园的繁华景象。
最后,戏曲文化空间的嬗变彰显了近代都市社会观念的变迁。上海素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伴随戏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每一次变革不仅是审美层面的创新,更蕴含着观念的变化。女伶登台演出极大地挑战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自同光年间始,上海梨园不仅出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演出班底,还支持男女同台的演出形式,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上演员性别结构单一化的格局。舞台上的坤伶演出不仅实现了女性自身的解放,还起到了启迪民智的作用。众多女性观众步入戏园,舞台上的戏曲故事丰富了她们的视野,舞台上的伶人也使她们意识到女性的社会作用不只是局限于家庭角色,甚至许多闺阁小姐与贵妇都曾以串客或票友的身份亲身登台,内心的解放意识以此得到宣扬。买办和富商对公众娱乐产业的经济支持也体现了近代工商观念和商贾阶层社会地位的变迁。当西方近代工商观念传入中国,最先受到影响的都市便是上海,事实上,商人是推动晚清上海戏曲变革的最主要消费者和核心力量,其推进方式不仅在于投资兴建大型戏园,还效仿明清时期的贵族、文士与伶人过从甚密,进行一系列捧角活动,在产生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一度成为其跻身上层社会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