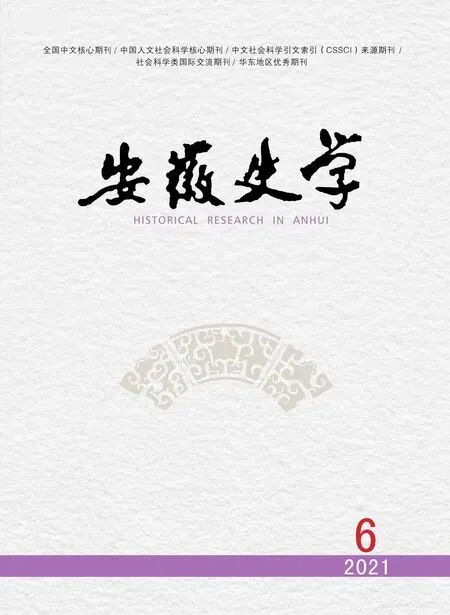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
——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2021-11-25王璐
王 璐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同治十三年(1874)无锡善士余治(1809—1874)因往来沪苏各地筹办慈善事务劳累过度于苏州病逝。其劝善之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经学大师俞樾(1821—1907)称:“莲村余君卒于苏州,苏之人无识不识,咸大息曰:‘善人亡矣’。”(1)俞樾:《例授承德郎候选训导加光禄寺署正衔余君墓志铭》,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5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作为晚清江南地区最著名的善士之一,学界对余治的劝善活动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2)黄鸿山、王卫平:《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王卫平:《晚清慈善家余治》,《史林》2017年第3期;赖进兴:《晚清江南士绅的慈善事业及其教化理念——以余治(1809—1874)为中心》,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刘昶:《晚清江南慈善人物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相关成果普遍认为余治是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在晚清时期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晚清慈善群体,共同推动了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明末以来江南劝善传统中还存在另一股力量,即以高攀龙等为代表的儒家下层经世运动,他们的劝善思想既与袁黄有显著差别,又同样与16世纪以来的儒家宗教化转向密切相关,且其活动地区亦集中在余治生活的江南一带。已有学者注意到晚明与晚清两个时代有着类似的积弱多病症状,其最终根源都在于县一级以下的基层组织脆弱而缺乏有序的构造(3)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348页。,但对这两个时代儒者劝善思想的比较研究仍值得深入。综上所述,我们尝试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以明末以来儒家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为背景重新探讨余治在江南劝善传统中的定位,并通过考察其劝善思想,揭示晚清以来地方劝善活动中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新动向,以期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余治劝善思想的重新定位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最为兴盛,这不仅与江南地区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有关,还有赖于前赴后继的善士群体,他们中大部分人为科举出身的儒家士人,其中既有如高攀龙(1562—1626)、袁黄(1533—1606)等高中进士并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士大夫,也有如陆世仪(1611—1672)、陈瑚(1613—1675)等功名低微的地方儒者。研究余治的现代学者经常提及晚清文人叶裕仁(1809—1879)的一段话:
吴江袁黄氏,生明之季,以祸淫福善之说化人,人从而化之。郡中彭氏,生重熙累洽之世,衍其绪论……功甫潘先生惄然忧之,得汪君石心为之助,宗净土之教,以之修己而劝人……于是莲村余君亦行其道于澄江梁溪之间。(4)叶裕仁:《尊小学斋集·跋》,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40页。
在叶裕仁看来自晚明袁了凡以来江南地区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劝善传统,现代学者遂以这段话为依据,将余治置于以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叶氏提及的余治之前的几位劝善人物都热衷于佛教活动:如袁黄有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以及刊刻藏经的经历;(5)参见何孝荣:《论袁黄与佛教》,《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彭绍升(法名际清,1740—1796)于34岁时受菩萨戒皈依净土宗,并编撰了著名的《居士传》;(6)参见胡艳杰:《彭绍升佛学思想探微》,《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潘曾沂(号功甫,1792—1852)晚年笃信佛教,自号复生居士,并以佛教为三教最终归宿;(7)邵佳德:《潘曾沂的信仰与生活世界:兼论清中叶江南的居士佛教》,《民俗曲艺》第204期,2019年。感谢南京大学哲学系邵佳德副教授为本文提供相关研究线索。汪天麟(号石心,1802—1863)为学颇出入二氏,《净土圣贤录续编》中有据其所述的居士传记。(8)顾广誉:《平湖顾氏遗书·悔过斋续集》卷6《汪石心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8—689页;胡:《净土圣贤录续编》卷2《往生王臣第三·张师诚》,《续修四库全书》第12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但翻阅余治文集及时人文献,却无法找出他参与佛教活动的明确证据。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异提醒我们,叶裕仁及现代学者对余治在江南劝善系谱中的定位或许与其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
王卫平先生曾指出,晚明时期士大夫在重建传统道德与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形成两种不同力量,其中崇奉阳明心学者与佛、道合流,强调行善积德、因果报应,而坚持程朱理学者则维护儒学正统,将救助贫困视为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前者以袁黄为典型,后者则以高攀龙、陈龙正为代表。(9)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这一观点具有启发意义。高、陈所创办的无锡、嘉善同善会在明清江南慈善事业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10)[日]夫马进著、伍跃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2—88页。,与袁黄等行善积德以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劝善活动不同,高攀龙等人的劝善动机主要来自儒家的经世理想,不妨称之为儒家劝善经世传统,清初太仓地区的儒者陆世仪、陈瑚也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11)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368页。余治在文集中经常提及同邑的东林先贤高攀龙,并认为家乡学者在其精神感召下“大多以躬行实践,切问近思为正鹄,故梁溪一脉,直接程朱”(12)余治:《尊小学斋集》卷2《孙仰晦先生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3册,第68页。,显示了他对高攀龙的推崇。在余治编撰的著名章程类善书《得一录》中收录了许多高攀龙、陈龙正、陆世仪等人劝善活动的相关论述及高氏遗作(13)余治:《得一录》,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84册,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51—55、87—91、99—104、333—335、417—418、1021—1028页。,相较而言,余治在文集中不仅未提及袁黄,其善书《得一录》中也未收录袁黄的作品,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处提及袁氏。若按照叶裕仁及现代学者的看法,余治属于以袁黄为代表的劝善系谱,那么为何他却缺乏宣扬袁黄思想的自觉和热情?
袁黄的《功过格》本为佛门云谷禅师所授,其原则是以所行善事获得相应的福报(14)吴震:《关于袁了凡善书的文献学考察——以〈省身录〉〈立命篇〉〈阴骘录〉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功过格》自晚明以来风行一时,吸引了大批儒家士人。然而其记善邀福的道德功利主义,与儒家强调道德自觉的根本立场相悖,故此明清以来儒者对袁黄及其《功过格》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这些批评在余治看来未免矫枉过正,他以《易经》“积善余庆”之说结合历史上诸多感应事迹,证明“行救灾之道,必有救灾之福”,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袁氏记功录过,大小厚薄各有成格,造物若称量以相偿,诚未免沾沾作计较。”(15)余治:《得一录》卷5《救荒有福说》,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84册,第399—402页。可见面对来自儒家内部发起的对于袁氏《功过格》的激烈批判运动(16)赵园:《〈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余治尽管持同情态度,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表明立场,与《功过格》“沾沾计较”的道德功利主义划清界限,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很少积极宣扬袁黄的思想。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余治对自身劝善活动的定位,据友人齐学裘(1803—1882)记载,余治自称平生有四大愿:“一复小学,一行乡约,一毁淫书,一演新戏。”(17)齐学裘:《见闻随笔》卷1《余晦斋杂论》,清同治十年刻本,第12页b面、第11页b面—第12页a面。这四者均属于儒家维护礼教秩序的经世活动。余治的经世思想与其师承有关,他曾于29岁(1837)进入暨阳书院跟随李兆洛学习举业,李兆洛是清代提倡经世的著名学者,被视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18)刘兰肖:《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等都曾受其影响。余治对李兆洛的学行人格深为感佩(19)余治:《尊小学斋集》卷5《祭李申耆师文》,第107页。,后者曾鼓励他“立身行道,上慰先人,显亲扬名”(20)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14、337、322—324页。,有感于李兆洛之言他“始有济世之志”。(21)俞樾:《例授承德郎候选训导加光禄寺署正衔余君墓志铭》,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44页。
齐学裘提及的余治平生“四愿”正是他实现“济世之志”的主要手段。就劝善戏而言,余治认为:“乐章之兴废,实人心风化转移向背之机,亦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也。”(22)余治:《尊小学斋集》卷2《庶几堂今乐自序》,第69页。他不仅亲自创作了一系列劝善戏,且自筹资金排演推广(23)齐学裘:《见闻随笔》卷1《余晦斋杂论》,清同治十年刻本,第12页b面、第11页b面—第12页a面。,甚至临终前仍嘱托弟子推广新戏。(24)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14、337、322—324页。而乡约制度在清代逐渐沦为形式化的具文,其实际教化作用微乎其微(25)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336页。,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为安抚人心、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江苏各县纷纷延绅设局、宣讲乡约。(26)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6页。余治是其中的骨干人物,他不仅上书当道提出改革乡约制度的各项建议(27)余治:《尊小学斋集》卷3《上当事书》,第82页。,还曾于咸丰四年(1854)在江阴寿兴沙通过宣讲乡约捕获盗首(28)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14、337、322—324页。,证明乡约对于社会治理确有实效。而余治之所以提倡“复小学”也与当时士大夫们的影响有关,其师李兆洛就主张学者须笃实践履小学工夫(29)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20《杂著·小学问》,《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3册,第304页。,晚清理学名臣曾国藩(1811—1872)、龙启瑞(1814—1858)等也曾提倡刊刻推广朱子《小学》。(30)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卷1《钞朱子小学书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1册,第457页;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2《内集·重刊朱子小学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5册,第277—278页。但与上述官僚士大夫不同,余治长期担任乡村塾师,深知大部分贫家弟子就读乡塾二三载便废业归家,当时一般训蒙塾师只重句读识字而忽视道德培育(31)余治:《尊小学斋集》卷4《学堂讲语跋》,第93页。,他认为:“不于发蒙时明白开导,一过此时,嗜欲渐开,气质易变,骄心惰志已成习惯,万牛之力难以挽回。”(32)余治:《尊小学斋集》卷4《小学斋书林引言》,第97页。因此余治先后编撰了《续神童诗》、《续千家诗》等通俗易懂的蒙书,并在江阴创设简便义塾,采取短期训蒙的方式向乡村贫民子弟普及道德教育。河南按察使沈秉成(1823—1895)赞曰:“世之从事小学,能推行尽利,驯致乎补化善俗之盛者,未有能过余君者也。”(33)沈秉成:《余君年谱序》,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01页。
综上所述,余治的劝善活动似乎完全可以置于明末清初以来儒家劝善经世的传统之下。就乡约而言,高攀龙、陆世仪、陈瑚等都曾强调过宣讲乡约的重要性;(34)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第335—342、73—76页。就劝善戏而言,明儒王阳明、刘宗周、陶奭龄等都主张利用戏子、院本来教化人心(35)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第335—342、73—76页。,《得一录》中亦收录了他们的相关论述;(36)余治:《得一录》卷11《翼化堂章程·儒先论今乐》,第787—788页。就小学而言,明末清初的儒者也重视小学训蒙,如陆世仪的《思辨录辑要》中专列“小学类”,陈瑚则在其著名的《圣学入门书》中特设《小学日程》。那么为何时人及后世学者会将余治归于以袁黄为代表的劝善系谱中呢?这是因为在他几乎所有的劝善活动中都掺杂了大量的宗教成分,以至于无法将其思想与上述正统儒者相提并论。以下将着重讨论余治劝善思想中的这一面向,并通过与明末清初劝善思想的比较,揭示两个时代领导劝善活动之儒者思想的巨大差异。
二、余治劝善思想中的果报观念
前文提及余治为袁黄《功过格》的辩护,显示出他对果报感应之说的肯定,这与清代的思想氛围有关,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清代儒者的思想世界中充斥着鬼神、果报等富有宗教色彩的观念。(37)龚鹏程:《乾嘉年间的狐鬼怪谈》,《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80页。清代的这一思想现象原因非常复杂,此处不拟深入展开。大体而言,这一现象不仅受到明末以来宗教善书及民间信仰之影响,也与宋明理学乃至儒家思想作为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力量的衰落密切相关。如所周知,明清之际思想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即对心学末流空谈心性的普遍不满和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代儒家转而关注道德教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不少清儒意识到儒家所标榜的成圣成贤之理想对民众缺乏吸引力,如清儒朱彝尊(1629—1709)就对比了儒家与佛、道教在教化民众效果上的差异:
小人之为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胜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书》《诗》喻之,彼谓迂阔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说,无不悚然共听。非真穷其义而乐其言,无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与信而导之,则为力也易。(38)朱彝尊:《曝书亭集二》卷35《感应篇集注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52页。
宋明儒者普遍采取以气释鬼神的理性主义态度,德行的培养并不依赖于超自然力量,而应诉诸于道德主体的自发性。然宋明儒学的道德修养工夫又非常繁琐严格,对普通读书人而言尚显得虚悬高远,对下层百姓更缺乏吸引力。相较而言,宗教信仰中的诸佛众仙反而更具威慑效果。儒家在社会教化方面的困境,使得清代前期不少儒者转而肯定民间佛道信仰所宣扬的轮回果报之说(39)王世光:《前清儒者视野中的民间佛道信仰》,《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晚清余治的劝善思想中。
前文已述,宣讲乡约是余治劝善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他看来当时乡约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形式上逐渐废弛,其内容也过于陈旧无法吸引民众。(40)余治:《尊小学斋集》卷3《上当事书》,第85,82、85页。对此余治提出两点应对措施:其一,乡约宣讲应当“照寻常讲书之例,天理、王法、人情及一切善恶果报均可列入。”(41)余治:《尊小学斋集》卷3《上当事书》,第85,82、85页。实际上,明末儒者高攀龙、陆世仪等在宣讲乡约时已融入果报之说,对此会在后文详述;其二,以宣扬果报的戏剧辅助乡约,他提出:“若以乡约之法出之以戏,则人情无不乐观……耳濡目染之余,必有默化潜移之妙。”于是他创作了“善恶果报新戏数十种,一以王法天理为主,而通之以俗情。”(42)余治:《尊小学斋集》卷2《庶几堂今乐自序》,第69—70页。可见不论宣讲乡约或创作新戏,因果报应之说都是余治所极力标榜推行的观念。此外,余治还将果报之说引入小学训蒙之中,据齐学裘称:“其为教,虽初学童蒙,必日与讲孝子悌弟及善恶果报故事一二条。”(43)齐学裘:《见闻随笔》卷1《余晦斋杂论》,第10页b面。余治批评传统蒙书《神童诗》《千家诗》等无益于道德培育,却称赞善书“足为小学羽翼”(44)余治:《尊小学斋集》卷4《小学斋书林引言》,第97页。,在其所撰的训蒙教材如《续神童诗》中,随处可见“暗地勿亏心,须防鉴察神”“惜字一千千,应增寿一年”等表述(45)余治:《得一录》卷10《蒙馆条约·附续神童诗》,第749—756页。,与《太上感应篇》等善书几无二致。余治的教育对象多为乡村子弟,对于他们而言,祸福果报之说显然比儒家高远的道德理想更具吸引力,浅近直白的语言和报应不爽的简易逻辑,令其所撰蒙书受到地方乡塾的欢迎,并一直沿用到光绪年间。(46)钟鹤笙:《论学堂新法教授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此外,余治还试图借助官方力量推广善书,他曾上书当道倡立“教习小学规矩局”:“专以教习小学规矩,讲说孝子悌弟、善恶果报等事为主”,并主张刊刻善书“发各图蒙馆师,加以谕单,责成分讲。”(47)余治:《尊小学斋集》卷3《上当事书》,第83—84页。实际上,余治将善书及果报观念引入小学的做法并非独创,其师李兆洛就曾说:“《小儿语》浅而可味,《读书日程》塾师定课,《功过格》提醒此心,《人谱》伦常模范,皆本朱子小学。”(48)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20《杂著·小学解》,第311页。如所周知,刘宗周作《人谱》正是出于反对袁了凡《功过格》大谈果报的道德功利主义,但显然李兆洛并不认为二者存在根本差异,这从侧面反映出其对果报之说的肯定态度。此外,清儒陈文述(1771—1843)也认为:“善书所言,皆儒书之理,儒书散而善书聚,儒书深而善书浅……即塾师教幼童,亦易于讲解也。”(49)余治:《得一录》卷10《义学章程·设义学说》,第685页。由此可见,以善书辅助小学训蒙已是晚清儒者的普遍共识。
对比余治与明末清初的陆世仪、陈瑚关于小学训蒙的论述,会发现两代领导地方劝善活动的儒者思想存在巨大差异。有学者指出,陆、陈二人对鬼神果报等宗教问题发言非常谨慎,其基本立场仍属于宋代理学以来的儒家传统。(50)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第324页。这一立场也体现在他们关于小学的看法中,在陆世仪看来朱熹关于小学教育的诸多理念已不合于当时的现实环境,因此他提出应当辑录《仪礼》中的古代礼仪制度,参以近礼,以三字或五字节为韵语,编为朗朗上口的《节韵幼仪》等教化弟子,此外他还强调村塾教育应以识字记诵为主。(51)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小学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4—5页。陈瑚在其著名的《圣学入门书》中也设立《小学日程》,其内容无外乎孝悌顺亲、仪容恭敬等儒家礼教思想(52)陈瑚:《圣学入门书》,《丛书集成续编》第6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0—351页。,并以小学为“童蒙时养成圣贤胚胎”的手段。(53)陈瑚:《确庵文稿》卷26《圣经讲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页。对比陆世仪、陈瑚与余治关于小学教育的思想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都强调小学的重要性,但施教理念和内容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陆、陈看来小学是儒家培养圣贤胚胎的入门工夫,其内容毋庸置疑应以儒家礼教为主,而余治所推行的小学训蒙之内容已非纯粹的儒家礼教,而是混杂了善书及果报信仰的通俗道德说教,这显然与陆世仪、陈瑚将小学视为“圣学之基”的理念已不可同日而语。且与陆世仪重视识字不同,余治认为:“窃意童蒙入学,若但教以识字而不教以为人,则识字乃适足以济其为恶逞奸之具,反不如不识字之愚氓,犹知畏法守分也。”(54)余治:《尊小学斋集》卷4《学堂讲语跋》,第93页。
综上所述,相较于明末清初的地方儒者,余治的劝善思想中善书及果报观念所占的比重大幅增加,说明此时宗教信仰已无法忽视,儒家对下层百姓的道德教化不得不借助其力量才能推行。他将儒家培养“圣贤胚胎”的小学训蒙转变为杂糅果报观念的通俗道德说教,也反映出儒家经典不仅对下层百姓失去引导力量,在地方知识阶层中的实际效力也日渐衰落。明末到晚清领导地方劝善活动的儒者思想中的这种巨大转变,固然与儒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及个人选择有关,亦可折射出时代变迁对他们思想造成的影响。王汎森曾指出,晚清太谷学派将儒家的思想及仪式宗教化,是清季儒家在下层群众中引导社会道德的一种尝试。(55)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76页。余治劝善思想的上述特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将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尝试,然而他似乎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在宗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余治劝善思想中的救劫观念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的重要观念之一即“末世救劫”说,由于清代以来各地道坛的主要推动者是一批深受儒家科举考试教育的士大夫(56)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第42期。,他们在造作和推广善书的过程中将儒家思想融入其中,使得当时善书中的末世救劫观出现了新的特征。法国学者高万桑将这种新的末世救劫观称为“近代精英末世论”,他概括了清代救劫道书精英化的两个方面:其一,带有劫运时间推算的命定式末世论不再出现,而代之以根据世人改过迁善而决定是否降劫的机动性末世论;其二,祛魔法事与道教仪轨逐渐式微。(57)[法]高万桑撰、曹新宇译:《扶乩与清代士人的救劫观》,曹新宇主编:《新史学》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6—68、66—67页。可见所谓“精英化”的救劫思想明显带有儒家理性主义色彩。道光庚子年(1840)被视为民间扶鸾救世运动兴起的肇端(58)王见川:《汉人宗教、民间信仰与预言书的探索:王见川自选集》,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11—430页。,此后出现了一批由扶鸾著书或文人编撰制造而成的善书,这些善书普遍宣扬一种玉帝因人心恶化降下劫难,而神佛则不断借降鸾来劝人行善以救劫的说法。(59)范纯武:《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第117页。咸丰年间上海、苏州等地出现的《潘公免灾宝卷》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学界普遍认为此书为余治所作。(60)赖进兴:《晚清江南士绅的慈善事业及教化理念——以余治(1809—1874)为中心》,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第124—137页;Tobie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 s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8-46.
《潘公免灾宝卷》包括上、中、下三卷,上、中卷主要描述潘曾沂死后成为玉帝所任命的“东岳府总册房监察主”(61)《潘公免灾宝卷》卷中,光绪九年刻本,第20页a面、第7页a面—第20页a面、第23页a面—第24页a面。,于太平军攻占江南前后托梦降示要求世人劝善改过,下卷主要讲述潘公生前的劝善事迹。该书内容及语言通俗易晓,其中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宝卷宣称因太平天国战争受难的百姓是由于其自身的道德堕落和有负皇恩,因此劫难的根源“不关国运,实为下民作孽太重”;(62)《潘公免灾宝卷》卷中,光绪九年刻本,第20页a面、第7页a面—第20页a面、第23页a面—第24页a面。其二,宝卷主张以“恐惧修省,急速改过,立愿斋戒”来挽回天怒(63)《潘公免灾宝卷》卷上,第4页a面。,还记录了一位塾师受余治的《训学良规》启发立愿刊刻宣讲而免于受难的事迹;(64)《潘公免灾宝卷》卷中,光绪九年刻本,第20页a面、第7页a面—第20页a面、第23页a面—第24页a面。其三,宝卷记录了潘曾沂生前在义庄举办惜谷佛会时,拈香先拜龙牌再拜佛像,乡民请问其中缘由,潘曾沂答曰:“君在亲前,忠在孝上,若非皇上,佛堂也难以自立。”(65)《潘公免灾宝卷》卷下,第20页b面。尽管宝卷的救劫观念似乎较为符合“近代精英末世论”,但高万桑还认为这一末世论所强调的修德并非以儒家为主,而是以道儒相济的修身理论为基础的 “三教合一”的伦理说教。(66)[法]高万桑撰、曹新宇译:《扶乩与清代士人的救劫观》,曹新宇主编:《新史学》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6—68、66—67页。然而在上文列举的几处内容中,强调忠君和重视小学的儒家立场显而易见,这一特点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余治的《劫海回澜说》中。
有感于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灾难,余治在咸丰同治年间作《劫海回澜说》上、中、下三篇,贯穿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如何通过修德挽回“天心”以救劫。在余治的表述中,上天俨然是具有严密道德计算功能和强烈情绪的人格神,人类之所以遭遇灾难完全是由于自身的道德堕落,但他并未将救劫的希望寄托于某位神祇或乩手,而是诉诸于儒家的修身资源。《劫海回澜说上》称:“人苟能善承天怒,急急恐惧修省,亦安见不能感格者?终古无不可挽之天心。”(67)余治:《尊小学斋集》卷1《劫海回澜说》,第60页。“恐惧修省”的说法源自《周易·震卦》的象传(68)朱熹撰、蒋勇校注:《周易本义》卷1《周易象下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中庸》亦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6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页。可以说儒家一直存在着自我戒惧、省察的修身传统,《劫海回澜说下》继续发挥这一思想:“曾子之三省也,孟子之三自反也,此物此志也庶几哉!普天下言人心不好者,胥转而言我心不好也。一字之易而天地间之大转关,已在是也。”(70)余治:《尊小学斋集》卷1《劫海回澜说》,第63,63,59、61,59—60、62页。这种将祸福成败全部归结于个体自身道德修养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由来已久,如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1611—1674)就认为:“天之生人一而已,其有智愚贤不肖之异,孰为之?自为之也。尊卑贵贱于是乎分,成败祸福于是乎别,无非自者。”(71)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自箴(并说)》,《杨园先生全集》中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13页。此外,余治还采纳了晚明以来儒家的各种省过手段,提出:“今而后我将以我讼我也,我将以心治心也。方寸之地,我应自为对簿也;动作之间,我应自为较勘也。”(72)余治:《尊小学斋集》卷1《劫海回澜说》,第63,63,59、61,59—60、62页。然而在余治这里已看不到明儒省过工夫所追求的成圣成德之理想境界(73)参见王璐:《明代儒家省过工夫的发展脉络——以儒家修身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而是直接指向末世救劫的宗教目标,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修身救劫”思想。
余治在《劫海回澜说》中还提倡“斋戒祷求”“敬惜字谷”(74)余治:《尊小学斋集》卷1《劫海回澜说》,第63,63,59、61,59—60、62页。,其本人也力行斋戒、组织惜字惜谷会。(75)齐学裘:《见闻随笔》卷1《余晦斋杂论》,第10页a面;吴师澄:《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10页。据林荣泽和梁其姿的相关研究可知,斋戒和惜字都是清代民间社会流行的信仰实践方式(76)林荣泽:《持斋戒杀:清代民间宗教的斋戒信仰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34、242—243页;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93页。,其共同思路是积累功德以获得现实福祉,可见余治的修身救劫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民间信仰成分。这一点也体现在其与扶乩活动的关系上。据《松江府续志》记载,道光末年江南地区乩坛盛行。(77)光绪《松江府续志》卷40《拾遗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982页。苏州彭氏家族及彭绍升本人都与当地的扶乩道坛有关。(78)范纯武:《近现代中国佛教与扶乩》,《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据齐学裘记载,同治八年(1869)余治重病极危之时,友人在杭州扶乩占得乩文称:“莲花会上有奇人,可以留名可立身。若到水穷山尽处,自然携手出迷津。”(79)齐学裘:《见闻随笔》卷18《义仆陆庆断指救主》,第3页b面。之后家仆陆庆将自己手指砍断煎药,余治进服之后竟痊愈,此事被视为乩文应验在当地传为美谈,还有传说余治死后成为申江仁济善堂乩坛的“主坛之神”并降鸾开示。(80)范纯武:《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第102、104页。柯若朴曾指出,19世纪后期由文人领导的鸾堂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满足其成员自身超度的精神需求(81)[德]柯若朴(Philip Clart)撰、毛鹏译:《孔子与灵媒:“民间儒教”是否存在?》,曹新宇主编:《新史学》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第8、9页。,可以说扶乩降神在时人眼中已成为余治修德有成、实现自身超度的佐证。尽管余治文集中并未出现相关记录,但他对鸾堂扶乩应该并不陌生,不排除有参与的可能。
以上种种证据表明,余治已然脱离了儒家正统,深入到了宗教领域,这应当与近世三教会通的思潮以及晚清江南地区兴盛的民间信仰所共同塑造的“宗教心态”(82)蒲慕州:《历史与宗教之间》,三联书店(香港)2016年版,第4页。有关。但细察之却会发现,三教会通的笼统说法无法掩盖余治修身救劫思想中牢固的儒家立场,例如他极力从儒家社会教化角度对斋戒祷求、敬惜字谷等宗教活动的合理性加以解释(83)余治:《尊小学斋集》卷1《劫海回澜说》,第63,63,59、61,59—60、62页。,而以“恐惧修省”来挽救劫运的说法,更彰显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内在信仰对余治具有重要感召力。这种试图在民间信仰中确立儒家主导地位的倾向在清代中后期十分普遍,如19世纪许多将传统道德规范与关圣帝君崇拜相结合的新式鸾堂就自我认同为儒教(84)[德]柯若朴:《孔子与灵媒:“民间儒教”是否存在?》,第9页。,此外晚清不少善书也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如嘉道年间的善书《无欺老祖全书》分别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五常”为题统摄各卷教义(85)袁志谦:《无欺老祖全书》,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839—977页。,林则徐的幕僚徐谦(1776—1864)编撰的《奉圣回劫显化录》更出现颜子、孟子等孔门圣贤降示的乩文,并以儒家的道德教化及修身方法为主要内容。(86)徐谦:《奉圣回劫显化录》,《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11册,第399—486页。
余 论
在余治去世20年后,康有为写了一篇《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他先是称赞余治“实江、浙袁学之大宗,潘功甫、汪小石之后劲也。”接着却笔锋一转痛斥当时儒者:“近世沟犹瞀儒猎训诂名物之琐微,上不能施于国,下不能济于民。自张其门为经学,而托迹善士以为佛道余派,不齿大道。……或又以墨子目之,则蒙于道术者。”(87)康有为:《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康有为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康有为的打抱不平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余治在“善人”的盛名之下确曾面临不少非议,这些非议主要有二:一是将其视为异端墨家,如清末民初的柴小梵(1893—1936)就认为:“(余治)其为人大类墨翟”;(88)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4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另一类是将其视为袁了凡的信徒,如前述叶裕仁的观点。在儒家看来:“墨氏兼爱尚同而二本流祸,至于灭绝伦理,故孟子辞而辟之;袁氏屑屑于铢两功过以邀福利,使人昧于天命之本然,故儒者屏而弗道。”(89)叶裕仁:《尊小学斋集·跋》,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40—341页。因此同情余治者往往以时势所迫为其辩解,如彭氏家族的彭慰高(1811—1887)就称:“君遭时益降,不得已而托于因果报施之言,较墨氏而更下。”(90)彭慰高:《梁溪余君墓表》,吴师澄编:《余孝惠先生年谱》,第351页。然而在康有为看来,不仅古代圣王本就崇奉鬼神,而且在救世之道上儒墨两家并不存在分歧(91)康有为:《诸子改制托古考》《儒攻诸子考》,《康有为全集·孔子改制考》第3册,第36—37、206页。,因此余治并没有背离儒家精神。(92)康有为:《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康有为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晚清以来儒者对余治评价的转变颇值得玩味,这固然与康有为自身的思想学说有关,也涉及儒家思想与宗教互动关系的新转向。
实际上,明末清初儒者的劝善活动已采用果报感应观念引导民众道德,如高攀龙在《同善会讲语》中称:“家家良善,人人良善,这一县一团和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和气……若是人心不好,见识歪邪……便成了极不好的风俗,这一团恶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恶气……不知者皆谓气数当然,不知气数是人心风俗积渐成的。”(93)高攀龙:《高子遗书》卷12《同善会讲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第720页。陆世仪也曾说:“一国之人心不亡,则一国之福未艾也;一方之人心不亡,则一方之福未艾也。”(94)陆世仪:《桴亭先生诗文集》卷3《水村读书社约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册,第31页。可见,明末儒者在地方劝善活动中已宣扬通过教化人心来感召天和、挽救灾难的思想,这与袁黄宣扬行善积德的思想似乎并无本质差异,毋宁说他们只是引入果报观念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而到了余治那里则更进一步将上天视为人格神并公然采用宗教救劫的话语。对比明末清初到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思想,可以发现,不同于明末儒者谨慎地在儒家思想框架内引入果报感应观念以引导民众道德,以余治为代表的晚清地方儒者则尝试将儒家修身资源重新激活,并创造性地与宗教救劫观念相结合,形成一套以儒门为宗、杂糅宗教理论和民间信仰仪式的修身救劫理论。如果说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在前者那里表现为在儒家思想中引入宗教观念,那么在后者那里则表现为在民间宗教信仰中确立儒家的主导地位。
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也体现在清末民初涌现的道德学社、万国道德会等救世团体中,它们普遍以“孔孟之道”为宗旨,将道德修身以救世作为共同主张,同时热衷于扶乩、斋戒等活动(95)范纯武:《民初儒学的宗教化:段正元与道德学社的个案研究》,《民俗曲艺》第172期,2011年。,因此被学者认为保持了强烈的儒教特征。(96)宗树人(David Palmer),“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and Salvationist Religion:Historical Phenomenonor Sociological Category? ”《民俗曲艺》第172期,2011年。这股带有儒家色彩的民间救世运动在板荡的时代中自下而上、由地方席卷全国,为清末康有为等弘扬孔教提供了思想土壤,或许这正是以“狂者”著称的康有为会褒奖余治这样一个地方儒者的原因所在。值得玩味的是,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以失败告终,而地方儒者借由劝善活动所酝酿的儒家与宗教的新型互动关系却影响深远,其余绪波及至今,在香港、台湾等地仍相当活跃。这提醒我们有必要将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