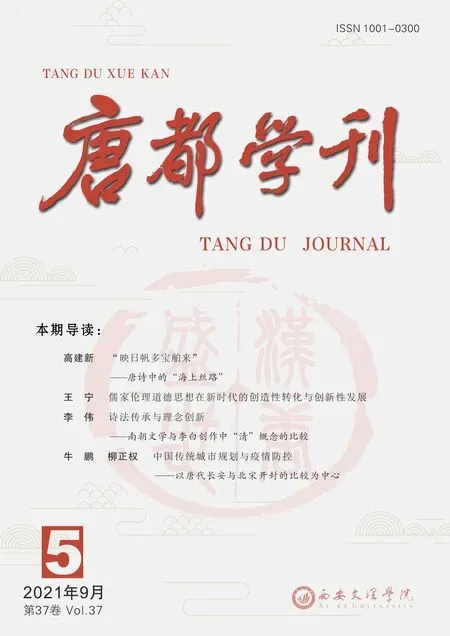汉族迁入少数民族型融合
——以秦汉时期岭南汉越融合为例
2021-11-25黎明
黎 明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互动和融合的发展史,许多古代少数民族融入汉族,部分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从历史上看,中华各族相互融合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二是汉族融入少数民族,三是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又可分为少数民族迁入汉族地区、汉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1]。
学术界关于民族融合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主要包括整个中国历史的民族融合[注]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载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载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载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某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注]参见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载于《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载于《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汪高鑫《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载于《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民族融合概念辨析[注]参见李龙海《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和民族文化融合概念辨正》,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王希恩《关于民族融合的再思考》,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金炳镐、毕跃光《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对于民族融合的类型却研究不多[注]民族融合类型研究仅有两篇论文。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方铁《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载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秦汉时期中原汉人迁入岭南与越人逐渐融合,是典型的汉族迁入少数民族型,研究这一问题对今日推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启发意义。
一、汉人南迁的前提:设置郡县、派遣汉官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的版图。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按照中原地区所推行的郡县制度,在岭南设置郡县,并派遣官吏进行统治,将岭南直接置于秦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秦朝在岭南设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担任南海尉,总管岭南三郡,赵佗任龙川县令。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布山(今广西贵港),象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注]臣瓒曰:“象郡治临尘”,参见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54页。目前,学界未对象郡治所形成共识,主要有“日南说”和“郁林说”,参见敬轩《本世纪来关于秦汉古象郡的争论》,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第9-12页。。
秦末,任嚣病故,赵佗行南海尉事,于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割据岭南近百年。赵佗把偏远的象郡一分为二,设交趾、九真二郡,派两个“典主”主持当地政事。仿照秦汉官制,设丞相、中尉、内史、御史等中央官,郡守、郡监、使者、县令、市府等地方官,大量官员由汉人充当。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岭南重设郡县,岭南地区被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交趾、九真、日南、儋耳九郡[2]3859。元封五年(前106),汉王朝又在岭南设立交趾刺史部,部治曾一度设在苍梧郡广信县[注]今广东、广西之“广”,最早出现于“广信”这一地名。(今广西梧州),后迁至龙编(今越南河内)、番禺(今广东广州)。
东汉王朝基本沿袭了西汉时期的建制,只是刺史部的地位和名称改变了,地位由原来的监察职能演变为郡之上的行政区,交趾刺史部改名交州。王朝派汉官赴岭南任职,锡光、士燮曾任职交趾郡太守,任延曾任九真郡太守,孟尝、士壹曾任合浦太守,邓宓曾任日南郡太守。
二、汉人南迁及汉越杂居、通婚
移民实边是王朝统治被征服民族的方式之一。为维护统治,王朝把威胁到统治的人,如敌对集团、大商人、罪人等发配边疆。不仅可排除异己,也巩固了边疆。作为秦汉王朝的边疆,岭南地区自然成为贬谪的重地。
秦朝统一岭南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即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3]253次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3]253后“尉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十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3]3086此外,唐代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说:“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有三十五代矣。”[4]这条史料从个体移民的角度证明了秦代岭南确有中原移民。
汉承秦制,汉朝也实行将罪犯迁徙岭南的政策。汉武帝征服南越国后,也组织了一次移民实边,“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5]1251。汉代的“徙合浦”现象,说明合浦成为西汉有罪官员及家属迁徙的重要地区。成帝北地郡浩商的兄弟杀本县官吏逃亡,浩商被捕杀,家属徙合浦[2]3413。京兆尹王章,被王凤诬告,“下狱死。妻子徙合浦。”[2]1334大司马董贤,“第门自坏……家徙合浦”[2]1376。
汉族官吏出任岭南任所、汉族士卒出征岭南而留居者,这些也属于政府组织的移民。任嚣、赵佗等官僚的子孙及其侍从人员留守岭南。秦瓯战争,秦始皇“前后用兵达五十万以上”,兵卒除去阵亡、病死及以后返回中原者外,其余部留在岭南,镇守郡治和关隘[6]65。同样,汉武帝平南越国,“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征讨之”[2]3857,平定后必有部分人长期屯守。东汉马援征交趾后,也有部分士兵留在岭南,被称为“马留人”。据《水经注》:“马文渊(马援之字)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返,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7]840。此外,《后汉书》载:“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夏四月,日南、象郡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郡县发兵讨击”[8]2837。 “永和二年(137),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8]2837。部分“郡兵”很可能是长期戍守的中原移民。
除政府组织的移民,也有部分士民为躲避战乱,自发移民岭南。西汉末年、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岭南相对安宁,且赋税较轻,不少中原人前来避乱。西汉末年,士燮的先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5]1191。南郡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人胡刚“值王莽居摄……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8]1504。李贲的先人,“西汉末苦于征伐,避居南土,七世遂为南人”[9]88。
东汉末年,汉王朝委任的交趾地方长吏士燮,不仅“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而且“体器宽厚,谦虚下士”,因此招来很多中原人南下避乱[5]1191。如许靖,“汝南平舆人”,为避董卓之乱,“走交州以避其难……既至交趾,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5]967。程秉“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5]1248。薛综,“沛郡竹邑人”,年少时遇战乱,遂“依族人避地交州”[5]1250。全琼,“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琼(时居桂阳)居者以百数”[5]1381。《三国志》载:“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专为亡叛逋逃之薮”[5]1253。说明岭南四郡边界处是东汉末年亡叛逋逃者的迁徙之地。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苍梧郡、南海郡、合浦郡。从公元2年到140年,苍梧郡的人口数增长了219%、户数增长了360%;南海郡人口数增长了166%、户数增长了264%;合浦郡的户数增长了50%[注]由《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户数、口数计算得出。。汉族移民构成了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大多数移民分布在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如番禺(南海郡郡治、交趾刺史部所在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广信(交趾刺史部所在地、苍梧郡郡治、桂江与浔江交汇处)、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郡郡治)、布山(郁林郡郡治、郁江边)四地。四地大量汉文化文物的出土是有力的证据。
汉人迁入岭南后,便与当地越人杂居。秦始皇徙民岭南,让其“与百粤杂处”[2]73,汉越杂居的局面开始形成。赵佗建立南越国后,更是“和集百越”。汉武帝平南越国后,进一步推行郡县制,将中原罪人迁徙岭南,“使杂居其间”[8]2836,扩大了杂居区域。
不少汉人迁入岭南后,与越人通婚。南越国建立后,为巩固政权,赵佗采取“和集百越”政策,提倡汉越通婚。越人丞相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苍梧王赵光与吕氏家族联姻,第三代南越王婴齐的妻子也是越人[2]3855。除上层之间的联姻,很多留守戍边的士卒也娶越女为妻。赵佗“求女无夫家者十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3]3086。被派去的女子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十万戍边士卒的婚配需求,大多数士兵很可能娶越女为妻。通婚后,夫妻俩必然要面对共同的经济与文化生活,这极大促进了汉越间生产、生活经验的交流。通婚成为推进汉越民族融合的重要方式。
秦汉大批中原汉族移民迁入岭南,不仅带来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也会有意无意地把中原汉文化带到岭南,特别是儒家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尚等。
三、汉越经济融合:开辟道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编户与征税、贸易与贡赐
汉越经济融合包括开辟道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编户与征税、贸易与贡赐。完善的交通不仅是中央集权国家传送政令军情的驿道,也是民族间经济交往的商路,贡品、商品由此形成古代的物流,政令军情商情因之形成信息流,官员商贾军队等赖以形成人员流。华夏民族正是依靠这种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将各部族融合在一起,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中,道路交通,以及作为交通节点的城廓的民族和经济意义,怎么估价也不过分。
秦开辟了四条通往南越的“新道”[注]参见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967、2968页;《通典》作“秦所开新道”,参见杜佑撰《通典》卷188《边防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5页。分别是自全州入静江一路(湘桂走廊),自道州入广西贺县一路(潇贺新道),自湖南郴州入连州一路,自江西南安逾大庾岭入南雄一路[10]。秦代开凿的“灵渠”,闻名于世。秦尉屠睢率兵进军岭南时,其粮食和军需品大部分需从灵渠运输[11]。西汉楼船将军出兵岭南,经过灵渠,“或下离水,或抵苍梧”[3]2975。东汉马援南征交趾也应经过灵渠[注]伏波山、伏波庙,传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到此而得名。参见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3页。。东汉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8]1156。其中零陵峤道就是途经灵渠的湘桂走廊。灵渠的开凿把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在一起,为中原和岭南地区的经济交流提供了有利的交通条件。至于潇贺“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古道沟通潇贺。古道起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圩,经广西贺州八步区开山,止于贺州八步区桂岭镇[12]。为进一步控制岭南,秦朝加修了“新道”,自湖南省道县双屋凉亭起,经湖南江永县、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接贺江为止,全程170千米,路宽1~1.5米,路面主要由青石块或鹅卵石铺成[13]。清人顾祖禹曰:“从道州而风驰于富川、临贺之郊,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14]4828。
汉代开辟了两条通岭南之道,即沿牂牁江下番禺一路,自福建之汀入广东循梅一路。蜀枸酱“自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后汉武帝伐南越国也利用了这一路线,顾祖禹称此路“自汉启之”[14]4804。广东揭阳与福建的陆路交通经盘陀岭,西汉时“为南越蒲葵关,闽、粤通道也”[14]4372。汉武帝伐南越时,经此路,“至揭阳以渡海”[10]。汉代中原至岭南的陆路交通已相当发达,“贡献转运”取内陆交通线,“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8]154。汉越交往亦取道海上,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南越)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越)。”[2]3861说明汉代已可经海路抵南越。交趾贡献亦有“从涨海(今南海)出入”[15]。东汉末年,北方战乱,许多中原士人浮海至交阯(趾),如桓晔、许靖、袁征等。
如果说郡县制是秦汉王朝共同推行的统一的政治制度,那么,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户口和赋税则是共同的经济制度。秦汉王朝统一岭南后,也统一了岭南的货币和度量衡,并开始编户和征收赋税。
秦代以前,岭南地区还没有货币,统一后则有了货币流通。广西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钱币。如平乐银山岭汉墓出土“半两”钱5枚[16]。罗泊湾2号墓出土了239克的金饼[17]。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发现宣、元时期的五铢钱7枚[18]40。梧州鹤头山东汉墓出土了33枚五铢钱[18]137。兴坪石马坪汉墓出土的货币包括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4种,其中五铢钱的数量达到1 600多枚[19]。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出土了三串钱币,包括五铢钱和大泉五十[20]。荔浦笔村一座东汉墓出土了铜钱70多枚,包括货泉、东汉五铢、剪边五铢[21]。半两钱、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都是秦汉王朝铸行的货币,说明秦汉王朝在货币制度上完成了对岭南百越诸部的统一。
统一度量衡是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治理的又一重要举措。度量衡是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标准的统称,统一的度量衡是民族形成中的重要经济制度,岭南地区通行秦汉王朝统一的度量衡,是这个地区诸部族纳入华夏民族一体的重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标志。在量器方面,岭南地区通常用尺子表示长度标准。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了西汉初年的三件竹木尺,其中一件完好,长23厘米,尺的正面有10寸刻度。另外两件都是残存尺,一把残存7寸刻度,总长16.1厘米;另一把残存2寸刻度,总长4.6厘米[22]。梧州郊区旺步一号汉墓出土了一件东汉铜尺,一边有寸的刻度,共10寸,长23.72厘米[23]。合浦汉墓出土了一件东汉铜尺,长23.7厘米[24]。这些尺子的长度都约为23厘米,每寸刻度约为2.3厘米,与中原出土尺的长度标准基本相符。在容器方面,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了4件刻有容量标准的铜鼎,如M1:31号铜鼎,鼎腹外壁一侧刻有“一斗九升”“布”;另一侧刻有“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半升”[22]。“布”“蕃”“析”表示地名,“布”为布山县,“蕃”为番禺,“析”为中原地区的析县。3种标准表明了三个地方的容量测量还有差别,这是封建制的遗存,但已经较为接近了。在衡器方面,罗泊湾一号墓岀土的几件铜器上刻有重量标准。如M1:10号铜鼓,上刻有“百廿斤”,实测为30 750克,每斤合今256.25克。M1: 4号铜桶,上刻“十三斤”,实测为3 484克,每斤合今268.08克。M1:35号铜钟,上刻“布八斤四两”,实测为2 188克,每斤合今265.45克。M1:36号铜钟,上刻“布七斤”,实测为1 866克,每斤合今267.14克[22]。这4件器物造型和纹饰不同于中原,均属本地产品。器物上列的重量标准,却与秦权、汉权的标准较接近,说明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重量标准已基本实现与中原王朝接轨。
秦汉时期,越汉杂居区有部分越人已被编户,并且要求纳税。南越国时期,部分越人已被编户。据《汉书》,武帝平南越时,“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雒四十余万口降汉”[2]3858,人口数字如此精准,当与南越国在桂林郡实行户籍制度有关。《交州外域记》载:武帝平南越国时,“路将军(路博德)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资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户口簿诣路将军”[7]3043。二郡户口簿的二郡指九真、交趾,连较落后的九真、交趾都建立了户籍制度,更为先进的西瓯、南越地区自不必说。《汉书》记载了平帝二年(2)岭南各郡的户口数和人口数,如南海郡19 613户,94 253人;苍梧郡24 379户,146 161人;郁林郡12 415户,71 162人;合浦郡15 398户,78 980人[2]1628-1630。《后汉书》记载了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的户数和人口数,其中南海郡71 477户,250 282人;苍梧郡111 395户,466 795人;合浦郡23 121户,86 617人[8]3530-3531。两次人口统计,说明当时岭南户籍制度进入常规管理阶段。
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合浦三地,成为东汉政府在岭南地区的税赋征收地[25]。永元十四年(102)七月,“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稾二岁”[8]190。象林是日南郡下面的一个边远小县,连岭南的边远小县都被征收赋税,岭南腹地的南越、西瓯地区自不待言。延熹九年(166)正月,为救济灾荒,对岭南实行免税政策,“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其灾害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8]317这则史料从侧面说明灾荒前,东汉王朝对岭南是征税的。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1),合浦太守肆意搜刮珍珠,造成“合浦珠去”[8]2473。汉顺帝阳嘉四年(135),交阯百姓“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8]1111-1112。汉末,“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5]1252以上引文也说明合浦等地的越人被征收赋税。
贸易是汉越经济融合的重要途径。秦汉之际,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大量引进汉族地区的“金铁田器”[2]3851。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题为“东阳田器志”的木牍,记载了从东阳(今江苏盱眙县境内)输入的用以陪葬的农具清单,其中有锸、锄、铣等,数量从数十到百余具不等[22],反映了当时中原的铁制农具输入到岭南地区。广西汉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铁锸,其造型与中原地区相似,可以断定属于中原铁农具系统。广西出土的某些器具上的中原地名[注]器物上刻的地名,即器物的产地。,是器物传入的有力证据。如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铜鼎上刻有“析”字,铜钫上刻有“犛”字,据考证,“析”即西汉时的析县(今河南郏县),“犛”指西汉时的犛县(今陕西武功县)。罗泊湾一号墓还出土木牍《从器志》,刻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中土”即中原地区,“中土瓿卅”指中原地区生产的陶瓿30个,“中土食物五笥”指中原地区生产的食品5笥[22]。此外,《汉书》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2]1270。说明岭南地区的特产珍玩成为中原商人经营的商品。
贡赐也是汉越经济融合的途径之一。商周时期,岭南百越就向中央王朝进贡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大竹、翡翠等[26]。赵佗称王后向汉廷许诺,“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2]3687。据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赵佗曾把岭南特产鲛鱼、荔枝、珊瑚等进献给汉高祖,以示称臣[27]。随后,赵佗又将土产白璧、翠鸟、犀角、紫贝、桂蠹、孔雀等物进献给汉孝文帝[2]3852。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曾在京师长安建筑“扶荔宫”,移植岭南的荔枝、龙眼、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等,然而都因北方寒冷和水土不宜,致“岁时多枯瘁”,最后“无一生者”[28]。于是,汉王朝便将荔枝、龙眼等佳果列为贡品,“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29]此外,还设“橘官”,专门负责“岁贡御橘”[30],从而使“岭南佳果”名扬四州,饮誉中原。除了珍玩、水果,东汉末年,士燮还向孙权进贡了葛布、马匹等[5]1192-1193。
四、汉越文化融合:推广汉字、兴办学校、传播经学和佛学
秦汉南越国统治者多推行教化。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固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文教振乎象郡”[9]17。汉高祖对其高度评价,称其“甚有文理”“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2]73。马援南征交趾,“中原冠冕至今来”[31]6。任延、锡光在岭南为官时,“教导民夷”,开创了“岭南华风”。任延在九真郡,“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8]2462三陈、士燮为岭南经学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推广汉字。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实行“书同文”。南越国时期,继续推广汉字。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器物,多刻有汉字,如“文帝行玺”“泰子”“赵昧”等。广州出土的瓦当,刻有“万岁”,为篆体[32]。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从器志》木牍共刻有372个汉字,铜器上刻有“百廿斤”“布八斤四两”“析二斗一升”等汉字[33]。汉代贺州、贵港、合浦、广州出土的铜镜也刻有汉字,贺州辅门的铜镜刻有“日有喜,宜酒食,长富贵,乐毋事”[24]307。汉字还传入交趾、九真两郡,成为当地的官方文字[34]。越南学者阮才书称:“中国人来到这里以前,越南人还没有文字。汉人来以后就把汉字传到越南来,从这时起,越南也使用汉字。”[6]75汉字的流通是越汉文化交融的重要一步,是共同文化生活的重要体现。
兴办学校。汉朝官员锡光在交趾郡,任延在九真郡,卫飒、栾巴在桂阳郡兴办地方官学。私学方面,士氏家族有家学传统,士燮、士壹均是通经之士。刘熙收徒讲学,门徒数百人,程秉、薛综、许慈都曾向其学习。南海郡黄豪、董正亦开办私学,教授生徒。
传播经学、佛学。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人均是经学大师,对岭南经学发展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清人屈大均称:“《春秋》者,圣人之心志所存。其微言奥指(旨),通之者自丘明、公、谷而外,鲜有其人。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35]东汉末的士燮亦是经学大师,精通《尚书》,撰有《春秋左氏传》[5]1191。在岭南任职四十年期间,与南下的士人共同研讨经学,对岭南经学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唐人刘知几称:“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36]刘熙长于经学,著书立说,收徒讲学,为岭南培养了大批人才。东汉末年程秉、许慈、薛综、袁徽、许靖、虞翻均是经学之才,集聚交州,研究探讨儒学经典,使得相对落后的岭南俨然成为南方的文化中心。此外,牟子致力于佛学,撰成《理惑论》三十七章[37],是岭南佛学传播的重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为缓解汉越矛盾,汉族统治者还因地制宜,某些方面推行越人习俗,客观上促进了汉越文化融合。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实行“和集百越”,入境随俗,“魋结箕倨”[3]2697,以“蛮夷大长”[3]2970自居。马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8]839,尊重越人习俗。
秦汉时期岭南汉越融合是典型的汉族迁入少数民族型融合。秦始皇通过军事行动,征服岭南,并设置郡县、派遣汉官,为汉人南迁和汉越融合奠定了政治前提。汉人南迁,并与越杂居、通婚,是汉越融合的主体和直接推动力量。开辟道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编户与征税、贸易与贡赐构成汉越经济融合的重要路径。推广汉字、兴办学校、传播经学和佛学构成汉越文化融合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