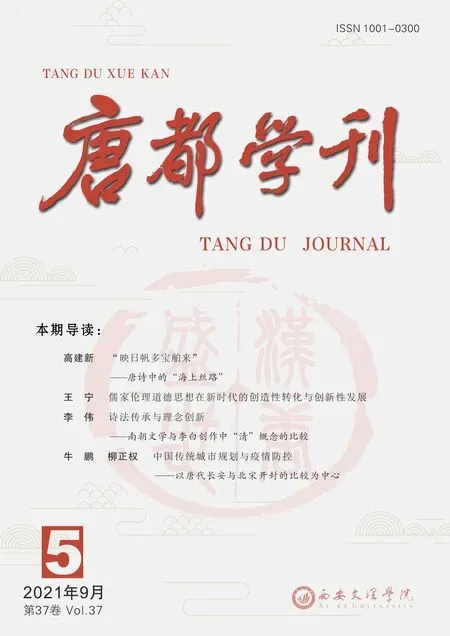朝鲜朝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诗风论析
——以士大夫诗人群、委巷诗人群为中心
2021-11-25杨会敏
杨会敏
(宿迁学院 中文系,江苏 宿迁 223800)
古代朝鲜近两千年的汉诗风流变历程如下:统一新罗(公元7世纪中叶至935年高句丽王朝建立)后期宾贡诗人群体诗学晚唐;高丽前半期(光宗至毅宗时期)宗尚初盛唐;高丽后期的“海左七贤”学宋诗;高丽末期的汉诗深受朱子性理学的影响;朝鲜朝前半期(朝鲜王朝建立至仁祖朝)的汉诗经历了由朝鲜朝初期兼容并蓄、多元整合的诗风至以性理学为根底的宗宋诗风再到以白光勋、崔庆昌、李达为代表的宗唐诗风的振起。而仁祖朝(1623—1649)以后,金昌协、洪万宗等朝鲜诗家在宗唐基础上提倡汉诗应表现自我情感,凸显自我,诗风为之一变。本文拟在探讨仁祖至景宗时期汉诗风新变的背景因由,分析这一时期士大夫诗人群体、委巷诗人群体宗唐诗风的具体呈现、各自特质及其在朝鲜汉诗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一、仁祖至景宗时期汉诗风新变背景原因分析
仁祖至景宗时期(1623—1724)汉诗风新变发端于对此前以崔庆昌、白光勋、李达为代表的宗唐诗人群存在情感缺乏、模拟过甚等弊端的反思与纠偏;此外,作为两大汉诗创作主体之一的辞章派渐趋萎缩,道学派不断壮大,从而导致了汉诗创作的衰退,而这一文学现象引发了金昌协、金得臣等诗评家的关注和思考,他们在前辈诗评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性情论、主意论、民族文学论等诗歌理论,诗歌风尚为之一变。除了朝鲜诗学发展的内部因由,中国明末至清代前期诗坛的宗唐风尚也是促成这一时期诗风转向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对仁祖朝前后宗唐诗派弊端之反思
宣祖(1568—1608年在位)年间自“三唐诗人”崔庆昌、白光勋及李达力倡宗唐后,大量的士大夫诗人、庶民诗人成为其响应者,再加之柳梦寅、李晬光、许筠等诗评家的推尊唐风的理论建构以及明代复古派诗集、诗论的东传,最终使宗唐诗风代替宋诗风成为诗坛主流。这一诗坛风潮发展至仁祖(1623—1649年在位)至肃宗(1674—1720年在位)年间蔚为大观。但随着宗唐的各类诗人群体在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模拟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端,已偏离了纠正当时受性理学、江西诗派余弊及科试制度所导致的不良诗风之导向。对此,具有敏锐眼光的诗评家金昌协(1651—1708)指出宣祖朝为李朝汉诗由宗宋转为宗唐的转折点,但对宗唐诗歌的评价即“轨辙如一,音调相似,而天质不复存矣”“读穆庙以后诗,其人殆不可见”[1]378,未免太绝对。虽然宣祖、光海君(1608—1623)、仁祖三朝受明代复古思潮影响最深,其时宗唐诗人的汉诗创作中程度不等地存在情感欠缺、过于重视格调形式、模拟过甚等弊端,但也不乏善于抒写真性情、彰显个性的作家,如生活在宣祖、光海君时期的许筠、车天辂、林悌等。许筠不仅主张诗歌要直率自然地表达诗人的性情之真,要“不相蹈袭,各成一家”[2],且其创作也不拾人牙慧、不做效颦之姿,均能抒写性情,独具特色。正因为此,其诗歌不仅在朝鲜诗坛独步一时,也获得中国明朝诗人的赞誉。车天辂诗歌以雄健奇壮之诗风见长,令明朝使臣朱之蕃(1548—1624)为之赞服:“朝鲜有车天辂者,文章奇壮”[3]2108,而林悌抒写的诚挚的爱国情怀和内心的苦闷最引人注目。因此,金昌协所评不免偏执,但所论“诗道之衰”自宣祖始是准确的,尽管仍有许筠、车天辂、林悌等人以诗歌鸣于当世,但卓著者毕竟不可与此前同日而语。
(二)宣祖朝辞章派的萎缩与道学派的壮大
朝鲜朝汉诗自宣祖朝衰退,除了宗唐风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外,还应归因于两大汉诗创作主体之一的辞章派的萎缩,而与辞章派对立的道学派则不断壮大。
虽然燕山君(1494—1506年在位)至明宗(1545—1567年在位)时期的四大士祸使道学派元气大伤,但明宗末年辞章派实力衰颓,其一部分残余势力转向道学派。继明宗之后的宣祖时期道学派大获全胜,由此掌握政权的道学派开始镇压不妥协的辞章派。而两派的争执焦点在其文学观念的不同,辞章派专心辞章,而道学派虽也认为写诗作文有必要,但更看重道学即性理学,斥诗文乃雕虫小技。这种争论由来已久,“己卯士祸”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两派文学观的不可调和:“又光祖等,偏重道学,排斥辞章,每于经筵,论辞章之弊,至谓人主不可作诗,亦不可令臣下制进。故先进文学之士,多不好之。于是有道学派与辞章派之反目焉”[4]。上文中的赵光祖(1482—1519)即当时道学派的核心人物。在野党的道学派除了抨击辞章派独掌权力、滥用职权外,还批判其不重经史之学问而只专注辞章,但道学派的排斥还未能从根本上削弱还处于政权中心的勋旧派的实力。而自宣祖登基之后,当政的道学派便开始镇压辞章派。三唐诗人、林悌等非辞章派的诗人大都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偏偏是处于逆境中的被辞章派打压的这些诗人诗才卓越。在光海君时代,甚至出现了因诗祸而丧命的辞章派文人,著名者如权韠(1569—1612)、许筠(1569—1618)。被许多评论家誉为朝鲜中期最著名的诗人权韠天性愤世嫉俗,一生未曾应举,志在放浪湖海,敢于讽刺时政得失、痛陈权门弊害,最终因写诗讥讽光海君之外戚专横的宫柳诗而罹难。他在遇害前将自己的诗稿打包托付给甥侄沈某保存,并在包袱背上题诗一首,名为《绝笔》:“平生喜作俳谐句,惹起人间万口喧。从此括囊聊卒岁,向来宣圣欲无言”[5]。诗人首先对其离经叛道的一生作了总结,后两句稍露出反悔之意,但为时已晚,三日后即被杀害。目睹朋友权韠以诗肇事,许筠发誓不再作诗,且试图以武装政变反对道学派的压迫,却最终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此外,还有因派别之争而死于诗祸的道学派文人,如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柳梦寅(1559—1623)在光海君时代属于北人,仁祖反正之后掌权的西人强迫他改事新君,深受儒家纲常濡染的柳梦寅坚持一臣不事二君,写《题宝盖山寺壁》一诗以表心志:“七十老孀妇,端居守空房。傍人劝之嫁,善男颜如槿。贯诵女史诗,稍知任姒训。白首作春容,宁不愧脂粉”[6],他最终也因这首诗而为旧主殉节。
宣祖年间,道学派内部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此后近二百年,仍然错综复杂。道学派对外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内部的党争使不少无辜的辞章派文人和士林中人惨遭杀害,这不可能不对幸存的文人产生震慑。因此,仁祖至景宗时期,辞章派只好选择屏声静息,辞章派的萎缩对汉诗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甚至使得朝鲜汉文学一度出现文盛于诗的倾向,如被誉为朝鲜朝文章巨擘的“月象溪泽四大家”即李廷龟(1564—1635)、申钦(1566—1628)、张维(1587—1638)、李植(1584—1647)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且这四人属于执政党道学派文人群体,代表当时文坛的主流。而这一时期的诗人有许穆、郑斗卿、尹鑴、南龙翼、金昌协、金昌翕、申维翰、金得臣、崔成大、洪世泰等,辞章派诗人寥寥无几。直到英祖、正祖以后,随着党争的缓和、性理学统治的松动以及以实学派为主的新的思想理念的兴起为道学派以外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由此才出现多元化的诗风。
仁祖至景宗时期汉诗创作的衰退引起了当时不少诗评家的关注和思考,除了上文提及的金昌协外,金得臣、洪世泰等在前辈诗评家许筠、李晬光、柳梦寅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性情论、主意论、民族文学论等诗歌理论,这种迥异于主流文学观的诗学转向成为一时之风尚,而诗风也随之产生新变。
(三)中国明清诗坛宗唐风尚的影响
明代文坛先后出现的“前七子”“后七子”皆倡导唐诗风。而明末清初诗坛,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的复古宗唐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占据主导地位,且对清初诗坛影响甚大。清初诗人吴伟业、朱彝尊、施润章等人,皆受到云间派宗唐风的影响。顺治初年,钱谦益、冯舒、冯班等人倡导取法中晚唐诗,使得对唐诗的学习更为全面,且明末开始流行的宗唐复古诗论仍在全国各地盛行不衰。可见,有清一代,直至康熙前期,宗唐仍为诗学主流。“面对中国明清易代、诗风更替的政治和文学格局,朝鲜诗家受国内北学派思想的影响,也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清诗”[7],施润章、钱谦益等清前期的诗人的宗唐风格受到了朝鲜诗家的关注与学习。如徐宗泰(1652—1719)对钱谦益诗风学杜的肯定与赞扬:“然触事咏物、感奋时事是杜老之遗韵,其忠忱则至矣。”[8]到了康熙中后期,康熙帝力倡唐诗,在其周围的以毛奇龄、朱彝尊为代表的执政大臣诗人群也倡导宗唐。李德懋在其《清脾录·毛西河》中称赞“毛西河奇龄全集,诗文高华逸宕”[9],并摘了若干诗句作为例证。而历经了顺康两朝的另一诗坛大家王士禛以宗唐为主,兼宗宋元的诗学主张,尤其是其神韵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乾隆朝,在异域朝鲜朝诗坛备受推崇,被誉为“海内诗宗”。
二、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诗风的具体呈现
仁祖至景宗时宗唐诗风的具体呈现主要在于以金昌协、金得臣、洪世泰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诗人群、委巷诗人群以唐诗为宗、注重“性情之真”与“天机之发”的诗学观。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士大夫诗人群的“性情之真”说剥离了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道德与理性因素,尤为强调自我与真情实感的抒发;而一生贫贱的委巷诗人群则有意在汉诗中凸显自己不为名利所累的豁达,形成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诗风。
(一)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诗论的兴起
金昌协所极力倡导的“诗缘情”“天机论”不仅在当时的士大夫诗人群、乐府诗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继之而起的实学派诗人群及发展壮大的委巷诗人群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响。特别是以唐诗为宗、注重“性情之真”与“天机之发”的诗学宗尚使这一时期的汉诗风也随之产生新变。
针对朱子学载道的文学观及宗唐复古中的模拟、偏重于形式等弊端,金昌协、金得臣、金昌翕、洪世泰等提出诗歌本于性情,且主张通过“天机”“灵气”“应感”等灵感抒发性情。这些诗论源于中国,“诗缘情”自屈原提出“发愤以抒情”[10]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11]已基本定型,且逐渐取代了“言志说”成为中国诗学主导性的命题;而“天机论”中“天机”一词虽最早出现在《庄子·大宗师》,但不具备艺术理论意义。将“天机”含义提升至文艺创作理论层面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不仅生动直观地描述了灵感现象,且用诗化的语言阐明了艺术创作中灵感思维的突发性、偶然性、创造性等重要特征。“诗缘情”“天机论”传入朝鲜后,为高丽至朝鲜朝诸多诗话家所接受,如崔滋、徐居正、许筠、柳梦寅、李晬光、李宜显、南公辙等皆认为诗本于性情、发于性情,孝宗(1649—1659年在位)至景宗时期,“诗缘情”说被进一步深化和突显;而“天机论”至16世纪初叶才为成俔(1439—1504)最先应用于文学领域,经由许筠、张维等人的积极推进,至朝鲜朝后半期金昌协、洪世泰等人的阐发而被赋予丰富的内涵。
总体来看,“诗缘情”和“天机论”通常被这一时期的诗论家相提并论,且呈现水乳交融之势,金昌协即为这方面的代表,其在《外篇》中言道:“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唐人诗,有得于此。故无论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1]375。他将性情、天机归于“自然”,认为“性情之发”“天机之动”的诗歌才具有“神情兴会”,才为自然之作。比之于宋诗,金昌协认为唐诗更胜一筹,因为“唐人之诗,主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1]375,主张学习唐诗,但不应模仿而贵在创新,不能只求“声音气调”之形似,而重在学习唐诗吟咏性情的精髓。当然,他认为宋诗虽以“议论”为“诗家大病”,但仍有表现性情之真的感人之作。金昌协对诗歌如何表现“性情之真”或“天机之发”也有独到的理解:“诗歌之道,与文章异者。正以其多道虚景,多道闲事。而古人之妙,却多在此。盖虽曰虚景闲事,而天机活泼之妙。吾人性情之真,实寓于其间。”[12]539金昌协认为诗歌本于与道德无关的性情之真,将性情从传统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肯定表现“虚景闲事”的诗歌才具有活泼的天机和真实的性情。这一诗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诗歌载道论,也为诗人进行个性化的创作鸣锣开道。
金得臣(1604—1684)将“天机论”上升到诗歌本质的高度,认为诗歌乃“得于天机”[3]2115的产物,由“自运造化”[3]2115促成。“得于天机”意即诗歌创作源于灵感,通过灵感表现天机,进而创造感人、入神的境界。如他评价前辈诗人郑士龙(字湖阴)的“江声忽厉月孤悬”一句“写景逼真”“对景益高”[3]2106,并将之归因于诗人同江声、孤月感性交融,产生共鸣,才创作出逼真入神的艺术境界。与天机论相呼应,金得臣欣赏浑然天成的诗风,他评洪万宗诗为“天然超绝,得唐人景趣”[3]2118。可见,金得臣认为唐诗得于天机,富有意趣。
金昌协的诗歌观还为同一时期以洪世泰为首的委巷诗人群的“天机论”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也使委巷诗人与士大夫文人一起活跃于文坛。委巷诗人的天机论,除了重视诗歌情感的自然流露外,重在表明诗歌创作与诗人身份的贵贱无关,身份卑贱的人可能创作出更具天机的诗歌。
洪世泰(1653—1725)的“天机论”极力彰显委巷诗人的存在价值:“夫人得天地之中以生,而其情之感而发于言者为诗,则无贵贱一也。”[13]473他主张诗歌乃情之发,即人的情感通过言语表达成诗,由于人的情感无贵贱之分,因此,诗歌本身也不会因为诗人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产生差别。否则,这些里巷歌谣之作也不会被圣人以追求平等的意识而收录到《诗经》中。洪世泰以平等为思想武器为委巷诗人争取诗歌创作权,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委巷诗人虽与士大夫诗人有身份差别,但同样能创作出具有天机的诗歌:“盖自荐绅大夫,一倡于上。而草茅衣褐之士,鼓舞于下,作为歌诗以自鸣”[13]473。文中的“草茅衣褐之士”即委巷诗人,他们虽然“为学不博,取资不远”,但所抒写的情景“风调近唐”[13]473,且皆为天机的自然流露。无独有偶,李天辅极力赞同洪世泰的“天机论”,他在《浣岩集序》中言:“夫诗者,天机也。天机之寓于人,未尝择其地,而澹于物累者能得之。委巷之士惟其穷而贱焉,故世所谓功名荣利,无所挠其外而汩其中,易乎全其天,而于所业嗜而且专,其势然也”[14]240。洪世泰强调诗歌创作应出于率真的性情,音韵自然流畅,有“神动天随之妙”[13]305,如果故作奇巧反而有滞涩之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工诗之士,多出于山林”[13]472的观点,他赞同庄子“嗜欲深者,其天机浅”[13]472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摆脱名利的羁绊,则不能作出好诗。以此推论,身份微贱者因为“嗜欲”少、天机深,比之于士大夫阶层的诗人,更能写出自然天成的诗歌。
(二)仁祖至景宗时期士大夫诗人群的宗唐诗风
仁祖至景宗时期(1623—1724),金昌协、金得臣、南龙翼、金昌翕等士大夫诗人群的汉诗创作践行了其以唐诗为宗、注重“性情之真”与“天机之发”的诗学观,其诗重视真情抒发,清新自然、含蓄蕴藉。
以金昌协为代表的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士大夫诗人群,他们所倡导的“性情之真”说剥离了朱熹“心统性情”[15]说中的道德与理性因素,这也从本质上决定了其不同于这一时期其他深受朱子性情说影响的宗宋或唐宋兼宗的士大夫诗人群。如对唐诗称颂有加却又不废宋诗的李宜显(1669—1745)主张“诗以道性情”[16]453,“宋人虽自出机轴,亦各不失其性情,犹有真意之洋溢者”[16]429。但他推崇所抒发性情应恪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皆有所补于世教”[16]453。只不过他所理解的性情之正不再局限于宋代朱熹、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所谓的合乎三纲五常的天理的雅正,而将“虽多荒怪不经之语,而忠愤慷慨”的屈宋词赋也界定为“性情之正”[16]447,这与清初提倡宋诗的黄宗羲所谓的慷慨激昂也属于儒家的中和之美的诗教观如出一辙,本质上别无二致。另有“性理之正学,经济之大猷,焕乎斯文之宗门”[17]的李瀷(1681—1763)及“身传正学,道接真源,嶷然为儒门之宗”[18]的尹东洙(1681—1763),二者陶写性情皆以深厚的朱子性理学为根底。而金得臣、南龙翼、金昌协、金万重等宗唐诗人群的性情之真与朱熹抑制性情与人欲的雅正大异其趣,不囿于道德、世教的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即为其诗歌创作的主题。
与其主张的“性情之真”相呼应,这一时期宗唐诗人群“天机之发”的诗学观既是诗歌创作源于灵感的本质论,又是不加藻饰、独创出奇、自然天成的风格论,这对此前宗唐诗派、江西诗派等出现的形式主义弊端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唐宋兼宗的李宜显在《陶谷集》中曾称赞“唐以辞采为尚,而终和且平,绝无浮慢之态。所以去古最近,末流稍趋于下”[16]403,批驳“李、何诸子起而力振之,其意非不美矣,摹拟之甚,殆同优人假面,无复天真之可见”[16]403,李宜显指出的前后七子复古导致的模拟、“无复天真”的弊病,其实,前后七子进行了反思与修正,如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晚年提出了真诗说、后七子核心人物王世贞提出真我说,与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士大夫诗人群的天机论不谋而合,也表明他们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接受日趋理性与深刻。
金得臣以唐韵、唐格、唐风、唐意趣品评诗歌,其汉诗创作也尚唐音,这一点得到诗论家的一致认同。如洪万宗评价金得臣《木川道中》等诗“极逼唐家”[19],又如任埅曾赞曰:“金柏谷得臣平生工诗,雕琢肝肾,一字千錬,必欲工绝,其贾岛之流乎!如‘落日下平沙,宿禽投远树。归人欲骑驴,更怯前山雨。夕照转江沙,秋声生野树。牧童叱犊归,衣湿前山雨’等作,何让唐人?”[20]与明代前后七子诗宗初盛唐不同,金得臣作诗取法晚唐苦吟派。朴世堂在《柏谷集序》中也曾指出金得臣继承晚唐贾岛等苦吟派作风,为了取境真实和穷形尽相,忘乎所以地“于境会象态”[21],以景抒情,感人至深。金得臣代表作有:《田家》:“篱弊翁嗔狗,呼童早闭门。昨夜雪中迹,分明虎过村。”[22]27还有《龙湖》:“古木寒烟里,秋山白雨边。暮江风浪起,渔子急回船。”[22]19前一首语言质朴,情境淡泊、逼真。后一首也无雕饰,自然天成,韵味无穷,被朝鲜朝孝宗(1649—1659年在位)称为“虽入唐音无愧”[22]235。
南龙翼(1628—1692)崇尚唐诗,且对初盛晚唐诗不分轩轾,其曾在《诗评·唐诗》中言其诗学之渊源:“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五律则学王摩诘,七律则学刘长卿,五绝则学崔国辅,七绝则学李商隐,五言则学韦苏州,七古则学岑嘉州”[23]。南龙翼《壶谷集》其主题内容大致可分为写景咏物、抒写闲适之情、表达忠君爱国思想等。不少诗作具有真率流畅、自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如其五律《过江西寺》:“为访江西寺,仍经水上村。草深分鹭色,沙软落潮痕。远树重重合,轻霞点点昏。清晨鼓棹去,微月在山门。”[24]诗人以景抒情、不露斧痕,所写之景明丽且宁静寥廓,小草、白鹭、沙滩、远树、软霞、微月一起营造了如梦幻般境界,令人感觉美妙无穷。
金昌协除了主张“诗缘情”“天机论”等诗歌理论,还极力提倡进行一场“真诗”运动,在仁旺山和北岳山之间的壮洞成立了“白岳诗坛”组织,其成员有金昌翕、李秉渊、金时敏、俞拓基、洪世泰等人。如其《又赋》诗云:“蒹葭岸岸露华盈,篷屋秋风一夜生。卧溯清江三十里,月明柔橹梦中声。”[12]358这首诗写景如画,物我交融,笔调闲逸雅致、天然浑成。
金昌协的胞弟金昌翕(1653—1722)尤为崇尚盛唐诗人,金亮行为其所作《行状》云:“其诗格法雅健,一洗程式之陋。……自三百篇楚骚古乐府,以及乎盛唐诸家,精治熟习,折衷模范,用成一家之则”[25]295。金昌翕擅长山水诗的创作,丁若镛曾赞誉道:“纵笔千万言,烟霞落纸面”[26]。如《访俗离山》一诗:“江南游子不知还,古寺秋风仗履间。笑别鸡龙余兴在,马前犹有俗离山。”[25]196诗人将宜人的秋色与舒畅欢快的心情融为一体,心旷神怡之感尽现。金昌翕在41岁时移居到檗溪,从此开始了从山水诗到描写山村景物、风土人情的题材的转变,又如《葛驿杂咏(其一)》:“寻常饭后出荆扉,辄有相随粉蝶飞。穿过麻田迤麦垄,草花芒刺易罥衣”[25]295。该诗则以畅达的语言叙述了饭后独步信游的田园春光,意境优美,有超然自得之妙。
(三)仁祖至景宗时期委巷诗人群的宗唐诗风
这一时期,委巷诗人的卓越代表洪世泰(1653—1725)以唐诗为宗,在《柳下集序·自序》中称其诗“斟酌古今,激扬清浊,浑融变化,合为一格,不出于唐杜之间”[13]305,而其得意门生郑来侨为洪世泰所作《沧浪洪公墓志铭》,赞其“而于诗家用工尤专,神精所到,潜透妙悟,其遇境摛藻,天机流出,音调气格,骎骎乎唐正宗诸家”[13]560。其《水村秋兴》一诗云:
寒郊莽苍日徘徊,九月西风吹水来。客里偏惊授衣节,愁时独立望乡台。
江天鸿雁不知数,野径菊花空自开。三角登高十年事,白云峰色满深杯。[13]314
作者有意拟杜甫迁居夔州后所作《秋兴八首》,以秋的苍凉与凄清抒写漂泊异乡、怀才不遇的抑悒和忧伤,意境浑然一体、深远蕴藉。洪世泰一生贫寒,愁怀满腹,特别是“老而益贫,无以自存”[13]560,极易与晚年贫病交加、忧世伤时的杜甫产生情感共鸣,正如郑来侨在《沧浪洪公墓志铭》中所言:“乃以公余,得放浪山海间,其诗益雄放横逸,人以为得远游跌宕之助,类老杜之夔后,公亦以为知言”[13]560。
而诗学洪世泰的郑来侨(1681—1757)虽“而甚贫窭,家徒四壁”[14]240“亦不免穷厄其身”[27]573,仍努力践行乃师的“天机论”,正如李天辅《浣岩集序》)所言:“余以为润卿之诗与文,一出于天机而已”[14]240,洪凤汉在《浣岩集跋》中甚至赞其曰:“自奋于孤寒之中,大肆于诗文之工,饥而其气也不诎,老而其操也冞坚,所成就殆与洪沧浪相伯仲,其贤则过之”[27]573。且看其《打稻歌,上竹西相公》一诗:
西风瑟瑟入深谷,村西村南稻粱熟。韦岩相公命驾来,葛巾野服东山麓。
黄菊篱边正烂熳,美酒瓮闲亦堪漉。漉出美酒采黄花,陶陶不知秋日斜。
相公高坐颜半酡,老农当席遂高歌。大儿能耕女能织,十匹粗布百亩禾。
终岁衣食自有余,不愿驷马与高车。高车从古多倾覆,愿公归来与我同此乐。[27]491
诗人描绘出一派诗情画意的丰收场景,农民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融洽、诗人远离仕宦的自得其乐之情跃然纸上,绝少藻饰的天机之美流露笔端。
另有崔奇男、金孝一、南应琛、崔大立、郑楠寿、郑礼南赋诗唱吟,且合编了第一部委巷诗人集《六家杂咏》,高时彦、蔡彭胤合编了《昭代风谣》,编纂诗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凸显这些贫寒之士能不为名利物质所累,创作自然天成之诗,如高时彦在《书〈昭代风谣〉卷首》中,说明了编撰此书的主要动机。他说:“与《东文选》相表里,一代风谣彬可赏。贵贱分歧是人为,天假善鸣同一响。”[28]
综上所述,朝鲜朝宣祖时期,由于宗唐风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两大汉诗创作主体之一的辞章派的萎缩,使得朝鲜汉文学一度出现文盛于诗的倾向。直到朝鲜朝英祖、正祖以后,随着党争的缓和、性理学统治的松动,以及以实学派为主的新的思想理念的兴起发展为道学派以外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由此才出现多元化的诗风、文风。这一时期不少诗评家关注和思考诗歌创作的衰退,在前辈诗评家许筠、李晬光、柳梦寅等人基础上,加之中国明清诗坛宗唐风尚的影响,金昌协、洪万宗、金得臣、南龙翼、金昌翕等士大夫诗人群进一步深化了性情论、主意论、民族文学论等诗歌理论,这一以唐诗为宗、注重“性情之真”与“天机之发”的诗学宗尚使这一时期的汉诗风也随之产生新变。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诗风的具体呈现主要在于以金昌协、洪世泰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诗人群、委巷诗人群以唐诗为宗、注重“性情之真”与“天机之发”的诗学观。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士大夫诗人群的“性情之真”说剥离了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道德与理性因素,尤为强调自我与真情实感的抒发;而一生贫贱的委巷诗人群则有意在汉诗中凸显自己不为名利所累的豁达,且形成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诗风。这一时期士大夫诗人群、委巷诗人群的诗学风尚一定程度上对继之而起的实学派诗人群的诗学观及汉诗宗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由此引领和决定了朝鲜朝后半期汉诗发展的基本走向和主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