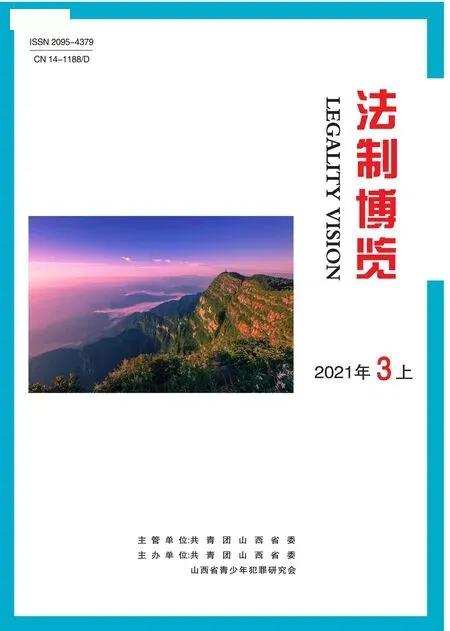完善女童受性侵防控机制的思考
——基于H省H市的实例分析
2021-11-25李霞
李 霞
(中共衡阳市委党校,湖南 衡阳 421001)
女童遭受性侵是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社会问题。2019年以来,H市公安机关对强奸女童案件立案91起,占全部强奸案件的67.41%。立案数据表明女童受性侵的形势十分严峻。本文通过对H市发生的女童受性侵的典型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原因,期望从社会治理和司法保护的角度提出有效可行的防控对策。
一、H市女童受性侵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8年1月至2020年7月,H市检察机关起诉性侵儿童犯罪134件,犯罪嫌疑人151人,涉及被性侵儿童188人,其中女童有169人。犯罪行为涉及强奸犯罪、猥亵儿童犯罪、强迫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等罪名。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女童受性侵案件从主体到案件本身都有鲜明特点。
(一)主体特征分析
1.受害者的基本特征
第一,年龄特征呈低龄化。据检察机关统计,2019年起诉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被害人97人,其中针对未满14周岁幼女的案件有被害人78人,占比约为80.41%。小学女童成为受性侵害的高危人群。被猥亵侵害的女童,最小的只有3岁。
第二,家庭背景呈监护不力状态。受害女童多为留守孩子,或单亲家庭孩子。有的寄宿学校,有的被年老的祖父母看管,得不到父母的有效教育。有的孩子因此反感家庭的管束,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崇尚金钱,加之正处在性格叛逆的青春期,极易迷失自己,受性侵后反而走上了违法道路。如2019年9月朱X(14岁)刚上初二,因谈恋爱逃学,与男朋友夏XX发生性关系后,以卖淫为生。朱X对亲属避而不见,打电话与母亲联系只问要钱。某分局侦办的“4.25”组织卖淫案受害人多达16人,大多数被害人父母离异或外出打工导致无人看管的女童。
第三,乡村地区是女童遭受性侵害的高发区。从女童受性侵案件数据的城乡对比来看,2019年以来,五个城区发案共14起,占全部案件的15.38%,其他县市占84.62%。
第四、智力缺陷女童受侵害风险大。农村性侵女童犯罪,多系邻居、熟人作案,对象多选择智障、智障者少女,据统计,受害少女中有精神或者智力障碍的有8人。
2.加害者的基本特征
第一,年龄分布出现低龄化趋势。按照年龄区分,犯罪嫌疑人中80岁以上的2人,50-80岁的19人,18-50岁的56人,18岁以下的38人,其中最小的仅13岁。
第二,职业分布以无业为主,但老师性侵女童占有较大的比例。2019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强奸女童案涉及的115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人员106名,有正当职业的9名,值得注意的是有6名犯罪嫌疑人系教师。我市法院系统受理的猥亵儿童案件中,2019年18个案件有4起侵害人为教师;2020年11个案件有2起侵害人为教师。小学教师往往利用职业便利性侵女学生,谎称补习功课,以小恩小惠笼络后实施侵害,犯罪地点一般选择教室或者补习场所、教师宿舍等,得逞后以恐吓、威胁手段威逼女孩不准告诉父母家人,不准报警。如犯罪嫌疑人周XX担任六年级班主任期间,利用给受害人雷XX下晚自习补课的机会,在其办公室对受害人雷XX实施4次强奸。
第三,熟人相犯的现象突出。2019年市检察系统起诉的侵害儿童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与被害儿童在生活中存在经常接触的熟人关系的,占性侵害儿童犯罪嫌疑人人数19.59%。
(二)案件特征分析
由于女童在年龄上的特殊性,女童受性侵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通过案件分析,可以发现区别于性侵成年女性案件的三大特征。
1.立案时机延误。很多强奸和猥亵儿童等案件发生后没有及时进入司法程序。一部分是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受到性侵的儿童或其家长忍气吞声,没有报案;另一部分是报案后,因为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不能及时立案的现象加大了案件侦破的难度,同时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置更多孩子陷于危险境地,以致罪犯往往性侵多人或犯罪延续很长时间才因偶然因素案发。
2.证据收集困难。第一,在案证据相对较少。强奸、猥亵等性侵案件,因犯罪过程隐蔽、报案不及时,物证没有及时提取导致证据类型单一,多为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等“一对一”的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方面,因被害人大多年幼,认知水平、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对所受性侵行为进行准确、全面的理解和完整、清晰的表述。
第二,受害人证据效力受限。首先,受害儿童尤其是年幼的受害儿童在证言中会省略掉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件,有相对较差的时间观念,并很难用成人的语言去表述差别,导致儿童的陈述通常比较概括,缺乏细节,前后陈述可能出现矛盾。其次,儿童的证词常常受到家长态度的影响。有的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不愿意孩子回忆受害过程,孩子很容易接受家长的心理暗示,弱化甚至虚构事实以减轻心理伤害。有的家长受愤怒情绪干扰,希望尽快找到犯罪人,甚至主观地预设犯罪人,并引导孩子以自己的预设作出证词。家长的主观引导使得孩子在事实认知上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也会出现言语反复不定、事实情节矛盾等严重影响证据效力的错误。
第三,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情形常见。犯罪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女童进行性侵,就是因为其认为女童年纪小,不懂事,自我保护能力弱,犯罪行为不容易被发现。而且犯罪嫌疑人多是预谋犯罪,多次犯罪,事前多进行了反侦查的心理建设。因此,即使公安机关将其抓获,也难以获得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证据。特别是在物证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有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庭审阶段也是拒不认罪。
二、女童受性侵的原因分析
(一)家庭层面的原因
1.父母监护缺位。根据案件统计显示,受侵害女童大多没有和父母共同生活。例如,某县阳光幼儿园原幼儿教师胡XX2018年7月期间,猥亵在其幼儿园上暑假补习班的多名儿童。这些幼儿都是因为暑假在家无人看管,委托幼儿园照管。农村地区是女童受性侵的高发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女童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不能有效承担监护责任。这些受害女童学习期间主要由学校负责吃住,放假后基本处于无人监护的状况。在这种家庭条件下,没有长辈关注她们的身心变化。因此,在有的案件中,受害女童受性侵的时间长达两年,直到怀孕,才被家人发现。
2.家庭缺乏正确的观念。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家庭只注重儿童文化教育,而忽略性教育,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教育。受害女童对于性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电视以及青春期同伴之间偶尔的交流,性保护知识的获得途径几乎没有。在个别案例中,受害女童直到案发时,都没有认识到自己受到了何种侵害。
(二)学校层面的原因
1.学校监管力度明显不足。一方面,对教师的监管不力。教师性侵学生案件的特点是受害儿童多、性侵次数多,影响极为恶劣。学校对老师师德方面的考核机制不完善,缺乏必要的监督。特别是农村学校,招聘老师的门槛较低,缺乏必要的入职审查。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监管不力。12-17岁的未成年人80%以上仍是在校学生,学校的监管措施能起到重要保护作用。但对于学生出入学校的管理,个别学校没有严格的规范制度,尤其是对住校生的查寝、点名等没有落到实处,让学生钻空子晚归,甚至夜不归宿。
2.学校忽视性教育课程的安排。小学阶段,很少有学校开设生理卫生课程。虽然初中学校在生物课上有涉及人类身体发育的内容,但是没有专门的性安全、性保护的课程。高中阶段,受升学压力的影响,即使有部分学校设置了心理健康老师,也主要关注的是学生学业造成的心理压力。
(三)国家层面的原因
我国《刑法》将强奸幼女作为极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司法作为国家层面的最后一道保障,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程序上不能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没有针对女童生理、心理特点的相关立法保护设计,使得受性侵女童司法保护程度较薄弱。诚如前文所说,性侵女童案件在取证方面存在困难,但是,目前相关法律规定还没有有针对性地提供程序上的保障和支持。例如,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没有设置专门的采信规则,没有规定采取技术手段,保障儿童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在程序上没有相关的规定确保询问能够遵循全面、一次的原则,也没有针对儿童特点规定必要的心理干预支持,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保护。
2.缺乏系统化的救助机制。受侵害的女童大多在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家人缺乏监护能力,特别需要得到相应的司法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意见》,对被性侵儿童实施有针对性的司法救助。但工作意见的落实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支持。例如,对身心受伤害较大的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聘请专业力量,提供心理干预和身体治疗方面的支持。但是救助责任由哪个部门承担,如何保障救助费用的有效获得,都没有制度规定。具体规定的缺乏,使得受害女童的救助工作呈现不确定性。有的女童能得到有效救助,有的却没有得到任何救助。
三、预防女童受性侵的相关建议
基于我市女童遭受性侵害案件的现状及原因,建议从社会治理和法律保护两个角度,探讨构建防范女童被性侵的防控体系。
(一)社会治理层面:多元主体合力,落实监护教育责任
1.提升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落实监护人责任。应当将教育、民政、司法等资源进行整合,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女童的“三位一体”联动保护机制。第一,学校加强对学生家长有关女童性保护的宣传指导。学校成立“学生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指导老师。建立心理咨询指导老师与学生家长的交流机制,帮助学生家长与学生顺利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身心变化。第二,探索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立家长学校,配备有社会工作经验或相关心理学知识的工作人员。家长学校可以为外出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临时监护人提供教育帮助,帮助他们与女童正确的沟通,提高监护能力。第三,强化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时,有责任问明未成年人与同行成员的身份关系,发现有异常情况或违法犯罪的,应立即与监护人取得联系,或向公安机关报告。
2.强化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管理,夯实主体责任。杜绝教师性侵女童的措施,主要在于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一是严格教师行业的职业准入禁止条件。禁止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是底线更是红线。必须完善教师队伍的入职审查制度和从业禁止制度,“通过隔离的方式防患于未然”。[1]二是严格学校和教育机关的管理责任。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管理松懈的,应追究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责任。三是构建分阶段的性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对女童的性保护教育是国外教育领域的有效经验,如美国就通过在学校对不同年级的儿童设置不同时长与教学内容的关于性知识的课程来开展儿童性教育。[2]我国可根据中国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生理特点,有针对性的设计性教育课程,分年龄段编写性安全知识教材,并纳入学校课程。
3.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由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妇联、教育局、民政局、卫健委和共青团共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自职责,畅通联系渠道,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例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时统计分析女童受侵害案件的特征,向相关部门提出加强防范工作的司法建议;妇联组织对妇女儿童的重大舆情案件第一时间在媒体平台发声,做好对受害家庭的社会支持工作等等。
(二)司法层面:强化司法救济与保护
1.完善受害女童个人信息保密体制。社会舆论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可能伴随其一生,因此受性侵女童特别容易受到二次伤害,一方面要强化程序性保护,例如对需要受害者做证的程序,采取保护其隐私的技术性手段。另一方面,在侦查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女童特点,进行司法创新。例如,目前H市正尝试在检察院办案区内或者其他合适场所设置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优化工作流程,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空间内,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人身检查、伤情鉴定、辨认等侦查取证工作,着力解决办案过程中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的“二次伤害”问题。
2.构建司法救助机制。第一,培养专业救助队伍,保护女童心理健康。儿童一旦遭受性侵害,往往担心、害怕、恐惧,不敢报案,也不敢和家长坦言相告。建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培训一批掌握儿童心理、智力发展特点的干警、检察官、法官专门办理儿童性侵案件。第二,建议对被性侵儿童实施特殊司法救助。委托专业机构或人员,为被性侵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治疗,并为每名被性侵儿童提供经济上的司法救助。第三,建议出台被性侵儿童身心健康等级鉴定,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确保被性侵儿童进行身心康复治疗支出的费用可以得到支持。第四、建立案件跟踪回访制度。人民法院审理儿童性侵案件,不能一审了之,应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建立跟踪回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