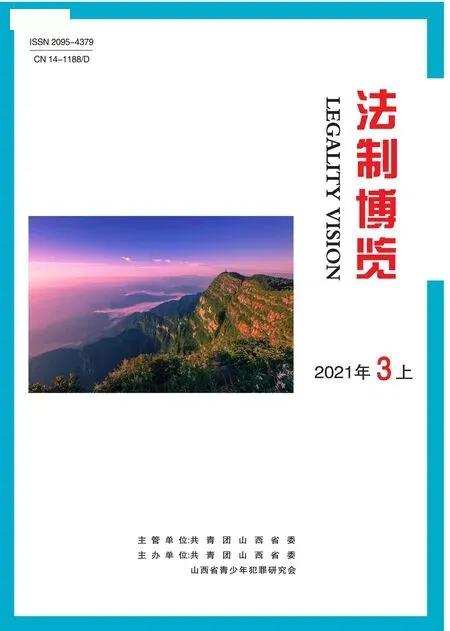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刍议
2021-11-25韩宇桐
韩宇桐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2249)
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该文论及了法律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中国古代法律之不足之处,堪称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法律史。梁启超主要借用西方法律学说、理论、分类和术语构筑中国法律史架构,但为后来的法制史研究所吸收,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1]其后,杨鸿烈承袭梁启超的西方法研究方式,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仍以西方法的原理和概念来研究中国法律,显然和中国传统法律大相径庭。然而正是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中国法律史学科才得以确立了其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学术体系。但总体而言,中国法学界一直都是以西方法的概念和理论来对中国法律史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因而,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令人尴尬。[2]尽管如此,中国法律史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创建的法学学科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其学术史进行梳理和评析,不仅可以为今后的研究做好铺垫,也可以发现研究中的不足,从而对于促进学科发展提供借鉴。
一、法律史学研究的意义
法律史学是指对中外历史上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学科类别。作为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独立的法学基础学科,中国法律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法律史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逐渐地被边缘化。尤其是部门法学的日益发展、法律学术人才的明显分流和大幅度向部门法倾斜,法学史学科人才日渐凋零。法律史学研究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3]法律史学之于法学研究究竟有何意义?进一步说,如果法律史学研究被淘汰了,对中国法学的学科发展有何影响?这都是法科学人们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对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意义,目前尚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认同,在人文学科领域内,法律史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律史学研究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它是维系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在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上,为当下的法学提供反思和借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指导思想上不断创新,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随着学科不断发展,中国法律史学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开始忧心忡忡,“何去何从”“风华不再”“边缘化”,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忧虑。这说明,法律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成果,但在学科内外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并未能给其他学科带来太多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那么法律史学对法学学科发展究竟意义何在呢?
众所周知,法律史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从属于历史经验维度对法教义进行探讨的法经验科学。它与社会学、人类学不同的是,它从时间维度,立足于从当下社会生活获取法的经验。[4]由此可见,法律史学作为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我们要想构建完整的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就要适度加大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史研究的力度,而不是一味地追捧西方法学研究学术史在中国的研究史。即应该用中国本土素材构建中国法律史学在本土的传承,在此基础上利用西方法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法律史学中的陈旧律例和弊端加以适度批判和变革。笔者以为,这对于我们重视中国法律史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内涵,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其意义不言自明。
二、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的重构
“创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早已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法学界就刮起了一阵“方法论”的旋风,这其实也侧面反映了法学界普遍出现的一种“集体焦虑症”,在应用法学越来越喧嚣尘上的时代,作为理论法学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律史学,其存在意义屡遭质疑,地位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该如何构建新的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以更科学更合理的方法对中国法律史作出全新阐释和定位,是值得再次探讨的重要话题。
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一直有这样一种传统研究范式,即习惯于从既有的史料中去寻找和整理法律史学知识。作为法学学科门类中的基础学科,法律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法学应用学科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和理论知识,由此必须秉承“科学求同,史学求异”的史学观。[5]这就造成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两极化,即“法学研究派”和“史学研究派”的针锋相对。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已经陷入了方法论的困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将会影响法律史学今后在学科发展中的命运。而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创新研究方法,重构研究范式。
如何解决中国法学界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是重构研究范式的重中之重。中国法律史学的存在一直都比较尴尬,处于双重边缘的地位,法学界和史学界都不看好它。因而两派围绕这一问题曾展开长期论争。2013年胡永恒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更使论争达到高潮。该文指出:当前的法律史研究应当朝史学化的方向走。其理由竟然是,和法律史研究相比,法学界的研究者史学基础薄弱的问题较为严重。[6]
笔者以为,这种观念混淆了法学和史学的学科分类标准,诚然,作为跨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中国法律史兼具了两个学科的特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法律史始终都是从属于法学学科的范畴,它是法学学科的综合,如果脱离这一学科属性,一味地追捧史学化的研究路径,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以偏概全,这混淆了研究中现象和本质的问题,没有弄清法律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法律史研究既要关照历史,又不能脱离现实,而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怀,才能凸显法律史研究真正的价值意义。
中国法律史研究到底该走哪条路呢?关于此问题,学界始终在讨论,各持己见,没有统一定论。除了上述胡永恒所持法史研究应该“史学化”的观点外,还有诸如“放弃学科之争”“法史研究本土化”之类的观点。不论哪个观点,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重构新的研究范式,就要有鲜明的学科意识,中国法律史研究作为中国法学学科的一部分,这是始终不能改变的,因而笔者以为,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法学化”的路径,“史学化”只能让法学研究越来越脱离法学学科,而最终烟消云散。当然,提倡“法学化”的研究路径,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史学化”的路径和方法,“史学化”的方法应该始终作为“法学化”的研究路径之一,而不应该取代“法学化”。
面对中国法律史的危机,该如何寻找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做好学科定位是关键。长期以来,学界给法律史的定位就是“非法非史”,始终被边缘化。今后,可以多多借鉴诸如社会学或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尽量摆脱法律史研究被“史学化”的尴尬境地;此外,在充分吸纳西方法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要利用中国本土的传统法律知识,在充分体现当代和未来价值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法学”的语境中。如何实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学化”和“本土化”,是今后研究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