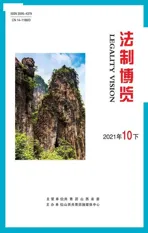关于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效力认定
2021-11-25李洁李谦
李 洁 李 谦
(1.江苏正太和律师事务所,江苏 无锡 214000;2.江苏宏润律师事务所,江苏 无锡 214000)
一、股权让与担保的定义与效力问题
(一)股权让与担保的定义
股权让与担保系指以让渡股权所有权为债权提供担保的交易方式。就此定义,对于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可做以下基本之理解与把握。其一,股权让与担保系基于担保之目的,可以归属于担保的制度范畴。当前,司法裁判相关纠纷时,事实上主要还是比照担保法律制度精神进行处理;其二,股权让与担保系以“股权”为标的物之担保。由此,“股权”二字成为股权让与担保显著的标志。现实之中,股权让与担保纠纷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范加以裁处的现象也大有增长态势。所以,研究与构建股权让与担保制度也决不能对相关公司法规范予以忽视;其三,股权让与担保系以“让与”股权方式提供之担保。由此,任何非让渡股权所有权的现象均被排斥于股权让与担保范畴之外。[1]
(二)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问题
效力问题是股权让与担保的关键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当前物权法定原则下,我国现有的典型担保无法完全满足实践中的融资需求。现有典型担保不仅程序繁复、费用高额,而且信用保障难以满足担保权人利益保障需求,导致具有迫切融资需求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创设各式新型担保,股权让与担保即是其中一种。但是,让与担保毕竟不属于典型担保,故其效力自始即受到质疑。司法实践中不同情形的认定更是使得相关案件的裁判尺度不一,亟待最高司法机关予以明确。
二、股权让与担保的演变
(一)相关裁判理念的演变
早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让与担保协议认识还较为模糊,但随着让与担保纠纷越来越多,最高院对此类问题的认识日渐清晰起来,当前总体倾向认为该类协议应当为有效,这在相关裁判之中亦可得到印证与体现。如2015年最高院在“王某维案”中即表示: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来担保债权实现的方式属于非典型担保中的让与担保,当事人可以依据约定主张担保权利,原一、二审判决将案涉担保方式认定为股权质押有误,对此应予纠正。2018年,最高院在“修水巨通案”中更是十分明确地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通过契约方式设定让与担保,形成一种受契约自由原则和担保经济目的双重规范的债权担保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演变
2004年,在《物权法草案》第二十一章之中曾出现过有关让与担保的条文规定,但由于当时尚有争议,故2007年最终出台的《物权法》并无该制度的身影。
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确认了以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合同担保的合理性,担保权人有权申请拍卖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在诸多法院看来,该解释实质上确立了让与担保的合法性,从而使得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更多地被裁定为有效。
2017年,最高院民二庭第4次法官会议纪要提出,应当按照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股权让与担保协议的性质。在此之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让与担保有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在债务无法清偿时,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可申请对让与担保标的物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债权,但不可请求受让该标的物。
这几次司法政策性质的意见阐述,显然是最高院总结全国法院关于让与担保尤其股权让与担保纠纷审判经验的结晶,此后司法裁判必将更为统一,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效力定将不断获得各级法院裁判之承认。
三、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效力再探究
(一)股权让与担保并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效力的质疑理由首先来自物权法定原则及其相关立法之规定。在主张让与担保协议无效者看来,物权法定乃基本原则与立法精神,任何自行创设非物权法所规定的担保类型均违背物权法定原则,均不应获得法律之承认与维护。[2]
在最开始创设时,可以说让与担保并非担保物权,但经过多年司法裁判后,让与担保已经逐渐被习惯法所认可。因而即便遵循物权法定原则,只要对该原则作适当缓和之理解与把握,以使物权法定原则不断适应并满足现实社会之需要与发展,则亦可以理解为并不实质违反物权法定之基本原则。此外,《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显然涵盖了让与担保合同。由此,再行过于严苛的理解与把握物权法定原则已明显不合时宜,任何再以所谓物权法定原则对股权让与担保进行法律上的限制与阻碍亦违反《民法典》之精神。股权让与担保已为《民法典》所保护并获得法律效力之承认与维护,对此不应再有任何之争议。
(二)股权让与担保并不属于虚伪意思表示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效力质疑还主要来自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认定与判断。“转让股权”仅是让与担保中一个环节的合意,转让担保股权以增强交易信用并以便担保权人权益的保障与实现,这才是双方达成的最为完整的真实合意。而且转让后的担保股权最终既可能回归也可能不再回归至担保人手中,这均是双方达成的存在着可以选择的、非单一方向的、综合性的整体真实合意。因此,仅以担保目的来衡量而即断然否定“转让股权”之手段非为双方之真意,甚至据此又进一步否定整个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效力,实则是以偏概全,是对转让过户乃整体担保交易必不可少环节的无视,与双方对于让与担保整体交易的综合信赖完全相违背。在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下,转让股权并非双方通谋的、虚假的、不拟发生效力之合意,而是为追求担保权益保障所达成的一致的、真实的交易对价安排。
(三)股权让与担保并不属于规避法律之行为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效力之质疑还有可能来自规避法律行为之认定与判断上。关于让与担保乃规避法律行为的主张,主要是认为让与担保实质规避了关于不得流押、流质的禁止性法律规定。这种认识在我国有着长期而巨大的制度惯性认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会将让与担保与规避流押、流质挂起钩来。
关于禁止流质条款之法律规定本身即不具有其合理性。结合《民法典》进一步考量,原《物权法》对应条文所谓不得约定流押或流质的文字内容均被删除,这显然意味着《民法典》对于禁止流押或流质规定的法律松绑,在《民法典》施行后,任何比照禁止流押或流质的规定而否定让与担保乃至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效力的裁判,均属不当。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效力不应再行受到禁止流押或流质规定的法律羁绊。
(四)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效力特殊情形可予排除
在当前理论与实践总体倾向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应作有效看待的大趋势、大背景下,也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之倾向,即不能将效力绝对化来看待。让与担保,尤其是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效力事实上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之影响,任何关于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均当然有效的主张,同样没有照顾到现实中特殊情形救济之需要。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作为协议之一种,显然也遵守各国法律关于合同效力要素之规定,凡违背合同有效要件或存在依法属于无效或可撤销之情形,亦同样可依法宣告无效或撤销。现实之中股权让与担保如果确系以欺诈手段而签订,或确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确有证据证明系重大误解而订立等,并非不可依法寻求相关救济,相关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效力自然得依法予以否定。[3]
四、结论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之协议效力,应当原则予以承认与维护,但例外情形并非不可否认其法律之效力,且对于该类协议的从属特性亦不能予以忽视。当前司法实践已经总体倾向认可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之法律效力,不仅仅是因为司法理念倾向,更是因为主张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与观点并不能成立。采取总体有效的原则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更代表着法律之进步,更能满足社会之普遍期待。
伴随商业之繁荣以及商业风险的提升,伴随公司制度的完善以及公司规模的发展,在中国这块较为古老的法律文明土壤中,股权让与担保定能由当前非典型担保朝着更加典型的担保地位与阵容迈进,人们对股权让与担保也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