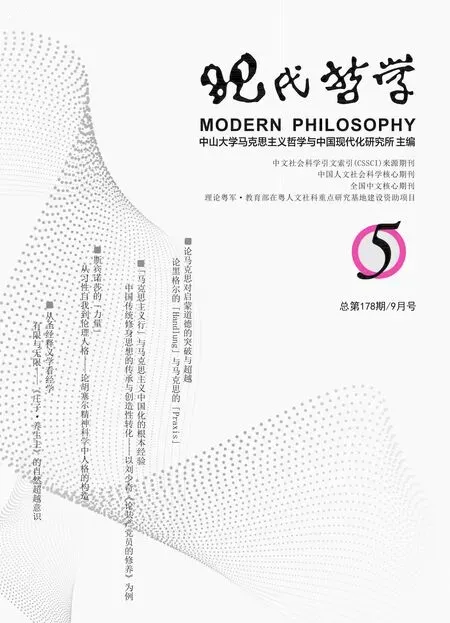再论罪与人性
——重思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的批判问题
2021-11-25高源
高 源
正如奥古斯丁经历了两次皈依(1)这里的两次皈依的界定主要是指在生活上从早年浪子状态向基督教信仰的皈依,在理论上从古典哲学(如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等)向基督教神学的转型。(See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51-177; Robert J. O’Connell,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he Odyssey of Sou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9; Gao Yuan, Freedom from Passions in Augustine (Religions and Discourse), Oxford: Peter Lang, 2017, pp. 1-3.),巴特的思想也经过两次转型,一是从自由主义转向基督教激进主义,二是从辩证神学向教会教义学的理论转型(2)张旭:《上帝死了,神学何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71页。。特别是在第二次转型中,巴特对原罪和人性问题有了新的诠释,即从“上帝启示之道”(Das Wort der Offenbarung Gottes)的视阈来审视“罪-人性-意志的捆绑”问题,并将其植根于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人类学基石之上(3)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9—153、165—176页。。在其《教会教义学》(DieKirchlicheDogmatik)第三卷(1951)与第四卷(1953)中,巴特集中勾勒了他晚年的神学人类学与历史神学图景,诠释了罪的生成以及恩典类比神学中的上帝与人的和解论(4)关于《教会教义学》的结构与内容,参见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175—176页、323—324页;[瑞]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精选本),何亚将、朱雁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75—376页;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4 volumes in 13 parts, ed. by T. F. Torrance & G. W. Bromiley, Edinburgh, pp. 1956-1975;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Zurich: TVZ, 1980。本文关于《教会教义学》的中译文参考何亚将、朱雁冰的译本,英译文参考T. F. Torrance和G. W. Bromiley的译本,在译本有误或翻译不清之处参照原文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Zurich: TVZ, 1980。本文相关引文的黑体均为引者所标。。然而,在最近的巴特研究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奥古斯丁缺乏“天性及本质/本体存有”与“存在存有”(5)本文的“天性及本质/本体存有”指Wesen,“存在存有”指Sein/Dasein,下不赘述。概念的区分,巴特严厉批判奥古斯丁及其影响下的主流拉丁西方神学简单地把罪理解为“善的缺乏”,造成“败坏的天性”与“意志的捆绑”这一绝望的决定论与宿命论的立场,使西方的人性观传统诠释建立在奥古斯丁这种错谬的原罪说与意志决定论上。我们首先考察这一批评性的研究立场及其主要依据。
一、拉丁西方神学根基的危机?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批判的讨论
在其著作《卡尔·巴特堕落预定神学:罪与发展》(KarlBarth’sInfralapsarianTheology:OriginandDevelopment)与《巴特罪与恩典本体论:奥古斯丁主题的变奏》(Barth’sOntologyofSinandGrace:VariationsonaThemeofAugustine)中,曾劭恺(Shao Kai Tseng)梳理了巴特与奥古斯丁关于罪与堕落人性的教义关联(6)See Shao Kai Tseng, 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920-1953, Downers Grove: Inter Varsity Press, 2016; Barth’s Ontology of Sin and Grace: 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Augustine, London: CRC Press, 2018.。特别是在《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7)[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8年第49期;Shao Kai Tseng, “Non Potest non Peccare: Karl Barth on Original Sin and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60:2, 2018, pp. 185-207.一文中,曾劭恺认为,巴特完全拒斥奥古斯丁关于“善性之缺乏”的说法,重新定义了“原罪”“人性”与“意志的捆绑”概念。在曾劭恺看来,奥古斯丁及其影响下的主流拉丁神学将罪视为“善的缺乏”会导致“罪是某种‘第二个神’”的错误结论,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作出像巴特一样关于“天性及本质/本体存有”与“存在存有”的区分;这种区分的缺失导致奥古斯丁所影响的拉丁传统乃建基于一种割裂“恩典”和“自然”的“意志决定论”的错误自由观上(8)[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2、134—139页。。其论证逻辑如下:
首先,在罪的来源这个首要问题上,巴特强调天性与堕落处境中人的存在存有的区分,重新定义“原罪”而拒斥奥古斯丁“善的缺乏”的诠释。不同于以往将人的本性简单理解为“堕落”“扭曲”“有罪”的奥古斯丁学者的界定(9)See Gerald McKenny, The Analogy of Grace: Karl Barth’s Moral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 Paul Jones, The Humanity of Christ: Christology in Karl Barth’s Church Dogmatics, London: T & T Clark, 2008, p. 176;[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23页注脚3。,曾劭恺认为,“巴特强调受造物之天性(Natur)及本质/本体存有在堕落的历史处境(Zustand)中全然完好无缺,而人的存在存有却受此历史处境的命定而全然败坏”(10)[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23页,第124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4、128—129页。。因此,人性全然之腐朽和罪是指尘世历史处境中“存有”的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全然良善的;而罪乃“本体上的不可能”,是“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实动的罪行‘从下方’(von unten)对存在范畴的‘存有’的命定”(11)[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23页,第124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4、128—129页。。此双重命定皆为全然。反观奥古斯丁将恶视为“善的缺乏”或“天性之良善的移除”的原罪观,就会得出“罪是某种‘第二个神’”的结论(12)[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23页,第124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4、128—129页。。
其次,在双重命定的理论基础上,巴特重新定义了“人性”观,即堕落人类保留“上方”的恩典与“下方”的罪这两种特性。人之天性意指人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约历史“从上方”的命定;而人的存有则不断地被“一种邪恶但非常可感知的方式”从下方来命定,是全然而彻底的腐朽(13)[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23页,第124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4、128—129页。。因此,巴特认为奥古斯丁所理解的“败坏的天性”或“扭曲的天性”站不住脚,因为“圣经指控人为彻头彻尾的罪人,但从不否认其完整而未被改变的人性,即上帝所造为良善的天性”,换言之,“人类从没有失去上帝所造的良善天性—连一部分也没有”;因而,奥古斯丁等主流神学家视罪为人之天性的腐蚀与扭曲的观点,是“一种割裂的‘恩典’与‘自然’的自然神学”(14)[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23页,第124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4、128—129页。。
再次,巴特重新定义了“意志的捆绑”,批评奥古斯丁“遗传的罪”的概念。在巴特看来,奥古斯丁传统中将原罪理解为天性之瑕疵的观点,“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决定论[determinism],甚至宿命论[fatalism]的暗示”(15)[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6页,第136—137页,第137—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141页。。对此,曾劭恺认为,巴特批评了奥古斯丁著名的“无能力不犯罪”(non posse non peccare)的命题:“除非以基督论为基础,否则任何建立或理解‘意志的捆绑’这宣言的尝试,必然是一个谬误。”(16)[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6页,第136—137页,第137—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141页。在巴特看来,奥古斯丁预设了人的天性在远处受造时不需要基督救赎的、“有能力犯罪、有能力不犯罪”的自由。而在堕落以后,扭曲的“天性”则命定人失去了不犯罪的能力。这种择善能力的缺失必然导致“使人成为非人之存有的转变”以及意志决定论的结论;因而,奥古斯丁的这套罪论框架是“[巴特]从一开始就致力反驳的”(17)[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6页,第136—137页,第137—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141页。。基于以上论证,曾劭恺得出结论:
巴特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关于意志的自由与捆绑的辩论,都建基于这错谬的自由观。奥古斯丁的错误在于,在他对“亚当的自由”的定义下,“彷佛犯罪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真实(本体)可能性,而不是上帝已然禁止并排除的”——彷佛上帝与蛇都是亚当及夏娃有“自由”可以拣选或弃绝的候选人;彷佛受造之人才是拣选之主。如此,奥古斯丁的思想不但导致了上述奥古斯丁主义-更正教的意志决定论,同时也导致了西方神学当中较为倾向唯意志论(voluntarism)或半佩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的流派所主张的非决定论。(18)[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6页,第136—137页,第137—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141页。
在曾劭恺看来,奥古斯丁影响下的拉丁西方神学对罪与人性的诠释根基,在巴特这里已经面临一种危机。无论从原罪的界定、人性的败坏,还是意志的捆绑等核心神学概念,都遇到根基性的挑战。这使得巴特建议用现在式主动直陈语气的“不能不犯罪”(non potest non peccare)来取代奥古斯丁的“无能力不犯罪”(19)[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6页,第136—137页,第137—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141页。,以展示实动主义本体论(actualistic ontology)诠释下的“意志的捆绑”以及基督在人堕落救赎史中的核心地位(20)[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6页,第136—137页,第137—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141页。。
以上的“天性本体存有/存在存有”双重命定论的视角及对奥古斯丁批评的立场,亦体现于科洛特克(Worf Krötke)、麦科马克(Bruce McCormack)、麦肯尼(Gerald McKenny)等(21)Wolf Krötke, Sin and Nothingnes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d. & trans. by P. Ziegler & C. Bammel, Princeton: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Bruce McCormack, For Us and Our Salvation: Incarnation and Atonement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3; Gerald McKenny, The Analogy of Grace: Karl Barth's Moral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巴特学者的论述中,展示了传统奥古斯丁主义的宗教人类学及其所影响的拉丁神学在进入现代语境特别是巴特神学时面临的一种挑战。基于以上学者批评性的论证思路,我们回归晚年巴特和晚年奥古斯丁一些著作关于宗教人类学的具体叙述,来评估巴特对奥古斯丁的批评的诠释进路及其真实立场。
二、“罪-人性-意志的捆绑”:晚年巴特与晚年奥古斯丁诠释之比较
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三、四卷的写作中展示了其晚年神学人类学的成熟思考。这种思考亦体现于随后发表的《上帝的人性》(Die Menschlichkeit Gottes,1956)与《莫扎特》中(22)Karl Barth, Die Menschlichkeit Gottes, Zürich: Zollikon, 1956; The Humanity of God, trans. by J. Thomas & T. Wieser, London: Collins, 1967; [瑞]巴特:《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朱雁冰、李承言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相较于1914年从自由神学转为辩证神学,巴特称后者为“第二次转变”,其核心是“上帝的人性”的主题(23)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248—255页。,即把神学人类学、教会教义学、创世论、末世论等理论建立于基督中心论之上。也就是说,巴特晚年对恶与虚无、人性论、神义论等问题的思考都是围绕着基督的神圣经论(divine economy; the economy of theology),脱离了自然神学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围绕“罪-人性-意志的捆绑”的主线,我们首先看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三第二部的论述:
在所有其他人中的一个人是耶稣。如果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偶然的和次要的,而是本体地决定性的……[我们与上帝在一起]也是基本的规定性,本原的和不变的。因此,无神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对人来说的本体的不可能性……而罪自身对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本体的不可能性。我们实际地与耶稣在一起,也就是说,与上帝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的存在并不包涵而是除祛罪的。(24)[瑞]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第211页,第207页,第176—177页,第206页。
这里将人的本性与天性的本体论依据定位于“耶稣”上,“人性的本体论规定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即在所有其他人中的一个人是这一个人耶稣”(25)[瑞]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第211页,第207页,第176—177页,第206页。。从本体上看,人的天性是上帝恩典的创造物,是“基本的规定性,本原的和不变的”;但罪被拒斥于本体之外,即“本体的不可能性”。换言之,相对于人性/天性作为本体论上造物主的“是”(Ya),“恶”被拒斥于本体之外,是“虚无”(Das Nichtige)的“不”(Nein)。更重要的是,在创世论中人性作为创造物是上帝的恩典和肯定,但上帝并没有创造让人去作恶的“捆绑的意志”。巴特进一步明确地界定“罪”(作为“虚无”)的本质和来源,以作为人的天性(恩典)的一种对立面。他在《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三部中说:
虚无的特征来自它的本体(Outik)的特性,即是恶……在他[上帝]的创造里,在他的关于创造物的保留和支配中,这在他与人的立约的历史中启示出来,是他的恩典……上帝所不意愿,因而所否定所拒绝的,因而只能是他的opus alienum(另一个作品),他的嫉妒、愤怒和审判的对象,是一种拒绝、抵抗因而缺他的恩典的存在。这一疏远、背离因而没有恩典的存在,就是虚无的存在。这一他的恩典的否定是混乱,是他所不选择或意愿的世界,是他所不能并没有创造的世界……在这个意义是说,虚无真正是背离(priration),是一种骗取上帝的荣耀和权力……作为上帝的恩典的否定,虚无是本来固有的恶。虚无既是使人堕落的,又是被堕落的。(26)[瑞]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第211页,第207页,第176—177页,第206页。
巴特展示了一幅较清晰的神学人类学图景,其基本思路是:首先,人的天性/人性最初是上帝的恩典,是一种上帝和人的一种“立约”,因而是本原上的纯善。而罪(“虚无”)是疏远、背离、没有恩典的存在,其本质是“背离”,其动机是骗取上帝的荣耀和权力(27)“因为恩典本是上帝的荣耀和权力,这也就是虚无企图夺取之所在。接受并生活在上帝的恩典里,这本是创造物被拯救的权利,这也是虚无欲妨碍和破坏的事情。”(同上,第177页。),故而是一种本体的不可能性。其次,在堕落之后,天性并没有因现实存有(sein/dasein)的败坏而失去良善,人性一方面被“上帝与人强有力并至高的实在性”所命定,另一方面“从下方,它(人的存有)不断地……以一种邪恶但非常可感知的方式所命定”(28)See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3, p.477.。这样双重命定的人性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在以上“罪”与“人性”两方面的观察基础上,巴特认为“意志的捆绑”并非指腐败的天性导致邪恶的行为(因为天性在堕落中也是全然良善的),而是堕落历史境遇中败坏的人之存有的“不能不犯罪”:“‘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八章34节)。在这最简短的圣经表述中,我们拥有整个意志的捆绑的教义。‘不能不犯罪’(Non postest non peccare)是我们对罪恶而怠惰之人所当作的形容。”(29)Ibid., p.495.而对人性和“不能不犯罪”的悲惨境遇的拯救则全然地依赖于耶稣基督,正如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四部所说的:
真正的上帝存在并显现于真正的人之中。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光荣驻于耶稣基督之中,凭依至高无上的上帝自己,我们也看见了人:谦卑的、遭责备的和受审判的罪人,失落的被造物。只有如此,只有在审判的烈火之中才能被超度被救赎……这就是真正的人,在这上帝神恩的镜子之中的人自己,上帝的恩宠在耶稣基督之中降予人。(30)[瑞]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第211页,第207页,第176—177页,第206页。
因此,巴特提供了他视角中的“罪”、双重命定中的“人性”和“不能不犯罪”的堕落意志,以及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人类学框架。以此为参照,我们回归晚年奥古斯丁特别是其《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所展示的“双城”视阈下的宗教人类学与历史神学图景,来考察其“罪-人性-意志的捆绑”链条诠释是否出现了危机。
与巴特的基督中心论与双重命定论不同,奥古斯丁将罪的起源、人性的特质和意志问题都纳入其动态的宗教人类学中,从“双城”的视阈特别是双城的起源(exortus)、过程(procursus)、终结(fines debiti)的历史神学中加以审视(31)参见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5—82页。关于“圣史”与“俗史”在奥古斯丁神学中的区分,参见R. A. Markus, Saeculum: 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1.。其中,朝圣之旅(peregrinatio)的主题又与双城概念密切关联,将历史神学(“圣史”)划分为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堕落前伊甸园生活、堕落后双城的交织、末世双城的分离和终结(32)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1.35): “Perplexae quippe sunt istae duae ciuitates in hoc saeculo inuicem que permixtae, donec ultimo iudicio dirimantur; De quarum exortu et procursu et debitis finibus quod dicendum arbitror, quantum diuinitus adiuuabor, expediam propter gloriam ciuitatis Dei, quae alienis a contrario comparatis clarius eminebit.”。在此背景下,我们来看奥古斯丁关于罪的起源以及人性与意愿的诠释。
在《上帝之城》第11卷7-9章中,奥古斯丁认为,起初所有的灵智被造物(“天使”)形成一个圣城(sancta ciuitas),并在其中享受和赞美造物主(33)天使是圣城(sancta ciuitas)中第一批城民。奥古斯丁解释说,当“光”(指“天使”)被造时,天使就在圣城中分享“永恒之光”(指上帝)。关于圣城中“光”与“永恒之光”的区分,参见De civitate Dei 11.9: “Nunc, quoniam de sanctae ciuitatis exortu dicere institui et prius quod ad sanctos angelos adtinet dicendum putaui, quae huius ciuitatis et magna pars est et eo beatior, quod numquam peregrinata, quae hinc diuina testimonia suppetant, quantum satis uidebitur, Deo largiente explicare curabo…ut ea luce inluminati, qua creati, fierent lux et uocarentur dies participatione incommutabilis lucis et diei.” ;以及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2章15节(Confessiones 12.15)、《创世记字解》第1卷第32节和第4卷第45节(De Genesi ad litteram 1.32; 4.45)。。这些被造物遵守自然法(lex naturae)(34)关于自然法(lex naturae),参见奥古斯丁的《论登山宝训》(De sermone Domini in monte 11.32)。,呈现出和谐有序的自然秩序,并形成“众星拱月”般的政治社会来服从上帝的权威(35)De civitate Dei 19.13:“……pax caelestis ciuitatis ordinatissima et concordissima societas fruendi Deo et inuicem in Deo, pax omnium rerum tranquillitas ordinis. Ordo est parium dispariumque rerum sua cuique loca tribuens dispositio.”。然而,双城的产生源于一部分天使的堕落,即拒绝上帝的权威而转向爱自己的权力,并想当然地认为权力和权威属于它们自己(36)De civitate Dei 11.13: “……suo recusans esse subditus creatori et sua per superbiam uelut priuata potestate laetatus, ac per hoc falsus et fallax, quia nec quisquam potestatem omnipotentis euadit, et qui per piam subiectionem noluit tenere quod uere est, adfectat per superbam elationem simulare quod non est. De civitate Dei.”,结果就产生了“罪”(peccatum)和“贪欲”(appetitus; concupiscentia)。至此,这些天使违背了自然法并陷入自我膨胀的虚幻状态中;它们颠倒的意志和爱成为“罪”的根源,并作为一种“骄傲”(superbia)来追逐权力(37)De civitae Dei 12.8: “Deficitur enim non ad mala, sed male, id est non ad malas naturas, sed ideo male, quia contra ordinem naturarum ab eo quod summe est ad id quod minus est…Nec superbia uitium est dantis potestatem uel ipsius etiam potestatis, sed animae peruerse amantis potestatem suam potentioris iustiore contempta. Ac per hoc qui peruerse amat cuiuslibet naturae bonum, etiamsi adipiscatur, ipse fit in bono malus et miser meliore priuatus.”。
奥古斯丁认为,这些天使(即魔鬼)的堕落是由于它们的自由选择的意志。这个堕落表面上是从“不变的好”落向“易变的好”、从“充盈”落向“缺失”、从“安全”落向“不稳定”,但根本上却归因于它们意志和爱的悖乱与错误指向。这样,天使形成两个“城”(集团),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并由两种“爱”来区别,即一个是“爱上帝”(amor Dei),一个是“爱自己”(amor sui)(38)De civitate Dei 11.16: “……cum ordine naturae angeli hominibus, tamen lege iustitiae boni homines malis angelis praeferantur.”。之后,出于嫉妒(inuidus),这些堕落天使(魔鬼)诱骗夏娃犯了罪,并让夏娃引诱亚当堕落。因此,天使集团的分裂(双城的起源)先于人的堕落,堕落天使出于嫉妒而诱骗人类始祖,并将堕落的一些特质(如悖乱、骄傲、爱自己等)传给了人。
初人堕落以后,“自爱”(amor sui)(39)奥古斯丁在《创世记字解》中区分了两种爱:自爱和爱上帝,或曰欲爱与圣爱(De Genesi ad litteram 11.15.20: “Hi duo amores, quorum alter sanctus est, alter inmundus; alter socialis, alter priuatus……”)。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强调私我之爱中欲望的向下的堕落作为“自爱”(self-love)的标志。而且,他指出意志或爱从至善上帝指向自我是“罪的起源”和“恶之根源”。另参见《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 12.9.14)。成为堕落之尘世之城的标志。其根本特质在于人的意志和爱总是从本应指向较高的善(造物主)而转向“自我”或低级的物质(如金钱或权力),形成“恶”“骄傲”与“自然之失序”。如奥古斯丁在《创世记字解》(DeGenesiadlitteram)第11卷13章17节批评摩尼教徒时所说:“恶的意志乃是一种失序的运动,宁向着较低级的善,背离较高的善,结果是,理性被造物的灵,若是以权柄和美德为喜,就是被骄傲吞噬,因此而从灵性天堂之福中跌落,只得在怨羡中枯萎凋零。”(40)[芬]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第34页,第35页,第37页,第77页。
在堕落状态下,奥古斯丁指出,自然秩序的破坏源自人的颠倒的意志(voluntas)和悖乱的爱(amor),而非人性或天性。从创造来看,即便是魔鬼,其本性也是善的,何况人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19卷13章33-37节驳斥[摩尼教]天性罪恶观时说:“因此,存在一种本性,其中没有恶,也不可能有恶;但却不可能存在一种本性,其中没有善。因此即便是魔鬼自己,本性也不是恶,只要还是本性;令其为恶的乃是悖乱。”(41)[芬]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第34页,第35页,第37页,第77页。
在此,奥古斯丁明确指出,被造物即便在堕落状态,其本性或天性都是善的,即便魔鬼也是如此。在《上帝之城》第22卷17章9-10节,奥古斯丁再一次确认,被造物的自然本善不论在堕落前、在尘世,还是末世的新造世界中都被保存而不会有任何削减,“身体所有的缺陷都除去了,本性却得以保存”(42)[芬]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第34页,第35页,第37页,第77页。。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的恶和堕落的根源乃是意志和爱的悖乱。然而,堕落后的意志和爱呈现出一种“重量”,即 “意志和爱之重”(pondus voluntatis et amoris)。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11卷16章26节论证说,正是悖乱的意志和爱的重量,破坏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秩序和安宁(43)[芬]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第34页,第35页,第37页,第77页。。在“意志和爱之重”的作用下,无论“人无能力不犯罪”,还是“不能不犯罪”,其根本思路都指向堕落状态的意志,而不是人性或天性。正如罗明嘉(Miikka Ruokanen)所指出的:
在奥古斯丁看来,恶并非本质,因为上帝从未创造过恶。毋宁说,恶是本质的缺乏(privatio essentiae),也就是缺乏从summum bonum(至善)中流溢出来的善。恶之基础在于意志与爱的悖乱,也就是将善置于所有存在与善的源泉之外。“恶并非正面的本质:善之丧失即名之为‘恶’”。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魔鬼自身之本质始终为善,以及他对人类生活中恶之存在的理解,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在本体地善的自然框架中,这些才是可能的。(44)[芬]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第34页,第35页,第37页,第77页。
至此我们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关于“罪”。巴特将“罪”视为疏远、背离、没有恩典的存在(“虚无”),并将其本质释为“背离”以及骗取上帝的荣耀和权力的阐述。奥古斯丁在双城视阈中以堕落的天使(魔鬼)为例,将“罪”诠释为“善的缺乏”以及失序的运动而对上帝的背离的说话。两者如出一辙,特别是两者在拒斥“罪”或“恶”的本体的不可能性方面。
第二,关于“天性/人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巴特强调受造物之“天性及本质存有”与堕落历史处境中人的“存在存有”的区分,强调天性即便在堕落状态中依然完好无缺。这种阐述在奥古斯丁关于受造物的本性/本质的诠释中可以找到原型。特别是奥古斯丁在诠释恶的来源时,将其视为意志与爱的悖乱颠倒,而非本性/天性的败坏;同时,他用“上帝的形象”(imago Dei)的扭曲来指称尘世的心性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受到堕落的污染(天性/自然本性依然没有削减),虽然他没有直接是用“本质存有”与“存在存有”这样的术语。
第三,关于“意志的捆绑”。奥古斯丁用“意志和爱之重”的概念来形容“无能力不犯罪”之意志官能的败坏(corruption of the faculty of the will)。而且,从以“自爱”为标志的堕落地上之城视角看,意志的运动往往背离较高的善而指向“自我”甚至更低秩序的存在,展示了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自然的失序和败坏。因此,巴特所表述的“不能不犯罪”乃是奥古斯丁“意志与爱之重”理论的应有之义。
基于这些观察可知,巴特并非是对奥古斯丁神学传统的反叛,而是对拉丁教父学传统的回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本质存有/存在存有”“不能不犯罪”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晚年奥古斯丁神学人类学的题中之义。因此,所谓“巴特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关于意志的自由与捆绑的辩论,都建基于这错谬的[奥古斯丁]自由观”,“巴特认为,奥古斯丁主义及宗教改革传统所理解的‘败坏的天性’或‘扭曲的天性……颇站不住脚’”(45)[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137—138、140页。,这些表述都是经不起深入推敲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晚年巴特在其《教会教义学》(特别是第三卷和第四卷)中建立了基于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人类学价值坐标系。其中,关于罪与人性问题,巴特从“上帝的人性”视角出发,拒斥“罪”(作为“虚无”)在本体上的可能性以及“天性的扭曲”这种观点,并进一步区分了“天性及本质/本体存有”与“人的存在存有”两种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当前一些巴特研究者所展示的,奥古斯丁影响下的拉丁西方神学对罪与人性的诠释在巴特这里已经面临了一种危机,无论从罪与人性的界定,还是意志的捆绑等核心神学概念,都遇到根基性的挑战。相反,奥古斯丁在其晚年的论述中,强调罪或恶之基础在于意志与爱的悖乱,而不在于被造物的良善本性(“即便是魔鬼,其本性也不是恶”),特别是“意志和爱之重”不仅指称“无能力不犯罪”的官能性朽坏,而且包括“不能不犯罪”的真实堕落境遇。因此,所谓的巴特对奥古斯丁主义的批评,不是真的挑战奥古斯丁神学传统的根基,而是回到拉丁教父传统,并进一步发展出以基督教中心论为基础的宗教人类学框架,拓清拉丁教父神学传统中罪与人性观所含蕴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