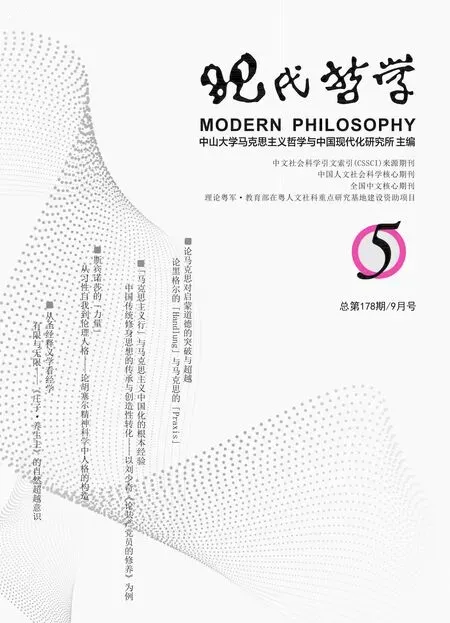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
——论《启蒙辩证法》的犹太人问题之思
2021-11-25郭延超
郭延超
阿多诺在其发表于1959年并于1962年复述的演讲“清理过去的含义”(The Meaning of Working Through the Past)中,在以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等为代表的苦难被越来越多人忘却、反犹主义浪潮复起的现实背景下,强调不能遗忘苦难(1)See Theodor W. Adorno, “The Meaning of Working Through the Past”, trans. by Henry W. Pickford,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9-103, 307-308. 关于这篇演讲的思想内涵,参见罗松涛:《奥斯维辛之后的道德沉思——从阿多诺“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一文谈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这一强调显然不是为了简单记录历史,而是为了警醒时人,类似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这样的苦难可能重现。阿多诺在与霍克海默十余年前合撰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警醒(2)霍克海默、阿多诺起初并未将反犹主义问题作为他们研究的焦点。直到 1938 年,霍克海默才在《The Jews and Europe》一文中第一次正式专门讨论反犹主义问题。只是彼时的霍克海默仅仅认为,反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上升阶段’的一个暂时性产物”。随着局势的愈加恶化,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很快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政权所实施的反犹主义行动已经不再是某个边缘问题,而是关于人类自身前景的根本问题。(See Robert Fine and Philip Spencer, Antisemitism and the Left: On the Return of the Jewish Ques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3-56; 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Antisemitism”, ed. by Peter E. Gordon, Espen Hammer, Axel Honneth,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178-180; Marx Horkheimer, “The Jews and Europe”, trans. by Mark Ritter,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by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p.92.),对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对此,有研究者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同样“受到反犹主义成见的影响”(3)Jack Jacobs, The Frankfurt School, 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78.,反犹主义“在犹太人的冲动那里有其源头”(4)Jonathan Judaken, “Blindness and Insight: The Conceptual Jew in Adorno and Arendt’s Post-Holocaust Reflections on the Antisemitic Question”, ed. by Lars Rensmann and Samir Gandesha, Arendt and Adorno: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94.。这无疑误解了两位思想家的本意。在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问题上,《启蒙辩证法》没有停留于简单的经验分析,更不要说将其归咎于犹太人自身的某种特质。
事实上,霍克海默、阿多诺延续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视作普遍性问题的思路,认为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同样具有普遍性。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病灶在启蒙理性自身,以及人类在孩童时期就形成的对于‘陌生’的恐惧心理”(5)马欣:《“启蒙理性”与“非家异感”——“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及当代启示》,《学术交流》2016年第8期,第56页。。这一观点准确地把握了反犹主义根源的普遍性质,但在对这一普遍性根源的理解上,或多或少忽略了《启蒙辩证法》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的继承,以致可能部分遗失了《启蒙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方面延续至今的深刻性。
一、作为普遍性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上,《启蒙辩证法》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与马克思一样,霍克海默、阿多诺也将看似只涉及犹太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性问题,视作有着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也正因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的普遍性质,犹太人所遭遇的问题同时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遭遇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下卷的分析,北美社会中的“现实的世俗犹太人”(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遭遇的自我异化问题有着普遍性根源。这一普遍性根源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使以金钱为唯一原则的金钱拜物教这一新的宗教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原则,金钱拜物教这一实际的“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实现普遍的统治”(7)同上,第54页。。这里,“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8)同上,第52页。。而北美社会中的“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之所以最突出地遭遇到这一问题,只是因为他们对“实际需要,自私自利”(9)同上,第49页。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刚好与市民社会的金钱拜物教原则相契合(10)参见张双利:《再论马克思的扬弃宗教的道路——从“犹太人问题”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 6 期,第29页。。在马克思看来,世俗的“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页。,其他社会成员也将因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遭遇到与北美社会中的“现实的世俗的犹太人”一样的自我异化命运。
与马克思一样,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也将犹太人问题处理为普遍性问题。他们很清楚,时人针对犹太人这一特定群体的憎恨与排斥的现象处处可见,这样的现象有着各式各样的缘由,带来不同类型的反犹主义。《启蒙辩证法》的“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章(以下简称“要素”)中,通过经验分析的方法,根据不同缘由,归纳出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四种反犹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被自由主义观念同化的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普通民众的反犹主义、资产阶级的反犹主义(12)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3—182页。在本文直接或间接引用《启蒙辩证法》之处,笔者以渠、曹的译文为主,并根据Edmund Jephcott的英译本进行部分改动,在改动时会同时参考林宏涛的译文,并仅标注渠、曹译本的页码。(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林宏涛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年。)。但就像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没有停留于对北美社会的世俗犹太人的特别关注一样,霍克海默、阿多诺也没有停留于对不同反犹主义类型的经验,而是将他们所处时代的犹太人遭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带来极致苦难的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问题,视作具有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犹太人的某些宗教因素与强权者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素是如何被强权者调用的。强权者之所以能够最终调用这些要素,其缘由在于以自我保存理性为核心规定性的现代启蒙,在反对基督教精神的过程中,可能反过来陷入基督教精神存在的缺陷。那么,自我保存理性所可能陷入的缺陷究竟是什么?这种缺陷如何影响到法西斯主义式的强权者施行野蛮的反犹主义活动?下文将依次考察《启蒙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重要思考。
二、基督教精神与自我保存理性的缺陷
在《论犹太人问题》下卷中,马克思在考察市民社会成员的自我异化问题时,更多关注犹太教的世俗基础,而非犹太教在宗教上区别于基督教的地方。与马克思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不仅特别关注到时人过分贬低犹太教的现象,而且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考察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13)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82—186页。。对他们来说,考察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差异,不是为了论证这一差异足以构成反犹主义的真实根源,而是为了论证:作为现代启蒙之核心规定性的自我保存理性,在反对基督教精神的时候,会同样陷入基督教精神在反对犹太教精神时所体现出的缺陷。对这一缺陷的考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反犹主义的普遍性根源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准备。
(一)基督教精神在反对犹太教精神时所体现的缺陷
对此,《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断定是:声称自己是高于犹太教的下一个环节的基督教,却堕落到巫术时期(犹太教诞生之前)的偶像崇拜水平;它将人对上帝的断定认作上帝本身,失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知。对此,霍克海默、阿多诺分别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原则性差异及其实践效果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在讨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原则性差异时,霍克海默、阿多诺特别选择从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着手。犹太教的上帝从自然的盲目循环中抽身而出,具有不可与之比较的超越性地位,对犹太人而言具有绝对的权威。这种绝对的权威特别体现在犹太教的律法传统中:犹太人将律法视作上帝启示的体现,不会将其简单等同于人对世界所作的有限断定,以此守住上帝与人之间的无限距离。相反,基督教特别突出了上帝对人的恩典与爱,认为上帝之恩典与爱是经由人子基督之死启示给世人的(14)参见同上,第20、183—185页。。作为中介的人子基督成为上帝与人之间建立直接关联的唯一中介,这一中介克服了上帝与人之间的无限距离。正是在此,基督教与犹太教在原则上拉开了根本的距离。总之,在犹太教那里,上帝与人的关系以上帝设定的律法为中介,这一中介表明上帝具有超越于人的不可通达性;而在基督教那里,上帝与人的关系以人子基督为中介,这一中介在作为有限者的人与作为绝对者的上帝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就缓和了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而言,基督教似乎比犹太教更进步。
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基督教仍然落后于犹太教,因为基督教再度陷入偶像崇拜。对此,霍克海默、阿多诺无疑同意人们通常的断定:作为绝对者道成肉身之结果的人子基督不仅意味着绝对者之成为有限者,而且意味着有限者之成为绝对者(15)参见同上,第183—185页。。但他们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更多关注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实践内涵:基督教教会“要求具有或是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或是新教仪式的信仰,它能让人们看到救赎之路……基督教或者超自然主义都变成了一种巫术仪式”(16)参见同上,第185页。。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基督教经由教会将人对上帝的断定认作上帝本身,并将在此断定的基础上人为制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视作上帝对人进行救赎的具体方式,人们一旦确信这种断定及其衍生的行为规范,就陷入偶像崇拜。基督教原本意图借由对人与上帝之间距离的缓和,建立起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联,却在实践中不仅否定了上帝之于人的权威,而且将人之权威放大到绝对。如果说在犹太教那里有着对上帝的永恒超越性的确信以及对人的有限性的自知,那么在基督教这里这一否定性环节彻底付之阙如。
(二)自我保存理性在反对基督教精神时所体现的缺陷
对此,《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断定是,以反基督教精神为首要使命的自我保存理性,反而可能像基督教精神一样,陷入偶像崇拜。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反基督教精神的背景下,现代启蒙理性以普遍的先验自我为基础,在认知活动与实践活动中谋求先验自我意义上的自我保存(17)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第68页;[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5—28页。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就开始使用“为了自我保存的理性”(a reason……for the purpose of self-preservation)这样的说法来刻画《启蒙辩证法》所要特别加以考察的理性。(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380.),而不再依赖于对上帝以及作为其俗世代理人的教会的信靠。
通过《启蒙辩证法》的各处论述可以发现,两位思想家受教于康德以及费希特、黑格尔等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将自我保存理性的规定性区分为认知理性、道德理性、批判理性。这三重规定性分别是指:每个个体都能凭靠各自的先验知性对外部自然进行认知;每个个体都能凭靠各自的自由意志自主规定各自的行动;人们对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自觉,比如被重点引用的费希特的“对思想的思想”(think thinking)、黑格尔的“有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等思想就特别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18)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0—21、25、81—83页。。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自我保存理性仅仅“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普遍性工具,完全是目的导向性的”(19)同上,第26页。,“任何可以被人们引证为一种所谓理性洞见的实体性的目标都是一种妄想、欺骗”(20)同上,第81页。。这意味着不仅道德理性规定性会被祛除,批判理性规定性也会丧失。道德理性规定性被祛除,是因为道德理性要以实体性的先验自我为基础,而实体性的先验自我会被当作幻象剔除掉。同理,批判理性规定性也会丧失。对康德而言,人之所以能够守住批判理性规定性,是因为人们对知性的运用,要在非实体性的理性理念的范导作用下进行,这使得人们在追求统一的知识体系的同时,还能坚守住对知性的有限性的自觉。但非实体性的理性理念,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时代却被当作能带来幻象与欺骗的实体而予以剔除。一旦能够对知性起到范导作用的理性理念被剔除,人们就无法顾及知性本身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只剩下单薄的知性这唯一内涵,知性自此成为各个生活领域的唯一根据。
那么,被置于绝对高度地位的知性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启蒙辩证法》的回答是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也就是说,作为理性形式之一种的知性,其形式性已经进展到形式主义的地步。奥德修斯刚刚逃脱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控制,就急切宣称其真名“奥德修斯”,而不再狡猾地自称“无人”(Nobody),“在语言中发现了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谓的‘形式主义’(formalism)”(21)同上,第57页。,即为霍克海默、阿多诺为论证这一点而特别分析的一例(22)《启蒙辩证法》借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途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一点。相较于混淆名称与事物本身的独眼巨人(代表自然),奥德修斯(代表自我保存理性)是知晓名称与事物本身之间的差异性的,当他狡猾地自称“无人”时,独眼巨人无法正确指认出他本人。可以说,奥德修斯身上体现了“唯名论这种资产阶级思维原型”。但离开独眼巨人掌控的奥德修斯很快又向其呼喊自己的真名,因为奥德修斯最终确信名称所代表的知性这一理性形式与事物本身之间有着同一性,如此才能守住自我的同一性,以防止在难以应对的自然面前,真的变成“无人”,被自然吞噬。与此同时,其代价也是严重的:原本具有唯名论性质的理性最终陷入形式主义的境地。(参见同上,第56—57、60—66页。)。一旦成为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反巫术的自我保存理性就会反过来陷入巫术的境况,即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特别表现为以数学为唯一表现形式的计算理性,它“把彻底数学化的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以为这样做就能够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去”(23)同上,第21页。。其结果是,停留于计算理性思维的人们会认为事实具有“永恒性”(24)同上,第23页。从而彻底服从于它,既不再可能追问既定事实之根据何在,也不再可能承认外部世界当中有人的认知能力无法认知的内容。总之,与马克思在论及犹太人问题时弱化对宗教差异的关注的做法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透过对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差异的特别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对基督教精神的自我保存理性,最终也可能陷入基督教精神在反对犹太教精神时所陷入的偶像崇拜缺陷。
那么,自我保存理性所可能存在的这种缺陷,如何影响到法西斯主义式的强权者所施行的反犹主义活动?对此,《启蒙辩证法》接续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将自我保存理性置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
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自我保存理性划向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的趋势,只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才逐渐成为现实。受教于尼采对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看法,他们进一步强调:在这一趋势成为现实之前,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在作为权力工具的同时,还能对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作用;一旦这一趋势成为现实,自我保存理性就会丧失对权力的限制,彻底沦为权力工具(25)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关于《启蒙辩证法》对转型前后的资本主义中的自我保存理性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本文认同张双利的基本观点,并将基于其观点,进一步分析《启蒙辩证法》在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问题上的深刻看法。。彻底沦为权力工具的自我保存理性,能够被强权者调用来进行虚假投射活动。在这一投射活动中,犹太人被特别地挑选为投射对象,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得以发生。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会被强权者特别地挑选为虚假投射的对象?他们分两步展开分析。
(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的自我保存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单向关系
霍克海默、阿多诺继承了尼采对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阐释,并对之做了进一步补充。根据《启蒙辩证法》的分析,尼采对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如下判断:第一,启蒙理性能够成为社会统治依傍的重要工具,社会统治因之显得具有合理性;第二,启蒙理性作为不同于权力的另一个原则,能够对权力加以限制,这尤其体现在它对社会统治者的行为、言语中的虚假性的揭示(26)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42页。。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尼采眼中的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双向关系适用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但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型为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这种双向关系就逐渐退化为单向关系,即作为现代启蒙理性的自我保存理性只能被用作权力的工具,而不再能同时对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作用。首先来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一方面,自我保存理性中的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规定性,成为资产阶级支配被雇佣劳动者的理性工具。两位思想家指出,“工具变为自律性的”(27)同上,第33页。,结合前文,这至少是说人们凭靠认知理性制造的机器不会被任何统治力量独有。而道德理性又“包含了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由观念”,这一强调普遍尊重的道德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思维”(28)同上,第8、85页。,它表达的是普遍自由与平等的资产阶级理念。但无论是结合马克思的论述(29)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论及的,资本家与被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建基于抽象平等原则的契约关系,为资本家占有私有财产、维持其相对于劳动者的支配关系提供了理性形式,就主要涉及这一点。,还是依托《启蒙辩证法》的一些论断,比如“哲学家作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正在一同实践他们在理论中所谴责的权力”(30)[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84—85页。,都能看到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背后站着社会统治力量。
另一方面,自我保存理性又不只是权力的工具,它还能对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自我保存理性中的批判理性维度会促使人们保有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自知,也就是知晓理性对世界的断定无法涵盖世界的全部内容。人们凭靠这种自知,就不会让统治者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此外,这还因为“人的自我保存理性被实现为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体系,统治者必须以所有人的自我保存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统治”(31)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这同时意味着,统治者也要受制于这一普遍性要求的制约(32)可以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所论及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所必须凭借的现代国家、法律等理性形式,能够同时作为被雇佣工人的理论支撑,支撑他们为谋求平等的合法权利而展开的斗争活动,也主要涉及这一点。。基于这两点原因,人们就能够保有对权力进行反思与限制的可能性。可是,一旦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自我保存理性就将彻底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33)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启蒙辩证法》对其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至少做了如下两点指认:
第一,“大企业消灭独立的经济主体,一部分是通过替代经营自主的商人,另一部分是通过将工人转化为工会的对象,彻底摒弃了道德决定的经济基础……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体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被他们仅有的对机制的贡献替代”(3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06—207页。。这意味着,由普遍享有抽象人格性的自由企业主们支撑起来的平等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转型至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就彻底失去其现实基础。隶属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的道德理性,自此再也无法成为支撑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系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机制的绝对服从。
第二,“只要那些仍旧被雇佣来操作机器的人们,只靠为社会统治者工作不多的劳动时间就能保证自己生活的话,那些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庞大数量的人口就会被训练成为一支后备军,并作为一种附加的物质力量服务于社会体制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宏伟计划……他们被贬低为单纯的管理对象,而管理在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语言与知觉)都起着作用,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有关客观的必然性的幻觉,他们认为自己在这种必然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35)同上,第34页。。这是指在高度垄断且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下,有大量社会成员成为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甚至发展成为单纯的物质材料,强权者能够任意处置他们。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实际沦为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如此单薄的理性无法对社会统治力量关于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断定进行反思,更不要说对社会统治力量进行限制。
(二)强权者对犹太人原始拟态特质的认定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基本断定是:强权者可以调用形式主义性的自我保存理性进行虚假投射活动,犹太人被特别地视作投射对象。对两位思想家来说,沦为权力工具的自我保存理性可以被强权者调用来进行虚假投射活动。关于投射(projection),他们有如下判断:第一,投射是人类“史前动物时期的遗产,是自我持存和获得食物的一种机制,是人体准备用于斗争的器官的延伸。所谓作好斗争准备,实际上就是高级动物对周围动静的一种反应”;只有当人类认定周围环境可能存在危险并为之做好防御工作,才能有更高的生存可能性,而这与“对象的意图”为何完全无关(36)同上,第195页。。第二,一旦人类进入文明时期,投射行为就逐渐开始包含人对自己关于外部力量的认定加以反思的环节。人在进行投射活动时,能够在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他人的思想、情感之间做出区分,“把从客体那里获得的东西归还给客体”(37)同上,第195、197页。,这种区分能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思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们在投射行为中,能够同时自觉到自己对外部力量的认定可能与外部力量本身不同。
但是,虚假投射与投射行为的这两层内涵不同。关于虚假投射,《启蒙辩证法》给出它的两层内涵:第一,投射行为失去原本具有的反思环节,自此不再会受到任何限制,虚假投射活动的发出者的权力欲可以被肆意释放。“主体在两个方向上丧失了反思能力:由于它不再反思客体,它也就无法再反思自身,它丧失掉了辨别力……它并没有通过省察自身的方式来破译构成自己权力欲的秘方。”(38)同上,第197页。第二,不再受到任何限制的投射行为可以对其投射的对象进行任意判定,完全不顾及对象本身具有怎样的特质,它甚至会“把最亲密的朋友说成是敌对者……没有限制地把自己的内在东西施予外部世界”(39)同上,第194、197页。。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我保存理性因为已经失去批判理性、道德理性这两种规定性,彻底形式主义化,从而成为社会统治力量进行虚假投射活动的最佳工具。
既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强权者能够调用自我保存理性,肆意进行虚假投射活动,那为什么特别地选择犹太人作为投射对象?这是因为,犹太人被强权者指认为是具有不被自我保存理性所容的原始拟态特质的族群,而强权者又是基于犹太人的某些宗教因素与他们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素,才做出这样的指认。透过两位思想家的论述,我们可以重构他们的论证过程:
第一,《启蒙辩证法》叙述了两个层次的拟态(mimesis)(40)例如,Owen Hulatt、陈旭东已比较集中地考察了《启蒙辩证法》的拟态概念。但他们更多考察的是拟态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被理性抑制的原始拟态层面,并没有特别关注到抑制原始拟态的理性(特别是自我保存理性)本身也是一种拟态的另一层面。(See Owen Hulatt, “The Place of Mimesis in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pp.351-364;陈旭东:《重思〈启蒙辩证法〉——奥德赛回乡之路的双重解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271页。)。巫术时期的原始拟态是人类在令人无比恐惧的自然面前的一种有限的应对方式,它表明人类对自然的至高无上地位有着真正的承认。自我保存理性同样是一种拟态,但已不再是原始拟态,它既能显得好像有着对自然之优越性的真实承认,又能在这种显得真实的承认中狡猾地与自然拉开距离,逐渐形成对自然的宰制。奥德修斯(代表自我保存理性)途径塞壬海妖(代表原始自然)时,以对死亡进行拟态的方式逃离了原始自然的支配,即为霍克海默、阿多诺为论证这一点而特别分析的一例(41)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7—8、27、51—56页。。
第二,作为另一拟态形式的自我保存理性会禁止任何原始的拟态性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古老恐惧,而且其中蕴含着的对人之有限性、自然之至高无上地位的真正承认,会对社会统治力量构成严重威胁。结合《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可知,这是因为社会统治力量原本是借由对自然的解释来安排社会秩序的,一旦人们意识到自然拥有着不可被完全解释、把握的一面后,就可能会对社会统治力量的这种安排产生质疑(42)《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在叙述启蒙文明史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共同体内部的统治者对其他成员的支配关系往往是借由统治者对令人畏惧的自然的解释来实现的,社会与权力之间具有统一性(the unity of society and power),“在社会整体中被建立起来的权力也为社会整体赋予更多的凝聚力与力量”。但赋予社会整体以凝聚力的权力,如果借由对自然的解释没能实际保全社会整体,就将面临来自社会成员的质疑。换言之,权力借助于对自然的解释以维持社会整体的持存,从而获得现实效力;但作为内在于权力之中的对社会整体持存的要求,又对权力构成限制。比如,在神话环节(启蒙的第一个环节),虽然共同体内部有着等级之分,与自然的实际交道(特别是重复的劳作)被安排给服从者,统治者连同祭司所要做的是,“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阐述、记载和解释本原……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占有者对服从者的统治就能够是任意性的,因为权力之落实必须借助于维持共同体的持存这一名义,而这一普遍性的名义又会反过来对权力进行制约。(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5—6、17—19页;张双利:《启蒙与社会统治:再论〈启蒙辩证法〉对权力的批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22页。)。
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强权者基于犹太人的宗教因素与他们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素,指认犹太人具有原始拟态特质。就宗教因素来说,犹太教强调对偶像崇拜的彻底拒斥,以坚守住上帝及作为上帝造物的自然的至高无上地位。就自然属性因素来说,尽管“丑陋的大鼻子犹太人的描述……很可能是最被广泛相信的关于犹太人的谎言”(43)[以]埃雷兹·莱文:《反犹谎言的五种形式》,李兰兰译,《以色列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7页。,但在法西斯主义式的强权者那里,他们仍然认定犹太人有着与其他族群相异的鼻子并偏好嗅觉。按照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分析,在强权者眼中,被他们认定偏好嗅觉的犹太人,体现了“一种对低等生存方式的原始渴望,一种与自然环境直接和谐一致的原始渴望”;与能够在观看活动中与对象保持距离从而得以保持自我同一性的视觉活动相比,这种渴望意味着自我完全消融于自然、丧失其自身的同一性(44)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91页。。被强权者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这一自然属性因素,连同前述犹太人的宗教因素,共同构成强权者指认犹太人具有的两种原始拟态要素。对强权者来说,这两种要素折射出犹太人对自然之优越性地位的真正承认,而这严重威胁到既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基于此,强权者将他们指认为虚假投射的对象。由此可以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犹太人遭遇极致苦难,其真实缘由是他们被强权者特别地判定为能够严重威胁到社会统治秩序的异在力量。
四、小 结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厘清了《启蒙辩证法》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深刻看法。霍克海默、阿多诺延续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思路,将看似只关涉犹太人这一特定群体的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问题,视作具有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根源,《启蒙辩证法》的看法是:在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型的前提下,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堕落为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彻底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对这一普遍性根源的呈现,首先可以解释犹太人为何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被特别视作需要加以清除的对象:这既不是因为犹太教本身,也不是因为犹太人的自然属性本身,而是因为犹太人的某些宗教因素与强权者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素,被强权者指认为是具有威胁到统治秩序的原始拟态特质,基于这一指认,强权者在调用自我保存理性进行虚假投射活动以维持统治秩序时,才会特别地将犹太人视作投射对象。
除此之外,这一分析的更深层用意在于提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之时,很可能有部分人群将因为上述普遍性根源依然存续的缘故,遭受与二战时期的犹太人一样的命运。换言之,像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那样的社会灾难,可能以非反犹主义的面目再度出现,而非只关涉犹太人这一特定群体。阿多诺在二战之后,仍然以各种形式向德国民众反复叮咛,绝对不能忘却人们(尤其是犹太人)不久前遭受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对反犹主义的普遍性根源可能存续这一点依然忧心忡忡。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危机的今天,“以反建制、反精英、反特定人群、反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西方民粹主义不仅盛行,而且愈渐趋向可被统治者肆意利用的“反动的民粹主义”(45)参见张双利:《再论〈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纪念中文版发表100周年》,《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比如它可以“借助民族主义对他者的排斥,重新塑造民粹主义所需的‘敌人’”(46)参见邹诗鹏、张米兰:《近年来西方关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现象的研究及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现实趋势下,霍克海默、阿多诺七十余年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上述洞见愈加显示出深刻的预见性与批判性。至于他们回应犹太人问题方面的想法,特别是对苦难的铭记这一点(47)阿多诺的许多著述都有关于铭记苦难的重要论述。除上文提及的题为“清理过去的含义”演讲,阿多诺早先参与撰写的《启蒙辩证法》也表明,正因为有了对苦难的冷静记叙,人们才可能会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后来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甚至认为“那种生动地表达苦难的需要是一切真理的条件”。阿多诺之所以在诸多论述中反复强调要铭记苦难,是因为对苦难的铭记能够为反思与批判法西斯主义式的新野蛮主义提供最低限度的契机。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一动机,阿多诺才会在二战后严肃地思考以“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为第一任务的教育问题。(参见[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74—76页;[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页;[德]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孙文沛译,邓晓芒校,《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在应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上述现实趋势方面又能提供什么重要启示,仍是需要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