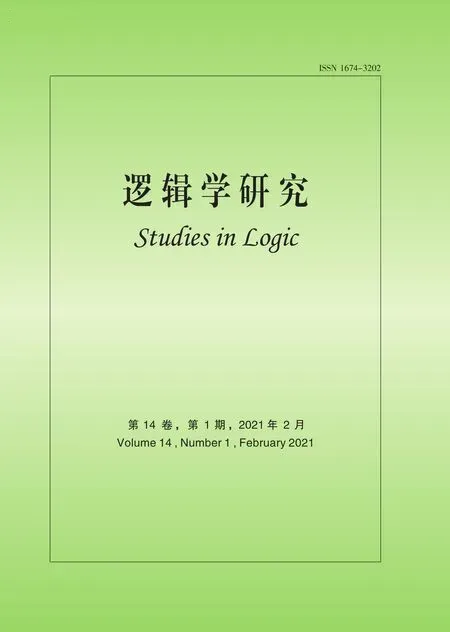从“有( )”式表达看何物存在
——兼论西方哲学的汉语研究
2021-11-25李巍
李巍
虽然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专属门类,但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即何物存在,并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属问题。因为与本体论的复杂形式构成鲜明对比的正是本体论问题的简单性,所以只能说非西方的思想传统对何物存在的回答不同于西方哲学,却很难说这个简单问题在非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根本不被涉及。当然,何物存在的非西方理解,尤其本文关注的来自中国思想的洞见,为什么值得讨论,这并非不言自明。特别是,如果是为了(1)在中国思想中寻找与西方本体论相对应的成分,或者是为了(2)揭示与本体论的西方版本不同的中国样式,就可能产生问题,因为研究者对什么是本体论的理解已经预先决定了中国文本中的哪些素材能被归于本体论,而这些素材又被用作中国思想具有某种本体论成分的证据,因此,整个研究其实是建立在循环论证的基础上。但排除(1)(2),我认为探讨何物存在的中国理解,其价值还有做其他考量的可能。比如,一种规范性的考量是未知领域得到探究,这本身就有价值;所以讨论中国古代何物存在的概念,能说是为了(3)推进关于中国思想的知识性了解。不过,本文更关注的是一种实用性的考量,即(4)厘定存在概念在中国思想中的可能意谓,有助于为西方哲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关于语义基础的说明。因为毋庸置疑的是,汉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语言之一;但人们通常忽视的是,以汉语讲述西方哲学,不仅依赖对西方本文的理解,更依赖对自身工作语言的理解。典型如“Being”的翻译,好像有待说明的只是这个语词在目标语言中的用法,其在翻译语言中的译名,尤其是“存在”这个词,则不言自明。果真如此吗?我将通过分析“有( )”式表达所意谓的存在概念,既包括来自中国心灵的一般理解,也包括来自道家经典《庄子·齐物论》的深层理解,说明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我无意反对某种翻译,仅是以翻译为例,说明基于汉语的西方哲学研究反思其工作语言的重要性。并且,我更期待的是这种反思能从名为“中国哲学”的知识成果中受益。
1 “有( )”:表性质与表关系
让我们从“Being”的翻译谈起。过去的争议,事实非常简单,就是将之译为“存在”的主流做法遭到了质疑。但学理上,是否能用“存在”翻译“Being”,不仅取决于对后者在目标语言中用法的理解,也取决于对前者在翻译语言中用法的理解。并且相当程度上,后一理解更为重要,因为要判断“存在”是不是恰当的译名,首先是出现“存在”一词的翻译语句是可理解的。但正如以下译文:
例1:不言自明,事物存在着。([14],第327 页)
例2: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8],第3 页)
所谓“事物存在着”或“在者在”,对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即便不是不知所云,至少也会感到怪异。因为谈论何物存在时,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说法应当是“有( )”或“存在( )”,而非以上译文所见的表达式“( )存在”或“( )在”。当然,根本的差异不在表达习惯,而在语义或概念,即“( )存在”意谓的x 存在是性质概念,但“存在( )”也即“有( )”所意谓的存在x,我将指出,来自中国心灵的一般理解并非性质,而是关系。1因此要附带指出的是,表达式“有( )”与表达式“( )存在”的差别不涉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因为汉语的古今之别主要在语法层次,而非语义层次,即无论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的“有( )”,都对应于概念上的存在x;现代汉语的表达式“( )存在”则对应于概念上的x 存在。所以,“有( )”与“( )存在”的差别无关于汉语语法上的古今之别,而是语义有别。
根据以下例子,“有( )”式表达描述的主要是事物与场合的关系:
例3: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礼记·檀弓》)
例4: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离娄上》)
例3 中的“有人”固然可以理解为存在某人,但确切说,是“中庭”这一场合“有人”,即存在某人实际是关系上的某人出现于某处。例4 更明确,“有肥肉”“有肥马”“有饿殍”的“有( )”,都是关联于特定场合的某物出现于某处,因此存在x就能解释为某一事物x 与某一场合y 的时空关系,即x 出现于y。不过,“民有饥色”的“有( )”似乎不同,虽能解释为民的脸上存在饥色,但不仅是说饥色出现于民的脸上,更意谓饥色的出现只在民的脸上,不其他地方。所以,存在x 作为x 相对于场合y 的关系也是一种隶属或所有格关系,即y 具有x,如民的脸上具有饥色。再比如:
例5:天下有物。(《汉书·艺文志》)
例6:物也者,天下之所有。(《公孙龙子·指物论》)
例7:积也者,非吾所有也。(《荀子·儒效》)
例8: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韩非子·制分》)
虽然例5 仍能从时空关系的角度理解,即“有物”意谓的存在某物是某物出现于某场合。但例6 中的“有物”被表述为“天下”这一场合的“所有”,不仅是时空上的出现于,更是某物专属于某处或被某处所具有;例子7、8 则更明确,表达式“( )者,( )所有也”的意思就是……被……所具有。那么倒回去看,例5 中的“天下有( )”更应当解释为“天下”这一给定场合具有……,类似如:
例9:天下有道(《老子》第46 章)
例10:天下有溺者,……天下有饥者。(《孟子·离娄下》)
例11:天下有圣。(《荀子·正论》)
这些例子描述的与其说是事物的状态,不如说是“天下”的状态,因此“天下有( )”这一表达强调的,不仅是存在某物,更是“天下”具有这些东西。
就此来看,将存在某物表象为某物被某场合所具有,就是存在概念的中国理解中较为特殊的方面,比如,英语通常只说某一场合存在某物(there is…),不说某一场合具有某物(there has…),中国心灵则允许事物被场合所具有——这或许能解释为某物出现于其中的“场合”,如“天下”,在中国心灵中不仅意指某一时空范围,更是某物作为组成部分构成的特定整体,因此场合具有事物就能理解为整体–部分的构成关系,如:
例12: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荀子·天论》)
例13: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
如上,事物在某一场合中(一物在万物中、万物在天地中、天地在阴阳中、阴阳在道之中),正是构成意义的整体具有部分。当然,作为事物整体的场合也能充当其他场合的部分,如:
例14: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列子·汤问》)
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嵌套式世界观,即“万物”嵌套在“天地”中、“天地”嵌套在“无极”中、“无极”又嵌套在“无无极”之中,乃至一切东西都嵌套在更大的东西中(“大小相含,无穷极也”)。这再次表明,何物存在的中国理解不仅是事物出现于某场合的时空关系,更是构成关系,即作为部分的某物被某一整体所具有。
因此存在概念的中西之分或许就能表示为:与西方哲学设想为性质的x 存在不同,中国心灵洞见的存在x 乃是关系,即x 被某一y 所具有。而此差别,或许就是“事物存在着”或“在者在”这类译文难以理解的原因。当然在西方哲学中,康德宣称“存在明显不是真正的谓词,不是能被添加到一事物的概念中的某些东西的概念……逻辑上,仅仅一是个判断的系词,……用于安置有关于主词的谓词”([3],第504 页),已经开启了对x 存在作为性质的反思。只不过,他涉及的仅是传统主谓逻辑中的谓词;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存在不是真正的谓词”则应理解为:∃xφx不说明个体变元的任何性质,因此“存在”不是表性质的一阶谓词。然而,中文的“有( )”式表达仍能视为“真正的谓词”,并且是表关系的一阶谓词,因为存在x 能被理解为事物与其整体(场合)的关系,正在于“有( )”实际上是省略主语的表达,2A.C.Graham 指出的,相对传统西方哲学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抽象表达“X is”,中国的情形是“当存在被断言时,有通常没有主项(subject)”,这就是我们说的,对存在的理解是具体场合中的存在x,而非抽象来说的x 存在——后者是“柏拉图传统最愿意归因于Being 的抽象实体”,但前者主要是一事物被外部世界所“具有”,并且“一事物的存在越是具体,世界就明显地‘具有’它”。参见[2],第343 页。其完整形式应该是表示……具有……的关系词“( )有( )”,如:
例15: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第21 章)
很清楚,“有(象)”“有(物)”“有(精)”正是“(道)有(象)”“(道)有(物)”“(道)有(精)”的省略表达。因此“有( )”所意谓的存在x 能被看成相对某一整体y 的关系,正在于其完整形式“( )有( )”意谓的是y 具有x 或x 例16:当你取任何一个命题函项并且断定它是可能的,即它有时是真的时,这就给予了你关于“存在”的最基本的意义。……至少有一个x的值,对此,这个命题函项是真的。([13],第281 页)这是对罗素的一个著名观点的翻译,而仅就中译文来看,“存在”被说成“至少有一个x 的值”使得f(x)为真,其实就是说:变元的取值范围中具有使命题函项为真的值。因此中文表达式“有( )”所意谓的存在x,作为关系上的……具有x,虽不是决定句子真假的∃x,但仍能为∃x的中文表达提供解释,即作为量词的“存在”意指的仍是整体–部分的关系,整体是变元的取值范围或论域,部分则是令命题函项为真的变元的值,其关系则是某一论域具有x 的这个值。 所以,从中国心灵对存在概念的关系性理解出发,前引表性质的译文“事物存在着”或“在者在”,并不容易理解。不过,翻译者也可进行这样一种辩护,就是与习语“有( )”或“存在( )”不同,译文“( )存在”或“( )在”只是语法上的人工制作,因此能赋予其全新的意思。但如果翻译纯粹出于人工制作,也就等于没有翻译,因为将“Being”翻译为“存在”与翻译为任何一种人工约定的符号没有本质差别。尤其是,因为“Being”的另一译名“是”,作为系动词,更接近现代汉语的人工制作,所以将“Being”翻译为“是”还是“存在”也没有可争论的价值,因为可以约定二者的用法相同。但显然不是这样,比如: 例17:上帝是存在。在这个命题里,宾词,存在……。([9],第42–43 页) 例18:在“上帝是存在”这个命题里,谓词是“存在”。 下面举例说明建立总杠杆模型进行企业经营风险分析的方法。以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公式推算,总杠杆系数可通过息税前利润、固定成本和负债利息的组合,或者以中间指标边际贡献、固定成本和负债利息的组合来表示。 以上,都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Gott ist das Sein,das Praedikat das Sein”这句话的翻译。([11],第40 页)字面上,“Praedikat”显然应当是例18 所翻译的“谓词”,例17 将之译为“宾词”则属汉译的改动。但此改动,或许正是为了使中译文能更好地体现原文中的微妙差别,即“Praedikat”所指的并不是句子“Gott ist das Sein”的语法谓词,即“( )ist das Sein”,而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das Sein”。所以将“Praedikat”翻译为“宾词”而非“谓词”,至少有助于读者注意到这个特征。相比之下,例18 翻译为“谓词”,虽然字面上更准确,但可能使上述特征变得模糊,即无法表明“谓词”指的是上述语法谓词还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这也不会导致明显的误解,因为“( )ist das Sein”中的“ist”只能翻译为“是”,所以,如果能在“das Sein”的翻译上与“ist”相区别,也能表明被称为“谓词”的并不是“( )ist das Sein”,而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可供选择的似乎只能是将“das Sein”翻译为“存在”,将“( )ist das Sein”翻译为“( )是存在”。但这样翻译是可能的,本身就表明译名“存在”不是人工约定的符号,必定有能区别于“是”的固有用法。 问题是,“存在”一词的固有用法是什么,这并非不言自明,翻译者至少应该考虑之前谈及的情况:(1)相对于译文中的“( )存在”,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是“存在( )”即“有( )”。而这两种表达除了语形不同,更有语义上的重要差别,就是(2)“( )存在”能被视为表性质的谓词,“有( )”则应视为表关系的谓词,也就是作为“( )有( )”的缩略语。由此就能初步洞见何物存在的中国理解,是(3)把“有( )”所意谓的存在x 看成x 相对于y 的构成关系,即存在某物或有某物就是某物在某一整体中并被此整体所具有。那么,关于“Being”的翻译,可以肯定,除了涉及对目标语言的理解,更涉及对翻译语言本身的理解。认为只有“Being”是需要探讨的,“存在”则不言自明,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不过,以上呈现的何物存在被理解为事物相对其场合或整体的关系,只是来自中国思想的一般理解,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道家文本尤其《庄子·齐物论》的深层理解,即存在某物表现为某物被某整体所具有——尤其是指某物作为对象,被谈论它的语言的对象域或论域所具有;因此存在作为关系,除了是(1)事物层面的部分相对于整体的关系,更是(2)事物相对于言说事物的语言的关系,并能归结为(3)某种事物语言相对于言说者的关系。对此深层理解的说明,我将指出,同样能为西方哲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完善语义基础的知识成果。 让我们从《齐物论》的以下文字谈起: 例19: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这些论述虽如绕口令般费解,其实正基于“有( )”式表达构造出来,其过程是: 1.将表达“A”置入“有( )”的空位形成“有(A)”(“有有”“有无”)。 2.给“有(A)”加前缀“未始”形成“未始有(A)”(“未始有无”) 3.将“未始有(A)”整体置入“有( )”的空位形成“有(未始有(A))”(“有未始有无”) 4.给“有(未始有(A))”加前缀“未始”形成“未始有(未始有(A))”(“未始有未始有无”) 5.将“未始有(未始有(A))”整体置入“有( )”的空位形成“有(未始有(未始有(A)))”(“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 1–5 的构造能解释为: 1′.“有(A)”意谓存在x。 2′.“未始有(A)”意谓并非存在x 或无x。 3′.“有(未始有(A))”意谓存在无x,是把无x 断定为一事物,如存在ψ。 4′.“未始有(未始有(A))”意谓并非存在ψ 或无ψ。 5′.“有(未始有(未始有(A)))”意谓存在无ψ,这又是把无ψ 断定为一事物,如存在∆。4关于这段文字的详细分析,参见[12]。据此看,例19 正是围绕存在问题的论述。 但要点是,如上例所见,用“有( )”意谓存在某物实际是将某物断定为对象,比如(1)存在∆断定了无ψ 是一对象,(2)存在ψ 则断定了无x 是一对象;或者更简单地说,(3)无ψ 或无x 被“有( )”断定为一个对象性的无。所以上例中的“有(无)”——其意谓绝非有与无或日常来说的有与没有,而应当是有一个无,即存在作为对象的无。因此,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无”的两种用法,即: 1.用作否定词,表示没有,如“无(物)”“无(有)”之“无( )”。 2.用作范畴词,意指对象,即“有(无)”之“(无)”。以上差别又能表示为,“无( )”是“有( )”的否定表达,与《齐物论》中的“未始有( )”意思相同;“(无)”则意指“有( )”所肯定的东西——或者就例19 中“有(有)”这一表达来说,“(无)”与“(有)”范畴相同,都是“有( )”所肯定的对象。这意味着,上述“无”的不同用法实际出于“有”的不同用法,即: 1′.用作断定词,表示存在某物,如“有(有)”“有(无)”之“有( )”。 2′.用作范畴词,意指对象,即“有(有)”之“(有)”。 那么,例19 最后说的无法在“有”“无”间划出绝对界线(“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就应当是说作为范畴词的“(有)”和“(无)”所意指的东西性质相同,即都是“有( )”式表达所断言的对象,因此在同一对象域中。所以,之前揭示的何物存在的中国理解,作为一种整体–部分的构成关系,不仅是某物作为部分被某一整体所具有,更是某物作为对象被某一对象域所具有。 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对西方哲学的汉语翻译提供借鉴。比如,前引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的译文(例2),除了“在者在”可能导致困惑,还可能引起困惑的是“为什么……无反倒不在”这个问句中的“无”,在用法上并不能与德文原文“Nichts”构成对应,因为后者作为“nicht”的名词形式,既有否定义、也有对象义,但作为中文译名的“无”,其否定义与对象义是分离的,如上所见,不属于“无( )”和“(无)”,所以翻译总会存在意义缺损的情况。而此情况,在以“有”翻译“Sein”的时候同样存在;只不过,例2 是翻译为“在”,但显然翻译为与“无”相对的“有”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如: 例20:如果我们宣称存在或有是绝对的一个谓词,则我们就得到绝对的第一个界说,即:“绝对就是有”。……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也就是无。……由此便推演出对于绝对的第二个界说:绝对即是无。 这是来自黑格尔《小逻辑》的译文,5参见[10],第189–190 页、第192 页。虽然采纳了“存在”作为译名,但主要说的是“有”,我猜想,就是为了与“Nichts”的译名“无”构成对应。换言之,这种翻译暗含了中国思想对有无关系的某种理解。但正因为“无”的用法并不对应于“Nichts”,所以并不清楚第二界说“绝对即是无”的“无”到底是“无( )”还是“(无)”;所以,也不清楚第一界说“绝对即是有”的“有”,作为与“无”相对的译名,到底是“有( )”还是“(有)”。 但要再次重申,我并不是反对某种翻译,只是通过分析翻译语言本身,说明为什么有些译文是难以理解的。不过,除了指出这个看似消极的方面,此类语义分析也有积极作用,比如,“有( )”意谓的存在某物是某物作为对象被某一对象域所具有——探讨这一来自中国思想的深层洞见,也将为理解西方哲学的观点带来启发。让我们再回到《齐物论》: 例21: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例22: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 如上,“古之人”认为“未始有物”,这是对客观世界予以否认吗?如果不采纳这种反常识的理解,只能认为例21 说的是作为对象的“物”并未出现在“古之人”的“知”或认识当中。因之当人们“以为有物”时,“有物”意谓的存在某物就能更确切地理解为所“知”的对象域中具有作为对象的“物”,也即形成了关于物的对象意识。但相比于认识上的对象域,《齐物论》更重视的是能够言说的对象域,也即论域(Domain)。因此例22 宣称的,“此”或“彼”作为“有言”的对象,无论相似还是不相似(“类与不类”),都能视为相似的东西(“相与为类”),这实际是说:任何被谈论的东西,无论其本身差别多大,在作为被谈论的对象这一点上是无差别的,即都是说话人论域中具有的东西。 因此,是否“有物”的问题就能进一步归结为是否“有言”,如: 例23: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虽然“万物与我为一”表象了事物的最大总体,因此任一事物的存在都能解释为被这个总体所具有;但这种具有并非纯粹事物范畴的构成关系,因为上引文真正关心的不是万物与我为一本身的意义,而是这个整体(“为一”)是否能被言说(“谓之一”),其主张则可重构性地表示为:如果万物与我为一充当了给定的事物语言L 的论域DL,能够谈论就仅是DL中具有的东西,DL本身则不能作为谈论的对象,因为在L 中: 1.“万物与我为一”谈论的万物与我为一,如表示为整体D0,并不包含这句话本身。所以存在D1,是由D0和断言D0的句子即“D0”叠加成的新整体(“一与言为二”)。 2.如果D1是“万物与我为一”谈论的整体,同样不包含这个句子本身。所以存在D2,是由D0和“D0”这两部分叠加形成的D1再次与断言D1的句子“D1”叠加形成的新整体(“二与一为三”)。 3.只要一个整体Dn是可谈论的,就存在Dn与断言它的句子“Dn”叠加形成的新整体Dn+1,这是个无穷上溯的过程(“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 4.所以任一整体Dx,如果能被L 谈论,则Dx 因此在事物语言L 中,只有DL具有的东西而非DL本身才是可谈论的,即说话人对何物存在的断言不能超出DL的限定,也即“有物”不能超出“有言”的论域。 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主张。典型如卡尔纳普认为的,接受一个事物的世界,不过就是接受某种言说事物世界的“语言形式”(lan-guage form),它是人们谈论存在问题的“语言框架”(linguistic framework),即只能在此框架内追问何物存在,不应追问事物作为整体是否存在,因为事物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接受一种语言框架时被给定了;所以将事物作为整体来追问其存在,如卡尔纳普所言,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选择一种语言框架替换另一种框架的实用性问题。而此类问题,因为已经超出了给定的语言框架,又被称为本体论的“外部问题”(external question);在语言框架内追问何物存在,则被称为本体论的“内部问题”(internal question)。([1])虽然这个区分,因为预设了分析/综合之分,遭到了蒯因基于更彻底的实用主义的批评([6]),并由此引发了持续的讨论;但导致卡尔纳普区分内外本体论问题的初衷,正如评论者指出的,“不能站在语言之外并从超语言的立场考虑本体论的问题”([4]),也正符合蒯因的看法,即“何物存在不依赖对语言的使用,言说何物存在则依赖”([5],第103 页),并关联于他对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的揭示,即谈论何物存在总是相对某种背景理论(back theory)和背景语言(back language)才有意义。([7])因此,卡尔纳普–蒯因所开辟的研究也被叫做“元本体论”(metaontology),正是指从“何物存在”这个本体论问题后退一步,探讨人们言说何物存在的语言。 但我不是说,上述中国思想对“有物”的讨论关联于“有言”是一种元本体论观点,因为这等于假定了中国思想中也有被称作“本体论”的成分——其或者是西方本体论的对应物,或者是一种本体论的特殊样式——而无论怎么说,都是循环论证,即本文最初指出的,关于本体论的理解已经决定了中国文本中的哪些素材能被归于本体论,但研究这些素材的目的又是为了证明这一点。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对中国文本的分析能触发关于某些西方观点的联想,比如“本体论的相对性”,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至少意味着思想研究的返回传统之中与走向传统之外并不冲突,所以研究视野的扩大总是可期待的。只不过,始终要警惕的是这种期待被异化为简单比附,所以仍然要强调,无论何物存在的中国理解看上去如何接近某种西方观点,都必须独立于后者得到揭示。 况且再次回到《齐物论》,也会看到中国心灵对存在问题的理解区别于“元本体论”的一个显著方面,就是“有( )”式表达所意谓的存在概念,作为表示……具有……的关系概念,不仅是事物相对于语言的关系,更涉及语言相对于说话人的关系,前者将“有物”意谓的存在某物表象为对象物被某种事物语言的论域所具有,后者则将“有言”意谓的存在某种言论表象为被说话人所具有,比如: 例24: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例25: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例26:夫随其成心而师之,……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 例23 中的“有言”正可视为例24 中“我则已有谓矣”的缩略表达,即存在某种言论的意思就是说话人具有这种言论。但例24 要强调的恰是这一具有关系并不确定,例25 则进一步表明,不确定的并非行动上的是否说话,而是语义上的是否“有谓”,即某种言论是否具有“所言者”或宽泛来说的言论的意义(meaning)。显然,“有谓”之为“有谓”,而不等于“无谓”,就在于说话不仅是纯物理的发声,更涉及非物理的意义或“所言者”。但如果“所言者特未定”,就意味着很难在说话与发声(如“鷇音”)之间划出绝对的界线。不过,例25 仍然承认说话不等于吹风,因此并不否认言论具有意义,则“所言者特未定”意谓的,大概只是一种言论相对于不同的交流主体具有不同意义。因而意义或“所言者”与其说是言论本身具有的、可被断定真假的客观涵义(sense),不如视为说话人内心具有的、他人难以确知的主观意图(intention),这就是例26 所说的智者、愚者都有的“成心”。 因此基于《齐物论》,中国心灵对存在概念的深层理解就是:(1)“有物”或存在某物指的是事物相对于语言的关系;(2)“有言”或存在某种言论则是语言相对于说话人的关系。(3)这两种关系都能解释为……具有……,即(A)“有物”指的是谈论事物的语言在论域上具有被谈论的对象,(B)“有言”则是指说话人具有关于对象物的言论,这又是指(B1)说话人的言论具有某种意义(“有谓”),并能解释为(B2)说话人具有某种意图(“成心”)。 以上,关于何物存在的讨论是从“有( )”式表达涉及的中国古代的一般理解与来自《齐物论》的深层理解入手,揭示存在概念作为关系概念的意义,即(1)“有( )”所意谓的存在x 实际是x 被某个y 所具有,因此(2)存在x 总是x 相对于y的关系。并且,对应于上述一般理解与深层理解,这或是指(3)事物作为部分被某一整体(场合)所具有,或是指(4)事物作为对象被某种事物语言的论域所具有。而要再次强调的是,(1)–(4)作为对中国思想的知识性了解,固然属于中国哲学的作业范围,其价值却不仅限于中国哲学,更能为西方哲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关于语义基础的说明。当然,对于“Being”的翻译,以上提供的只是一种消极说明,即中国心灵对存在x 作为关系概念的理解,很难对应于“事物存在着”或“在者在”等译文表达的作为性质概念的x 存在,这正是此类译文难以理解的根源。但是,为强调对工作语言的反思之于汉语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聚焦于说明已有的翻译为何难以理解,显然比提供新的翻译更有价值。因为翻译是否恰当,正如前述,不仅取决于对目标语言的理解,更取决于对翻译语言的理解,所以,首先能谈论的只是译名出现其中的翻译语句的意思。如果翻译者整个绕开这一辨析语义基础的环节,直接以“Being”在西方文本中的用法作为判断其是否能被译为“存在”的依据,就预设了“存在”这个中文译名不言自明,更混淆了目标语言与翻译语言——因为无论如何,说明“Being”的用法与说明“存在”的用法是两回事,而只有独立于前者说明后者,才能考虑“Being”是否能被翻译为“存在”的问题。2 《齐物论》中的“有( )”:何物存在的相对性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