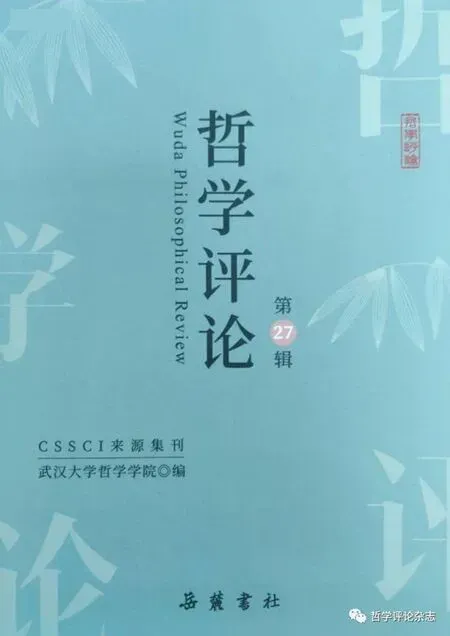凝思生命的芳香
——读韩炳哲《时间的味道》
2021-11-25包向飞
包向飞 姚 璇
一、三种时间观
《时间的味道》(Der Duft der Zeit)一书由韩裔德籍作家、文化理论家、德国柏林艺术大学韩炳哲教授(Byung-Chul Han)所撰写。在两百多页的篇幅中,韩炳哲将历史梳理与学理思辨相结合,在此他不仅阐发或批驳了哲学史上有关“时间”的主要论述,同时也系统探究了当今时间危机的诸多症状及缘由。
书中提及了三种时间观[1]该书区分的三种时间观只是种理想化的概括。现实生活中的时间观多是复杂交错的。例如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并不是神话式的,而是类似于革命式(循环式)的时间观,它属于历史性时间观的一种,正所谓:“一盈一虚,一治一乱”相互交替。此外,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时间观也可能是有差异的。:古代前历史的神话式时间观、近现代的历史性时间观和后现代的原子化时间观。三种时间观的图示呈现出从二维平面经一维线性(线段或射线)到零维断点的变化。三种时间观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古代神话式时间是一种以二维平面和向心化为特征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人是被抛的(geworfen),人并不是主宰者。诸神作为一种权威,是时间的稳定器和校准者。一切都须遵从诸神创造出的不可动摇的秩序轨道,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固定的位置。诸事物的价值(Stellenwert)就是它们所处的位置(Stellen),它们如若失位便失去自身的价值。在这种时间里,诸事物处于稳定的、富有意义的关联之中,世界的图示如同一幅静止不动的平面。原则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前进和后退或加速,因为它们都不会促成任何(真正的)改变。
第二种时间观是近现代的历史性时间观。根据书中的阐释,历史性的时间是被定向的、连续不断的、相互追赶的线性时间。这时,万物并非以诸神为中心。万物也不安排在不可动摇的秩序里,它们反而处于一种变迁与发展的状态之中。历史如同语言的句法,它能照亮、挑选诸多混乱的事件,并将其有序地纳入线性的叙事轨道。根据该书,这种历史性的时间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末世论的时间:它以创世为开始,以最后的收割为终结。在此,人不是自由的主体,他被强行抛入终结的命运中。个人的财富和努力都是徒然的。(二)革命式的时间:“革命”(Revolution)在词源上意指恒星的运转。“革命”作为统治形式发生变更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以回返往复的形式重复着自身。换言之,统治形式的更迭有着与恒星运转一样的定律。看似人在进行革命,事实上人如同恒星,必须遵守其循环的轨道。(三)目标明确的、进步的线性时间:启蒙运动以来,人不再屈从于被抛状态。人们积极筹划自己的未来,诸事物的可操作程度大大增强。
第三种时间观是后现代的原子化时间观。时间在原子化后呈现出一维断点的样态,线状的历史让位于点状的信息。在这种时间中,由于点与点之间缺乏由整体叙事给予的张力支撑,时间轨道上的诸事物无方向地游离着。在断点间的空隙中,间断性的经验和长久的无聊涌现出来。在这种时间中,人的筹划和加速优先于一切。遗憾的是,这些筹划和加速实际上并没有整体的关联和明确的方向。于是“不良时间”[1]“不良时间”不具备整体性和持续性特征,同时不良时间也显露出直接化、均匀化和去叙事化倾向。后文的论述有助于理解此概念。逐渐形成。按韩炳哲的说法,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法散发芳香。
综观全书,因时间的原子化而引发的时间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当代社会缺乏整体的叙事结构。该书断言,我们正在经历的原子化时间是一种断点状的现时时间。整体的叙事结构无法在这种时间的轨道上建立起来。根据该书的阐述,原子化的时间一方面缺乏整体性,另一方面在这种时间里“叙事的终结首先是一种时间危机。这终结摧毁了把过往的和将来的东西聚合到现时之中去的时间引力。如果时间上的聚合付之阙如,时间就会崩塌”。[2]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叙事的作用在于,它建构起一个张力结构。这一张力能聚合时间,并为时间轨道上的诸事件赋予意义。而如今的时代充斥着繁杂的、几乎毫无差别的连接。这就造成某个方向或选择相对于其他的方向或选择并没有不可替代的优先地位,事物失去了终极的确定。在这种不具备整体叙事的时间结构中,人们重新开始的成本大大降低,标志持续性的时间现象(诸如真理、经验和认知)和实践行为(例如承诺、义务、忠诚等)难以出现。
第二,人们逐渐丧失凝思逗留的能力,人们越来越容易被刺激的轰动事件吸引。散点化的时间不具备整体的张力结构,于是无聊(Langweile)就隐藏在时间轨道上那长久的空洞(Lange Weile)中。为了抵抗无聊,点状时间需要通过直接无碍的、花样繁多的新鲜事和轰动事件填补空洞。遗憾的是,刺激的事件无法持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一来,相对长久的关注只能通过叠加事件的数量或加快事件的接替频率来获得。美学上的张力由事件或信息的稠密化而产生出来,稠密化取代了审美上要求的持续性。书中的这一阐述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的观点。按照本雅明的理解,机械复制不仅导致艺术品“灵韵”的消失,它也致使艺术接受方式产生转变,即从侧重价值的膜拜转变为侧重价值的展示。前者强调有距离的审美静观,后者看重零距离的直接反应和艺术品的消遣娱乐性。[1]参见瓦尔特·本雅明:《艺术社会学三论》,王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也就是说,在如今的时代,本雅明所说的“灵韵”(萦绕在艺术品上的完整的历史经验)在“震惊”(外部刺激唤起的对瞬时事件的特别关注)中四散。[2]参见张文杰:《艺术“裂变”时代的文化美学:本雅明艺术美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14页。可以看出,虽然韩炳哲与本雅明的出发点和思路不同,但他们对当今时代危机作出的美学方面的诊断有不谋而合之处。
第三,人逐渐变得均匀化、大众化。在无法聚拢自身的散点时间中,人也丧失着自身的连续性和持存性。可以说,时间危机致使人的自我认同产生危机。人的均匀化和大众化成为一种时间现象。书中借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我曾是的人再也存在不起来了,我是另外一个”来加强该论述。另外,该书对海德“常人”的援引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对下一个新事物的期望之中他(即常人)也就已经忘却了旧有之物。……非本真的历史性生存……寻觅着,负载着对它自身而言变得无法辨认的‘过往’的遗产,即现代性。”熟悉海德格尔的读者很容易想到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代的代表现象——“常人”的总结:“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1]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修订本,第148页。书中提到,就大众化和均匀性这一方面而言,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与尼采的“末等人”几无差别。
第四,死亡成为一种人们极难面对的事情,“会死”变得尤为困难。生命时长的有限性让人们一直将死亡视为生命时间的终结。死亡的威胁大大增加着现代人的恐慌感。这种恐慌感常常表现为人们害怕错失时机,并竭力通过提升体验速率来实现“充实的生命”;或穷尽方法保持健康,以此对抗衰老和死亡。书中提到,现代人无法像查拉图斯特拉呼唤的那样“适时地死去”。原因是什么呢?韩炳哲在书中区分了“死亡”的“终了性(Sterblichkeit)”与“有终性(Endlichkeit)”。在前者中,死亡被作为一种从外部接入生命的强制性的暴力;而在后者中,人们将死亡领受为“从生命、从生命的时间之中产生出来的完结”。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书中推崇的正是后者那种“塑型性的、自由的、完成性的死亡”。
二、时间与生命之思
《时间的味道》一书在探讨“加速”“无聊”和“凝思生命”等核心问题时,着力驳斥了下述三个观点:
第一,加速导致了时间的原子化和凝思生命的丧失。书中首先借鲍德里亚诠释了这种观点。鲍德里亚就将历史的终结和意义的流失直接关联到速度问题。对此,《时间的味道》针锋相对地提出:上述观点错误地颠倒了原因和结果。加速并不是时间原子化和凝思生命丧失的原因,加速只是事后性地作为它们的结果。换言之,加速呈现为一种缺乏锚定的无停居状态,它只是时间消散成断点后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原子化的时间中,选项间的无差别促使人们逗留于一地的迫力和必要性难以形成。人们凝思逗留的能力正因这种迫力和必要性的不足而逐渐消失。而恰是凝思能力的丧失,才可能造成一种逃逸的力量,结果是一种普遍的仓忙与加速。就此,该书再次借助海德格尔所称的“常人”来支持这一论述。“我没有什么时间”是“常人”的一种代表性说法。“常人”总在“非本真”地生存着,他劳劳碌碌地把自己丧失于所操劳之物。另一方面,如今人们虽然保持着启蒙运动以来加速前进的惯性,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原子化的断点无法建构整体的叙事结构,这必然导致加速失去方向。因为加速本以定向的流动为前提,没有方向地向前狂奔绝非是真正的加速。该书认为,清闲实则为一种特殊的能力。人们不会停留的无能感致使人们只能通过加速前进来削减内心的慌张和忧虑。在这点上,韩炳哲承袭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就曾将现代社会普遍奔忙的现象归结为一种能力的丧失,即人们没有能力体验止息、悠远和从容。
第二,仓促与迟缓、充实与无聊是互相冲突的概念。但该书借助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里“匆匆忙忙的无眠之夜”这一看似是悖论的表述阐明:这些初看为对立的概念其实是同源的。或者说,它们是由于时间缺乏叙事张力这个同一的深层原因而衍生出的不同现象。根据该书的理解,时间张力可以将现时从其无终点的、无方向的延续中释放出来,并载之以重要性。只有在一个处于指向性的时间性张力关系内部,真正的时间才得以形成。时间张力的缺失使时间断裂成不具备指向性的点状,这样时间上就产生出诸多跳跃和动荡。当叠加无序的事件涌入现时,现时便漫无头绪,只顾仓促地向前奔忙。与之相对,若这些事件普遍无区分地存在着,时间的步调便会显得迟缓笨重。可见,仓促和迟缓是同源的。另外,虽然无聊常出现在轰动事件未在场之处,但该书强调,无聊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误解的那样,它只出现在散点化的时间间隙之中。事实上,无聊并非是充实的绝对反面,恰恰是永不停歇的积极行动加剧着无聊。该书用怀疑的目光审视阿伦特在《积极生命》中的主张:复原“行动生命”的活力和“作为”。阿伦特主张,积极生命必须展示出生命的不同显现形式。《时间的味道》明确批驳了阿伦特的该论述,该书认为阿伦特混淆了“单纯的充满”和“充实的生命”。前者以集合论的方式展现着生命,它仅仅是事件数量上的叠合和累积,而充实的生命不一定充满着变化的事件,它建立在具备张力和支撑的整体叙事结构之上。韩炳哲将优良时间的轨道比作一支悠扬的曲调。曲调具有韵律,韵律起到强有力的挑选和划分作用。时间轨道上的加速和减慢也可追溯到韵律的缺失。因为韵律使时间节奏化,它调和着仓促与迟缓、充实与无聊,并让它们实现和谐的变换。
第三,“积极生命”与“凝思生命”、“作为”与“停歇”是相互冲突的。“积极生命”常常与辛勤的劳动挂钩,而“凝思”总关联到停歇或倦怠等负能量词汇。在此,该书依旧将阿伦特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表。阿伦特的看法是:凝思表现为行动的停歇。正是凝思致使了积极生命的平面化,凝思要为积极生命降格为劳动负责。而《时间的味道》一书明确批评了上述观点。该书认为,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和谐一体的。凝思并不表现为无所事事的停歇,反而是一种安居自身的逗留。如书中所说:“于自身中安居着的却不一定没有任何运动和行动…于自身中在这里只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对外在事物的依赖,人是自由的。”换言之,凝思创造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一种必需之外的状态和场域。相比之下,劳动一般被视为最典型的行动。劳动并非以自身为目的,它作为生存的手段总关乎着紧迫性和必须性。此外,凝思并不像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会导致生命的平面化,因此凝思也不需要为积极生命降格成劳动负责。事实上,人正因为丧失了凝思的能力才沉降为劳动的动物,人的行动才降级为纯粹的劳动。书中解释了人们将“积极生命”和“凝思生命”、“作为”和“停歇”对立化的原因,即:人们忽视了它们可调和的一体性。积极生命不意味着将非行动的东西完全排除出生活。诸如休息、停顿等看似停滞或被动的状态,它们不仅对行动是决定性的,它们也具备自身的价值。换个角度来看,某种程度的被动性也是十分必要的,人只有被触动才会凝思。“被触动”意味着人受到某种关涉或召唤。对此,熟悉海德格尔的读者很容易想到他在《语言的本质》中提及的:“在某事(可以是物、人或神)上取得一种经验意味着:某事与我们遭遇、与我们照面、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1]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7页。可见,在凝思或触动所暗含的十分重要的被动性上,韩炳哲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很多启发。
为了强调凝思不同于闲散,也不同于外在身体上的劳动,韩炳哲援引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经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直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诸多论述。不难看出,《时间的味道》一书对凝思的呼唤并不是突发奇想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前人的智慧。
三、时间危机与解救之道
《时间的味道》是一部讨论当今时间危机的哲学书籍。它不仅在内容上极具广度和深度,而且其在用词(隐喻的使用和概念区分)上也十分考究。
首先,书名《时间的味道》[1]该书标题的德语名为“Der Duft der Zeit”(时间的芳香),“Duft”的准确含义为:香气、芳香。隐喻性地概括出了香气与时间、香气与凝思生命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香气(der Duft)”具有持续、迟缓和间接的特点,而香气的这些特点正是优良时间的主要特征。其一,香气与优良时间都具有持续性。该书指出,原子化的时间是一种不良时间,它是没有芳香的。只有当时间取得一种持续性的时候,当它获取一种叙事张力或者深层张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散发芳香。那么如何抵抗不良时间,进而恢复芳香的优良时间呢?该书将目光投向古中国的熏香之印,并将其作为优良时间的一种象征化示例。人们利用熏香测量时间与利用水和沙漏不同,因为熏香将时间空间化了。人们可以从香气(嗅觉层面)和余温(触觉层面)中感知时间的流逝。香印燃烧之时,它给人两种持续的视觉图像:保持着笔法造型的火晕和升腾团起的烟云。对此,书中借麦克卢汉在其《可会意的媒介》中的表述来解释:气味感官是“象形的”。气味在熏香中得以画面化,人们也愈发整体化地感知时间。香气在视觉、嗅觉和触觉上的持续感受替代了时间的瞬时性。其二,缓慢性是芳香的优良时间的标志。韩炳哲认为,匆忙时代是一种被视觉广泛影响的、影片拍摄式的时代,它是一个没有芳香的时代。在快速接替的过程中,持存着的事物难以存在,凝思性的逗留无法产生。对应地,香气是迟缓悠长的。香气自身很难像视觉图像一样实现快速的交接。人们也无法像看到沙的滴漏或水的流逝那样看到香气的消逝,香气是弥漫的。其三,优良时间总是避免直接地享用,它是间接迂回的。同样,香气的萦绕需要时间的累积。可以看出,香气和那蕴含凝思的优良时间一样,都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萦绕和安居自身的缓慢聚合。
(二)“气”常常关涉着呼吸、灵魂和生命,时间的“香气” 实际上也与凝思的生命紧密相关。或许词源学早已展现出“气”与呼吸、精神、生命以及灵感之间的关联:古希腊语中“pneuma”词源义为“气、呼吸”,后来它增加了“灵魂、精神”的含义。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spiritus”,spiritus源于拉丁动词“spirare(吹,呼吸)”。这里可以参见英语动词“inspirate(激发灵感)”。从构词法上来理解,就是“向里吹气(inspirate)”,它意指那带来生命的呼吸。正如《时间的味道》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精神自身要将其形成归结为时间的盈余、一种清闲,呼吸的一种悠长之态……丢落呼吸的人,是没有精神的。”此后,该书阐明了时间香气与凝思生命之间的关系:“时间的这些芳香之气并非是(宏大)叙事性的,而是凝思性的。”换句话说,生命时间拥有自身的芳香,它无须神学(神话式时间)和目的论(历史性时间)也能运行,但生命时间预设了凝思生命的恢复。因为在上述两种时间中,人都必须从属于诸神、上帝或必然性预设的既定轨道。韩炳哲的这一主张表明,宏大叙事已无法重建,也无须重建。用书里的话说,面对时间的原子化,现实的唯一出路便是“借力于自身的生存上的鼓动”。基于香气和优良时间、香气和凝思生命的共同点,该书的标题十分契合,书中论述的展开也显得非常连贯。
其次,该书严格区分了四组相似的概念。[1]书中也对死亡的“有终性”和“终了性”、生命的“充实”与“单纯的充满”作出了区分。本文的第一、第二小节已阐述过它们之间的区别,在此不再赘述。
(一)“叙述”不同于“列举”:叙事并非是机械地对诸事件的计数和枚举。叙事预设了时间具有整体性的结构。时间的轨道由此获得了韵律,诸事物得以区分和被挑选,同时它们被赋予含义和关联。该书以中世纪的日历作比方,认为当时日历的功能不只是为了计算日子,而是以节假日等固定节点形成蕴含生活意义的站点。这些站点串联起时间并使之节奏化。韩炳哲将这种具有节奏和整体叙事结构的时间比作引人入胜的、张弛有度的小说;相比之下,原子化的时间却在不断地去叙事化,时间崩塌为诸事件的时间列表。事件只是被“列举”而非被“讲述”出来。叙事退场,让位于信息。机械的列举无法将事物的关联和含义拢入序列之中,一连串事件的单纯计数并不能造就吸引人的故事。韩炳哲的这一阐述与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的论述主旨不谋而合。该文通过评述19世纪俄国作家尼古拉·利厄斯科夫的创作问题,阐明了“讲故事”(丰富的叙事)与“新闻报道”(信息的枚举)的不同。本雅明哀伤地感叹,“讲故事的艺术”与他所称的“灵韵”一同在现代社会中消亡了。
(二)“思想”不同于“计算”。思考作为一种凝思性的观察是建基在静观和清闲之上的。思想并非总以直线的方式前行,它常常暗示着绕行和曲折。熟悉德语的读者不难想到德语动词“沉思(sinnen)”的原初义便是“漫游”。漫游是悠闲的,人们在漫游时多没有明确的前行目标,往往会走弯路。相反,计算遵循定向的线性轨道,它具有直接性和目的性。因而人们可以对计算的过程实现加速。这种思想也显然受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1]参见高山奎:《试析海德格尔哲学的技术之思及其限度》,《云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21页。书中有曲调是思想的典型特征的说法。人们也常说:思想在跳舞。正如法国诗人瓦莱里所言:“行走如同散文,瞄准一个确定的对象,行走这个行动是指向某个事物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和这个事物会合。指挥行走步伐的是一些实际情况,比如对某事物的需要,欲望的驱使……它们为行走规定方向、速度,为它指定一个确定的期限。”[2]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
(三)“认知”不同于“信息”。认知是充满过程性和持续性的,它的形成立足于时间的延展和视域的交叠;而信息的产生并不依赖时间的聚合。信息游离在时间轨道上,呈现出点状的形态,它们可以被随意地检索或储存。
(四)“道路”不同于“通道”、“朝圣者”不同于“游人”。道路将出发地与目的地分离了,它是居间的、间接的。相反,通道强调即时性和直接性,它在不断地去远化,去除着过渡。朝圣者的意义存在于路途中,行走意味着忏悔、解救或感恩。朝圣之路不是单纯的通道,而是朝向异地的过渡。而游人将道路变成空洞的通道,他们在走马观花地浏览着接踵而来的新鲜事物。
四、几点思考
尽管该书将历史梳理和学理思辨紧密结合,但书中的论述仍存在不清楚之处。现举出两点不足,以供读者探讨。
第一,该书对线性历史时间的分析不够细致,尤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时间观的分类较为笼统。启蒙运动将人从被抛状态(Geworfenheit)和事实性(Faktizität)[1]属于事实性的是一种被动性,它在被关涉、被抛、被召唤等用语中得以表达。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人既不被抛入时间的终结(末世论时间)也不被抛入诸事物的自然循环(革命式时间)。人的筹划和自由操作代替了命运的安排。该书不仅将启蒙运动以来的时间观都归为自由进步的、开放未来式的时间观,还将其都归为线性的时间观。实际上,这样含混的阐述和笼统的归纳是有问题的。比如,黑格尔—马克思式的时间观同样属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线性时间观,但它强调一种必然性,从严格意义来说,它并不属于开放未来式的时间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本源,是宇宙万物的内在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同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自由意味着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在这种时间观中,他们所强调的必然性实际上为历史预设了一个既定的运行轨道和前进方向。然而,《时间的味道》一书在谈到启蒙运动后的线性历史时间时,它单单强调与该时间观对应的可操作性(自由)和开放性。该书并没有注意到黑格尔—马克思式时间观中所凸显的必然性。
第二,该书在归纳三类时间观的样态特征时存在两处不太准确的表达。(一)在阐述神话式时间观时,该书提到“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ehr)”。这一描述很可能导致人们混淆神话式时间与回返的革命式时间,继而让读者误以为神话式时间强调的是圆圈式的运动轨道。诚然,循环往复的运动在两种时间中都会出现,但神话式时间强调万物向心(围绕诸神)及万物固定不变的位置。在这里,叙事的逻辑掌握在诸神手中,原则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前进和后退。可见,与其说神话式时间是轮回的,不如说它是静止的。也就是说,在神话式的时间中,向心和恒定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循环往复的轨道是第二位的,万物的价值在于“不失位”。相反,虽然革命式的时间轨道为圆圈式的,但它在一个具体的截段上仍有前进或后退的方向。在革命式时间中,圆圈式的轨道是第一位的,位置(Stelle)是第二位的,万物的价值在于“不脱轨”。(二)书中将历史式时间与神话式时间作对比,从而彰显线性的“历史性时间并非是回溯性的,而是相续不断的;不是重复性的,而是追赶着的”。然而,这些描述却是成问题的。首先,线性时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不一定是“相续不断的”。例如其中的末世论时间是从创世到收割的一个线段。连续性和逻辑性恰恰是末世论所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行动是散点化的。另外,线性时间不一定是“追赶着的”。例如,最后的收割全凭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不存在个人的进步和后退;革命式时间也遵循“天机”回返往复地运行,“追赶”也是无意义的。所以说,在这两种线性时间中,并不存在书中所描述的“前后追赶”。
总而言之,在韩炳哲看来,今天的人们正经历着宏大叙事终结后的原子化时间。时间的原子化使时间失去了聚合自身的能力,时间无法建构起整体的张力支撑。过去和未来不再能为现时赋予意义,加速失去了最终的方向。在断点式的时间中,时间的韵律逐渐消弭,富有意义的时间节点无法形成。同时,积极生命的绝对地位也在侵蚀着人们凝思的能力。不停歇的劳动不仅让人们被加速感所带来的焦虑所裹挟,它也让“用于运动的曲调的眼睛和耳朵”消失掉,人的行动降格成一种纯粹的劳动。笔者认为,韩炳哲对现代社会的这一诊断是发人深省的。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典美学的对美的理解:美可归为一种持续、沉淀和凝思式的聚拢。美是时间沉淀的结果,它如同晚霞,而不是刹那间的光辉或吸引力。“直接地享用”是没有能力获取美的。可见,在韩炳哲的理解里,美的特征是持续性、缓慢性和间接性,而不是直接性。该书似乎想借此尝试,在保留(一定的)叙事的前提下(凝思在宽泛的意义下也是叙事的),将叙事与美相结合(这是古典美学所反对的),由此恢复优良时间。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叙事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把这种叙事称为“香气叙事”。在这种叙事里,叙事和美似乎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