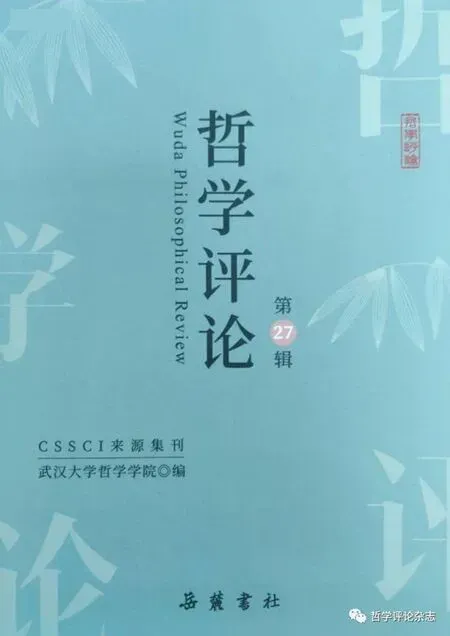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好恶之心”能否保证“仁”?
——论钱穆诠释孔子仁观的情感向度
2021-11-25李亚奇
李亚奇
孔子之“仁”曾被历代思想家论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文》:“仁,亲也。从二从人。”[1]王平、李建廷编著:《〈说文解字〉标点整理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董仲舒则以“博爱”释“仁”,还提出“仁,天心”[2]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俞序第十七》,苏舆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161页。,将“仁”与“天”联系起来。宋儒以“生生”之体来说“仁”,朱子就将“仁”看作“爱之理,心之德”[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阳明将“仁”与“良知”合起来讲,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4]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页。。戴震也认为“仁”乃生生之理,“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卷上》,何文光整理,中华书局,1982年,第62页。。但是,他重视人之情欲,此“理”指气化之条理,与宋儒之“理”不同。民国时期,西方生命哲学的传入,使得学者们开始将“仁”与“意欲”“生命冲动”联系起来。以牟宗三为主的新儒家则主张接着宋明儒学的思路,将“仁”理解为“仁体”。之后,李泽厚、蒙培元、黄玉顺等都重视儒家的情感哲学,看重“仁”的情感向度。综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两条线索,一是注重从情感方面来说“仁”,二是强调将“仁”提升到本体层面。作为史学大家,钱穆也是以一种情感思路来诠释孔子之“仁”,并提出“仁”乃一种“好恶之心”。对此,前人多从史学角度论述,本文则从道德哲学视域出发,解析钱穆诠释孔子仁观的情感向度,挖掘其中的问题意识,而此种“好恶之心”能否保证“仁”则是本文着重省察的问题。
一、钱穆诠释孔子仁观的双重向度
钱穆称孔子思想为“心教”[2]钱穆:《灵魂与心》,《钱宾四先生全集》(46),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4页。。牟宗三也曾提出:“孔子未说‘心’字,亦未说‘仁’即是吾人之道德的本心,然孔子同样亦未说仁是理、是道。心、理、道都是后人讲说时随语意带上去的。实则落实了,仁不能不是心。仁是理、是道,亦是心。”[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牟宗三全集》(5),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26页。然而,钱穆虽然也以“心”释“仁”,但“心”之意蕴却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所说不甚相同。他说:“自其内部言之,则人与人相处所共有之同情曰‘仁心’。自其外部言之,则人与人相处公行之大道曰‘仁道’。”[4]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8页。可见,从情感角度切入,钱穆对孔子仁观的诠释呈现出双重向度。
(一)“好恶之情”释“仁心”
从《论语要略》和《论语新解》中可以看出,钱穆多次用“好恶之心”解释孔子之“仁”。钱穆具有历史慧解,他参考了历代注释[1]钱穆在《论语要略》中指出其参考的资料:“何晏《集解》,可以代表魏晋及两汉人对《论语》之见解;朱熹《集注》可以代表宋明人对《论语》之见解;刘宝楠《正义》可以代表清儒对《论语》之见解。各时代学者治学之目标与方法既有不同,故其对于同一书之见解,亦不能出于一致。学者当平心参观,乃可以兼其长而略其短。”(参见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8页),正是在扬弃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孔子“仁心”的内涵。
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为“仁”下一明确的定义,但孟子却以简单的话语解说了孔子之“仁”。孟子曰: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
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
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仁”即“人”[2]“‘仁者人也’本生之义,我觉得原来只是说‘所谓仁者,是很像样的人’的意思。在很多人中,有若干人出乎一般人之上,为了把这种很像样的人和一般人有一个区别,于是后来另造一个‘仁’字。这应当即是‘仁者人也’的本义。……《论语》的仁的第一义是一个人面对自己而要求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的自觉自反。真能自觉自反的人便会有真正的责任感,有真正的责任感便会产生无限向上之心,……道德的自觉自反,是由一个人的‘愤’、‘悱’、‘耻’等不安之念而突破自己生理的制约性,以显示自己的德性。”(参见徐复观:《释〈论语〉的“仁”——孔学新论》,《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90页);“仁”乃“人心”;仁者爱人[3]“德性突破了自己生理的制约而生命力上升时,此时不复有人、己对立的存在,于是对‘己’的责任感,同时即表现而为对‘人’的责任感,人的痛痒休戚,同时即是己的痛痒休戚,于是根于对人的责任感而来的对人之爱,自然与根于对己的责任感而来的无限向上之心,浑而为一。经过这种反省的过程而来的‘爱人’,乃出于一个人的生命中不容自己的要求,才是《论语》所说的‘仁者爱人’的真意。”(参见徐复观:《释〈论语〉的“仁”——孔学新论》,《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90—291页)。钱穆对孟子这三种说法的解释是:首先,“仁者人也”的“人”指的是人群,“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4]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页。。其次,“仁”乃人心,即“人道必本于人心, 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5]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6页。。最后,仁者爱人,“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1]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页。。那么,这种“温情”具体指什么呢?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钱穆的解说为:“仁即是我心之好恶,何远之有?”[2]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0页。钱穆指出,“人心不能无好恶,而人心之好恶又皆不甚相远”[3]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9页。,“仁者之好恶,即是好仁而恶不仁”[4]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9页。。既知道自身的“好恶”,也知道他人同样有“好恶”的人乃是“仁人”,“仁者,人我之见不敌其好恶之情者也”[5]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0页。。在钱穆看来,“人群当以真心真情相处,是仁也,人群相处,当求各得其心之所安,亦仁也”[6]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5—86页。。可见,钱穆所谓的“仁心”乃是一种“好恶之情”。
在钱穆看来,“好恶”的发显、增进都需要个体做相应的情感工夫。而这种工夫即是孔子所论之“直”。在钱穆看来,“孔子论仁,首贵直心由中”[7]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7页。。钱穆论“直”主要有四点:一、“直”者“诚”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钱穆对此注曰:“‘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8]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7页。“直”即“诚”,就是“心有所好恶”如实畅遂而出。二、“直者,由中之谓,称心之谓”[9]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8页。。“子为父隐”这一行为,表现其子由中之真情,即是“直”。三、“直者,内忖诸己者也”[10]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9页。。“直”与“曲”相对,不仁者不能“内忖诸己”,揣度别人之意向,是迎合他人的乡愿之徒。四、“言直不可无礼也”[11]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1页。。此处涉及“直”的两个问题,一是以何“直”,二是“直”之对象。在钱穆看来,当以“真心真意”而直,“孔子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诈邪曲待人也”[1]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2页。。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钱穆注曰:“人之相处,首贵直心由中,以真情相感通。致饰于外以求悦人,非仁道也。”[2]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8页。“直心由中”表现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以真情感通[3]钱穆所说“感通”汲取了焦循之“情之旁通”之义。(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全集》(17),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592页)此与唐君毅所说的生命之“感通”并不一致。“至对宋明儒之言仁之说,吾初本其体证之所及而最契者,则为明道以浑然与物同体及疾痛相感之情怀、心境言仁之义。并以唯此明道之言能合于孔子言‘仁者静’‘仁者乐山’‘刚毅木讷近仁’之旨。此浑然与物同体之感,又可说为吾与其他人物有其生命之感通,而有种种之爱敬忠恕,……德之原始,亦通于孔子之言法天道之仁,人事天如事亲,与‘仁于鬼神’之旨者。”〔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3页〕他人,“饰于外以求悦人”不可谓“仁”。所谓“直”之对象关乎两者。在内心中,对象为“物”,即“内不以自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对象为“人”,即“外不以欺人”。不仁之人出于某种目的展现“好恶”,将私欲看作真情,此“直心”不正。所以,钱穆认为个人不仅要能“直”,还需要行“忠恕”之道。他说:“若夫肆情恣志,一意孤行,而不顾人我相与之关系者,此非孔子之所谓直也。故欲求孔子之所谓直道,必自讲‘忠’‘恕’始。”[4]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2页。他还指出:“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人心有相同,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所欲所恶,无大悬殊。”[5]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34页。人心所欲所恶无大悬殊,情感能够相互贯通。钱穆以“人心”言“忠恕”,仁人即是以直心之好恶,在人情的感通处、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实现仁道。
(二)“以礼导情”解“仁道”
钱穆认为,“仁”为“好恶之心”,那么,求仁首先应当本于“心”。但是,“仁虽本诸心,犹必见之事焉。凡舍事而言心者,则终亦不得为仁也”[1]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5页。。钱穆将现实中的规范提到与内在之情同等的地位,希望仁、礼能够内外辅助,实现仁道。他指出,“仁者,从二人,犹言人与人相处,多人相处也。人生不能不多人相处”。[2]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8页。人们不仅需要心与心的感通和交流,而且需要将这种情感的交往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就涉及为情感的交往寻找一个正当规范的问题,即钱穆所说的“以礼导情”。
钱穆有言:“曰仁,曰直,曰忠,曰恕,曰信,皆指人类之内心而言,又皆指人类内心之情感而言。孔子既为一慈祥恺悌、感情郁之仁人,其论人群相处之道,亦若专重于内心之情感者,而实非也。盖孔子一面既重视内心之情感,而一面又重视外部之规范。……至于孔子专论外部之规范者,则曰‘礼’。”[3]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1—102页。作为人群相处之道,仁不仅指内心之情感,而且指外部之规范。“礼”就是孔子所谓外部之规范。“直心由中”体现了各人在好恶之心上的感通工夫。交往之礼的提出,则为人之相处提供了节度分限。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惧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钱穆认为,孔子说“直”必须要有“礼”。孔子又曰:“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可见,“直”与“礼”需要相融合,而要学的东西即是礼:
礼者,人群相处之节度分限也。人之相处,其存于内者,不可无情谊,故孔子言忠言直。其发于外者,不可无分限,故孔子言礼言恕。约而言之,则皆仁道也。故言礼者,不可忘内部之真情。言直者,不可忽外界之际限。[4]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1页。
作为一种人群相处的节度分限,“礼”以内在之情为基础,为“好恶”界定际限。钱穆并不赞同清儒对“礼”的诠释,因为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上讲“设礼以限仁”,乃是束缚于“礼”而不知“仁”,“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其意义”[1]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3页。。在钱穆看来,清儒 “以礼代理”的做法并不能凸显孔子仁观中“仁”“礼”关系的真实意蕴。钱穆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礼”与“仁”的合一。孔子也常常“仁礼”并言。“仁存于心,礼见之行,必内外心行合一始成道,故《论语》常‘仁礼’并言。”[2]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18页。在钱穆看来,孔子之“礼”是人心之仁的外在表达,虽然这种表达要化为现实中种种的制度规范,但依然不能抹杀其仁心情感的本质。正是在这种种的规范制度之中,人的感情才得以完整而真实地表达。
钱穆认为:“盖人之精神,虽若存于内部,而必发露为形式,舒散于外表。故外部物质之形式,即为内部精神之表象。礼乐之起源在此,礼乐之可贵亦在此。”[3]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3页。人的好恶之心,虽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必然需要应物而发,发露出来就成为外在的礼,而“礼”实际上仍然是内在精神的表达。可见,“礼”作为外在的规范,能够引导人们在真实的环境中表达自身的真挚感情。故钱穆说:“夫礼乐本自吾人内部情感之要求而起。”[4]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4页。孔子之“礼”所要表达的是在现实的交往环境中抒发情感,即“以礼导情”。他还指出,“礼”的本意为“导达人情”,“人有郁恳挚之感情,乃以礼乐为象征,以导达而发舒之,使其感情畅遂,得有相当之满足也”[5]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3页。。钱穆主张,仁心需要以“礼”为形式在现实的事物中真诚地表露。然而,在现实中,“好恶之心”往往在发露的过程中有所偏失。所以,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失不仅需要我们在内心处行“忠恕”,而且要我们在具体的礼节规范中导达、发舒真情,进而实现人与人心灵的感通和交往。钱穆说:“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若人心中无此一番真情厚意,则礼乐无可用。如之何,犹今云拿它怎办,言礼乐将不为之用也。孔子言礼必兼言乐,礼主敬,乐主和。礼不兼乐,偏近于拘束。乐不兼礼,偏近于流放。二者兼融,乃可表达人心到一恰好处。”[1]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73页。他认为,孔子时常“礼乐”并提,事实上,“礼乐”也都是人们之间真情的表达。
二、钱穆论说孔子仁观的问题意识
钱穆早年已经对孔子的仁观做过全面的论述,《论语要略》一书是其最早一部论述孔子思想的著作。虽然此书只是他编写的教案,但此书语言简明,内容通俗易懂。早年,由于受到梁启超和胡适等人思想的影响,钱穆接受了清儒的实学思想,再加上他喜爱历史,不满西方割裂超越与现实的二元论体系,更是加深了其对中国儒学实践精神和一元论体系的看重。所以,他对一些儒者区分形上形下的做法表示不满,却十分欣赏阳明。因为在他看来,阳明和清儒一样,都具备实行精神,并且能够遵从孔子之意,重视人生之好恶情感。他曾指出:“以义理为虚,以气质为实,又清初言理者一特征也。其后颜习斋、戴震于此等处皆竭力发挥,以为攻击理学之根据。然阳明以吾心之好恶是非为良知,又以实致吾心之好恶是非于事事物物为致良知,实已走入此一路,故蕺山、梨洲、乾初皆先言之。”[2]钱穆:《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1),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82页。所以,钱穆借用阳明的“好恶”之说[3]钱穆在《心与性情与好恶》一文中指出:“我的《论语要略》,有几处只从好恶之心来释仁字,固可谓是本原于阳明。”〔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钱宾四先生全集》(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04页〕,延续清儒的实行精神,进而形成了自己诠释孔子仁观的问题意识。
(一)消解“仁”之形上意义,紧扣人生情感论“仁”
钱穆特别提出“好恶”二字来论说孔子之“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其实,《论语》中这些说法都展现出一种“好恶”观念。《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此也是对美德之“好”。《孟子》中有:“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这是说人们对声、色、味有共同的喜好。胡五峰曾指出:“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1]胡宏:《胡宏集》,吴仁华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页。对此,朱子曰:“好恶固性之所有,然直谓之性则不可。盖好恶,物也,好善而恶恶,物之则也。”[2]胡宏:《胡宏集》,吴仁华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331页。阳明则指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3]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以“是非”和“好恶”来论说良知。可见,许多儒者已经注意到“好恶”这一概念。
用“好恶”论“仁”与“性”,清儒的说法就比较多了。戴震指出,从孟子所谓“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孟子·告子上》)可以看出,“以好恶见于气之少息犹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气也”[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卷中》,何文光整理,中华书局,1982年,第71页。。焦循对“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解释为:“仁者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故为能好能恶。必先审人之所好所恶,而后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恶恶之,斯为能好能恶也。”[5]焦循:《论语补疏》(上卷),陈居渊主编,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633页。凌廷堪则有《好恶说》,对“好恶”这一概念做过细致的论述。他指出,《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言“诚意”即在“好恶”。“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中之“好恶”即《大学》中之“好恶”[6]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142页。。在钱穆看来,戴震及其后学之“好恶”和阳明所说之“好恶”很是相近。他指出:“其(指戴震)论性语,尤多与阳明谓近。凌廷堪主以礼为节情复性之具,而曰‘好恶者,先王制礼之大原也。性者,好恶二端而已’亦与阳明‘良知只是好恶’之说合。焦循子廷琥为其父《事略》,称:‘府君于阳明之学,阐发极精。’今焦氏《孟子正义》及《文集》中语,依据良知立说者,极多。阮元《说一贯》、《说格物》皆重习行,即实斋‘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之意。”[1]钱穆:《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1),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36页。可见,钱穆表面上借用了阳明的“好恶”概念,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戴震及其后学的“好恶”观,展开了其对孔子之“仁”的论述。
一方面,钱穆指出,孔子所论之“仁”关乎“人道”,对“天道”涉及较少。他认为,“孔子论学,皆切近笃实,不尚高妙之论,而犹注重于现实之人事”。[2]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6页。孔子论“仁”,着紧在人生一面,并不从形上角度论述“性与天道”。孔子所谓“道”是人伦日用之道,其含义亦在于人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钱穆解释道:“天道犹云天行,孔子有时称之曰命,孔子屡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3]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7页。在钱穆看来,孔子之后,墨子、庄周爱言“天”,孟子、荀子喜言“性”,这才开启了此后思想界的争辩。但是,学者不该以孟子说《论语》,“孟子之书,诚为有功圣学,然学者仍当潜心《论语》,确乎有得,然后治孟子之书,乃可以无病”[4]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7—168页。。“孔子之教,本于人心以达人道,然学者常教由心以及性,由人以及天,而孔子终不深言及此。”[5]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7页。他还指出,学者在理解“五十而知天命”一语时,不宜轻言知天命,只当知道孔子心中有此境界即可,“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6]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5—36页。。另一方面,钱穆认为,“好恶之心”是一种经验的人生情感。他指出,孔子本人心以立教,不应好高骛远以求之,否则会失其真义。孔子虽然不多言“天道”与“性”,但很早就注意到人之先天原始的本心。此“心”一本之于“天”,表现为人类最初的一种好恶之情。其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心”,其实“孝心”即“仁心”,此“心”纯以“天”合,与生俱来,自然有之。“孔子论学,都就人心实感上具体指点,而非凭空发论”[1]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9页。,人们能对别人有同情,能关切,这是人类心灵最宝贵的地方。
由上可知,钱穆认为,孔子论“仁”,主要指人心,归本于人生情感。钱穆消解了“仁”的形上意义,并没有特别看重“天命”“天理”这些形而上学的依据。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是“天”所赋,但针对这一禀赋的天命本原,我们不必过于追求,只应根据现实的好恶之情来做工夫即可。
(二)注重“好恶”之践履能力,贯穿实践动向于“仁”
在钱穆看来,孔子之教,言“人”不言“天”,言“心”不言“性”,只有不断地为学和实践,才能使人生行事与心情合一,人文与自然之天合一。孔子只就事论事,来求人文之实际,而一切人文,都是从天地自然而来,也必在天地自然中实现。因人生可以见自然,人若要明白天地自然,在人生中实践即可。
首先,钱穆发挥了孔子之“直”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直心由中”。钱穆之所以重视孔子之“直”,与他早年读了阳明的《传习录》有关。那时候,他认为朱子将“仁”说成“心之德,爱之理”似乎不近人情。“因若抹杀了人心之好恶来言仁,那仁字就会变成仅是一个理。我们一见理字,总会想它是一个空洞的,又是静止的,决定的,先在的,而且或许会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因此,我们抹杀人心现实好恶而径来说天理,说仁,其流变所极,会变成东原所言之以意见杀人。”[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钱宾四先生全集》(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04页。如果“仁”变成“理”,失去了欲为能动的情感倾向,就不能彰显“心的生命”[1]“其实常惺惺亦只是如运水搬柴皆是神通之类,与心斋放下相距无几。总之是随动顺动,无自内而生的活力。无勇不前,可说是心的体态,绝非心的生命。”〔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五册),《钱宾四先生全集》(2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32页〕,那么,这种僵化的“理”就有可能成为伪仁义、伪道德。钱穆在解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时也指出,此处“恶”字并不是善恶之“恶”,而是“好恶”之“恶”,“‘无恶也’,乃指示人心大公之爱”[2]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18页。。也就是说,人们只要存心在“仁”,对他人便没有真所厌恶的了。可以看出,钱穆比较看重“好恶”作为欲向动力对行为的推动作用。因此,钱穆十分欣赏阳明“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3]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这句话,并且非常重视阳明的“诚意”说。此处,我们暂且不论钱穆的“直心由中”与阳明的“诚意”是否具有一致性,仅就钱穆揭示出“好恶”这种情感的践履能力这一点来看,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从道德哲学视域来看,人的“好恶”能力确实在行为的实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次,钱穆还将“礼”解释为情感的外在表现,提出“以礼导情”之说。钱穆早年即已接触到清儒的许多著作,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实际上并不满足于清儒对孔子的论述,而是在反思中建构了自己的观点。他在后来特别指出凌廷堪对“礼”的论述,认为他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礼的情感面向。如果只用外在规范来节制“好恶”,而不是积极地引导“好恶”,这是无法真正契合于“仁”的。所以,他说:“礼之本在于双方之情意相通,由感召,不以畏惧。”[4]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3页。在丧礼之中,我们最能看出情感的价值。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钱穆指出:“生人相处,易杂功利计较心,而人与人间所应有之深情厚意,常掩抑不易见。惟对死者,始是仅有情意,更无报酬,乃益见其情意之深厚。故丧祭之礼能尽其哀与诚,可以激发人心,使人道民德日趋于敦厚。”[1]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页。在钱穆看来,儒家并不主张死后灵魂的存在,所以不提倡宗教信仰。但是,儒家特别重视葬祭之礼,常以“孝”来导达人类之仁心。因为祭礼乃是“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即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2]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7页。。
总之,钱穆之所以用“好恶之心”来诠释孔子之“仁”,一方面是表达对情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好恶”作为一种践履能力的价值,展现“仁”的实践动向。在他看来,孔子之“仁”,极其高深,但又平易近人,“亦不过在人性情之间,动容之际,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常,出处去就辞受取舍,以至政事之设施,礼乐文章之讲贯”[3]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22—323页。。 “仁”并不是一种舍弃具体可见之情感,而另外推论的一种不可窥寻之道。仁道的实现有赖于人之“心”,此“心”非一人一己之心,乃是人文全体大群所成之文化心。所以,孔子教人无不贴近人文世界,通过一己之心,融会历史大群之心。
三、“好恶之心”能否保证“仁”?
由上可知,钱穆诠释孔子仁观的双重向度和问题意识是较为清晰的,但是,其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从道德哲学的视域出发,省察钱穆所谓的“好恶之心”能否保证“仁”。这种省察主要从三个问题切入,第一,“好恶”是否为道德意义上的,能否确立道德的应然性?第二,“由中”之“直心”是否为道德判断原则?第三,导达人情的“礼”与“仁”的内在张力问题。
说起“好恶”,人们总觉得它不放心。作为一种感性之情,“好恶”的价值难以确定,它往往随物而动而变成私欲。“好恶”是否为道德意义上的?如果它本身的道德意义不明确,“好恶之情”如何能保证“仁”呢?徐复观曾就此点提出异议:“按中国过去所说的好恶,指的是由‘欲望’发展而为‘意志’的表现。……因此,好恶并非人所独有。而且最能以好恶之真情示人者亦莫过于一般动物。其次,一种好的行为,要通过好恶而实现,一种坏的行为,也是通过好恶而实现。”[1]徐复观:《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4—205页。“好恶”由欲望发展而来,并且动物也有“好恶”,好的、坏的行为都可以通过“好恶”来实现。因此,“好恶”本身无所谓善恶价值。那么,钱穆所谓的“好恶”是否为道德意义上的呢?
事实上,钱穆认为,“好恶之情”与“私欲”是有区别的,从他对凌廷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探得究竟。凌廷堪《好恶说》中有:
好恶者,先王制礼之大原也。人之性受于天,目能视则为色,耳能听则为声,口能食则为味,而好恶实基于此,节其太过不及,则复于性矣。……然则性者,好恶二端而已。……《大学》“性”字只此一见,即好恶也。《大学》言好恶,《中庸》言喜怒哀乐,互相成也。好恶生于声色与味,为先王制礼节性之大原。[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140—141页。
性受于天,即是所谓目、耳、口之能视、能听、能食。“好恶”也是基于人的官能之欲而产生的,所以,先王制礼来节其“太过”与“不及”。钱穆注曰:“此以好恶言性,其说甚是。顾专以声、色与味言好恶,则非也。好恶固有关于声、色、味者,然实不尽于声、色、味。……要之为荀学之承统而已。”[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全集》(17),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640页。钱穆认为,以“好恶”来说“性”,并无差错,但如果说“好恶”只是声、色、味之“好恶”,则是继荀子之承统,与孔孟传统不相一致。他曾指出:“‘情’失其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辨。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4]钱穆:《孔子与论语》,《钱宾四先生全集》(4),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53页。可见,在钱穆那里,除了声、色、味,人生还有更大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追求。作为人之本能的自然之欲,在人之本原处与好恶之情是一致的。“饮食男女既为人生所必需,并可说此人生本质中一部分。因此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内,即包括有食、色。孟子说性善,连食色也同是善,此乃人生之大欲,人生离不开此两事。食色应还它个食色,不该太轻视。”[1]钱穆:《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钱宾四先生全集》(24),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59页。但是,当“情”失其正,成为“私情”“私欲”,“好恶之情”与“欲”就必须被区分开来。
然而,钱穆并没有认清“情”既可表现为恶的私情(私欲),又可展现为自然中立的情感(好于声色味),还可为善的道德情感(四端之心)。他否认了“好恶”指向恶的“私欲”,但也没有挺立起道德情感之善的道德意义。所以,他似乎是将自然与道德混为一谈了。比如,上文提到他认为“此以好恶言性,其说甚是”,“好恶固有关于声、色、味者”。由此看来,钱穆十分肯定与“私欲”处于同一层次的自然中立的情感,并且将这种中立的“好恶”与道德情感混同起来。他曾说:“然要之求衣求食,为人类比较低级之冲动;求道与学,为人类比较高级之冲动。吾人惟能以高级冲动支配其低级冲动者,乃得为君子。”[2]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11页。钱穆将“求衣求食”的自然本能和“求道与学”的道德要求归于一类,只以“低级”与“高级”来分别,即是将此二者视为同质,且同属于情感意义下的“好恶”冲动。当高级冲动支配低级冲动时,就能形成所谓“善”的行为。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在实现一个行为时,我们如何能够不将私欲看成道德呢?这就涉及道德的应然性问题。徐复观就曾指出:“儒家不抹煞好恶,决不是即在好恶上树立道德人生的标准。因为好恶之本身不可以言善恶”[3]徐复观:《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他还说钱穆“完全以‘好恶’来解释《论语》的仁,即将儒家精神完全安放于‘好恶’之上,我想,这是继承戴震的思想,而更将其向前推进一步的”。[4]徐复观:《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钱穆在《心与性情与好恶》一文的回应中并没有否认他受到戴震的影响,但也指出他并不完全赞同戴震,而是认为阳明以“良知”论“好恶”更为亲切。那么,钱穆的“好恶之情”与阳明所说的良知一样吗?
阳明曰:“良知即是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1]王守仁:《与马子莘》,《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又说:“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2]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可见,此“天则”即天理,是指人类先验普遍的道德原则。陈来曾指出:“天理作为道德法则的意义仍是宋代理学的基本用法。”[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然而,钱穆却指出,要做好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先必在理论上承认各人自有一个知善知恶之良知”[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钱宾四先生全集》(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12页。。看到这里,我们可能欣喜钱穆认为各人应该有“知善知恶之良知”;但是,话锋一转,他却说“今若否认别人智慧,认为他不够分辨善恶与是非,但他至少能自有好恶”[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钱宾四先生全集》(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12页。。不仅“知善知恶之良知”是在理论上存在的,而且如果一个人并不确信他能够分辨善恶与是非的话,他至少还能自有好恶。所以,钱穆说:“人类乃由其好恶而转出是非与善恶之价值批判的。”[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钱宾四先生全集》(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12页。虽然钱穆指出,“好恶”有其价值,有其“天则”,但“就人文历史演进之实迹观之,则人类显然从与禽兽相近之好恶中而渐渐发现了人类本身的许多天理与天则,而又逐步向其接近”[7]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钱宾四先生全集》(1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06页。。可见,钱穆所强调的人人具有的“好恶之情”是一种自然中立的能力,此与阳明将良知看作普遍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天理”并不相应。所以,在钱穆那里,道德的应然性并没有被确立起来。“由于我们人类有感性生命底带累,道德的要求对于我们的现实意志(意念)而言,具有强制性,因而是一种命令。”[8]李明辉:《儒家与康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50页。钱穆只守住了“好恶之情”中有道德价值这一点,并没有弄清自然之欲与道德情感的异质性[1]在钱穆看来,性中有“欲”,“欲”与“情”一脉相生。“欲于己者,后世则专谓之‘性’,不谓之‘欲’。实则性中自有欲。”〔参见钱穆:《晚学盲言》,《钱宾四先生全集》(49),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53页〕,这样就容易导致情欲、善恶的混淆。“情”虽然以“好恶”为基础,但“理性之好恶”与“感性之好恶”并不相同,如果不能将显发行为的“情”与道德原则从根本处融为一体,就不能引导行为成为道德的善。我们要区别两种意义的“善”:道德之善与自然之善。“前者即‘善的意志’之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善;其价值在于它自身,而非在于它之能实现或达成另一项目的。反之,后者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善;其价值仅在于它之能实现或助成所预设的目的。”[2]李明辉:《儒家与康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51—52页。自然中立的“好恶之情”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虽然它能够为行为提供动力,却缺乏一种绝对普遍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从此确立起道德的应然性。
作为与自然之欲混合的现实情感,“好恶之情”的道德应然性不能确立,道德的判断原则就会落空。那么,“直心由中”之“中”是否能成为道德的判断原则呢?钱穆认为,孔子之“直”与阳明之“诚意”相似,“直”即“诚”。他不满于阳明在《大学问》中拘泥于大学文本将“诚意”解释为“意有善恶”,而认为“讲良知只辨好恶”[3]钱穆:《阳明学述要》,《钱宾四先生全集》(1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10页。。在钱穆看来,阳明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解诚意,本属无病。“诚”即“直”,“如实以出之”之义,“在心既无善恶,在物也无善恶,只有此心之好恶,便是天理”[4]钱穆:《阳明学述要》,《钱宾四先生全集》(1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13页。。“阳明从此心好恶上指点出良知,从好恶才分了是非,从是非再定了善恶。而良知的好恶则是先天的,人间的善恶是后起的。”[5]钱穆:《阳明学述要》,《钱宾四先生全集》(1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8页。然而,钱穆并没有指出“好好色、恶恶臭”与“好善恶恶”的本质不同。所以,如果仅仅把诚意理解为如实地按照意之指向去做,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好”于声色也是“好”,但这并不具备道德意义。所以,陈来指出,“《大学》把诚意解释为不自欺,显然预设了两个自我。要求不欺自我,这个自我是指人的德性自我,而‘诚意’又是对治意之不诚而发,不诚之意是指人的经验的自我”。[1]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果如钱穆所说“在心既无善恶”,那么此“不欺自我”之自我就会成为中性的无道德意义的自我。诚其意之好恶才有善恶之起,那么,这里就有将良知混同于中性之“意”的倾向。但是,在阳明那里,“知”与“意”却是不同的。在提出“致良知”说之后,阳明特别重视“意”与“知”的关系问题。他说:“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2]王守仁:《答魏师说》,《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可见,良知并不与“意”等同,而是意念的道德判断原则。这种道德判断意义即表现在良知的“明觉”和“知是知非”上。此“明觉”并不是认知意义指向对象的知觉,也不是意识现象的本来状态,而是本体意义的本心之知。本然之意和本心之知是有差别的。“因为即使在‘意无不诚’的境界,意与知仍然并不就是同一的。”[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作为经验层随物而动的“意”与作为道德理性的“知”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同一性。所以,阳明要将“诚意”与“致知”联系起来,“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4]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0页。。
所以,钱穆所谓“直心由中”与阳明“致良知”提出之后所说的“诚意”并不一致。由中之“直心”与“是非之心”两者有本质差别[5]“对宋明儒而言,他们所谓的作为人之为人根据的‘仁心’‘仁性’不仅与天道、天理通而为一,而且具超越个人的生死与天道、天理同在的绝对性、普遍性、恒常性,故他们那种既超越又内在的‘仁心’或‘仁性’并非指经验性的认知心、感性的血气之心、心理学意义的心或自然性的人性、社会性的人性;他们所谓的‘人’是与天道、天理贯通的贯通人,并非仅仅是生物性的人、社会性的人。”(参见文碧方:《论作为“为己之学”的儒学》,《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郭齐勇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钱穆的“直心”强调应物而起、应人而有的“好恶”。此“好恶”作为一种中性的情感反应能力,混同了“好色恶臭”和“好善恶恶”,与能动性的意欲较为相似。他曾多次强调“心”之欲为能动性:“只说是不为外物所动,却没有指点出此心之对外物,自有他的一番进取与活动。自有他一种感的力。”[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五册),《钱宾四先生全集》(2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31页。钱穆将良知看作是个好恶之“诚”,知道此“诚”,随物进取而活动,“诚意之极”才是真能好恶。可见,“直心由中”之“中”只是一种“意无不诚”之本然之意,或者说是随物而动的情感平衡状态。
钱穆对实践工夫的过分重视导致他并没有把握到心之“明觉”的道德判断原则意义。“直心由中”之“中”作为一种主观的、随物而动的“意无不诚”的情感平衡状态,并不能够成为“好恶之情”的道德判断原则。因此,他强调,在仁道的实现过程中,我们不能空谈仁心。钱穆认为:“盖礼有其内心焉,礼之内心即仁。……言复礼,则明属外面行事,并有工夫可循,然后其义始见周匝。”[2]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3),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19—420页。所以,他非常重视孔子之“礼”的实践工夫意义。然而,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规范,导达人情的“礼”是否就是“仁”呢?这就涉及礼与仁的内在张力问题。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人际关系对于‘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它是一个内在性的原则。这种‘内在性’意味着‘仁’不是从外面得到的品质,也不是生物的、社会的或政治力量的产物。……‘仁’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并不是由于‘礼’的机制从外面造就的,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它赋予‘礼’以意义。”[3]杜维明:《“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张力》,《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胡军、丁民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0页。钱穆将“仁”之内在性归于现实的“好恶之情”,实际上并没有挺立起“仁”的道德应然性和主宰性,这与牟宗三将“仁”归根于“觉”与“健”合一的真实的本体[4]牟宗三:《中国哲学之特质》,《牟宗三全集》28,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32页。确实不同。所以,钱穆要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提出一个节制“好恶”的“礼”。同时,钱穆不得不将“礼”提到与“仁”的地位一样的高度,因为只有这样,外在的力量才足以辅助内在之情。然而,如果始终没有一个“内发而对其好恶发生自律或超越转化”[1]徐复观:《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的道德原则作为主宰,那么,“礼”是否能将人指引到道德的方向上去,却是或然的。“礼”在后天实践的地位虽然不容抹杀,但从根本上说,“礼”作为“导达人情”的节度分限并不能取代内在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内在的道德原则没有被坚强地挺立起来,或者说它呈现为一种后天积累的状态,那么仁道的实现,仁与礼的合一,将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实践过程。
四、结语
总的来说,钱穆提出“仁”乃“好恶之心”,是以一种情感思路来诠释孔子仁观的。钱穆对孔子仁观的诠释呈现出双重向度,即“好恶之情”释“仁心”与“以礼导情”解“仁道”。这些都展现了他消解“仁”之形上意义,紧扣人生情感论“仁”;注重“好恶”之践履能力,贯穿实践动向于“仁”的问题意识。钱穆并不认可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对超越与现实的隔离,他希望通过对情感的强调来实现两者的合一。他对孔子思想内在性和淑世性的倚重显然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为了应对西方哲学的侵扰而开显孔子精神的内在超越性[2]关于“内在超越性”,杜维明指出:“儒家有它超越的一面,也有可以离开现实而构建的精神价值。但是,这个超越是内在于现实来实现的。”(参见杜维明:《超越而内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载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60页)确有不同。从道德哲学视域来看,钱穆由“情感”切入“道德”的做法并不透彻。从区分“情”与“私欲”来看,钱穆守住了儒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但他并没有认清“好恶”之自然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本质不同。“好恶之情”作为一种自然中立的情感,与阳明所谓作为普遍道德法则的良知并不相应。钱穆表面上借用了阳明的话语,却从实质上改造了阳明即体即用的良知。他消解了“仁”之形上意义,希望在经验之情感中为行为寻找根据。然而,“直心由中”只是一种随物而动的情感平衡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意无不诚”之本然之意。本然之意和本心之知是不同的。钱穆对实践工夫的过分重视导致他并没有把握到心之“明觉”的道德判断原则意义,而作为“导达人情”的节度分限的礼也不能从根本上内发而对好恶发生超越转化的作用。最终,钱穆所谓的“好恶之心”并不足以保证“仁”。现在看来,“好恶之心”何以保证“仁”呢?首先,我们需要区分“情”与“欲”的不同性质;认清善的价值在于好恶之动机,而不是“好恶”本身,挺立起绝对普遍的道德原则,从道德意识摆脱自然生命欲望的基础上理解自然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本质差别。其次,要区分心的两种不同状态。心之“明觉”知是知非,是意念的道德判断原则,而钱穆所说之应物而起的“好恶”侧重于能动地辨析是非。最后,还要认清礼与情的内在张力。虽然起到实践作用的“礼”之地位不容抹杀,但其不足以内发而对好恶发生超越转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