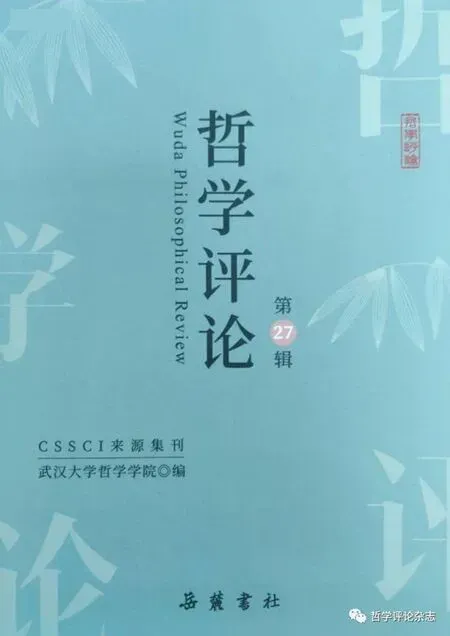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歧路灯》与理学修养观
2021-11-25朱燕玲
朱燕玲
一、引言
《歧路灯》为河南宝丰李海观(1707—1790)所著。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有关其生平、家世及诗文的研究,参见栾星、吴秀玉等学者的研究[1]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栾星:《李绿园家世订补》,见中州古籍出版社编:《〈歧路灯〉论丛》(第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7—303页;栾星:《李绿园家世生平再补》,《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1期,第258—271页;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6年。,兹不赘述。《歧路灯》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脱稿之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至民国十三年(1924)始有洛阳清义堂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才有北京朴社出版之由冯友兰、冯沅君校点的一册二十六回排印本——此乃《歧路灯》成书百五十年来首个正式出版品。在漫长的传抄过程中,《歧路灯》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关于《歧路灯》之流传与版本研究,学界已有丰硕成果[2]栾星按照有无《家训谆言》、过录题识、作者题署将《歧路灯》的传世抄本分为新安传出本,宝丰传出本,新安、宝丰二者的合流本。吴秀玉、徐云知亦持是议。在此基础之上,王冰依据回目、文字之多寡、异同,将现存及新发现的《歧路灯》版本分成国图抄本、上图抄本两大系统。朱姗根据作者题署时间先后、以第九回为代表的相关情节和回末诗之详略有无,以及不同版本的全文比勘,将存世及新发现的《歧路灯》版本分作甲本系统、乙本系统、介于二者之间呈“中间态特征”的甲本系统的分支形态。,此处不赘。1980年栾星以十一部抄本、印本为底本校勘而成的百八回《歧路灯》出版之后[3]李绿园:《歧路灯》,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随着《歧路灯》不同传世抄本的不断发现,栾星校注本的疏漏舛误之处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余辉、王恩建、苏杰、王冰、刘洪强、朱姗对此均有校勘研究。按:栾校本虽不免舛错,然开辟之功,不容抹杀。为研究之便利,本文以栾校本为底本,凡所引用,均出此本,不另出注。,引发了学人对于《歧路灯》题材归属、史料价值、文学地位,尤其是语言学、文献学、民俗学方面的广泛、热烈关注,相比之下,关于《歧路灯》思想内涵的研究则相对冷清、薄弱。尤其是,学者虽已注意《歧路灯》与《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章的指涉关系,如《歧路灯》屡次引用“牛山之木”章的关键概念:“萌蘖”“平旦之气”“夜气”等[4]苏杰:《〈歧路灯〉引用儒家典籍考论》,《兰州学刊》2010年第8期,第167—172页。,然“牛山之木”章的主旨究竟如何理解?“牛山之木”与《歧路灯》到底有何关系?李绿园为何在《歧路灯》中反复使用“牛山之木”章的相关概念?就笔者管见所及,似无相关讨论。但理解“牛山之木”的章旨,是了解李绿园学术立场及《歧路灯》主题与结构的关键。质言之,李绿园以朱子对于“牛山之木”章的诠释为根据,将仁义之心人所固有,应时时处处用力做操存涵养之工夫,使良心常存而勿放舍,与《歧路灯》浪子回头、改过迁善的主题相结合。将理论上之“梏之反覆”与《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翻来覆去之误入歧途又立志改过的情节相映照,使理学观念与小说主题、结构相贯通。是以,深入理解“牛山之木”章的主旨,诚为深化李绿园及《歧路灯》研究的关键。
本文首先分析朱子如何诠释“牛山之木”章,从字词之训诂到章句之阐释,与其他儒者有何区别及为何有别,引出由于儒者对于心、性、气等概念及其关系之理解不同,是以各自之工夫进路亦有差别,重点在于阐述程朱理学之操存涵养工夫。进而探析李绿园如何受到程朱理学修养观之影响,以及《歧路灯》怎样从主题与结构两方面体现程朱理学之修养观:良心善性先天本有之心性论,与人心易为外物牵引、私欲遮蔽而放舍,须无时无处不用其力,以存复良心善性之工夫论,是《歧路灯》浪子回头、改过迁善主题的理论依据。谭绍闻屡次誓言改志,却因心无主张,一为匪人引诱即落入下流的情节结构,是“梏之反覆”抽象理论的具体呈现。
二、“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歧路灯》多次引用“牛山之木”章的相关概念,如“平旦之气”“夜气”“萌蘖”等,如第二十回:
冲年一入匪人党,心内明白不自由。
五鼓醒来平旦气,斩钉截铁猛回头。
第二十五回:
那绍闻睡了半夜,平旦已复。灯光之下,看见母亲眼睛珠儿,单单望着自己。良心发现,暗暗的道:“好夏鼎,你害的我好狠也!”这正是:
自古曾传夜气良,鸡声唱晓渐回阳;
天心徐逗滋萌蘖,依旧牛山木又昌。[1]据朱姗所说,新发现之吕寸田评本《歧路灯》第二十五回回末诗前有“这正是:牛羊牧后留萌蘖,只怕明早再牿亡。有诗为证”一句,则其他《歧路灯》传世抄本可能亦有引用或化用“牛山之木”章之例。朱姗:《新发现的吕寸田评本〈歧路灯〉及其学术价值》,《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总第114期),第132页。
第二十六回:
且说谭绍闻五更鼓一点平旦之气上来……
第三十六回:
又添上自己一段平旦之气……
第四十二回:
人生原自具秉常,那堪斧斤日相伤;
可怜雨露生萌蘖,又被竖童作牧场。
第八十六回:
原来人性皆善,绍闻虽陷溺已久,而本体之明,还是未尝息的。一个平旦之气撵回来,到孝字路上,一转关间,也就有一个小小的“诚则明矣”地位。
此外,《歧路灯》还几次运用“树”这一意象,显然亦与“牛山之木”相关。这一点容后再论。然“牛山之木”章的主旨如何理解,既关系李绿园之学术立场如何判定,亦牵涉《歧路灯》之主题定位、结构设定如何把握。换言之,面对不同时代、学派的儒者对于“牛山之木”章的不同诠释,李绿园认同何种学说?《歧路灯》又是如何从主题、结构两个层面体现其学术宗旨的?
解读“牛山之木”一章,关键在于“平旦之气”“夜气”“存”“亡”“出”“入”如何解释?“日夜之所息”者为何?“梏亡”者为何?“夜气不足以存”者为何?所“养”者为何?如何“养”?如何“操”?孟子为何以及如何从“牛山之木”说到“仁义之心”?
宋儒朱熹谓“‘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或“善心滋长处”[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4、1902页。。“平旦之气”是“未与物接之时清明之气也”。[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2页。所谓“梏亡”者,非如先儒所说“梏亡其夜气”,而是“梏亡其良心也”。[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8页。“夜气”非如前贤所说为良心[2]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8页。,“夜气者,乃清明自然之气”[3]朱熹:《朱子语类》卷52,《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16页。。“夜气只是不与物接时”[4]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1页。。亦即“夜气”与“平旦之气”皆为未与物接之时清明之气。“夜气不足以存”,学人多解作夜气不存[5]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8页。汉儒赵岐即以“夜气不能复存也”注“夜气不足以存”。据朱子所写之书信,可知宋儒张栻即持是议。(分别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1,《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52—1353页。),唯伊川说“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6]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第321页。,换言之,夜气之所存者,即“本然底良心”[7]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8页。;“夜气不足以存”,非“心不存与气不存,是此气不足以存其仁义之心”,“‘操则存,舍则亡。’非无也,逐于物而忘返耳”,“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则是在这里,出则是亡失了”[8]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0、1905、1904页。。又说“所谓入者”不是“此心既出而复自外入也”,而是“逐物之心暂息,则此心未尝不在内耳”。[9]朱熹:《四书或问》卷11,《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86页。“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处”。[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5,《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62页。
按照朱子之诠释,“牛山之木”譬喻“人之良心,句句相对,极分明”[1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2页。,亦即“山木人心,其理一也”[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2页。。牛山之木原本茂盛而秀美,如同人生而本有仁义之良心。牛山如今光秃秃没有草木,并非牛山原初即无材木生焉,是因其临近齐国之都邑,国人皆以斧斤砍伐其草木以为柴薪,促使牛山丧失昔日生木之本性。人之所以放失其本然之良心,亦复如是,物欲之斧斤日日戕贼其本心,固有之仁义因而不能复存。山木虽遭砍伐,其根株之未尽除者,得日夜之生息、雨露之润泽,犹有嫩芽旁枝潜滋暗长。良心虽已放失,平旦之时未被利欲、事绪纷扰,其气清明之际,本心必然有所呈现。萌蘖既生,如能加以培植养育,山木之美,或可复见。良心既显,如能加以存养扩充,天理之良,或可复存。然山木既伐之后,萌蘖之发育甚弱,又遭牛羊之畜啃食践踏,山之美材遂尽失而若彼濯濯。良心既放之余,发见至微,所存无几,又被白昼之胡作非为汩没陷溺,人之天良遂尽丧而违禽兽不远。总而言之,山木不存而若彼濯濯,非山之本性不生材木,其害在于遭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失培养之力。良心放失而违禽兽不远,非人之秉性无为善之材,其咎在于为外物所牵、利欲所诱而无涵养之功。
宋明儒者大多遵从朱子之注解,然亦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朱子言:“‘平旦之气’自是气”,“平旦之时,即此良心发处。”[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4页。亦即平旦之时未与物接,未被利欲、事绪纷扰,其气清明,良心于此发见。明儒黄宗羲则谓:“此气(平旦之气)即是良心,不是良心发见于此气也。”[2]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孟子师说》,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好恶与人相近”,朱子解作“得人心之所同然”[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2页。,即理义之心,凡人皆有。清儒焦循则谓:“相近即‘性相近’之相近。”[4]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776页。“性相近”,伊川曰:“此只是言气质之性。”[5]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第207页。质言之,“好恶与人相近”,朱子是从义理之性说;焦循则是就气质之性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伊川言:“心本无出入,孟子只是据操舍言之。”[1]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第297页。朱子谓:“出入便是存亡……要之,心是有出入”,“人心自是有出入”[2]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7、1908页。,此四句“只是状人之心是个难把捉底物事”,“此大约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论心之本体也”[3]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4页。。宋儒张栻则曰:“心非有存亡出入,因操舍而言也。”“心本无出入,言心体本如此……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而心体则实无出入也。”[4]张栻:《张栻集》,杨世文点校,中华书局,2015年,第551、1258页。明儒王守仁亦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有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入的。”[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页。在朱子看来,心之本体,虚静灵明,然“心不是死物,须把做活物看”。[6]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4页。心既然会活动,即可能为外物牵引,被私欲蔽锢,而流于不善。“操则存”,即虚明之本体发见于此;“舍则亡”,即心走作逐物,本体之明隐而不显。存亡出入,是兼动静、体用而言,心“非独能安靖纯一,亦能周流变化,学者须是着力照管,岂专为其已放者而言耶?”“专指其安靖纯一者为良心,则于其体用有不周矣。”[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5,《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32页。质言之,朱子坚持“心是有出入”,“不必要于此论心之本体”,理由在于,就经验世界而言,本心之呈现并无必然之保证,良心为物欲戕贼,则放失不存,人之行止去禽兽不远。朱子坚持“此大约泛言人心如此”,是以为孟子引孔子之言,不是为个别资禀纯粹,心常湛然虚明之人言之,是就普天之下的一般人或寻常人而言。要之,朱子认为,先圣之用心在于警示众人操存工夫之紧切,当时时处处用力,使气常清而心常存。“此章不消论其他,紧要处只在‘操则存’上。”“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则存,舍则亡’上,盖为此心操之则存也。”[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1、1903页。
综上所述,就“平旦之气”“好恶与人相近”来说,朱子之诠释与伊川相同,而与黄宗羲、焦循有别。就“夜气不足以存”“出入无时”而言,朱子之疏解不仅和王守仁不同,和伊川、张栻亦有区别。总而言之,不同时代、学派甚至同一时代、学派之儒者,因对心、性、气等概念及其关系之理解不同,对于“牛山之木”章之诠释亦有别。理学、心学、汉学、宋学对于心、性、气等观念及其关系之理解为何及有何区别,非本文研究之重心,本文重点在于借由诸儒学说之歧异,引出工夫进路之不同,进而判定李绿园之学术立场,探究《歧路灯》如何体现李绿园之学问宗旨与工夫进路。以下详述由“牛山之木”章之阐释所彰显的程朱理学工夫论。
依照朱子之解释,“牛山之木”章说“平旦之气”“夜气”,其实“止为良心设尔”,“其所主却在心”,“专是主仁义之心说”[2]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8、1899、1901页。。孟子之用心不是教人存养夜气,而是“教人操存其心”[3]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6页。。亦即所养者不是气而是以气养心,“只是借夜气来滋养个仁义之心”[4]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1页。。有误认工夫为存夜气者,有错用工夫于出入者[5]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5、1905页。。朱子认为,“工夫都在‘旦昼之所为’”。“夜气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昼’理会,这两字是个大关键,这里有工夫”[6]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6、1896—1897页。黄宗羲谓:“朱子却言‘夜气上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昼理会’,未免倒说了。”(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孟子师说》,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之所以说不是在夜气上而是于旦昼间做工夫,一来是紧扣旦昼所为与梏亡交相为用之关系。白日所作所为若合乎理义,则良心存而不放,夜气愈加清明,良心益得其养,久而久之,即旦昼之所为,亦皆良心之发见。白昼所作所为若不仁不义,则平旦未与物接之时清明之气所存之良心又汩没了,日间更加胡作非为,日复一日,夜气不复清明,良心亦存立不得。二来是着重于应事接物上见分晓,以区别于释氏之枯坐默守,遗弃人伦日用。“心不是死物,须把做活物看。不尔,则是释氏入定、坐禅。操存者,只是于应事接物之时,事事中理,便是存。若处事不是当,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这里,蓦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则亡’也。”[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4页。“然所谓涵养功夫,亦非是闭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后谓之涵养也,只要应事接物处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68页。既然“操则存,舍则亡”是“用功紧切处,是个生死路头”[3]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4页。,那么操存之法该当如何?朱子引程子之说:“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4]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第151页。应事接物时固然要做工夫,未应接之先依然要做工夫,保守此心于戒慎恐惧、常惺惺的状态。且唯有常操常存,工夫毫无间断,使仁熟义精,事务纷至沓来之时,才能方寸不乱,应付自如。“人心‘操则存,舍则亡’,须是常存得,‘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有一息间断。于未发之前,须是得这虚明之本体分晓。及至应事接物时,只以此处之,自然有个界限节制,揍着那天然恰好处。”“若是闲时不能操而存之,这个道理自是间断。及临事方要穷理,从那里捉起?惟是平时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将这个去穷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5]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05、1907—1908页。总而言之,朱子以为,“牛山之木”大旨是要人操存涵养天之所与的仁义之良心。操存之方是居敬涵养,格物穷理,或者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三、“天心徐逗滋萌蘖,依旧牛山木又昌”
如前所说,《歧路灯》多次运用“树”这一意象。开篇即言,人生道路不过成立、覆败两端,成立之人,“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开宗明义,以树喻人,正如“牛山之木”以山木譬喻人心。山木尝美,犹如人本有仁义之心。唯其固有生木之性、天理之良,所以既遭斧斤之伐、物欲之害,仍有萌蘖之生、几希之存。换言之,就萌蘖之生、几希之存反推,益可知牛山原有生木之性,人本具仁义之心。亦即生木之性是山木为斧斤戕害之后,得雨露之润犹有萌蘖之生的前提;仁义之心生而本有乃人心被利欲戕贼之后,遇平旦之气犹有发见之时的预设。质言之,良心善性受之于天,是人能改过迁善的形而上学根据。“牛山之木”章的主旨,正是《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改邪归正之所以可能的理论依据。谭绍闻误入歧途,且渐行渐远,终至鬻坟树以抵欠债,致使原本“坟上一大片杨树,蔽日干霄,好不威风”,如今“只见几通墓碑笏立,把一个森森阴阴的大坟院,弄得光鞑剌的”(81回),被妻子讥诮“为甚的坟里树一棵也没了,只落了几通‘李陵碑’?”(82回)嗣后,因族兄谭绍衣顾念族情,欲修理坟院,派管家梅克仁周视形势,归途于饭铺听闻老人谈论:“说起谭宅这坟,原有百十棵好大的杨树,都卖了,看看人家已是败讫了。如今父子两个又都进了学,又像起来光景。”(95回)谭绍闻既立志改过,又得谭绍衣提拔,以抗倭有功,官任黄岩知县,其子谭篑初考中进士钦点翰林,父子二人前往祖茔祭奠之时,“周视杨树,俱已丛茂出墙。俗语云:一杨去,百杨出。这坟中墙垣周布,毫无践踏,新株分外条畅”。(108回)《歧路灯》坟树之消长不仅与家道之兴衰、子孙之成败相始终,且与“牛山之木”山木之消长相映照。
《歧路灯》描述谭绍闻误入歧途至改过迁善的过程,及夏鼎胡作非为至遣发极边的结局,正是李绿园吸纳并融贯程朱理学修养观的体现。谭绍闻因年幼丧父,母亲溺爱,无人管教,又被匪徒引诱,以致结拜兄弟、掷六色、行酒令、养戏子、认干儿、狎尼、宿娼、抹牌、通奸、揭息债、斗鹌鹑、开赌场、打抽丰、请堂客、烧丹灶、铸私钱、鬻坟树,倾家荡产,甚至屡次自杀寻死、上衙门打官司,几乎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纵然被视作“世族中一个出奇的大怪物”(89回),但谭绍闻并非天生即为下流坯子。《歧路灯》反复说他“良心未尽”(1回)、“触动了天良”(14回)、“良心难昧”(21回)、“良心发现”(25回)、“触动良心”(47回)、“良心发动”(59回)、“触动本心”(63回)、“良心乱跳”(86回),且明言:“绍闻本非匪人,只因心无主张,面情太软,渐渐到了下流地位。”(63回)“原来人性皆善,绍闻虽陷溺已久,而本体之明,还是未尝息的。”(86回)又借左邻右舍之闲谈私议:“谭相公明明是个老实人,只为一个年幼,被夏鼎钻头觅缝引诱坏了。又叫张绳祖、王紫泥这些物件,公子的公子,秀才的秀才,攒谋定计,把老乡绅留的一份家业,弄的七零八落。”(87回)“老乡绅下世,相公年幼,没主意,被人引诱坏了,家业零落。”(88回)在在说明,谭绍闻本具天理之良,之所以流于不善,皆因心无主张,被匪人引诱。然其本然之良心并未丧尽,是以遇平旦其气清明之时,父执耳提面命之际,良心仍能发见。不单谭绍闻如此,即便是“街上众人最作践的那个兔儿丝”(19回),因作奸犯科以致革职充军的夏鼎,也说“我虽下流,近来也晓得天理良心四字”(42回),“也有天良发现之时”(70回),也会因为坑骗谭绍闻,“这一点良心,也有些难过处”(81回),因而在谭绍闻面前献好心、设善策。即此观之,愈加可证仁义之心本是受之于天,凡人皆有的。正如朱子所言:“孟子说‘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昼梏亡’,又曰‘夜气所存’。如说‘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为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浑然至善,故发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识得,虽至恶人,亦只患他顽然不知省悟。若心里稍知不稳,便从这里改过,亦岂不可做好人?”[1]朱熹:《朱子语类》卷117,《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8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78页。就算是穷凶极恶之人,只要知错能改,即可存其良心,复其善性,由恶人变作好人。
谭绍闻之所以落入下流,主要是年幼失怙,失调少教,被盛希侨、夏鼎、张绳祖等匪人引诱,吃酒、赌博、嫖娼,险些葬送前程、断送家业。近匪人,入匪场,吃喝嫖赌,即是以物欲之斧斤戕贼固有之仁义,旦昼之所为梏亡本然之良心。换言之,人虽秉具天理之良,然心易为物欲汩乱,因而良心放舍,流于不善。李绿园说:“不知人心如水,每日读好书,近正人,这便是澄清时候,物来自照;若每日入邪场,近匪类,这便是混浊时候,本心已糊,听言必惑。”(61回)朱子以井水为喻:“譬如一井水,终日搅动,便浑了”,“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浊了”。[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5、1896页。皆谓人心本自虚静,然为事物纷扰,情欲牵缠,则良心陷溺,放而不存。虽有良心发见之时,若无操存之功,则已放之余仅存之良心亦终至亡失。如夏鼎为张绳祖之鹰犬假李逵所窘,逼讨二两银子欠账,夏鼎向立志读书的谭绍闻求告,谭绍闻施以援手,以一方端砚相赠,解其燃眉之急,夏鼎当了三两纹银去张家还钱,张绳祖以十两银子为诱饵,蛊惑夏鼎引诱谭绍闻再入赌场。夏鼎口口声声说:“我虽下流,近来也晓得天理良心四字,人家济我的急,我今日再勾引人家,心里怎过得去。况且人家好好在书房念书,现今程公取他案首,我若把他勾引下来,也算不得一个人。”然受不了张绳祖奚落:“你回家去吃穿你那天理,盘费你那良心去。嘴边羊肉不吃,你各人自去受恓惶,到明日朝廷还与你门上挂‘好人匾’哩。”(42回)尤其是经不起十两银子诱惑,即刻改变心意,与张绳祖狼狈为奸,串通一气。由此可知,一时之良心发见无济于事,须继之以操存之功。否则,此几希之善端如同初生之萌蘖,迭遭物欲之斧斤的戕害,终至荡然无存。诚如朱子所说:“此心自恁地虚静。少间才与物接,依旧又汩没了。只管汩没多,虽夜间休息,是气亦不复存。所以有终身昏沉,展转流荡,危而不复者。”[2]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6页。夏鼎便是无操存之功,汩没靡所底止,至于“终身昏沉,展转流荡,危而不复”,以充军流放为结果者。
所谓操存之功,是要常操常存,无时无处不做工夫。否则,一为物欲牵引,即前功尽弃。如谭绍闻输钱之后,撞墙寻死,平旦之时,良心发现,对仆人发誓改过自新。然在书房“独坐三五日,渐渐觉的闷了”(26回),夏鼎以妓女红玉相诱,勾引谭绍闻再入张绳祖家嫖赌。谭绍闻于赌场买金镯,卷入盗赃官司,得父执求情取保,对天发誓改邪归正。世叔兼业师智周万为宵小污蔑,以思乡为由归家之后,谭绍闻独坐书斋,“七八日霪霖霏霏,也就会生起闷来”(57回)。乌龟三顾书房,以妓女珍珠串为饵,引诱谭绍闻又入夏鼎家赌博。恰如谭绍闻自白:“质非牛马,岂不知愧!但没个先生课程,此心总是没约束。时常也到轩上看一两天书,未免觉得闷闷,或是自动妄念,或是有人牵扯,便不知不觉,又溜下路去。”(55回)这便是不能时时处处用力,使良心常存之过。
谭绍闻虽几次矢志改过,转瞬又近匪徒,入赌场。谭绍闻将自身之堕落归咎于心无主张及匪人引诱,心虽易为外物干扰,归根结底,毕竟是自己不能操存涵养之过。朱子即言:“大者既立,则外物不能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个只在我,非他人所能与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勿与不勿,在我而已”。[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5、1906页。谭绍闻立心改志,遵循其父临终遗言:“用心读书,亲近正人。”(12回)节制私欲,资以问学,与狐朋狗友保持距离,与正人君子相亲相近。尤其是第三十八回虽提及张正心,谭绍闻却与之并无来往,至第六十七回(其时谭绍闻已断赌)始与其密切往来,且日益亲厚。第八十九回,谭绍闻领儿子在书房读书,夏鼎前来拍门,谭绍闻借口钥匙不在手边,将其拒之门外。稍后张正心前来叫门,谭绍闻随即把钥匙扔至墙外,让其开门入室。李绿园论说:“看官,这一回来了一个夏鼎,又来了一个张正心,谭绍闻一拒一迎,只在一把钥匙藏在屋里、丢出墙外而已。把柄在己,岂在人哉?”谭绍闻立志自新之后,兼之用心读书,方能自正其心,不复昔日心无主张故态。且谭绍闻“正心”之后始与张正心交厚,李绿园对于《歧路灯》之人物命名及情节安排[2]《歧路灯》多次提及《大学》之“诚意正心”,如第三回、第三十八回、第三十九回、第四十回。张正心之命名显然即来源于此。,显然富含深意。
四、“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
《歧路灯》为何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谭绍闻失足、改志又堕落、自新之经历?如能理解“牛山之木”章“梏之反覆”的含义,即可领会李绿园之良苦用心——谭绍闻误入歧途且渐行渐远的情节安排,正是“梏之反覆”理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质言之,《歧路灯》改邪归正的主题是李绿园对于“牛山之木”章旨的忠实传达,谭绍闻之所以能够改过迁善,是李绿园从心性论到工夫论层面对于程朱理学修养观念的具体呈现。谭绍闻堕落又改悔,立志改过复又落入下流的翻覆经历,是李绿园将抽象的“梏之反覆”理论融贯于具体的小说结构设置。
何谓“梏之反覆”?朱子说,旦昼“无工夫,不长进,夜间便减了一分气。第二日无工夫,夜间又减了二分气。第三日如此,又减了三分气。如此梏亡转深,夜气转亏损了。夜气既亏,愈无根脚,日间愈见作坏。这处便是‘梏之反覆’,‘其违禽兽不远矣’”。[1]朱熹:《朱子语类》卷59,《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7页。又说:“‘梏之反覆’,非颠倒之谓,盖有互换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气为旦昼所为所梏而亡之矣,以其梏亡,是以旦昼之所为谬妄愈甚,而所以梏亡其清明之气者愈多。此所以夜气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也。”[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5,《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32页。意思是人之良心虽已放失,然夜间清静,不为利欲、事绪纷扰,良心必有所生长,故平旦未与物接之时,其气清明之际,良心必有所发见,恻隐羞恶,得人心之所同然。但良心放失之后,所息甚微,所存不多,日间又不做精进工夫,则此几希之良心又被梏亡。旦昼之所为梏亡越甚,夜气所存者越少;夜气所存者愈少,旦昼之所为愈谬。心与气互相牵动,日复一日,久而久之,虽至夜间,其气亦不复澄静,人之天良遂尽丧而不复存。这便是“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
《歧路灯》写谭绍闻被夏鼎与张绳祖算计,输了一百八十串钱,撞墙寻死(25回)。平旦之时,良心发现,对家仆王中矢志改过。夏鼎以娼妓红玉相诱,勾引谭绍闻复去张绳祖家赌博,输了二百八十串钱(26回)。游棍茅拔茹为骗赖银钱,扭结谭绍闻上衙门打官司(30回)。王中劝诫家主,谭绍闻恼羞成怒,将其赶出家门(32回)。此为谭绍闻一言改志,一上公堂,一逐王中。孔慧娘婉转劝告谭绍闻收留王中,谭绍闻再次对王中誓言改志(36回)。夏鼎与张绳祖设套,谭绍闻又往张家吃酒赌博,输了四百九十三两银子(43回)。张绳祖结交官府,诬告谭绍闻欠债不还,谭绍闻再上衙门打官司(46回)。王中怒骂夏鼎,惹恼谭绍闻,谭绍闻又将王中逐出家门(53回)。这是谭绍闻再言改志,再上公堂,再逐王中。谭绍闻于赌场买金镯,卷入盗赃案件,被押上衙门听审(54回)。王中求程嵩淑等进衙署递呈词,恳恩免解,谭绍闻得以当堂取保。因听从父执教诲,谭绍闻对天发誓,改邪归正。(55回)此乃谭绍闻三上公堂,三言改志。谭绍闻世叔兼业师智周万为奸人诬陷而离去,夏鼎等人又设计让乌龟三顾书房,以妓女珍珠串为饵,引诱谭绍闻再到夏家赌博(57回)。谭绍闻输了八百两银子,引颈投缳(59回)。这已是谭绍闻二度自杀。因听取师伯教训,谭绍闻立誓改过自新(63回)。至此,谭绍闻已经四言改志。
谭绍闻误入歧途又立誓改志,立志自新又落入下流,翻来覆去,出尔反尔。起初在张绳祖、巴庚、夏鼎处嫖赌,后来竟在自己家盘赌窝娼。且越赌越凶,越输越多。因赌博两次三番寻死觅活、闹出人命案件、上衙门打官司,嗣后甚至险些做出违法犯禁之事——铸私钱。谭绍闻失足堕落且越陷越深,差点无法回头,落到张绳祖、王紫泥、夏鼎一般结局。谭绍闻误入歧途之经历即是“梏之反覆”之抽象理论落入经验世界的具体表现。“梏之反覆”不仅拓宽了《歧路灯》情节展现之广度——三教九流之人之为非作歹具体有哪些形式,或者说人之成德进程会面临何种诱惑历经多少崎岖;且提升了《歧路灯》主题意蕴之深度——不做操存涵养之工夫,终日胡作非为之人究竟会沦落至何种地步。
五、结语
李绿园出身中州理学名区并服膺程朱理学思想,及《歧路灯》化用《孟子》“牛山之木”章语词之情形,已有学者撰文论及。然李绿园究竟受到程朱理学什么影响,《歧路灯》到底怎么体现程朱理学之影响的,学界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不同时代、学派之儒者对于心、性、气等概念及其关系之理解不尽相同,对于“牛山之木”章之诠释亦有差别。朱子以为,如同牛山之木原本茂盛秀美,人先天本有仁义之心。牛山之木遭斧斤之砍伐而丧失其美材,人为利欲之斧斤戕害而放失其良心。山木虽遭斧斤之伐,得雨露之润,仍有萌蘖之生。良心虽为利欲所害,遇平旦气清之时,犹必有所发见。萌蘖虽生,又遭牛羊之牧,是以若彼濯濯。良心虽有所发见,又因旦昼之所为而梏亡,辗转更迭,终至良心丧尽,违禽兽不远。人以今日之牛山濯濯如此,而以为昔日之牛山原无美材。人以放其良心者异于禽兽者几希,而以为其人本无为善之材。然以萌蘖之生视之,可知牛山本有生木之性。以平旦之气验之,可证人固有仁义之心。人心本自虚静,然易为外物牵引,私欲障蔽,而流于不善。是以,唯有持续不断做操存涵养之工夫,才能保持良心常存而不放舍。朱子以其二元、三分之理论架构为心性论依据,证明良心善性受之于天、与生俱来,并落实到居敬涵养、格物穷理之日用工夫。
《歧路灯》写谭绍闻因年幼失怙、为匪人引诱而误入歧途、破产败家,最终迷途知返、改邪归正而功成名就、家声重振。谭绍闻改过迁善何以可能,及其为何三番五次誓言改志又落入下流?朱子关于“牛山之木”章之诠释显然是李绿园撰述之根据。仁义之心为人所固有,即便是违禽兽不远者,亦先天本有仁义之心。正因凡人皆有本然之良心,如能节制私欲,资以问学,做操存涵养之工夫,则都可以复其本然之良心善性。这便是谭绍闻之所以能够改过迁善的形上学根据。心活泼灵动,易于走作逐物,而流于不善。若无操存涵养之功,则良心放失,惰慢邪僻之气趁机而入,邪气愈盛,良心愈亡,所作所为更加不仁不义。这便是“梏之反覆”,良心不足复存,谭绍闻誓言改志又落入下流的理论依据。朱子以为,孟子以牛山之木譬喻人之良心,由仁义之心为天之所与收归到本然者不足恃,须无时无处不用其力,使良心常存善性尽复,提点操存涵养工夫之紧要。经由“牛山之木”章之诠释而显示的理学修养观念,正是《歧路灯》展示的改志换骨或浪子回头主题之理论背书。谭绍闻翻来覆去之改悔又堕落的经历,正是李绿园从情节结构层面对于“梏之反覆”理论要义的具体呈现。总而言之,李绿园将程朱理学之修养观内化于《歧路灯》之文本创作,《歧路灯》从主题到结构,均体现了程朱理学修养观之影响。因李绿园自觉采纳程朱理学之修养观,使《歧路灯》招致“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及思想落后、腐朽、反动,卫道过甚、说教过多之类的罪责[1]冯友兰:《〈歧路灯〉序》,收入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04页。关于《歧路灯》思想方面的批判,散见于中州书画社编:《〈歧路灯〉论丛》(第一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编:《〈歧路灯〉论丛》(第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然就小说主题与结构而言,文本表述与理论表达是浃洽而融贯的。本文旨在探析《歧路灯》所载之道为何,李绿园又是如何以《歧路灯》载道的,至于《歧路灯》载道是否应当及载道是否高明,则俟知道者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