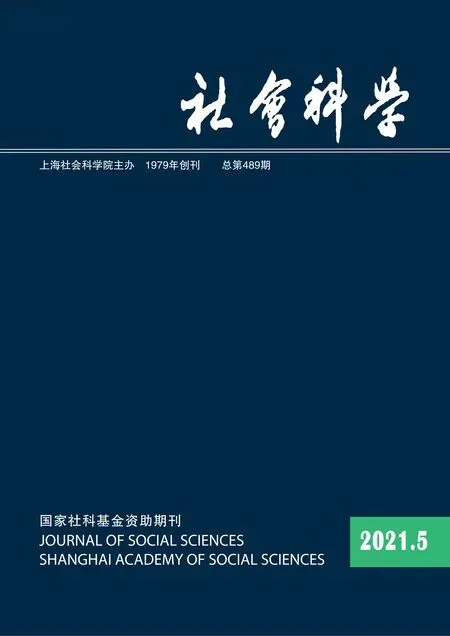万历三十八年“郑继芳私书”与辛亥党争*
2021-11-24黄阿明
黄阿明
明神宗中年以后长期深居宫禁,不视朝政,朝臣群龙无首,内阁又乏驾驭政局能力,廷臣以各种关系拉帮结派,出现“东林党”“浙党”等政治势力,廷臣一举一动皆有背景,一言一行皆可激起轩然大波。万历朝党争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围绕国本之争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一是君子小人之争,后来二者与内外大计考察纠缠在一起,以致关系愈加错综复杂。(1)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3页。于是,六年一次的京察制度,成为党派之间互相争斗、打击异己势力的重要工具。因此,京察成为明末朝廷人事安置、党派势力消长和朝局形势变动的关键,成为观察明末政局的窗口。为了打击政敌、排挤异己,党派势力往往借助甚至不惜伪造匿名书信、传单、揭帖,使之发酵成为公众事件,煽动舆论,罗织罪状,利用京察处置异己,以达排挤、驱逐之目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续妖书事件与乙巳京察、万历三十八年(1610)郑继芳私书事件与辛亥京察,即属此类典型事件。关于续妖书事件与乙巳京察,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2)赵毅:《明万历朝妖书案抉微》,载《明清史抉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8页;杨向艳:《议狱缓死:万历朝续妖书案之皦生光狱始末》,《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杨向艳:《开罗织之端:万历朝续妖书案之周嘉庆狱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杨向艳:《续妖书案之达观狱与万历政局》,《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杨向艳:《续妖书案之沈令誉、毛尚文狱与万历党争》,《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杨向艳:《续妖书案之胡化狱与万历党争》,《江淮论坛》2017年第8期。然而,万历三十八年郑继芳私书事件之于辛亥京察却至今无人措意。本文勾稽史料,就郑继芳私书事件与辛亥党争进行初步考察,藉以深刻理解匿名文书与明代京察、党争之间的关联。
一、辛亥京察前的党争形势
万历前中期的朋党之争,集中表现为内阁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3)徐洪星:《朋党与中国政治》,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2页。万历后期党争主体有所转移,表现为浙党与东林党、科道系统内部以及部司之臣间的政治势力斗争。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京察,东林党全力以赴,目的是为了驱逐浙党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及其党羽。结果是浙党领袖沈一贯虽然最终去职,但其党羽依旧占据朝廷要津,而东林骨干御史刘元珍、朱吾弼、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在京察中被察处,与东林关系密切的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等同样被劾致仕,可谓两败俱伤。(4)杨向艳:《沈一贯执政与万历党争》,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6-352、358-368页。然而,浙党在朝诸人一直伺机报复。
在首辅沈一贯、次辅沈鲤相继去职后,浙党成员朱赓成为内阁首辅,晋江人李廷机、福清人叶向高万历三十五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廷推入阁。李廷机系浙党领袖沈一贯门生,与沈一贯关系甚密。以这一层关系,李廷机被推后,在朝东林党科道官员极力阻其被推,具疏论劾,(5)《明史》卷217《李廷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740-5741页。因此李廷机不得不上疏求去,自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以后便称病家居,不复入阁办事。(6)《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南炳文、吴彦玲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7页。万历三十六年,首辅朱赓卒于任内,内阁缺员不补,遂成叶向高一人独相局面。陕西耀州人王图,以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充日讲官,“是时,郭正域、刘曰宁及图并有相望”。图兄国又为保定巡抚,“廷臣附东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毂图兄弟”,礼部侍郎郭正域以妖书案被逐,刘曰宁卒,“时论益归图”,“旦夕且入阁,忌者益众”。时朝中孙丕扬掌吏部、孙玮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皆陕人,诸不悦图者,目为秦党。(7)《明史》卷216《王图传》,第5706页。而秦党(亦称西北党)在政见方面,又与东林相近,与浙党处于对峙局面,孙丕扬、王图等与顾宪成等时有往还,扼制浙党在朝势力。在浙党眼中,秦党与东林实为一党,对之恨甚。(8)(明)吴应箕:《东林本末·门户始末》,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9、19页。
通州人李三才,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讲求经世务。万历二十七年(1599)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后加户部尚书。在任期间,屡陈矿税之害,请撤天下税使,淮人德之。李三才又与东林领袖顾宪成交厚,深得宪成信任。万历三十四年,明神宗以皇孙生,诏开矿税、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既而不尽行,李三才颇疑首辅沈一贯阻之,上疏论奏,阴诋一贯甚力,与浙党形成对峙立场。时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三才又当合适人选。(9)《明史》卷232《李三才传》,第6063-6065页。东林党人属意李三才,浙党极力阻止,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外计时合谋驱逐李三才。工部郎中邵辅忠疏劾李三才“结党遍天下,前图枚卜,后图冢宰”,“真天下大可忧”。(10)(明)蒋平阶:《东林始末》,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御史徐兆魁继之,“极其丑诋”,李三才盛气陈辩,不自引退,于是“攻者四起”,李三才只得三疏乞休。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绍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给事中金士衡、段然相继为李三才辩雪,东林领袖顾宪成致书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诸老,谓“三才任事任劳,功不可泯,当行勘以服诸臣之心”,徐兆魁转而疏参顾宪成,“一时攻淮抚者并攻锡山”。(11)(明)叶向高:《蘧编》卷3,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载《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0册,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605页。李三才被劾,“参者什一,保者什九”,然而明神宗一概不报,(12)《明神宗实录》卷470,万历三十八年四月丁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3年版,第8881页。“物议纠缠,大狱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13)《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七日,第2707页。李三才的去与留,遂成为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
显然,在此形势下,众望所归的吏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便最有可能成为被会推入阁之人选。
时词林最有名者宣城汤宾尹、昆山顾天埈、湘潭李腾芳,互为交游,最可挂议者亦此三人。(14)(明)叶向高:《蘧编》卷4,万历三十九年辛亥,第611页。汤宾尹与顾天埈、李腾芳皆欲图大拜,各自广召朋徒,干预时政,时人目为宣党、昆党。(15)《明史》卷306《王绍徽传》,第7861页;(明)史记事:《大乱将作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刊于《续修四库全书》第4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196页。万历朝言路习气几变,张居正当政,打击言路,“科道皆望风而靡”;申时行以后,言路势张,抗章参劾阁臣,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万历末,言路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16)(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36-837页。是时,言路已渐分齐、楚、浙三党之势,与宣党汤宾尹、昆党顾天埈,“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大臣多畏避之。(17)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纲目》卷7,万历三十九年三月,第462-463页;《明史》卷224《孙丕扬传》,第5903页。
万历三十八年(1610)系外计之年,又系会试之期。会试,由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翁正春知贡举,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萧云举、王图为考官。(18)《明神宗实录》卷467,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乙卯,第8802页。分校官右庶子汤宾尹徇私门人韩敬,越房取卷,与会试官礼部侍郎吴道南盛气相诟。比出闱,吴道南欲劾汤宾尹,以王图劝阻而止。(19)《明史》卷216《王图传》,第5706页。万历三十八年九月,汤宾尹已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20)《明神宗实录》卷475,万历三十八年九月癸卯,第8961页。但其先历翰林院京察,仍由掌院王图注考,宾尹惧庚戌会试徇私事被黜。(21)(明)叶向高:《蘧编》卷4,万历三十九年辛亥,第611页。汤宾尹欲通过其门生、王图同乡给事中王绍徽为之请,绍徽“极誉宾尹于图,而言道南党欲倾宾尹及图,宜善为计”,王图峻拒之,王绍徽不悦而去。汤宾尹为先发制人与王绍徽商计,令御史金明时先发劾图。(22)《明史》卷216《王图传》,第5706页。御史德清人金明时,“居官不职,虑见斥”。(23)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纲目》卷7,万历三十九年三月,第463页。实际上,这意味着昆党与浙党在政治上的结盟。
由此可见,迨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前,明朝在朝廷臣已经大体上分为东林与非东林两大党派势力。东林党由东林主体和西北秦党构成,非东林党主要由词林之宣党、昆党与言路之浙、齐、楚三党构成。党争的核心,实质上仍是争夺阁权。礼科给事中周永春说:“近时之谋为宰相者,一时有一时之局,一事有一事之案。”(24)(明)周永春:《察疏候检日久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305页。对于明廷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万历三十七年(1609)云南道御史史记事奏上一疏,详陈浙党、昆党合谋,预料朝局即将大乱。(25)(明)史记事:《天下将大乱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194-197页。在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前,浙党、宣党便意欲借助辛亥京察有所作为,阻止王图入阁,驱逐阁臣叶向高和在朝西北诸臣。万历三十八年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私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被以浙党为核心的非东林党人充分利用,成为辛亥京察时期党争的主要话题之一。
二、浙江巡按郑继芳私书与辛亥察前党争
郑继芳私书一节,由浙党成员、御史金明时在参劾王图的奏疏中首先揭出,遂成为辛亥京察前东林与非东林两党争辩的焦点。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廷臣奏请明神宗钦定察期之际,十二月初七日,陕西道监察御史金明时出于逃脱察处的目的,充当宣党先锋,先发制人,奏上一疏,参论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金明时参劾王图纵子贪淫、害兄结党和包庇其子王淑抃告病改教逃脱察处三大罪状,奏疏结尾部分说:
又闻奸党朋谋,捏造按臣之家报,一箭三雕,人人股栗。总由太宰八月间发访贪廉四款,令[徐]缙芳五六人辈顿夺其魄,而久生其奸,以故做出弥天之事,装成遍地之殃。廉访未确,未敢指名参究。(26)(明)金明时:《察典关系匪轻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13页。
金明时认为,八月间吏部尚书孙丕扬发放贪廉四款访单,令徐缙芳等五六人夺其魂魄,于是朋谋捏造按臣家报,一箭三雕。但金明时又说“廉访未确,未敢指名参究”,亦未说明家报内容。对于金明时的劾奏,吏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原工部营缮司主事拟授江西道御史徐缙芳,很快于初九日疏辩回击。王图疏称御史金明时劾论自己,“其祸有根,而其发有自,其来最远,而其机最深”,自万历三十七年二月自己被推掌翰林院事以来即“已知之酝酿至今日”,就金明时所论三大罪状,一一进行辩驳。(27)(明)王图:《病亟思归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15-216页。王图似乎并未意识到金明时所谓奸党朋谋捏造按臣家报一事其实暗指是他指使主持,因此并未对“私书”作辩。徐缙芳辩疏指出,自己被金明时无端波及,明时参劾王图的真实意图在于要挟察事,“为致死求生之计”,但亦未对明时奏疏所云“捏造按臣家报”一节予以回应。(28)(明)徐缙芳:《贪臣巧避察典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14-215页。
针对考选御史徐缙芳辩解反劾之疏,十二日,御史金明时上疏辩解自己并无逃察之意。疏中有云:
王图身为表率,甘受若辈驱使,假捏按臣郑继芳与科臣王绍徽、台臣刘国缙书,内云“福清当逐,富平、耀州继之,秦脉渐断,吾辈可以得志”等语。王图手录其书,面缴太宰,阴中三臣,所恃太宰,至虚至明,无固无我,断不因若辈惑志。顾其设心甚险,贻祸甚奢。按臣身羁越土,敷奏尚稽科臣台臣,灾已剥肤何切,无申辨之章,令长安市上怀疑不决。臣不知其解也,装成“莫须有”之风波,入人不可解之罪案。其他东挑西激,出主入奴,个中机括,秃笔难尽。(29)(明)金明时:《险臣秽恶昭彰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18页。
在这份奏疏中,金明时关于“捏造按臣家报”的基本信息的叙述就比较翔实了: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与徐缙芳等合谋,假捏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之手伪造家报一封,寄京中同官科臣王绍徽、御史刘国缙,书信内容有“福清当逐,富平、耀州继之,秦脉渐斩,吾辈可以得志”等语。按所谓福清指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富平指吏部尚书孙丕扬、耀州指吏部右侍郎王图与其兄保定巡抚王国,秦脉指在朝陕人。王图手录一份,亲自面缴吏部尚书孙丕扬,阴中郑继芳、王绍徽、刘国缙三人,以“莫须有”之名入其至不可解之罪案。在这里,金明时谓王图手录“郑继芳私书”,面缴孙丕扬。
由于受到金明时责问,贵州道御史刘国缙于十四日上章申辩,对私书问题作出回应,声援御史金明时。刘国缙疏称自己与台臣郑继芳、科臣王绍徽虽系同年同咨,“臭味相投”,然未尝一次杯酒相邀,“以结私款”,惟相会接谈间“以肝胆相倾,许以忠义相激发”,从无傍人门户行径,比郑继芳奉命按浙,自己与王绍徽共事春明,不无一二书信相通,“然皆可以悬之国门,与众共视”,自己立朝素意人品忠邪,以为终身从违之准。继之,又说:
忽二日,长安道上[遍传]郑御史寄书与臣及科臣王绍徽,大约谓“福清、富平、耀州当次第驱逐,须断秦脉,然后吾辈可以得志”等语。臣闻之,不胜惊骇。因拜客遍问之,则遍能言之,皆云“五鬼”作祟伎俩以成,而尚不知耶?臣问“五鬼”为谁?此书何在?则皆云:“徐缙芳等,夜聚晓散,合谋于王图之家有日矣,长安呼为五鬼,造成假书,图手录一通,送之冢宰,灾剥肤矣,而尚不知耶!”臣闻之且信且疑,以为言虽有据,终属风闻。臣等可诬,公论难掩,因置之。有爱臣者曰:“而不言则其书真矣。”臣笑应之曰:“谚不云乎:‘事果有,说将大;事果无,说将罢。'且缙芳等诚何足惜?”……无何,御史金明时参王图之疏出,有“假捏按臣家报一箭三鵰”之语,臣骇曰流言遂可闻于君父耶?然以发难于浙,有犯时忌,臣心殊不畅。越二日,见王图、徐缙芳辨疏皆不照此款。且冢宰向王绍徽云“书诚有之,然尚不至此”,绍徽因索观之,不与,且曰:“见之则其说长矣。”盖恐臣等之有言也。然臣实不欲有言,以伤雅道。无奈徐缙芳之辨疏放肆无礼,以致金明时复有言,且咎臣等之不言。如臣终不言,而长安市上怀疑不决,诚有如明时之所云矣。夫郑继芳寄此书与臣等,此何等机密事,臣等当何等谨秘收藏,而缙芳等何自而得之,岂真有“五鬼”神通入人室,攫人厨柜之物,而令人不见耶?(30)(明)刘国缙:《人言波及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19-220页。
由此可知,到刘国缙上疏时,“私书”已发挥效用,遍传京中。刘国缙奏疏进一步提供了伪造私书的信息,即郑继芳私书是吏部右侍郎王图与“五鬼”日夜聚于王图家合谋捏造而成,王图手录一份送于吏部尚书孙丕扬,科臣王绍徽向孙丕扬求证,证实确实存在私书,索观被拒。不过,刘国缙认为金明时不当将私书流言一事奏闻于皇帝,徒增滋扰。值得注意的是,刘国缙在此疏中首次冠名“五鬼”之称呼。“五鬼”,是万历后期非东林诸党对考选御史徐缙芳、李炳恭、徐良彦、李邦华、周起元东林五人的诬称。(31)(明)郑继芳:《直发邪谋所由成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98页。按(明)文秉《定陵注略》卷9《辛亥大计》载“五鬼”为徐缙芳、周启元、马孟祯、陈一元和刘策,与郑继芳所说“五鬼”不尽一致(第13页)。以郑继芳系私书事件的当事人,其说更可信,故本文采郑氏之说。刘国缙称郑继芳、王绍徽和自己之所以取罪于王图,主要是因为曾经反王图未遂而招致报复,所以“五鬼”合谋捏造假书是为利用孙丕扬借助京察报复自己等三人,是王图“以愚冢宰,则图负冢宰矣”,“缙芳等如此以愚图,则缙芳等负图矣”。刘国缙质问“书出谁手”,要求明神宗召吏部尚书孙丕扬面问此书来历,下九卿科道会勘真伪。(32)(明)刘国缙:《人言波及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20页。
针对刘国缙无端攻击自己,考选御史徐缙芳不得不呈上揭帖一份,乞发私书来历。徐缙芳揭称,金明时、刘国缙之所以切齿于己,不过是因自己曾出书救顾宪成,因此“突生捏造按臣家报一节,虚悬笼罩,令人茫然不知所从来”。他说:“私书一节,既云明时投之太宰,授者有人,则书所从来?岂能逃于太宰之明鉴乎?职不知按臣何以有私书而得达之太宰也,职不知私书何以达太宰,而得闻之明时也。明时何不质私书之所从来于太宰,而故悬猜疑之词?太宰何不发私书之所从,授以明示,而致开罗织之网?职每痛恨四明之余党与昆山之私人,日以摧折忠良为谋,密造蜚语,叠出奇事……今奈何又作一鬼魅一着,为一网打尽之阱也。”又说:“抑闻长安啧啧,有谓明时称书为假,而耀州一着已甘心于秦。若以疏为书,后应也。此明时之未及检点,未可知。又有谓明时辈密谋为此书,挠乱察典,踪迹败露,计无复之,先自发觉,反真为伪,以为逆守,似此则又鬼魅之杰,而天理之所必诛者也。”(33)(明)徐缙芳:《揭贪臣设谋布毒》,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21页。徐缙芳提供了一个不同于金明时、刘国缙的关于私书的说法,不是吏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手录私书一份面缴吏部尚书孙丕扬,而是由御史金明时投于孙丕扬。徐缙芳追问何人授书于金明时,私书又是从何而来?徐缙芳声称自己此前并不知有郑继芳私书一事,自己还是通过金明时奏疏才得知此事的,他也希望吏部尚书孙丕扬公开此书,告知私书来历。徐缙芳认为私书是沈一贯余党与昆党合谋所为鬼魅之着,“为一网打尽之阱也”。徐缙芳又谓京中或谓金明时等密谋私书,以挠察典,以“踪迹败露,计无复之”,故而先发觉之,“反真为伪”。可见徐缙芳将“私书”由来指向了金明时、刘国缙一方。
与此同时,王图又提供了“私书”的一些细节。他说在京察咨访时:
偶于十一月间,传闻有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贻京中同官一书,内有“欲去福清先去太宰,欲除太宰先除仓场及耀州兄弟”,又有“斩断秦脉”、“以秦攻秦”等语。臣一闻之,患在剥肤,颇切惊惧,细加访问,未睹实迹。臣已置之不信矣。是何人谋欲逐臣,乃捏言是臣手抄,转送太宰,诳诱耸动,丛祸于臣?既云系臣手抄,出自何人眼见?又云转送太宰,其字迹必在,发付公庭,一辨可知。奈何以捕风捉影之词,强入人于天罗地网之内乎?大计在迩,臣衙门之事臣为政,闻有大奸大恶思脱计典,故设此机阱,计欲逐臣。(34)(明)王图:《直臣(陈)私书闻见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22页。
据王图此疏可知,所谓郑继芳私书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间开始在京中传播,王图曾细加访问,但未睹实迹,所以王图始终未探查出何人谋欲驱逐自己,何人捏言他手录抄送孙丕扬,因此也希望孙丕扬能将私书“发付公庭”,辨认笔迹。王图指出,围绕捏造私书而造成的捕风捉影之词,是“强入人于天罗地网之内”。王图又说听闻私书一事是有大奸大恶之人思脱计典,故设此机阱,计欲逐己。实际上是暗指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
又,湖广巡按史记事奏说:“去岁(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辞陛出都,至七月终抵臣家,九月间有客自北来者,径为臣问京中消息,客欷歔言人情愈险愈奇,近有二说:一说欲铲断秦脉先参掌院王图,以杜大拜,并参臣以杜敢言;又一说群小畏内计不免,欲为先发制人之术,要参一二正人以自救。臣叹曰:断脉之谋其蓄已久,而先发之说则新闻也。”(35)(明)史记事:《邪党蓄谋已久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31页。可知斩断秦脉驱逐在朝秦人计划似乎早在万历三十八年七八月间已在密谋进行之中,最后发而为“私书”事件。
前因御史金明时奏劾王图害兄结党,因此王图其兄保定巡抚王国上疏辩解。二十五日,金明时上疏驳斥王国,再次攻击王图引进徐缙芳辈“弄出翻天覆地之狡谋,造成出神入鬼之邪算”,并说:“若假书一事,图果[与]五鬼同谋,如御史刘国缙所云,恐将来秉钧当轴之大臣,不应有此举动,国岂能为图讳?”(36)(明)金明时:《抚臣饰辩可原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25页。显然,金明时认定私书是王图与“五鬼”合谋捏造。值得注意的是,金明时意识到“私书”称作“假书”更合适,所以在奏疏中不再称“私书”,而是径称“假书”。
但是,与“私书”最为密切相关的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却一直未出来辩解。这主要是因为郑继芳身在浙省,对京中发生的争辩事件的了解需要一段时间。此外,双方辩疏提到的“五鬼合谋捏造私书”仅指明考选御史徐缙芳一人,始终未指明其余诸人,因此五人中仅徐缙芳一人往还争辩,人们并不都清楚“五鬼”究竟所指何人。
直到万历三十九年正月,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才递上辩疏一封。郑继芳奏疏,开篇就将“私书”产生的根源追溯到万历三十七年论劾工科给事中王元翰(37)《明神宗实录》卷455,万历三十七年二月丙寅,第8585页。而出现的浙党与西北党、东林党党争,谓捏造私书实是东林党、西北党中二三提控线索之人阴谋深中自己。他说:
而今且京师喧传,谓有捏造臣之家报,暗投铨臣,谓臣参辅臣、太宰及仓储侍郎诸大臣,以绝西北之脉。夫臣生长京师,夙寡交游,甘退守恬。受命以来,矢一心以报主,见有奸贪煽乱,愤为一击,直以死生争之,不知有所谓东西南北之党,乃诸奸每欲假此庇元翰以言臣。臣之伶仃,家有七岁稚子耳,臣有家报商议,臣将谁与议乎?
家报若果有之,自是密秘,何得入讐人之手?是前之屡欲欺皇上者,其计既不得行,今之巧于耸当路者,其奸固易售乎?堂堂圣明之朝,济济冠裳之众,而乃有此造言生事欺君罔上之流,即向来妖书之窃发,亦此无忌惮之辈,而甚焉者。若不亟为严究,以杜其渐,将来魑魅魍魉且不知所底止。
然前之喧传者,原谓今考选候命江西道御史徐缙芳与考选候命四川道御史李炳恭,亵衣小帽,连三四夜,入翰林院掌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图之幕,共为谋陷。三臣之长班皂隶守门人役,无不见且骇之,以致长安烦言啧啧。及假书一出,的系王图之笔迹,所以閧然相传,载之小报。臣正具疏欲辨,尚不敢直指其人。今见御史金明时之疏,乃知其所传为不虚也。(38)(明)郑继芳:《邪谋愈出愈奇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28-229页。
据此可知,郑继芳其实很早便知私书流传情形,至于其如何获知此事,且不必论。郑继芳为余姚胡存忠之婿,又是陈治则最厚门生,(39)(明)胡忻:《欲焚草》卷4《辩郑御史疏》,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3b页。是铁杆浙党成员。但他却否认自己结党,声称自己生长京师,夙寡交游,甘守恬退,受命以来,矢心报国,不知有所谓东西南北之党。他又称若果有家报,自是极其秘密,又如何会落入仇人之手?这一说法与御史刘国缙一致,因此郑继芳认为这是其政敌东林党人造言生事,以售其奸,甚至径指万历三十一年妖书也是东林党人所为。他说传闻“假书”是王图与徐缙芳、李炳恭等幕客密谋而成,是王元翰、王图、胡忻、史记事、徐缙芳等辈“惟利禄名位之共图”,“突出一奇以为报复”,恳祈明神宗敕下部院将流传之“假书”取王图与自己笔迹比勘辨明,置之于法。引人注目的是,在郑继芳奏疏中,“五鬼”之名,又出现考选御史李炳恭一人。
李炳恭原任湖州府归安县知县,拟授四川道试御史,因被郑继芳无端诬陷,正月二十日被迫上疏辩解。李炳恭首先疏陈自己与郑继芳毫无嫌衅,闻有欲甘心于自己者以私书相攻,借以相诬,念事属乌有,不辩终明,但郑继芳为急于自白,误听人言诬及自己,不得不辩。李炳恭指天日鬼神起誓:“臣果与谋,敢当寸斩。”他说构诬他人“贿赂东林,尤为近来排击善类套语,按臣亦为是言耶”?又说:“按臣有私书之疑,而后有参臣之疏,长安有邮筒之报,而后生按臣之疑矣。夫按臣精神梦寐,皆为王元翰一事牵怀萦虑,臣于按臣有德,于元翰绝无交,至于王图并未识一面。臣硁硁之守,且不轻于晋谒,又何至变冠裳而入幕,躬败检之行反怨之常,谋捏私书以相倾陷。此事至愚者不为,至愚者不信,而按臣顾落人挑激播弄术中耶!”李炳恭提醒郑继芳万历三十八年南衷参疏可为殷鉴,不可为人所诳,恳乞皇帝敕下部院,“将私书根原查究真确,庶谗口无可乘之隙,善类免株连之祸”。(40)(明)李炳恭:《按臣误信挑构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34-235页。
御史金明时不胜不休,又上一疏攻击湖广巡按史记事,谓记事“邪正倒置、黑白混淆”,“假书”一事,“果得自耳闻,直云出自何人之口,果其得自目击,当直云出于何人之手”,如原无此书,则王图直陈私书见闻一疏何以“含糊怨望,不吐不吞”,为造书者曲庇,以假作真,朋谋合算,一唱众和。(41)(明)金明时:《险臣贪肆谲邪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38页。对于金明时一再攻击徐缙芳和自己,史记事在乞放疏里径指金明时此举“为沈一贯、李廷机等,顾天埈、沈思孝等,陈治则、申用懋等报复”,他认为私书与此前诬陷朱吾弼匿名帖情形一样,由此推之,“何人不可诬,何言不可捏,何事不可生也?私书、匿名或出一派乎?匿名帖不敢认,私书又谁敢认?无怪其张皇若是耳。明时不认私书是矣,然两疏字字与私书相应,窃恐自为私书之证也”。(42)(明)史记事:《微臣病不可支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1,第238、240页。显然,在史记事看来,“私书”实际上是御史金明时一派为浙党沈一贯、李廷机等人报复伪造而成,故不敢承认,金明时两疏即是自为私书之证。
需要指出的是,在“私书”传播以及两党关于“私书”进行争辩的过程中,与“私书”密切关联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皆早知“私书”之事。叶向高晚年追忆:
亡何,复有传御史郑继芳所遗同官刘国缙书于太宰,中言“欲逐余,必先逐太宰与耀州”。耀州者,王公图也。太宰出其书,以示少宰萧公云举。萧公即呼国缙告之,国缙素与考选御史徐良彦、李邦华、徐缙芳、周起元、李炳恭不合,遂谓此书乃良彦辈所捏造,露章言之,号其人曰“五鬼”。朝中大纷。萧公复欲余向太宰索此书。余曰:“仆正欲去,有人能逐之,大幸,何必问也。”太宰亦以告余。余谓书真伪不可知,愿勿谈。太宰唯唯。(43)(明)叶向高:《蘧编》卷4,万历三十九年辛亥,第611-612页。
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出于大局考虑以及辛亥察典避嫌,采取置之不理的冷处理方式,以息流言,并未张扬此事,借题发挥。吏部尚书孙丕扬亦未公开私书、出面澄清。
要之,所谓“郑继芳私书”大概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间在京中朝臣之间私相传播,曾达于吏部尚书孙丕扬之手。私书的内容大意是欲去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必先逐吏部尚书孙丕扬、仓场总督孙玮及王国王图兄弟,斩断秦脉,以秦攻秦。科道系统中的宣党、浙党成员金明时、刘国缙、郑继芳等指“假书”是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与考选御史徐缙芳等“五鬼”为中伤郑继芳、王绍徽、刘国缙三人,合谋捏造而成;而属于东林党系统的王图、徐缙芳、史记事等则认为“私书”其实是金明时、刘国缙等一派出于为浙党沈一贯、李廷机等报复而自己所为,目的是为了驱逐在朝东林党和西北秦党诸人。在双方疏辩的过程中,双方有一共同诉求即都希望收到私书的吏部尚书孙丕扬能够公示此信,当廷比勘笔迹,辨明真伪,遏止流言。由于辛亥京察临近,因此双方关于“私书”一事争辩了两个月并未争出个所以然。
三、辛亥察后围绕“私书”展开的党争
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初二日举行京察。吏部尚书孙丕扬以要挟察典参劾御史金明时,不准赴吏部听考,令其静候万历皇帝发落,(44)(明)孙丕扬:《免过堂告示》,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45页。因之金明时连疏辩解,孰料触犯御讳,径遭削籍处分。(45)刑部等衙门:《喧哗道臣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73-274页。京察疏上,翰林侍读学士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行人顾天埈、御史刘国缙等浙党、宣党官员皆在察处名单,(46)(明)文秉:《定陵注略》卷9《辛亥大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b页。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御史乔应甲、御史岳和声三人又以年例转外。(47)(明)孙丕扬:《摘参诸臣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80页。这一察处结果招致浙党、宣党强烈不满,上下閧然。
三月十三日,在科道拾遗未上的情况下,刑部主事秦聚奎奏上《舍死报国疏》,代御史金明时辩解。秦疏主旨谓今天下大势惟有秦人而已,考察大典本凭以黜幽,却成为秦人借以发私忿的工具,倚之以发伏人言,并质问“私书之有无,胡不见丕扬一言相证耶”?(48)(明)秦聚奎:《舍死报国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50-253页。由于秦聚奎明显违反朝廷京察禁令,因此吏部尚书孙丕扬、河南道掌道御史汤兆京、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等主计诸人从京察制度程序的合法性及察处结果的公正性方面对辛亥京察进行了申辩,并劾论秦聚奎反噬察事、阻挠察典。(49)(明)汤兆京:《灵蘐阁集》卷2《参部臣阻挠察典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08页;(明)曹于汴:《考察国典攸关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58-259页;(明)孙丕扬:《据单秉公考察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60页。
由于察疏未下,浙党、宣党成员已接连遭受处分,其党羽并不接受主计诸人所作说明,于是群起围攻主持和佐理辛亥京察的科道诸臣,企图反噬察事,从而引发了一场持久广泛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党争。“私书”自然成为党争之焦点。
四月下旬,东林党人礼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荐上疏指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持议不坚,主张主察堂官持议当坚,邪党宜破,并明指浙党、宣党为邪党。(50)(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1《正人心息纷嚣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61-664页。紧跟其后,浙党成员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奏上一份长疏,从攻击御史史记事起,进而攻击东林党。他说:东林党人自万历三十六年由南都科臣段然参论顾天埈、李腾芳开始,指称顾、李希图大拜而尽芟除以前碍手之人,其真正用意其实在于拥戴吏部侍郎王图。王图欲跻大位,以工科给事中王元翰为主,以顾、李为用,阴收四方之力,连横设局,步步经营,挑激太宰孙丕扬,借助京察希冀一网打尽阻碍之人,“惟有京察,庶几可张弥天之网,于是着着安排,处处布置,自号提督”,“其千头万绪,不过一脉,总为京察一着,不知费多少计算耳;其打算京察,总为王图枚卜一着,不知费多少经营耳”。王图为至揆路,不择手段,“昔金吾捏称之书原属乌有,而今王图伪造之书果成”,“总不离断秦脉一语,以动太宰而激其怒”。朱一桂还颠倒金明时参劾王图奏疏内容的主次与轻重,径谓:“金明时之参王图,原为假书之故,假书不问而反坐要挟之诛;秦聚奎之论察事,亦有直言之律,直言未行而先得阻挠之罪。明时之疏不下,而参明时者何以随奏随发;聚奎之疏不下,而参聚奎者何以欲处便处?”(51)(明)朱一桂:《特反大乱将作之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87-289页。辛亥党争正式拉开大幕。
二十八日,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千里上疏驰援朱一桂,疏云:“今岁京察之典,其于权相之渠魁、奸党之元恶并物议夙腾而又久应黜逐者,俱一旦去之,不可谓不公。然公道所共为不平者,虽止三四人,而或出于私讐,或出于谋捏,实皆大有关于邪正治乱之数。”又说:“[王]元翰之党大操势权,且有以一身而处处着脚,如史记事辈者益为合谋,并力安排布置,要地尽是私人,蜚语妖言,多单竟出同手,乘考选植私交,则有五鬼,如徐缙芳等皆得入幕。一年以来,晓夜聚谋,何所不至?以去年十一月间,王图等亲造臣之家报,以中臣与科臣王绍徽、台臣刘国缙等,其辩疏凿凿可据。虽似掩耳盗铃,而弥天之网已就,毕竟二臣不免……人人自危,故科道传有公单,内云五鬼倾险阴贼,造捏妖书,名教罪人也。”(52)(明)郑继芳:《直发邪谋所由成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297-298页。郑继芳所持立场、奏疏内容与朱一桂奏疏大旨相同,但言辞更为直接激烈,确指“假书”乃王图与“五鬼”合谋假捏。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郑继芳在这份奏疏中首次完整指实“五鬼”系考选御史徐缙芳、李炳恭、徐良彦、李邦华和周起元五人。
齐党骨干礼科给事中周永春,亦为浙党、宣党助阵。他说:“近时之谋为宰相者,一时有一时之局,一事有一事之案。”客观地说,此论可谓切中万历朝党争之肯綮。而后,又说“奸相沈一贯罢去,至今言者骂不绝口,稍有一隙之明者断不肯入其阱中”,如今党邪庇贪者,“动辄以四明为题,强牵合东西南北之人,并作一路”,丁元荐谓沈一贯授衣钵于顾天埈,以成顾、李一案;顾李被人觑破,李三才遂成奇货,引科道相攻,三才又一案;今之局面,王图之案也。王图雄据之心太痴,“而趋炎之徒争藉以赴功名之会,人名曰西北正人,招诱朋徒,其门如市,图见羽翼已成,而日夜恐人之伺其后也,无端有弓影之惧,逢人起窃铁之疑”,因此捏造假书,利用太宰孙丕扬借助京察驱逐、铲除对其不利之人,“假书”中牵连之人,果在辛亥京察中被一举尽歼,即是明证。(53)(明)周永春:《察疏候检日久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306页。
此前刘国缙、郑继芳等并未将“五鬼”之名全部指实,因此除徐缙芳、李炳恭外,“五鬼”中其余三人一直不便发声。现在郑继芳既然将“五鬼”之名全部指实,考选御史李邦华、徐良彦、周起元就不得不上揭辩白了。李邦华揭称:
自私书发难,而“五鬼”暗刺职辈,虽可自信无辨,而刘国缙势成骑虎矣。“五鬼”恶名,国缙捏诬,恐公论以造妖言议其后,而不得不以闻察预箝职等。传单不经,恐生纠驳,于是借台省公具以涂人耳目,然国缙不敢认也。一穷于副院之诘,而称并未他付;再穷于职之诘,而称绝无相干。当岁首初二日,职质之文山先生之祠,合郡咸在,众目共见,职曰:“人心难昧,鬼神难欺,私书无据,而忍相诬者,神鉴之。”国缙大失色,曰:“我无此说。久知老先生与王衷白一刺未交,何着私书,幸毋见罪。”……夫国缙不敢认单,而假手继芳,漫入私书事,此果国缙愚继芳,抑继芳自愚,而欲因以愚人?夫私书,人明之后,人已知职之受诬,人益忿国缙之无忌。(54)(明)李邦华:《揭私言诬蔑久明》,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2,第303-304页。
可知,御史刘国缙信口指称“五鬼”合谋捏造“私书”,围绕“私书”导致辩讼纷纭,刘国缙被推至舆论与党争的前台,反成骑虎难下之势。因此,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初二日在文天祥祠中,考选御史李邦华在众目睽睽下和刘国缙对质“五鬼捏造私书”之事,“国缙大失色”,极尽尴尬,当面否认自己无此说,并请李邦华“幸毋见罪”。然而刘国缙奏疏具在御前,白纸黑字,终不能掩“五鬼”之名出自其口之事实。
五月初二日,即明神宗发下察疏之日,徐良彦亦疏揭察前假捏公单流言四起也出自刘国缙之口,称国缙“欲剪其所忌,无罪可藉而借以私书”,将自己推入于耀州之党。良彦曰:“职于耀州无奈交也,未同知言君子耻之,乃欲作密语耶?且伪书,细人事耳,何其以小人腹相度?”(55)(明)徐良彦:《揭邪谋构陷叠出》,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12页。同日,拟授湖广道御史周起元亦奏上一揭,称自己就选以来杜门谢客,罕相晋接,“忽遭刘国缙指造私书、假捏公单,极口丑诋,复密报之同党郑继芳,抄入疏中”,入都首尾二三年,“于王图不惟不识其作何面目,且绝无及门之刺”,“私书一事,无而造之,为神奸巨蠹;有而传之,为偷寒送暖,均市井之行,君子不为也。国缙宜质之太宰,核其从来,乃上之致媚词,下开钳网,标以绰号,诋以恶名”,复传报于浙省“又误继芳”,二人合谋流毒,“意不过欲去其所拂,阿其所亲,广肆侦探,悬空揣摩,忻然幸有私书题目以安排陷阱”,以驱逐异己。(56)(明)周起元:《揭险人假捏公单》,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15页。
李邦华等人揭帖,揭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假捏公单、“五鬼合谋捏造私书”,皆出自贵州道御史刘国缙之口,然实属子虚乌有,刘国缙却将此乌有之事密报于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
在徐良彦、李邦华、周起元连上三揭之后,浙党骨干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跳将出来,大肆攻击东林。徐兆魁说,“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于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肋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顾宪成等身在山林,飞书走使,操纵朝廷黜陟予夺之权,移书捏单,假计典尽剪其所忌,将持正之士几一网打尽。又说:
计典之滋议,则始于假书之播弄;私书之把持,成于金明时发假书之一疏,激于汤兆京要挟之八字,太宰不言假书之有无,其意甚婉。兆京欲为人杜发假书之隙,而以要挟驾词,其计巧而实拙。假书终于未发出,难以径坐王图,至以“断秦脉”三字误太宰处诸臣,则王图、南师仲、胡忻均不得辞其责者也。乘计察,而私书荧惑者,东林为祟,至差家人总赍书者,吴正志也;代为送者,胡忻也。私书私单,总非整体,属垣有耳,方寸难欺。当事者不此是察,而预绝其源,乃徒咎于秦聚奎之阻挠。复虑台省之有言,不已左乎?(57)(明)徐兆魁:《部臣借事发端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17、320页。
徐兆魁谓各党利用察典打击排除异己倒是客观揭示出万历朝党争的实质。但在李邦华当面对质刘国缙以后,徐兆魁仍坚持认为是王图之党捏造“假书”,特别是徐兆魁奏疏中增衍出“私书”赍送一节,节外生枝,径指赍书者是御史吴正志,代送者是太常少卿胡忻,将与此无甚相关的吴正志、胡忻攀扯进来。
由于徐兆魁肆意攻击察事,导致参与察事的河南道掌道御史汤兆京极度不满,即刻上疏驳斥。汤兆京说,迩来烦言具攻王图,以齮龁太宰并笼罩臣等,王图已出国门矣,今徐兆魁忽移师东林,又齮龁臣等并笼罩管察诸臣,以“私书”说事,“不以私书处吴正志,为徇私交”。汤兆京谓秦人、东林风马牛不相及,徐兆魁混为一涂,总在一“怨”字,不能忘情于东林耳。(58)(明)汤兆京:《灵蘐阁集》卷2《题台臣议察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13-514页。又,前工科给事中、现任太常寺少卿胡忻因被徐兆魁奏疏无辜祸及,愤而疏辩。胡忻说:“乃徐兆魁谓职以断秦脉误太宰处诸臣,又谓职为吴正志代送私书,荧惑众听。夫职虽太宰同乡,然自去秋以来绝未私见一面,即名帖亦未数投,门簿可查,门上人可问也,何从关说以误之?冤矣。吴正志虽职同年,然自谪降出京而后,绝无一字相闻,家人总赍私书,有何踪迹?职代为送,是何班皂隶?无风无影,悬空坐之。又冤矣。”胡氏谓徐兆魁辈计在一网打尽,甚至连“计闲局之南师仲亦不免焉”,又说:“假书之有无,职不敢知,而绝秦脉一语何机局,符合若此耶。大抵诸臣挠乱察典,以扼太宰孙丕扬,必尽甘心秦人而后已。”(59)(明)胡忻:《微臣无端被指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22-323页。
然而徐兆魁决意求胜,再上一揭反驳汤兆京。他自称疏发东林举动及计事滋议之事,“自信一字不欺”。关于“私书”,徐兆魁揭云:
当日假书,孙太宰曾与萧少宰看,萧援笔书“得非诈乎”四字于柬后。太宰亦曾对四司言之,语泄于外,金遂闻而具疏,所云字迹类谁,不知语于何起。今王少宰出城矣,萧少宰必继去矣。为假书者,其祸亦甚烈矣,而播弄之人犹以假书来历未明之故,获逃吏议,岂不幸哉!(60)(明)徐兆魁:《揭支吾饰辩》,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33页。
这里,徐兆魁揭帖又增衍出“私书”若干细节:吏部尚书孙丕扬收到“假书”后,曾示吏部侍郎萧云举,萧书写“得非诈乎”四字于书后,孙丕扬又将此信内容对四司言之,才导致书信内容泄露于外,御史金明时遂闻而具于疏。徐兆魁亦感慨“假书其祸亦甚烈”,吏部侍郎王图已去职出城,吏部侍郎萧云举也必定继而去职,但播弄之人犹以“假书”来历未明获逃吏议。徐氏此疏,又将参与主计的吏部右侍郎萧云举牵扯进“私书”一事。
五月初九日,协理京察巡按直隶御史乔允升亦奏上一疏,揭露吏部右侍郎萧云举在“私书”传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乔允升称,辛亥京察前后党争与吏部侍郎王图和萧云举暗争、希心大拜密不可分,王图轻信流言,将“私书”一事闻于吏部尚书孙丕扬,孙丕扬又以其事示之吏部侍郎萧云举;萧云举为了倾轧王图,故意将“私书”一事泄露于御史金明时、刘国缙,因而才出现金、刘临察疏参王图之机局。(61)(明)乔允升:《国是混淆愈甚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38-339页。乔氏影射徐兆魁播弄是非却成为漏网之人,并在奏疏中历数吏部侍郎萧云举在京察中营救其党汤宾尹、刘国缙、金明时等,收受贿赂,周旋于吏部尚书孙丕扬之前,遭拒,遂令刑部主事秦聚奎挺身代辩,反噬察疏。要之,乔允升一疏另具新说,将吏部侍郎萧云举深度牵扯进“私书”事件之中,视其为“私书”流传的关键人物。
至此,关于“私书”之争已是愈辩愈奇,攀扯之人亦愈来愈多,故而东林党与非东林党都希冀弄清“私书”来源,揭明真相。
五月初十日,徐缙芳上揭恳乞吏部尚书孙丕扬公开私书之来历:“职等拙守寡交,刻自砥砺,第以缙芳救顾泾阳一书,遂来谗口,并广株连,而候命之人无可瑕摘,突出私书,大生罗织于时。考察伊迩,职等不欲多言混淆,亦谓太宰终当发露,不意察疏迟留,而谗言复借以摧陷。今察事已竣,私书未了之案,不可不明。果如徐御史揭云是萧少宰已见其书矣,果如乔御史疏云是王掌院传之冢宰矣。职总不知,第其私书之根由,可不诘乎?书而真也,何自得来?书而伪也,谁人捏造?及今掌院未离国门,可核可证。此其中惟太宰洞晰之,职等有无干涉一言,可以立破,不然坐令黑白淆乱,而授奸人以口实,是祸职等也。”(62)(明)徐缙芳:《恳发私书来历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40页。十五日,静候御旨放去的吏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缄默数月,按捺不住,再上一揭:
忽阅邸报,见海石道长(徐兆魁)有疏谓郑道长私书,少宰曾寓目矣;又见乔鹤皋道长(允升)有疏谓私书一事,职轻信而闻之太宰矣;又见徐十洲(缙芳)等有揭,复讹以“闻”字为“传”字矣。夫“闻”字犹涉风影,“传”字则近实事。“传”之一字,职何能受?总之,皆系揣摩臆度之言,非真见也。
方私书初起时,长安喧播已两月,职访之,殊无指实。时察事方殷,职绝不敢闻之太宰。可问也。此讐职者,借此欲陷职并陷徐十洲等,遂致议论沸腾。职不得已移书太宰,询其得书根因,太宰答云:“目今访单纷纷,不知几千百张,若欲知其授受,诸葛亦难。不肖何能记其一二,又何能辨其真假?”又移书少宰,询其见书始末,并询笔迹果出何人?少宰答:“书前寒暄语,不述。后云读教翰,惊汗浃背,斯何人也,乃为斯语哉?弟与仁兄讲性命之学,方欲绞干情浪,扫尽凡尘,何乃于世法中更生嫌疑,从来无后言,亦无违心片语,即闺帷中可亮也。私书之说,太宰绝不经谈,弟绝不入耳。自与太宰相处二年,□书出一札相示,安得坐人以无影之事,而使我至厚弟兄自生离间,鬼神在上,天日可欺乎?”
二老回札如此,词白极其明晰,今见藏职处,人人可看,二老俱可质问,则所谓少宰曾见私书,识其笔迹,诸人借此驾诬于职,并牵缠徐十洲诸公,其属冤陷可知矣。时有劝职,将此二札发抄以自暴白者,因职兄有不许传播手札之戒,深佩其言,故二札亦曾间以示人,并不敢发抄,将谓事久论定,谗间自熄。不意蔓延至今,犹然猜度横生也。顷徐海石有私书难以径坐王某等语,乔鹤皋有私书不知出自何人何手等语,可见公论亦知与职无干,独徐十洲等有掌院未离都门可核可证等语。职实悚然,不敢自诿于羁栖萍梗,不为诸公明白分豁,以留后来不了之局也。(63)(明)王图:《揭再陈私书闻见》,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3,第350-351页。
王图此揭,首先申述自己既未曾将“私书”一事闻之于吏部尚书孙丕扬,更未曾传之丕扬;其次,王图说明了一事,即在“私书”喧播京中二月后,王图曾致书询问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私书来历、何人笔迹,孙、萧二宰以书札答复云云,并将二老答札公诸于众;最后,王图希望通过公开二札,分豁诸公不明之疑,以结不了之局。
果如徐兆魁所说,十八日,吏部侍郎萧云举以被论奏请乞去,并力辩:“伪书不知出自谁手,然共所共睹,孰不知之,何独于臣疑其漏泄?盖以讹传讹,日甚一日,无端无影,与臣何干?至于臣与王图极厚极善,相爱相戒,交欢莫逆则有之矣。”(64)(明)萧云举:《风波突起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53页。
在王、萧二人相继奏上揭、疏之后,关于“私书”如何闻之于吏部尚书孙丕扬一节已相当清楚,“私书”之争辩也因此暂时归于停歇。但是,“私书”究竟系何人伪造,依然不得而知。
不过,浙党、宣党并不打算放过翰林院掌院吏部侍郎王图,继续围攻王图,他们借助辛亥京察与“私书”驱逐王图的目的非常明显。六月初三日,南京科道加入党争,福建道御史王万祚、山东道御史曾陈易同日上章,一面为吏部尚书孙丕扬宽解,一面攻讦王图。王万祚称辛亥京察造成“倒翻世界,转成昏黑”的局面并非吏部尚书孙丕扬初心,然丕扬偏听成奸,独任成乱,“竟为[王]图所误,而牵固深入争之不能得者,岂非以假书之故乎”?他说,“假书”真伪并不难辨,“假书”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激怒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仓场侍郎孙玮和翰林院掌院王图,以此之故,王图借“假书”而发挥,借助察典排除异己,“附秦者留,非秦者逐”,“假书之功,顾不称大哉”!因此,王万祚认为“丕扬真大可哀也,图大可恨也”!(65)(明)王万祚:《黜幽大典宜结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61-362页。王万祚仅仅斥责王图利用“假书”排除异己,应该说还算是比较理性的看法,曾陈易则大不一样。曾陈易径谓王图为权奸,系群小大关头,纵子庇匪,报私怨,图速拜而忌同官,“伪书出王图之手明甚”,激怒孙丕扬,驱逐异己。(66)(明)曾陈易:《邪关一言可破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63页。鉴于南都科道论救北察察处之人并肆意谩骂王图,波及吏部尚书孙丕扬,六月初三日孙丕扬接连上疏抗辩,他说:“中间意向又自宽臣,而大有怨于王图,若将谓臣偏于乡曲而信图者。夫臣掌察典,遏恶以报国恩,何人不访,何事不查,而独问图哉?”(67)(明)孙丕扬:《科部救人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65页。河南道掌道御史汤兆京继之亦上疏辩陈京察程序,以谢南都。(68)(明)汤兆京:《灵蘐阁集》卷2《题南臣议察疏》,第518-519页。
然而,浙党、宣党众人对吏部尚书孙丕扬、河南道御史汤兆京的辩解并不买账。浙党之刑科给事中彭惟城继曾陈易之后,不仅指斥王图为权奸,甚至还以“刽子手”之名加诸其身,谓其“害及众君子”。(69)(明)彭惟城:《纯臣义不讳过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70页。齐党户科给事中徐绍吉称,今岁“察典之误,始于假书为祟,终于要挟激成,以众君子维之而不足以一二险人乱之二有余”,(70)(明)徐绍吉:《言路渐轻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87页。影射王图、徐缙芳等人。兵科给事中朱一桂上疏诬蔑史记事、丁元荐等为邪臣,阿附翰林院掌院吏部侍郎王图,“记事等之耽耽逐逐,正在拥戴王图,而苦不协时望”,“乘京察之举,为一网之计,正在借大典以箝制人口”。(71)(明)朱一桂:《邪臣阿附甚明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91页。汤宾尹门人、宣党骨干归子顾上疏代汤宾尹、王绍徽辩解,称“奸人巧于害正,往往以流言中人”。他说:“至若秦脉一书,尤属刺谬,情辞不伦,奸人挑激晓然,此何难识?乃王图既非自造,何不质其人以明心迹,不然亦宜付之一笑,胡怆惶狼狈,奚怪金明时一疏,不复引罪而尽疏中所连及之人并重疑。”又说主计之人不察书之踪迹,一接飞矢,风吹草动,尽属疑城,“支言片语,辄搴毒焰,致误计事,大启纷嚣”,流言一节则是“从来纷嚣之本根”,信用流言尤今日害政之大孽,“今假书未明,而用假书之人未去”,因此他认为必须亟执投递之人,案问假书来历,依律治罪,倘系蜚闻尤当禁止转相传布,“务使支蔓,永消嫌怨”。(72)(明)归子顾:《流言贻祸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94-395页。
需要指出的是,进入万历三十九年六月,在吏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离职去位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以浙党为核心的非东林党人固然对王图继续进行穷寇式追打,但实际的攻击重点已转变为主要攻讦吏部尚书孙丕扬。湖广巡按史记事一言揭破这一真相,他说:“私书明疏,远近叫应,今参孙尚书者见累累相继,而反谓职等欲参太宰,左道惑人,大言欺世,继芳可胜诛矣。”(73)(明)史记事:《邪人得势益张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4,第398页。
以史记事疏中指斥郑继芳,七月初一日,郑继芳连上疏揭各一封,围绕“私书”再次展开辩解,进而又掀起一轮“私书”争辩小高潮。郑继芳依然将“私书”的伪造者指向王图等人,他说:“奈何党同者毫无忌讳,而必欲以百假胜一真,使孤忠者一犯其锋,卒令含冤以去,而祸机犹不已也……而何其党王图、胡忻、史记事等百计弥缝,多方诬蔑,改奏揭、假公本,挑激主察,蒙蔽圣聪,无所不至,而最后一着,图与徐缙芳等捏出假书以为报复,更是异闻,故京师一时有五鬼捏造妖书之号,所以图之辩疏,呈出本来面目,而肺肝毕露。”进而指出,徐缙芳等不欲问私书来历于王图,却欲问孙丕扬,“是又欲借太宰陷要挟故智,为骇人之谬举”!(74)(明)郑继芳:《假书虽败而害已行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5,第410页。郑继芳甚至称,王图、徐缙芳等伪造“假书”目的在于察期临近取劾速,事情泄露后,旁逞杀机以嚇见之者不敢认,王图与徐缙芳等彼此交讳,并反坐徐缙芳、李炳恭等“五兄与不肖作难”。(75)(明)郑继芳:《揭假书情形难掩》,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5,第412-413页。“私书”之争辩,聚讼纷嚣,兜兜转转,又转回到原处。
胡忻以曾为王元翰疏辩,被郑继芳扯进“私书”事件,指为王图邪党,参与谋捏“私书”。胡忻愤懑难平,疏云:“私书,臣未之见,书之真假,臣亦未之知,惟是王绍徽、刘国缙之处,当事者或别有所为,非为私书。若以私书,处继芳实为戎首,何预绍徽、国缙事?继芳而果未为私书,当事又未尝以私书处人,何不脱然坦然,顾汲汲皇皇,葛缠不可了,岂神明之舍亦有不自安者耶?”(76)(明)胡忻:《欲焚草》卷4《辩郑御史疏》,第13b页。胡忻以其之矛戳其之盾,谓若以“私书”之故,京察当首处郑继芳,而实际上却没有被处,这说明王绍徽、刘国缙被察处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私书”之故,因此郑继芳何必汲汲皇皇,纠缠不了,何不脱然坦然处之呢?
初五日,继胡忻之后,考选御史李邦华、徐缙芳同日奏上揭疏,反驳郑继芳。李邦华怒斥郑继芳犹揭指职名为私单、假书捏造者,为刘国缙强脱罪名,他说:“夫书之或真或假,在继芳为中心之隐忧,在职为无干之妄扯;在继芳有不得不求明之情,在职有不求明而自明之券。”李邦华谓自己与王图半面不识,一刺未通,风马牛不相及,“而猥云合谋捏造假书,以滋一网,不知谋何从合乎”?李邦华又称,郑继芳止为“私书”二字,寝食难宁,明知职等无干,特欲激职代为之白,故肆口诳赖,但是自己“私”亦不知,“假”亦不知,却被郑继芳等攻击东林,目为“秦党”,推入陷阱之中,继芳即能以“假书”坐王图,却必不能牵扯与王图无交之人,“即欲为国缙脱匿名之罪,必不能为国家宽倾害善良之罪”。(77)(明)李邦华:《揭长安公论甚明》,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5,第420-421页。徐缙芳亦疏云,关于“郑继芳私书”一事,若非二三臣有疏,自己实不知也,中间源委种种,自己亦皆不知。缙芳指出,据云捏出私书,为王元翰报复计,但是王元翰去国业已数年,自己未尝救元翰,顾宪成亦未尝救元翰,“事不相涉”,报复之说何来之有?徐缙芳又说:“今日私书一节,孙太宰问而不应,萧少宰又不直言,臣等之有无干涉,坐令小人口实陷阱无已。”因此吁请王图、萧云举、孙丕扬出面,公开回应“私书”一事。(78)(明)徐缙芳:《险臣借事设窍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5,第421-422页。
以徐缙芳一再指名要求王图、萧云举、孙丕扬出面回应“私书”之事,初八日王图只得又上一疏剖陈“私书”情实。王图疏云:“臣自被言以来,一味求去,是非毁誉俱付公评。乃言之者弥烦,而中之者弥毒,臣今去矣,若不明白剖析,恐闻之者转相煽惑,臣伏林莽未得安枕也。”王图揭破今日党争实质,不外乎就是指自己以“私书”假借察典中伤排挤异己而已。王图说,“郑继芳私书”一事,太宰孙丕扬绝未尝示人,书之有无真假,自己不能知,太宰、少宰回札可证,“太宰未尝行此私书也,亦未尝信此私书为真也。若行私书,继芳实为首祸,何以得免”。但是,王图尖锐地质问道:“书果假矣,今诸臣南北合攻,一则曰秦党,二则曰秦党,此与断绝秦脉之说,合乎否乎?显行其事,而阴讳其名。”(79)(明)王图:《孤臣招祸有因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5,第423-424页。七月十二日,吏部尚书孙丕扬在去国前终于奏上最后一份揭帖,因应各方有关“私书”来源之求问:
《大明律》内“投匿名文书,告言人罪者即毁。”此国家之典章也。前冬末,臣为考察,博访人言,临近投单之时,中混有“假书”一纸,以为必有仇害人者,遂付之烈焰,业已灭迹。而忽有问臣者,臣默而不答,盖为察事近也。不谓今日犹然聚讼,以臣愚见,殊与诸臣不同。盖借私书而害人也,则造私书者可罪;行私书而害人也,则行私书者可罪。今皆无之,到底作何结果,犹之匿名帖者,谁肯自认?又将拟罪于谁乎?独憎滋多口耳。(80)(明)孙丕扬:《假书无根疏》,载(明)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5,第426页。
孙丕扬这份揭帖,正面回答了各臣要求公开“私书”来历的疑问。孙丕扬说,“假书”是夹杂在投放京察的访单之中,见之以后,根据律条规定已经付诸焚毁,业已灭迹,不知是何人手造,亦不知何人夹入,因察典临近故而自己一直沉默未言,不意以“私书”一节诸臣至今犹然聚讼纷纭,借“私书”害人,造“私书”者当然可罪,行“私书”亦当然可罪,但问题是不知谁是造书者,谁是行书者,更不会有人肯自认,因此又将拟罪于谁?最后,孙丕扬语重心长地说道,言官系海内之澄清,关民生之休戚,自有宗社大担,不应将精力放在“私书”一事上,而应顾意于国家社稷方面的建树。
吏部尚书孙丕扬揭帖所说“私书”来历之情形是否真实,当时已无从核实,今日则更难考证。但不管怎样,孙丕扬对于“私书”一事也算是给出了一个公开的交代,而且声明原书业已灭迹,浇灭了诸人乞敕下发“私书”公庭当面辨别真伪的念头。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在朝诸臣如再继续纠缠“私书”一事便显得不可理喻了。因此,在孙丕扬公开揭帖之后,除兵科给事中朱一桂一人呶呶不休外,关于“郑继芳私书”一事的争辩遂逐渐消歇,最终不了了之。此后,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便转而摭拾其他琐碎之事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持久的党争。万历四十年以后,朝臣奏疏中偶有论及“私书”者,亦多是出于检讨、总结辛亥京察的历史教训,作为一种“记忆”而发。(81)例如,万历四十一年,户科给事中姚宗文说:“辛亥内计之前,有欲构害正人,且自为解脱之计者,讹传御史郑继芳一书,绝无形影,巧弄机关,几成空国之祸,乃其捏造秘密,无从踪迹,迄今有余恨矣。”(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7《明勘私书以清议论疏》,第597页。)万历四十二年,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王宗贤云:“忆当时合谋偷单、捏造假书反间,原自有人,人所共知。”(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8《愚臣万恳退闲疏》,第648页。)
结 语
综观万历三十八年“郑继芳私书”与辛亥京察、党争的整个事件和结局,自辛亥京察察前至察后,吏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事王图、保定巡抚王国、吏部尚书孙丕扬、河南道掌道御史汤兆京以至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相继离职,与“私书”所说内容相符若契。尽管《明史》作者认为“私书”“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郑继芳辈”,(82)《明史》卷224《孙丕扬传》,第5903页。“私书”制造者也已然埋入历史之尘迹,然而,就辛亥党争结局推测,“私书”很可能是出自浙党分子之手。
实际上,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谁是“私书”制造者,而在于“郑继芳私书”事件之于辛亥京察、党争和“续妖书”事件之于乙巳京察、党争,惊人地相似。“私书”事件,被浙党、宣党充分利用,在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期间作为打击、排挤异己和政敌的手段,酿成万历朝东林党和以浙党、宣党为主体的非东林党之间的一场规模广大、时间持久的党争。党争范围从内到外、由北而南,聚讼纷纭,攻讦不绝。“私书”事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私书”中欲驱逐之东林党人,在“私书”事发后的党争展开过程中相继去位,最终实现了“私书”制造者所欲达到的初衷和目的,为明末党派借助京察公器私用、排除异己提供了有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