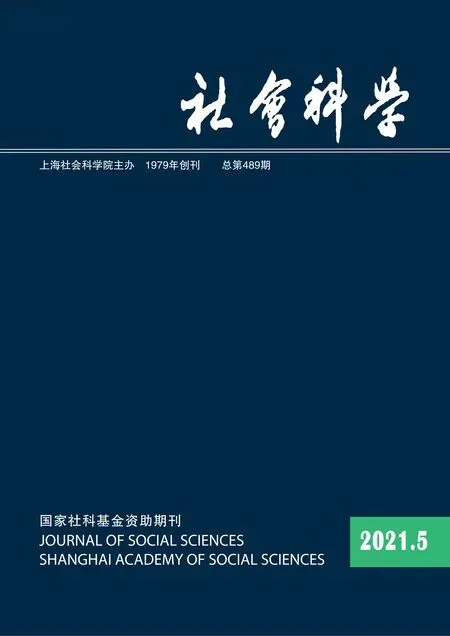北宋衙前役法考论
2021-11-24董春林
董春林
宋代役法问题是研究宋史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役法变革或演进中尤以衙前役法最为重要。宋人司马光回顾募役法改革时尤言:“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乙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759页。聂崇岐先生亦云:“宋代色役之最为民病者,首推衙前。”(2)聂崇岐:《宋役法述》,《燕京学报》第33期,1947年,第202页。北宋政府推行募役法始为解决衙前差役面临的问题,北宋中后期役法的变革及争论,均绕不开衙前役法如何改革或推进之类的话题。关于衙前役是职役还是差役,衙前称谓的由来,衙前役的种类及其职能、作用,此前已有聂崇岐、邓广铭、周藤吉之、漆侠、裴汝诚、王曾瑜、黄繁光、唐刚卯、张熙惟、李华瑞等前辈学者研究和关注。但宋代衙前役法相关问题异常复杂,文献记载中又多有前后抵触之处,此前研究者难免有所错漏,对于一些关键术语的解读不足,或过于笼统,使得我们无法完整了解宋代衙前役法的全貌,更无法对北宋役法更革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基于此,本文将对北宋衙前役法中“长名”“投名”这两种称谓进行再解读,对元祐役法改革中提出改“雇”为“招”的文本内涵再深入挖掘,并且对“助役法”“免役法”的殊途同归进行比较和探究,希望借此对北宋衙前役法乃至北宋役法变革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论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长名”非“投名”:熙宁役法前后衙前称谓变迁
募役法前的“长名衙前”和募役法下的“投名衙前”是否相同,这个问题看似有些多余,因为此前学者多认为两者所指为一。(3)周藤吉之先生曾指出,长名衙前即投名衙前,是人民投充衙前者。参见[日]周藤吉之《宋代州县的职役和胥吏的发展》,《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第662页。裴汝诚先生认为,熙宁变法以前有些吏人自愿投名,官府也需要有人投名或延长自身役限,长名衙前便成为衙前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长名衙前的增多和取得雇值的现象,催生了以货币形式支付役人雇值的募役法。参见裴汝诚《略论宋代的衙前役》,载《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79页。漆侠先生认为,衙前主要是从乡村户等中差派的,熙宁变革役法之前的若干年里,各地区都曾出现自愿投名充当衙前的投名衙前或长名衙前。参见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载《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2页。唐刚卯先生则认为,宋仁宗朝已有官卖坊场支付、支酬投名衙前的案例,熙宁变法实是仁宗时几种方法综合的发展,长名衙前显然即投名衙前的前身阶段。参见唐刚卯《衙前考论》,载《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37页。李华瑞先生认为,衙前主要是从乡村户等中差派的,但自宋仁宗以后,在各地兴起来一批自愿到官府投充衙前的,称之为投名衙前,或长名衙前,这类应募的长名衙前,有乡村诸户等,但更多的是坊郭诸户等,官府对这类投名衙前,也是以酒坊作为酬奖的。这类酒坊承担者,除交纳官府规定的酒课之外,自负盈亏。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张熙惟先生则认为,招雇衙前主要是官府招雇城乡居民为衙前,或称“长名衙前”,意为长充衙前之役,因此又有“投充长名衙前”之称。参见张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质》,收录自《学思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轮差者往往有歇役期限,故北宋人在不少场合下是将“投名衙前”与“长名衙前”互相通用的。(4)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一)》,《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之所以会造成两者概念的混淆,可据以下两条文献材料进行分析。一是元祐元年(1086),苏辙曾言:
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5)(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17-4318页。
苏辙所谓“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讲的是长名衙前的酬奖是允许其经营酒坊,上交官定酒税之外息钱自有,也就是官卖转私营作为优酬的一种激励政策。至于“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言外之意是说新法改制中官府雇募衙前是给予现钱激励的,这即是募役法下投名衙前的激励措施。此前研究者多着眼于熙宁以前诸路多长名衙前之语句,认为苏辙所论的“长名”即为此前的“投名”。二是熙宁四年(1071),曾布曾云: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潜为内应。(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802页。
曾布的奏言旨在论证募役法的合理性,“今投名衙前半天下”,并非指熙宁以前的长名衙前诸路过半之说。“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并不是熙宁以前的长名衙前之实,因为长名衙前“同乡户衙前一样,在主管官物期间不出差错,年满之后给以坊场作为酬奖”,(7)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载《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2页。若没有经历“十分重难”,自然得不到酬奖。失陷官物的衙前多是不谙公家事务的乡户衙前,并不包括精熟官场游戏规则的长名衙前。坚持反对募役法的司马光尤言:“至于长名衙前,久在公庭,勾当精熟,每经重难差遣,积累分数,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二五,第7811页。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两种衙前称谓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弄清楚两者含义,其次将它们放在役法变迁的视域中重新解读,最后指出两种称谓的内涵所在。
就“长名衙前”来说,一般指熙宁以前差役法下精熟主典官物工作,并且为获坊场酬奖而自愿长期从事衙前工作者。(9)有学者总结:“负司牧之责者乃点差应里正之户为衙前,是为里正衙前,而军将之充衙前为长名衙前。嗣是官吏以里正衙前质朴易制,间有迫使永久充役为长名衙前者。外此,复有民户应募之长名衙前(亦曰投名衙前)及富人被派之乡户衙前。”参见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03页。军将充长名衙前尚未见史料支撑,里正衙前充长名衙前,富人被派的乡户衙前,即差役法下的长名衙前,民户应募的长名衙前在宋仁宗时南方地区就已存在,熙宁役法下即依投名方法完备,总体来说,长名衙前者得名自差役法下自愿应募者。有学者认为,将吏衙前是武人出身,押录衙前是人吏出身,长名衙前是应募投充的,都不属于差役范围。(10)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这种认识多起因于将长名衙前与募役法下投名衙前划等号,忽略了长名衙前精熟主典官物工作的役法背景。熙宁以前长名衙前并不是一开始就应募投充,政府招募长名衙前也不早于差役衙前,甚至长名衙前除了招募之外也可能定差,或由定差衙前转变而来。宋初里正衙前、押录衙前皆为定差,但由于“押录”本身原来即属于低阶吏员,他们久在官衙、熟悉公事,故期满时转迁衙前,因其数额不多,后来渐被招募式的“长名衙前”所取代。(11)黄繁光:《宋代衙前之役的特性与乡户的关系》,载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36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59页。当然,长名衙前也并非差役法下的固有称谓,募役法下长名衙前也一直存在,毕竟愿意长期从事衙前工作,为政府省去了很多麻烦。熙丰役法之后“长名衙前”不仅始终存在,并且还是衙前工作的主力军,“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按熙宁二年(1069),吕惠卿主持初订役法条例云:“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12)(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第4299页。元祐初,司马光力主恢复差役法时提到“旧日将坊场、河渡所折酬长名衙前重难”(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八,第6259页。。吕惠卿所讲的经过重难分数的“投名衙前”当指“长名衙前”,买扑酒税坊场息钱和免役钱是其固定的酬劳,(14)有学者认为,募役法施行时免役钱并不用于衙前。参见魏峰《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这样的说法并不妥当。按熙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司使沈括上言:“今州县重役,不过衙前、耆户长、散从官之类。则州县易为衙前即坊场河渡钱自可足用,其余于坊郭、官户、女户、单丁、寺观之类,因坊场河渡余钱足以赋禄,出钱之户不多,督敛,重轻相补,民力自均。”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七,第7806页。沈括所谓衙前只需坊场钱、河渡钱即可足,只是考虑民力匮乏提出的建议。按熙宁三年五月,时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令当役人户以等第均出,曰‘免役钱’。而一切募人充役,随本役轻重以钱给之”。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第5130页。吕惠卿所谓“一切募人充役”当包括衙前,他在草定募役法时提出这样的认识,显然更具法定意义。熙宁三年十月,“颁募役法于天下。内外胥吏素不赋禄,惟以受赇为生,至是,用免役钱禄之,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参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1页。所谓禄钱即工食钱,又称雇食钱,衙前的雇值及日常食补即为雇食钱,这无疑说明免役钱也是支酬衙前的一部分。显然是拿过去应酬奖“长名衙前”的场务收益和现在征收的免役钱继续补偿给“长名衙前”。但“长名衙前”役人并非都是自愿承担衙前工作,差役法下按户等差役,有符合条件者故意躲避衙前重难,也会遭到官府定差。皇祐中,就曾“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使募人为之”(1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3页。。熙宁初年,“白脚奸户”丁怀纠举已经历过衙前重难工作的一等户胡真应该继续应役,时任福建路转运使陈襄上奏状指出,丁怀是未曾应役者中的高强户,请求“定差丁怀充长名衙前”(16)(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六《乞均差衙前等第状》,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至于“投名衙前”,较多出现在熙丰役法施行期间,似为“雇募衙前”的代名词,但作为一种时代性名词,并不确指某种衙前称谓。“投名”可释义为自愿报名,“投名衙前”可释义为自愿充当的衙前。之所以有些学者理解投名衙前为“长名衙前”,多是循着其充当者的自愿性去理解。《淳熙三山志》曾表明“建隆以来,并召投名”(17)(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县役人》,载《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88页。,“元丰三年,以募役衙前三十三人并入长名九十二人”(18)(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县役人》,第7889页。。由此可见,“投名”衙前这种应役方式由来已久,熙丰役法制定也是对先前经验的总结。王曾瑜先生认为,衙前入役,差、募兼行,实施于北宋前期至中期。北宋人使用投名衙前之类称呼,其实都是就其入役方式而言的。(19)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一)》,《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可是,“投名衙前”这种雇募衙前方式,在熙丰役法改革后才真正合法化,并且成为“长名衙前”的主要募充方式,毕竟“雇募衙前”并入“长名衙前”已很平常。据《淳熙三山志》记载:
熙宁三年,乡户衙前增为七十二人。明年,行募法,令人出免役钱。七年,州定长名衙前一百一十七人(情愿投名,不请雇钱)。雇募衙前三十七人内,主押纲运、搬请官物三十三人,主持馆驿四人。八年,减罢方山、太平、小若三驿专知三人,存留渔溪一驿,每岁增支庸钱。九年,裁减长名二十五人,存九十二人。元丰三年,以募役衙前三十三人并入长名九十二人,总一百二十五人,均轮优、重差使。(20)(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县役人》,第7889页。
按熙宁七年(1074)福州地区的长名衙前“情愿投名,不请雇钱”,只是指不用免役钱,并不表明其不要坊场酬奖。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当是按照吕惠卿初订役法条例中的办法给以酬奖。(21)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据史载,熙宁四年(1071)十月一日颁布的募役法,“诸户等第输钱,免其身役,官以所输钱立直,募人充役”。(2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二,第7803页。此亦可见,“投名”只是一种应役衙前的方式,“长名衙前”和“雇募衙前”极少例外情况下的区别是使用免役钱与否,更多时候两者区别不大,当然这取决于应役者是否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以及官府的需要。据上文可见,元丰三年(1080)福州地区即“以募役衙前三十三人并入长名九十二人”。元祐改制之后,官府更是鼓励“投名衙前”投充“长名衙前”。元祐四年(1089)八月十八日宋哲宗下敕:“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处。……如愿投充长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钱即全行支给。”(23)(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五,载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85页。
事实上,元祐改制后的“投名衙前”并非“雇募衙前”。征募乡户自愿“投名”,仍然是官方解决衙前重难工作的重要手段,只不过这个投名方式在元祐初年有所调整。早在熙宁八年司马光反对免役法时就提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2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二六,第7811页。司马光所谓募人投充长名衙前,仅以场务税钱酬奖,所以并非雇募人投充衙前,“投名”显然并不是专属于“雇募衙前”的应役方式。
至此可见,“长名”和“投名”并非都指向衙前称谓,“投名”只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应役方式。随着宋代社会发展,“长名衙前”和“乡户衙前”仍然是熙丰变法时期主要的两种衙前。由于一些精熟衙前工作的乡户长期充当长名衙前,最后这类衙前逐渐职业化,成为专业的职役。从事长名衙前者多是为了雇值优利,熙宁新法之后依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有学者即提出,“一般说来,长名衙前得到官府一定的雇值,但也有不付雇值的。长名衙前增多和取得雇值的现象提示人们:衙前役有着固定职业化的趋向”。(25)裴汝诚:《略论宋代的衙前役》,载《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二、“雇”“招”两意:衙前征募的官私属性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尽废新法,但募役法并非完全被旧的差役法取代,文献表述中似废“雇募”为“招募”,至于“招募”为何义,牵扯到“元祐更化”的彻底性。有学者曾认为,司马光上台后力主全盘恢复旧法,但后来他的态度稍有变化,认为可以征收六色钱,为掩盖衙前实行雇募之实,又将“雇募”改为“招募”。(26)唐刚卯:《衙前考论》,载《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39页。这样的认识未免过于草率,“雇募”和“招募”之间存在差异。元祐元年,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言要求“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27)(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第4311页。据此可见,招募人投充长名衙前,与差乡村人户充衙前不同。“招募”似非“差役”,那是否就是“雇役”呢?
元祐元年(1086)二月六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门下侍郎司马光奏定役法云:
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日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计作助役法。自后条贯优假衙前,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干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大将管押。其粗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间陪备亦少于向日,不至有破家产者。若犹以衙前户力难以独任,即乞依旧法,于官户、僧寺、道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免。其余产业,并约此为准。所有助役钱,令逐州桩管,据所有多少数目,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每分合给几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各有不同,欲乞于今来敕内更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州县,委逐处官看详。(2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五,第6245页。
司马光最初提出衙前行差役法时显然并没考虑周全,只着眼于募役法下民间陪备(赔费)过重,现在改成差役法,差将校、官员或使臣殿侍军大将管押官物,“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间陪备亦少于向日,不至有破家产者”,这样的想法有一些问题。熙宁以前差充衙前之所以“最号重难”,并不完全因为赔偿押送纲运中所失官物,“既已充役,入于衙司,为吏胥所欺,縻费已及百贯,方得公参。及差着重难纲运,上京或转往别州,脚乘、关津出纳之所,动用钱物,一次须三五百贯;又本处酒务之类,尤为大弊,主管一次,至费一千余贯”。(29)(宋)郑獬:《郧溪集》卷一二《论安州差役状》。应役期间衙前日常花费在募役法时也都由官方支付,元祐三年新役法即规定:“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3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五七,第7829页。总体来说,若差役衙前,乡户陪备(赔费)并不止于对“失陷官物”(31)(宋)郑獬:《郧溪集》卷一二《论安州差役状》。的偿还,其他支出亦不在少数。另外,差将校、官员等管押并不现实,知枢密院章惇曾质疑说:“自行免役法后来,凡所差将校干当厨库等处,各有月给食钱。其召募官员、使臣,并差使臣、将校、节级管干纲运官物,并各有路费等钱,皆是支破役钱。今既差役,则无钱可支,何由更可差将校管干,及召募官员管押?”(3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三五,第7816-7817页。主要因为司马光主张停收免役钱,并未说明如何支酬管押的官员。苏辙就曾指出:“若依旧法,用坊场酬奖衙前,即未合召募官员、军员、将校等押纲,用何钱支遣?若无钱支遣,即诸般重难还是乡户衙前管认,为害不小。”(3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四,第7821页。这样的话,乡户衙前的负担甚至比熙宁以前还要重,衙前工作只会更加麻烦。司马光的解决办法是按一定的标准征收助役钱来召募衙前,并且“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这样的酬奖标准显然过低,这也是元祐初年朝臣关于役法改革争论的热点。
用助役钱来支给衙前应该和差役法下让衙前经营场务作为酬劳有些差别,但也和雇募衙前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废除免役钱。针对此事,新设置的详定役法所曾给出一些解释:
元祐元年闰二月十五日,详定役法所言:“司马光奏请天下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令、佐揭簿定差。今看详,欲乞下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场、河渡钱,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除合召募外,并行定差。其差衙前有妨碍,或别有利害,许依闰二月四日指挥施行。”从之。(3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一七,第6252页。
十六日,详定役法所言:“乞先次行下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场、河渡钱物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本所再详‘雇募’二字,切虑诸路承用疑惑,却将谓依旧用钱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为‘招’字。”从之。(3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一九,第6254页。
此处说“衙前一役先用坊场、河渡钱物依见今合用人雇募”,即是熙宁新法下的雇募投名衙前的意思,详定役法所基本接受了司马光所谓先雇募再差役的措施,这里解释改“雇”字为“招”字的原因是担心诸路产生疑惑。事实上,元祐变法时是雇募还是招募,执政者或详定役法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里担心诸路产生疑惑的主要原因是现在的雇募并非完全用现钱雇募充役,应该和此前熙宁役法的雇募有所不同。在宋人眼里,雇募即出钱招人来干活,雇钱即庸钱,是必须先期准备好的本钱,由官方组织雇募活动,即为官雇。熙宁二年(1069)八月十六日,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36)(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第4299页。苏辙的说法并无过错,后来募役法下应役户出免役钱即为解决差役的问题,雇募投名衙前的庸钱主要来自于官府经营场务收益的坊场、河渡税钱。元祐役法更革之时,详定役法所言欲改“雇”字为“招”字,苏辙即指出:“众谓此法既不以钱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37)(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八《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十三日)》,第666页。苏辙所谓“以钱雇人”,指募役法以钱雇人,元祐初年的招募并无相应的专项经费支持。苏辙曾细致地估算:“盖见今诸路,每年所入坊场、河渡钱,共计四百二十余万贯,而每岁所费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纲钱,共计一百五十余万贯,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纵使坊场、河渡价钱,别行裁减,不过比见今三分减一,则是所费亦不过所入之半。”(38)(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八《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十三日)》,第666页。但元祐役法筹划者“未委每年所得坊场、河渡钱四百二十余万贯,除支酬衙前重难及雇募押纲钱外,其余欲将何处支用”,(39)(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八《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十三日)》,第666页。“今坊场既已抅收入官,必无人愿充长名。则应系衙前,并是乡户,虽号为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投名,与差无异”。(40)(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八《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十三日)》,第666页。这里基本弄清楚的是,苏辙理解的雇募衙前要支出现钱,坊场、河渡钱用于支酬衙前应绰绰有余,但坊场已由官府经营,长名衙前无利便无人投充,乡户衙前仅仅以免役之利而投充,和差役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苏辙等人对司马光招募衙前意见的置疑,司马光也对他最初提出的衙前招募法做了修正,他说:“若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自可支酬衙前重难分数得足,则官户等更不须出助役钱。从来诸州招募人投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此自是旧法,今来别无更改。惟是旧日将坊场、河渡所折酬长名衙前重难,令自出卖。今官中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分数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只此与旧法有异。若乡户差足,续有投名者,即先从贫下放乡户归农;即乡户愿投,亦听。”(4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五四,第7827页。司马光的解释旨在说明现在招募长名衙前和熙宁元年乡差长名衙前的区别是支酬出卖坊场、河渡钱的方式不同,长名衙前自卖与官卖的结果似乎差不多。这种解释看似区别了招募与雇募的同一性,实则模糊了招募衙前的役法背景。那么,是否可以将招募与雇募划等号呢?笔者认为两者本质上是有所差别的,司马光所谓“官中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分数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即是熙宁四年施行募役法时雇募衙前的意思,这和募役法施行前差役法下招募衙前支酬其坊场经营权并不相同,根本差别是差役法与募役法时代背景的差异。事实上,熙宁役法变革之前的差役法下长名衙前或乡户衙前的投充也是官府招募而非雇募。据史载:“皇祐中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使募人为之。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4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3页。募充的酬奖是坊场酒榷经营权,司马光所谓“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即指招募长名衙前不足便可按这个酬奖标准定差乡户衙前,减免或免除投名衙前的坊场税钱,即是旧法招募衙前的酬奖方式。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元祐元年司马光主张废除免役法的最初思路是恢复到熙宁役法改革以前的差役法,这样的役法背景下衙前断不是雇募,招募一词是符合这样的役法背景的,但与熙宁役法行用多年的社会背景相矛盾。元祐元年司马光上台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国家财政吃紧,坊场、河渡的官营断不可再恢复到新法改革前由衙前私营,若这样便无法支酬衙前,遂遭到苏轼兄弟等人的反对,最终元祐衙前役法是官雇制,只不过哲宗亲政以前是在差役法背景下施行的衙前官雇制,与熙宁四年制定的募役法有所不同。
有学者曾指出,衙前役对应役者的财产要求颇高,且在仁宋时期已经采用先投名,不足方轮差的原则,有能力与意愿代役之人一般已经通过投名入役,博取坊场酬奖。(43)黄敏捷:《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所谓通过官方投名代役,即由招募方式承担长名衙前工作,这种衙前应役者的财产丰厚,投入风险系数高,对回报的诉求也高。坊场优酬的比例或标准直接受到不同区域生活水平的影响,以致元祐役法下便遇到一些招募衙前并不如意的情况。
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十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云:“大抵支钱既足,万无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宁以前,无一人阙额,岂有今日顿不应募?臣今起请,欲乞行下诸路监司守令,应阙额长名衙前,须管限日招募数足,如不足,即具元丰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来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钱雇募,即与本路监司商议,一面施行,讫具委无大破保明闻奏。若限满无故招募不足,即行勘干系官吏施行。”(44)(宋)苏轼:《苏轼全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9-1220页。苏轼认为招募长名衙前效果不好的原因是支钱不够,需要添钱雇募,当闻奏施行。次年九月,苏辙也上奏说,元丰以前官雇役人规避了私下雇人的弊端,最好还是恢复元丰以前官雇钱数,“纳钱入官,官为雇人”。(45)(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五《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第790页。据此可见,元祐役法中所谓招募,表面上手段与雇募差不多,朝臣们也没有对两者概念进行区分,仅论两者效果的差异。从元祐差役法敕行时王觌提议,即使出卖坊场钱支酬重难分数,“或内有不愿依旧投名之人,重别召募不行,方得乡差”,(4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三九,第7819页。到元祐四年苏轼提议“若愿就长名,则支酬重难尽以给之,仍计日月除其户役及免助役钱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钱支募”,(47)(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第4323页。在朝臣们理解的支酬重难的坊场钱、河渡钱之外另当优待,这都和熙宁三年吕惠卿提出的官卖坊场钱、免役钱支酬衙前重难看起来相似。另外,由于衙前招募效果不佳,朝臣们也曾提议“合以旧支雇食钱添入重难分数”,(48)(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五《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第785页。也是增加支酬标准刺激投名者的手段。
笔者认为,元丰以前的雇募衙前和元祐时的招募衙前效果不同的关键是,司马光旨在否定熙丰新法,尽管允许优先招募衙前,但仅用坊场钱、河渡钱衙前支酬重难,投名不足时可贴补的助役钱也有所折扣,这都造成招募衙前时激励应役人的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募役法下“以免役钱雇投名人,以坊场钱为重难酬奖”,(4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三,第7821页。坊场、河渡钱支酬衙前不足还可使用六色助役钱补贴,(50)元祐元年九月十七日,宋哲宗下诏:“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皂迓送飱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钱助用。”(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第4320页。这样的衙前支酬必然对应役人产生一定的吸引作用。之所以元祐时改“雇”为“招”,实际上并不惟此,而是在宋儒看来,元祐役法必须有别于此前的募役法才是关键。元祐元年(1086)二月,宋哲宗曾下诏令将苏辙奏折送役法所审定,选择其中较为重要的先行实行,“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51)(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第4316页。差雇兼行下衙前并不都需雇钱实际上并不是改“雇”为“招”的关键,本来雇募衙前时才支雇钱,这和定差衙前不出雇钱并不冲突,关键是助役钱和免役钱都免输了。马端临曾评价司马光言衙前当招募时说:“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既曰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于官,当役者合输之。”(5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5页。但司马光又主张废除免役钱,尽管可向坊郭上等户征收助役钱补助,应役人出钱雇募的内涵已不复存在,只是一种名不副实的官雇制,所以宋廷改“雇”为“招”可能只是为了区别于熙宁募役法下的雇募制而已。
有学者曾指出,元祐初,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与此相应,也提出了服衙前役者仍旧恢复重难役人的坊场酬奖制,但对衙前未能完全恢复旧时酬奖法,尽管仍然以现钱计值支酬衙前,依然是用免役法,官府采用同等额钱优先衙前和先交十分之七额钱的办法加以照顾,但并未能完全恢复熙宁变法前的旧制,元祐中衙前重难只有部分恢复到熙丰之前的旧法,在实际生活中,民户买扑坊场和衙前经历重难之后,仍然采用熙宁、元丰时期的实封投状法。(53)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单纯就“招募”一词而言,可能并非具体募法意义上的特殊名词,而是指一种笼统的招引、募集方式。熙宁年间,募役法施行时司农寺即言:“始议出钱助民执役,今悉召募,请改助役为免役。”(5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51页。所以,我们追究“雇募”和“招募”的差别,可能最后落脚点仍在免役法上,免役法的兴废与否,实在关系到北宋役法的成败兴衰。
三、助役或免役:衙前役法变奏的两个维度
无论是衙前“雇募”或是“招募”,都关系到国家财政支出问题。元祐元年二月,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哲宗乞罢免役》云:“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55)(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8页。此“助役法”即为“免役法”,旨在解决衙前重难问题。熙宁以前差役法下只准许个别地区招募长名衙前,并未完全解决里正衙前或乡户衙前轮差面临的压力问题。
一是招募长名衙前的地区并不统一。据史载,景祐中,宋仁宗下诏:“川陕、闽、广、吴、越诸路衙前仍旧制,余路募有版籍者为衙前。”(5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2页。有学者还指出,在北宋时期的差役中(这里主要论述熙宁变法前已转化为劳役、成为充役户负担的那部分差役),从承担差役的乡村上户到代表本地区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僚,从各种改革差役的建议到部分差役的具体实施,都多少存在着一条隐约可见的南北区域界限: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和川蜀地区乡村地主上户,在承担差役上多倾向以钱代役;北方地区乡村上户接触和得到货币的机会少于南方乡村上户,对于那些可以“身自出力”的差役,就宁愿以“正身充役”。(57)王棣:《北宋差役中的南北差异》,《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二是应役者免役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先是里正衙前轮差过程中遭遇重难以致破家,成为宋廷最为棘手的役法问题。至和二年(1055)夏四月,罢诸路里正衙前之后由乡户承担衙前工作,衙前重难继续由乡户承担。但若役乡户衙前为长名衙前,主观上解决了招募长名衙前不足的问题,却进一步加重乡户衙前的负担,并且招募长名衙前退化为定差长名衙前,后来官府不得已又下令“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5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3页。其中官府禁止了衙前免役的问题,地方官员“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及得钱,则以给他用,而役如故”,(5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5页。这无疑引起宋廷的注意。庆历元年(1041)八月,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6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4页。致使皇祐中,宋仁宗下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6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4页。里正衙前输钱免役可能有违差役法,乡户衙前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至此可见,熙宁四年十月开始推行免役法当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旨在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应该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据史载:“初,嘉祐中,州取酒场钱给衙前之应募者,钱不足,乃俾乡户输钱助役,期七年止。后酒场钱有余,应募者利于多入钱,期尽而责,乡户输钱如故。”(62)(宋)曾肇:《曾舍人巩行状》,载《全宋文》第110册,第93页。酒场钱即坊场钱,招募衙前支酬坊场钱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所在州坊场钱若不足,由乡户输助役钱,确实也是无奈之举,问题是坊场钱足以支酬衙前时民输助役钱如故。权且不论免役法如何解决乡户输助役钱得到补偿,此处助役钱实在是意义非常。检阅文献我们发现,熙宁免役法推行之前,宋廷准备颁布的是助役法,司马光尤言:“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6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五,第6245页。又据史载:“(熙宁三年)助役法行,诏诸路各定所役缗钱。”(6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四四《鲜于侁传》,第10937页。熙宁三年(1070)九月八日,“(曾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65)《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一,第1088页。此即可见,“助役法”之名应该是存在过,尽管有时候和免役法混为一谈,但其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熙宁四年免役法确定之前,助役法曾是役法改革讨论的热点,这种募役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已切实得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免役钱”“助役钱”已是该种募法的主要内容。(66)按蒋静作《吕惠卿家传》云:“公以为今欲除去宿弊,使民乐从,然所宽优者,则乡村朴惷不能上达之甿;所裁取者,则仕宦并兼易致人言之豪户;以至衙司、县官皆恐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新法之行,尤所不便。官吏既不能明见法意,抑又惑于言者之多,筑室道谋,难以成就。于是为牒具析所以措置施行之状,极于详尽,檄诸路监司,使之如法推行。卒罢差役法,令当役人户以等第均出,曰‘免役钱’,而一切募人充役,随本役轻重以钱给之。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者,皆以等第均出,曰‘助役钱’。”(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第5130页。考吕惠卿熙宁三年五月十七日判司农寺,同年九月一日母丁忧离职。熙宁三年九月八日,曾布同判司农寺。那么,吕惠卿提出“免役钱”“助役钱”当在免役法颁布之前。熙宁四年十月,司农寺上言:“始议出钱助民执役,今悉召募,请改助役为免役。”(6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51页。旨在说明“出钱助民执役”,只是对募人执役的一种帮助,是一种不彻底的募役手法,并非免役法那样通过出钱免除自身应役的义务。(68)有学者认为,主户向官府交纳役钱,由官府以役钱雇自愿之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宋人称之谓“免役法”“助役法”“募役法”“雇役法”等。参见黄敏捷《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混淆了“免役法”与“助役法”的差别,若是同一役法不同称呼,司农寺何以改“助役”为“免役”呢?反对免役法的刘挚曾说:“为官自雇人之法,率户赋钱,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69)(宋)刘挚撰,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忠肃集》卷五《论役法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8页。这样的说法几乎搪塞了助役与免役之间的区别,主要原因是其对役法中应役义务的曲解或对阶层固化意识的坚守。在免役法颁布之前,熙宁四年五月,东明等县百姓诣开封府投诉地方官超升等第出助役钱的问题,甚至后来“突入王安石私第”,此事的直接影响是超升等第可能成为助役法的最大诟病。同月十九日,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70)(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第4301页。同年六月,他在《上神宗论助役》中详细解释说:“退而访闻得司农寺超升等第因依,乃是不依逐县元定户活等第,却从司农寺将见管户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抛降与逐名令管认,户力次第升降,重别造成笺簿,依条限晓示人户知委,须管于农务前了当。臣今举一县以言之。只如酸枣县,乡村第一等元申一百三十户,今司农寺抛降却要二百四户,即是升起七十四户;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户,今司农寺却抛降三百六户,乃是升起四十六户;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户,今司农寺却抛降四百五十九户,乃是升起一百二十户。”(71)(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2页。
除了超升等第之外,助役法中户等的认定也多被诟病。先是同年七月,杨绘提出质疑:“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顷者,少至三顷者,皆为第一等,百顷之与三顷,已三十倍矣,而役则同焉。今若均出钱以雇役,则百顷者其出钱必三十倍于三顷者矣,况永无決射之讼乎!”(7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六至七,第7800页。御史中丞刘挚连上《上神宗论助役》《论助役法分析疏》《论助役法分析第二疏》,列出助役法十害:“敛钱用等以为率,则非一法之所能齐”,“旧籍既可不信,则今之品量何以得其无失”,上、下户之役不同则“优富苦贫”,“不取旧簿者,意欲多得雇钱”,“助钱非若赋税有倚阁减放之期”,“助法皆用见钱”,“及起庸钱,竭其所有,恐人无有悦而愿为农者”,“使国家受聚敛之怨”,“雇直轻则法或不行,重之则民不堪命”,“今既雇募,恐止得轻猾游浪奸伪之人”。(7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三四至三六,第7883-7884页。他指出:“今司农新法,乡户衙前更不差,其长名人并听依旧以天下官自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以酬其重难。臣谓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自来以承应官中配买科率,亦难使之均出助钱外,场务给衙前对折役过分数多估价不尽,亏官实数。……助役之法,望一切寝议。”(7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三六,第7884页。杨绘、刘挚皆指出助役法户等确立问题,五等户分法肯定存在不均,早在仁宗朝差役法下差衙前役即推行“乡户五则之法”,(75)据史载:“(皇祐中)知制诰韩绛、蔡襄亦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机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财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第4297-4298页。与此五等户应出助役钱如出一辙,但这两位御史中丞均选择性淡忘了,其根本原因是助役法触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其说是反对助役法,倒不如说是反对应役者身份的重构。刘挚所谓坊郭十等户不应再出助役钱,实则是反对六色助役钱的支出,反对向官户、寺观等特殊户征收助役钱。吕惠卿设计征收助役钱时规定:“凡坊郭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有产业物力者,旧无役,今当使出钱以助募人应役。”(7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第5521页。联系刘挚反对坊郭十等户出助役钱,以及他对役法下户等制的质疑,显然表明了他对特权阶层利益的维护。刘挚对役法不满的表面对象是助役法,实则“以为使天下百姓赋税贷债公私息利之外,无故作法,升进户等,使之概出缗钱,皆非为人父母爱养基本之所宜为者”。(77)(宋)刘挚:《忠肃集》卷三《论助役法分析第二疏》,第58页。曾布曾对此作过回应:“臣观言者之言,皆臣所未谕,岂蔽于理而未之思乎?抑其中有所徇,而其言不能无偏乎?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7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九,第7801页。两者的出发点之差异集中体现在役法是否为国创收或节省,是否为民所乐受。遗憾的是,反对新役法者根本未曾思考过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仍以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作为久安的根本。
熙宁四年,宋神宗召二相到资政殿轮对,冯京认为:“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宋神宗则说:“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认为:“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宋神宗却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说,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则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7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7页。文彦博的说辞毫不掩饰役法反对者的价值判断,但役法反对者在论及雇募衙前时却少有异意,所以并不借助吐槽“助役法”来否定出钱雇募衙前的免役政策。元祐更革之际,司马光所提的助役法即为免役法,只不过他在半恢复差役法的情况下坚决停止征收免役钱,对助役六色钱的征收对象也重新确定了户等,也可以说是废止了应役者出钱雇募实现应役身份转移的途径。
至此可见,助役法者,主要指按既定户等交纳助役钱,用于招募人投名应役,“从司农寺将见管户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偏重于考量户等及助役钱数;(80)据史载:“自熙宁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势以至僧道、单丁该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输钱,无所谓复除矣。然数者之输钱,轻重不等。”(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二》,第389页。熙宁四年四月下旬,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于大均之域,或有羡余,即以待水旱之岁,免取于民,此虽尧、舜之用心何以臻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乙未,第5421页。理想的助役法显然可以解决差役之不均的问题,其方案是淡化户等,稍显公允。但在免役法将施行的时代背景下,确定户等征收助役钱,若户等不均必然损害上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一如差役法时一样。柳田节子即指出,宋代的户等制在职役科派方面最具体地发挥它的机能。参见[日]柳田节子《宋代乡村的户等制》,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代宋元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1页。王明荪亦认为,宋初对役法稍具改革性的言论,最初是以定户等之议开始。参见王明荪《北宋中期以前役法的改革论》,载《宋辽金史论文稿》,(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版,第144页。免役法者,主要指应役户出钱免役,政府代为雇募人完成应役任务,“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偏重于遵从投名者的自愿性和应役户应役任务的转移。宋朝政府改助役为免役的原因:一是回应反对助役法的声音,以及平息由户等不规范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免去上等户重役之苦,征收六色钱以求公允;(81)宋晞:《宋代役法与户等的关系》,载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77页。一是激发应募者的积极性,落实应役户责任属性,切实解决北宋赋役问题。当然,这其中衙前这种职役问题是役法变革的首要问题,也代表着役法变革的趋向。有学者曾考述:
宋初行差法,役之名色虽多,重难者厥惟主官物押纲运之衙前。衙前本以厢军充任,资深者既有酬奖,又可得官。此种人久在公门,干练者多。地方长吏以其不易欺也,乃违法点差催税里正以代之,是为里正衙前。浸假而各地里正遂成包拯所谓之“准备衙前”矣。里正衙前,来自乡村,质实椎鲁,动被鱼肉,于是因役而倾败者前仆后继。至和中,用韩琦议,罢里正衙前,改差一县赀高者为乡户衙前。然此知二五不知一十之办法,终未能解决衙前之痛苦,故不十年,乡户衙前又多以破产闻。由是司马光等纷纷论列,而有以坊场河渡钱雇募长名衙前之制,继乃有王安石募役之法。是以差役之弊,胥为官吏枉法苛虐之所致也。(82)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68-269页。
按“以坊场河渡钱雇募长名衙前之制”,解决了差役乡户衙前造成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问题,(83)孙毓棠先生曾指出,衙前之役充分反映了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参见孙毓棠《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简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张熙惟先生认为,衙前制的这些变更,实质主要在于解决乡户轮差,主要解决乡村上户即地主阶层服役的问题。参见张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李志学先生也认为,上下户之间的界限, 实际上是地主与农民的两个对立阶级的界限。参见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应役乡户免除衙前工作当是其关键,助役钱是否用于酬其重难并不是主要问题,助役钱并没有因为更名助役法而废除,但上等户如何均衡承担衙前重难,也是免役法解决的关键问题,更是平息由户等不规范带来的矛盾与冲突的关键。针对宋人丁怀与胡真的纠纷,陈襄曾在免役法颁布前夕提出:“乞今后自未降雇役新法以前,如外州军亦有似此差长名衙前及纠决别户,且依差乡户衙前勅条。有替罢衙前及五年以上、见系物力最髙如第一等人户数少,即许依空闲人户例定差。所贵上等色役之人,苦乐均济。”(84)(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六《乞均差衙前等第状》,载《全宋文》第50册,第36页。陈襄所期待的雇役新法即是解决应役衙前者户等纠纷的关键,这也是宋廷回应杨绘等人的初衷所在。(85)元祐年间,张行在反对恢复差役时亦说:“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以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纳,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元祐三年二月丙戌条,第9931页。也有学者认为,全部执役人都通过自愿应募而来,不再要求三等以上税户执役,欲借此打消三等以上主户对自己既需交役钱又需应役的疑虑,这当是曾布奏改助役为免役的着眼点。参见黄敏捷《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第48页。
尽管免役法与助役法形式相近,但由“助”变“免”解决了役法不均及衙前之大弊。元祐更革之后,恢复差役法的语境下,尽管废除免役钱仍称助役法,但衙前雇役之实却不可更易。正如苏辙所言:“然则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余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86)(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五《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第784页。
余 论
北宋衙前役法牵涉问题繁多,前后称谓易混、概念矛盾者皆如前文所述。“长名衙前”并非“投名衙前”,前者是种衙前称谓,后者仅可理解为一种应役方式,投名者自愿也。“长名衙前”和“里正衙前”“乡户衙前”均属衙前称谓,通常可以理解为长名衙前多由乡户通过投充方式来应役。不过,募役法下相关文献表述中多见“投名衙前”,有时也被指代为“雇募衙前”,因为募役法下官方主持雇募衙前或招募长名衙前,多由乡户自愿投充。据此可见,投名与否和役法性质并无关系,“长名衙前”作为一种自愿性质的衙前,在募役法前后及其施行中都颇为常见,因为这种衙前规避了衙前重难问题,受到官方欢迎。除此之外,不难发现,“投名衙前”与“长名衙前”性质上的差异并没有遮蔽其同一的自愿性。既然是自愿,那么北宋衙前役法当中的差役、募役之别又该如何理解?
一如前文所论之结果,元祐元年司马光主持恢复差役法,改衙前“雇募”为“招募”,实则是为了表明差役法下衙前役法有别于熙宁募役法下的衙前役法,并且为停征免役钱提供一个虚伪的役法环境。事实上,“招募”一词并不单适用于元祐役法改革时,熙宁募役下也常见招募衙前的说法,甚至北宋初期差役法下长名衙前也是通过官方招募来实现。但三个阶段的招募有所不同,熙宁募役法以前的招募制度仅针对长名衙前,并且酬奖以酒坊经营权,是差役法下较为变通的衙前役法模式,属于坊场税与衙前重难工作交易制;而募役法下官方代应役人招募衙前,并不惟长名衙前,酬奖包括坊场钱、河渡钱、免役钱等,属于代雇式的雇募制;元祐役法改革时招募衙前,是通过官方经营场务现钱来酬奖衙前,属于官雇制。正因为“招募”一词屡见于北宋诸时期役法活动中,研究者多未曾深究其意,遂多将“雇募”与“招募”等同视之,便认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为免役法,其他时期多为差雇并行,(87)王曾瑜先生认为,北宋前期至中期衙前入役差募兼行。参见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一)》,第78页。甚至有学者认为熙丰时期少数坑冶作为“酬奖”令衙前经营,或派衙前承办坑冶,衙前作为“主吏”也是“当役者”,是一种招募制度。(88)魏天安:《熙宁、元丰时期坑冶“召募制取代劳役制”质疑》,《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笔者认为,“招募”只是衙前入役的方式或行为,同“投名”类似,前者为官方行为,后者是私人行为;而“雇募”是种役法手段,确定了应役人与代役人的关系。回头来看元祐元年改“雇”为“招”,并不是简单的近似词汇换用,必须从北宋役法变革的大背景来分析,这里同样关联到衙前役法中屡见的“助役”与“免役”两个易混淆概念。
熙宁四年免役法(募役法)颁布时司农寺曾上言请改“助役”为“免役”,这之前反对新法的杨绘、刘挚曾接连上奏指摘“助役”的不便,元祐元年改革役法时司马光又称,先前为了解决衙前重难问题才颁布了“助役法”。“助役法”一词在元祐役法改革时也被提及,是否借此指代“免役法”不得而知,至少可见作为一个役法名词得到了执政者的认同,并非有些学者所谓“助役法”只是“免役法”的最初版本,是一种差雇兼行的办法。(89)黄敏捷认为,“助役”其实是一种差雇兼行的办法,实施过程复杂,官吏容易上下其手;对于上三等户来说,既要出役钱,又要应州县役,容易落下既出钱又不免役的话柄;在东明县民上访事件前后,众臣包括曾布在议论役法时,“免役”一词只是针对当役户说的,当说到整个雇役制度时,用的都是“助役”一词,但司农寺奏行免役法之后,其余人尤其是反对变法的大臣们都还在用“助役”一词时,曾布已经改口为“免役”了。参见黄敏捷《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第48页。笔者觉得,“助役法”若是差雇兼行的办法,当与免役法不同,杨绘、刘挚反对究竟是前者或是后者,显见疑惑;另外,“助役”一词若只是杨绘、刘挚未及改口的称谓,因何元祐役法改革时又被他们习惯性提及。助役法因何在前后两个时代遭遇两种不同的待遇,这其中牵涉到的仍是免役法的性质问题。熙宁助役法面临的问题是户等核定标准有时无法体现公平性,在此基础上征收助役钱便成为害民之弊,并且助役钱的征收涉及到了特权阶层,助役法解决问题的方向仅是役钱,遂成为反对者攻击的对象。由“助役”改为“免役”,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明晰了役户的责任属性,应役户并不包括特权阶层,役钱则全面征收,征收数额差别化,在相对的社会公平下切实解决了北宋赋役面临的问题。从两种役法称谓的差别来看,应役者出钱雇募实现应役身份转移,或代役者角色的法理化,当是北宋役法演变过程中的一抹浓彩。
衙前役法在元祐元年役法改革后经历的循环波折演变,是因为衙前问题关系到地主阶层矛盾问题,(90)张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元祐役法改革后施行的招募衙前制度,只是建立在差役法的基础上实行的官雇制,尽管仍以六色钱补助,但酬奖重难总量大幅缩水,之后虽然有所补充,仍以长名衙前为主,但衙前名额终究无法核定。哲宗亲政之后恢复元丰免役法,衙前役仍雇募。衙前役法屡改屡变,甚至牵涉整个役法变革,其主要原因是衙前经历重难后往往赔费,轮差衙前难免造成乡村形势户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衙前役都有赔费风险,里正衙前和乡户衙前赔费高于长名衙前,所以熙宁前后士大夫们对该问题的反应有强弱之别。(91)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赔费差别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决定衙前役法更革的关键,能否从物质方面激励应募者或代役者,是否从社会角色转移方面解决应役身份转移,才是问题的关键。以坊场经营权酬奖衙前,也有经营不善导致破产者,但官方直接以坊场税钱招募衙前,激励效果当十分明显;社会角色转移,政府和民户在相互选择中实现劳务购买关系,(92)有学者即指出,宋朝的衙前役从差雇并行到最终的只雇不差,是当时社会商品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和民户相互选择的最优方案,政府利用财政收入,支付一定的费用,购得所需的劳动力,从而扮演了购买者的角色。参见黄子卿、李晓《宋朝衙前役演变的博弈论分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从而创造制度红利。
当然,衙前役法演进过程中,并不能抹煞衙前作为乡村形势户的事实,但也不能回避衙前经历重难后多破产的事实;(93)王曾瑜先生指出,宋朝职役具有复杂的性质,就乡村和城郭上户角色来说,吏役主要表现为吏的属性,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特权;就乡村下户甚至某些上户来说,吏役又表现为役的属性,作为一种受官府压迫的负担。参见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二)》,第55页。既不能抹煞衙前役与其他役之间的差别,更不能回避它与役法大背景的协同性。所以说,北宋衙前役法的演进,使得深层次挖掘和认识北宋中后期役法改革成为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