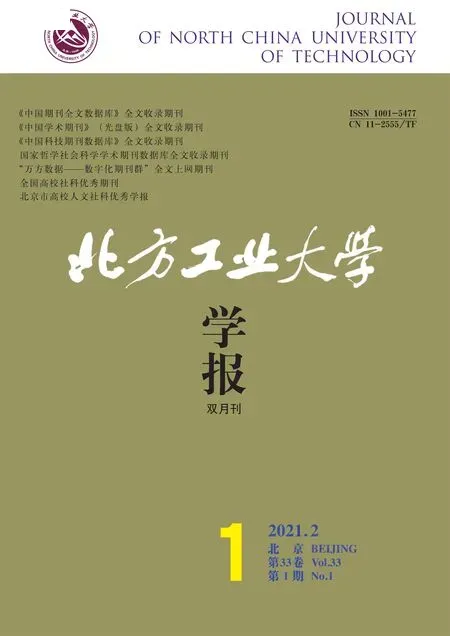清代平定碑告成太学考*
2021-11-23黄茜茜
黄茜茜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100007,北京)
元代实行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尊孔崇儒的形式多样,规模也超越了前代。[1]大德六年(1302)六月朝廷开始修建北京孔庙,大德十年(1306)八月,在今址正式建庙。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此举虽与其心腹阎复的提议有关,但主要目的是借助孔子的儒家思想,笼络汉族官僚和士人,以维护蒙古对中原汉地的统治。
明朝建立后,洪武皇帝朱元璋继承了元代尊孔重学的思想和政策,洪武二年(1369)下诏云:“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2]朱元璋在治国策略上兼用儒、释、道,但在体现国家主体意识形态的祭祀体系上则坚定地秉承儒家思想。他任用儒学名士制礼作乐,所制定的国家祭祀制度均以反映儒家治国理念为中心。[3]
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嘉靖皇帝“易孔子神位用木主,奉安于文庙,遣国子监祭酒许诰行祭告礼”[4],即通过降低祭物规制,将孔子置于儒师、君师而非王者的地位予以尊崇,避免孔子在祭祀体系中与君主的地位出现冲突。说明当时的孔庙只是作为朝廷继承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不可与君权相提并论。[5]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清朝比明朝等汉族王朝更迫切强化非汉族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推崇作为正统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获得汉人尤其是士大夫们的认同,消解民族对立的隔膜。康熙皇帝也是首位亲自去曲阜孔庙拜谒并行“三跪九拜礼”的帝王。
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朝皇家祭孔的场所,现存的碑刻不仅有赞颂孔子及颜、曾、思、孟等四圣的赞碑,记述祭礼活动、修葺孔庙的纪事碑,还矗立着七座告成太学碑,不但具有宣扬国威的作用,也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清代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艰辛与辉煌。
已有学者对国内其他省市的平定碑进行过研究但目前少有人将北京孔庙的告成太学碑作为专题,对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6]在新的历史时期,告成太学碑在宣告武功、界定疆域、统一舆论等方面的重要性应得到更多重视,从而推动学界对清代平定西北边疆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本文以北京孔庙七座告成太学碑为研究重点,在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对碑刻内涵及为何立碑于太学进行考证和梳理。
1 清代平定碑缘何立于太学
太学是汉代以来在京师设立的中央最高学府,清代则从隋朝的改名,称为国子监、国子学,是元、明、清三朝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在一些复古的场合,又以太学相称。唐代以来,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确立了“庙学制”的学政合一形式。[7]
随着太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的舆论导向具有制衡现实政治运作的精神力量。朝代嬗递之际,汉族儒家文人弟子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都发生着变化。清朝帝王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以尊孔崇儒为切入点,笼络汉族士子以免他们以“尊孔复明”的理由反清,有利于巩固清朝统治根基。汉族知识分子也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走上执掌国家、地方的仕途。
《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中载:“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释眚灾,洁事禋望,为亿兆期升平之福,而大臣们请纪功太学,垂示来兹。朕劳心于邦本,尝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顾兹武略,大臣们佥谓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绩于有永也。朕不获辞,考之《礼记·王制》有曰:“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而泮宫之诗亦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又《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奏凯乐,大司乐掌其事。”则是古者文事、武事为一,折冲之用,俱在樽俎之间,故受成、献馘,一归于学,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向意于三代,故斯举也,出则告于神祗,归而遣祀阙里。兹允大臣们之请,犹礼先师以告克之遗意,而于六经之指为相符合也。爰取“思乐泮水”之义,为诗以铭之,以见取乱侮亡之师,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实,或者不戾于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尔”。[8]
康熙皇帝托辞因大臣们的请求才进行告成碑的撰写,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前提下为武力征伐,开拓边疆的举措寻找合理的解释,阐明立碑于太学是依托《礼记·王制》中对天子出征的军礼规定。“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9]康熙皇帝严格遵循儒家经典礼记,还原周朝礼仪制度。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写道:“(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上复勒铭狼居胥之山而还。朔漠平,至京师御门受贺,上亲撰碑铭,勒石太学。古帝王武功,或命将,或亲征,惟以告于庙社,未有告先师者,在泮献馘,复古制,自我圣祖始。”阐明过去的皇帝功成归来,奏凯献俘,一般都是告成于太庙和社稷坛,从不曾告成于太学。
综上所述,康熙皇帝首次将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绩立碑告成于太学的原因一是昭示天下,宣扬国威;二是恢复《礼记·王制》中的完整释奠制度,具有继承和弘扬传统王朝礼制的寓意;三是利用北京孔庙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来强调官方意识形态。
2 清代告成太学碑碑文内涵和形制
这七座大理石材质的告成太学碑均为螭首龟趺式,由螭首、碑身、龟趺、海墁等部分组成。海墁之下为整石雕刻的海水江崖纹长方形地衬。碑首阴阳两面均屈身盘踞两龙,龙头垂于碑首两侧,两龙腹部缠绕处的位置即为额题所在,内侧前肢对称上举,捧祥云托宝珠。碑身左右边框饰二龙戏珠,上下边框饰有行龙图案。碑文除皇帝御笔外,均为清代官方馆阁体。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位于大成殿西北,是清代在北京孔庙立的首座“告成碑”,康熙皇帝撰文并正书,碑阳满汉文合璧。碑文内容讲述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击溃噶尔丹蒙古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事迹。纵观康熙朝发生的历次平定战争,由康熙皇帝亲自上阵指挥的仅是此次征剿噶尔丹之战,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
康熙皇帝将平定碑立于太学之举被雍正皇帝所继承。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位于大成殿东南。雍正皇帝撰文并正书,碑阳满汉文合璧。碑文先追溯了康熙皇帝征讨朔漠的杰出功绩,再叙述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和奋威将军岳钟琪的战绩。碑文载“廷臣上言,稽古典礼,出征而受成于学,所以定兵谋也;献馘而释奠于学,所以告凯捷也。宜刊诸珉石,揭于太学,用昭示于无极,遂为之铭曰……”[10]以因有廷臣之请而宣扬勒碑于太学的正统性。碑文中“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诺木齐等三人献俘庙社,受俘之日,臣民称庆”讲述了战争胜利后举行了献俘仪式,此事在《清史稿·礼志九》中也被提及“清初太祖、太宗以武功征服边陲,俘虏甚众,其时献受犹无定制也。雍正二年,讨平青海,俘至京,始定诹吉先献庙、社。”说明清朝初年战事频繁,俘虏众多,却不曾制定献俘礼,雍正二年(1724)成功平定青海之际才确立了献俘典礼。
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皇帝撰文,梁诗正书丹,碑阳满汉文合璧,将“大臣们举皇祖朔漠、皇考青海成例,请勒碑成均,以示来许”[11]作为立碑缘由。碑阴为乾隆皇帝御笔《御制释奠诗》,分别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初五和二十一年(1756)二月初九。
碑文中主要描述傅恒、岳钟琪领兵最终平定大金川的战绩。碑文中存在粉饰之词,如“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义同休戚,毅然请肩斯任”,夸赞傅恒在危急关头主动请缨出征,与历史文献中记载乾隆皇帝指派傅恒出征的史实之间存在出入。
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皇帝撰文并正书,碑阳满汉文合璧,碑阴刻有满汉文版本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和乾隆二十三年(1758)七月的《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碑文载“武成而勒碑文庙,例也。礼臣以为请,故据实事书之。”[12]溯源于康熙和雍正的成例并将立碑原因归结为众臣有此请求的盛情难却。碑文记述康雍两朝陆续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的概况及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达瓦齐的情况。
碑文中反驳了人们对边疆“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的认知偏见,强调“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感慨“昔时准夷,日战夜征;今也偃卧,知乐人生。曰匪准夷,曰我臣仆”认为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虽保留有汉唐宋明等前朝的印记,却有着本质区别,边疆民众不再是“蛮夷”而是大清朝的子民,宣扬西北边疆地域已被纳入清廷所管辖的范围,形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共同体。[13]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皇帝撰文并正书,碑阳满汉文合璧。碑文详细叙述了乾隆皇帝用兵回部的原因、争议及战争经过。碑阴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四日,乾隆皇帝撰文并御笔的《释奠孔子并国学落成即事诗》。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位于大成殿东南方。乾隆皇帝撰文并正书于碑阳,碑阴为满文版本的碑文,讲述二征金川的原因、经过及战争的艰辛。平定大、小金川是乾隆年间耗时最长、耗银最多的战争,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金川地区民族交流与生产力发展,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碑文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而德与功皆赖言以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之时义大矣哉……勒碑太学,用遵成例”阐述文字纪实性的意义及立碑于太学已成惯例。
19世纪的清朝边疆危机日益严峻,道光皇帝前后调兵数万,耗费1000多万两白银才平定张格尔叛乱,并将其生擒后押至北京午门受俘。道光九年(1829)将《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立于北京孔庙第一进院落西侧,这也是清朝最后一座立于北京孔庙的告成碑。道光皇帝撰文并正书,碑阳为汉文碑文,碑阴是满文碑文。碑文载:“我武惟扬,天之所助者顺也。礼曰:执有罪,告成于学。故据事书之。系以铭曰”,依旧以复古周礼为由,勒石太学纪录这次重要政绩。
3 结论
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入关以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识,对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的接受就是重要的体现,凸显他们比之前的皇朝在继承儒学思想等方面更加正统。立碑于太学将清廷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宣扬大清王朝建立新的疆域版图供后人瞻仰,使中国大一统的新局面成为普遍共识。平定碑的演变以及在清代产生的影响,成为后世重新解读清史及边疆民族问题有价值的资料来源。
但告成太学碑的属性是以清廷为官方立场的宣传工具,并非以客观记录历史为目的,碑文中有些内容是在其所归属的时代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的要求之下进行了再加工的“伪真实”,导致清廷的对立方被后世严重误读。如多年来国内学者对噶尔丹策零的评价持否定观点,斥之为勾结沙俄的“叛乱”势力。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应对噶尔丹策零与清廷之间的关系给予客观评价。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撰文讨论,以期对重新解读边疆民族问题有所裨益。
在大一统事业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清朝武力开拓边疆后将告成碑和释奠太学的仪式发扬光大,既有对传统刻石边疆和告于庙社礼仪的继承,又加入了“告成太学”这一创新之举,反映出清王朝在告成礼建置上登峰造极的状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