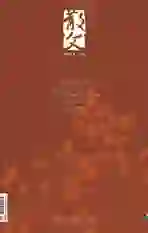闲草志
2021-11-19孙远刚
孙远刚
仙人掌
手边正有一盆仙人掌,样子像一峰骆驼。
虽近在眼前,也天天见面,可我总是忘记给它浇水,一忘就是好几个月。好在它天性耐渴,不需要经常浇水。等想起来浇水,手头正好有茶,我就请它喝口凉茶了事,省得等会儿忘了,一忘又是好几个月。
读汪曾祺先生《昆明的雨》,文中说:“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这盆仙人掌,我用来防辐射,不为辟邪。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条不算太深的巷子里,挂山开门,门朝东,东边丈外就是邻家的西院墙。那时候邻里关系和中苏关系一道紧张,东邻在他家的西院墙上种满了仙人掌。
巷子口有大门楼,门楼顶上,也摆着一丛仙人掌,举着一只只惨绿的掌,森森地吓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东邻所为。
东邻“不栽花栽刺”的行为,让我父母很恼火,也很无奈,这种情绪影响到两家孩子,孩子学大人,见面也不说话,搞得跟斗鸡似的。邻家男孩和我同龄又是同班同学,我们关系很要好,可是有一次,他把一片仙人掌藏进我的书包,我的手被扎得生疼。
仙人掌浑身是刺,有顽强的生命力,又得“仙人”之名,用它辟邪,当然是可以的。现在想来,我家门前的仙人掌,特别是巷子口门楼上的仙人掌,也许并不是针对我们而仅仅只是用来辟邪。我们那沉淀于岁月深处的纠结,也许只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误会。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误会,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现在那条老巷子没人住了,仙人掌早就不知去向,只剩几茎狗尾草瑟瑟在秋风中。
车前子
裔跃华先生授我们“先秦文学”时讲到《周南·芣苢》,特地从自家院中寻来一棵车前子,手持着,眼望着,读:“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芣苢”,即车前子,很得诗意的一种草,采集车前草,也是很有诗意的一件事。西周故地,春日载阳,农家妇女旷野采集,前呼后应,如在目前。车前子亦寻常植物,古代妇女采它作甚?《毛诗传》曰:“车前也,宜怀妊焉。”对此一说,我很有疑,如此公开的、兴高采烈的、大规模的采集,不像是在采集一种治疗隐疾的药——车前子肯定别有用途。
冬春之际,下学的孩子有一项劳动是挑猪菜。挑猪菜要识猪菜,不能见菜就收,像辛辣的蓼,像牛误食了会发疯的泽漆(我们称作“牛大眼”)。车前子我们也是不取的,取了,猪不吃。
不可小瞧了“体制外”植物的生存智慧。连猪菜行列也挤不进去的车前子,早就练就了随地生根的本事,只要你看,它就满眼都是,跟种似的。它沾泥即活,被碾进车辙里,也能顶着一身泥浆活。有一年,供销社的药材组收购车前子,我们采集了很多,用板车拉去卖,到了却被告知不收,我们只好将它拉回来加工成猪饲料。青棵子猪不吃,加工成粉末猪却肯吃。那年,我家的黑毛猪养得很好,肥得从毛根流油。
蒲
农历五月旧称蒲月。
蒲和艾都是端阳旧臣。巢含一带在春秋战国,时而属楚时而属吴,唤作“吴头楚尾”,民俗也就时吴时楚。端午这天,便是没钱称肉的人家,也要买一把艾蒿靠在门口,充作“艾人”。讲究的“艾人”,要背插两柄绿剑似的菖蒲,才显得精干漂亮,摆在门前威风如戏台上的武生。
蒲苇是蒲的一种,柔弱却有韧劲,古人用它来喻坚贞。“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发生在庐江旧郡,这个地方的水边泽地,至今蒲草青青。
小城的西环城河是我的最爱,我常常独自缘水西行,看夕阳,看柳色,看青荇,看莼菜,当然更多所见的是芦苇和蒲苇。和芦苇水蜡烛不同的是,蒲苇总是离水一步,一丛丛在岸上白头。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上事出自《世说新语·言语》,顾悦很会说话,只是拿“蒲柳”和“松柏”作比,似有不妥,植物不是人類,生存之外,没有多余的虚荣。
我爷爷得糖尿病是在几十年前,那时没有胰岛素,也没有二甲双胍。民间传一单方,说吃臭(菖)蒲草的根可治,于是我父亲就去挖,到十几里外的山外去挖。现代医学证明,菖蒲根有健胃消食的功效,用它治疗糖尿病,适得其反。爷爷病逝于1947年,那年,父亲才十四岁。
葛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这是壮族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每当我听到它缠绵悠扬的曲调,便要想起家乡山中那些猴子一般调皮的,又有一股韧劲的葛藤来。
葛在山中已经很久。有一首织布女唱的歌,名叫《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豆科,藤貌。葛根粉是一种误读,粉来源于它的块茎而非根,这跟藕是一个道理。秋冬季,山寒水瘦,是采葛根的时候。这时候的葛根紧实,圆气,出粉率高,一年一季的葛根粉能给山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近些年山中人口减少,且多为老年,上山采葛的也少,野生葛根粉的价格大涨,有不少城里退休老夫妻,开着车专门进村收葛根粉,不是贩卖,只是自己吃。
起初,葛的主要用途还是制衣织履。《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越王自吴归国,欲得吴王欢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黄丝之布以献之。采葛妇感伤于越王用心之苦,边采边唱:“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
医生说我血糖偏高,但还没到吃药打针的程度,管住嘴就好。我听医生的话。一年冬至回家,想上山挖点葛根。山中情形我是知道的,上山的路也熟悉,我放弃了陡峭的前山,到相对缓和的后山去,结果没有发现一棵葛藤。我是山里长大的,葛本是老相识,为何见了故人避而不见?大概是见我肩扛锄头目露凶光而藏匿了起来。堂兄说,前山肯定有。但我还是说不去了。伤害多来自于口腹之欲,人的命并不比草木高贵。
薜荔
读刘基的笔记《郁离子》,读到“唐蒙薜荔”一节,不禁一笑。
唐蒙(菟丝子)和薜荔这两个攀缘高手,在树下讨论该投奔谁的问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唐蒙说:朴树,“不材木也,荟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其膏入土,是为琥珀……其干耸壑而干霄……”它决心依附松。薜荔说:松,“信美,然由仆观之,不如朴矣”。理由是“山有金则凿,石有玉则劚,泽有鱼则竭,薮有禽则薙。今以百尺梢云之木,不生于穷崖绝谷人迹不到之地,而挺然于众觌……吾知其戕不久矣”。于是各自攀附不表。岁余,齐王使匠石取松为雪宫之梁,唐蒙死,而薜荔与朴如故。
历来,站错队的后果很严重。
薜荔在刘基笔下化身为庄子,替他输出道家的处世哲学。
薜荔在我们这里叫“爬山虎”,乡人只知爬山虎不知薜荔。它喜欢爬树,更喜欢爬石头,只要有裸露的大石,不久就有薜荔来爬,然后在石头上葱茏起来。乡人用它这一点来护石堰,也用于垂直绿化。北宋梅尧臣是皖人,他写过一首《咏刘仲更泽州园中丑石》,其中有“窍引木莲根,木莲依以植”,木莲即薜荔。诗外的故事是:刘仲更作园,嫌园中石头丑,梅尧臣从老家引来薜荔种在石头上,这样,“秋蛇出其中,舌吐霓虹色”,相得益彰,作诗以记。
冬天放羊,山上无青,羊以啃啮石壁上的薜荔为乐,薜荔是山羊冬季的时蔬,若是我们在石壁上撒一泡童子尿,那羊就吃得更欢了。这是旧事,“朗朗而够”。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屈原《九歌·山鬼》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这样的句子,这里的“薜荔”是一种叫作“山芹”的草,属于香草的行列。
荼糜和蓼
冬阳蜂鸣。在午后的阳台上,端一盏茶,听昆曲《牡丹亭》,听到《寻梦·懒画眉》一折:“是睡荼糜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丝竹江南,咿咿呀呀。
我一直不能分清荼糜和蔷薇,虽然我一直很想分清。后来有行家告诉我说,色白单瓣者为荼糜,我还是很雾水。《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有这样一场“花酒”:
湘云便绰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这面上一枝荼糜花,题着“韶华胜极”,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开到荼糜花事了”……麝月问怎么讲,宝玉愁眉,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
荼糜是送春之花,麝月是大观园群芳的“关门人”,曹公是借花言情。
在我们江淮乡下,送春的角色历来由蓼子担任。春秋时期江淮有蓼国,后来被楚国吞并,想必曾是个遍地出蓼的所在,就是现在,蓼子仍然随处可见。江淮的蓼属于辣蓼,叶茎穗颜色偏淡。都说世上无闲草,蓼子可以说是真正的“梁山军师——无用”。它味辛辣,猪牛不吃;它白色的汁液弄到皮肤上火烧火燎;用它烧锅,会熏得人流泪;农人不喜欢它,见到就铲,可怎么也铲不尽。我们这里只派它两个用场:一是踩进烂泥里沤肥;二是有人将它捣碎后,撒在水里“醉”鱼。
蓼子开花已经是夏末秋初了,农谚曰:“楝树开花你不做,蓼子开花把脚跺”农谚里没有丝毫的伤感,蓼子混到这步田地,在整个“草字头”中也是很失败的。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