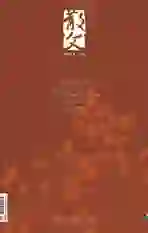我有我的路
2021-11-19周洁茹
周洁茹
已经是三年以后了,去上班的路还是两条,但不是三年前的那两条路了。不是公司换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是我换了去公司的路。
曾经最近的那条路已经修了三年,还要再修三十年的样子,我不再走那条路了。两边的餐馆也都沒有了。有过一个贝果店,可能是全香港最好吃的贝果店,一个店员,又收银又烘贝果,小茴香籽的贝果配软奶油起士,我也吃过几天好早饭。我不再走那条路了。要说还有什么惦记,废品站的台阶下面,有一位纸皮老太太,我时常想起她。还走那条路的时候我往往一下巴士就取一份《头条日报》,经过纸皮老太太的纸皮堆,就放在那上面,有时候她坐在那里,我们互相讲早晨,有时候她不在那里,我放下报纸,继续往前走。不走那条路以后,我有几次在路口又看见她,推着一车沉重的纸皮,她看我一眼,似是认出了我,又似是没有,大家都戴口罩了,我戴口罩的脸,我自己都觉得很陌生。
穿过那个路口,就要开始快步,因为路口一个肉档,肉条和内脏都挂在外面,气味也叫我难受。屏一口气经过那个肉档,那十秒,总像是人生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总会经过,但要小跑几步。有时候买肉的人太多,堵住了路,我那几步就会很靠近肉档,非常近,脚下血水横流,跑起来的时候,真顾不得旁人的眼睛。
过了肉档就是个街坊饼店,曾经关了一阵子,再开张仍是卖包饼,并没有什么变化。买过蛋沙津包,也买过菠萝油,吃不出来分别,不是这里长大的人,也许更愿意去连锁店,至少滋味都是一致的。
然后就是一个玻璃的小门,没有任何标识,进了那个门,上一层楼梯,就进入了一个庞大的楼群,每一幢楼都是相连的,人在里面可以走很远,即使外面暴雨,完全影响不了里面走的人。这一条路是三年前就有的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新近才知道,如同那个没有门牌也不标注的玻璃门,也许就是不招待陌生人的意思。
楼里的每一个拐角都摆了艺术装置,非常艺术,非常装置,每个艺术装置都有解释。突然想起来,这路原是十年前就走过了的,那时的楼群都是有些暗的,艺术品们也与现在有些不同,一个立住的大青苹果,印象最深,不知道去了哪里。十年前的我,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停下来买一个牛油果三明治,在一个轻食店,也记得起来,轻食店的前身是一个也卖鲜花也卖巧克力的店,主要卖什么,记不分明了,如果还要卖很多别的,总叫人记忆有些混乱。贝果店是很迟才来的,那个店面也空了好久,非常骄傲的贝果店,每天下午四点就关店,总叫我想起三年前的那间,只是都不同了。又开了一间未来素肉店,门面精致,却总是冷冷清清。有一天不想再买贝果,也不想再吃牛油果,走入未来店,一丝烟火气都没有的一个店,一个店员,像是站错了地方,困惑地看了看客人,客人也困惑地看了看他,假装无事地走了出来,尽显尴尬。
过了一个天桥,一排西餐馆,一街露天位,有时候很夜了,过这个天桥时往外面看一眼,就看得到那些露天位都坐满了人,人手一杯酒,聊到更夜。
转一个弯,再过一个天桥,又一个隐秘的玻璃门,推门而出,下两层楼梯,就出了楼群。公司在另外一幢楼,单独的一幢,不与任何其他楼相连。我往往选择货梯,上一层到停车场,仍是货梯。我宁愿与货物们一起搭电梯,那几分钟的静默,也很珍贵。
如果转一个弯,再过一个天桥,不从那个隐秘的玻璃门出去,就再往前,一架扶手梯,下一层,一间比利时餐馆,左转,也一样出了楼群。
那间比利时餐馆,时常有朋友找我在那里喝一杯,蓝莓啤酒或者不地道的杧果莫吉托,喝第二杯的时候她就会告诉我一个新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每天晚上都要枕着自己的存折睡觉,有一天晚上她来我这儿,我说我只剩一万块了,后来她告诉我,那个晚上她没睡好,一直在想我以后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我说,“你只剩一万块了你还睡得着?”
那就喝第三杯,等下一个新故事。
那一排西餐馆,有一天也是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晚上,被人带去了一个露天吧,喝了一杯很冻的黑啤酒,喝完夜已经很夜,不知去哪儿搭车,他们带我转了个弯,就是一排过海的红的士。
过了一两年了,我才突然意识到,就是那排西餐馆,那一街露天吧,每天上班的路,都要经过那里。
到了中午,停在天桥下的那台餐车才会开业,卖的也全是未来的素肉,新式泰菜。早上上班的路上,还是会多看它一眼,一架银色的未来车,沉默地停在那里。天桥下面的路,没有人走,所有上班的人都在楼群里穿行。
有时候巴士会开过站,或者开出一点站头,走哪条路完全取决于车门在什么时候打开,有时候一定是要到了站牌下面,那就走另外一条路。
车站旁边的山崎饼店买一个蘑菇包,或者菠萝酥,蘑菇包很快就不出了,还总是时时去看看,总存着一点希望,看了一年多,终于接受,菠萝酥也不要了,空着手出了山崎,往左,经过一个街市,再往前走,靠外的是两个水果摊,总摆着各式水果,很多我也不认得。总想要买点什么,总是什么都没有买,太害怕了,凡是要开口的买卖,总叫我害怕。再往前走一段,经过一个印尼杂货店,到了一个也卖早饭的茶餐厅,肠粉豆浆买了好多次,才发现他们还有粢饭,犹犹豫豫问一声走肉松得唔得,爽快地答,得。轻减版粢饭,像是定制版的早饭,吃起来总有一丝欣喜。
再往前走,左转,一条斜路,左转再左转,就到了公司楼下。
斜路上有一间糖水铺,也卖早点,买到过一次番薯糖水,再去,总说还没有煲好,也就不再去了。户户送网购了来做午饭,同事奇怪:糖水当午饭的?
不是这里长大的人,就是会把糖水当午饭啊。
约了个同事一起吃午饭,她也是吃素,时间比我还长些。一起等电梯,等很久,入了电梯,层层停,最终挤满了要去吃午饭的人,人人屏住气的一段电梯时间。
两个人一起走去了那台银色的未来车,两份辣炒未来肉,车旁的一张木桌,面对面吃起了午餐。
“好吃吗?”她问我。
“还好。”我讲,“以后再来,也可以叫上别人。”
她笑笑,说:“一盒素肉饭,八十八,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为什么?”我说。
“至少得有真的肉吧,”她说,“对大多数人来说。”
我也笑笑。望了望天,上面是天桥,很多打工人走来走去。
我吃素也有三年了。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