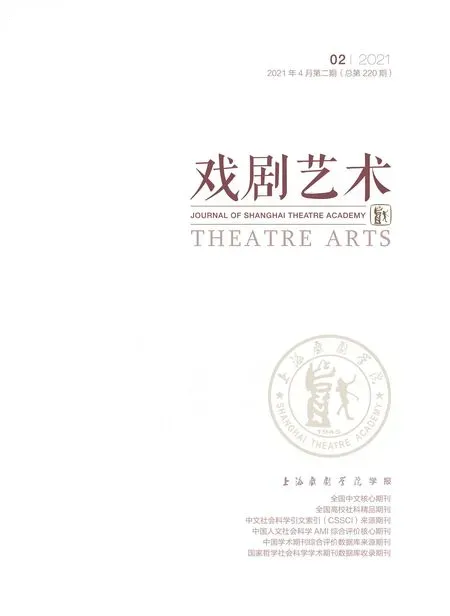跨媒介叙事:当代百老汇音乐剧的叙事策略
——以音乐剧《圣诞颂歌》为例
2021-11-19温馨
温 馨
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首次提出了跨媒介叙事概念,他颠覆性地打破了以文字叙事为研究主体的传统,着眼于跨媒介叙事学理论,为后经典叙事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这个媒体裂变的时代,无论是电影、动漫、游戏还是音乐行业都在思考跨媒介叙事语境下的社会发展给行业本身所带来的变化。而音乐剧作为综合艺术的载体,将音乐、戏剧、舞蹈、舞美和商业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集经典性和观赏性、专业性、流行性和挑战性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产品。它是公众审美与专业审美的纽带,也是近现代文明中美学新思想、新视角和新趋势的特别体现。
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在法国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走入学界的视野,随后又陆续诞生了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视线瞄准戏剧、音乐、电影和绘画等领域,尝试以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去研究、分析和归纳这些超文学载体的叙事策略。如,布莱希特吸收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论,创立了系统的叙事体戏剧理论;莫妮卡·弗卢德里克 (Monika Fludernik) 为戏剧的叙事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曼弗雷德·普菲斯特(Manfred Pfister)则用“视角”佐证了叙事戏剧的可行性;安东尼·纽康(Anthony Newcomb)、弗雷德·莫斯(Fred Maus)等人打开了音乐叙事学的大门。尽管戏剧叙事化、音乐叙事化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但时代的发展让来自不同空间的多元文化与多种生活方式相互激荡, 使原先单向单线的、统一的、均匀的和理性的时空观趋于解体。(1)严锋:《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而各媒介之间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叙事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必然推着叙事学理论不断发展和前进。
其实,仅从西方音乐剧的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叙事基因以一种特殊的形态融入了音乐剧文本及音乐本体中,使之成为了一种以“综合性”为特征的跨媒介叙事载体。而经典文学作品在艺术裂变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不同媒介进行文学重构,重新阐释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从纸张呈现到舞台承载和音乐演绎,经典文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本文对西方叙事音乐剧的产生原因、发展因素和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梳理,以跨媒介叙事语境为路径,从后经典叙事理论的角度审视由查尔斯·狄更斯小说改编的叙事音乐剧《圣诞颂歌》(AChristmasCarol)中的叙事空间、叙事视角、音乐叙事和媒介性,探讨音乐剧演绎与原版小说对叙事的不同利用方式,以及给叙事学研究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笔者有幸担任了百老汇音乐剧《圣诞颂歌》的制作人,全程参与了这部音乐剧的制作与公演,怀揣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梦想,希望结合自己当美国戏剧奖托尼奖(Tony Award)的评委的一些经历和感悟,通过理论思考和探索,分析和借鉴百老汇音乐剧的创作与实践的经验,对音乐剧叙事理论及中国音乐剧行业的健康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
一、百老汇叙事音乐剧兴盛的文化背景
叙事学作为当今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尽管已经被用来探索各种各样的文学、戏剧和音乐问题,但音乐剧从未成为叙事学研究的主题。事实上,最初的叙事音乐剧其本质与叙事歌剧大同小异,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瓦格纳就已经开始考虑叙事歌剧这个问题了。他注意到了叙事性在一些作品中的缺失,于是在1852年《歌剧与戏剧》(OperundDrama)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要摆脱传统歌剧美学中较为空洞的程式化、公式化的创作结构,并对未来的歌剧提出了设想。叙事的地位和作用也开始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之中。尽管他的革新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反对和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他的艺术革命还是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歌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开创了叙事歌剧的新局面,也为日后叙事音乐剧的出现做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铺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艺术家都开始重新思考战后世界给艺术带来的变化。此时的美国有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艺术家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里,奥斯卡·哈姆斯坦(Oscar Hammerstein)让迅速崛起的百老汇音乐剧受到了世人瞩目,从而开始蓬勃发展。从艺术表现形式看,百老汇音乐剧在解构重组维也纳的古典轻歌剧、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法国的喜歌剧和黑脸滑稽剧等表演形式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了来自非洲的音乐特质,还融入了美国本土的黑人灵歌、布鲁斯和爵士乐等音乐元素,后又转化了踢踏舞、查尔斯顿舞等歌舞形式,才形成了自己的雏形。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的移民风潮在提升了整个国家活力的同时,也刺激了娱乐行业的市场繁荣,由于语言、风俗和文化的不同,审美风向从精英渐渐偏移到大众阶层。歌剧、严肃戏剧等高雅艺术成为曲高和寡的“取笑对象”,改编和调侃莎士比亚的戏剧行为更是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2)吕艺生、文硕:《美国音乐剧对欧洲说No》,大连:大连出版社,2008年,第52页。为满足大众审美及其所在阶层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国陆续衍生出了以杂技、逗趣、讽刺为卖点的滑稽秀、杂耍秀、综艺秀和实事秀,甚至还有以暴露身体为卖点的富丽秀。无论是剧作者还是剧院经理人,为了票房的保障不得不与这种低俗的秀文化打交道。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存在着割裂性。此时美国的音乐剧与其他文化的联系逐渐断裂,已严重偏离了真正的音乐、戏剧的美学思维轨道。这种过于功利性和背离传统经典的审美不仅饱受诟病,也引发了一些从业者的思考。这种困境与冲击加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音乐剧的改革。
20世纪20年代,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尽管城市化浪潮很快给美国主流文化贴上了商业化的标签,但此时的大众逐渐从媚俗的娱乐中醒来,转而追求更具时代性、价值性的文化产品。在文学、美学、戏剧学、音乐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下,美国音乐和戏剧的艺术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思潮、新观念让剧作家们开始思考和审视自己的作品。奥斯卡·哈姆斯坦(Oscar Hammerstein )邀请吉罗姆·科恩(Jerome Kern)合作将畅销书《演艺船》(ShowBoat)改编为音乐剧。在当时严肃经典与娱乐至上这两种“新旧势力”较量的背景下,小哈姆斯坦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正面呈现美国异族通婚、种族歧视和文化认同等敏感的社会现象,为观众讲述了密西西比河上一条演艺船上三代人的离合悲欢。在展开剧情、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现象批判和人文思想高扬的统一。该剧题材聚焦于黑人靠苦力谋生的辛酸以及底层人民在面对社会不公而斗争和反抗的精神。这种社会矛盾的真实性映射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情境,使许多观众感同身受,所以该剧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舞台艺术呈现上,此剧将音乐、舞蹈和戏剧等元素进行有机整合;从文本上来看,它实现了小说文本、戏剧文本和音乐文本的兼收并蓄;从音乐上来看,它博采众长,延续了欧洲的音乐传统,增加了当时社会主流的蓝调、爵士等音乐元素并配以独唱、合唱和重唱的表演形式。该剧首演大获成功,使美国音乐剧彻底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盲目依附欧洲歌舞剧的局面,也转变了以媚俗秀去娱乐取悦大众的观念,叙事音乐剧逐渐成为当时美国音乐剧的主流。至此,美国音乐剧文化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二、跨媒介叙事:百老汇音乐剧发展的内驱力
百老汇现已成为集美国现代歌舞艺术、娱乐产业和旅游文化于一身的代名词。在其发展历程中,跨媒介叙事学理论的影响不容小觑,当然叙事文学、叙事戏剧和叙事音乐等意识形式和理论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学术界对媒介的定义相当多元,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媒介不仅仅是管道或者传输概念,也是符号、技术和文化的实践。本文所说的跨媒介研究不仅包括言辞文本(verbally narrated texts),也包括非言辞(nonverbal)文化文本,如影视、美术、音乐、戏剧和晚会等,还包括虚构与非虚构纪实文本。(3)凌逾:《跨界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诚然,文学的美学维度不应当只考虑其书面文本部分,视觉空间中的叙事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跨媒介叙事中,演员、音乐、舞美乃至观众都可以参与叙事,共同完成叙事文本。音乐剧就是以文学、音乐、戏剧和舞蹈为载体,为观众讲故事。戏剧文本和音乐文本是音乐剧的灵魂所在,音乐不仅参与叙事,且在表现剧情的同时传递重要信息,在连续叙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些艺术实践都印证了不少学者的观点,即“世界艺术生态的消解与重构, 传统文学语言的线性叙事结构被视觉空间的拼接所取代”。(4)(德)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就百老汇音乐剧产业来说,好莱坞的介入使其率先体现出跨媒介叙事特征。从《演艺船》开始,《西区故事》《窈窕淑女》和《音乐之声》等音乐剧被陆续搬上了荧幕。紧跟其后的迪士尼集团在打造动画王国的同时,亦努力拓展音乐剧、书画、游戏和文旅等领域。为推出音乐剧版《狮子王》,迪士尼公司于1997年斥巨资购买了位于纽约时代广场旁的阿姆斯特丹剧院,(5)Michael Kantor,Broadway: The American Musical,2018,403开启了新的商业版图和多功能的文化互动。音乐剧《狮子王》也不负众望地成为了当季百老汇的票房冠军,并于次年获得多个托尼奖奖项。艺术形态的重组、视觉空间的拼接,让原本受众群体大部分为青少年的动画,拓展出更多可能性。《电影艺术词典》对于动画的解释为:“它以绘画或者其他造型艺术作为表现手段,运用夸张、神似、变形的手法,借助于幻想、想象和象征,反映人类的生活、理想和愿望,是一种高度假定性的电影艺术。”(6)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2005年,第443页。动画片《狮子王》用拟人手法塑造了一个弱小的狮子在亲情、爱情和生离死别中寻找正义和担当,并最终排除万难成长为王的角色。文本中所描绘出的动物世界亦是一个人类社会,有狡诈、嫉妒、凶残,也有善良、仁慈、宽容。故事所映射出来的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以及对和平世界的向往,对亲情、爱情、友情的愿景,都与人类现实生活遥相呼应。与动画的荧幕叙事不同的是,音乐剧文本中的非洲草原是通过布景、灯光、木偶、皮影乃至真动物马戏等手段生动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演员们身着动物服饰,将面具置于头顶,脸上的油彩和表情清晰可见,与观众的亲密互动再加上整场的音乐氛围的烘托,观众仿佛置身于非洲大草原中,亦真亦幻。当经典主题曲《今夜爱无限》(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响起时,现场演唱和乐队伴奏的震撼使得那种隔着屏幕观看动画的疏离感一扫而光。这种跨媒介叙事在不断发展中挖掘并丰富了原有的经典内涵与艺术价值,求同存异亦追求平衡。在同一故事框架下,从动画中通过转化、改编和再生来完成事件叙述。通过音乐、舞蹈、戏剧等手段在同一个故事框架下进行新的诠释,各尽其职但又互相呼应,充分实现了跨媒介的叙事目的。可见,跨媒介叙事音乐剧这个新的媒介,取长补短,将角色塑造、视觉风格进行了革新,平衡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适应了时代的审美需求。
跨媒介叙事具有强烈的角色感,同时还能在一个既定的场域中形成具有逻辑联系的整体感。正如学者詹金斯所认为的那样:“跨媒体叙事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故事世界可以通过游戏来探索,或者作为一个娱乐公园景点来体验。任何一个产品都是进入作为整体的产品系列的一个切入点”。(7)(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周宪、许钧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页。比如近年来火爆百老汇的浸入式戏剧《今夜无眠》,是根据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麦克白》改编的,颠覆了原有的叙事空间,打破了舞台、观众席这种传统观剧模式,把场景设置在一个废弃的五层酒店中,在近9300平米的空间中,设有阴森的疯人院、满是墓碑和黄土的墓地、落满灰尘的大书房、灯光炫目的宴会厅、华丽精致的卧室等不同场景。大大小小近百个房间中的每个道具都制作精湛,就连一个小发卡都隐含着剧情的线索,可谓细微之处见真章。
观众需全程戴特定的白色面具,可以自由选择剧中任意角色跟在身边,近距离观察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直接参与探索体验。这是一个需要奔跑的舞台,观众需跟随演员按照剧情发展在不同楼层跑动。詹金斯提出了这种剧的可钻性(drillability)特征,强调提供可钻性是戏剧故事世界扩张的方式之一。可钻性意味着有好几层叙事,鼓励读者去钻研。而在这个被打造出来的真实可触的世界中,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故事脉络。人物上从麦克白到麦克白夫人,乃至一个小护士、一个仆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剧情。演员会突然请观众帮助拿一件衣服,也会拉着某一位观众到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小房间。多线索、多层次、多视角的叙事让原文本更加丰满,叙事空间的开放性让观众、演员、场景、道具等参与叙事,共同发展故事情节并完成叙事文本的生产,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可见,百老汇音乐剧作为舞台表演艺术和叙事媒介,在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打破叙事传统,演员观众互动促进了故事世界的扩张,引发了文化、情感和审美上的共鸣。这种不同媒介协作、互补打造叙事世界的叙事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以及大众审美需求的转变。
三、音乐剧《圣诞颂歌》的叙事策略
《圣诞颂歌》百老汇音乐剧版本于2019年11月7日至2020年1月5日在百老汇街的兰心(Lyceum)剧院进行了为期8周的精彩演出,反响空前热烈,不仅打破了兰心剧院的售票纪录,而且同比超过了《狮子王》和《芝加哥》等热门剧,纽约时报频繁报道,赞扬此剧绝对是一场难忘的体验。剧作家杰克·索恩(Jack Thorne)和导演马修·瓦库斯(Matthew Warchus)对狄更斯笔下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诠释。音乐剧作为舞台表演艺术和新的叙事媒介,在戏剧叙事的基础上,揉入音乐、舞蹈等元素,在连续叙事中连结并传递重要信息。它打破了叙事传统,吸收叙事文本原有的审美特质并试图削弱晦涩、深奥的成分,将解构重组后的文本投射到舞台上。从剧场表演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场表演中的每个角色是如何从对应经典文本中的人物设定及其元素演变而来的。这种协作展现了文学的生命力和跨媒介叙事创意,扩大了受众范围,且各有风采。文学文本与戏剧文本、音乐文本一经结合,便碰撞出光芒四射的火花,焕发出新的生机。其叙事策略有如下独特之处。
(一)跨媒介叙事的巧用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杰出的作家,他用富有节奏感的叙事手法和倡导人道主义的写实精神,创作出很多深入人心的小说,如《雾都孤儿》《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他的经典代表作《圣诞颂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在西方世界中更是家喻户晓。故事讲述了一个自私、刻薄、吝啬的商人斯克鲁奇,在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精灵指引下穿越时空找回了人性中的温暖、善良和慷慨。小说第一个版本于1843年12月19日问世,至今已有177年。它被陆续改编成动画、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剧甚至游戏。如今,圣诞前夜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看《圣诞颂歌》已经成为一种圣诞节的约定风俗。而圣诞文化里的家庭聚餐、交换礼物和装扮圣诞树也是在狄更斯第一版《圣诞颂歌》问世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就连圣诞老人也可在其第二版的文本中找到原型——“他穿着一件镶着白色毛边的绿色披风,头上只戴了一个青色的花环。他有着一头黑褐色的长卷发和慈祥的面庞。”(8)Charles Dicken, A Christmas Carol(New York: Royal Fireworks Press,2004),47.绝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认为,这部作品奠定了圣诞节在西方的地位和价值。值得肯定的是,狄更斯所传递的精神触动了当时社会中许多人的内心,三个精灵与斯克鲁奇的对话也同样是对许多人的灵魂拷问。
《圣诞颂歌》这个经典文学文本吸纳了多种艺术媒介。“一个跨媒体的故事穿越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一个平台都有新的内容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的、有价值的贡献”。(9)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34.1938年12月16日美国首次播出了片长一小时9分钟的《圣诞颂歌》同名黑白电影,引起了不凡的反响。1971年由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执导的动画片版本的《圣诞颂歌》搬上了荧幕,并一举囊获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1994年相继推出了芭蕾舞版,2001年英国上映了名为《圣诞礼赞》的动画版,邀请了众多明星为其配音,影响深远。2009年,迪士尼公司第一次借用IMX3D技术发行了动画电影版本的《圣诞颂歌》,通过真人表演捕捉达到了动画人物表情逼真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戏剧版本也被改编成不同语言,每一年在圣诞节期间都是剧院文化的热点。游戏平台上的几个游戏版本也是各有千秋,有的是对原故事的还原,有的是开发者和游戏者对叙事文本共同创造的延续,一同扩张其故事叙事线索。2019年英国再次推出了《圣诞颂歌》改编的三集同名电视剧,可见其流行历久不衰。
(二)浸入式双曲线情感叙事策略
在音乐剧《圣诞颂歌》的叙事中,处理好感性与视觉、叙事者和感知者的关系尤为重要。从小说到电影、动画、影视剧、游戏再到音乐剧的改编,无论如何跨越媒介都离不开叙事这个底色。在狄更斯笔下的时光之旅叙事中,时空逻辑被打破,为读者营造出一个认知和想象空间。在迪士尼2009年上映的动画版本中,原著中斯克鲁奇与其未婚妻贝拉的关系被改写。贝位提出分手,理由是她认为自己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而这句话在整部电影中也显得格外地刺耳。精灵带着斯克鲁奇到了贝拉的家,看到贝拉身边围绕着活泼可爱的儿女,还有一位温柔体贴的丈夫,贝拉与丈夫谈到斯克鲁奇的时候充满关切和同情。似乎人人都只看到斯克鲁奇的吝啬、冷酷、自私,但贝拉却看到了斯克鲁奇内心的恐惧。当贝拉在面对眼前这个改过自新的男人时,纵使心境万般复杂,只是凝结成了一句话,我现在有一个爱我的丈夫,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两个人之间对话虽没有丝毫刻意煽情的痕迹,却格外令人动容。斯克鲁奇与贝拉颤抖的双手,略显拘谨又绝对亲密的拥抱,湿润的眼眶,饱含深意的语气等等,这种舞台视觉带来的冲击性作用在观众身上产生的道德移情反应比阅读文字更加直接。此刻视觉与情感很好地构建起了一个良性的观演关系,这里的观众不仅是“公正的旁观者”,对叙事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且围绕着同情,构建出了双曲线的情感叙事。
由于整体的剧情不拖沓,在空间性上,演出与文本相辅相成,从舞台场景的布局构建到演出细节的处理,处处都围绕着《圣诞颂歌》原文本。而文本中未提及的细节却给了舞台叙事更多的发挥空间。音乐剧《圣诞颂歌》采用了叙事主体分化的策略,除了故事中的所有角色之外,剧中演奏小提琴、大提琴、吉他、手风琴等的乐队演奏者们在作为音乐叙事者的同时亦充当叙述者的角色,剧中的旁白发声使得剧情脉络更加清晰。演出开场时,身穿黑色礼服的乐手在台上奏响欢快的乐曲,同时还有旁白演员在观众席发放饼干与柑橘。叙述者(表演者)从一开始与感知者(观众)的互动就尤为频繁,每一句“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似乎都在提醒着大家这不是一场演出,而是大家一起分享假期的喜悦。
音乐剧《圣诞颂歌》还巧妙地体现了感性与视觉交替的叙事手法,让感知者(观众)的情绪游历于故事内外。当观众依旧沉浸在斯克鲁奇与前女友有缘无份,感叹彼此错过的遗憾时,曾经的吝啬鬼邀请他的侄子和助手全家一同过圣诞节,这时斯克鲁奇还在一楼的主舞台上,而他的侄子和助手在二楼的包厢座和三楼的观众席中往一楼舞台上扔下两条窄长的布,一边吆喝着,一边用布当作滑梯将橙子、火鸡一一传送到舞台上。传送到香肠的时候,更是让作为感知者的观众成为了故事发展的一部分,共同将香肠以击鼓传花的形式递到斯克鲁奇的手中。这种客观视角与体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新的互动机制,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感同身受。亲情、爱情和友情在舞台上一一展现出来。观众穿梭于故事的内外,对音乐剧文本的观察和体验更加深入。感性与视觉的综合运用,与音乐一同拓展了原文本的内涵和外延,为经典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 唤醒与延伸:音乐叙事策略
177年前,查尔斯·狄更斯将蒂姆·克拉奇蒂(Tim Cratchit)介绍给了世界,怀着怜悯的心情写下了这个孩子的处境:“可怜的小蒂姆,他拄着一根小拐杖,四肢靠铁架支撑着!”。从那时起,这个角色就成了《圣诞颂歌》的象征。这个多病但乐观的孩子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颠覆者,感染并推动了斯克鲁奇的改变。百老汇音乐剧版本大胆启用了两个患有脑瘫的男孩扮演剧中小蒂姆的角色,他们的加入为故事中的小蒂姆一家人所面临的挑战增添了一层重要的现实色彩。
如果说文本是叙事音乐剧的肉身,那么音乐便是其灵魂。音乐剧中的音乐直接参与叙事,可以连接故事情节、唤起故事情感,同时,音乐在音乐剧叙事中的战略性布局在实现情节发展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慈善的层面上,百老汇音乐剧版《圣诞颂歌》的跨媒介叙事用音乐文本唤醒了人们本真的爱与善良,助力了慈善事业。在音乐剧中,音乐分为声乐与器乐两种表现形式。声乐是台词,是语言的外部形式,文本通过歌词被人声传递,是显层的叙事。器乐作为弥补人声音色单一的最佳方式,也是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段,是一种深层的叙事。音乐中的多层叙事鼓励了观众参与和探索故事。在《圣诞颂歌》的尾声,全体演员无伴奏演唱的《平安夜》将全局推向了高潮,无对白、无伴奏,简单的手持铃铛汇集成音乐文本感人至深的一幕,用最简单的音符唤醒了人们在忙碌生活中失去的本真。当小蒂姆摇响《平安夜》的最后一个音符,所有人沉浸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好平静中,这种简单的音乐深层叙事引导了观众去思考人生与家庭的真谛。两小时的演出里,观众跟随三个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灵,见证了斯克鲁奇从吝啬、刻薄、冷漠到慷慨、宽厚、慈爱的重生与救赎。“斯克鲁奇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转变,更是对社会价值观转变的期盼。”(10)E.L. Gilbert,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 Charles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 PMLA,1975,22.如果观众还记得那些饼干和柑橘的开始,就会看出一些端倪。在斯克鲁奇努力为他所做的坏事找借口,为他的吝啬行为找理由的同时,反观现实世界,演出一开始就奠定了整部剧的基调。
在演出结束后,《圣诞颂歌》的制作团队联合非盈利组织黄金之心基金会一起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或者单亲妈妈筹集了善款。(11)https://www.ny1.com/nyc/all-boroughs/news/2019/12/18/-a-christmas-carol--on-broadway-raises--12-000-for-charity这部经典之作将慷慨、善良和慈爱传递下去,与世人共同谱写爱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