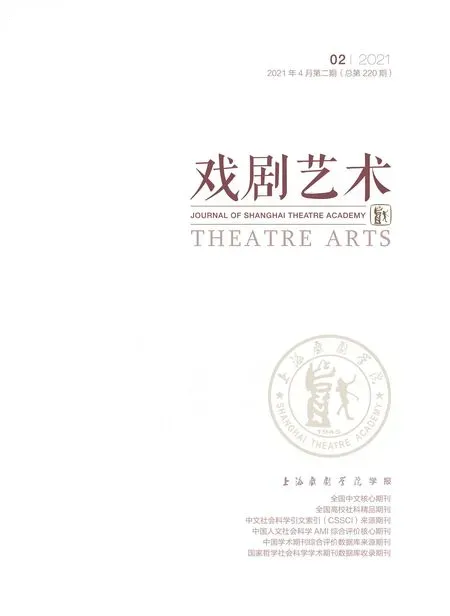现场表演中影像的交互性
2021-11-19刘志新
刘志新
我们处在一个高度视觉化的、影像繁荣的时代。清晰逼真的影像已经成为日常阅读的对象,它不断超越界限、占据我们的空间,将我们包围在图像的海洋里。德国戏剧理论家汉斯·雷曼指出:“在实验剧场理论中,对媒体社会中的视听条件进行分析、反思和解构成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任务。”(1)(德)汉斯- 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修订版),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二版,第220页。今天,如何定义和看待现场表演中的影像,成为了一个必须深入探讨的戏剧美学问题。从戏剧发展的角度来看,剧场是一个多媒介融合的环境,它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整合不同媒介讲述故事,既展示了各种媒介的特点,又保持了剧场艺术自身的特性。乌特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媒介研究学者齐尔·凯特贝尔特(Chiel Kattenbelt)认为:“媒体剧院是一种超媒体,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可以包含所有媒体的媒体。”(2)https://cursointermidialidade.files.wordpress.com/2014/08/kattenbelt-theather.pdf——CHIEL KATTENBELT Intermediality in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Definitions, Perceptions and Medial Relationships.在当代媒体剧场中,影像与现场表演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表演形态,它不仅丰富了剧场艺术的表演手段,也改变了现场表演的生存环境,记录影像、实时影像和数字影像与现场表演的融合创新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戏剧艺术跨媒介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影像与现场表演
影像是人或物在光线照射下的一种视觉显现。它是光影构成的图像,现实存在物的影子。影像的活动是一种幻觉,是一连串静止图像在视网膜上形成的视觉暂留现象。静止的图像存在于空间之中,它偏于客观记录;动态的影像不仅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时间之中,它偏重于主观情感表现。客观影像是基于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观影像则源于创作者内心的感觉、记忆和想象。影像的本质是记录性的,是摄影机镜头对物质现实的准确还原与复制。“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的艺术特质第一次从头到脚由它的复制性所决定。”(3)(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5页。在现场表演中,大多数影像都是预制的、可重复的光影媒介,它确保了表现对象的真实性,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丰富性。影像参与现场表演和戏剧叙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影像与戏剧最早的结合形式是“影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戏剧家用影像来交代戏剧事件背景,烘托舞台气氛,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验。德国政治剧场导演埃尔温·皮斯卡托认为“电影可以给在舞台上所描绘出的世界赋予一种现代的、技能性的扩大与延伸。”(4)(英)J.L.斯泰恩:《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刘国彬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1月,第687页。他“用电影、幻灯、标语牌、硬纸牌和机械装置等替代毫无生气的布景”,(5)张仲年:《影像作为舞台导演叙事性语汇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通过“混合性媒介”与演员表演的并置来增强戏剧表演的真实性,提升了现场表演的政治煽动力;苏联导演维塞沃洛德·梅耶荷德追求戏剧时空的表现力,认为只有电影化的戏剧才能和电影展开竞争。他用“电影化戏剧”的创作理念,将电影蒙太奇手法运用于假定性的戏剧场面调度中,创作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戏剧作品,如《森林》《拿下欧洲》等;50年代以来,捷克舞台美术家约瑟夫·斯沃博达(Josef Svoboda)将多屏投影与现场表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复合投映 (Laterna Magika) 的光影戏剧形式,重构了影像与表演之间的叙事关系。他认为,演员动作是影像的出发点,影像应该跟随表演动作的变化而变化,与演员表演相互配合。“我们应该把屏幕和舞台上的动作关系衔接起来,既不能机械呆板,又不要引起幻觉,既不是图解说明式的电影投影(皮斯卡托那种),也不造成自然主义的现实幻觉。”(6)(捷)约瑟夫·斯沃博达:《戏剧空间的奥秘:斯沃博达回忆录》,刘杏林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3月,第195页。同时,斯沃博达还强调影像不只是表现看得见的东西,也应该把看不见的东西呈现出来。在布拉格民族剧院创作《最后的一切》时,他通过现场表演动作与放大的影像动作之间的对比来创造一种视觉隐喻,“我们造成一种记忆与现在时的对照,一种演出现场观众的体验与她被演出唤醒的以往体验的对照。”(7)(捷)约瑟夫·斯沃博达:《戏剧空间的奥秘:斯沃博达回忆录》,第101页。他作品中的光影变化是动作交流的媒介,也是心灵沟通的语言。60年代后,电视媒介迅速普及,电影、投影和电视直播不断介入现场表演,使影像成为戏剧中越来越独立的叙事性元素,并对演员身体的表演提出了挑战。就在身体表演逐渐消失在影像媒介中的时候,戏剧家们担心影像会将现场表演引入歧途,让剧场艺术失去其自身的独特性。为了将它抵御在剧场的门外,他们倡导一种以身体为主的质朴表演形式,强调现场表演的真实性、连贯性和不可替代性,拒绝用影像干扰演员表演、阻碍观演交流,提出用现场性理论来引导人们思考戏剧表演的独特本质。
德国戏剧理论家费舍尔·李希特指出:“在发明和发展相应的技术之前,人们没有谈起过‘现场’演出,而只谈演出,只有当‘现场’之外,还出现了媒体化的演出,那么这个‘现场’概念才会有意义。”(8)(德)费舍尔-李希特:《行为表演美学——有关演出的理论》,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98页。现场性理论是在电子录像技术出现后提出来的,是一个用来区分现场表演与影像表演的概念。现场性指观演双方在现场表演中所获得的一种全感官的活性体验,包含了身体的物质性、时间的一过性和意义的不可复制性。在戏剧中,演员和观众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相遇,既是空间上的“此地”,也是时间上的“现在”,在观演双方的交流互动中,创造出了一种不可重复的意义,显现出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用即时即地性组成的原真性描述了原创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属性。“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7页。美国学者佩吉·费伦认为:“表演唯一的生命就是现在。表演是不可以被储存、录制和存档的,或者参与对再现的循环:一旦表演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变成了表演以外的东西。”(10)Peggy Phelan:Unmarke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Lodon/New York, 1993),146.现场表演完全不同于影像的复制特性,每一次表演都会产生意义的动态变化,“在舞台上,演员的演出每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每次都具有原始意义。”(11)(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37页。它是观演者身体、情感与心灵在场交流的活性形式。现场性理论描述了演员和观众身体同在现场的真实状态,强调戏剧表演是一种进行时态的、一过性的、无法替代的在场行为。在场(presence)、实时(liveness)和交互(interactivity)是现场性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一,现场表演是人与人的相遇,面对面的交流,是观演双方一起在场完成的聚会,不需要任何中间媒介。它强调观演双方身体同在现场,戏剧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在此地发生,并在此地所见,观演双方都是现场事件的见证者;其二,转瞬即逝是现场表演的本质。现场表演是进行时态的,不仅发生在现场,也发生在现在,即现在发生在现场。现场表演的生命存在于当下,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失的,是一个无法抓住的、一过性的流变过程;其三,现场表演既是观演双方身体动作的交互过程,也是内心共同经验的过程,他们可以随时调整交流的内容和方式,一起建构在场表演的意义。
现场性理论与实践并没有阻挡住影像渗入现场表演的步伐,相反,戏剧媒介化的趋势却改变了人们对现场表演中影像的认知,并逐步改写了现场性的内在含义。80年代后,大量投影、实时影像和数字影像被运用在实验性或商业性的现场表演中,关于“电影戏剧” “现场电影”和“数字表演”等新表演形态的作品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柏林剧评家拉尔夫·哈默塞勒(Ralph Hammerthaler)在一份剧院调查报告中指出:“如果说1990年代的戏剧界有一种趋势,那就是电影的趋势。”(12)https://epub.ub.uni-muenchen.de/13098/1/Balme_13098.pdf——Süddeutsche Ze itung , 12.1.1998, np表演评论家菲利普·奥斯兰德在《现场性:媒介文化的表现》中,描述了在媒介化社会中对现场表演的复制无所不在,探讨了影像媒介侵入现场表演后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对现场表演与媒介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媒体化’了,90年代,首先是在美国又激烈地进行了一次争论,这次争论围绕着在特别的媒体条件下的戏剧演出,围绕观众和演员‘身体的同在现场’,围绕所谓的‘现场性’。”(13)(德)费舍尔-李希特:《行为表演美学——有关演出的理论》,2012年9月,第98页。现场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与艺术形式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美)昆廷·菲奥里、杰罗姆·阿吉尔编;何道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9月,第182页。事实上,影像与现场表演之间不是相互抵触,彼此对立的,而是一种相互影响,彼此增进的关系。戏剧中的影像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实录现场演出的记录性影像;另一种是参与现场表演的交互性影像。记录性影像是戏剧演出的媒介化复制品,是对现场表演实况的记录与保存。一旦戏剧演出被转化成为过去时态的影像媒介,现场表演的活性就完全消失在影像之中,它就不再是现场表演本身,而是成为一种不在场、非实时、无互动的影像表演资料。记录影像对戏剧演出的媒介化保存,不是为了替代现场表演,而是为了让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可转播、可传阅的媒介形态,有助于演出艺术的研究与推广。与记录影像资料不同,交互性影像是一种参与现场表演、介入戏剧叙事、融入戏剧场面调度的媒介形态,具有虚拟在场、实时交流与灵活互动的属性。在媒体剧场中,交互性影像不是独立于现场表演之外存在的,它既存在于影像与身体表演的动作关系中,也存在于影像与演员、观众以及现场叙事的行动关系之中,是一种在戏剧场面调度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活性媒介。交互性影像的活性源于戏剧的二度创作,具体表现在:记录影像与表演动作、场景调度之间的配合叙事;实时影像与现场表演之间的互动叙事;数字身体与演员身体之间的交互叙事。影像的现场活性是观演双方在表演现场的互动中产生的,它取决于创作者对戏剧场景中表演元素的综合调度处理与设计安排,因此,媒体剧场中的影像是记录性的,也是交互性的,具有记录与交互的双重属性。影像一方面可以记录和复制现场表演,把预制的影像媒介内容与戏剧场面内容结合在一起,营造灵活多变的表演形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实时影像、数字影像参与戏剧场面叙事,与观演者一起创造出鲜活生动的现场体验。交互性影像与现场表演的融合建构了一种新的媒介表演形式,不仅增强了戏剧的表现力,延伸了戏剧的表现空间,也创造了新的现场表演的可能性。
二、交互性记录影像
在传统的剧场中,影像一直被视为预制的、过去时的、无法与现场观众和演员进行实时互动的视觉“异物”。现场表演是身体的、物质性的,而影像表演是光影的、虚拟性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无法穿越的时空屏障。在当代媒体剧场中,影像不是单向度的播映媒介,而是双向度的互动媒介,它不仅能够应对现场表演的变化、展开在场的交流,还能够将故事中非视觉的东西视觉化,用一种话语力所不及的方式触动观众。“媒体剧场艺术对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相比较而言,图像更具有魅惑力?在可以选择关注现实或是关注虚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魔力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图像?”(15)(德)汉斯- 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第224页。交互性记录影像是依据剧本情节和现场表演内容提前预制的光影媒介,它可以配合现场表演动作、协同场面叙事、创造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具有虚拟在场、实时交流、即兴互动的特点。
交互性记录影像强调光影媒介与现场表演的互动性,因此,影像的构图、动态和节奏变化都必须按照现场表演的动作内容来设计和处理。智利电影戏剧团(Teatrocinema)是一个立足于影像与表演互动融合、探寻新的戏剧叙事语言的表演团体。近20年来,剧团用独特的视觉设计方法将投影、动画、灯光、道具、声音与肢体表演等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批有新意的舞台演出作品,如《给蝴蝶喝水的人》(TheManWhoFedButterflies,2010)、《爱情故事》(LoveStory,2013)和《电影女孩》(TheMovieTeller,2015)等,他们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影像与演员交互表演的光影盒子——现场表演处于正投纱幕和背投银幕之间,演员动作与双重投影能够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交替叙事,形成了一种影像表演与现场表演无缝融合的舞台演出形式。2015年,胡安·卡洛斯·扎加尔(Juan Carlos Zagal)根据智利作家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利尔(Hernán Rivera Letelier)的小说创作了《电影女孩》,作品采用身影交汇的表演方式,表现了擅长“口述电影”的玛丽亚·玛格丽塔给穷困家庭和矿区小镇带来欢乐与幻想的故事。剧中富有想象力的影像设计突破了舞台时空的限制,巧妙地与形体表演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舞台表演的蒙太奇效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玛格丽塔童话般的精神世界和残酷现实中的磨难人生。在前期创作中,创作者根据剧本大纲构想出每一个戏剧场面的表演动作和影像内容;然后,用故事板的形式将影像构图变化精确地设计出来,并在演员排练和影像制作阶段不断进行双向的修改和调整;在后期合成排练中,逐步让表演动作与影像动态、灯光变化、画面音效等元素磨合一致,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多视觉元素之间精准融合的魔幻艺术效果。胡安·卡洛斯·扎加尔说:“在我们演出过的所有地方,观众总是用不同的语言告诉我们,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演,不管喜欢与否。但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致力于一个有趣的表演形式,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时间,精力和资源,我们会让它变得更完美。”(16)https://www.latercera.com/noticia/gemelos-la-obra-mas-exitosa-del-teatro-chileno-reciente-regresa-al-teatro-municipal-de-las-condes/他们的创作实验证明,记录影像的活性是在二度创作中产生的,场面调度重构了影像与现场表演的意义,一方面影像需要表演的配合来赋予现场互动的活性,让影像更加生动,另一方面表演也需要影像的协助来突破叙事时空的制约,使现场表演更加自由。
记录影像的交互性不仅体现在影像动态与表演动作的互动变化方面,也表现在影像内容与戏剧情节之间的叙事作用上。《回到兰斯》(ReturningtoReims,2017)是柏林邵宾纳剧院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迈尔(Thomas Ostermeier)以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本(Didier Eribon)的回忆录为素材创作的戏剧作品。该剧通过配音演员凯蒂(尼娜·霍斯,Nina Hoss)、导演保罗(布什·穆卡泽尔,Bush Moukarzel)和录音师托尼(阿里·加德玛,Ali Gadema)一起完成埃里本自传性纪录片的后期配音工作展开戏剧叙事。剧中的纪录片是依据作家埃里本的真实生活提前预制的,它是剧场演出中组织戏剧行动和承上启下的核心元素,由托马斯·奥斯特迈尔和塞巴斯蒂安·杜波耶(Sébastien Dupouey)共同执导。纪录片的摄影机镜头跟随埃里本的视点,真实记录了埃里本在父亲去世后,回到离开了三十多年的兰斯看望母亲的旅程,细腻再现了回忆录中描述的怀旧场景——走进贫困的兰斯郊区,重温过去的生活环境,与母亲一起看老照片等。大量的历史电影镜头、存档录像带的新闻资料再现几十年来法国政坛的风云变化,表现了作者自己年轻时到巴黎重建同性恋作家梦想的生活轨迹以及对保守工人阶级家庭政治立场转变原因的反思。
《回到兰斯》采用了大量的影像叙述和文本读诵,就像尼娜·霍斯所说:“这是在舞台上进行的自由对话,第一次与出色的演技无关。”(17)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returning-to-reims-a-german-theatre-companys-meditation-on-the-politics-of-working-class-families作品的现场表演主要围绕着纪录片内容展开,影片、回忆录和现场争辩三者之间互为动因,层层推进。戏剧的表层动作是纪录片旁白的录制工作,纪录片一直投射在凯蒂头顶的大屏幕上,她用一种深思内省的语调跟随着流动的影像,原汁原味地朗读着回忆录文本,大量的图片、影像和回忆录语音描述了过去和现在的各种政治势力对抗,为人物之间矛盾的展开做好了内容铺垫;戏剧的深层动作是凯蒂、保罗和托尼三人对影片旁白删减问题构成的思想和行为冲突。凯蒂是一个严谨机智的人,她对纪录片表现的内容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与保罗的矛盾源于对回忆录中一段旁白文案的处理。凯蒂站在回忆录作者的立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困境是邪恶力量造成的,而保罗则倾向于把责任归结到分崩离析的社会体制问题上。从这个情节点开始,戏剧矛盾的焦点从关于旁白处理的辩论转向了录音棚中三人之间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基于性别问题的凯蒂和保罗,还是基于经济问题的保罗和托尼,他们都共同面对着阶级隔阂、性和性别等社会盲点问题。演出结尾的处理非常巧妙,奥斯特迈尔将主演尼娜·霍斯的父亲威利·霍斯的亲身经历植入演出的内容中,用凯蒂的口吻讲述出身工人阶级的威利如何成为工会组织者和德国绿党创始人,帮助亚马逊河土著人捍卫自己权利的故事。作为接通现实生活的方式,导演将凯蒂手机上威利·霍斯的照片投射在她身后的屏幕上,引导观众一起回望自己家族的历史,回想埃里本回忆录中所描写的“原始场景”,共同思考个人成长的历程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回到兰斯》主要基于纪录片预制的内容展开叙事,影像既是构成戏剧事件和情节的素材,也是推动人物矛盾和冲突的要素,它折射出创作者朴素真挚的情感和自我反省的精神,使影像成为现场表演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元素。
无论是按照演员的现场表演来设计影像内容,还是依据影像的故事情节来构建戏剧场面行动,影像与表演的活性意义都是在二度创作中通过舞台行动与影像的互动交融创造出来的。约瑟夫·斯沃博达在总结《最后的一切》的创作时指出:“整个演出中反复的电影图像成为一种符号,它给予舞台事件一种新的、辩证的意义。另一方面,图像通过与舞台行动的对照也获得一种补充的意义。”(18)(捷)约瑟夫·斯沃博达:《戏剧空间的奥秘:斯沃博达回忆录》,第103页。由此可见,记录影像与现场表演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影像是表演动作的依据,它可以丰富身体表演的内容;另一方面表演动作是影像内容的延伸,它能够增强影像的现场表现力。交互性记录影像与身体表演的协同叙事,突破了传统表演的美学边界,改变了戏剧的叙事语言和创作方法,创造出了更生动、更有活力的现场表演形式。
三、交互性实时影像
影像在不断地改变剧场艺术以及我们对现场表演的体验方式。实时影像是摄影机对表演现场实况的即时呈现,而交互性实时影像则是一种与现场表演同步进行表演的形式,它不仅能表现此时此地发生在现场的事件与动作,还能让在不同空间中摄取的影像如同场景中的人物一样,参与现场表演,与演员互为表演主体地讲述故事。法国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通过描述戏剧的三个基本原则,反衬了电影作为一种新形式和新语言的艺术优势,“1.观众可以看到演出中的整个场面,始终看到整个空间;2.观众总是从固定不变的距离去看舞台;3.观众的视角是不变的。”(19)(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7页。由此可见,电影在叙事视点、镜头变化和时空转换方面比戏剧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影像与身体的双向即时交流是交互性实时影像的重要特征。实时影像直接参与戏剧叙事和现场表演,改变了传统戏剧叙事的时空结构与叙事方式,提升了现场表演叙事的自由度。
在现场表演中,实时影像融入了戏剧与电影场面调度的综合特点,突出叙事视点,强调镜头语言,重构叙事时空,不仅让观众可以直观演员在舞台上的行动,也可以借助于现场实况影像,从不同的角度实时观看不同景别的现场演出,生动地展现在场表演的活力。从2006年开始,英国戏剧导演凯蒂·米切尔(Katie Mitchell)一直在努力探索实时影像与现场表演融合叙事的演出形式。她与59制作公司(59 Productions)共同创造了一种称为“现场电影”(live cinema)的戏剧演出方法,将传统现实主义表演理念与实时影像拍摄以及女权主义主题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混合媒介戏剧作品。《禁区》(TheForbiddenZone)是她2014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Salzburg Festival)的委约作品。故事是依照科学家克拉拉·伊默瓦(Clara Immerwahr)和她丈夫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真实生平创作的。1915年,弗里茨·哈伯发明了氯气后,计划将这种毒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克拉拉得知后非常气愤,她认为科学应该用来改善生活,而不是毁灭生命。在劝阻丈夫无效后,她开枪自杀了。30年后,孙女克莱尔·哈伯(Claire Haber)成为了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光气解毒剂的化学家,她面临着祖辈们遭遇的相同困境。《禁区》的舞台空间采用多层布景设计,通过横向移动来表现地铁车厢、书房、花园、医务室、盥洗室等场景变化,五台摄影机实时跟拍现场演员的表演动作,突出重要的人物情感和细节内容。实时影像被投射到大屏幕上,与历史影像资料编织在一起,无缝地把现场表演、实时影像和不同时空的内容联接成为叙述整体,形成了一个现场与影像双重表演的叙事结构——观众既可以看到演员的在场表演、布景、灯光、摄影机运动以及同步拟音、配乐等变化过程,又能通过投影屏幕看到转换成为影像的现场表演效果,他们可以在现场选取自己喜欢的场景和内容,组成个性化的欣赏视角,创造自己独特的审美意义。
凯蒂·米切尔的“现场电影”兼具戏剧与电影艺术的两种传统。一方面她尊重传统现实主义的表演美学原则,强调人物性格的塑造,确保人物情感表达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她充分运用电影叙述视点和摄影机镜头语言来讲述戏剧故事,让影像深入人物的主观世界,展现人物细腻的心灵活动和微妙的行为变化。她认为剧场的物理空间给观众造成了一种冷静旁观的感觉,他们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视角,保持着不变的距离,只能通过语言对话来了解人物脑子里的想法。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意识流小说给米切尔提供了创作灵感,她开始探索用影像来描绘戏剧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复杂的人物行为活动,借助于实时影像来重构现场表演。她作品中的影像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她善于选择影像叙事的主观视点。无论是在戏剧还是电影作品中,“用谁的眼睛来看”既是讲述故事的视角问题,也是创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问题。2010年,她创作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时,将厨娘克里斯汀设定为主角,所有的剧情内容都依据她的主观视点来重新组织和结构。她说:“从这样一个人物眼中看世界,会让人触动,很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历史的宏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旁观的小人物。”(20)http://www.lifeweek.com.cn/2014/0509/44464.shtml叙述视点的改变使克里斯汀成为了朱莉小姐和男仆偷情事件的见证者,观众可以跟随她的视线去窥视和偷听,从中感受人物卷入情感矛盾时的复杂心理活动,同时,也能够切身体会到创作者对事件受害者的同情和怜悯。在《禁区》中,导演凯蒂·米切尔选用克拉拉·伊默瓦和孙女克莱尔·哈伯的视角来讲述她们在战争中的经历,探讨女性、人性、战争与化学武器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创作者对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独特思考和女性主义立场。其二,她善于运用特写镜头表现细节。凯蒂·米切尔认为现场表演的观演距离是制约观众视觉体验的重要因素,“大于现实”的特写镜头能够拉近观演双方空间的距离,增强现场表演的亲密感,并使不同位置的观众都可以从最佳角度来审视戏剧内容的变化。特写镜头具有放大、突出和强调的功能,能够让观众接近人物,近距离观察人物的微妙表情,更加细腻地展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活动。凯蒂·米切尔以特写镜头为主要表现手段,将人物的细微动作放大呈现在屏幕上,让观众从人物的眼神、手势、肢体以及物件道具的局部影像中,直观地理解戏剧矛盾中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为现场表演注入活力。“现场电影”的戏剧演出方法将电影的叙事手段与现场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软化了影像与现场表演之间的界限,创造出了具有现场性、实时性和互动性的现场表演新形式。凯蒂·米切尔说:“为了保持剧院的生命力,我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审视我们为什么要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做,这样我们才会与人们的需求保持同步。”(21)https://www.theguardian.com/stage/2008/jul/15/theatre.culture
在戏剧中,实时影像以视点和镜头语言增强现场表演的表现力,用影像蒙太奇手段和多屏影像组合方式,突破时空制约,改变叙事结构,不仅呈现了此时此地发生的事件,也表现了此时多地、此地多时发生的戏剧事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实验性表演艺术团体,如伍斯特剧团(The Wooster Group,1975)、戈伯小分队(Gob Squad,1994)等不断尝试用影像媒介来重构现场表演,探索影像与身体表演融合的各种可能性。“在伍斯特剧团的所谓‘后叙事’剧场中,电子图像成了一种自我反思的工具,直接和表演者的生活现实或舞台行为相关。”(22)(德)汉斯- 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修订版),第223页。从1975年开始,伍斯特剧团致力于将现场表演与影像、舞蹈、音乐、装置以及多种媒介科技交织在一起来解构经典戏剧作品,创作了《哈姆雷特》、《琼斯皇》和《毛猿》等前卫戏剧作品。他们以表演车库为创作基地,不断突破常规的束缚,运用混合视听媒介进行实验创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后现代叙事拼贴的表演风格。由英国和德国艺术家组成的“戈伯小分队”专注于交互视频与现场表演的探索与实验,擅长使用流行文化元素来探讨日常生活的复杂性,经常在非常规的演出环境中,创造现场行为表演与实时视频编播相结合的跨界艺术作品。2012年,他们在称为“现场电影表演”(live film performance)的《戈伯小分队的厨房》(GobSquad'sKitchen)中,把舞台空间分割成为三个实时拍摄的表演场景,并用巨大的投影屏幕将观众空间与表演空间隔离开来,让观众只能通过同步投影来观看三个空间中的表演行为。当演员从屏幕走入观众空间,或观众被演员拉入影像空间时,这种貌似游戏的观演关系发生反转,表达出艺术家对影像与现实、虚构与真实、亲近与疏离之间关系的独特思考。“在媒体交流技术中,数字化间隙把每个主体相互分开,以至或近或远的距离都变得无足轻重。”(23)(德)汉斯- 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修订版),第221页。同样,在互动现场电影(interactive live film)《客房服务》(RoomService)的创作中,他们将四个扮演旅客的演员各自封闭在酒店的房间里,每人都被摄影机监控着,只能通过电话与外界联系。在酒店的会议室中,观众从并排放置的四台视频监视器上观看演员的一举一动。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的六个小时里,演员与观众可以通过电话一起聊天、玩游戏,也可以请观众帮助挑选服装或者邀请他们到房间一起唱歌,他们无所事事,需要彼此之间的帮助,一起分享漫漫长夜中的无聊和恐惧。“剧场中的一种变化确实必须得到人们的重视:剧场变成了相距很远的合作伙伴之间通过技术手段的一种互动,虽然在技术上、内容上,这种互动现在都还处于原始阶段,但这种互动不断变得更加完美。”(24)(德)汉斯- 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修订版),第220页。交互性实时影像改变了观众的观看视角和关注焦点,它通过平行或交叉的场面组合方式,将现场观众视觉范围之外的、不同场景、不同时空环境中的故事内容呈现在观众面前,重构了现场表演的时空关系,创造了一种多时空维度、多表演场景、多媒介形态的复合型现场表演形式。
四、交互性数字影像
数字影像源于计算机的数据运算,是图形图像技术对人和物的数据化描绘与重塑。与记录、平面、线性的影像特性不同,数字影像是拟仿、立体、非线性的,它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依据想象和虚构,用模拟和仿制的手段创建出虚幻世界。数字影像是虚拟生成、“无中生有”的交互性仿真媒介,可将物质现场表演转变成为一种虚拟与现实共存的数字表演形态。史蒂夫·狄克生(Steve Dixon)将数字表演定义为“在所有的表演作品中,只要计算机科技在表演内容、技术、美学或呈现形式里,扮演一个主要而非辅助的角色。”(25)Steve Dixon:Digital Performance: A History of New Media in Theater, Dance, Performance Art, and Installation,(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7),3.数字表演是计算机图像交互技术与现场表演相互融合产生的一种新表演方式,它对演员动作的拟仿需要通过视觉设计、脚本编程、动态捕捉和人机交互来实现。一方面数字影像是观演者的虚拟替身,它的背后是表演者的活性身体;另一方面数字影像受“技术脚本”的控制,它必须按照脚本编程的指令来进行交互性表演行动,因此,数字影像在现场表演中既是自主性的,也是随机性的。在数字表演中,数字身体与演员身体互为主次、交互叙事,弥合了身体与影像之间的鸿沟,增强了戏剧表现复杂事件的能力。
基于RGB相机的在场人体姿态分析与实时数据驱动计算的动捕技术系统,在3D虚拟空间中实现了数字身体与演员身体之间表情动作的即时互动,为交互性现场表演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交互性数字影像通过图像显示设备和传感装置将拟仿影像“投射”到虚拟环境中,让演员和观众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依据自己的意志来控制现场表演行为,完成演出脚本的表演内容,满足现场演出的行动性和叙事性的需求。《VR_I:沉浸式舞蹈之旅》(VR_I:AContemporaryDancePieceinImmersiveVirtualReality)是一部多人、多场景的交互式虚拟现实舞蹈作品,由吉尔斯·乔宾(Gilles Jobin)当代舞蹈公司和阿塔尼姆(Artanim)技术团队联合创作。作品基于红外摄像机捕捉的肢体动作数据,用3D引擎实时渲染处理现场表演,借助于多种可穿戴传感设备将观演者融入交互式3D表演场景,创建了一个可与虚拟角色进行实时互动的“超真实”拟仿世界。在虚拟场景中,当一座大山像盖子一样被揭开,山洞中的五个虚拟角色才猛然发现已经置身于空旷的荒漠之中,宛如一只小蚂蚁被虚拟世界的巨人所注视。五个不同视觉造型的数字角色分别绑定五个观演者的肢体,他们既可以注视到自己的数字化四肢、身躯阴影和周围的数字角色,也可在沙漠荒野、建筑物客厅和城市公园广场的拟仿空间中进行自由自主的行动交流。交互性数字影像通过体感装置驱动数字角色的动作,让原本封闭在虚拟空间的数字角色与现实空间的身体表演连接在一起。他们在现场和虚拟界定的360度空间范围内,可自主选择参与表演的行动路径,自由调整关注的视点、角度和景别,随意挑选不同对象进行互动。在体验的过程中,观演者能不断介入现场表演,改变场景的表现内容,既是虚拟场景中表演的观看者,也是表演的参与者。导演、舞蹈家吉尔斯·乔宾创作的虚拟现实舞蹈作品将物理身体与虚拟身体无缝地衔接在一起,消除了人与技术物之间的界限,让现场身体表演走进了数字影像空间,通过人机的自主融合与交流,提供了独特的、身临其境的互动感官体验,创造出一种实时交互、虚实相生的舞蹈表演新形态。
交互性数字影像突破了主观与客观、真实与拟仿、物质与虚无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将视觉、声觉、触觉和嗅觉等结合在一起,建构一种全感官沉浸体验的表演形式,改变了我们观看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提升了数字表演的现场性和沉浸感。沉浸感是一个隐喻性的术语,源于将物体浸入液体中的物理体验,它被描述为一种主观状态,一种持续性的浸入与参与。最初的沉浸艺术始于全方位的图像景观,它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焦点上,营造一种抽离现实环境的幻觉体验。沉浸感分为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身体沉浸是指肢体连接虚拟影像,与拟仿物进行“类物理”交互时产生的存在感,它是计算机交互技术与身体感官综合作用产生的连通感受,这种感受是生理上的,直接而且强烈;心理沉浸是指情感卷入虚拟环境产生的心理认同,表现为对一个角色或一个事件的持续参与、吸引与共情。德国戏剧理论家汉斯·雷曼指出:“媒体信息技术在再现、展示、仿真现实方面似乎拥有无边的能力,把剧场的模仿能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26)(德)汉斯- 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第220页。当代VR戏剧是一种多感官参与、多媒介融合的沉浸体验艺术形式,它不仅强调物质与数字身体之间的相关性,也注重身体、媒介物与技术物之间的协同表演带来的沉浸式心理感受。
2017年,加拿大编导乔丹·坦纳希尔 (Jordan Tannahill)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和英国国家剧院的支持下,用自己与身患绝症母亲的感人经历创作了VR戏剧《让我靠近回忆》(DrawMeClose)。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VR戏剧作品,包含了戏剧事件、人物行动和时空变化。作品用一对一的现场表演互动来展现母亲和儿子之间的亲密关系,真实还原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碰触和心灵交流的感觉。现场的表演体验不仅实现了数字身体与演员身体的互动交流,还将道具、装置、触感、声音、气味等元素融入表演现场,创造了一种全感官沉浸体验的表演环境。作品中的母亲是一个虚实结合的复合形象,虚拟场景中的母亲形象是用黑色线条勾勒出来的数字角色,而她的表情、声音和动态则是由女演员在现场完成的。在演出现场15分钟的母子交流中,扮演母亲的演员始终陪伴着以孩子身份出现的观众,细心地用肢体引导着孩子的每一个动作环节,让孩子倍感亲切温馨,从而唤醒体验者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导演乔丹·坦纳希尔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者,身体是我的核心工具之一。对我来说,创造一种触觉上的体验很重要,它会引发观众对自己身体和另一个人身体的全感官意识。我想唤起童年的记忆,让它变得栩栩如生,可以触摸和互动。”(27)https://uploadvr.com/draw-me-close-childhood/创作者为了表现母子心灵之间的亲密感,增强虚拟表演的真实性,设计了丰富的多感官体验的装置和细节,如推开花园里一扇物理的门,打开窗户让微风吹进房间,用电子记号笔画画,与母亲的热情拥抱,让袜子踩在毛绒绒的地毯上,一股扑鼻而来的汗水味以及上床钻进被子与母亲一起聊天等。近距离的身体接触和物理装置的介入创建了一种全感官沉浸式交互体验的模式,将现场物体与数字影像连接了起来,实现了演员身体与观众身体、物理身体与虚拟身体之间的多通道交流。“一切媒介都是人的某种官能,心理或身体官能的延伸。”(2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美)昆廷·菲奥里、杰罗姆·阿吉尔编,第24页。交互性数字影像融入现场表演之中,延伸了观演者的身体、感官和意识,拓展了戏剧时空和感知维度,改变了现场表演的心理体验方式和演剧观念,促进了影像与现场表演的互补融合以及当代剧场感知系统的进一步变革。
结 论
记录影像、实时影像和数字影像参与戏剧场面叙事,重构戏剧时空,营造沉浸体验,创建了影像与现场表演的新型互动关系,改变了戏剧表演、观演和创作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戏剧表演的现场性、交互性和叙事语汇,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场表演美学观念。约克大学教授伊恩·加勒特(Ian P. Garrett)说,“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表演艺术行业可能永远不会恢复正常,它的未来可能依赖于沉浸式技术来支持人的表演。”(29)https://news.yorku.ca/2020/06/15/are-hybrid-productions-the-future-of-performing-arts-york-expert-on-immersive-media-available-to-discuss/未来的现场表演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网络是否具有提供实时协作表演的可能,VR戏剧是否能够成为大众接受的剧场表演形式,如何运用当代交互技术来提升表演现场的观演体验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的。“自古以来,艺术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时下尚未完全满足之问题的追求。”(30)(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57页。当前,剧场艺术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我们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新技术、新方法对现场表演艺术的影响。“新媒介产生新的结构形式”(3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向未来的麦克卢汉:媒介论集》,(加)理查德·卡维尔编,第33页。,任何一种新媒介,都是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戏剧艺术永远需要新媒介的融入来推动它的创新发展。随着生物量子芯片、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技术和影音交互科技的发展,更多的媒介技术物将与人的身体、行为和认知结合在一起,开启一个崭新的、更具想象力的全感官交互演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