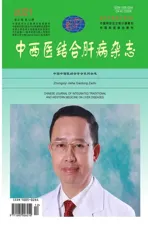中医药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的现状与思考*
2021-11-19吴佳栩
吴佳栩 江 锋 薛 婧
1.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 100700)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消化科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指由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化学药物、传统中药、天然药、生物制剂、保健品、替代补充剂及其代谢产物乃至辅料等引起的肝损伤[1]。西方国家DILI的发病率在一般人群中为1/10万~20/10万。2019年中国大陆的DILI临床回顾性研究显示,普通人群的年发病率估计为23.80/10万,由于分析仅纳入住院患者,因此实际发病率可能更高[2]。DILI临床表现不一,轻者表现为无症状性转氨酶升高,部分患者呈急性肝炎表现,严重者可发生肝衰竭而死亡,由于其临床表现多样,客观诊断及特异性治疗方法缺乏等,被认为是消化病学家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疾病之一[3]。因此,寻找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当前DILI治疗研究领域的重点与难点。
目前,DILI仍以对症治疗为主,抗炎保肝药物的使用有进一步加重肝脏负担的风险,免疫机制介导的DILI采用激素治疗需充分权衡获益与风险比[4]。近年来,中医药治疗DILI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示中医药能够调节免疫、减轻肝脏炎症、改善临床症状,具有多层次、多靶点、多途径的整体调控作用。但随着中草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中草药相关药物性肝损伤(HILI)报道呈升高趋势,对中医药治疗DILI的争议逐渐凸显。有鉴于此,笔者从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及基础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医药治疗DILI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思考,以期为有效发挥中医药治疗DILI的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1 中医药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的现状
1.1 理论研究 传统中医学没有“药物性肝损伤”的病名记载,根据临床症状的不同,一般将其归于“黄疸”“胁痛”“积聚”“肝着”等范畴。当前中医对于DILI的认识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其一,基于中医学理论针对“黄疸”“胁痛”“肝着”等疾病的辨证施治。如王国玮将DILI重症以中医“黄疸”范畴治之[5],认为黄疸色晦滞者为阴,属脾病;色鲜明者为阳,属胃病,不嗜食之“黄疸”为阴黄,已食如饥者之“胃疸”为阳黄,以茵陈蒿汤为主方辨证加减,临床注重多法合参,在临床观察中具有较好的疗效。李凫坚则以“黄疸”、“胁痛”辨证治疗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以肝脾失和、肝郁气滞兼湿热内蕴为病机,治疗以疏肝健脾解郁、清化湿热为法,具有良好的疗效[6]。肖小河等[7]制定的中草药相关肝损伤(HILI)临床诊疗指南,指出HILI中医辨证分型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临床应参照《中医内科学》中“黄疸”、“胁痛”、“积聚”等病症辨证施治。
其二,基于名医名家临证经验的辨证施治。各医家治疗DILI时多强调“治未病”理论的指导作用,注重调和肝脾,在培土建中的同时,根据原发病类型的不同,兼以养阴柔肝或苦寒泻肝等。尹常健在运用中医药治疗DILI时遵循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念[8],本病虚实夹杂,当以扶正祛邪为治疗原则,并结合肝胆的生理特点,治以疏肝健脾、行气活血、清热解毒。常占杰提出益脾养肝法治疗DILI,以脾胃虚弱为辨证中心[9],注重脾胃阳气,时时顾护胃气,深刻地体现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指导作用。路振宇等[10]认为抗肺结核合并真菌感染药物所致肝损伤以肝、脾、肺气血亏虚为本,疫毒、湿热、气滞、血瘀为标,从疏肝、健脾、清肺入手,拟定百丹疏肝方,发现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肝功能,有效控制原发病的进展,为进一步的抗结核、抗真菌治疗打下基础,临床疗效显著。其三,基于近年来创新性提出的“药物毒”、“药疸”等理论的辨证施治。近年来“药物毒”、“药疸”等病名的提出,创新和丰富了DILI的临床理论,从病因病机学等方面将DILI的临床发病机理更加合理化,认为“药物”作为致病因素,在DILI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本病的致病邪气——“药毒”,从临床实践出发更加重视“扶正祛邪”的治疗大法。赵文霞认为药毒侵犯为本病的直接病因[11],肝阴不足为病机之关键,湿热、痰浊、血瘀为病理产物,治宜养血柔肝,注重标本同治,以柔克刚,兼顾肝体阴而用阳的生理特性,扶正祛邪。钟森认为DILI由化学药物直接损伤肝脏所致[12],其病因、病机、辨证、治疗都有别于传统黄疸分类,因此提出了“药疸”的新概念,认为其治疗应以驱邪兼顾扶正为原则,具体治法为通腑泻浊、利湿退黄、活血消肿、柔肝健脾。
1.2 临床研究 随机对照试验(RCT)是临床研究方法的“金标准”。笔者通过汇总分析注册于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和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linicalTrials.gov)的肝损伤临床试验资料发现,肝损伤临床试验注册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对象以DILI患者为主[13],以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研究最多见,化疗药物性肝损伤、中草药相关性肝损伤、抗生素相关性肝损伤、抗甲状腺药物性肝损伤等研究也逐渐增多。中医药干预措施中,中成药占比最高,包括甘草酸制剂、水飞蓟制剂、六味五灵片、五酯胶囊、护肝片等。研究表明[14,15],中成药在增效减毒的同时,改善了肝脏生化指标,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及广阔的研究前景。顾瑾等[16]采用随机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评价水飞蓟宾对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研究共纳入568例初治肺结核病患者,研究中心涉及全国11家单位,临床研究质量较高。显示出中药提取物水飞蓟宾保肝护肝的良好作用。
真实世界研究起源于实用性的临床试验,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医诊疗的特点,同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RCT研究设计原则使外部真实性较差的弊端,真实世界证据已对临床实践、医疗卫生决策等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7,18]。近年来,中药复方制剂治疗DILI的临床观察研究很多,主要为经方加减、名家经验及专方专药,可分为清热利湿、疏肝健脾、活血化瘀及扶正祛瘀四大类。清热祛湿类以茵陈蒿汤为主要代表方剂,具有泄热、利湿、退黄之功,切中病机,对“黄疸”的治疗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明显降低DILI患者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改善黄疸、乏力、纳差等临床症状。疏肝健脾类以逍遥散加减应用广泛,临床疗效明确,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原发病的治愈率。活血化瘀以及扶正祛瘀类主要用于DILI疾病后期,肝郁脾虚,瘀血内停,主要表现为黄疸、面色晦暗等,慢性DILI可见肝脏肿大、肝掌、蜘蛛痣等体征,临床多在清热利湿、利胆退黄的基础上辅以益气活血化瘀之品,切中病机,在肝损伤临床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3 基础研究 随着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各种质谱联用技术、生物信息学等技术的应用,中医药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不断深入,已逐渐由整体动物模型研究向细胞、分子水平发展。现阶段中医药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单味中药、中药复方、中成药及中药制剂等方面。
单味中药治疗DILI活性成分的相关药理学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相关活性已转化成部分中成药及中药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已经用于临床的中药活性成分包括甘草酸、水飞蓟宾、多糖类等,其它许多中药活性成分包括环烯醚萜类、黄酮苷类、生物碱类,也已经证明具有确切的保护肝细胞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应用。中药活性成分对肝损伤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现阶段认为其有效机制主要在于调节炎症、氧化应激,调控转录因子及信号通路等,改善微循环,保护肝细胞、降低肝酶,促进损伤肝细胞的修复[19,20]。
近年来,在分子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医药干预DILI的靶点。王玉琳等[21]研究显示,肝细胞线粒体是药物肝损伤的重要靶标,中药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可以从多方面对线粒体起调节作用,可利用线粒体自噬来清除受损线粒体。付冉等[22]研究发现,孕烷X受体(PXR)及其下游基因的失调可能导致药物的治疗效果下降和/或药物肝毒性增加,以PXR为靶点进行中药活性成分筛选,可显著降低PXR诱导的DILI发生的风险,同时进一步以PXR作为防治DILI的潜在靶点进行中医药治疗干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中药复方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不断深入,治疗所涉及到的肝损伤类型不断扩展,涉及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化疗药物性肝损伤、抗甲状腺药物性肝损伤、抗精神病药物性肝损伤等。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疑难疾病治疗过程出现的DILI的高质量基础性研究,如郭娅娅等[23]对鳖甲煎丸治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RRT)后肝损伤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发现鳖甲煎丸降低了脾指数,有效降低肝门静脉压,改善肝微循环,降低ALT,有效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张磊等[24]通过比较银屑病DILI组、病例对照组及健康组之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和群落参数的差异认为嗜酸性粒细胞群落参数在中药治疗银屑病DILI监测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 关于中医药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的思考
2.1 正确认识HILI与中医药治疗DILI的作用 随着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逐渐提升,HILI的报道也呈升高趋势。因果关系评价虽作为鉴定中药诱导肝损伤的重要标准,但其性能受到草药资源鉴定不准确、病例数据不完整、使用期限说明和肝功能评价缺乏等诸多因素的限制[25],导致中医药治疗DILI的作用受到一定争议。
中药安全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能过分地为现代医学所拘泥。盲目排斥中医在DILI治疗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崇拜或者夸大中药治疗肝损伤的作用都缺乏科学性,应该合理看待中草药肝毒性的问题。需要摒弃中医药绝对安全及部分中药绝对性致肝损伤的“全或无”观念,客观评判中药源性肝损伤的总体形势[26]。不能把中医药与中草药的概念混淆,中医药有其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辨证立法、组方用药(包括中成药),有较为完整的配伍理论。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故无殒”理论在中药安全性评价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故无殒”的原则最初用于孕妇患大积大聚之病,但现代临床上逐步拓宽了其指导范围,认为疾病只要辨证准确,就无需拘泥于其单味药物的毒性,这为发挥中药的保肝作用拓宽了思路。近年来基于“有故无殒”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草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以中医药辨证用药减毒、“有故无殒”等传统理论为指导,融合系统毒理学、预测毒理学和精准医学思想和方法,提出要发展中药病证毒理学[27]。在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局面下,更加科学地发挥中医药在肝损伤方面的安全防治优势,对于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治疗DILI的临床研究质量 虽然中医药治疗DILI的研究很多,但治疗方案并不统一。治疗方案作为中医临床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中医临床研究设计,继诊断标准优化之后要考虑的要素之一,也是目前中医临床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28]。随着对DILI的认识逐步深入,根据DILI的临床特点,应建立DILI的个体化和规范化综合治疗方案,针对相应治疗方案之间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和优化,加强临床疗效的可重复性。注重研究基础的积累,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临床疗效,是提升DILI临床研究质量的关键所在。
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设计及健全的疗效评价标准是临床研究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医药治疗DILI亟需提升临床研究的循证医学证据级别,进行科学再评价,但由于中医药治疗DILI的诊疗标准不够健全,临床医生治疗DILI主要依据各自经验用药,疗效指标结局评判的主观性偏倚较大,临床实施受到限制。采用改良德菲尔法构建临床问题,可促进临床问题的提炼解决,加快临床专家共识、指南意见的进一步制定[29]。此外,将中医症状、体征等相对模糊性的描述,转变成相对客观的指标,是形成疾病证素动态演变规律研究中的技术关键[30]。随着临床流行病学、数据挖掘技术、医学统计学等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应用,为解决这一技术难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3 加强中医药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 中医药治疗讲究理、法、方、药,讲究辨证、动态地看问题,而单味药研究的孤立、静止、片面性与中医药理论相悖[31]。目前中医药治疗DILI的机制研究中,对中草药肝毒性的研究多是单味中药或单一成分,考虑到其与传统中医理论和临床应用并不完全一致,故应加强中药复方治疗DILI的机制研究。
机体状态被认为是DILI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异质型DILI的研究更加揭示了药物、机体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近年来研究发现,在DILI的发病机制中,基因多态性差异对疾病的易感性与体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体发病倾向的理论相吻合,为中医药治疗DILI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32]。在中医理论中,人的禀赋差异、后天所养所造成的体质差异是中医辨证论治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探讨不同体质人群DILI的发病机制,以及中医药对于不同体质DILI患者发挥效用的机制,将有助于阐明中医药治疗DILI的科学内涵。
开展中医药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人类肝脏疾病病理机制相似的实验动物模型的建立和应用。目前常用的肝损伤模型特征各异,肝损伤形成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动物实验的疗效与临床实际疗效也会存在差异。由于大多数中草药引起的肝毒性不能在实验动物模型中实现复制,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更为适合的DILI实验动物模型,加强实验方法与临床病理的一致性。通过合适的动物模型,可以更加高效、准确地筛选保肝中药,发现中药及其活性成分对于DILI的靶点干预作用,探索其保肝作用机制,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医药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水平,对于DILI新药源的拓展以及中药开发与临床应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语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DILI的理论传承与创新、临床及基础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整体研究水平仍有待提高。首先,要正确认识中草药肝毒性,需要客观评判HILI的总体形势,发挥中医药在肝损伤方面的安全防治优势;其次,通过优化中医药治疗方案,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提升中医药治疗DILI的循证医学证据水平;最后,应加强中医药治疗DILI的基础研究,探索建立更为适合的DILI实验模型,从而更加高效、准确地筛选保肝中药,揭示中药及其活性成分对于DILI的干预作用机制,促进DILI临床转化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