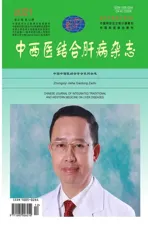态靶辨治中以疾病时间轴为特征的整体观念刍议
2021-11-19莫少丹郑景辉
莫少丹 郑景辉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 南宁, 530011)
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是中医学最基本的原则和特点,强调了疾病治疗过程中“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陈士铎《石室秘录》曰“同治者,同是一方而同治数病也。……然而方虽同,而用之轻重有别,加减有殊,未可执之以治一病,又即以治彼病耳。”仲景《金匮要略》在杂病的治疗中灵活运用“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之法,为后世医家治疗疾病的典范。目前多数医者在疾病辨治过程中,只重视刻下之证,而少有辨病者。即使寥寥辨病论治者,只不过是病下不分证而已,即所谓的“专病专方”。仝小林院士把传统中医的优势和不足总结为“三强三弱”——刻强轴弱、个强群弱、态强靶弱[1]。仝院士认为目前中医对辨病的认识不足。一个完整的整体观应当是全方位的、动态的、连续的。在把握疾病的发展态势问题上,要以“病”为纬,以“态”为经,基于“病证结合”思维模式,在疾病横向和纵向认识上层层剥离分析,从而实现对疾病的全方位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态靶辨治的理念。本文对态靶辨治中以疾病时间轴为特征的整体观念进行初步探讨。
1 古人辨证论治中的疾病整体观
《黄帝内经》开创了辨病论治理论之先河,非常重视疾病的空间及时间上的整体性。《灵枢》中有言“五色各见其部,视色上下,以知病处”、“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在”。《素问·离合真邪论》中提及“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藏以期之”。这里特别强调了病位的整体性。“知病”和“审病”即认识和了解疾病整体病位。《素问·脏气法时论》中描述肝病的变化规律:“病在肝,意于夏,夏不意,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意在丙丁,丙丁不意,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此处特别强调了肝病的传变在时间轴上的规律。此外,《素问》中的风论、痹论、厥论、咳论等多篇均描述了如何辨病,强调了《黄帝内经》对疾病整体认知的理念。《黄帝内经》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并由此产生最早期的病证结合为基础的辨证论治的萌芽,但《黄帝内经》对病证结合理论缺乏完整的认识,难以对诸多疾病诊疗做出辨病与辨证的结合,是以辨病论治为主, 寓辨证于辨病之中, 形成了辨病辨证论治的雏形[2]。
张仲景的《伤寒论》六经病证是典型的以时间轴为特征的疾病整体观的体现。他以“犹未十稔导致其宗族二百人死亡三分有二”的伤寒病作为一个整体,按照疾病的发展过程分期为三阳三阴,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同时提出了越经传、表里传、直中、合病、并病等时间发展规律,体现了张仲景“辨病”发展观、整体观的思想[3]。张仲景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分证治疗,如《伤寒论》第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汤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体现了《伤寒论》中“辨证”的思想。在杂病治疗方面《金匮要略》也是特别重视疾病发展的时间观,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篇》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牌,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如补之……”。此处也是以时间轴为特征对疾病的整体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所以,只有用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待疾病才能知其过去,瞩其未来,做到断前因、防未病的效果。
晋唐时期是承先启后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编纂、校注经典著作,阐述医学理论,研究养生,辑集方剂等方面颇多贡献。《诸病源候论·中风候》按照风气中于人-藏于皮肤之间-其入经脉-行于五脏-各随脏腑这样的动态发展规律描述整体疾病的过程。此时病证结合理论初步形成,在病的基础上分证治疗。众多医家对疾病的了解和认识比较深入,力求先辨病再辨证,辨病与辨证论治相结合[2]。
宋金元时期医家形成了以辨证为主的病证结合模式,如《素问玄机原病式》非常重视《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强调疾病的传变,如张从正《儒门事亲·三消之说当从火断》“今心为阳火,先受阳邪,阳火内郁,火郁内传,肺金受制,火与寒邪,皆来乘肺,肺外为寒所搏,阳气得施,内为火所燥,亢极水复,故皮肤索泽而辟着,溲溺积湿而频并,上饮半升,下行十合。”对消渴的传变进行了精准描述。朱丹溪《丹溪心法·中风》云“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详述了中风发展的分期,并提出了“《局方》风痿同治,大谬”的观点,指出了不同的疾病的本质特征,当然也不能异病同治。朱丹溪《格致余论》:“乳子之母,不知调养,怒忿所逆,郁闷所遏,浓味所酿,以致厥阴之气不行,故窍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阳明之血沸腾,故热甚而化脓……于初起时,便须忍痛,揉令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疖。”“……忧怒郁闷,昕夕累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描述了乳房疾病从乳腺炎最终发展成乳腺癌的疾病全过程。
明清时期叶天士和吴鞠通创造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为核心的温病病证结合模式,是病证结合理论的充实和完善;近代汇通医派开创了西法断病结合中医辨证的模式,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使其在实际运用中较为片面,对西医病名疾病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的了解较为浅显,但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对病证结合模式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4]。至现代,姜春华创造性地提出西医病名诊断与中医辨证施治相结合,为中医辨证论治注入现代医学科学的新鲜血液,其主张掌握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西医知识,克服中医辨证论治的局限性,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为中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5]。除了时病外,在杂病方面李用粹的《证治汇补·三消传变》提出“凡消病火炎日久,气血凝滞,能食者,末传脑疽背痈,不能食者,末传噎膈鼓胀,皆不治之症也”。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强调临证要知疾病传变之规律,未至而先治,阻病于未传。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所言:“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症状所由异,然后考虑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方必有主药。
2 当代中医对疾病辨治的不足
中医传承中辨病论治落后于辨证论治。由于时代背景和诊疗条件的限制,古代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比较笼统,很多疾病仅仅是根据症状或体征命名,如咳嗽和黄疸,所以中医更注重根据刻下症状判断身体的状态、动态和态势。中医多数病名在病理演变上难寻找其自身的特征性质变化规律和与类似疾病的鉴别点,故在治疗上也就难以体现遵循其自身的病理变化规律进行施治,也许这正是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滞后于辨证论治发展的主要原因[6]。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疾病从病因、解剖、病理到病理生理可以更深入更系统的进行了解和划分,与古代对病的认识截然不同。但当代和中医更强调的是辨证论治,强调的是刻下之状态,已不能适应现代人们对疾病的认知。
中医有“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之说,“同病异治”体现了中医个性化的特征。“异病同治”在于把握疾病的共同病机,但过分强调“异病同治”缺乏了对特定疾病发展变化时间轴的整体把握;“同证”寓于疾病的“异”之中,若忽略各个疾病传变规律的差异,只是强调治疗相同的证,可能会忽视掉疾病整个核心病机,便不能最大化的发挥中医药的效能。比如胃溃疡引起的胃痛和溃疡性结肠炎引起的腹痛均表现为湿热证,但不同疾病的整体时间轴不同,其各个阶段的表现和传变规律有明显差异,所用之方亦不相同。仝小林院士认为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属于缓慢起病的自身免疫性1型糖尿病,由于血糖检测的普及使得糖尿病诊断端口前移,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实证成为早中期糖尿病的主要证型,基于现代早诊断和专科化,疾病的全貌得以被揭示[1]。“消渴”理论作为古代中医诊治晚期糖尿病的辨治理论,显然已不能指导现代早中期糖尿病无明显三多一少症状者的诊治。运用态靶辨治思维,针对该病的早中期阶段,可予黄连类方调整患者的中满内热之态,再加入穿山龙、雷公藤抑制自身免疫反应的靶药,临床取得较好的疗效[7]。
慢病的长期性、反复性使得疾病的时间轴不够突显。中医擅长纵向观察疾病,把握疾病当下整体的“态”,审视疾病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态”,抓住每一阶段的核心病机,以确定理法方药,利用中药的偏性调整疾病的偏态,使体内的自调节、自修复、自平衡的能力得以最大效能的发挥[8]。但中医缺乏对疾病横向的全方位的认识,特别是慢性疾病,即仝小林院士提出的中医“刻强轴弱”的问题。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病有2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胃炎、慢性肝炎等,这些疾病具有病程长和反复发作的特点,病机虚实夹杂、错综复杂,难以准确把握疾病处于时间轴上的哪个阶段。辨病是中医的弱势,疾病的发展是一个横向推进的过程,疾病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较大,体现于外在的“证”随之改变,疾病各阶段的症状表现亦不相同。西医将疾病依病理改变分期,如肝病可分为肝炎-肝硬化-肝癌,糖尿病可分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早中期-糖尿病并发症期等[9]。对疾病的认识,中医是纵向整体,西医是横向把握。而一个完整的整体观应当是全方位的、动态的、连续的。在把握疾病的发展态势问题上,要以“病”为纬,以“态”为经,基于“病证结合”思维模式,在疾病横向和纵向认识上层层剥离分析,从而实现对疾病的全方位掌握[1]。
当前中医忽略了对现代医学及中药药理学知识的借鉴。由于中国古代科技条件的限制,中医缺少对疾病发展全过程的全面认识,临床诊疗中多聚焦于患者刻下症状,通过望闻问切收集四诊信息,对患者当前的“态”进行判断,并施以方药调整其自身偏态,从而完成辨证论治。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增加,现代疾病患者不仅重视临床症状的改善,更关注疾病的微观病理指标[10],尤其是临床症状不明显却有检验指标异常的患者,所以要求现代中医在宏观调“态”改善症状的同时,也要对微观病理指标进行针对性治疗。长期以来,中药药理学研究主要依靠于现代医学技术,以西医疾病为模型探究中药的药效及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医药理论,尚未能全面系统地揭示中药防治疾病的科学内涵[11],其在本质上并不符合中药作用的特点。中药作为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媒介,现代中医应努力完善病证结合模式下的中药药理学研究,贴合中医实际临床用药特点,增加中药药理学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价值,灵活运用现代医学先进的科学技术,借鉴中药药理学和中医理论,全方位把握疾病发展规律的全过程,动态的把握疾病各阶段的特征,促进中医诊治疾病的现代化。
3 “态靶因果”辨治中的疾病整体现念
疾病是一纵向的时空综合体, 证候是疾病某一时相的横断面[12]。现代人们多认为中医“治本”“见效慢”、西医“治标”“见效快”,是由于中医宏观调“态”是对人体内环境的一个大方向调节,但对疾病产生的具体机制和诊断,则缺少现代科学分析的依据,是对生命和疾病本质规律认识的欠缺[13]。基于临床实践,仝小林院士提出“态靶因果”的临床辨治方略,即借鉴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按照中医思维,审视疾病全过程,理清疾病发展各阶段,归纳核心病机,以确定理法方药量,并大力寻找治病的靶方靶药,关注疾病之前的“因态”和疾病预后的“果态”,实现对疾病的全方位掌握[8]。“态”是疾病某阶段的整体概括,蕴含状态、动态、态势之意,机体所处的环境一旦出现阴阳失衡,所表现出的即为“病态”,其中包括“因态”和“果态”[8]。“因态”是指重视病因,切断疾病的源头,防止疾病的进展。《素问·至真要大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言: “凡治病,先须识因; 不知其因,病源无目”、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起病之因,便是病本”均体现了传统中医对于把握病因的重视。“果态”是指重视疾病传变的结果,是“治未病”中“既病防变”的表达,《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叶天士《温热论》“先安未受邪之地”均描述了预防疾病传变的重要性,当兼顾预见性的治疗。“靶”是治疗的主要着力方向,具体是针对疾病、症状和临床指标的靶向性。“精准医学”是人类医学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医未来发展的方向[13]。中医用药对现代指标治疗的靶向性不足,无法精确的保证疗效,而西医依靠精细的仪器辅助可以精确的打“靶”,能及时解决刻下症状。因此仝小林院士将自己的处方原则总结为“态靶同调主病君,症靶标靶佐君臣,断因来路是为佐,防果形成谓之使”,在这种辨治模式下所开具的处方,就会从“态靶因果”4个角度全方位展示仝小林院士对患者病情的理解,方中的每个药(或药对、药组)都有的放矢,每个药(或药对、药组)都有据可寻[14]。
古有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均描述了疾病按时间轴传变的表现,每种疾病都有时间横向上的传变规律和分期,疾病的每一期在空间纵向上都有自己的特征性表现,故曰“一病一伤寒”。动态把握疾病的全过程及每个阶段的特征,对疾病建立起三维立体的“整体观”,便能弥补中医“轴弱”、“群弱”和“靶弱”的缺陷。仝小林院士将疾病“分类—分期—分证”后,完善了以病分期为纲的时间轴上整体观,更有助于中医宏观调“态”、微观打“靶”,进一步把握以态靶为纲的空间轴上的整体观,这便从时间和空间上搭建了现代医学辨病与传统中医辨证的桥梁,形成完整的中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最终目标是重新构建以态靶辨治为核心中医诊疗体系和以症靶标靶为核心现代本草体系。
4 “态靶因果”辨治肝硬化验案赏析
调查研究表明我国肝硬化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15]。肝硬化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可以并发上消化道出血、腹水、肝性脑病、肝癌等,最终可导致死亡。中医常把肝硬化归为 “鼓胀”“胁痛”“积聚”“肝积”等范畴,显然是按照患者刻下症状或体征单纯的对应,忽略了肝病整个疾病发展的全过程。仝小林院士认为肝病的整个时间轴传变可归纳为“郁、瘀、积、癌”四部曲,分别予疏肝、活血、化积、破癌治疗,如“郁态”予四逆散加香附、佛手,“瘀态”予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16]。当疾病过渡到肝积阶段,其病机特点为“正虚血瘀”,要抓住肝硬化“瘀阻血络”的核心病机,瘀血贯穿肝硬化整个病变过程。
验案赏析:患者,女,46岁。主诉: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17年,肝硬化2个月。病史:患者17年前体检发现 HBsAg、HBcAb呈阳性,诊断为乙型病毒性肝炎,2个月前行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考虑早期肝硬化变化,刻下症:鼻衄,齿衄,纳谷不馨,口干口苦,眠安,二便调。既往有2型糖尿病病史20余年。生化检验:ALT 55 U/L,AST 48 U/L,ALT 24.8 μmol/L,IDBIL 20.1 μmol/L,乙肝五项检验:HBsAg、HBeAg、HBcAb 阳性;腹部CT:考虑符合早期肝硬化改变,胆囊多发结石,慢性胆囊炎。舌脉: 舌质暗红,舌体胖大,苔薄黄、少津,舌底瘀滞,脉略滑数。诊断:中医诊断,肝积,肝经湿热、毒瘀阻络证;西医诊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代偿期),2型糖尿病。治法:清热化湿,活血消积。处方:鳖甲煎丸加减。方药组成:赤芍、丹参、三七、广郁金、龟板、醋鳖甲各30 g,酒大黄6 g,五味子20 g,虎杖12 g,鬼箭羽15 g,冬虫夏草3 g,桃仁9 g,水蛭3 g。之后复诊随症加减,五诊后多次复查HBsAg阳性,HBeAg、HBeAb阴性,ALT、AST、TBIL均在正常范围,复查超声示肝脏表面欠光滑。随访2年,未见病情进展[17]。
根据仝小林院士的“态靶辨治”用药经验可以“以方测证-以药定靶”。首先慢性乙型肝炎发展成肝硬化的主要病因病机为湿热疫毒之邪内侵,伤及肝脾,久病入络,而成积聚,病因究于乙肝病毒感染之“毒”邪,故审因论治需重视抗病毒治疗[18]。肝硬化的“果态”则为积聚成癌,需注重疏肝调脾、活血消癥,要预防“果态”发生发展成癌,符合中医“既病防变”的思想。依据仝小林院士提出的肝病“郁、瘀、积、癌”四“态”和糖尿病“郁、热、虚、损”四“态”,要从宏观把握“态”的主次,仝小林教授基于多年临证体会,提出肝硬化治疗关键在于早期干预,积极治疗原发病以防进展[17],治疗中应根据疾病发展时间轴上所呈现的不同的“态”和“靶”,分清主次,把握主要矛盾,该患者有17年肝病病史和20年糖尿病病史,现发现早期肝硬化,抓住肝硬化“瘀阻血络”这一根本病机,则应为“瘀态”兼“热态”,辨证为“肝经湿热、毒瘀阻络证”,故以鳖甲煎丸清热化湿,活血消积。
本案以鳖甲煎丸为首方,后渐精简为丹参、赤芍、醋鳖甲3味联合作为治疗肝硬化的小靶方,仝小林院士善重用赤芍治疗肝病,常用量为15~30 g[19],常配伍丹参、五味子、茵陈、虎杖治疗肝源性糖尿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虎杖、茵陈清热解毒、利胆除湿,具有降糖作用,可促进乙肝表面抗体由阳转阴[20],赤芍、丹参清热凉血、活血化瘀;五味子益气生津,可保肝解毒,使糖尿病合并肝炎者的转氨酶下降。上述5味靶药的常用量均为15~30 g。仝小林院士将活血化瘀通络法贯穿肝纤维化及肝源性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治疗的始终,使用的靶药包括赤芍、丹参、虎杖、大黄、水蛭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之品[19]。此外,仝小林院士认为沉疴痼疾非重剂无以至,根据多年临床经验针对肝硬化腹水治疗,针对性的使用商陆、葶苈子、车前子3味联合作为小靶方,常用剂量范围为商陆9~15 g,葶苈子 15~30 g,车前子15~30 g,临床上取得良好的消减腹水效果[21]。
态靶因果辨治,以现代医学的疾病为一个整体单元,运用发展观的哲学思维,注重疾病时间轴理念以及各个不同阶段的基本病理特征;从整体上把握一个疾病,然后宏观调态、微观打靶,从而实现了中西医的结合,宏观微观的结合,必将成为中医未来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