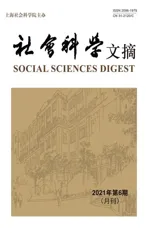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2021-11-15曹兵武
文/曹兵武
二里头文化以豫西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及其典型遗存命名,目前已发现遗址500余处,其分布以豫中和豫西的环嵩山周边地带为中心,鼎盛时期北至晋中,西至陕东和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鄂北,东至豫东,其影响范围则更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经过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和校正,时代大致上被确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二里头文化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原的腹心地带;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因此,无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都不影响其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早期华夏文明形成与演进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角色的地位。从考古学文化内涵来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也的确有诸多非同一般的表现,与之前和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包括龙山时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遗址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多重文化要素聚合的文明核心横空出世
首先,二里头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很多学者都从类型学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过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随着考古学发现与认识的深入,多数学者同意,就作为当时日常主用和考古学文化最精确标记的陶器组合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和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融合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因素,经短暂的新砦期快速发展而成。当然在此前后,山东、安徽尤其是西北方向的陶器等文化因素也曾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因此,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对周邻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广泛吸收与整合创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学文化往往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变或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选择性地甚至是主动地聚合了周邻包括远方的多个考古学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里头遗址所见铸铜、玉器与绿松石加工和应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贝等新鲜因素,大都是广泛借鉴并经过改造提升和赋予新的内涵后再加以使用。在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形态中,传统中国的五谷六畜,除了马,其余已初步齐备,复合型的农业经济俨然成型,同时已有了高度发达并专业化的制石、铸铜、造玉和制骨等手工业及专门作坊,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率先采用复合范制造青铜容器并作为垄断性礼器的高超技术。显然,相对于之前多地零星发现的并未在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类小件铜制品,只有二里头文化才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铜时代的源头。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诸多地域性文化相互作用中表现出了突出的超越性。二里头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仅超乎原有诸文化或文化类型之上,还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响。就纵向时间轴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其所在地区经过仰韶时期区域一体化的高峰、分化、相对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范围的统一与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阶段一样,也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广泛的辐射性影响。如果以二里头式牙璋、鸡彝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文化因素的分布来衡量,其辐射范围之大完全不亚于仰韶文化顶峰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不同之处是,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让周邻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如东方的岳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等,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文化——黯然失色了,这些周邻文化不但缺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高级产品,而且原来已有的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显示出粗鄙化趋势。这显然是这些文化的社会上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响之后,对意识形态物品的有意放弃所致。
以上两点使二里头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时期周邻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也不同于各地百花齐放阶段的诸文明制高点,如红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脱颖而出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华夏正统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标志,诚如许宏先生的概括:二里头文化让早期中国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发展到月明星稀。
文化大统的形成与地域协同防御模式的出现
苏秉琦先生认为,早期中国各文化区基于早期农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并次第发展到古国这一阶段。戴向明先生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可能已经走到了王国阶段。而二里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进一步走到了王朝——万邦来朝的阶段。周边诸考古学文化或者被二里头文化所整合,或者要面向二里头文化来朝拜正统,同时也受制于这个正统所代表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传统的钳制。而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早期中国文化的相互作用圈中,还上演了接续这个正统乃至争夺这个正统的历史趋势,直到秦汉时期稳定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比如,商与周都是与二里头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却共同接续完成了同一个文化正统,不仅加盟了这个文化大统,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样将其发扬光大。而在考古所见的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里边,可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缔造了这个超越各地区早先的族群文化传统的大传统,并让其他区域性文化传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格为小传统。
自农业和定居的村落产生之后,各地逐渐孕育的地域性文化传统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化乃至族群上的共同体。这种传统可以细分为血统、器统、艺统,还有心统(包括后世常被提及的道统、学统、正统)等,它们各有谱系传承,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定地理单元内基于早期农业的萌兴,缘于血缘关系自然地发生、发展和扩展,并与周邻诸文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其中,仰韶文化曾经借助区位优势和大暖期的环境机遇,在区域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占得先机,率先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据广大分布范围,为华夏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语言基础。
在以农业部落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出以内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设防聚落为统领的金字塔式复杂社会。二里头文化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地域协同式防御模式,以巩义稍柴、郑州大师姑和东赵、新郑望京楼、孟州禹寺、平顶山蒲城店等多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对二里头大邑形成拱卫之势,而二里头自身则仅在行政中枢部位建设宫城进行有限的防御。二里头和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所在,构成文化的中心区,而超出这个文化中心区的重要地点,比如交通要道或关键的资源地,则运用防御性极强的中心聚落将其置诸管辖之下,如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这一全新的空间防御与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岗文化全盘继承并扩展。考古发现表明,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新郑望京楼、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重要遗址纷纷在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在二里岗阶段进行了改建或重建,继续扮演区域性中心聚落,和新崛起的郑州商城形成共荣关系。二里头自身也在延续的同时渐渐被近旁的另一个二里岗文化的大邑偃师商城所镇压、取代。显然,这些现象应该是国家或者国统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现。
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文化正统的诞生
二里头文化这种能够整合各区域传统的更大的文化传统,或可以政统之始视之。区域传统演进过程中自然也伴随社会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分层之分,以及相应意识形态的诠释系统,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则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阶级和各类文化因素的系统嵌套和整合。因此,尽管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里的若干地区都曾经发展到复杂的初级文明社会,但终未迈过国家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在对当地和周邻诸族群的文化要素的传承、交流、吸纳、整合、改造和辐射中,缔造了一个超越区域内部不平等乃至区域间相互攻击、掠夺的新型的相互作用与社会治理模式,并可能达成了某种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共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超越诸族群文化传统之正统和大统,又被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所接续。显然,被接续的正是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一种华夏文化正统,此后,它又继续被周人和秦人接续并发扬,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朝向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华帝国演进。能概括这样一种政统及其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也只能是“国家”这一新的发明创造。所以,中国的国家文明自二里头文化始。
支撑这一国统的正统文化观念,比如宇宙观、意识形态系统、祭祀系统、礼制系统等,同样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快速发展并被传承下来。考古发现主要体现在继承创新的高等级器物的生产工艺和组织形态方面,其中尤以青铜礼器及其代表的礼仪文化最为重要。二里头遗址迄今已发现的青铜器超过200件,有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几乎包括当时东亚大陆各文化中的各类青铜器类,而青铜容器则为二里头文化综合各地青铜冶炼、制陶工艺及造型技术和观念等所进行的独创,已经发现的器类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铸铜作坊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紧挨宫城南部并以围垣环绕,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最末期,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国铸铜作坊,并且可以肯定是由宫廷管理并进行生产的。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也极具特点,和东部海岱、红山、良渚等文化中大量的饰玉、巫玉以及西部齐家、石峁、清凉寺等文化的财玉、宝玉等在制作与使用方式上也表现出根本性区别,比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等,尽管较多地借鉴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已经无关,而多直接用在各种场合中表现贵族的权威。发掘者许宏先生推测它们或许已经是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阶段已超越了原来丧葬与巫术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礼玉文化。再往后,又进一步借鉴并整合各地尤其是东部巫玉丰富的文化内涵,发展为更加完善的中国传统礼玉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早期玉器的形制和含义已经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显然,二里头这些复杂的高等级器用与工艺品背后蕴含着新的意识形态观念,已经形成了与国家正统相对应的新的知识、含义和礼仪系统。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较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与突破,其文化因素、聚落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体现出超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一是得益于中原内部族群与文化互动的前期基础和特点,二是受到自仰韶晚期以来中原周围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高峰的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源自西北地区的人群与新鲜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到龙山时代晚期,由于文化自身演进和环境的变化,各地考古学文化间互动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强。中原地区因为仰韶时期之后相对的低潮和空心化,以及相对适中的地理环境,可能还要加上黄河在新气候环境背景下冲积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空间这个因素,成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个方向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剧向这里聚集,形成交叠融合的态势。同时,由于羊、小麦、冶铜等新文化因素的引进,加上持续的高强度开发与环境变迁,在距今4300年左右,北方地区人口大规模增加,文化开始蜕变,相互之间的竞逐空前加剧。今天的长城沿线地带在这一阶段兴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群,以及像石峁那样的巨型中心军事聚落,这可能也成为相当广阔地域内的野蛮征服掠夺者迫使晋南盆地地区人口大规模集中并快速走向复杂社会的原因。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经试图整合各方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经初步跨越国家的门槛,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时空张力下被颠覆而崩溃。作为仰韶兴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等文化的动静不可能对中原腹心地带的族群没有影响。它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区域性整合,并主动向各方出击,尤其是着力于西北方向,直接将晋南作为资源要地和缓冲地带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寻求在先进文化资源和日益复杂的互动格局中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
赵辉先生在《“古国时代”》一文中将这一波巨变概括为社会复杂化或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第三波,但除了赵先生所说时空上的异同之外,这一波的模式和意义也和前两波完全不同。第一波是自发性的,是农业文化传统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高潮,仰韶文化拔得头筹,而东方大汶口—龙山、东北红山、东南的崧泽—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等各有精彩华章,甚至后来居上,快速步入高级酋邦社会。其中大汶口、屈家岭等环境优裕、物品丰盈型社会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举挺进中原,估计也会有不少移民趁机填补此地仰韶后期的相对空白。但随着第二波源自北方的激荡,长城以北自庙底沟二期以来各种快速变异和新颖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断南下,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长江中下游甚至更南的东亚大地,让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为之骤变,区域传统间的竞逐进入白热化阶段,连同良渚和石家河那样的巨型中心聚落所表征的早期文明也轰然坍塌。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主角的第三波才真正整合了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铸出以国家为载体的华夏文明的正统和文化自觉。
结语
古人常说逐鹿中原。中原地区的地理位置确实便于各族群和文化的你来我往,但是如果说仰韶文化还只是一种因为人口增长引发对外拓展的不自觉的奠基与辐射效应,那么二里头文化才是真正的整合式聚变,显示出吐纳有序的辐辏效应,使得中原地区在东亚大地脱颖而出,最终树立起华夏文明的文化正统地位。所以,环嵩山的中原被称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这里既是东亚大陆南北地理与气候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国地势西北高地和东部低地的交接之处,还是黄河中下游黄土流失和堆积的转换点,溯河而上和沿河而下的文化交流聚集效应十分明显。不同时期的不同族群、文化、技术、产品等在中原地区层累,并因在原始耕作条件下易于开垦的土地具有极强的黏着力,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罕见的族群和文化熔炉之一,由此成为早期华夏文明核心的不二选择。
人类在东亚大地上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上传承不断的族群集团和国家文明的形成,则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产生以来各区域性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了旧石器时代业已奠基的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融合、东亚基于早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及其相互作用圈的充分发育和搅拌发酵,甚至包括西亚、中亚文明因素的不断涌入和刺激。华夏文明核心从仰韶的雏形到二里头的定调,实则是一个不同族群、技术、物品、观念以中原为轴心的不断交融、磨合的长期过程。作为各种文明要素集大成者的二里头文化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断融合、反复融合、合之又合的结果。但是,二里头文化以其独特的模式合出了新意,合出了自信,并合出了一个跨族群的格局和境界,最终合成了一个脱颖而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和大统,凌驾于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上并被整体性地传承和光大,整个东亚文化相互作用圈由此完成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