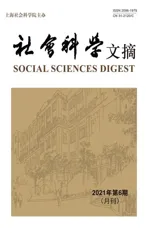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考察
2021-11-15沈长云
文/沈长云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逐步实现,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探寻中华民族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关乎时代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华文明有多久远?如何起源?怎样形成?这些问题不仅是学界、公众的关注焦点,也是党和国家关心的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与考古工作者有责任“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本文将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从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
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强调以农为本。农业产生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才会有社会分工,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贫富分化,由此产生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最终发展为国家。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农业产生为上限,以国家的出现为下限。
中国古代文献将农业产生的原因归功于神农氏。《易·系辞下》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即以神农氏为教民使用农具、进行农业耕作活动的第一人。这篇文献还提到神农氏以前的伏(庖)牺氏,称伏牺氏创造了八卦和结绳记事,并发明了网罟,教民“以佃以渔”,即进行田猎和捕鱼活动。后来的一些文献又提到伏牺氏之前还有燧人氏,他发明了钻木取火之法并教民熟食。以上三人被人们尊为“三皇”。“皇”的意思是光明、伟大,后引申为对圣王的尊称。其实,无论是用火、渔猎,还是农业,都不应是个人发明,农业刚刚诞生时,也没有真正的“皇”或“王”。“三皇”时代应当理解为自远古直至农业产生过程中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古代文献中,常将神农氏与“炎帝”并提,这种情况或许反映了我国早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神农氏又被称作烈山氏,“烈山”的本义是“烧山”,亦即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据研究,炎帝生活在陕西渭水上游一带,表明渭水流域是我国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三皇”之后的“五帝”时代,是向国家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是诸多文明因素蓬勃发展的时代。所谓“五帝”,出自孔子所传《五帝德》和《帝系》,具体指夏代以前的五位古帝王,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但所谓“古帝王”,也只是前人的一种解释。实际上,“五帝”是夏以前一些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早期文献称黄帝、颛顼为“黄帝氏”“颛顼氏”,又称颛顼为“高阳氏”,称帝喾为“高辛氏”,称他们的16位后人(所谓“才子”)为“十六族”。这些称谓也反映出所谓“五帝”应是我国上古时期一些氏族部落首领。这些氏族部落势力有限。《国语·晋语四》记载了黄帝、炎帝两个氏族部落的情况:“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他们都生活在陕西西、北部一带。另外,那时所谓的“帝”也不止五位,仅《山海经》就谈到“五帝”之外还有帝鸿、帝俊、帝江,其他未有“帝”称号却与“五帝”地位接近的尚有蚩尤、共工、祝融、太昊、少昊等,他们也是部族首领。
“五帝”以黄帝为首。黄帝生活在距今4500年或4300年前后,这意味着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所谓龙山时代大体相当。此时社会分化已相当明显,各氏族部落及部落内部的不平等已是普遍现象。氏族上层役使下层民众,驱使他们掠夺其他部族的财富,引发部族间的冲突和战争。黄帝和炎帝之间就发生过冲突。文献记载他们因为“异德”而“用师以相济(挤)”,即两个部族为利益而相互逼迫,以致发生阪泉之战。黄帝与东夷部族首领蚩尤也发生过一场战争,史称涿鹿之战。据研究,涿鹿与阪泉都在今河北张家口地区,由此可以推想其时黄帝的势力主要在北方,并没有扩展到中原一带。但是,战争和掠夺对国家的产生起到推动作用。各部落为了自卫,纷纷建起城墙,有的还附带壕沟。正如恩格斯所言,“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这正是我国文明社会产生前夕社会面貌的生动写照。
经过“五帝”时代的发展和战争催化,夏朝诞生了。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其诞生可以作为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有学者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可以说抓住了夏代国家的最主要特征。从制度上说,尧、舜担任氏族部落联盟首长时,实行禅让制,即由部落联合体内各部落首领推举联盟首长的制度。启继禹位,开启了“家天下”的世袭制,才形成真正的王权国家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夏朝将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如《左传》《国语》所载之有虞氏、有扈氏、有莘氏、斟灌氏、斟寻氏、有仍氏、有戎氏、昆吾氏、豕韦氏、有穷氏等,纳入其统治,其中有的部落与夏后氏不同姓,可见夏显然已经具备了恩格斯所说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一国家形成的标志,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
夏建立在豫东鲁西一带。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古河济之间即今豫东鲁西地区。这里正处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与世界上其他发源于大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一样,我国最早的文明古国的产生也与河流滋养密不可分。
在文献传说中,夏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紧密相连。禹由于治水成功,取得了对参与治水部落人力、物力的控制,并逐渐成为凌驾于这些氏族部落之上的统治者。禹治水的地域问题涉及治水之事的真实性问题。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专作《洪水解》一章,根据我国地形特征和历史发展阶段,指出大禹治理的洪水并非《创世纪》记录的世界性大洪水,其发生地域主要是在兖州,即古代的河济之间。这个说法与上述我们推测的夏代地域相呼应,证明前人有关夏朝史事并非凭空捏造。
夏直到灭亡前,其中心区域仍在古河济一带。《诗经·商颂》记载了商人对夏的征伐,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豕韦、有扈、昆吾皆属河济地区的部族,可见夏桀居处仍在东方。夏朝灭亡后,其后裔在更远的东方建立起杞、鄫两个小国,这些都证明夏是建立在东方的国家。
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阐释
考古学成果表明,我国农业产生的时间大致在距今1万年前后,即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开端。较早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黄河流域主要种植粟、黍两种粮食作物,长江流域基本种植水稻。到距今8000—7000年,随着农业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稳定,村落也出现了。其时黄河流域几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如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及大地湾文化等,都发现有村落遗址。南方的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四周还有壕沟和土筑围墙,俨然是一个设施完备的村落。在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北方的村落数量已发展到5000余处,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河姆渡、马家浜、大溪等)的村落数量也已超过2000处。仰韶文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时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已达到整个东亚的最高水平。与“五帝”时代相当的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如前所述,这个时期是我国文明社会的前夜,许多大型遗址或城址——良渚、陶寺、石峁、芦山峁等——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仰韶文化前期,由于整个社会尚处在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阶段,聚落数量虽多,但规模有限,面积一般仅有数万平方米或十余万平方米。聚落之间未发现明确的从属关系,聚落内部成员基本平等。迨至仰韶文化中后期,情况发生变化。不仅聚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现象,而且随着聚落间人口和经济实力差距的出现,各聚落也产生了等级分化,并出现了一些强势聚落对弱小聚落的控制现象。在聚落形态上,呈现出以一个较大型聚落为中心、四周伴以若干中小聚落的所谓“聚落群”结构。至龙山文化时期,各相邻聚落群或因血缘相近的关系,又往往集结成更大的聚落群团,这应当就是人们习称的“族邦”。那时各地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族邦,文献所称“五帝”时期“天下万邦”的政治格局,便是这样产生的。
“五帝”时期,物质文明的进步十分显著。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具有文明进步标志意义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历史文献将众多发明创造归功于黄帝,反映出“五帝”时期是一个文明较快发展的时代。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作篇》专言历史上各时期的发明创造,所言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多数与该时期(不限于黄帝时)的考古发现相印证。如打井技术的出现,旗帜、冠冕、服饰、器用、埋葬等礼仪制度或用品的使用(例如玉礼器的使用),礼乐、乐器与乐律的出现,等等。
还有一些“五帝”时期发明创造的记载,如羲和占日、伶伦造律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沮诵、仓颉“作书”,即创造文字。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文字产生的年代仍有争论,但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文字雏形的观点,获得大部分学者认可。考古发现山东、江苏一带龙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晚期的陶文,有多个符号连用的现象,说明它们已经具备了记录语言的功能。另外,传说黄帝妃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与这一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织残片亦可相互印证。如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距今4400—4200年)出土丝线、丝带、绢片等使用的蚕丝,经鉴定为家蚕丝。
“五帝”时代以后,便是有关夏代的考古。谈到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一般会想起分布在今河南省西部伊洛汝颍一带的二里头文化,认为该考古学文化就是夏文化。笔者赞同二里头文化包含夏文化的遗存,但不认为二里头类型可以反映夏文化的全貌。因为据张雪莲等学者的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这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主要是夏代后期。偃师二里头遗址也确实是夏晚期的一处都邑,因为文献明确记载这里是夏桀的居处,但是二里头类型以前的夏文化面貌却并不明朗。有学者将搜索的目光落在二里头遗址东南方向的新砦遗址上,但新砦文化存续时间较短,也难说是早期夏文化。一些考古工作者认为,新砦遗址中的许多文化因素,来自更靠东方的造律台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这表明早期夏文化,或者说其中的部分文化因素,也应来自东方。由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当是夏朝末年向西扩张后修建的一处别都性质的邑落。文献有夏末几个君主在此活动的记录,这与二里头文化中存在来自东方文化因素的现象可以相互印证。
笔者认为,有关早期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应当到东方去寻找。如上所述,文献记载夏的地域主要在今豫东鲁西一带。这一观点,在考古学材料上并非没有线索。其一,部分夏的都邑及诸侯居邑已可与河济地区的考古遗址对应,如濮阳高城之于夏后相所都之帝丘,曹县莘冢集之于有莘氏,滕州薛国故城叠压着的龙山夯土层之于任姓薛国等。其二,《禹贡》所述禹时民众“降丘宅土”,亦可以落实。豫东鲁西一带至今仍留有许多土丘,不少可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当时人们很可能是依靠这些土丘躲避洪水。与中国同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大多兴起于河谷或平原地区,在河水泛滥时会利用人工垒筑的土丘避难。其三,考古发现古河济地区存有不少龙山时代的夯土城址,城墙有抵御洪水的功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鲧禹在此抗御洪水的真实性。其四,这一带曾发现早商时期的沟洫遗迹,虽时代稍晚,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禹治水“尽力乎沟洫”的历史线索。
中华文明起源的人类学考察
文化人类学是探寻人类各种文化形态的科学,与历史学对各个具体民族历史的考察不同,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民族调查,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及文化演进展开研究。其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国家等理论问题的讨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参照价值。
首先是我国文明起源跨越了人类学中哪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过去,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摩尔根(L.H.Morgan)的进化理论,提出人类早期社会经历了原始群、氏族组织、国家三个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却有些笼统。特别是从氏族组织到国家这一发展阶段,到底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如何过渡至以不平等、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未能作很好的解释,以至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从原始社会(societas)到政治社会(civitas)的政治变迁,相对而言是突然发生的。”有鉴于此,以塞维斯(E.R.Service)等人为代表的新进化论者提出,在平等的氏族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不平等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即“酋邦”。应当说,酋邦理论确实能够更好地阐释有关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问题,其构建的国家形成理论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说,“酋邦时代”的提出,对马克思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有所补充和完善,对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有借鉴意义,对相应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有推动作用。
就我国历史而言,酋邦的出现或可上溯至仰韶文化中晚期,也是出现社会分化的时期。此前,我国基本还处在平等社会阶段。直到此时,社会才开始进化到不平等社会,亦即酋邦社会阶段。上文已述,龙山时代是“天下万邦”的局面,这里的“邦”就是酋邦,也即部分考古学者所说的“古国”。“古国”的性质并不是真正的国家,而只是酋邦。从事聚落考古研究的学者发现,龙山时期的社会实由许多聚落群构成,每个聚落群由一个较大的聚落统率若干小聚落,若干聚落群又往往构成更大的聚落群团,这些聚落群或聚落群团实际便是一个个酋邦。聚落群或聚落群团的这种分层结构,正是酋邦社会的典型特征。酋邦有大有小,一些较大型的酋邦可称为复杂酋邦,但其性质仍然是单纯的氏族组织,并不是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群组成的社会组织。
酋邦在适当的地理环境中,随着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一般会发展成国家。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世界历史发展,我们认为,由酋邦过渡到国家的道路一般有两条:一条是在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酋邦内部结构的改变,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建立起对下层民众和奴隶的统治,即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形成的道路;另一条是通过众邦(众酋邦)的不平等联合,即在一个大邦的控制下,通过这个邦首领的身份性质的转换,从而建立起对各个族邦的统治性政体。后者涉及的地区更为广泛,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轨迹与此类似。
对于经由后一条道路建立起国家制度的民族来说,由于未对原有酋邦组织进行彻底破坏,在国家建立以后,这些酋邦组织及相关氏族制度仍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以保留,并且新的国家还要依靠各酋邦及氏族组织对广大民众进行统治。据此,我们可以称这些国家为“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就是早期国家。在整个三代时期,酋邦或由酋邦演化成的各种血缘组织一直存在,直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