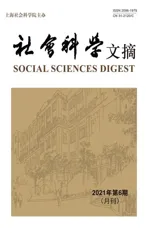人文学科的“科学”与“人文”
2021-11-15葛剑雄
文/葛剑雄
学界通常所谓“文史不分家”,其中的“文史”应指所有的人文学科。各个人文学科都包含人文与科学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它们所涉及的事实、文本等属于科学范畴,适用于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切的理解和评价等则属于人文范畴。我们提倡科学与人文结合,关键在于科学与人文、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相互尊重。
何为“文史”
学术界一直有“文史相通”的说法,我没有查到此话的最早出处,不知道始于何时,但以往常听老师前辈这样说,或者说成“文史不分家”。年轻时以为“文史”就是指文学和历史,以后才明白不是那么简单。
如清人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这里的“文史”都是就史学而言。章氏认为史学包括史事、史文、史义,“文史通义”的大意就是通过对史事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所以这里的“文”是指历史文本和所记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指文学。
我理解“文史相通”中的“文”,并非仅指文学,而是泛指人文、文化。古代中国没有现代的学科分类,《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除了史部以历史为主,其他三部都可以概括为“文”。所以“文史”实际上是指所有的人文学科,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今天,中华书局的《文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所刊登的文章,也并非只限于文学和历史,而是涵盖所有的传统的人文学科。我注意到,《文史哲》杂志的宗旨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自然亦不限于文学、历史和哲学,同样是指传统的人文研究的全部内容。
在传统文化中,“文史”二字的涵义是不成问题的。但到了近代学科体系中,“文史”具体对应哪一门或哪几门学科,就需要特别加以明确了。前几年有人提出要将国学设立为一级学科,要设立国学博士、硕士学位点,就遇到这个问题。无论是教育部的学科设置,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分类,都是按照现代学科的标准,无论几级学科,都没有“国学”一门。另一方面,“国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古代部分、传统部分,却不是这些学科的全部,更没有涵盖所有的人文学科。硬要在两套不同的学科体系中采用同样的标准,自然会左支右绌,无法自圆其说。
现在又提出要建立“新文科”,我认为前提是要说明“新”在哪里;有了具体目标,才谈得上建设。我国现行的“文科”,实际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或者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广义的哲学都属于人文范畴,与社会科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体系。以往主管部门往往不顾两者的明显差异,使用统一的“文科”标准。例如在项目申报或评奖时,无论是人文类还是社会科学类,均专设一栏曰“社会影响”或“经济效益”。我在参与评审人文项目或论著时,总是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如实填写的话,只能写“没有”,至多写“极少”;但要这样写的话,岂不是降低了对它的总体评价!如果其他人不是按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我这样评岂不是断送了这一项目的胜出可能?那么,“新文科”的“新”是要体现在打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呢,还是要在两者内部重新划分学科,或者兼而有之?如果完全要新构建一个学科体系,是根据什么理论、什么原则、什么标准?
科学与人文如何结合
多年前,周振鹤教授提出“历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说法,我赞同其言,得到很大启发。此后我经常引用,并一直在思考两者的关系及其对学科分类和学术研究的影响。
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来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它的基础是物质,是一个整体,人类按研究的需要才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科学和各门学科。而人文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人类出于训练、学习和研究的需要,才将知识和技能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学科。严格意义上的精神文化的基础在于精神,但物质文化也离不开物质基础。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既可定性,也可定量,所以科学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或结论,可以检验,也可以重复。但精神出自人的意识,没有客观的定性或定量标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通过科学手段加以定性或定量,或者可以被正确地存储、记录下来。所以人文现象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或结论,其无法重复,更难验证。
精神是人类特有的产物,又因具体的个体而表现差异。迄今为止,还没有科学客观的手段对精神加以感知和记录。即便是本人的精神,也只能通过自身的动作、语言、文字等信息来显示、表达、传递,而未必能做到恰如其分地准确解释自身。而他人,即使与传主保持着贴近的接触并予以即时、详细的记录,也无法绝对保证与其本人完全一致。何况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过去存在的精神现象,岂能找到唯一的答案、相同的结论?又怎能被重复和验证呢?
正因为如此,现代人文学科,都包括人文与科学两部分。作为研究主体的精神部分属于人文范畴,但我们已经无法直接感知、记录和研究这些精神本身,只能借助前人记录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中涉及的人和物,总之是通过物质而不是精神来研究,这无疑属于科学范畴。
以历史学和历史研究为例。以往存在过的人物,其生卒时间和地点、事迹和遗迹、作用和影响、因其产生或消亡的物质,有关这一切的直接或间接的记录及其文本;以往存在过的事物,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演变过程及遗存、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有关这一切的直接或间接的记录;等等,这些都是物质,都属于科学范畴,都可以用通行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而且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也可以得到验证。
即使对历史上一些最机密、最敏感的人和事,历史事实和结论也只有一个。其中有一些之所以成为千古之谜,甚至永远无法解答,主要不是科学因素,而是人文因素所导致的。例如,一片土地应该归属于哪个国家,只要证据还存在,无论是当事国家的历史学家,还是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如果采用科学的研究态度,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相同的。但对这个结论是全面公布还是片面公布,是保密还是销毁,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正确解释还是断章取义,就取决于国家利益、价值观念和利害关系,都属于人文范畴,与科学无关。如果毫无证据或证据太少,由臆测或推理得出结论,或者仅仅通过电脑程序、IT技术、大数据得出结论,即便是出自杰出的历史学家或天才的科学家,仍然不能被承认为科学。它们最多作为“猜想”,而猜想只有百分之百得到验证,并形成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才可能成为科学。而对这一切的评价,对它们涉及的精神部分、历史价值观念和历史哲学,都属于人文范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找到唯一正确的结论或答案。
同样的,文学、哲学、美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无不如此,都内含有科学与人文两部分。它们所涉及的人物、事物、文本、实例等,本质上都属于物质,都属于科学范畴,都适用于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或结论。但对这一切的理解和评价,对它们涉及的精神内容、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就属于人文范畴,不适用于科学的标准和方法。
即便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尽管它们的主体是科学,也不能缺少人文。譬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都包括相关的人物、思想、制度、理论、观念、历史等,无不包括科学与人文两部分。就算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如果涉及它们的历史、人物、事件等,也都离不开人文。
人文是一个整体,并无学科之分,无须也无法人为“打通”——不存在标准答案或唯一正确的结论。科学是由具体的个体构成的,个体之间都存在差异。科学越发达,个体划分越细,差异也越明显,答案或结论也越精确具体,由此产生的知识和信息随时都在爆炸性地增长。从这一角度说,在科学内部,相互之间是无法“打通”的。哪怕是最杰出的天才人物,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倡导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在科学家、专家学者中提倡人文精神,并不是要打破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实际上也不可能打破,而是体现在科学家、专家学者本身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体现在其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运用中,体现在其对社会、国家、人类的贡献。譬如基因编辑的原理和技术是科学,有标准答案,没有国家、民族和群体间的差别;但如何评价、运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依据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则属于人文范畴,不同的国家、民族、群体甚至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和决定。
像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不论何种专业,都要求学生在本科阶段必须学习多门人文课程。在这些人文课程的教学中,从来不要求联系本专业的实际,也从不考虑是否有利于学生今后具体的专业学习和研究。这些课程的目标显然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增加人文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历史观念、科学态度、职业道德、审美观念、生活情趣,教学成果主要体现在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的提高和他们今后通过科学技术为社会和人类做贡献。
儒家思想与儒家社会
1989年12月21日,先师谭其骧先生在“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发言,他指出:
儒家思想是发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种学问,当时社会不管是封建制也好,奴隶制也好,领主制也好,总而言之,与现在大不相同,与未来更没有什么关联。儒家思想是历史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孔子以后,历代都有儒家思想的发展,比如两汉的经学、宋明理学,我们都应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况来研究、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它们到底是先进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反动的。
有的人听了以后,认为先师是在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其实他的主要观点是要将儒家思想与社会实际区别开来,即儒家思想不等同于儒家社会。而这一点恰恰是被混淆或等同了,不少学者有意无意地认为凡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或独尊的年代,当时的社会就已是儒家社会,儒家思想已经转化为社会存在和社会现实。然而持这样观点的人往往只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却没有认真研究过相应的阶段的历史,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一段历史。
儒家思想本身属于精神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属于人文领域,但记录儒家思想的文本是物质,属于科学范畴。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人之间不可能完全形成共识。但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包含科学部分,离不开文本,必须符合公认的基本概念和逻辑推理关系。至于儒家思想中有多少成分已经转化为社会实践,在当时整个社会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有多大比例,这个社会能不能称之为儒家社会,都是事实存在,属于科学,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找到确切的证据。不能认为文本就反映了社会现实,更不能将文本当成社会存在的唯一证据。
正是基于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深入理解,先师认为:“无论是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千弟子以来的二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二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理学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社会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意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遗憾的是,那些不赞成这一观点的人,从来没有对这些事实提出过相反的证据,或者提出过他们自己的对自孔子以降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的看法,而是一味对儒家思想予以颂扬,或者坚守“学科”界限而不越雷池,只讨论哲学、思想。但果真是如此,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讨论古代社会,甚至想当然地肯定古代社会就是儒家社会呢?
郑和下西洋的科学问题
自从梁启超重新“发现”郑和,并肯定郑和是中国最伟大的航海家以来,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不计其数,近年来更成为一门显学。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历史事实,郑和及其随员其人其事、船队的规模、携带的物资、航行的路线、到达的地点、停留的时间、与当地人的交往、产生的影响、留下的直接和间接的记录等,都是客观存在,对它们的研究属于科学范畴。可是迄今为止,相关的科学研究少得可怜,在很多方面几乎是零。
譬如郑和所乘之“宝船”,其船队的数量、人数是客观存在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但由于原始档案早已被销毁,有关记载中的数字一直有争议。但现有的争议局限于文本本身,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有关尺寸的文字不见于马欢的原始记录,而是由后人加进去的,所以并不可靠。但是从国家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直至今日,这些数字还在作为事实被普遍使用,并用来显示明初造船和航海成就的伟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船舶力学的权威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槱先生在2004年便告诉我,木制船舶龙骨绝对不可能超过100米,因此无法造出符合“宝船”尺寸的船,按这个尺寸的长宽比例,造出来的船是无法在海上行驶的。遗憾的是,他早已发表过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然而赞成宝船尺寸的人对此置若罔闻,依然坚持旧说。海峡两岸的学者曾策划按此尺寸模拟造一艘宝船,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流产。南京倒是造了一艘,可惜只是模型,根本无法下水航行。
其实,以今天的科研水平和物质条件,即使不按等大比例模拟造一条宝船,也完全可能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文学者不懂科学技术,就要倾听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接受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我们提倡科学与人文结合,不是要求人文学者都懂科学,或者科学家都了解人文——实际也不可能做到;而是科学与人文、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相互尊重,科学方面听科学家的,人文方面听人文学者的。至少不能对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懒得了解,或者超越自己的研究范围和能力,越俎代庖,对另一方面妄言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