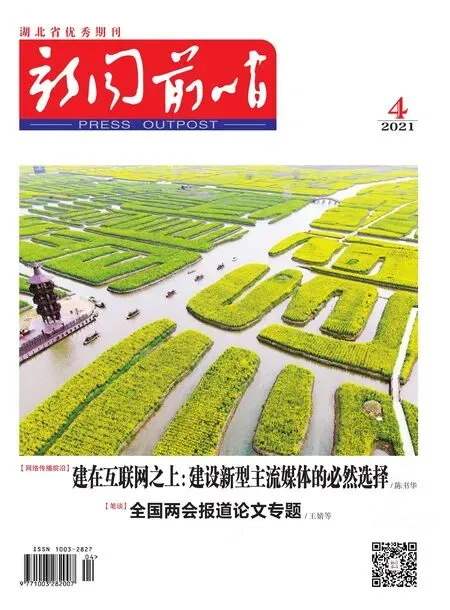孔子的传播“仪式观”与其传播思想写作的“表演性”
2021-11-13陈睿清
◎陈睿清
先秦时期无论是孔子传播思想的“三纲五常”的基本内涵亦或是“游说办学”的教化传播形式,都是一种独特的传播“仪式”。它们都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有关。反映了共性、共有、共享与沟通。笔者认为,孔子的这种传播的“仪式”并非仅仅是承载着儒家思想信息的高效扩散,更多的是建立一种时空上的“社会联系”;不是单纯的信息分享行为,而是建构一种观念共同体或信仰共同体的集体认识。
一、孔子的传播“仪式”
(一)传播仪式观的概述
按照凯瑞的观点,传播的仪式观源自于宗教观。但它并不看中布道、说教和教诲的作用,而是为了强调祷告者、圣歌以及典礼的重要性。美国诸多学者所认同的传播起源的仪式观,并非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而是为了建构出一种与传播模式的秩序与意义相一致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秩序。更明白的说,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通过信息的传递模式所维系的人类社会秩序或文化秩序的重要性,而非信息本身。
从仪式的角度来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同样,在传播的仪式观中,我们要分析的也并非传播内容的内涵,而是这种内容的传播如何“邀请”受众参与其中。因此对仪式这一概念做出详尽的阐释也固然重要,笔者在这里将“仪式”假定为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一整套社会行为方式或文化交流模式,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内用以维系社会关系或文化生产关系的途径。仪式不一定是在特殊时刻或某一特殊事件的典礼活动,也可能是孔子的传播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仪式化”传播结果。
(二)孔子的传播“仪式”
孔子的传播思想学者大多归结为以下几点:从国家层面看,儒家思想的传播核心“仁”,主张施行“仁政”已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从传播层面看,孔子重视对传播功能的认识,如“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论语·子路》,以下引用只保留篇名)等认为传播对舆论以及民心的影响举足轻重;从个人层面看,孔子主张“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行》)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这样的人伦思想或人世关系时至今日仍弥存于世人的观念当中;从社会层面来看,孔子做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关系论断。所谓社会关系,是要解决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因而必须强调个体的社会性。因此在社会层面,孔子毅然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人际交往原则,强调社会秩序。在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的共同建构中,如何使“旁观者”或受众自发地参与其中,则正是孔子传播模选择的意义。
孔子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建构一种普世价值,譬如孔子对“恕”的最高评价,称其乃一言而可终生行之,也有后世所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在道德范式。这种普世价值的建构,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其作为价值的“价值”必须为社会所共识;其二,其作为价值的手段必须为社会所共享。而孔子理想的社会状态则是一个以“礼”为社会规范的“和而不同”的社会,可见孔子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其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差距很大。与西方所推崇的“非理性”不同,孔子的主张往往是“理性”的,在春秋战国霍乱时期,这种理性的认识与传递在笔者看来映照了其“普世”价值的意义,也更能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世人情感所接受。正是在这种知识的建构与传播中,这种传播的“仪式”才得以形成。孔子的一整套儒家思想体系,更像推动了一场“理性”或“伦理”认识的启蒙运动。
在儒家思想的集成《论语》中所建构的道德规范、礼乐制度和社会秩序,正是当时人们心中能够感知却从未触碰的“文化世界”。与其说这是一种正当的社会秩序,它更是一种仪式的秩序。建构这样的“文化世界”其意图也非常明晰,孔子说:仁者,其言也切。”(《颜渊》),意味“言”与“仁”被认为是同样的高度,孔子身为一名教育家,始终以“教化大众”为己任,这就要求其言行一致,行思合一。而孔子所要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观或世界观,他希望在所处社会的人际交往当中,通过这种“仪式”的传递,能完成“言”与“仁”的合一。孔子的这种传播模式不仅仅是在传播中传递知识,更在于放大“传播”本身的意义,也为后人延续这种“传播”的思想铺开道路。孔子的弟子不仅继承其传播的思想也延续了孔子传播的“仪式观”;不仅继承了作为文化的传播也延续了作为传播的“仪式”。
二、思想史写作的“表演性”
(一)思想史的写作
古代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无法从历史时间段中做明确的区分,但其新闻思想史的萌芽最终还是寓于历史“写作”之中,后续的诸多学者所研究的古代新闻思想史同样是从春秋时期的诸多史料中开始着手。历史的写作也并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史书的真实性也是有条件的,历史的记录与刻写未必就是历史本身。同样史书的“记忆”也具有选择性,比如人物或者事件,它本身就藏有社会想象的空间,很难说是求真。而书信和其他文学著作则更具有表演性,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深思熟虑的。因此历史的写作乃至思想史的写作可能其内容并非是历史的真实而是“需要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有选择性的,无论是从当时的社会情境还是生存环境来说都更能够使其具有留存意义的历史和思想。且历史或思想史书写的挑战,也正是让“今日”社会中的价值体系,在“明日”的话语体系中检验其存在和意义。
(二)思想史写作的“表演性”
谈到的思想史写作的“表演性”包含但不仅限于“个性”,这与孔子的传播思想恰为一体。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同时他又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教育家,坚持“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讲学游说之风,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那么何为写作的“表演性”?孔子本身就是其传播思想的本体,是个人行为的典范,因此其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就包含了自身说要表达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内涵,他是“身体力行”的告知自己的学生及各国知识分子。因此其本身就存在“表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播个人思想的“现场表演”(游说列国);二是归整思想的“写作表演”(著书立说)。具体来说,孔子游说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学说,以及“和而不同”的传播理念,其重要路径就是通过自己的身、行、言、表的“表演”来演绎“仁”与“礼”的统一。
而著书立说则是孔子包括其弟子对儒家思想精华的梳理和记录,在整理与记录之中,赋予旧文献以新内涵,赋予旧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书写的表演”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演绎:其一,重视非语言符号的功能:孔子清晰的认识到“察言观色”、“巧言令色”(《颜渊》)非语言符号的重要意义,以其在传播中有着与语言符号同等的重要性;其二,传播其受众思想:孔子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里仁》)这与千年之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传播只对摇摆不定的人有用”的观念近乎一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学而》)通过对个人、社会以及历史的思考与归总,孔子希望通过这种带有“表演”色彩所书写的价值体系或文化体系被受众所认同。
三、对孔子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些思考
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正确地认识传播的功能,自觉地进行传播实践活动,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模式的雏形建构作出了辉煌的贡献。正是由于其传播思想和传播活动,才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经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仍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至于文中笔者所提到的孔子的传播“仪式观”及其传播思想写作的“表演性”是试图从传播学的不同角度对儒家传播思想进行剖析,在对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著作《论语》以及诸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展开了仔细的研读后,认为孔子的传播思想中确有包含着传播“仪式观”的可能与痕迹。笔者想要发掘的也正是孔子的传播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中诸多传播符号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而并非是对其现代价值的研究。孔子的传播模式与思维模式一直得到了保存和延续,其传播思想核心中并不包含“以控制人为目的”传播的传递观观点,相反,孔子秉持的始终是“和而不同”的情理交融与知行合一。
陈力丹提出,“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传播结构,由于把人置于“伦常日用之中”,人生理想满足于社会性的人群关系和日常交往,也许不会使中国人产生现代社会的那种人的孤独感,也许能够使人们在高度物质文明的条件下有一个愉快而和谐的现实精神的安息场所。也有人论证,这个传播结构虽然成功地仗社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但代价是牺牲了个体的尊严与主体自由。”孔子的传播思想在近年来确有诸多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质疑,认为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这种唯一性、教条性的权利叠加与血缘关系之上的关系纽带在当下早应不是主流所追寻的唯一精神联系。况且“人”的高度也不单单是以“仁”的高度来衡量,儒家传播思想的教化性质从今天来看并未包含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全部的活动信息与社会文化。社会不应被单看作为权利的秩序或者经济的秩序,社会生活也不只是权利与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