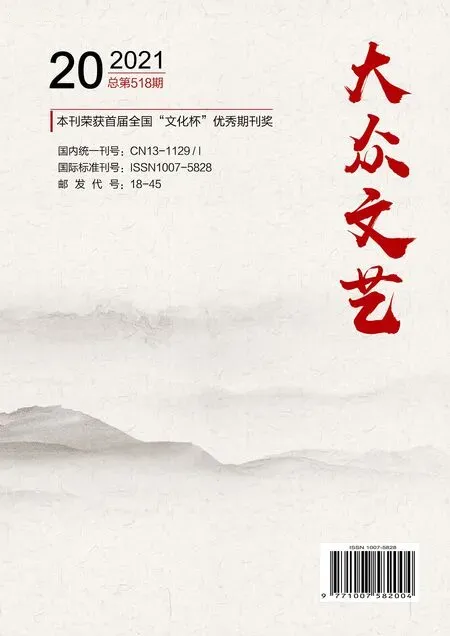女性“为自己而活”的坚守与屈从
——以电影《我的姐姐》为例
2021-11-12秦雪影
秦雪影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现实主义电影《我的姐姐》作为一部女性视角的作品。影片探讨了姐姐安然“为自己而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安然要在抚养幼弟和自我发展间拉扯,另一方面安然还要同“长姐如母”“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的传统规训进行抗争。简言之,女性想实现“为自己而活”的关键是要摆脱同家庭的直接联系。然而,事实上女性的生活轨迹大都是从一个家庭(父家)走向另一个家庭(夫家)。即使在现代社会,女性不婚或者大龄未婚女性的待遇相较于男性来讲仍然苛刻。虽说代际更替下现代女性自我意识在不断获得提高,但女性并没有完全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是处于一种既想拥有“为自己而活”的空间,又难以从“为他人而活”的藩篱中脱身的两难境地的博弈状态。
一、女性“为自己而活”的坚守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女性的日常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空间由家庭逐渐走向社会。社会向女性敞开更大的生存空间,让“女性在家庭、教育、工作、立法与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样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贡献她们的力量,书写属于“她的历史”,并让他们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以及拥有自我的职业和一定的生活空间。
拉康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类社会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变化。父权社会常使女性主动或被迫地丧失‘自我主体’身份,成为被要求的‘他者’。”电影《我的姐姐》中的姐姐安然就是一个被人为变成的“他者”。通过影片开头安然在父母车祸现场可知,安然同父母生物遗传上的血脉延续并不能佐证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因为父母随身物品里没有关于女儿的生活痕迹。虽说安然是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鲜明的主体意识的新时代女性,但事实上她依然要同封建思想做斗争,在被要求成为“他者”的现实中,努力争取被剥夺的女性“自我主体”身份。安然小时候,父亲为了有个生男孩传宗接代的机会,便谎称女儿是个瘸子。当街道办的人来家里核实时,却看到安然穿着红色的裙子在和煦的阳光下跳舞。失去二胎生育机会的父亲恼羞成怒地暴打安然一顿。面对父亲“装一下瘸子又怎么了”的质问,安然倔强地喊出:“我不是瘸子”。面对父母的不公平对待,安然并没有委曲求全,她倔强地忍受着皮肉之痛,依然坚守自己是一个身强体健拥有“自我主体”身份的正常人。同样,高考志愿被父母偷改后,安然并没有自怨自艾,在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同时兼职供自己读完大学。
毕业后,成为一名护士的安然,在紧张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依然坚持保有对职业的热情,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家庭”作为女性的归宿地,背后牵扯的不只是传统的家庭血缘亲情,还有代际间传统观念与当下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博弈。所谓个人价值观就是“把个人的自我实现摆在第一位,把家庭价值和亲情摆在第二位。”逃离原生家庭实现个人价值是姐姐安然坚守的梦想。她骨子里认为男女应平等,女孩也有继承房产的权利,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谁就是房产的拥有者,是家庭的主宰者。然而,事实诚如李银河所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男权的乡土社会,女孩早晚是别人家的人,男孩才是传宗接代的人,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父母养老的依靠对象。这种性别偏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家里的宗族亲友认为男性(弟弟)才是根,是财产理所应当的继承者。房产证上的名字在传统父权文化面前不值一提。姐姐安然据理力争坚决不还房产不惜得罪家族众人,弃养具有血缘关系的幼弟。从传统家庭价值观来讲,她的行为是对家庭价值和亲情的背叛,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实质上,这是姐姐安然坚持以自我价值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的体现,也是女性男女平权思想的体现,是新时代下女性个人价值观的呈现。
姐姐安然单纯地认为只要自己考取北京的研究生就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达到逃离原生家庭,获取“为自己而活”的机会。在积极选择生活的过程中,安然坚持不懈地学习,在病床前背英语、专业理论知识,做考研真题等。安然希冀和男友一起考研,共同到北京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当安然发现“妈宝男”男友事事听从母亲的安排,安于现状,不敢反抗,阳奉阴违后,果断同男友分手。由此可知,安然是一个不依附于男性、不迷恋爱情的独立女性。
总而言之,女性在“为自己而活”的生活选择中,身处个人的自我实现同家庭价值和亲情的撕扯中。虽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不断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生活选择范围,实际上女性可供选择的生活范围仍然有限,大多数的选择几乎都是围绕家庭展开,即使工作获取的收入大部分要回报家庭。尤其是作为家中长女的姐姐,更是母职完美的替代者。可以说,“长姐如母”的身份既有主流文化的寄寓,也有女性意识觉醒后而进行自我革新的激荡。
二、面对“长姐如母”的屈从
“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是。”这是电影《我的姐姐》中姑妈的一句台词。“姐姐”指的是比家里或其他同辈出生早的女性。实质上姐姐作为一个称谓考查其的历史演变可知,“早在《说文》中就有‘蜀谓母为姐’的记载。这种蜀地方言在今天已经消失,但是在湖南的耒阳方言和江永方言中,以及福建的莆仙戏中还可以考察到称母为姐的遗风。”由是观之,姐姐作为女性的一种身份,早已天然地被赋予了母亲的身份、使命和责任。尤其是母亲角色缺少的情况下,身为女性的姐姐或妹妹自然就成了家庭母职的延续者,或者说替代者。
姑妈是母一代传统女性的代表,她们遵循着“长姐如母”的世训,帮扶家庭抚养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分担一定的家庭事务,是她们作为姐姐所背负的“母职”的责任和义务。她们的生活范围大都是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继续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影片中,姑姑忙碌的身影随时可见。在安然父母的灵堂前,姑姑一边痛哭着早逝的弟弟,还要忙着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抽空照顾瘫痪的丈夫,顾及儿子饿不饿,提醒打牌的女儿注意言行。在安葬了安然的父母后,姑姑还要协调众亲友商量安然抚养幼弟安子恒的事。姑妈遵循着世代对女性的规训,面对家庭性别差异化的待遇,被剥夺的受教育权利和失去的创业机会,她接受并屈从于这种不公平的命运安排,如同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在规训的鞭子的抽打下,埋头手不停脚不沾地的为父家、夫家力所能及地贡献着自己的价值。
“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这说明传统传承的延续性特质,然而,“传统在其根脉延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添加或减少一些东西。”表明传统在传承的同时也会发生质的或量的变化。相较于对传统全盘接受的姑妈来讲,姐姐安然对传统规训的接受就有意识的进行了“添加或减少”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表明了子一代女性安然试图脱离传统女性的人生轨迹模式,尝试作为独立的个体从“为他人而活”实现“为自己而活”,并获得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
影片中姐姐安然的职业是一名护士,护士参与救助护理病人,但对病人却没有决定病人生命的权利。安然在面对孕期子痫的孕妇一家,她竭尽全力力劝孕妇及家人终止妊娠,但受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荼毒的孕妇和家人为了能生一个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儿子”枉顾孕妇的生命。此时的安然只能痛苦地朝着远离的救护车苍白地喊出:“儿子就那么好吗?”如李银河所言:“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男权的乡土社会,形成了家庭中绝对的重男轻女,这种性别偏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面对封建思想,女性个人的坚守是自不量力的,在现实面前只能无助地屈从。安然的高考志愿被父母更改,只能屈从于在本省读一个护理专业。为了得到父母的夸赞:“我女儿还可以”,安然自己挣大学学费养活自己,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面对幼弟安子恒,安然开始是拒绝的,她宁愿弃养,被家族众人打骂也不愿意扛起抚养幼弟的责任。最终安然在放弃到收养家庭看望弟弟的合同时,安然或许是被血缘亲情打动,或许是弟弟往日一杯热茶的关心激起安然内心深处的母性,安然带着弟弟逃离了收养家庭,决定和弟弟一起生活。
最终,姐姐一定程度上向传统的血缘亲情投降,承担起抚养幼弟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从公序良俗、法律上来讲,这是家庭成年子女对未成年子女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相较于母一代女性被迫担起抚养幼弟妹的家庭重担来讲,子一代女性是主动承担起抚养幼弟妹的责任,是主动的选择。实质上姐姐安然作为独立女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未来的路依旧要靠她自己走,她并没有放弃依靠自己,也不等同于放弃她坚持的梦想——考研到北京深造,开启新的生活篇章。以姐姐安然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她们崇尚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的权利,是封建思想的反抗者。她们希望通过对传统的“添加或减少”开启女性生活前景的“新模式”,得到更多塑造自我生活的机会。
三、女性自我实现的困境
“在男性生活中,教育和工作上的优势经常被用来和他们自己或父亲先前的地位做比较,而女性生活中这些相似的优势,则是针对‘为他人而活’的传统背景,既是新生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女性和男性在成长过程中的参照标准完全不一样,自然会有截然不同于的人生轨迹。
现实生活中,子一代女性的成长参照结构基本依托于上一代女性母亲、奶奶等,而老一辈女性如影片中的姑妈是典型的奉献者。老一辈女性的一生就是为父家、夫家贡献自己,生活空间狭窄,在封建世训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物质性的享受和追求,放弃受教育的权利。如同影片中的姑妈为了弟弟能上学放弃了读西师俄语系的机会,为了照顾弟弟的下一代放弃了在俄罗斯开辟事业的机遇。结婚后,姑妈继续操持着父家、夫家的一切,不仅要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照料瘫痪在床的丈夫和子女的生活,而且依旧要撑起娘家的一片天,照料甚至养育侄子女。姑妈作为老一代的女性,认为自己从生下来就是姐姐,就要为家付出,就是一个“客体”,没有自我意识的“工具人”,为父家、夫家不断的付出青春、汗水,做出“可见”的贡献却不能求任何回报。闪现着传统中国女性勤劳、忍耐、任劳任怨等的传统美德。唯独不能成为“人”,无法拥有自己的身份,不能继承父家、夫家遗产。这些对女性的传统道德约束如同片中的“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将女性生活、命运裹住,让女性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人生的选择余地。
安然作为子一代女性相较于老一代女性姑妈们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生活空间。新一代女性们在教育、工作、公共生活等领域或多或少都有了“为自己而活”的希望和选择。然而,现实中安然依然无法决绝地摆脱和家庭的直接联系,去寻找自我主体的发展机遇。影片对姐姐安然的表现运用了大量的特写、近景镜头,狭小的空间(陈医生躲在墙角暗自伤心)预示着女性逃离现实困境,选择自我生活要处处碰壁,可选择性较小。虽然安然认为只要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努力复习考研到北京就能逃脱所面对的现实困境。事实上,女性对自我的追寻同现实境遇是撕裂的,她们想要脱离家庭,自主选自生活的美好想象只能是乌托邦。
简而言之,代际更替间的女性自我实现的博弈如同一场接力赛。上一代“姐姐”们所遭受的困境,如同接力赛般下意识地被交给下一代的姐姐们。所不同的是以安然为代表的新时代的“姐姐”是主动选择面对生活的困境,而不是老一代“姐姐”们被迫选择不得不这样生活。老一代女性和新一代女性之间产生了极大差距,老一代女性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却难以被子一代女性认同。这一差距变化并不足以支撑子一代女性坦然处理个人自我实现同家庭、亲情的关系,她们依然在自我实现的困境中挣扎。
四、小结
现实证明,女性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变化,仅有觉醒女性对传统的反抗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女性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自主能力,能脱离父家、夫家的能力,需要社会为女性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喊口号,实质却依然需要依靠男性,这样的话女性生活仍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拘囿,难以脱离家庭和男性存活。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仅是与自我的和解,与家庭亲情的和解,更多的是通过女性个体的努力达到同生活的和解。所以电影《我的姐姐》这样的结局是合理的,说明安然懂得了和解的价值,寻找到了舒适的方式面对现实困境,不让自己陷于被动接受生活遭遇的困境。
注释:
①[德]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著,李荣山,范译,张惠强译,个性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4.
②蒋淑香,《我的姐姐》:女性意识与人性解读[J].中国电影报,2021.4.28,第010版.
③④⑧李银河.对《我的姐姐》的一个社会学分析.红星新闻.https://static.cdsb.com/micropub/Articles/202104/44602c963 a069719758fcc856516d6d.htm1,2021.4(03).
⑤袁庭栋著.古人称谓[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5:124.
⑥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
⑦毕新伟著.性别与德性——文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踪影[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4.
⑨同①.20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