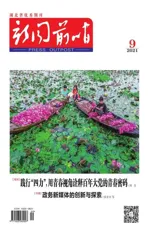从“网红医生”现象看短视频对舆论场的重构
2021-11-12费吟梅
◎费吟梅 高 星
(费吟梅: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武汉晚报新媒体编辑;高星:武汉市第四医院宣传科主任)
舆论场,是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人都不得不参与的社会关系,其形成的舆论场,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变化。本文试图通过短视频时代的几个本地“网红医生”样本,来说明短视频产品对特定舆论场的重构功能。
一、悄然崛起的“医生网红”
“网络红人”(Influencer),一般是指在网络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或者是长期持续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都是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而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其身份接近于传播学理论中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一词在传播学中的含义,是指活跃在相关专业内和新闻媒体中,尤其是新媒体中,为广大公众提供建议、意见和观点,对他人和事件事态 发展产生影响的公众人物,如医学界的知名专家、专业机构代表等。这些“意见领袖”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充分的信赖基础,公众对其观点和相关言论接受度高,容易影响舆论走向。
因为医生群体掌握了专业的医学知识,占据了健康传播的高地,当前的短视频平台个性化推荐机制,更倾向于迎合用户的私域需求,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成为资讯需求类别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根据短视频平台快手在2020年发布的监测数据,医疗健康类的短视频占据了视频总量近6%,排名位列前十强。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大批医生网红应运而生,并且因为他们本身综合素养高、表达能力强,结合临床实际有源源不断的案例可以讲述,具备了更为高质量和可持续的输出能力,填平了横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一道知识鸿沟,他们的人设更为稳健,在粉丝数、点赞量、互动频率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被称之为“中部医都”,医生群体庞大,本文列举在部、省、市三级医院工作,年龄跨度从60后到70后再到80后的三位医生,来作为分析网红医生群体的样本。
60后医生余昌平,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他作为感染者现身说法,记录了自己从感染到出院的过程,在非常时期给了很多患者及家属以信心和力量。其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粉丝91.3万,获赞998.2万次。
70后医生程才,为同济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医生,因疫情期间,除夕之夜还在抗疫一线,带领同事们吃方便面年饭,为武汉加油打气的视频被人民日报转载而走红。程才的口号是“轻松地讲科普,严肃地说段子”,目前在抖音上的粉丝有51.8万人,获得点赞544.2万次。
80后医生方禹舜,爱好拍摄和剪辑,视频作品妙趣横生,疫情期间也因为自己被感染,但后来又迅速康复走上工作岗位而知名,被央视等官方媒体和华中科技大学官方微信报道。目前粉丝数8.7万,获得点赞197万。
二、传统的医患关系舆论场不断消解
医患关系,是医疗市场化之后的一个词汇。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医疗事业的发展、社会稳定及人民健康。正常的医患关系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信任。医生在对患者的救治过程中也是在学习积累,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医务人员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帮助。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败,医患双方都渴望并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化解矛盾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
医患关系的又一个潜台词是“医患纠纷”。造成医患矛盾因素之一在于患者对医学知识掌握不充分。医者因素体现在部分医生给予患者的人文关怀不足,没有建立良好的医患信任。社会因素对于医患关系也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大城市的虹吸现象造成的卫生资源和医疗人才的分布不均以及部分舆论媒体对于医患冲突评论失之偏颇等。
实际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医疗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纠纷的。我们对医生的描述,都是赞美,比如大医精诚,橘井泉香。即便是医疗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时代,我们还在以先模典型来支撑医患关系。
当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为之色变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传染病专家桂希恩教授,邀请艾滋病患者到家中吃饭,以这种方式来向全社会宣教: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是明确的,不会通过日常生活接触而感染。大众也由此获知,很多患者的意外感染也与道德水准无关,因为贫穷。桂教授这种精神无疑带来巨大的感召。
各大媒体都在批判大处方,大医院门难进,而基层医疗一直发展不起来时,武汉媒体又发掘了小处方医生王争艳,从来不给病人乱开药,她开过的处方绝大部分都是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赢得社区居民爱戴。
大医院的医生日常医疗业务繁忙,很少有时间与患者进行详细的沟通,而语言处方医生蔡常春,精心为患者制作PPT,给患者耐心讲解,不仅挽救患者性命更赢回患者信赖,经媒体报道传为美谈。
与网红诞生的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不同,以上医生先模典型的诞生,都出现在传统媒体垄断传播渠道的时代,他们是标签化的产物,每个人就是一个代表特定意义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有意无意地投射到同行的身上。
但医疗行为本身是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比如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和健康知识的普及,艾滋病患者得到了全社会的关心和关爱,有专门的渠道来收治,已不再需要某一个专家去为其奔走呼号。“小处方”医生王争艳固然可以解决常见多发病的小问题,但复杂疑难疾病还是无法解决,还是需要到上级医院,且要花费不菲的费用,或许与人们的期许有别,但医学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语言处方虽然暖人心,但实际临床过程中绝大多数专家确实无法分摊更多时间给患者。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己迅速增长至5.6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2亿。网络环境使得诸多社会关系随之发生着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医患关系作为医疗行业中的重要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对于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的传播方式(直播、动画等)有着较为一致的群体偏好选择,并保持了良好的使用黏性。
在当今互联网、信息化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传播主体多元化、方式迅速化、内容片面化,当传统媒体渠道垄断的优势被消解,人们很快发现,典型人物的标签并不可复制和推广,典型宣传和个人感受出现了偏差,它只是一根有赖于个人的修为的单线条,无法在复杂的医患关系舆论场中,鸣奏出切合实际的和弦。
三、“网红医生”多维呈现让医患舆论平衡
如今,已经有很多医务工作者走上网络平台,用自己的所知所学,通过自媒体、短视频等互联网手段,为患者提供医学科普知识,传递健康理念。他们当中很多人,专业知识过硬,同时深谙传播规律,已经成为了网友眼中的“医生网红”。
医生不是神,他也是人,也会生病,所以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这种区域性的医学中心,其呼吸科专家余昌平也不慎感染新冠病毒性肺炎时,容易在广大受众心中形成共鸣。并且余昌平医生极为普通的形象也颠覆了人们对专家的认知,原来专家也是个普通老头子。但正是这种接近性,让他在大众最绝望时期普及的相关知识,更加深入人心,更加给人以信心。
同济医学院心脏血管外科的专家程才,则个性特别鲜明,比如对复杂手术的高昂手术费用从不讳言,程才的短视频作品中,大胆地突破了很多医生不愿且不敢突破的禁区:患者没钱了,还治不治?那些能救命但费用高昂的医疗设备,应不应该用?当传统认知认为医生就该无私奉献时,程才的短视频作品则在不断强调一位专家成长之难,价值所在,只论奉献不求回报之不科学。
30多岁的新锐医生方禹舜,更是以一个短视频极客的形象存在于网络平台,他运用很多拍摄的技法,来呈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新时代的医生已不再是一个古板而刻苦的形象,他们有自己对工作的热情,也有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他们传达的是一个多维而立体的形象,医生也是普通人,从医只是他们热爱且为之奋斗的一个职业。
四、不断在舆论场重构中增进传播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具体到我们医疗单位,“网上群众路线”的要旨就在于,“患者在哪儿,我们的医护人员就要到哪儿去”。患者即网民,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也要走出病房,学会互联网生存的技能和本领。
从文字到视频再到短视频,从单向度传播到个性化推介再到互动性传播,资讯的呈现形式越来越灵活多变,资讯的密度也在不断的提高,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和医院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应该思考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中,把优势为我所用而扬长避短。
首先是要孵化一批网红医生,不是人人都有当网红的潜质,要善于发掘那些有输出能力、有输出技巧的医生,对其进行挖掘和催化,提升他们在视频化生存时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方面促进健康资讯的传播,另一方面打造专家个人品牌和医院品牌。如何发掘和打造属于自己的“医生网红”,已经成为了时下各个医疗机构所研究的重点。当然,各个医院、学科的情况不一样,各人的资质、特长也有区别,发展的路径肯定是不同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群众认可的“网红”,不一定在于级别多高,名头多大,也不是每次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要真正以患者为中心,从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次是要不断学习,短视频平台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新的趋势新的玩法需要及时地掌握,在传统的传播关系中,受众的成长往往被忽略,而在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在摄像头前的情况下,一定要对受众的兴趣点时刻保持敏锐。
最后是拿捏好尺度保持好礼仪千万不可以踩红线。短视频平台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最低门槛、最低成本的传播平台,但正向的作用和负面的反噬一样来得激烈,一定要遵从各类生存规则。营造清朗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