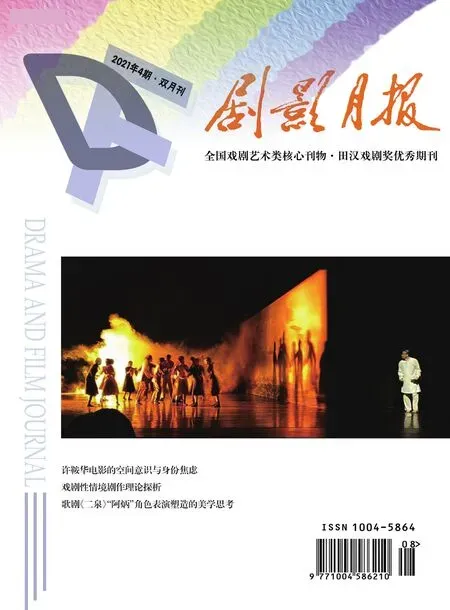视点、主题与驱动机制
——《辛德勒的名单》与《波斯语课》的艺术对比
2021-11-12朱天寒
■朱天寒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1993)与《波斯语课》(2021)均改编自受真实历史事件启发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两者皆以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作为叙事背景,以传奇性的人物事件作为具体描摹对象。《波斯语课》的故事源自德国导演兼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撰写的小说《语言的发明》,讲述了一名犹太人在德军集中营中谎称自己为波斯人,并通过向德军军官讲授自己编撰的波斯语而侥幸得生的经历。《辛》片则改编自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同名小说,描述了一名贪婪的德国商人在人性光辉的感召下,拯救1100名犹太工人的伟大传奇。相较而言,《波》片的原著蕴含了作者更多个人虚构的情节元素,在真实性上有着先天不足,而《辛》片原著本身是基于对二战幸存者的采访汇编而成,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与纪实感。
一、叙事角度:视点的内聚焦与外聚焦
视点(Point of view),即叙事性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在《波斯语课》里,导演刻意地将叙事资源过度集中于吉尔斯,企图形成一种叙事的合力,加深观众心理自居作用和想象性认同。《波》片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便开始着重建构主人公吉尔斯的限制性视角。当主人公作为一名俘虏进入车辆时,电影的镜头便开始取代其“眼睛”的一部分功能,进行观察和记录主人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遭遇。这样的限制性视角,在吉尔斯与德军军官两人情感关系线的构建里得到了很好运用。作为观众审视德军军官科赫最重要的窗口,吉尔斯的“限制性视角”完美展现了其性格的双面性,一方面是其作为武装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面对俘虏与下属时的残忍、狡猾、多疑,另一方面是其作为一名波斯语学习者时的坚毅、勤恳、自律。
但令人惋惜的是,《波》片在对“视点”的勾勒过程里完全忽视了对于“叙事者”自身情感及思想的表达。影片整体叙事视点的逻辑完全顺从于一种道德化的“无意识”,即以现代化的道德情感模式来嵌套事件的整体,继而影响故事整体的叙事节奏与叙事内容,而非进行一种深层次的、有历史代入性的叙事考量。这种电影思维逻辑上的缺失直接表现在了电影“叙事视点”方向、运动轨迹及“被视物”的选择上,如在吉尔斯与科赫两人在书房不同阶段交锋的叙事上,《波》片几乎完全没有能够体现出两者之间随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地位、情感变化。这虽与演员自身的表演技巧存在联系,但更在于创作者对“叙事视点”设计上的呆板与平庸,不能从“视点”里表达出人物的态度与情绪,给观众造成了一种两者过于“平等”化的思维错觉。
反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叙事视点的选择上极为全面。其完全遵循于两条清晰的故事线,即纳粹组织对于犹太人的残忍屠杀及辛德勒对于犹太人的人道救赎。在《辛》片中,重要的“叙事视点”囊括了辛德勒、军官葛斯、会计斯泰恩、被送去集中营的犹太妇女等。这种“多视点”的外聚焦性,既给电影构建宏大的叙事空间提供了可能,也使得电影主题具备了多样化的解读视角。此外,《辛》片还极注意对于“叙事视点”细节之处的构建,在方向、运动轨迹和“被视物”这三点上做出了完美的平衡与协调。影片中段,辛德勒的目光集中在了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身上,“视线”伴随着小女孩在混乱的人群里穿梭,最后在小女孩打开一扇小门后收回。“红衣小女孩”作为这部黑白片中唯一的色彩,她作为“被视物”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与隐喻。同时,辛德勒俯视视角的“叙事视点”不仅构建了小女孩的卑微、无助的生存困境,也表现了辛德勒与纳粹军官在电影中的主宰力与统治感。如上述“叙事视点”的细节设计在《辛》片中还有许多,“全方位视点”的彼此交叉,相互关联,让电影看似有限的时空有更多的外部性延申表达。
通过如上分析可知,《波斯语课》所采用的是一种“内聚焦”叙事,局限于主人公个体的所知所感,但由于对“叙事视点”细节的粗糙安排,使电影本体在叙事主题与叙事重心的塑造上过于涣散。而《辛德勒的名单》采用的“外聚焦”叙事,完美展现了多视角的时空、人物刻画,建构出了一场真实可感的历史记忆。
二、新历史主义:“人性光辉”的深层与浅表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即对于历史的论述,应该是叙述者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其本身具有复杂性与多义性的特点。而历史的多义性阐释究其根源是由叙述者自身文化背景、权力话语和先验性所决定的。所以电影创作者在运用电影语言塑造历史的过程中,必然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自身主观意识形态及伦理价值取向。《辛德勒的名单》与《波斯语课》作为对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历史的改编,两者在电影创作上有较大的共通之处。两者都以人物传奇作为了叙事题材,以展现“地狱”中“人性的光辉”作为电影中重要的母题表达。但这同样的母题却在两部电影里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深度与广度,并直接造成了两者在艺术哲理性上的巨大差距。
《波》片中“人性”的光辉主要集中表现在了影片主人公吉尔斯、科赫的身上,相较于《辛》片中斯皮尔伯格选择的单个主人公辛德勒而言,瓦迪姆·佩尔曼的这个选择显然更为激进、冒险。吉尔斯作为电影的主人公,其身上“人性光辉”的表现来自于对受难者的同情与抚慰。在电影开端,导演便通过吉尔斯接受一名犹太人用书换三明治的请求来作为人物性格的铺垫。其后,通过吉尔斯对意大利兄弟食物上的救助来对吉尔斯身上的“人性光辉”进行刻意强化。最后在电影末尾,导演设计了意大利人为拯救吉尔斯杀害了波斯人,吉尔斯又用自己替代即将被处死意大利人的叙事桥段,形成一种环形封闭的“命运轮回”,不仅表现受难者群体中“人性光辉”的绽放,也暗含了“善恶有报”的朴素理念。但在这种“人性光辉”的展示里,导演将杀害无辜的英国波斯裔飞行员作为拯救吉尔斯的唯一手段,大大降低了电影中“人性”光辉这一母题的思想深度,使得其更像是一种粗暴、愚蠢的“报恩”行为。
科赫作为纳粹武装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在电影的开端便表现出了残暴、多疑、易怒的性格特质,并且导演有意的将这个特质一直保留到了电影结尾。对于科赫而言,他在电影中“人性光辉”的展现被局限在了与吉尔斯谈话片段之中,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种“人性”光辉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同样,吉尔斯与科赫的对话作为展现科赫“人性光辉”,推动科赫从“兽”转化为“人”的重要推手,其内容也显得极为单一。导演仅选择了以科赫对亲人与梦想的眷恋为叙事落脚点,放弃了对于谈话内容思想层面上的进一步深化,使得这种“人性”光辉的表现极度缺乏冲击力,而显得流于表面。通过电影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除却“身份符号”后的科赫作为“普通人“时善良、充满理想的一面。通过电影后半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科赫作为吉尔斯“朋友”时可靠和强硬的一面。但一如上文中对于吉尔斯的阐述一样,在科赫的身上所展现的“人性光辉”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于亲人与理想的追思更多源自于其对于纳粹正面战场失利而被迫寻求后路的担忧,对于吉尔斯的信任与偏爱是源自于其与吉尔斯之间“波斯语学习”的交易。即便在最后对吉尔斯的“拯救”中,其所带有的“人性光辉”同样是一种朴素的“报恩”理念,而并非源自于人性深处“善”的驱动力的支配。在电影末尾,导演设计了科赫被抓的片段,这虽顺应了整部电影的剧情发展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吉尔斯对他“人性”拯救的一种失败,这对于电影“人性光辉”的母题而言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伤害。《波》片的导演瓦季姆·佩雷尔曼是乌克兰裔加拿大裔美国人,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为德国人,所以在对电影主题的把握上俨然有一套与受害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批判角度,其更集中于表现战争对于德国普通人“人性”的抹灭,是“施暴者”群体对于自我的反思与批判,“人性”光辉的母题在电影里依赖,从属于这更高一级的主题的表现,故而显得浅薄与乏味至极。
在斯皮尔伯格的访谈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明镜:十年前,当我们与您对话的时候,您已经预告了您的下一部影片将是关于辛德勒的。为什么您犹豫了这么多年,至今才拍?斯皮尔伯格:当时我还不敢接这部片子。我缺乏勇气,我发誓这是实话。当时我离这个主题还有距离,它是那么复杂、深邃。”这段访谈中所谈及的困扰斯皮尔伯格许久的主题究其根源是对主人公辛德勒行为动机的研究,而这种行为动机的追溯最终形成了电影真正的主题——“人性的光辉”。在电影里,辛德勒所面临的每一次的选择与转变都必然有足够的情节铺垫形成强而有力的动作导引,如电影中“奔跑的红衣女孩”、“隔离区内的枪声”、“挤压在一起的犹太人”等,这使得电影的主题表达有了一套完整且合乎情理合理的叙事逻辑。在电影的结尾,导演更是通过工人们在送给辛德勒的戒指里所刻下了的“犹太法典”名言:救人一命,如救苍生,来深化电影“人性光辉”的主题。与《波》片相较,这种受难者与统治者之间相互“拯救”所展现出的“人性光辉”更具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庄严感与神圣性。
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叙事中不仅用“受害者”的叙事立场来着力展现了一个“德国人”的人性光辉,还放弃了以往惯用的好莱坞式商业电影元素,使电影整体风格更偏向于严肃的欧洲艺术电影。这种电影叙述角度与主题意蕴上的选择不得不说是与斯皮尔伯格自身文化背景、权力话语和先验性有着极大的关联。也正是因此,《辛》片才具有了《波》片难以比拟的高度哲理性与思辨色彩。
三、驱动机制:“原型”的丰富性与缺失性阐释
驱动机制,即对人物心理、行为动机与电影整体叙事逻辑的分析与探讨。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人物动作与思想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电影时空的衍变,所以是否能在有限的时空内构建出强而有力的驱动机制,满足观众对于人物转变动机的心理解释需求,就成为了评价电影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
在《波》片里,主人公吉尔斯经历了多重身份的转换,如:俘虏、波斯语教师、厨房帮工、抄写名单的书记员等。这种身份上的不断转变,既是顺延故事时间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导演为了圆合叙事逻辑的一个必要前提。在《波》片开端,导演便向我们阐述了主人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求生策略。其中“生存困境”概念的建立决定了“生存”将处于吉尔斯一切动作“驱动机制”的领导地位,而“编造波斯语”作为的谋求“生存”策略,是从属于“生存”的次级“驱动机制”。不仅于此,与“编造波斯语”属于同等次级“驱动机制”的还包括主人公吉尔斯在集中营内所遭遇到的突发性困境。
在此基础之上,导演在整部电影的叙事时间线上先后安排了“厨房务工”、“与拜尔发生冲突”、“抄录俘虏名单”、“野餐困境”、“采石场求生”等多个叙事段落。在这些叙事段落里,“生存”作为“驱动机制”的核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点突出,如吉尔斯“被迫”选择返回集中营、躲避拜尔的针对、在病中用“波斯语”呼喊等,这些都是吉尔斯在“生存”这一“驱动机制”支配下的有意识行为。但在对于次级“驱动机制”的处理上,导演的设计就显得刻板且生硬。在《波》片中段,拜尔为吉尔斯设下了一个“逃跑即死”的圈套,吉尔斯在“求生”本能的驱动下被动陷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瓦迪姆·佩尔曼在电影中临时设定了一位“智者”角色来为吉尔斯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并成为了吉尔斯做出“返回集中营”的最直接“驱动机制”。这位“智者”形象的塑造,仅存在于吉尔斯在树林中的情节片段里,此后整部电影便再无展现。可以说,这一关键性的“驱动机制”与电影整体叙事逻辑性之间的联系是生硬的强行并和,是为满足剧情发展的一种“人工产物”。从叙事效果而言,浮夸的法国老军人以类似“天启”一样的神学形式强行“驱动”人物动作,不仅极大程度上破坏了电影原本严肃、纪实的风格基调,还损耗了观众在前期观赏中积攒下的情感惯性,对电影整体的“驱动机制”塑造产生了一种极糟的负面效果。
在《波》片结尾,吉尔斯在盟军军营向书记员们回忆起集中营中2000 多名俘虏姓名的片段中,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一种对于电影共情感的缺失。这种缺失溯其根源是来自对于导演对于人物行为“驱动机制”构建的乏力上,吉尔斯记忆两千多人名字的“驱动力”是源自于其对“编造波斯语”的需要,或者可以阐释为更高一级的“驱动”即“生存”的需要。这种“驱动力”缺乏了对于被俘者群体同情、怜悯、愧疚等心理元素,造成了“驱动力”本身与电影结尾中表现出的“大爱”之间有着难以缝合的情感断层,且这种断层造成的撕裂感只有通过创作者在电影里进行多重“驱动机制”的铺垫才可以解决,而非仅靠影片中主人公短而乏力的“他们并非无名之辈”进行修补。
反观《辛》片结尾,辛德勒花光一切积蓄拯救犹太工人的叙事片段中,我们可以与电影里的辛德勒在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感源自于人类普世价值观对我们的召唤。在这种强大的心灵“驱动力”的引导下,一个贪婪的纳粹党商人完成了一场史诗般的“善恶”转变。这种强大“驱动力”的确立得益与斯皮尔伯格对于整部电影“驱动机制”的完美构建。在《辛》片完整的叙事情节线上,斯皮尔伯格设立了一场精妙的三重推进,这三重推进来自于电影中三个重要的配角,即斯泰恩、红衣小女孩与党卫军司令官葛斯。斯坦恩作为辛德勒最重要的助手,向辛德勒引荐了一位前来感谢的独臂犹太老人。这虽未彻底促成辛德勒性格上的转变,但却完成了“救赎”这一重要理念的导入,为之后的发展埋下了一股“隐性驱动力”。其后,红衣小女孩的出现是促成辛德勒转变的关键因素,辛德勒从“窥视”的角度见证了红衣小女孩在战争里那脆如羽毛的悲惨命运。这是对辛德勒一次深入灵魂的冲击,这场冲击第一次唤醒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的“人性”力量。最后,来自于焚尸炉内红衣小女孩的尸体与葛斯残酷暴行的冲击成为了最后一股“驱动力”,这股“驱动力”伴随着灰蒙蒙的骨灰与焚烧尸体的恶臭彻底击碎了辛德勒内心冷酷的“堡垒”,让他内心的“人性光辉”得到了真正的复苏。三重推进构建而成的“驱动机制”奠定了《辛》片完美的叙事逻辑,也让辛德勒身上的“人性之光”照耀了整个世界电影史。
视点、主题与驱动机制作为电影叙事的三大重要元素,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一部电影艺术成就的上限标准。《波斯语课》作为近几年难得的二战影片佳作,在叙事题材与电影制作工艺上都有着超出平均水准的优异表现。但相较于二战经典之作《辛德勒的名单》,仍存在有较多的不足与缺陷。通过上述两部电影中艺术对比的分析,将对我们的剧本编写与影像摄录提供一定的有利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