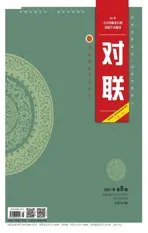以郑孝胥为例看“人品与书品”的关系
2021-11-12孙辉
□孙辉
一、人品与书品
历来书法评论中多探讨人品与书品关系,通常将两者看作是正相关,如汉代杨雄“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柳公权“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刘熙载“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论语·季氏》中按照学习能力和智力,分为上、次、其次和下等级的品;随时代发展人的品评延展到各个方面,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描写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的品。“品”字在书法评论上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庾肩吾《书品》中,之后有初唐李嗣真仿其体例的《书后品》,二者是书法评论的重要典籍,品第书法家高下,或单独品评书法作品之优劣。书法评论中艺术作品被视为艺术创作者人格化的体现,书法艺术本身和书法家的人格因素都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书法家书法技艺水准高超,但人品有缺憾,必然会使他的书法艺术被遗弃甚至唾弃,那“人品”即书品吗?本文以郑孝胥为例探讨两者是否具有相关性。
二、郑孝胥人品
(一)坚毅自强
郑孝胥前半生是典型传统知识分子。12岁熟读《仪礼》,22岁乡试解元,24岁进入李鸿章幕府。因在广西任边防大臣有功,1911年初升任湖南布政使,但辛亥革命爆发,郑孝胥未能成行便前往上海隐居。此期间郑孝胥傲骨而坚毅的人品毋庸置疑。日本1905年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学生们罢学回到上海,建立中国公学。郑孝胥担任该校监督并勉励学生“内执谗慝之口,外夺强梁之气”,学习先进知识改变中国“内为政府所虐,外为异族所凌”的局面。郑孝胥1911年之前的生活对其后半生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八岁丧母,十七岁丧父,家计困顿,郑孝胥将扭转家族气运的责任扛在肩上,郑孝胥于日本任职后家中状况有些许好转,但妹妹病故消息却又传来。他的老师宝廷虽为贵胄但去世后家人遭难生活窘困,这些都让郑孝胥追求功名之心日益强烈。同时,在儒家文化教化下郑孝胥心目中“国君”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故“忠君”与“爱国”等同。
(二)固守己见
1911——1931年期间他以遗民自居,这一阶段他的思想始终困至在传统士人观念和大国自信之中。1917年9月15日他的小儿子将《日本在中国之势力》的文章拿给他看,里面提到“日本挑成中国之内乱,渐肆其吞并之阴谋”。郑不以为然,认为问题出在政府身上,夸大“民国”的对立性质,并对日本持轻视态度,言“使日本能助我军械、兵费,则吾力可以渐展也”。郑想将日本当作实现复辟的一个辅助伙伴,借他人力量维护儒家传统的完整性和顺延性是他心中爱国的体现。(三)抱薪救焚
1931—1938期间的错误抉择让郑孝胥人品被人所诟病。日本承诺“帮助”建立帝制后,使急于实现复辟理想的他开始将重心和筹码放在日本人身上。但当到达东北后,人身自由都受控制,何谈心中的王道理想国。郑认为“境土离合”在复国大义面前是“微末小节”不值得在乎,他又认为,要洗刷自己罪名就必须成功建立王道理想国,将自己行为赋予正义性,但陷入了以主权作为条件建立王道理想国的虚假陷阱。以现代人品的评判标准看郑的人品是两面的,郑孝胥对家国是有爱的,但他爱的是清王朝统治,具有狭隘性,导致后来抉择错误,深究原因一方面是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郑对现实的惧怕,对功名的追逐和不甘,走错了道路,为世人所唾骂。
三、郑孝胥书品
(一)书艺成就与思想
今天我们看到的郑孝胥作品多为遗老自居阶段所书,其书法在当时海上早有声誉,认可度极高,卖字收入可观“1917年2月5日使小乙结算丙辰年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郑孝胥是少有的集碑帖融合有成的书家,其作品为后世碑帖相融提供借鉴,在此分析展示其思想与艺术成就。首先是倡导楷隶相参。郑孝胥曾说:“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然则不能隶书者,其楷,其草理不能工,试证之《流沙坠简》而可见矣。”题魏碑册:“蔡君谈谓瘗鹤铭乃六朝人楷隶相参之作,观六朝人书无不楷隶相参者,此盖唐从前法,似奇而实正也。”这些观念里都突出他对隶书及楷隶相参的重视。在“百年世德看乔木”对联作品中,楷书隶书行书笔法相杂,用隶法破楷体,“百、年、看”字中横画收笔都是波挑的笔势,卷字以上覆下,字形压扁有隶意,实践与他隶楷相参的主张相一致。
其次强调率意险绝。郑孝胥在清雄强书风的基础上,不斤斤计较于点画笔墨,纵横开合,具有清刚之气,其晚期作品融各家之法,率意潇洒。晚年作品“胸吞云梦略从容”,“吞”字撇捺飞张舒展,若以迟缓的速度则无法写出;“云”中雨字头横勾横向冲出上方短横,对比强烈,似挥笔豪迈一贯而下,势落而不可遏,无速则不能率意。日记言“试用颜鲁公结体,盖捷而易工矣”,亦可见他本人推崇快写,追求率意。
最后郑孝胥师古但不盲从,也不甘落古人之后,贵在创变。其诗作《壬辰年诗》中“必随人作计,毋怪落人后……”又言“利于抒发灵性者,皆不拘成法,为我所用”强调个性独造,法为我所用。他在实践中也践行这一理念,郑的行楷书师法唐宋,有苏、黄的稳健洒脱,加入汉魏笔意,取舍相宜,形成独特个性的书法风格。
(二)书艺影响与传播
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较高知名度,皇帝圣旨、石碑和民间匾额等常见其字,林则徐祠堂中的御碑即由他书写后刻成碑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书法界中传“北于南郑”之说,“南郑”即郑孝胥,足以见当时郑孝胥在书坛的声望之隆。郑孝胥在上海办学期间广收弟子,其弟子中有许多名人,如徐志摩、林语堂和曹聚仁等。胡适曾多次拜访他并赠送“唐仵君墓志”。沙孟海先生亦评价他“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郑孝胥在日本任领事多年,与日本书家交游,回国后,许多日本文化名人和收藏家拿着郑孝胥日本友人的介绍信不远万里来中国向郑求字,对近代国内外书法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四、郑孝胥的人品与书品
以现代人品品评标准看,书品可以说是一个人在书法上的价值和影响,从郑孝胥“书品”看,成就和影响不可忽视,所书“交通银行”沿用至今。从“人品”来看,包括敬老孝亲,政治立场等,其人品本身具有矛盾性,错误的抉择使他的“人品”为人唾骂,从郑孝胥看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存在统一,也存在着矛盾。“投敌”之前,郑孝胥爱国爱家,书名大盛,性情桀骜,这时他的人品与书品是统一的;“投敌”之后,有亏气节的人品与他颇有名气的书法是对立的,是存在矛盾性的。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思想倾向和道德情操。苏轼“神气骨肉血”的提出给予书法完整的生命体系,实际是对人格的关照,即书如其人,书学即人学,书之美在于人之美。一个真正书法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是书法获得更高认可的要素。历史中如蔡京、张瑞图等等,人品与书品矛盾的现象不在少数。对书品与人品的探讨,需要不断挖掘未知的史料,多元角度获得更多的理智与真实。
五、结语
郑孝胥可谓清末民初期文学和艺术的标杆性人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诗人和书法家,但人品即书品在他“投敌”之后是矛盾的。不过“书以人重”的审判标准在当代仍然适用,厚德载物,故人品修养与学习书法技艺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