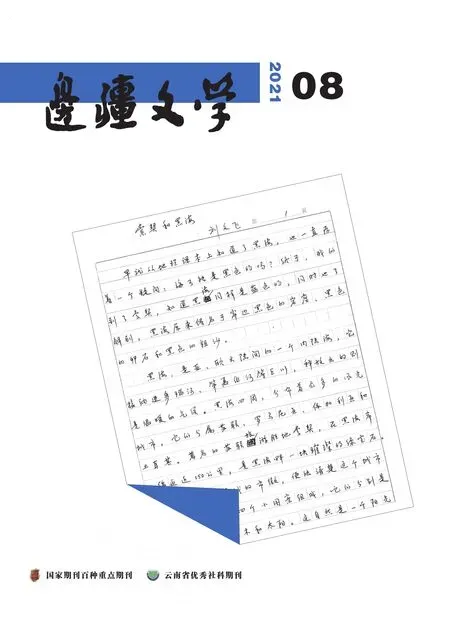和晓梅纳西世界中的感性力量 评论
2021-11-11刘玉霞
刘玉霞
“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工具理性盛行,感性及感性方式被排挤忽视的今天,和晓梅的作品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性力量,它舒缓却有力温柔却坚定地表达着作家对于世界、社会、时代、民族、个体生命等问题的认知与思考,而古老的纳西文化就是这种感性力量的源泉。具体而言,她作品中的感性力量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一是对于“情死”的阐释;二是对于不可知力量的敬畏;三是对时空关系的审视;四是对于个体成长的关注。
一
“情死”的动力来源于爱情的不可拥有,它指向未来的情感乌托邦。具体而言,“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这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空间。”纳西族情侣投身“不真实空间”的情死无形中反衬出了世俗生活中爱情的奢侈与珍贵。这种爱情本质上是一种缘于生命本能的热烈情感,是感性力量最激烈最深刻的表达。在这种生命热情的激发下,人们会神往爱情并为它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本能才得以确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抵制、压抑或其他手段)必须以强烈的本能不满足为前提。”面对这种“文化挫折”,纳西族青年男女会通过一起殉情的情死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爱情,具体而言就是纳西族相信有一个爱神康美久蜜金佑护着一个爱情的国度——“玉龙第三国”(《飞越玉龙第三国》),能释放一种神力,可以解救有情人不能相守的苦难,进入这个国度相爱的男女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以说,在爱情没有发生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平静有序的,意中人的出现激发了他们极大的生命热力,非他不嫁,非她不娶,可是命运弄人,依现实条件他们无法结合,因为女方往往出身富贵,家长自然要求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子婚嫁。结果女孩子却偏偏看中穷小子,并执意而为,直至做出情死的选择。《情人跳》中土司的女儿吉佩尔和她家的雇佣短工吾西木的情死就非常有代表性。
不过,小说中虽然经常出现情死的男女,但作家对女性的感情态度报以更深的同情,因为女性对感情的态度更坚定更决绝。在她的作品中退缩或畏惧共赴爱情永生国度的往往是男性,比如《女人是蜜》中美国情人郭盾·布朗是因为战争意外来到村子里的外国士兵,在隐藏他们的过程中,阿菊且与郭盾相恋并怀孕,在郭盾因大雪封山不得不离而又返之后,阿菊且约郭盾情死,但最后一刻郭盾畏惧放弃,阿菊且在生命将逝时,还求族人放过郭盾,不仅没有哀怨苛责,反而包容宽恕,可见阿菊且人之善良。女性也有没死成的,但会背负极深的负罪感苟活于世,一有机会一定会果决地再赴康美久命金。《情人跳》中的五姨,年轻时约定与情人情死,但却没有死成,在她带领姐姐姐夫找到“情死”的吉佩儿殉情之地时,她也毅然决然地跳崖,终于践行了当年共同赴死的诺言。
显然,由于实现爱情途径的匮乏,情死之风才会盛行,直至成为纳西民族感情表达的标志性情结。从作品可以看出,在传统的纳西族社会中,婚恋的门户观念及相关的礼法规矩是相当成熟的,伦理风俗并不鼓励以情感满足为目的的爱情获得,更强调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职能与作用,这一点与儒家伦理高度相似,“若是一个社会生产技术很简单,生活程度很低,男女在经济上所费的劳力和时间若需要很多的话,这种社会里时常是走上偏重夫妇间事务上的合作,而压低夫妇间感情上的满足。”这自然与浪漫的无目的追求美的感情诉求矛盾对立,在追求扩张家族势力获得现实利益的婚嫁前提面前,除了强行拆开别无二途。
和晓梅作品再现了纳西族的爱情乌托邦,这是一个人道化的世界,情人们弃绝的是等级分明规矩烦琐的礼法社会,是文明对于自由的限制,他们坚信只要抛弃了有形的肉身,就可以获得未来时空中的圆满爱情,这种对爱情未来的幻想唤醒了激发了久被压抑遮蔽的本我,为了能够永远自由相爱,男女双方抛弃了现世,以肉身的牺牲拯救自己的情感。
情死在和晓梅的作品中是一个关于写作的理想维度,在讴歌礼赞古典爱情的同时,又无形中具有一种潜在的超越与否定的价值指向,这也是作家成长的现代性痕迹所在。至少如果没有伦理礼法的羁绊与现实利益优先的前提,情死就不会有发生的土壤,纳西族对于自由与自我的实现也就不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呈现,但在回望这一爱情乌托邦时,作家的沉湎和眷恋之情会更甚一些。
二
对于前现代社会中神秘的不可知力量的呈现,主要以鬼神及灵异诡谲的人物为代表。农业社会里人们“需要巫师和牧师。通过他们的合作,简单的循环和节奏(日复一日、季复一季、年复一年)发生于伟大的宇宙循环之内。”“巫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牧师照管的是整个世界”,在纳西世界中人们敬畏鬼神,相信祭司与巫术,也相信并向往那个美好的彼岸世界。在纳西的传统世界中,鬼神是人世的引领者和陪伴者,说鬼神主宰着人的生活也不为过。当人们陷入困顿,无法解决问题,找不到出路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求助于鬼神,能沟通天地的人多为东巴女祭司、巫师,在通神驱鬼的同时他们还兼有医治疾病的能力。
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诅咒下蛊。《宾玛拉焚烧的心》中宾玛拉金成为女祭司,又成为哲格当总管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一个人生活,有自己的练药房,有一头牛陪伴她,结果牛被四个人偷走了,于是她对四个偷牛的人下了咒,这四个人后来分别死于她的诅咒。宾玛拉墨见证了这一切,在宾玛拉金死后继承了她的练药房。《女人是蜜》中恒之的母亲因为憎恨诱惑她儿子私奔的我母亲,诅咒我们,尽管姑太太去河边烧香散钱,但我的母亲仍然疯且病了,姑太太请来东巴女祭司治病,她说病因是淫魔附身。《蛊》是一篇专门以“蛊”命名的小说,摩些人头领的大女儿被有妻室的汉族官员负心后,她请求东巴女祭司对负心的汉族情人下了情蛊,汉族情人中了情蛊,她死后女儿水月白也误中了她留下的情蛊。难以释怀的情怨导致了古大侠古萧汉和凶恶的山贼头目惨烈的共同毁灭,水月白挖出双眼永不流泪的枯守。下蛊的缘起是感情的恩怨,结果是大家共同毁灭。
有的人身上有着特别的感知能力,这赋予他们更多的灵异色彩。《有牌出错》中我的奶奶是大东巴的长孙女,不仅聪慧,而且有着异于常人的赌博技能,凡赌必赢,只有一次是她故意出错牌,让自己离开她厌倦已久的生活,出去流浪了十年又再次返回。东巴女祭司本身就是神人参半的存在,上可以通神下可以驱鬼。《女人是蜜》中我的母亲又疯又病的时候,请的是东巴女祭司来诊治病情,驱走了附在母亲肉身上的淫魔。《女人是蜜》中阿菊且的画像一直挂在外婆家里,但小女孩是被禁止看情死女人的眼睛的,否则长大后也会受到蛊惑死于情死。我曾经长久地注视阿菊且的画像并为之着迷,外婆急忙把画像打落,把中了蛊的我送到东巴女祭司阿八奶奶手上,把我的魂魄从康美久蜜金手上及时要了回来。《宾玛拉焚烧的心》中的宾玛拉会制药懂巫术。
生活的尘世常有一种可以觉察却又难以说清的诡谲,成为无法逃脱的冥冥中的命定。《女人是蜜》中阿菊且情死后留下遗腹女,遗腹女又莫名地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孩被山里的一个驼背收养,先做女儿后来成了他的媳妇,但患有顽疾“桃花疯”,春天桃花一开就犯病,桃花一败就好,三代女人都难逃命运中的桃花劫。《水之城》中母亲最初拒绝嫁木姓土司儿子以拯救家族,历经生活的劫难,最后还是嫁给了那个最初要娶她的那个木姓土司的儿子,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古巷深井》中的二伯妈是一个有着幽灵之气的女性,整天带着她又肥又丑的猫只做事不说话,家族里的人对她和她的猫都非常不友好,觉得那猫的眼神和二伯妈的一模一样,带着鬼气,想方设法要除死它,看二伯妈更像一只成精的猫,对她厌恶排挤。人们的感觉似乎是精准的,因为二伯妈和二伯失和三年,却和三伯有了私情,三伯妈不甘心丈夫被抢,把他们的私情公之于众,造成了二伯开枪打死二伯妈,三伯打死二伯后逃亡十年杳无音信,三伯妈上吊自杀的混乱恶果。
不难看出,作品中的此类话题都与那个渐行渐远的传统东巴社会有关,都与东巴教丧失了对纳西族的绝对影响力的文化现实有关。“宗教观念的心理学根源”“是幻想,是对人类最古老、最强烈、最迫切的愿望的满足。它们力量的奥秘就在这些愿望的力量中。”前现代社会中,宗教允许很多无法言说清楚探究明白的存在,承认人存在的有限性,承认人对世界认知的有限性,在人陷入身心困顿时给予人一种精神安慰。鬼神主宰了天地万物与人的一切,而人也更愿意把所有的责任交给鬼神,虽然有被鬼神主宰的恐惧与怨憎,但在对鬼神的宗教敬畏之中,人也会获得安全感、归属感。所以身处于神秘感性的世界里的人们,将自己与宗教合而为一,显然东巴教曾经为纳西文明提供了重要服务。
“在此过程中,科学精神没有止步不前;能获得知识财富的人数量越多,背离宗教信仰的现象就越普遍——起初,只是背离那些陈旧的、令人生厌的虚饰,但后来也背离了宗教信仰最根本的原理。”当科学发展,鬼神随之隐退,这种由鬼神赠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随之丧失,不再相信和敬畏鬼神的人们更多地只能靠自己承担起全部的责任,责任是沉重的,会让人不时的感到疲惫,缺乏幸福感。感性本身就是人本质力量的一部分,对感性方式、感性力量的排斥、消解乃至抛弃,对于物质理性的过度推崇,最终导致人无处适从无所顾忌,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三
列斐·伏尔把时空分为城市时空、农业时空、工业时空三种,城市时空“由重建的时空构成,这种时空是一种不同于农业时空(周而复始和并置的地域特殊性)和工业时空(趋向于同质性,合理的和被规划的强制统一性)的布局。”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时空关系是一体的,人们的生命与周而复始的自然时序相吻合,在某一时间发生的事往往对应着具体的地域空间。在这种时空关系中,时间是属于神的时间,自然定时给人的束缚和压力是有限的,人在这一时空中更多的是与自然规律相和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和晓梅的作品多以自然时间为底色,人们在自然时序自然定时中起作休息,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从年轻到衰老,一代代繁衍生息,承继自己的家风和民族神秘的文化基因,即使是遭遇疾病和不测,比如中邪、情死,人的认知与行为也无法超越自然定时和鬼神的范畴。传统生活固然有其艰难辛苦的一面,却无法抹杀其与人类和谐合一的本质。经济发展造福了人类,但是利益的追求又反作用于人类,人们被迫从抒情的富于诗意的自在状态中走出来。都市时空“表现为差异,每一处和每一时刻只在一个总体中存在,通过对比和对立使之与别处和其他时刻相连并与之区别。”这时,神已隐退,时间从空间中抽离,时间和空间很难具体对应。时间不再是神的时间,在这一时空中人要服从时间,被机械定时限制、锁定,疲于应对,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诗意的生存方式。
《是谁丧失了记忆》中和烟杨与她所生活的宅院的关系可以看出时空关系的转变。在市场经济繁荣之前,宅院是托付人一生的居住地,房屋作为一个有形空间,它往往包含着一个人一生所有的经历与情感,它可能是一个人的情感纪念物,也可能是一种空间乌托邦,和烟杨一生都在为拥有自己的独立院落而奋斗。5 岁时被做妾的母亲带她寄人篱下,她没有空间的归属感。继父死后母亲跟马锅头走了,留下她在那个院落里自生自灭,继父家人对她坚硬而冰冷,随时可能将她抛出门外。在初长为女时就把自己嫁给了隔壁卖凉粉的余家,拼命干活,在第三次怀孕时终于成为家业的继承人,在婆家有了自己的空间权力。从此对家业和具体的院落筹划便化入了她的骨髓,即使丈夫和小戏子情死,双双吊死在戏台上;丈夫死后她又生了一对被视为不吉之兆的龙凤胎;婆婆死了;大嫫死了等等,这些人和事帮她慢慢地把继父家和婆家的两个院落合成了一个,将之变成了保护自己的坚固堡垒。她终于用一生的心血挣得了一处安放自己身心的大院落,将一个对空间的乌托邦梦想变为现实。
但是,随着都市时空意识的深入,人们“掌控时空的主动性、参与性空前加强,世界是什么已变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对我意味着什么,存在被完全价值化,使得自在的意义不太可能,由此导致的是将一切效用化的功利主义倾向。”仍然以《是谁丧失了记忆》为例,和烟杨在四方街的大宅院正是都市时空取代农业时空的代表,它成为都市新理念——提供消费娱乐、生产经济价值的载体。作为可用空间,“空间本身开始被购入与出售。”“空间不再仅仅是中立的媒介、地点的总和,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实现和分配。它变成了社会劳动的产物,非常一般的生产对象,从而是剩余价值的构成物。”老宅作为一个可用的空间被后辈待价而租,参与了都市空间的社会生产。老宅自居只能证明和烟杨曾经的能干和家庭的兴旺发达程度,但在追求消费娱乐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商业化都市里,客栈既是城市建筑又是一种城市空间,它遵循和阐释的是商业城市新理念,而再也不是那个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放疲惫身心的农业时空的标志性存在。
四
表达了传统感性力量被削弱的焦虑,一种失去了方向的迷惘。从创作看,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纳西的世界,投向了传统与过去,总是凭借回忆展开文本。涉及现代社会里的人和事,更多的是困惑与无措,缺乏回顾往昔时的眷恋与热情。
城市文明使个人从原本紧密的家庭家族关系中脱离出来,然后再把自己重新融入新的关系和组织,吉登斯用“脱域”和“再嵌入”界定和分析了现代人这种脱离原有文化体系后进入城市文明关系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的不适迷惘与痛苦,但却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世界性趋势。《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摩梭族少年泽措在他成丁礼的那一天正巧赶上他母亲临盆,祖母即将离世,她们在生死屋中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没有人顾得上他一生中重要的成丁礼。后来生父找来,接他去了北京,希望他以后能接替自己的公司。他继续接受教育,又去美国留学,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威廉,成了名正言顺的财产继承人,但他在独处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想起摩梭人的生活和那个令他遗憾的成丁礼。因为“仪式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是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摩梭人的成丁礼以仪式的形式公开肯定了一个男性的长成,明确了一个成年男性应该承担男性责任与义务。但他却与他的成丁礼失之交臂,即使他去了大城市生活工作,留学接手公司,拥有财富,但在摩梭人眼中他的成长仍是有缺憾的。
和晓梅对女性的自我奋斗精神给予了更多的表现与肯定,因为男性有着天赋的优待与特权,而许多女性不拼命奋斗就无法生存,但是都市经济又解构了她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意义。《是谁丧失了记忆》中纳西老妪和烟杨在和医生的对话中不断回顾自己一生的奋斗史,从一个寄居于继父家无所依靠的小女孩,成长为撑起一个家族的能干妇人,再到老年时迷惘于时代的巨变。和烟杨的郁闷和不解是为什么自己奋斗辛苦了一辈子,最终却失去了自己的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而活着,生活怎么又变成了这样。
与决绝的共同赴死的情死不同,纯洁美好的爱情被功利因素败坏毁坏。《春季 落雪的昆明》中沈纤惠是个漂亮早熟孤独的女大学生,因为身材傲人而经常遭到女生们的嫉妒猜疑,而她其实是个内心缺乏爱非常渴望爱的女孩子。在同学的排挤与寻爱热望的共同驱使下,她做了别人的外室,又因爱而不能给情人下了安眠药,然后将他肢解。沈纤惠索取的是爱,而她的情人,一个有钱有家室的中年男人却只想花点钱享受她美好的青春。作为一个内心渴望被爱的人,沈纤惠最终以毁灭一切的极端方式索取爱。作为一个内心无爱冷酷贪婪的中年男人来讲,被肢解似乎更像一个恶因恶果的明证。
现代社会欲望膨胀,人们往往丧失了应有的定力。《我和我的病人》讲述了我和第一个病人小敏的混乱人生。病人的心理问题其实是由诸多欲望对现实生活的扰乱造成的,加之女性更年期情绪差,对丈夫疑神疑鬼,导致自己神经兮兮,夫妻关系极差。我是一个作家兼心理治疗师,又想投资挣点快钱,经常奔波于杂志社、诊室和各色人等之间。到处都是像小敏和我一样不时被兴奋、焦虑、挫败、无力感折磨的人,作品中总出现一条有着美丽花纹的蛇,象征着人们难以穷尽的欲望,最终蛇被扔出了车外,第二天死了,意味着有的欲望人必须抛舍,断掉不必要的奢念,不然难以正常的生活,更谈不上幸福的生活。
作家在作品中呈现了一个充满感性的心灵化的世界,传递着一种难以确言的民族的群体的感性力量,它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固化为或仪式或规矩或宗法或伦理,不断传递着一种情感,明示着一种信念,即人生虽然苦痛,但仍充满了希望与期待,命运虽然看上去残酷无情,但又对人充满了灵性与慈悲,使个人的平凡生活与追求具有了美的可能性和价值取向。当传统被销蚀、被淡化、被漠视,甚至被丢弃时,人们无暇无心再对感情、鬼神、时间、成长轨迹给予关注时,心理的归途人生的方向便经常会模糊起来,人也便会不由自主地堕入迷惘与虚无,甚至陷入新的迷信。人的异化文明的危机已经成为研究共识,文明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与便捷,尽管“今天,人类已经非常接近了他的理想,他自己也快变成一个神了。”“实际上,人类已经变成了一个装着假肢的上帝。”但是“现代人并不为自己上帝般的特征感到幸福。”而感性的方式可以把我们从身体的疲惫精神的困顿中解救出来,为我们开辟一条善意温暖美好的诗性通道,不断赋予人生世界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