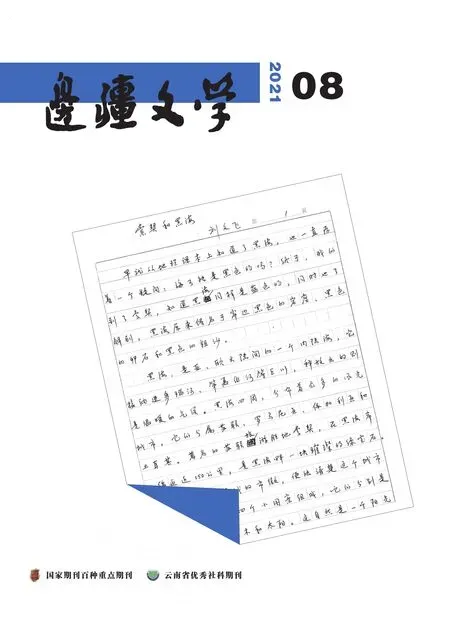吾马普
2021-11-11艾傈木诺德昂族
艾傈木诺(德昂族)
有三条江从兰坪的心口流过,他们从洁净的雪峰一路奔驰而来,然后肩并肩地各自向南北而去。
造物主用洁白的冰川、雪峰、湖泊和苍莽的林海以及广袤无垠的草甸来分割平行的三江,切割出水草肥美的河谷盆地和断陷盆地。
在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上,北纬27 度附近,伫立着延绵不尽的碧罗雪山的山脉。
梅里雪山向南延伸连起太子雪山、碧罗雪山和怒山。
然后,大地造出横断山脉纵谷地带,让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隔着永不相见的山脉并靠前行,亘古至今他们从来不相互眺望,只默然无言相依着岁月,流经云南西北部400 多公里。
四山与三江都是念青唐古拉山的孩子,由西藏一路进入云南。
碧罗雪山主峰海拔4379 米,云海茫茫,植被茂密,物种丰富。
攀越上天空的云杉林和冷杉林构成幽幽森林,高原草甸上漫步着羊群,高原湖泊像一颗颗剔透的明珠镶在绿森林,高山杜鹃一开一百里,无数奇珍名贵中草药就是居住在这雪山上的小仙子。
碧罗雪山一山劈开两江,由怒江东部纵横至贡山县、德钦县和维西县之间。
经两江切割,形成了漕涧盆地、瓦窑盆地、保山盆地、六库盆地和上江盆地。
兰坪县躲在澜沧江东岸的群山之中,隔江相望的西岸就是碧罗雪山山脉。
站在东岸看西岸,入眼的只有天与山,江和路,就如同一副搁置许久未完成的硬笔山水画,太旧了,太瘦了,太冷了,仿佛露着骨头。
只有久久地盯着,看那炊烟飘成渺渺的心事,也只有等一轮明月掩不住对岸疏散的灯火,才幡然得知满箩的心事就是过江去,去那炊烟升起的火塘边坐一坐,去那开满山杜鹃的路上走一走,如果天黑了,就去遇一遇那些在夜里提着灯的人。
5月是吾马普最好的季节,就算站在最高的山顶,天还是比山高,还是比平时更宽一些,云朵也更白,更随意一些。
被几场入夏的初雨刚刚叫醒的泥土,摆出一副松软懒散的样子。
旧时,吾马普属兰州西南境,归兔峨土司罗氏管辖。
在民国十年《兰坪县治绘图地志说明书》区域划分中,并没有找到吾马普的名字。按地理划分吾马普应当在第四区兔峨里,或者民国十年吾马普还不叫吾马普,又或者以山为家的傈僳人还没有被土司府收管。
再看民国二十一年的兰坪县划区报告表中的第四区报告,四区有4 乡,面积420 方里。很好奇这个表里的计算方式,2764户,10176人,从人口数量来看,当时西岸碧罗雪山山段居住的村落显然没有被统计进去。
表中交通概况是这样描述的:“该区东至二区,南通三区,四至五区,北至维西,以山崖峭壁,路政不易整理,每觉举足为艰。”
当时的经济概况记载为:“该区以山货、皮货为小数之出产,略有生丝以蚕桑不知讲求致生产少而品亦劣,农业虽属霁求而地居山国,每多歉收,至盐一项,出产尤微,铜铁亦有产焉。”
从这张报告表中,不难猜出民国二十一年的吾马普还是一个族群形式的部落,偏居在碧罗雪山一隅,少为人知。与当时的主流社会,跟雪峰之顶到江岸上一样遥远。
除了山崖峭壁,就是密密的云杉林和灌木丛,所有的路面上,只有人和马走过的足印。当然,所谓的路也仅容一匹强壮的马由主人牵着开路前行,真真正正的鸟道羊肠。当经过时间的生息繁衍,走的人多了,路稍宽了,路上有人来,也有人往了。如果两个主人带着各自的马匹相遇,总还是有一个人和一匹马要爬上坡坎相让,只能让,不能退。不对,应该还有狗和羊,他们都拥有梅花般的蹄子,会在雨后的泥路上留下去向。
整个兔峨在那个时代,最丰盛的往来贸易也许就是为小数产出的山货和皮货。那时,傈僳人刚刚度过穴居岩洞、架木为巢、猎禽兽为食的阶段,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就是将剩余的猎物拿到山下换取盐和布。
雪山上的傈僳猎人,善用木弩。使弩的猎人有两种,一种只使用竹子制成竹箭的弩,也只猎飞禽。这些猎人,了解鸟类生息,他们的箭从来不射,九月飞向月亮的鸟儿,靠着星星找路的鸟儿。那些羽毛白不过雪花的雪鸡,常常就成了这些猎手的猎物。
另一种猎人,用的也是木弩,也是竹箭,但箭头会喂上毒液。这些猎人猎的是游兽,森林到处是忧伤的黑麂和赤麂,它们每天都在商量着如何躲过带毒的飞箭。傈僳猎人的箭毒用乌头、箭毒木等植物制成,从来不取蛇毒,也不捕蛇。
那时居山国,每多歉收,略有生丝蚕桑,能织锦为衫的估计也只有土司府。有盐,有铜铁,仅是微产。高居山国之巅的傈僳人家,还用不上金属箭镞打猎,但木弩竹箭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有收获的猎手。
时间是摇摇晃晃地故去的,每一个时段的往事,就像宇宙中的星辰,远远地散落在人类共有的记忆之中。
现在的吾马普,陆续醒来的草本植物欢欣雀跃起来,争先恐后地伸出嫩叶,吐出花蕾。狩猎的弩弓还挂在木楞房柱上,落满烟尘,猎手们早已忘记了追寻猎物的技能,只有乌头和箭毒木没有丢掉看家本领,见血封喉,生还无术。在它的春夏,开它的花。
有路进村了,从沿江而立体的山坡上,来回折叠着向上。不能用蜿蜒这个词来说这条路,蜿蜒有着旋回的柔软,这条路的曲线只有坚硬感,绝没有一丝柔韧之意。穿凿而过的巨石,以欢迎的姿势热情地让车轮走过去,完全没有破碎后的沮丧,它接受挖掘机的所有破壁与碾压。
路把布、盐、药以及文明科技带进与生俱来就有着隐居精神的吾马普。
如果用险来形容进村的路,不如用怕更为直接和贴切。无论什么车,开上这条路就被天宽地窄的压抑感压缩成一只甲壳虫,紧握方向盘,打了又回,回了又打,不能多,多了会飞下悬崖,也不能少,少了转不过弯,也会飞进峡谷。
石布子村、土巴克村和吾马普村都陷落在两座山之间的缝隙底部,两座山之间都流淌着一条河水,两山都孤傲地直挺着身,人们只好在这斜地上架木为巢。人类智慧,是在资源贫乏中产生的。傈僳人的生存智慧,只要有三尺平地就可起一个家,木楞房一半着地,一半悬空,悬空的那部分用两根木头做支撑。然后再用一根根圆木铺成地板,地板下面是石块砌成围墙畜生圈,一家人全部的财产就放在这个小空间里,三两头猪、一群羊,马则栓在旁边的核桃树下,树枝上栖着鸡仔一家,与马儿做了楼上楼下的好邻居。
木楞房就是整间房子全部用木头建成,取木为梁,取木为瓦,取木为墙。梁上挂着经年不息的炊烟,高寒山区人们靠火塘取暖,火塘里煨着茶和苞谷沙沙稀饭。劳作归来,拨开火塘添两根木柴,土罐里的茶水跟着火苗沸腾起来,一碗浓浓的酽茶解渴,一碗喷着腊肉香的苞谷沙沙稀饭管饱。
柴烟穿过木片瓦,袅袅地从谷底飘出森林,飘上天空,飘向远远的云朵。烟和云是对孪生姐妹,只是一个分配到大地上,另一个值守天空。
木楞围成的墙,到夏天就有了穿墙风,凉习习地吹过来,地板下猪儿羊儿的味儿也会被风不管不顾地带给鼻腔。我起初很抗拒与一群动物共居,日子久了就习惯了,午夜梦醒,可以听见猪哼哼,羊咩咩。稳稳守着自己财富的安全感,总是会让人安心。
只是莫名地就会有人生病了,拉肚、发烧、咳嗽,先求求山神、水神、树神,不见好,就扯把板蓝根、黄连、紫花地丁煨水喝,如果还不见好,那就下山去卫生所看看吧。
一早出门,傍晚归来。带回肠炎宁、止咳散、去痛片、还有方便面,红牛和V8 啤酒。日子久了,村中泥泞的四野遍布着红色的塑料袋,白色的饮料瓶,东倒西歪的V8 啤酒罐,仿佛一直沉醉着不醒。
吹了千百年的山风,突然就顽皮起来,放着好好的枝条和落叶不吹,偏偏将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掀起来挂到树枝上,将轻飘飘的瓶瓶罐罐吹打得滚下山坡。最终,落叶会将它们覆盖,它们是地球的肿瘤,在地心经年不化,却不断癌变,蚕食人类家园。
从前,人们用树叶包物,用竹筒盛水,用木仓存粮。一切生活用度,都是可以被泥土消解的。后来,丰衣足食有了新的释义。那些人类投放、自然界被迫接纳的垃圾变成肿瘤细胞,以微尘的形态随风飘荡,渗入泥土,又被地上的野草、玉米、大麦、荞子、洋芋汲取,然后沉积到人的骨骼和灵魂中,跟附一生。
终于,在民国三十四年的一场大瘟疫的记载中看到了土巴克的名字,这是我找到的有关吾马普的最早的记载。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兰坪县长熊光琦向省社会处呈报兔峨镇长罗星递交的疫情报告上说:国民三十四年夏天兔峨发瘟疫,有死伤,三十五年秋,又发生兽疫,到三十六年夏天,瘟疫再发,沧江西岸的干鼻、花地坪、土巴坎、康悟古都有疫情发生。死亡最严重的是千各村,疫情流行广,死亡极多。兔峨偏居一隅,无医无药,袖手不忍,应付无方。
不知那连续三年发生的瘟疫是伤寒、疟疾还是回归热。据记载一得病,人就头痛,周身发热,不思饮食,然后昏迷不醒,三五日内出汗或者红汗还有生还的机会,到第七日未出汗就无救了。这里说的红汗很难理解,百度后得知人有时会有不同色泽的汗液,称异色汗。这里说的是否是异色汗就需要更多的考证了。在那场瘟疫中死去的男人被记为丁,死去的女人记为口,合计数那栏写为丁口。
土巴坎,就是现在的土巴克了,好多记录都是音译,只好把这些蛛丝都当作马迹来,辨别远久的一个地名以及地名里的人和事。有记载说1979 前吾马普属花地坪管辖,在前期的史料查找中,我可能忽略了这一点,一直在兔峨找吾马普。据村中老人说,石布子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土巴克、吾马普和克叶多多都是从石布子分流出去的,全村人差不多都是亲戚,完全是一副清晰的部落发展简史,或者是部落民族的社会直过史。
唯一的一所小学建在土巴克一个仅有三尺平地的陡峭山坡上,有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个班。一间教室,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一米宽的校室门口长着一棵很老很老的核桃树,树上挂着一个投篮框,就是孩子们的运动场,孩子们在这里投篮、跳绳、下棋。其实这样的小学校,原来有三个,只有土巴克小学留到2019年7月,7月之后土巴克小学完成了他的使命,随着扶贫大格局的计划目标,土巴克和其他三个村小组全部搬迁出雪山,孩子们也将在山下有了新的教室和运动场。
土巴克从前多松,所以它叫傈语土巴克。正午的土巴克只有阳光穿过寂静的云南松针叶,细细碎碎地落在大地上,这个世界,和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离山下很远很远。遥远到,一个居住着两百多人的村庄没有一个厕所。事实上,碧罗雪山上还有许多村庄都没有厕所,解决问题都是钻进树林和草丛。
含着长烟锅的老阿婆坐在核桃树下,把兰花烟砸得巴扎巴扎地响,她身后柴门微启,家园破旧,木水槽,小石磨,长坡路,人声犬吠。这是傍晚的土巴克。虽然同是人间,他们却艰难太多,幸而年底就整村搬迁。几年后,如此的原始部落的景象再也不会有了。
两山之间必有溪河,靠山面水大抵就是傈僳人居住观里的最佳宝地。
水是用木槽引进村的,也有些人家要到溪河里背水。
石布子、土巴克和吾马普都算得上集中居住的村落。食有木,居有木,一生依靠着树木的吾马普人,等到十月就要整村搬下山,舍家弃屋,变成城里人。
传说最早来到石布子的人,看到这里满山遍野地结着野木瓜,他选了棵巨大的野木瓜树,建了一个树屋住下。然后,他在这片河谷筑房引水,修建粮仓,娶妻生子。从一个人,到一村人,这片河谷因木瓜而得名。夏天又热又雨,冬天又冷又雪,在漫长的时光里,石布子人在贫困中安居,只到深情的光阴把石布子带到了纪元的2019年。
67 岁的楚四阿龙坐在他低矮的木楞房的门槛上,面容悲戚,一边眼神无助地望着蹲在篱角的工作队员小杨,一边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他焦心的事,去年大儿子从刚修通的路上翻下悬崖,才38 岁,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小儿子残疾还得靠他春种秋收地供养。搬下山他和小儿子都打不了工,怎么活啊?
小杨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咂烟,也一支接一支地给楚四阿龙传烟,一个认真地说,一个认真地听。直到站起来告辞了,小杨才重复着向楚四阿龙说,阿爸,不要担心了,政府管呢,有养老金、低保金、残疾补助,好几种呢,够你父子两个吃了,我过几天又来看你。
这样的场景隔三岔五都要有一遍。楚四阿龙的焦虑在一遍一遍的倾诉中松下来,一遍一遍的倾听让工作队找到症结,对病开方,为10月的整村搬迁把握人民群众最关注的细节。
楚四阿龙在他木楞房的火塘边做苞谷沙沙饭,与到新楼房做的苞谷沙沙饭会有什么不同?当然有,新楼房里煮的苞谷已经不是自己地里打的粮,不是火塘边煨的饭,那是电炉子和煤气灶煮出来的香味。
已经历尽无数的荒凉与孤独,石布子就要寻得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了吗?
夜晚有穿过山谷的风,卷起木楼外面核桃树上的枝叶,沙沙的声音扑打着屋顶的瓦沿,像有人扣门,像一个久别的故人来拜访。沉入美味睡眠的寂静的人们,从不醒来。在夜阑之中,石布子肥美的木瓜花,一朵比一朵艳丽,开在低矮的木楞房廊前。被月光的亮点染着,在夜色里像一盏盏微红的木瓜灯。其实我到石布子的时候,木瓜花已经开过了。山坡上,尽是黄澄澄的小麦,等着收割。
去石布子要先经过吾马普,在吾马普听不到溪涧的流水声,小溪在谷底,吾马普在半坡。只有一蓬蓬被风吹起长长头发的白竹丛,在坡下摇摆。白竹其实是灰白色的,细长的叶子上还有一层灰白,所以吾马普就是傈僳语里的白竹坡。
进村的时候,正遇上一群羊子回家,牧羊人赶着几百只分几家人的羊子归来。羊子自认家门,头羊带着队伍一只一只有序走进羊圈,主人则站在木厩上只管点数。还没到家的羊子低着头继续走,到家的羊子则咩咩叫着与伙伴们告别,牧羊人点着长烟锅,悠悠地走在羊群后面。
已近黄昏,无边的森林进入苍茫的暮色,夕阳的余辉被一座连着一座的山峰掩埋。在这里,不读报纸,不听新闻,外面的世界没有我们,只有日月依旧推移。在5月之末,我们只能听到大自然的消息,成熟的小麦在坡头说快来把我收割回家吧,小红豆早就跳出豆夹哗啦啦地在竹箩里欢笑。牛膀子和贝母,龙胆草和竹节草,小柴胡和细辛,伸着懒腰悄悄地长身体,空气里到处都是绿芽和花朵的清香。这是种令人躁动的气息,让黄昏繁忙起来,这是一亿个夏天出现过的同样原始的黄昏。
这也是在宁波打工的鱼四叶在吾马普之外从来不曾遇见过的黄昏,万鸟归林的寂静,完全是草的时节,叶的时节,花的时节,人只是路过这里。大都市归来,鱼四叶出乎寻常地淡然,外面的世界虽然好,可他说没想法,还是爱这山里,没有人跟他大声说话,也不用费力气猜别人想啥。而且他怕山下有房了,口中却无粮,但如果人人都搬走了,他也不想一个人留。
世世代代靠山的人,这会叫他下河捞鱼,并把他推到水边了,他不会使船,不会织网,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凫水,惊慌失措想必是不能免。鱼四叶姓鱼,他的淡定也许是命定的。
只有克叶多多建在面向澜沧江峡谷的山梁上,村委会就设在克叶多多,村名是傈僳语的音译,意思是好玩的地方,建村前原来是一个对歌场。据说曾有一任县长到了克叶多多后说,这是一个猴子经过都会打抖的地方。相比较石布子和吾马普村,我觉得克叶多多居住环境好很多了。克叶多多已经用上自来水了,家家门前都有个水龙头,原以为一拧开就有清清亮亮的山泉水就流出来,事实上拧开就有水的好时候并不多,现在雨水还没有来,村里人只能抢水用。
驻村工作队,常常没有水洗澡。工作队长是从独龙江来的独龙族李金荣,他用浓得化不开的独龙口音进村讲搬迁政策。他和他和两个队员,从克叶多多走到石布子,走到吾马普,走到土巴克。一天时间分给了山路,再分一些给路上的树,路上的风,路上的灰尘以及路上的醉汉,剩下的只够走一个村。
回到村委会,三个大男人,挥刀斩菜,埋锅造饭。一顿饭的工夫即是吃晚餐也是歇脚休息,放下饭碗,去小组长家问问,再去发展养殖的老支书的鸡场看看,这一来一去,又是好几公里。
老支书是参加过自卫还击的老兵,在战场上28 天,睡过猫耳洞,攻过老山顶,是机枪手,也是代理班长,曾经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虽然头发花白,扛过枪的双肩依然让人觉得可以依靠,2000年从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退伍后回到家乡,当了大队支书,在任时最想做两件事,修路和建学校。那时修路是个巨大的工程,老支书没能达成心愿,不遗憾的是在没有一分钱的资金的情况下,和村民一起取木搬石建了三个木楞房学校。最愧疚的也有两件事,一是没有带领大家富起来,二是愧对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曾守着、哄着、吓着去做了结扎手术的那几位乡亲。一生最不能忘怀的是,当年在战场上运送子弹的民兵。老支书健谈,有见识。他在村边的一个斜坡建了个养鸡场,黄鼠狼常常来偷小鸡仔,他每夜都要在半夜起来绕着山坡巡逻,像个战士一样。他也种芸豆和荷包豆,种玉米和花荞,还养着几箱蜂蜜,他用春天的花蜜招待我们。
楚三林发是第一批搬迁户,已经住进建在兔峨的新楼房。他夜夜的梦里都是哗哗哗的江水声,无论他如何努力,他想象的世界都走不脱刺骨冷,刺目亮的碧罗雪山雪、拱进鼻腔柔软的苔藓味、耀目的豌豆花荞麦花,浅黄色的小山羊和厚厚的马蹄、不停打架的灰松鼠和偷鸡吃的黄鼠狼。他就像被困在想象的世界,不自觉地要努力把一切想来。
于是,楚三林发悄无声息地回到旧木屋来寻个好觉,他儿子楚格格鲁隔天尾随他回到克叶多多的家。楚格格鲁三个月前突然患腿疾,不得不辞工回来,吃药打针,看遍大小医院,多份诊断书说明是神经功能症。楚格格鲁觉得解释不通,分明是中了别人的巫蛊,放蛊人将他的名字画上了蛊符,所以他才百医不治。他得回到祖灵之地,祈求已往他界的祖先护佑。他果然用一块红布向祖先求来援救,将红布扎在两腿,以驱万恶之魔。
自从系上红布,楚格格鲁说他病已去半。如若拆旧之后,再生病不知要去那里为祖先烧煮祭品。某种意义上,祖屋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归处,尤其是对楚格格鲁这样一个直过而来的山地民族来说,文明世界中万恶的愚昧落后,曾是我们深入骨髓浪漫情怀。每个世界都没有出逃的阶梯,也没有可到尽头的边界,当楚格格鲁问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也在问怎么办。最后,只得把问题推给时间。
在时间给出答案之前,问题其实都落在誓为中国减贫的政府,然后分解到各省各县各乡各村各驻村工作队肩上。无论给出多么优渥和美好的前景,要把一乡人、一村人、一家人从自古以来的生存之地剥离,生生扯着心肺那种疼痛,真的没有人能说感同身受。
星星都准备睡了,村委会的木板楼上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所有的劳累总会被一场睡眠消解。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一个时代新生衍出来的职业,像一群绿背山雀扑棱棱地闯进村,用城市的经验解释幸福。
这场史无前例的贫穷歼灭战的战旗插上每座雪山上,每一方贫瘠的土地上,人们手握着一个有体系的幸福,开始胆战心惊地尝新的迁徙。这些大山的子民,要退出雪山和森林,退到平坦的坝子,退到斑马线,退到红绿灯,退到长满幸福的地带。那些冒着炊烟的河谷不仅是人类家园,更是山川的耻骨,森林的心脏,江河的母腹。
几百年来,这山,这水,这土,这草养活过的一代代人,要把山还给山,水还给水,还不了的只有时间和记忆。
在这个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快速,越来越多彩的时代,以雪山为生存资源的傈僳人,有了一个明亮美好的未来世界。建立在45度坡角的那些低低矮矮,人畜共居的木楞房,只能留给时间和记忆。
经历了无数劫难,澜沧江西岸碧罗雪山上的傈僳人,仍然在这里燃起火塘议事,在这里住着自己设计的小木屋,他们在这里相爱,在这里老死。然后,从这里迁移,换一种活法,换一种爱法,也换一种死法。从农耕劳作到市井有然,从嫁鸡随鸡到可以选择做自己,从入土为安到焚烧炉里魂归祖灵。这种更换需要漫长的历程,需要几代人的适应,我们只能等。
很快密不可透的时间就会把这一切掩埋,然后就连猫头鹰锐利的眼睛也找不到我们来过的痕迹。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只能坐在夏天的烈阳下治疗我们人人患有的怀旧病。所有一切都只能成为从前的一个故事,一个片段,一个回忆,这也是历史的病。
整个夏天,吾马普人都是在马上就要住上新房子的兴奋中度过,当然也不能省略混合在兴奋之中的恐慌和无助。特别是年纪大了的老人,当年轻人就要铺开锦绣前程,他们面对的是在无论山上还是山下很快就会来的死亡。
是的,吾马普将让鸟鸣于树,鱼跃于溪,五味子摇头晃脑,竹节草随风摆动,乌嘴柳莺从冷杉身旁飞过。
至秋末冬初,羊群被羊贩子装进货箱拉下山,突然空出来的羊圈和突然空出来的木楞房等待着卸下他们的使命,突然就孤单起来的山路,就连常常醉倒路边的醉汉,也收起了砍柴刀,忙着把火塘边沾满火烟味的被褥打包。整个山谷,一夜之间,突然生出一种蚀骨荒凉和苍老。
马作为傈僳人家主劳力的辉煌时代已经完全过去,说是马,其实是骡子。在山路上,骡子比马更灵巧。在家畜界,骡子因为跨物种的杂交身份被另眼相看,却是山地民族最喜爱的家畜,我们仍一直称它们为马。旧时马邦队伍中,就有许多是由骡子组成的,骡子更能掌控攀山越岭的本领。现在,马鞍子被闲置在木楞房边的空地上,经过一个夏天暴雨冲刷,变得很旧很旧。连同那些不知去向的骡马,终究是要成为雪山上一个远久的故事。
2020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大疫,没有波及兰坪,更不会出现民国三十六年那样无医无药之状。吾马普村全村258 户904 人,全部搬迁下山,他们大部分在兔峨安家,少部分到了县城和平六库等地,开始新生活。
一切将要发生的,都会按时发生,不会早,也不会晚。就像吾马普也曾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过往一样。砍柴的也种地、牧羊的也放放马、收割的也播种、酿酒的也醉酒,他们是永远的吾马普人。然后,他们终会成为泥瓦匠、出租车司机、修理工、小摊贩、守夜人、公务员或者律师。从崎岖山路到车水马龙,从山月皎洁到街灯辉煌,我们有可能是那个成功的佼佼者,也有可能是那个失眠的夜游人,在各自不为人知的境遇中走散,又聚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许多年后,吾马普今天发生的变革就成了吾马普人共同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