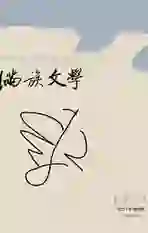漂洋过海
2021-11-08陈再见
老城四十来岁了,几年前离了婚,儿子快要参加艺考,前前后后花了他几十万。前妻不吭一声,他也没吭声。他知道她不是很容易,去年刚嫁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听说出租车司机喜欢把路上的怒气带回家,她的那点小脾气根本就起不了作用。老城多好啊,一点脾气也没有。老城想,可能也是因为脾气太好了才离的婚。女人有时就喜欢折腾。
打十几岁开始,老城就跟着人干装修,他干的是木工。装修行业里的木工可不是木匠,不需要使用刨子、凿子,使的是切割机和钉枪。老城每天听着钉枪噗嗤噗嗤地响,晚上睡觉时,耳边依然噗嗤噗嗤地响,像是警钟长鸣。后来就习惯了——没离婚时,他也试图把前妻的唠叨当作钉枪的声响,习惯了就好。问题是前妻不习惯。前妻觉得老城干木工把自己干成了一块木头,于是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跟一块木头怎么过日子?
干装修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住所,听工头的召唤,随时等着“部队转移”。离婚后,儿子又住了学校,老城更是心无旁骛,到哪都能安心地住下来,白天和工友们说说笑笑,一天的活干完,带着一身木屑,回到临时住所,洗个澡,躺在架子床上,看会书。老城喜欢看书,有时还喜欢写点,这是他辍学后唯一保留下来的喜好。说到底他还是喜欢闻书页的味道,跟一身的木屑味差不多——大概是,凡是出自于木头的东西他都略有好感,也就难怪妻子说他越来越像一块木头了。
这些年,老城去过的地方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小城镇,小县城,大城市,甚至北上广,他都呆过,只不过多是走马观花,再说他是干活去的,干完活就走人,就像过客,过客也谈不上,就是路过一阵子,不能妄自尊大,还把自己当客人了。不过有一个地方,对老城来说是有感情的,有感情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给了他什么,可以这么说吧,這个地方永远也不可能给到老城什么了,房子买不起不说,现在连租房都贵得离谱——是老城傻,单纯地无条件地喜欢上这个地方,他喜欢这个地方的热闹,也喜欢这个地方的包容。这个地方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自然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去大排档吃个宵夜,坐在他身边的可能是亿万富翁,却穿着拖鞋抽着十几块钱一包的香烟;也可能是三餐难保,夜里还要出来吃点东西的,穿得体面而光鲜,谈吐还不俗……老城真是爱死这个地方了。哦,这个地方就是深圳。
老城在深圳租了一间房子,固定的,即便不住,他也按时交租,当然只是个小单间,小得只能放下一个架子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光线也不好,大白天的一定得开着灯。无所谓,老城需要的是一个人为固定下来的东西,就像钉枪把一块木板给固定在吊顶上,牢牢的,至少短时间内不会掉下来。既然干了这行,人是固定不下来了,总要有一样东西能固定下来。所以,有了间位于深圳的租房,老城便可以自诩为深圳人了,反正政府也是这么说的,来了就是深圳人嘛。老城也不算大言不惭欺瞒人。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一旦在某个小县城或小城市干完活,跟工友们告别,工友问,下面去哪啊,老城就高声回答,回深圳。
深圳确实是老城比较熟悉的地方,毕竟呆过的时间也多些,没活干的时候,他可不想整天呆在出租屋里看书,书是看不完的,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他喜欢的作家。他觉得有些作家还不如他写得好。他没事就喜欢到处跑,从他住的地方,那自然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往热闹的市中心跑。到了吃饭的点,他就想一想,附近有没有认识的人,约出来一起吃个饭。要是晚上,就去大排档吃宵夜,或者找个唱歌房K歌。他还真有不少朋友在深圳,其中不乏一些有钱人,老乡啊,曾经的老板、工头工友等。因为喜欢写点东西,他还认识不少文学爱好者,他们也不是纯粹靠写作吃饭,跟老城一样,写作只是休息的时候躺在架子床上消磨时间的玩意——所以啊,深圳的写作者背后都有另外的身份,富二代、官二代、炒股的、忽悠的、拉皮条的、官商之间的掮客……要啥有啥。老城认识的人多了,他从不嫌认识的人多,他爱交朋友,也爱把朋友叫出来,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当前妻说他是一块木头时,老城还反省了一下自己,是嘛,是木头吗?如果前妻有机会去问他的那帮朋友的话,他们肯定个个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怎么可能?老城不是木头,如果非要安给他一个比喻,那么也应该是一把打木头的钉枪,噗嗤噗嗤,一天响个没完。
事实上,有些朋友是怕了老城,见到老城的电话,或者微信叮的一声响,他们准知道老城又在附近转悠了。嘿,哥们,在干嘛呢,有空吗?我在附近,出来聚聚啊。老城总是这么说,他的声音有时和蔼,是商量的口气,有时又变得十分生硬,像是工头给工仔安排工作,让人听了不舒服。他们倒也不是怕老城蹭饭什么的,老城这人不小气,相反还挺大方,他招呼人出来,一般都是他准备请客的,除非那个被招呼的人太有钱了,根本不好意思让老城请客,老城想付账都感觉冒犯了人家。朋友们怕老城是因为不是谁都有那么多时间,即便有时间,也不一定要陪老城啊,他们还得陪老婆孩子,哪像老城,光棍一条,没人管没有催,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
老城便也有请不到人吃饭的时候——就像这天,他在坪洲地铁站出口,拨出去的电话响了很久也没人接。他知道对方不是一个随意让手机脱身的人,不接电话其实就是不想接电话。这自然不是老城第一次遇到了,借口说出差在外地的,骗说在开会的,还有正在干那事的……老城都可以理解,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敢接,这要是真有急事呢?朋友不应该是这样的。老城很失落,他突然觉得眼前的街道也变得落寞起来,尽管傍晚的地铁口人来人往,几乎可以说是接踵摩肩。老城继续往街上走,请不到朋友吃,他自己也要吃,就算胃口已经减了大半。不远处是一排露天大排档,街灯刚刚亮上,除了吃食就是等待吃食的人,大多是年轻人,活泼而热闹,是老城喜欢的氛围,他有着一颗年轻的心,朋友们老的老,衰的衰,唯有他,还时常错以为还是二十好几的年轻仔,顶多也就三十来岁。要是以往,也就是说能顺利约到朋友的时候,老城最喜欢领他们去的,首选也是大排档,露天的,不露天的大排档基本是耍流氓。要是真赶上下雨,深圳的夏天雨说下就下,老板过来撑一把伞,就可以继续吃喝,毫无影响。就算是一个人,老城还是愿意往大排档走,包间虽然舒服,还有空调,在他看来却跟他工作的环境差不多,憋闷得慌。老城喜欢宽敞的地块,当然也不是时时都能遂愿,比如他在深圳就租不起宽敞的房子。
好不容易选了位置坐下,四个座位的桌子,老城一个人占着,正是生意好的时候,难免有些不厚道。老板忙,迟迟没过来,老城得装出一副要呼朋唤友的样子,老板这才过来,笑着问,先生几位啊。老城没正面回答,把手机放下,拿起桌面的菜单直接点菜,一盘小龙虾,一份麻辣香锅,半只鸭子,一条烤鱼,还有凉拌黄瓜。这哪是一人的吃食。他是故意的,既然占了人家四个座位,那他就不能点一个人的吃食。要说老城厚道,在这些细节便可以看出来。老板站在边上记着,一脸油腻的笑,以为顾客还在等人,便问,等人来齐了再上?老城说,不用,先上。老板说好嘞,转身走了。老城一人坐着,周围一桌一桌的都是人,几乎都坐满了,男男女女,相互错开,嬉笑怒骂,是年轻人的江湖。他一个人混在他们中间,倒显得格格不入了,像是被遗弃在大街中央的落寞老头。老城连续抽了三根烟,又喝掉了半瓶啤酒,才等来了第一道菜。直到这时,老板才确定老城是一个人,没有需要等的人。老板特意过来敬了老城一根烟,似乎读懂了老城的满腹心事。老板临走时说,哥们,喝好吃好。老城端起酒杯敬了老板一下,他多想把老板拉下来陪自己喝几杯。可是,这个舍不得坐一下的老板显然觉得赚钱比什么都重要。老板说他是湖南人,邵阳的,邵东的,煤矿厂出来的,拿手的菜式就是做鸭。老板这么介绍自己,像是把老城当朋友了。老城却看不出诚意,觉得他说话太油。
老城慢悠悠地吃着,大排档越来越热闹,街灯也越来越亮。
卖唱的女孩到来时,老城没注意。女孩走过每一桌去询问要不要点歌,同时递上她的点歌单,满满一页A4纸——唯独就把老城这一桌给漏掉了。漏掉就漏掉了,别说老城没在意,就算他在意,他也不会觉得被冒犯,他犯不着跟一个女孩子计较。他又不点歌。问题是,隔壁桌点了歌,老城就算不想听,那也像是看演唱会捡了个大便宜,给挤到第一排去了。近距离,老城看得很清楚,女孩顶多二十来岁,长得那是一个漂亮,藕色T恤上衣,下身是浅蓝色的牛仔裙,五分裙,裸露在外的腿脚又白又匀称,不胖不瘦,刚刚好,就像是一块木板被钉枪钉在恰当的位置上,分毫不差。老城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可人的女孩,她唱歌还好听,抱着吉他,连着一个便携的小音箱。她先是唱了一首《大风吹》,接着又唱了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邻桌那几个小年轻,显然已经喝多了,都脱了上衣,露出胳膊和胸口的文身。他们一连点了五首歌,似乎不太愿意放女孩走。
唱完第五首歌,他们便开始动手抢夺女孩的话筒,把大排档当K歌房了,自顾自地唱了起来,一人唱一首,最后再合唱一首《兄弟》,噪音之大,让老城都有些受不了。他起身上了趟洗手间,回来时,发现小女孩已经快哭了。她显然是个新手,缺乏应对类似场面的能力。如果他们不把话筒还给她,等于她就得在这一桌子耗一晚上。她又不敢去抢回自己的话筒,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子,可能刚入行,来深圳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也有可能之前在某个小公司上班,没赚到钱,受人怂恿,购置下这一身行头,瞄准一条街的大排档就开始推销歌单了。
老城觉得有必要帮女孩一把,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怕事的人,路见不平,他最乐意大吼一声。哪怕此刻他孑然一身,对方人多势众,他没想过打架,即便打起来他也不害怕。他只想着帮女孩一把,因为她可怜,受人欺负,或者纯粹就因为她漂亮。他都无所谓,就算事后被人揍一顿,他也不后悔。老城从来不做后悔的事。
于是,老城站了起来,举起手臂,服务员还以为他要加菜或买单呢,向他走了过来。老城却大声喊道:“姑娘,我这儿要点歌。”声音之大,几乎盖过了话筒那既跑调又粗俗的歌声,所有人都纷纷扭头看老城,邻桌几个喝多的年轻人也停下酒杯,愣愣地看着老城,像是他们之中某人的父亲,搞了突然袭击,抓了儿子一个现行。几秒钟的沉默过后,小女孩很快接过话,“好咧,老板。”她壮足了胆去拿回自己的话筒。那个一首歌只唱了一半的男孩长着一张满是痤疮的脸,不知是因为喝了酒,还是愤怒,抑或是痤疮发炎,他满脸红得像是被人在额头上划一刀,血流了一脸。痤疮男似乎还本能地拒绝了一下,就像话筒本来就是他的,当他意识到唱了一半的歌不能再继续往下唱时,话筒一下子又成了累赘。女孩拿到话筒,拖起小音箱,慌里慌张地就要离开。这时老城又高声喊:“嘿,你还没收钱呢。”女孩立住,老城的提醒及时而重要,她把歌单向痤疮男递过去,那上面有收钱的二维码。痤疮男愣了一下,似乎还弄不清楚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這位多管闲事的中年人到底是谁,不在家里好好呆着,看电视刷抖音,跑出来瞎闹什么。他还想说句话,以挽回已经丢失得一干二净的面子,边上的小青年却抢先付了钱,并伸手拉他坐下。痤疮男总算有了台阶下,他坐下去时嘴里咕哝了一句“我丢”,在声量上,显然就缺乏老城的气势。总之,老城赢了,他看着女孩匆匆忙忙往他这边挪来,心里也松了口气。
“老板,点什么歌?”女孩微红着脸,眼神里有对老城出口搭救的感激。
老城没有去接女孩手里的歌单,他问:“姑娘,会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吗?”
女孩使劲点头,说会。
女孩试了几下弦,果然弹起了前奏,是熟悉的和弦,女孩没骗老城。女孩刚唱出第一句,老城就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在K歌房,这也是老城必唱的歌目,每次他都习惯闭着眼睛唱。他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使他不用看歌词都可以完整地唱完。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首歌,却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它时的情景。那年他去一个名叫海东的小城装修房子,中午休息,他躺在满是木板碎屑的阳台上,看一本杜甫的诗集,对面阳台隐约传来悦耳的旋律。当时春天的阳光正好,把对面阳台照耀得像是空中花园,于花草的缝隙里,他还能窥见一个女孩的倩影,也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妇人。他作为装修工,可不敢对着别人家的阳台胡乱张望,他重新躺下,继续听。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动听的歌曲,他瞬间泪眼朦胧,由此还想起了很多,想起家乡的山河和田野,想起童年,想起母亲,想起初恋,想起儿子刚出生时那一双小巧的脚丫还沾着血迹,想起前妻心情好的时候会给他煮一瓯猪红,说是可以去掉他肺里吸进去的木屑和尘土……他睡着了,醒来时,隐约还记得旋律,可他试图向工友哼出来时却怎么也哼不像了。他很懊恼,那一天根本没能好好工作,满脑子在想那首歌的旋律。遗憾的是,对面阳台虽然还继续放歌,却再也不是那一首了,也许在听歌人看来,那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首,不值得重复播放。直到有一天,在打钉枪的噗嗤声中,老城竟然随口就哼唱了出来——“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他太惊喜了,怎么就能唱出来呢,连歌词也一并唱了出来。他立马又唱了一遍给工友听,工友是个小年轻,整天干活还戴着耳机,脑子里装的就是一个歌曲库,立马就给了老城答案,“这不就是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当晚,老城兴高采烈,请了众工友到小城寻了一家KTV,唱到深夜。老城不记得听了多少遍又唱了多少遍,才把这歌唱得滚瓜烂熟。
此刻,女孩又唱出了别样的风情。她的嗓音和气质很适合这首歌,刚在邻桌唱的歌就很俗气,配不上她的音质。女孩唱完了,老城还迟迟没有睁开眼睛,他感觉眼里湿湿的,不太确定,那是不是泪水。他怕睁开眼睛,那种湿湿的感觉就没有了。他想好好体验一下眼里湿湿的感觉,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湿润的感觉了。
“大哥。”女孩改了口,亲切地说,“唱完了。”
老城这才睁开眼睛,果然,眼睛一睁开,湿湿的感觉就消失了。
“多少钱?”
“一首三十。”
老城用手机扫码,付了款,突然问,“能加下你微信吗?”
女孩迟疑一下,不过很快就点了点头。老城加了女孩的微信,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女孩的微信,而且这一举动对一个儿子已经快要高考的男人而言显得很猥琐,似乎他之前做的一切都带有目的,就是为了加女孩的微信。当然,加微信不是目的,加微信只是开始。老城越想越糟糕,直到女孩拉着小音箱离开,去另外一家大排档卖唱,他甚至都想把刚加上的微信给删了。他打开女孩的微信,发现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微信昵称,叫小玉眉。地区那一栏里,也不是写着深圳,或者其他什么国外的城市,而是老老实实写着“安徽淮南”。这是一个来自安徽的叫小玉眉的女孩。
老城把桌上剩下的啤酒喝完,菜还剩下大半,他也懒得打包了,结了账,就离开了。他走时,隔壁那桌年轻人还在闹,看来他们得喝到天亮去了。老城不得不赞叹,年轻真好!
没过多久,老城就收拾好行李,去了汕尾。那儿有一家商场要装修,工装是比家装要快,不过架不住商场大啊。这么一走,估计也要个把月。老城算了算,每年在深圳呆的日子超不过三个月,零散地分配在每个季度里,好在深圳春夏秋冬也不明朗,所以老城也体验不到光阴的流逝。他总觉得深圳是不变的,就像他的故乡,安静地等着他出走又回来,长时几个月,短则三五天。尽管多年来已经习惯,每次打包好行李,关好门窗再去二楼跟房东打声招呼,他还是觉得依依不舍,像是房间里还有个人等着他回来似的。事实上,屋里除了他这些年零零散散买的几百本书,就没有其他称得上值钱的东西了。老城每次还会往包里塞几本喜欢的书带上,看过的和没看过的,工作之余,他除了睡觉,就想看点书。他看的还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或网络小说。有一回工友把他的书拿去翻了翻,叫苦连天,说这是什么玩意啊一句都没看懂。老城笑着说,说实话,我也没看懂。工友把书一掷,说了一句,有病啊。那是一本暗灰色封面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
在老城眼里,每一座城市,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小城市小县城,它们都是不一样的。声称每个城市都一个样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根本就没认真去感受过。从深圳北站到汕尾站,高铁其实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老城去一趟罗湖都不止一个小时。初到汕尾,老城就感觉这地方有一种面朝大海的生猛气息。等待装修的商场刚好就位于海边公路,站在门口抬眼就能望见码头的渔船和远处的海湾。老城虽说不是第一次看海,眼下的海确实又跟景区不太一样。他去过深圳的大梅沙小梅沙,那些地方的人工痕迹太明显,像是化了浓妆的女人。老城还是喜欢原始的,甚至是粗糙的感觉,他想深圳以前的海應该也是汕尾这样子的,看着就让人心潮澎湃。
第一天夜里,老城就请了工头和其他几个工友去码头街边吃了海鲜。吃海鲜,他们都是外行,不过也吃出了大海的味道。和工友结伴往回走时,老城想起了小玉眉,借着醉意,他把一张白天拍的海景照发了过去,也没打字,又不发语音,就一张照片,倏的一声就发过去了。发了就发了,他也没在意,把手机放在兜里,继续沿着海边公路往回走,他轻轻哼起了歌:“记忆它总是慢慢地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要在这出门就是海的地方呆一个多月呢,他总得做点什么打发时间,给小玉眉发图片试图建立对话,如果不成功,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靠谱的决定。他准备写一篇文章,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几万字吧,在一个月之内可以完成的长度。他已经很久没写过这么长的文章了,之前写的都是短文和诗歌。他把诗歌投给一家诗歌杂志,陆续发了一些;又把短文打包投给一个文友提供的邮箱,那个文友说,这个邮箱是全国最牛的散文杂志的编辑——结果,在出发汕尾的前一天,老城接到那位编辑的电话,说他的一组短文即将在今年第七期上发表。老城当然开心啊,他写文章虽然不是为了发表,能发表终归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所以,老城的心情还算不错,他有信心弄个长一点的,到时再给这家杂志投稿。
回到临时住处,老城才发现小玉眉竟然回了他的微信。
小玉眉说:“帮我预定一艘船,我要漂洋过海去远方。”
老城噗嗤一声笑了。
当天晚上,老城枕着海浪声入眠。他梦见他果真在码头登上了一艘船,不管那船是怎么来的,也不知是渔船还是游轮,迷迷糊糊的,他就上了船。船在海水里摇晃不定,他没站稳,差点跌坐在甲板上。甲板上的木头干翘翘的,是经过海水浸泡的红杉木,真是好木头。老城用手敲了敲,木头发出清清的声响。梦里,他一直焦急地期待船能启动开走,去往大海深处——他还没出过海呢,如果这算是遗憾的话,那么他想在梦中弥补得了。可是船迟迟不开,应该说,除了船和他,并没有开船的人,驾驶舱里空空如也……他想自己跑过去开船,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开,或者说,船好不好开,如果像开车那样,他十几年前就拿了驾照,驾照都期满换过一次了,却一直没用上,没真正开过一次汽车上路。这倒没什么。但是,他想在梦里出海,他站在海风中,却突然醒悟过来,船之所以迟迟不开,那是因为他在等人。还有人没有上船,似乎他们之前就约好了的。等谁呢?老城醒来时,不禁哑然失笑。天还没亮透,他坐起来抽烟,工友迷迷糊糊,在说梦话,叫的是女儿还是儿子的小名。
那个叫小玉眉的女孩看来很闲,话也多,一点都不像她表现出来的样子。老城有些惊讶,两人聊上后,她几乎每天都会找老城聊一会,说她前一天晚上又遇见了什么人,有想调戏和揩油的,也有看样子是喜欢上她了,给钱时多发了一个零,还有很小气的,歌都唱完了才讲价,硬是给二十的,她也没计较,收了就跑,反正也不吃亏。她发来一个大大的笑脸。老城问她是不是打算这么一直卖唱下去。小玉眉说,怎么可能,她们姐妹都说了,这是青春饭,跟明星似的,哪一天老了就没人愿意点歌了,你以为他们真喜欢听你唱歌啊,天真!老城笑了笑,他倒成了那个天真的人了。他可是真觉得小玉眉歌唱得不错,尤其是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小玉眉问老城,要是有不累工资又高的工作还请介绍介绍。老城拍了一张工作现场的照片给她,照片里是装修中的战乱一样不堪入目的商场。老城说,你看,我就干这活,工资是蛮高的,想不想干呀?小玉眉回复一个淌汗的表情。
几天后,小玉眉跟老城说,我真的不想干了。
又几天后,小玉眉再跟老城说,我已经不干了。
不干了也好。老城还为女孩松了口气,随便去商场找个收银的活,也不至于天天晚上看别人脸色。老城觉得年轻人是不能痴迷于赚快钱、赚轻松钱的,那样迟早得付出代价,或者已经在付出代价了。如果为人唱一首歌,就得接受客人目光的侮辱,还有毛手毛脚的,那代价就更大了,养成了惯性,保不准以后继续在受人宠溺又凌辱的道路上滑走,离去娱乐场所坐台也就不远了。老城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他有时去洗脚按摩什么的,跟女孩们聊天,几乎个个都有发财的宏大理想,却又不肯吃苦。老城想啊,做梦吧,要么,就去做鸡。
老城没想到的是,小玉眉竟然会找他借钱。
那天吃完晚饭刚躺下休息,老城顺手就给小玉眉发了个微信,问她找到工作没有。隔了好大一会,小玉眉回说,大哥,能先借我一千块钱吗?我和闺蜜吵架了,刚从她租的房子里搬出来,现在没地方住,身上又没钱租房子。老城一看,有些懵,这架势,如果不是见过面,还聊过一段时间,他立马就应该把她拉黑,这明摆着就是出来骗钱的嘛。老城皱起眉头想了一会,还是选择相信小玉眉,就因为他见过她,还经常想起她被人欺负时羞怯又无助的样子。那就帮人帮到底吧。老城想。不过,他也不是热血冲动的年轻人,当真就转钱给她。老城是不差这么点钱,为儿子艺考的事他托朋友去深大找教授,十几万都花出去了,眼睛也不眨一下。但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他用钉枪一下一下打出来的,血汗钱,如今他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孩子,犯不着急赤白脸的,就给人家打钱过去,像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在人家身上得到什么补偿一样。老城这点成熟稳重还是有的。他沉了一会,前前后后又想了一下,突然有了主意,何不让小玉眉去自己的租房暂住一段时间呢?反正他短期内也回不去,让小玉眉住个十天半个月的,等找到工作,她自然就有住处了。这么一想,还真是两全其美,如若小玉眉不愿意,那不就正好证明她心里有鬼么。老城急忙跟小玉眉这么一说,她听后很高兴,答应了,一个劲地谢谢老城,说他真是个好人。老城这下放了心,看来她真是遇到困难了,否则也不会贸然应承去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住。既然如此,老城就得好人做到底,帮小玉眉一把了,他先是给房东打电话,骗说是老家的妹妹过来深圳找工作,要去他那里住一段时间,让房东把备用钥匙给她。房东和老城早是老相识了,自然没问题,还问老城什么时候回深圳,一起喝酒啊。老城说工程还没完呢,可能还要个把月。老城回头又把地址和房号发给小玉眉,让她到了直接去二楼找房东,就说是老城的妹妹。
第二天,小玉眉当真拖着行李箱住进了老城的单间。她给老城发了张屋内的照片,熟悉的室内布置,幸好走时收拾得还算整齐,突然住进一个陌生女人,不至于尴尬。老城看着照片,感觉还挺奇异,就像几年前他和前妻离婚,前妻收拾属于她的物件搬走,一件不留,家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原来属于老城的东西真的寥寥无几——那种感觉也十分奇异。当然,前后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房间里,那时他们一家人还租住在宝安区,一个三居室的大房子,站在阳台能望见碧海湾公园小山顶的圆形亭塔。老城现在既希望小玉眉能住下来,同时又想在他回深圳之前,她能主动搬走。如果等他回了深圳,小玉眉还不想搬走,那么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么想时,老城竟然暗自发笑,他想的实在是有些美了。
小玉眉又发来几张屋内的照片,很显然,她已经把屋内收拾了一遍,地也拖洗了。看来家里有个女人还真是不一样,后面的照片看起来,比前面要洁净亮堂许多,地板都泛起了白光。老城平时还算是个爱干净的人,没离婚时,他也做家务,做完饭,连带砧板锅铲都会洗刷干净,灶头也擦拭得一滴水渍都没有。
末了,小玉眉发来几个字:大哥,你看这么多书啊。
老城能想象小玉眉站在那个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实木书架前,面对密密麻麻一墙书籍时的情景。她肯定伸手去抽出来一本,不知道抽的是哪一本书?但愿她能抽到一本读得下去的书籍。
一个礼拜后,十天后,半个月后,小玉眉都没找到工作。她跟老城说,你还是得先借我一千块钱,要不我会饿死在你家里的。老城心里打颤,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到最后房子给她住了,钱还是照给。就算怀疑小玉眉是个骗子,也必须给钱了,否则她赖着不走,老城也会拿她没办法。思虑再三,老城更不想小玉眉饿死在他的租房里。老城给小玉眉打了一千块,他就当是丢了。希望小玉眉拿了钱能早日离开,或者早日找到工作。老城确实有些烦了自己,泛滥的多情,最终耽误的还是自己。
收了钱,小玉眉果然安静了不少,甚至一连好几天都不跟老城联系了。老城有时会试探性地问一句,主要是想知道她是不是把他的微信给删了。没有,微信一直没删,而且只要老城说话,她都会秒回,有时几个字,有时一个表情,看样子似乎还挺忙。最后,老城也懒得试探了,他不说话,小玉眉也不主动说话,两人就像恋人闹分手似的冷了下来。再一个礼拜后,老城猜想小玉眉应该是搬走了,但他又不想找她确认,怕打草惊蛇似的,又回来缠着他不放。这样挺好,彼此都识相,悄然消失,一个认栽一个知足。老城花钱买教训,同时也舒了一口气。装修工程也差不多了,过几天收尾就可以返回深圳。对老城来说,回深圳一直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他喜欢深圳,喜欢深圳的街道和气息。回深圳之前,他又去码头转了一圈,看着那些摇摇晃晃的渔船,他不知道这些渔船最远到达过什么地方,沿着茫茫大海,去到了地球的另一半?即便是去到了地球的另一半,它们最终还是会回来,一艘艘停靠在这波澜不惊的海港的码头上,像是一群围坐在村头榕树下默默吸烟的老人。
老城坐傍晚五点多钟的高铁,从码头雇了一辆三轮车到高铁站,几乎就横跨了整个汕尾城。到达深圳北站时,已经是傍晚六點十分了,再转地铁,再坐摩的,老城总算在天黑前到了位于布吉的租房。他提拎着行李箱爬上五楼,钥匙还没有插进去,就感觉屋里有人,也就是说,小玉眉还没走。他的心一下子蹿到了嗓子眼,手停在半空,迟疑着要不要去开这扇门。老城在门口站了一会,他不能再继续站下去了,再站下去,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了。他毅然插进钥匙,转动,推开门,果然,屋里亮着灯,小玉眉穿着睡衣,正在厨房里往外端菜。摆放在屋子中央的桌子上铺着崭新的格子布,上面是几个做得还蛮精巧的小菜,土豆丝,番茄炒蛋,还有一盘烫生菜。打眼一看,这个家已经被小玉眉布置得温馨而雅致,不单是餐桌铺了餐布,连冰箱、电视机和书架,也被覆盖上了颜色各异的布帘,甚至是电视的遥控器,都被装进一个小小的布兜里……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城都快认不出自己的房间来了,就像是一个人不仅是换了一套衣服那么简单,简直还变了性。老城哭笑不得,他站在门口愣住不动,连行李箱也不敢贸然往里面拖,像是一个突然串门来的羞怯的客人。小玉眉呢,她对老城的出现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她笑着说,回来啦,我刚做好饭,过来吃吧。
老城不知道说什么好。平时他要是一回来,首先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再抓起床头的书,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现在,他可不太敢这么做了,不要说屋里多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孩,就看那张床,也不是他随便就能往上躺的了,从枕头到床单再到床垫和蚊帐,几乎都换了新样式,换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品味。老城真不知道睡在这样一张床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真香。
“吃饭啊。”小玉眉催促着说,“还站着干什么?”
老城只好坐上去吃饭。小玉眉做的饭菜还挺合胃口,兴许是肚子饿了,老城吃了两碗米饭,几个菜也被吃得精光。小玉眉只是动了几下筷子,全程似乎都在看着老城吃饭。
吃饱抹净,老城觉得必须说话了。
他说:“你打算怎么办?”
小玉眉说:“你回来了,我明天就搬走,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母婴店当导购员。”
“哦。”老城像是叹了口气,“那今晚……不好意思,要不我去外面住一晚,明天再回来。”
“不用。”小玉眉坚定地说,“这可是你的房子。”
老城却支支吾吾起来,“那我……那我打地铺吧。”
小玉眉起身收拾碗筷,她没说话。
等小玉眉洗好碗筷出来,老城已经吸了三根烟了。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家里吸烟,让他觉得不自在。既然小玉眉确定明天搬走,那么不管这个房间变成什么样,还是会恢复回来的。老城就没有什么需要顾虑的,他甚至有意把烟抽得猛些,故意让屋里拥有曾经熟悉的味道。
小玉眉说她看了老城几本书,并把书本摊在床上,给老城看,老城看了,是几本小说,都是一般读者能读进去的,有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毛姆的《面纱》和余华的《活着》。老城相信小玉眉能把这几本书读完,这都是比较好读的小说,故事也好看。小玉眉说她读《活着》时哭了好几次,她以前看连续剧会哭,没想到看书也看哭了。她说她想起了自己,当然她没书中的人物那么惨,和身边的姐妹比,她只是有些不如意。她在老家读完初中就出来了,去过合肥,去过上海,第三个地方才是深圳。她读书时成绩一般,喜欢英语,不喜欢语文和数学,她从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她扭头看着床上摆放着的三本书发呆,她说她在这一个月里,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躺在床上读这三本小说,一本接一本,先是《寻羊冒险记》接着是《面纱》,最后读完的是《活着》,昨天刚刚读完。这么厚的书,她竟然都读完了,她实在有些吃惊,原来自己也是会读书的,也是可以把这么厚的书读完的。她说着这些时,神情有些激动,像是个小学生,或者小孩子,就等着得到老城的赞许,似乎老城就是她的老师,她的父亲,她的兄长。老城突然有些感动,他点点头,跟小玉眉说,如果以后还想读书,可以来跟他借,不过借了要还的,钱无所谓,书就一定要还。老城本以为是开玩笑,小玉眉却一下子激动起来,她说不,钱我也一定会还的,大哥你放心。老城尴尬一笑,说,我看你那一千块也差不多都花在我家里了。小玉眉红着脸,她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让它好看一点。
老城问,“你是真的找到工作了吗?可不许骗人哦。”
小玉眉说,“真的,不过有点远,在龙华大浪。”
“那就好。”老城突然瞥见墙角处倚着小玉眉的吉他,“要不,你再弹唱一首吧。”
小玉眉笑着过去拿起吉他,背上,“老板,要点什么歌?”
老城微笑著,闭上双眼,“姑娘,会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吗?”
小玉眉使劲点头,“老板,会。”
一曲终了,待老城睁开湿润的双眼,他发现房间里的布置,和去汕尾之前一模一样。
2021年6月5日初稿,西乡
2021年6月18日定稿,东海
【责任编辑】邹 军
陈再见,男,广东陆丰人;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