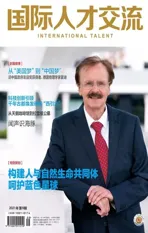卡尔逊与中国工合运动
2021-10-25刘国忠
文/刘国忠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美国驻华武官,是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官,1940年曾历时3个月偕同艾黎一起考察中国工合运动在东南和西南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受命组建了“袭击者”突击营,以“工合”为精神教育训练队伍,在袭击马金岛和瓜岛战役中一举成名,使“工合”一词入选英文词典。卡尔逊是“工合”团结奉献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在斯诺的帮助下,考察中共抗日根据地
卡尔逊1896年2月26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的西德尼,1912年虚报年龄参加陆军,1917年退役,1922年又加入了海军陆战队。1927年2月奉命到达中国上海执行任务,1928年6月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鼓励他亲自去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此后,他结识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同时也是上海英文版《密勒氏评论报》老板和编辑J. B. 鲍威尔,并通过鲍威尔认识了埃德加·斯诺。斯诺在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编辑时,卡尔逊每周到报社来一次同斯诺交换情况。斯诺认为卡尔逊是“一个罕见的集理想主义和实际才干于一身的人”,而他们之间互信的基础也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办公室打下的。因为他们都喜欢历险,而且都对普通人民有深厚的感情,这使他们日后成为亲密的战友。
1933年卡尔逊第二次来到中国,在美国驻北平使馆卫队中做情报工作,同时担任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公使馆卫队新闻》编辑。在北京工作期间,卡尔逊不仅自己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陶瓷、艺术和建筑,而且开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讲习班,请通晓中国文化的各种专家给公使馆的警卫讲北平的历史、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讲中文,增进士兵对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的了解,培养士兵的工作责任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得知埃德加·斯诺带着新婚夫人海伦·斯诺到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时,他喜出望外。这一时期,他与斯诺夫妇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常常听斯诺讲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斯诺夫妇都喜欢卡尔逊,认为卡尔逊刚强勇敢、任劳任怨、拘谨,具有美国人的魅力和善良的品德。尽管如此,当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发表观点时,也会开诚布公。在一次散步中,当卡尔逊抨击美国劳工联合会时,海伦突然发起火来,义正词严地驳斥卡尔逊,使卡尔逊很是震惊。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人跟他这样讲话。但几年之后,卡尔逊告诉海伦,那次谈话使他终生难忘,第一次真正唤醒了他,激发他回到美国去实地了解劳工的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卡尔逊第三次来华,因为战事的需要,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亚内尔要他做海军情报观察员,努力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作战的,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细节。年底他见到了老朋友斯诺,并得到了斯诺刚刚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他钦佩斯诺的正直和勇敢,满怀激情地阅读了手稿,但对书中所描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游击战术等难以相信。斯诺建议他亲自去八路军所在区实地了解,卡尔逊本人也渴望前去,毕竟这对他太有吸引力了。这之后,在斯诺的帮助下,卡尔逊进入八路军活动区进行考察,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4000多公里,并同朱德等领导人深入交流。这次考察中所见到的共产党军队的教育训练以及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彻底改变了卡尔逊对中国人的看法,他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可以学习的长处,这也印证了他的老上级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的观点:“他们丝毫也不比我们低下。”1938年8月27日,卡尔逊在结束中共抗日根据地第二次考察20天后写道:“我有机会观察到一群中国人,他们和我们传统上对中国人的认识完全不同。无私、真诚、诚实、谦虚,富有奉献精神。毫无疑问,我对这群人寄予深切同情。他们的事业如此崇高,我要与我以往的生活方式决裂,投身到他们的事业中去。”
卡尔逊的挚友史沫特莱女士认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卡尔逊影响很大,中国改变了卡尔逊的思想。卡尔逊曾经与斯诺一起目睹上海战争的许多战斗情况。在他们讨论日本侵华后中国的未来时,作为一名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人,卡尔逊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她的所有工业基地,要同日本的那种现代化军队作战是不可能的。”卡尔逊深入观察了八路军后方的种种情况,时间虽短,但却看到了中国抗战的新潜力。他认为,这个后方就是对付现代化日本军事机器的良策,但从长远看,急切需要解决八路军的军需问题,在这方面不仅要精心指导农业生产,解决军民口粮,而且还要积极在农村发展一些小型工业,通过就地取材,鼓励人们协作发展生产,减少战争造成的损失。这种观点与后来兴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一致。

卡尔逊 (来源于The Big Yanke: the Life of Carlson of the Radiers)
1940年秋,卡尔逊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与斯诺夫妇再次见面。此时,卡尔逊写完了《中国的双星》,想经马尼拉去中国再次访问,而斯诺夫妇此时正在碧瑶,一方面宣传工合,另一方面休养、写作。在马尼拉,卡尔逊还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菲律宾分会的邀请到菲律宾大学讲演,在这里卡尔逊也再次见到工合的另一位创始人路易·艾黎,并应艾黎之邀自费到中国考察工合运动开展情况。
与艾黎实地考察工合
1937年秋,卡尔逊与艾黎在上海初识,1938年又在汉口重逢,这是他们的第三次见面。此时,卡尔逊已经辞去了军职,靠积蓄和写作生活,他要以普通人的身份不受限制地把中国正在发生的战争真相公之于世。这个时候,艾黎是工合的技术顾问,正在为东南部的新四军根据地工合中心建设筹集资金。此时卡尔逊对工合有了“兴趣”,想了解它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能有什么作为。他认为工合便于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还能以多种方式在各地推广。因此,怀着了解工合运动情况的迫切心情,在告别斯诺夫妇后,卡尔逊随艾黎前往中国考察工合在东南和西南的开展情况。卡尔逊传记(《卡尔逊与中国》)的作者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认为,艾黎对卡尔逊的下半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0年秋,离开斯诺夫妇后,卡尔逊与艾黎经香港乘船到内地步行到淡水,再到惠州,通过日占区,到达东江沿岸的龙川。从那里起,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许多工合中心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乘坐的是拥挤不堪的老古董公共汽车。
卡尔逊对他所看到的每一个方面——不论是在南雄对身患黑水热的少年采取的措施,还是在兴国对伤残军人作出的努力,不论是对于都新办的陶瓷厂,还是对延平(译音)的制伞工人,都很感兴趣。在考察过程中,他们不仅对所看到的合作社工作情况进行讨论,提出他们对工业合作社开展工作的想法,也对所看到的当地人文历史或所想到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交流看法。
随着考察的深入,渐渐地,卡尔逊明确了他下一步所要做的工作:“他要再回美国,敦促当时有权势的人物,向他们陈述世界局势的紧迫性。他还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他确信这场战争不久也会落到美国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它想要干什么,组织上实行民主,并且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来自普通百姓。”
在皖南的茂林,除考察工合事务外,卡尔逊还会见了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并在回太平的路上,与刘少奇进行了长谈。在考察完新四军的驻地后,他们又设法搭乘公共汽车和卡车经皖南和浙江,再回广西。在那里完成任务后,仍乘公共汽车和卡车,经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四省,最后抵达战时的首都重庆。此次考察历时三个月,行程6440多公里,视察了600个各类工厂以及为其他工厂生产机器的工厂,产品包括纺织品、火柴、皮革制品、鞋、纸张、糖、肥皂、酒精、建材、军火、烟草、蜡烛、雨伞、手电筒、电池、卡车零件。
卡尔逊将考察情况写信告诉罗斯福总统,在信里他详细描述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所领导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认为工合运动是为了恢复被日本破坏了的中国工业,这是游击战术在工业中的运用,一旦日军来袭,工厂能够迅速地撤走。
这次考察,卡尔逊目睹了工业合作社的工作,看到了工业合作社员工们不计报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团结互助,组织生产各种工业产品和军用物资,利用当地原料进行生产自救支持抗战,看到了社员们团结协作、努力工作的积极状态,深入地了解了工合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他深刻认识到,没有经济战作为支柱,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战争永远也不能取得胜利。关于此次考察,从艾黎给工合的报告中可见一斑:
在曲江,我们看到叶乐健工程师和他的同事们挤在一个机器合作社很破陋的小屋子里,他们的事务所被敌机炸毁,会计员蔡伏波君因逃避空袭,溺死水中。虽然如此,工作仍照常进行,全所同仁精神颇为振奋,机器合作社很赚钱,工人们个个精神饱满……很痛心的是,在我们离开曲江后不久,叶君便不幸患伤寒病逝。叶君是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和干练的合作运动家,实为工业合作理想的技术人才。他生前毫无储蓄,除生活费外所余尽以帮助同仁,如辅助社员疾病医疗费或家属迁移费等。病入医院时,他拒绝住头等病房,坚持住在三等。这种献身的精神,足以感人。
……
兴国工合小学,有些教员系伤残军人,义务任职。社员子弟学校的设立,大大提高工人工作热情,因而促进了生产。合作社工作的巩固有保障,吸引了许多很好的技工。他们在其他地方入运输事业等,本可以赚更多的钱,做较短时的工作。但是他们为了得到长期性的工作,宁愿参加合作社,得到工作保障和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改善。
——摘自《三月工合视察记——艾黎》,载于《工合通讯》第二卷二、三期合刊
在重庆,工合协会全体人员开会欢迎卡尔逊,卡尔逊在演讲中说:
“在我没有到这里以前,三个月的旅行在东南和西南差不多走了八省,到处都可以看到分散在各地的工合事务所、合作社,正向着开展之途迈进。我虽是军人出身,我对工合工作的困难却很了解,很希望在总会的同志们今后多有机会到各区事务所实地看看。这些基层工作同志,所受到的痛苦、刺激和愉快,有许多是我们在歌乐山的同志们所不能想象的。我们相信各位参加工合运动,都抱有很大决心。工合运动不但对抗战有很大的意义与贡献,就是对于整个社会与我们自己人生,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与影响。
“目前世界正在剧变中,自从几个侵略的野心家,在欧洲与远东燃起了战争的烽烟之后,有很多的国家失去了自由独立,有很多的人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在这惊涛骇浪中,能够从事工合运动,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为建立民主政治而奋斗,是很荣幸、很自豪的事。
“不久我回到美国之后,我一定竭尽我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工合事业努力宣传、呼吁捐款。”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回到美国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工合,为工合争取支持。
传承工合精神
卡尔逊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一旦认准了的事,就会毫不犹豫、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回到美国后,他不仅在《美洲》杂志上撰文记述他考察皖浙工业合作社的观感,介绍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而且去华盛顿见了罗斯福总统,积极争取美国政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提供一笔贷款。在纽约,他同负责中国工合事务的美国委员会进行了接触,敦促一定要支持路易·艾黎和香港霍尔主教主持的实行民主领导的合作社。
因为坚信日本会对美国开战,卡尔逊申请回归海军陆战队。1941年5月25日,他获批参加海军陆战队,并担任作战情报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5日,卡尔逊以中校军衔受命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第一独立营,之后被正式命名为“第二袭击者”。
在队伍训练的过程中,他倡导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训练方法,强调官兵平等,在官兵中鼓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并将“工合”作为“袭击者”营的精神和口号。他说:“工”就是工作,“合”就是协力,“工合”就是协力工作。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工合”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都要遵守纪律,尊重知识。“工合”的重要性还在于大家个个都是战斗员,“工合”会给予大家信心,而这种信心在战斗中可以使成员产生主动性和勇气,提升大家的战斗力,由此就可以用较少的牺牲给敌人带来更大的损失。艰苦的训练让“袭击者”营在马金岛战役中出了名,“工合”也因此成为“袭击者”营的象征,“工合”一词入选英文词典,“工合”团结奉献、努力干的精神也得到广泛的宣扬。
“工合”这个词最初是卡尔逊从上海一个为前线送饭的苦力那里听到的,意思是“合力工作”。卡尔逊再次听到“工合”这个词是在他与八路军司令部政委任弼时讨论军民关系的时候。任弼时曾说,军民关系就像鱼水关系一样,人民也要学会掌握自己,学会协调一致地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工合”就是“共同工作”。官兵之间要做到“工合”,就要做好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教育使官兵都做到诚实、谦逊和团结合作。卡尔逊认为道德教育是八路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秘密武器。
卡尔逊再次听到“工合”时,“工合”不仅是团结协作,“努力干,一起干”,也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在与艾黎考察工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卡尔逊发现工业合作社特别强调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精神,强调团结协作。卡尔逊曾满怀激情地说:“这(合作)不仅是对中国未来的回答,也是对全世界民主制度未来的回答,让所有地区的人民得到在平等基础上合作的机会……”
艾黎认为卡尔逊是有创造力的人,属于那些“主宰他的环境,披荆斩棘探讨未来”的人们。
1947年卡尔逊病逝后,他的老朋友艾黎说:“卡尔逊是为美好的世界而战斗的有识之士,许多正直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海伦·斯诺认为卡尔逊把他对自己“道德规范”的基本观念——基督教自我牺牲精神与工合“努力干,一起干”精神,以及八路军不怕困难、团结协作的精神进行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