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现代
——《法哲学原理》“伦理总论”释义
2021-10-14庄振华
庄振华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 710119)
提要: 黑格尔伦理学说是对近代早期以来一直困扰学界的“群己权界”问题的一种深刻回答。黑格尔认为,社会活动与人际关系均扎根于生活世界整体(伦理实体),而且后者的概念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更高层面上绝对者的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在实体性根据的意义上看待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与世界历史,又不能以这些伦理形态为终极根据,误将它们(比如国家)当作世界的归宿。以往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从黑格尔同时代人到霍耐特的研究)大都撇开了它的形而上学根据,仅仅就法哲学(或其部分内容)而论断法哲学。菲韦克重视法的形而上学根据,但在对伦理的逻辑学定位上却产生了偏差。针对这些研究,有必要将《法哲学原理》放回它与其他著作(尤其是《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构成的相对位置中去,通过对关键文本的详细阐释,既探明伦理的重要性,又勘定其局限性,方能了解其现代意义何在。
“群己权界”是困扰近现代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一个难题。表面看来,它似乎仅仅涉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而与绝对者和宇宙秩序无关,近代政治哲学的种种争论,基本都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且不论近代早期伴随着权力政治兴起而产生的马基雅维利学说与“国家理由”学说,单就社会契约论各流派来看,无论假定自然状态下人人为敌(霍布斯),还是假定那时人人自由平等(洛克),抑或在更思辨的意义上设定理想的“公意”状态并以此达致每个人的自由(卢梭),这些流派都没有越出上述两种关系之外。但在黑格尔看来,不仅这些关系扎根于生活世界整体(伦理实体)①,[1-2],而且它们的概念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更高层面上绝对者的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既要在实体性根据的意义上看待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与世界历史,又不能以这些伦理形态为终极根据,误将它们(比如国家)当作世界的归宿。
对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往人们大都关注黑格尔是否是普鲁士国家辩护士(黑格尔主义者及同时代人)、社会②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或者在近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讨论黑格尔关于契约、个人自由、国家政制等问题(英美学界),近些年则比较热衷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研究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霍耐特、丕平等)。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撇开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根据,仅仅就法哲学论法哲学。也有部分德国学者(亨利希、菲韦克)对于去形而上学化的做法有所警惕,正如菲韦克所言,目前“在对《法哲学原理》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大多是认为必须放弃形而上学根据的立场”,然而单就“伦理”篇而言,“在开头几段(第142节)这种企图就必然落空,那里逻辑学的基础明白无误地被确定下来了”[3]232。但正如后文将要表明的,菲韦克尊重形而上学背景的意图虽好,他以《逻辑学》的“概念论”为《法哲学原理》定向的做法却是一种逻辑错位,最终还是落入主体性自由的窠臼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工作是不彻底的。
重视形而上学根据的做法显然更合乎黑格尔的本意,而要恢复黑格尔法哲学的本来面貌,“伦理”篇是一个极好的切口,因为该篇以“实体”这一明确的逻辑学定位表明了黑格尔对于伦理的地位的看法不同以往,但“伦理”在整个精神哲学中上通绝对精神的关键地位又不容许我们将任何一种伦理形态(包括国家)视作绝对。下文首先以《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为坐标,确定“伦理”篇的体系位置,间接透显其思想旨趣,然后从正面对“伦理总论”(第142-157节)部分进行文本释义,一方面表明伦理具有个体道德、主体际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透显伦理并非究竟之境,指出伦理层面的局限性,最后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现代激流中黑格尔伦理学说的潜力。
一、伦理的体系位置
在当今的日常用语中,“伦理”与“道德”几乎是同义的。然而在现代思想中,黑格尔的“伦理”(Sittlichkeit)概念却是个新事物③,[4][3]230(Bemerkung)。菲韦克认为,黑格尔并非简单造出一个新说法,而是将一整个范畴(Kategorie)引入现代实践哲学,该范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Schlüsselbeg-riff)[3]229。从家庭教师时代对实定性(Positivität)的逐步接受,到耶拿时代的《哲学批判杂志》系列文章和《伦理体系》,经过《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伦理实体”的论述,直至《法哲学原理》中体系化的“伦理”篇,黑格尔逐步形成一套看似独特,实则深具传统色彩的伦理思想。这体现出他在现代语境下承接西方古典传统的一贯抱负,他绝不愿意仅仅局限在同时代道德哲学的视角下就事论事[5]。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总体来说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学者们对伦理的逻辑学根据以及法哲学在整个精神哲学中的地位不予重视,或者进行了错误的定位。照此看来,要读懂“伦理”篇,首先必须从不同方面准确把握该篇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不能仅仅在法哲学的框架下考察“伦理”篇,要将法哲学还原到精神哲学的整体中;鉴于精神哲学是“一门应用逻辑学”[6-7],还要将精神哲学放到与逻辑学的良性互镜关系中来考察;另外为了充分理解伦理的实体性与绝对性特征,也要将《精神现象学》对“伦理实体”的论述④纳入考量。由此我们看出:伦理是作为实体性根据的“现实性”,但还不是《逻辑学》“概念论”意义上的“概念”,因而人们在这个层面上虽然开始承认各伦理形态的基础性地位,但毕竟无法避免“本质论”意义上的种种反思性设定。因而人们一旦将伦理绝对化,便有封闭化与自我固化的危险。以下我们由远及近地考察“伦理”篇的体系地位,以期澄清该篇的思想旨趣。
(一)《精神现象学》的“精神”章
在《精神现象学》中,“精神”章处在极为关键的位置,因为它达到了此前从未做到的自觉立足于事情本身的境界。黑格尔在该书的前五章描绘了意识的五种形态⑤,而在前四种形态下,意识无论停留在最肤浅的感性印象和事物的单纯“存在”(“感性确定性”章),还是在个体内部试图裁决事物与各属性或统一性与差别性的争执(“知觉”章),抑或在类概念与类概念之间建立规律以图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知性”章),又或者在尊重他者内在无限性的前提下,在欲望或承认中寻求建立利己的相互关系而不得(“自我意识”章),毕竟都还处在较为抽象或局部的层面,意识还没有像“理性”这样达到对“整个世界合乎理性”的信念,可见前五种意识形态由“理性”总其大成。然而理性也有它无法突破的“瓶颈”,它以吞吐洪荒的伟力,经历了举凡近代人所能设想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领域,却发现所谓世界的合理性(知识、规律等)原不过是理性在世界上截取的一张合乎它要求的皮(“观察的理性”),或者说只是它自己认为公正因而强加于人的一些规范(“合理的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而实现”)。这样的合理性不可谓不客观,但绝不等同于事情本身。于是该章第三节中,理性试图承认事情本身的力量,最终却由于其行事方式而陷入与事物本身互为外在个体的窘境。总而言之,在“理性”章中意识发现生活绝不仅仅取决于理性的本事,理性最多只能达到一种自以为客观的主观信念。因为理性终究会发觉,有一些高于它之上的因素是它不得不接受的。这便进入了“伦理实体”的形态:事物并不取决于理性对它的描述或推进,“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某个东西不是自相矛盾,所以它是正当的。毋宁说,正因为它是正当的,所以它是正当的”;不仅如此,人还前所未有地以事物本身为自身的本质了,“由于正当事物(das Rechte)对我来说是一个自在且自为的存在,所以我存在于伦理实体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实体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而自我意识则是伦理实体的现实性和实存,是伦理实体的自主体和意志”[8]。这种“还事物本身于事物本身”,而不再以理性勾画的世界图景代替世界本身的行事态度,正是“精神”章要描绘的[9]。
但话说回来,在“精神”章中人虽然立足于事情本身,毕竟还是从意识的角度在看问题。“精神”章展示的便是意识在承认精神根本地位的前提下的成长史。具体到“伦理”(希腊伦理世界与罗马法律状态)部分而言,这个阶段因尚未陷入中世纪教化与近代启蒙、道德世界观这些二重化的世界格局之中,相对而言尚属“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某种较质朴状态⑥。这种状态尽管在黑格尔的家庭教师时代与耶拿时代尚未得到系统总结,在后来的精神哲学与法哲学体系中又经历了相当大的删削变形,但始终是黑格尔心目中一个“纪念碑”式的典范。从黑格尔历次法哲学讲座中对伦理实体本身的描绘,以及对城邦神与家族神的反复提及,都不难看出古代伦理实体依然是这里的重要参照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所谓“参照”意义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古代伦理状态由于没有经过中世纪与近代二重化世界观的“锤炼”,尚属朴素先民状态,这意味着它还没有打开内心化的信仰与道德境界,也没有我们熟知的近代以来这种主体反思性义务与权利[10],因而严格来说不同于法哲学中的伦理。
(二)从《逻辑学》看“伦理”篇的体系定位
如果通过《逻辑学》的构造来间接理解“伦理”篇的体系定位,那么考虑到《精神哲学》是一门应用逻辑学,“伦理”篇大致对应⑦于《逻辑学》的哪个部分呢?《法哲学原理》文本中常见的“理念”“概念”“活生生的善”等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逻辑学》的“概念论”,实际上亨利希、菲韦克就是这样做的。亨利希早年便试图用概念论中三种推论的模式看待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3]232,而菲韦克则这样概述自己的想法:“在自由的理念的意义上,伦理事物显现为目的,显现为活生生的善,显现为成了现成世界和意识本性的概念。这里问题便被回溯到《逻辑学》概念论的整个第三部分,被回溯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被回溯到从推论学说(尤其是各推论构成的体系)经过目的论和生命直至认识的理念与善的理念的统一的那条路。”⑧,[3]231
二人的这种做法看似有很多文本“依据”作为支撑,实则问题很大,最主要的问题是混淆了精神形态的具体运作方式与其体系地位,误将伦理相对于抽象法、道德而言更深刻的思辨性混同于概念论在《逻辑学》中具有的最根本地位。不可否认,经过《逻辑学》锤炼的思辨思维,已经达到了绝对理念,由此再进入《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概念论中“推论”“理念”“概念”这类范畴的确可以运用于上述两种“应用逻辑学”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运用这些范畴的地方在体系地位上就对应于概念论或概念论第三部分了。否则黑格尔曾说所有的法都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80,照此说来岂非整个法哲学都要置于概念论层面?那么黑格尔为什么又说作为伦理形态之一的市民社会是抽象自由的层面、知性的层面[2]415-416?又比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过一切理性的东西都是一个推论,推论可以充当理性的一般形式[11],这当然也不意味着一切合乎理性的东西在体系地位上只能“回溯”到概念论层面。再比如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多次提及的概念与理念关系,其实可以运用于整个精神哲学上,“精神……是自然的真理,……在这个真理中自然消逝了,而精神则表明自己是达到了其自为存在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客体和主体都是概念”[12]。
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喜爱穿凿附会。促使他们有意忽略《精神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学说或《法哲学原理》中关于伦理作为“实体”的诸多论述,如此这般方枘圆凿地将“伦理”篇锚定于概念论之上的,恐怕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主体主义观念。由于亨利希的研究成果极多,梳理这些成果的工作非本文所能容纳,这里我们且以相对较晚近的菲韦克作品为例。他援引黑格尔的某些文本,将概念论第三部分(“理念”)进一步归结为一种主体主义式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并反过来以此融摄整部《逻辑学》,将该书称为“某种主体性哲学的奠基”[3]231-232,最后又顺便扩及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自我规定和自由(Selbstbestimmung und Freiheit)这些思想在本质上(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既塑造了逻辑学的论证路径,也塑造了实践哲学的论证路径”[3]234。不出意外的是,基于这种将伦理定位于概念论的策略和以主体性自由为核心的立场,他还努力将宗教、艺术和哲学“沉降”到国家范畴内⑨,[3]248。菲韦克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以本质论消解了概念论,一定会赋予伦理形态某种不适当的绝对性地位,对于黑格尔法哲学而言是极不公正的。
笔者以为,伦理在整个《精神哲学》中的地位与《逻辑学》中的“现实性”相应,这一点有三个主要的依据:(1)仅就“伦理总论”而言,黑格尔反复以“实体”“现实”界定伦理、善⑩,以强调个体主体并不自外于实体,而是以实体为自身生活的根基,这恰恰是《逻辑学》的“现实性”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2)在《逻辑学》中,“现实性”对于意识而言具有不容否定的绝对者地位,但那毕竟与概念论层面就绝对者本身而言的绝对者不可同日而语,而法哲学中关于伦理地位的论说也与此相似。表明这一点的一个明确的证据是,黑格尔在1818—1819年为先前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所写的讲座笔记中说伦理整体不是想象中的整体,而是古代家神和民族神意义上的“现实的神”(wirklicher Gott)。(3)与此相关,文中屡次提到希腊伦理世界及《安提戈涅》,这证明黑格尔依然以古代相对和谐的伦理实体状态为典范。黑格尔在逻辑意义上向来以“实体”界定古希腊世界,在整体上并未以概念论视之。
(三)《精神哲学》中的“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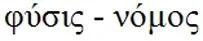
二、从“伦理总论”看伦理的重要性与局限性
作为“伦理”篇的导论,“伦理总论”与前两篇(“抽象法”和“道德”)进行对照,主要论述的是伦理作为个人生活以及抽象法、道德之根据的实体性地位,以及由此对个人义务(及德性)与权利的关系带来的影响。对于“伦理总论”部分的整体布局,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深研黑格尔实践哲学的荷兰哲学家佩佩尔扎克有极为精当的分析[10]169-170,现按照他对各段落的分划进行一个文本释义。
(一)伦理概念(第142—143节)
法的所有形式(抽象法、道德、伦理)都属于人力所能及的层面,是人站在有限者的立场上与他人人格、自己内心以及作为伦理实体的事情本身打交道的方式,因而在本质上都受制于《逻辑学》本质论揭示出的二元架构。在这个前提下,从具体运作方式(而不是体系地位)来看,在所有这些形式中,伦理又是最具思辨性的。这意味着客观上对于读者而言,自由理念的两个环节(意志概念与作为其定在的特殊意志)不再像抽象法层面的各种法现象那样直接过渡,也不再像道德层面那样陷入内心自律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对立,而是有意识地、内在地相互蕴含并互为条件。但当事双方的视角又有所不同:伦理生活的当事人明确意识到共同体是自身存在的根据、动力和目的;而共同体的存在又仅仅体现为每一个具体当事人的行动,此外无他,因而具体当事人并非它的他者,而是它本身的成全者。但又必须留意到,尽管伦理已是法的最具思辨性的形式,它毕竟还没有达到概念论的层面,因此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既互为条件,又可能发生矛盾。因此,黑格尔在1822—1823年的法哲学讲座中才说:“因此实体的各环节就是意志的概念与其自内反思,但伦理的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已经是总体了,而且双方已经是知识了,因而既是对它们的区别的知识,也是对它们的统一的知识。因此伦理就是意志的理念。”[15]
(二)伦理的客观方面(第144—145节)
伦理从客观方面来看就是一些超出了主观意谓(Meinen)之上而自在自为存在的规律(Gesetzte)与机构(Einrichtungen),或者说是一些伦理势力(sittliche Mächte)。黑格尔在144节“补充”中说安提戈涅宣称伦理规律是一些无人知其从何而来的永恒东西[1]294,这表明伦理势力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法逾越的崇高之物,个人植根于它们之中,如同子女对于生养他们的父母或故乡一般。
伦理势力与个人的关系远比抽象法和道德层面深刻:个人并不像受到抽象法管制那般与伦理势力貌合神离,心生怨念却无如之何,也并非仅仅在内心怀揣其万分珍惜与崇敬的道德规律,实际上却使得后者沦为抽象的异己之物,而是如同偶性从属于实体、肢体从属于整个有机身体一般,既服从伦理势力,又仅仅在这势力中才获得自身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并非个人的任性,而是依循伦理势力中的必然性规定而来的。而通过伦理的必然性规定之所以能达致个人自由,根本原因在于伦理本身就是理念的规定的体系,是意志的合理性事物(das Vernünftige des Willens)[13]291[2]397。换句话说,伦理势力不是外在的权力,而是使意志得以收束自身的内在形式与方向。它们规定了意志能理解的执行路径,需要意志坚韧不拔地努力克服任性才得以持存。这便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持家之道”“治国之道”等,它们仅仅对于个人的利己私欲而言才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具有更深广、更宏阔眼光的人而言,恰恰能在比个人私利更高的层面达成他们的自由。
(三)伦理的主观方面(第146—155节)
1.伦理的主观方面分为义务(德性)与权利两个环节(第146—147节)
伦理实体与个人的自我意识内在融合在一起,而且除了这种自我意识之外别无其他存在方式,通过这种自我意识才达到对其自身的知识。所以从主观角度来看,一方面伦理实体有其独立且高于个人的存在,其坚固程度甚至超过了自然事物,因为自然事物仅限于外在的、个别的形态,而伦理实体的制约作用则深入人内心,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另一方面伦理的种种规律和力量并非个体的外物,反而是个体的本质和依归,因为主体只有在它们内部才有其特殊存在,才产生自身感(Selbstgefühl)。上述两个方面中的前一方面指向义务,后一方面指向权利。
2.义务(德性)(第148-151节)
在伦理层面,义务(Pflicht)是个体在伦理实体那里感受到的约束力。与此相应,伦理的义务论是“伦理必然性圆圈的系统展开”,一种内在而连贯的义务论不是别的,只能是“国家内部因自由理念而成为必然的诸关系的展开”[1]297。因而作为个体之本质与依归的种种伦理形式固然以“必然性”的形象制约着个体,而且这般的必然性并非零星、个别地出现,而是环环相扣、自成一体,但个体在其中感觉到的并非外来强力的威势(抽象法义务),亦非符合遥远目标的抽象的“应当”(道德义务),而是足以拔升自身的崇高使命(伦理义务)。
黑格尔还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能使人获得解放(Befreiung)的义务的性质。只有对于单纯遵从主观好恶(“任意”)的“自然意志”而言,伦理义务才是一种强制和约束;但真正说来个体通过义务得到的乃是解放,因为义务令人摆脱自然冲动和抽象道德反思的牵绊。这种解放并不是顺从主观好恶,而是摆脱主观好恶本身的局限,是沿着各种伦理形式拾级而上的“实体性自由”(substantiellen Freiheit)[1]297-298。在黑格尔心中,只有这种实体性自由才真正合乎“人的概念”。同样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只有依照伦理规律生活的人才得其所哉[15]499。或者说,义务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肯定性自由(affirmativen Freiheit)的赢获[1]298。
正是在通过自觉实现伦理规律而获得自由的意义上,才出现了适当考察德性(Tugend)与正直(Rechtschaffenheit)的时机。在抽象法层面,个体行动的标准唯有与其他个体保持外在的法律关系,因而只有合法与非法之别,谈不上什么深度;到了道德层面,个体行动倒是具有了内心反思的深度,但内外两分的格局注定了该行动与事情本身的隔离,因而该行动只有抽象的善良与邪恶之别;只有到了伦理层面,个体行动才既体现主体反思的自觉性,又具有客观实体性,这便是我们通常说到“德性”与“正直”时不言而喻的内涵。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体现在自然性格上便是德性,而德性就个体对义务的适应而言便是正直。就德性学说不仅仅是抽象的义务论,还包括性格与自然中的许多特殊因素而言,它是一部自然史。在堪称“伦理世界”的古代,人们更喜欢谈论德性,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因为伦理事物包含许多特殊因素,在个体身上总有多少之别,便探讨作为中间状态的德性;而现代人表面上不太谈论德性,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没有德性了,而仅仅反映出德性一方面更受制于主体内心的道德反思,另一方面伦理在现代不那么体现为英雄式的个体形象,而采取了更具公共性的形式,成了公共领域中的职分。
伦理凝结为个体的现实生活与行事方式,便是伦常(Sitte)。正如大自然形成规律,自由的精神也产生伦常。因此伦常是人的第二自然,而教育便是引导人走向第二自然的过程。第二自然使得自然意志与主观意志的对立消失,使精神不再受制于主观念头,也使理性的思维获得自由,由此伦常成为人的定在,是一种贯穿性的灵魂、意义和现实,是展现为一个世界的活生生的现成精神。在伦常问题上,黑格尔提到“过”与“不及”的两种做法,认为那两种做法都不合适:一是中国人过于重视伦常,使得伦理事物成了外在规律;二是道德还算不上精神,因为它还沉陷在主体与事物本身的对立之中。
3.过渡节(第152节)
在个体克制了私意,向伦理的普遍东西提升自身的前提下,他的主体性不仅值得保留,甚至还成了伦理实体的绝对形式与实存现实(die existierende Wirklichkeit),由此伦理实体性便达致其正当状态与效用。换句话说,主体性构成了自由概念的实存基础。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持存的必要性,便是伦理“权利”。
4.权利(第153-154节)
黑格尔并不抽象孤立地看待权利,他强调主体无论对于其自由的追求,还是对于其特殊性的坚持,都只能在伦理实体中达成。主体之所以确信自己是自由的,而不陷入主观空想,那是因为他处在客观的伦理实体中,能在其中推进客观的事务。由此这种确定性(Gewissheit)才能成为真理(Wahrheit),才能实现其内在普遍性(innere Allgemeinheit)。黑格尔还举了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来强化这个意思:一个毕达哥拉斯派成员回答一位父亲关于如何培养儿子有德性时说,让他成为一个有良法的城邦的公民;而卢梭在《爱弥儿》中描绘的封闭隔离式教育则是黑格尔不敢苟同的,因为那违背了教育使个体权利与精神世界之整体相贯通的本质规定。
个体对其特殊性的权利也只有在伦理实体中才得到维持,因为特殊性不是别的,正是伦理实体的显现。人或许会以为自己的特殊要求是他个人独享的某种私利,殊不知要是没有伦理实体,这种特殊要求既无法存在,也没有意义。
5.义务与权利的统一(第155节)
那么在伦理层面,个人事务从其自觉向普遍东西提升的角度来看便是义务,从其维持自身特殊存在的角度来看便是权利,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体的。我的义务就是我的权利,因为我通过义务助其成全的伦理实体只存在于千百万个“我”的权利之中。这与抽象法和道德层面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在抽象法层面,一人有了权利,另一人才有义务,一人与另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外在地相互依赖;在道德层面,我自己所知、所愿、所选的权利只是“应当”与义务合一罢了。当然,黑格尔是很现实的,他不会抽象地陶醉于权利与义务合一的美好愿景,他也看到了阶层与职分的区别导致权利与义务不断细化的情形。另外,相反的情形他也考虑到了:奴隶这种彻底臣服的非人状态,当然无所谓权利,也谈不上什么义务。
(四)小结(第156节)
伦理实体包含自我意识同其概念的统一。黑格尔在这里还表明,他在伦理中提到的绝对者其实并不是在概念论层面而言的,而是在本质论层面“现实性”范畴的意义上而言的,因为它是希腊家族神、民族神一类的精神实体。
(五)“伦理”篇结构(第157节)
黑格尔对这一结构的勾画已是众所周知,此不赘述。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伦理层面的国家并非家庭、市民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果,它反而是家庭、市民社会的前提与根据;二是艺术、文学、科学虽然需要在国家内才能繁盛[2]412,但只是将后者作为生长环境,而并非以国家为根据,因而它们并非像菲韦克暗示的那样那样沉降为国家层面的公民自由。
结 语
在黑格尔去世之后,世界上各种“主义”的争执不曾稍减。人们对他的法哲学的一个典型看法是,它太过理想了,以至显得抽象甚至空洞。从左翼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没有基于社会现实看问题,反而不适当地以越来越抽象的观念之物(国家、上帝等)充当社会的根据,根本不符合与资本主义斗争的需要;从当代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是核心问题,在黑格尔那里一切更高的东西都应该服从于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学者们即便强调伦理实体作为抽象法、道德之根据的地位,仍然会以沉降的方式消解绝对精神及其思辨性思维。
诚如佩佩尔扎克所言,法哲学原理展开的法的理念相对于世界上任何现成的法系而言都是一种理想,黑格尔虽然坚持该理想的现实性,但同时深知他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他心目中真正的国家形象相符[10]172。作为实践的产物,伦理既坚实又脆弱:坚实在于一旦时代趋势合乎事情本身的秩序,便会很好地实现这种伦理;脆弱在于人们将目光聚焦于人力所能及的层面并追求自身利益时,黑格尔对精神的高级层面的描述并不实用,反而显得抽象而不近人情。由此人们似乎有资格反问黑格尔:伦理的各种形态何以一定是精神的体现,何以一定是合乎理性的?难道这些形态不是又在两个方向上濒于瓦解的危险吗?——在过于形式化的方向上,伦理可以被描述得合乎宇宙秩序,但那种“不接地气”的秩序岂非虚悬而自行架空了?在过于质料化的方向上,个体如果过分专注于可见利益的分配,其他一概毋论,就有从伦理实体松脱下来的可能,此时伦理实体其实什么也不是[10]173。伍德基于类似的担忧提出的辩难也颇具代表性,在《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的末章(“现代伦理生活的各种难题”),伍德发现,黑格尔伦理理论的主要目的虽然是展示伦理秩序的合理性(rationality),但与此同时黑格尔也认识到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是:穷人陷入的既无权利亦无义务的窘境与该目的相冲突;乌合之众心态(rabble mentality)对于整个现代伦理,乃至对他的整个客观精神理论要达到的根本目标,都是一个威胁。虽然黑格尔意欲肯定自己的那些原则,但正如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每个时代原则的反思性自觉都会导致该原则的终结,他的法哲学的界限似乎也由此被揭示出来了[17]。
上述这些现象固然都是现代的核心难题,但笔者以为,黑格尔伦理学说对于现代生活首要的启发并不在此。认为这种伦理学说最大的毛病是“不切实际”,这终究是以当代人的眼光在要求黑格尔。殊不知在黑格尔看来,恐怕这依然是一孔之见,因为如果片面强调伦理的实体性而忽视其局限性,最终忽视黑格尔整个精神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在贯通于宇宙秩序方面的根本旨趣,恐怕这种实体性最终也确立不起来。原因在于,如果人们不就上述更大的背景讨论伦理的实体性,终归会像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许多解读那样,将绝对精神沉降到伦理中。更糟糕的是,人们不会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以非伦理的态度看待伦理,亦即使得家庭、社会、国家成为人的权力意志的支配对象。若以《逻辑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便是消解了概念论,落回本质论的封闭状态。所谓“封闭”,指的是如果人们单纯就事论事谈论个人与伦理形态、社会与国家、义务与权利的关系,无论他们强调的是这些“对子”的“分”还是“合”,都只是固化人的利益,没有达到黑格尔超迈于时代之上的远见。追求“天理”抑或“人欲”、开放的宇宙秩序抑或封闭的人造世界图景,这恐怕是人类永恒的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伦理学说有着整个近现代哲学中都极为罕见的潜力,尚待抉发。
注 释:
①《法哲学原理》第151节正文曾将伦理实体界定为“作为一个世界而活生生的和现成的精神”。黑格尔在另一处也说过,伦理是一个世界。
②当然马克思并未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框架,他是在他自己锻造出的全新社会概念的尺度下讨论这个问题的。
③这个概念在黑格尔去世后还一直困扰学界,以致学者们在它的译名上也很犯难,现有的英译名有“ethical life”(A.Wood)、“customariness”(R.Pippin),日译名有“公の秩序又は善良の風俗”(公序良俗),中译名有“伦理”(范扬、张企泰)、“伦理法”(邓安庆)等。
④鉴于耶拿前期以及更早时期的伦理思想尚未成熟,暂不纳入本文考量之内。
⑤或简称三种形态,如果将前三种(感性、知觉、知性)统称为“意识”的话。
⑥这当然只是相对于中世纪与近代而言,细察希腊与罗马伦理形态内部则并非铁板一块。希腊人直接隶属于具体的伦理势力,而这些伦理势力相互之间很可能是对立的;罗马时代的人服从的是抽象的法权,而皇帝只是相对虚置的。
⑦这当然不意味着《逻辑学》的每一个范畴死板对应于《法哲学原理》中的一种伦理形态,而只是以前者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参照大致理解后者的各种伦理形态的相互关系,对两部著作内部结构的考察应先于对它们之间参照关系的考察。
⑧菲韦克对逻辑学的概述跳跃闪烁,将很多不同层面混同起来,比如“认识理念”(die Idee des Erkennens)在黑格尔那里是涵括了真的理念与善的理念的,而非如菲韦克所说的与善的理念并列;目的论与生命也不在一个层面,菲韦克却将二者并列;而概念论第三部分虽然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理念),却不可与菲韦克所谓的“那条路”并提,因为后者其实是整个概念论。
⑨在菲韦克笔下,道德、市民社会、宗教、艺术和科学都被还原为公民的权利:良心自由,宽容,宗教自由,艺术和科学的自由。
⑩第142节正文,第144节正文与补充,第145节正文与补充,第146节正文,第147节正文,第148节正文,第149节正文,第151节正文与补充,第152节正文,第153节正文,第154节正文,第155节笺注,第156节正文与补充,第157节正文与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