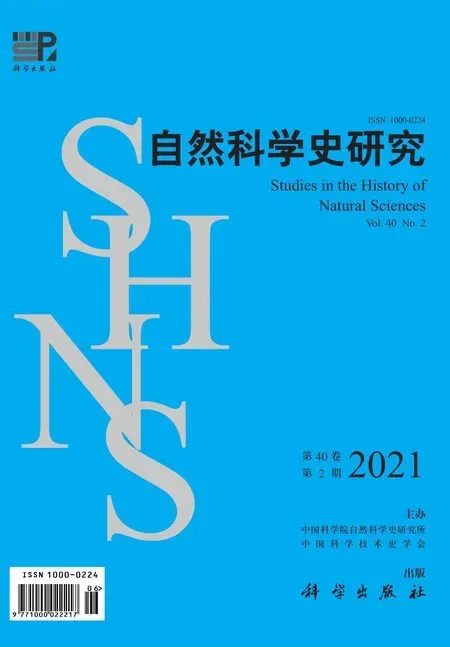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东北地区的考察
2021-10-13范丽媛
范丽媛 韩 琦
(1.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太原 030006; 2.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杭州 310058)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对外开放,在丰富自然资源的吸引下,各国传教士、学者、商人等纷纷来华进行动植物的调查和采集。他们将收集到的大量标本引入西方,相关研究扩充了博物学知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我国博物学等学科的发展。近年来,西方来华博物学家的考察活动逐渐受到科学史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多集中于18至19世纪(1)有从殖民主义的视角讨论博物学与帝国权力关系,参见文献[1];有从文化史视野下考察博物学的文化遭遇,参见文献[2]。,但对20世纪以来西人在中国的博物学考察关注较少。这一时期众多外国考察者中,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则比较特殊。1885年,他出生于山西太原,幼年在中国度过,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能讲流利的中文;青年时期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此后在中国生活工作五十余年。在华期间,他进行了多次生物考察,足迹遍布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南方的上海和福建等地。其中,尤以对东北地区的考察影响较大,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汉学家林仰山(Frederick Sequier Drake,1892—1974)曾评价他是20世纪初在中国生活的西人中“最著名、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9],144页)。
目前学界对苏柯仁的生平事迹已有较为清晰的论述(2)李天纲对苏柯仁有过简要介绍,参见文献 [4]、[5]。戴丽娟在其《展示自然——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1874—1952)》中对苏柯仁的生平有所论及,参见文献 [6]。罗桂环对苏柯仁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一些考察活动做有简要说明,参见文献 [7],246—249页。西文对苏柯仁的相关研究参见文献 [8]、[9]、[11]、[28]。,然而关于他成为博物学家的缘由、为何来华考察缺乏细致梳理,对他在华的博物学考察经历、相关研究成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生物学发展起到的作用均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本文依据苏柯仁的自传、相关研究著述(3)1923年,苏柯仁在上海创办了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27年杂志改名为The China Journal,并开始在英文名下附中文名为《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36年改中文名为《中国杂志》。1941年11月该杂志停刊,共计出版35卷。201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将该杂志全文影印出版,书名统一为《中国杂志》,参见文献[3]。李天纲为本书撰写了导论,该内容同时发表于《上海文化》,参见文献[4]、[5]。,并结合时人及后人评价,首先对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博物学的道路,为何选择来华考察,又是如何成为职业的博物学家等问题逐一进行解答。其次以他在东北地区的考察为例,分析考察原因,还原考察路线,并探讨相关考察成果对中国生物学发展的影响,以期丰富20世纪以来西人在中国的博物学考察的相关研究。
1 苏柯仁的成长背景与博物学机缘
苏柯仁出身于博物学世家,其高祖詹姆斯·索尔比(James Sowerby,1757—1822)和曾祖詹姆斯·德·卡尔·索尔比(James De Carle Sowerby,1787—1871)都是英国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高祖是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是皇家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著有《英国植物学》(EnglishBotany)、《英国矿物贝类学》(MineralConchologyofGreatBritain)等。这两本专著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被广泛使用([8],9页),后者为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很多研究基础([9],144页)。其曾祖也是著名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创办了英国皇家植物学会(Royal Botanic Society)和学会植物园(4)该植物园位于伦敦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内,约18英亩。,并担任第一任秘书长和园长。面对这些优秀祖辈,苏柯仁引以为豪地写道:“显然从我的祖先詹姆斯(高祖)和植物学家詹姆斯·德·卡尔(曾祖)那里继承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特殊才能。”([10],80页)
相较于苏柯仁的祖辈,其外祖父(Isaac Clayton)对他有更直接的影响(5)1890年苏柯仁的父亲休假,全家人一起回到英国,在他母亲(Louisa Clayton Sowerby)的家乡梅登黑德(Maidenhead)和其外祖父一起生活了两年。在《苏柯仁传奇》(The Sowerby Saga)中,苏柯仁评价其外祖父是“一位天生的博物学家,有许多好的博物学著作”。参见文献[10],67页。。他小时候最大的兴趣是观察外祖父小箱子里的动物毛皮、标本、小型哺乳动物,包括鸟类和鱼类等。从外祖父那里,苏柯仁阅读了大量优秀的博物学书籍,这些书籍是他快乐的源泉([10],67页)。可以说,他对自然的热爱及日后成为博物学家,与其外祖父不无关系。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是他(苏柯仁外祖父)让我开始了后来成为我生活中主要职业(博物学家)的事情。”([10],67页)
苏柯仁的父亲苏道味(Arthur Sowerby,1857—1934)是英国浸礼会的一名传教士。1881年来华,在中国传教近40年,晚年曾担任袁世凯之子的家庭教师([11],123页)。苏柯仁在家中排行第二,其童年基本是在太原度过的,那里多山的环境为他提供了很好的远足场地。他常常去山中调查各种花卉和动物,也“常常背着步枪在平原上骑马,猎取大鸨、大雁、野兔、鹌鹑甚至是鹧鸪,或者上山去捉斑鸠和野鸡。”([10],101页)在这里与自然的多次亲近使他领略到了大自然的财富,也是其作为“博物学家人生的开始”([10],76页)。苏柯仁成长在传教士的大家庭中,除父亲之外,他的大多数兄弟姐妹也从事传教事业。虽然他没有走上传教的道路,但是家庭氛围使他不仅勇于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情,也塑造了其友爱的性格和正直的品质。
除了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苏柯仁的教育背景也为其博物学生涯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期间,他除了1897年在山东芝罘学堂学习一年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原的家中学习,由家庭教师和父亲进行辅导,主要学习拉丁语、法语、希腊语、历史以及数学。1899年,14岁的苏柯仁随家人回到英国,在梅登黑德现代学校(Maidenhead Modern School)学习了化学和物理。此外,还在梅登黑德艺术学校(Maidenhead Art School)训练绘画。据其自传所述,在艺术学校的培训使他“决定受训成为一名艺术家”([10],79页),这是苏柯仁首次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规划。1901年,苏柯仁全家从梅登黑德搬到英格兰西部的巴斯,同年他进入巴斯艺术和技术学校(Bath Art and Technical School)学习艺术。在此期间,他选修了植物学课程,在老师的带领下收集和观察了许多动植物。此时,艺术课程对苏柯仁的吸引力已经减弱,而植物学课程的学习则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成为他将来从事博物学职业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1904年,苏柯仁结束了在艺术学校的学习,进入布里斯托大学,他并未继续学习艺术,而是选择了理学课程,所学内容主要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和有机化学。在他看来这些科目都十分有趣,在学习上他也十分努力刻苦。然而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大学期间,他的未婚妻改变主意,并告诉他不会嫁给他。情感上的挫折使苏柯仁无心继续学习,他放弃高等教育,先是前往加拿大进行了短暂的冒险,之后因父亲来信的提议,他决定回到中国与家人团聚。在他放弃学业,做出回到中国的选择后,便开始憧憬在山西西部的野地里进行狩猎的场景,为此他在启程前为自己购买了一支步枪、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把猎刀。他认为“这些都是我未来探险所需的装备”([10],97页),由此正式开启了他的博物学之路。
虽然苏柯仁没有完成学业,但他日后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反而是感激当初的决定([10],93页),而近一年的学习和积累也为他今后的博物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苏柯仁选择博物探险,除成长环境的影响外,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19世纪以来,英国博物学的发展,与国家殖民扩张、贸易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3页)无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利益的驱使,抑或是私人兴趣,人们对到国外探险和考察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憧憬。而前来中国,不仅因为他的家人生活在这里,也因中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自然环境,给他带来许多美好的记忆。
1905年,苏柯仁回到太原与家人团聚。不久后,他听闻传教医师叶守真(Eben Henry Edwards,1855—1945)(6)叶守真,医学士,外科学硕士,英国内地会传教医师。1882年来华布道,初驻安徽安庆,两年以后来到山西太原。曾带领重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的斯科菲尔德纪念医院,该医院于1906年建成,改称耶稣教施医院。想在医院旁的大厅创建自然博物馆([10],101页)。他热情地提供了帮助,猎取鸟类和哺乳动物,将其制作成标本,置于玻璃展览柜中,同时还配置了动物栖息地的自然环境。这些技能均得益于其外祖父(7)从苏柯仁传记中的记载得知,其外祖父早期出于兴趣爱好开始从事动物标本的制作,后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参见文献 [10],67页。。在他看来,这种形式的标本制作及展出是中国首例([10],101页)。几个月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时,天津英华学院的校长赫立德(Samuel Lavington Hart,1858—?)(8)赫立德,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获文科硕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892年来华,在天津等地布道。1902年创办天津新学书院并担任校长,后又主持创办了华北博物院。正计划组建一个与该学院有关的自然博物馆(华北博物院,Anglo-Chinese School Museum),听闻此事后,写信邀请苏柯仁担任该校的自然老师并管理该博物馆。
1906年,苏柯仁正式成为天津英华学院的老师,教授英语、地理、算术、生物、绘画和写作等课程。第一学期寒假,他前往太原西部的荒山区和森林区探险,为博物馆搜集动物标本。这次探险是他“作为一名博物学家的职业生涯中,一个新的、有趣阶段的开始”。他将收集到的大量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制成标本,陈列在博物馆中。1907年,该博物馆完工,与在太原的情形一样,展出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0],106页)
1907年秋,苏柯仁受邀加入贝德福德伯爵东亚探险队(Duke of Bedford’s Exploration in Eastern Asia),前往华北地区进行考察,为大英博物馆收集标本。通过这次考察,苏柯仁进一步精进了捕捉和保管动物标本的技巧。此次探险结束后,他又接受了纽约探险家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的邀请,担任其探险队的博物学家。1908—1909年,对华北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
由于苏柯仁对探索自然的喜爱和热情,以及在考察过程中的优秀表现,克拉克决定雇用他继续在中国考察和收集标本,并将收集的动物标本送往美国国家博物馆(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如此一来,与被政府或者博物馆等其他机构直接雇用不同,私人雇佣使他在中国的考察更具灵活性,可以自己决定想要考察的地点和时间。克拉克曾表示“你(苏柯仁)可以从我的库存中拿走必要的设备,也可以从商店中购买你所需要的东西,去你喜欢的地方,并随时告诉我你在做什么。”([10],136页)不仅如此,克拉克还资助他到英国学习。1910年5月,苏柯仁前往英国,期间他加入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并接受了学会安排的天文和地质等相关课程的学习。此外,还拜访了在大英博物馆哺乳动物部门工作的托马斯(Oldfield Thomas,1858—1929),并多次与美国国家博物馆哺乳动物系主任米勒(Gerrit S. Miller,1869—1956)(9)米勒,1869年出生于纽约彼得伯勒,美国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189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美国农业部任职,1898年担任美国国家博物馆哺乳动物部门的负责人,1909—1940年担任史密森学会的生物学秘书。进行学术交流,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几次考察探险经历,让苏柯仁积累了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的职业经验。而在英国近一年的学习则使他进一步强化了博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建立了有利于其博物学实践的关系网络。此后,他又在中国不同地区进行了多次生物考察,将收集到的部分动物标本寄往美国国家博物馆,部分则留在中国进行研究和展览,这些考察活动有效促进了中西方的生物学发展。
2 苏柯仁在东北地区的博物学考察
2.1 考察背景
自17世纪以来,博物学的快速发展便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至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对自然的不断“征服”仍然是西方国家彰显其实力的重要方面,而将“自然”通过博览会、博物馆等形式向公众展示,也是在提醒“侵略者”,发现“新的自然”依旧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一时间,博物馆在西方国家进行了大量扩建,博物学也在博物馆的引领下,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学史家法伯(Paul Lawrance Farber)表示“没有什么比19世纪末自然博物馆的构建和扩张更能显示博物学的荣耀了”([15],112页)。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博物馆不再限于科学家研究使用,而是随着向公众的大量开放,增添了教育、科普等重要角色。这使博物学在大众中流行起来,也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各国对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考察活动。
20世纪初,各国来华考察更加活跃,受雇于博物馆等机构下的来华探险者数量与日增多,他们为所在机构收集各种生物标本。苏柯仁虽是直接雇用于克拉克,但因克拉克是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赞助人,所以他也间接为史密森学会下的美国国家博物馆服务。他与该博物馆的工作关系从加入克拉克探险队开始直到1954年去世,历时近50年([8],70页)。
在此期间,苏柯仁与美国国家博物馆形成“共生关系”,彼此满足相互需求:他向博物馆提供了大量动物标本,丰富且扩大了博物馆的动物收藏;而该机构则为他在华考察提供了相应保障。例如向他提供了“收集所需的大量枪支和数万发弹药的许可证”([8],68页),为其开具介绍信,说明他在中国管辖土地上旅行的目的,以便利其相关考察工作。(10)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开放,外人得以在华传教、通商和旅行,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政治局面。1858年,我国被迫与西方多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与英国签订的该条约中,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参见文献[39],第190页。此外,由于中国在当时还不具备鉴定相关动植物标本的条件,因此只有通过与这样具有一定声望,且有大型博物馆的机构建立联系,才能正式和准确地鉴定所收集到的标本,确认其发现并使之合法化。不仅如此,通过博物馆的有关反馈也使他能够知道自己在工作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与成就。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考察的探险者大为增加,尽管苏柯仁致力于将科学作为其理想追求,但面对同行间的竞争,他也在寻求学术界的认可。因此发现新物种取得优先权,是为自己在该领域内奠定地位的有效手段。如果说在贝德福德东亚探险队以及克拉克探险队的两次经历使他成为一名职业的博物学家,那么紧接其后对东北地区的博物学考察和研究,则使其学术工作得到了学界认可,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
2.2 东北之旅
中国东北地区动植物群极为丰富,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木材储备充足,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这里长期受到西方探险家的关注,但在清王朝的控制下,该地区对外封闭,阻碍了外界对其探索考察的脚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大量开放,西方各国加速扩张,对我国多地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生物学考察,其中也包括东北地区。
较早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探险考察”的多为俄国博物学者和军人(11)清代俄国在黑龙江两岸的大片地区进行了扩张,拥有政治势力,禁止旅行家前去考察(实际只禁止了英国籍旅行家)。直到1914年,苏柯仁到俄国管制下的地方(阿穆尔河流域一带)考察,依然遇到了怀疑和不友善的对待,受到官厅的阻止。参见文献[18],第II页。。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地处北部的沙俄帝国为了商业利益和殖民扩张南下至我国东北地区,“这种扩张极大地推动了他们在华的地理考察和资源普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7],166页),为其侵占领土打下基础。1842年,冯·米登道夫(Alexander von Middendoff, 1815—1894)经俄国科学院委派,对黑龙江上游及黑龙江支流结雅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进行过博物学考察和标本收集。1854—1856年,施伦克(Leopold von Schrenck,1826—1849)(12)施伦克是俄罗斯著名的动物学家、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对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河流域等地区的生物、地质、气象、人文等情况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不少德裔俄国人也对东北地区进行了考察,例如马克西姆维奇(Carl Johann Maximowicz,1827—1891),于1854年至1859年期间,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和植物标本的收集。还有马克(Richard Maack,1825—1886)、拉德(Gustav Radde,1831—1903)等,同样在黑龙江一带进行了考察研究。(13)有关俄国人在东北地区的考察活动,参见文献 [7],第167—173页。
相较于俄国,当时欧美其他国家对东北地区考察较少。其中,最早对东北地区进行考察的英国人是詹姆斯(Henry Evan Murchison James,1846—1923)及其同伴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14)荣赫鹏,1863年生于英属印度(今巴基斯坦)穆里的一个英国军人家庭,是英国陆军军官、探险家、作家及外交家。1886—1887年,荣赫鹏到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方进行考察,之后加入皇家地理学会。1919—1922年,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和富尔福德(Harry English Fulford,1859—1929)。1886年,他们游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并且参观了长白山。詹姆斯在1887年出版了《长白山,或满洲里之旅》(TheLongWhiteMountain,or,AJourneyinManchuria)一书,此书成为早期英美国家了解该地情况的主要来源。
1911年,苏柯仁回到中国,他注意到东北地区拥有大片壮丽的森林,这里地形多样,物产富足,是“博物学家的天堂,大自然的花园”[16]。虽然对该地区的探索已有不少,但他认为仍存在着“欧洲人从未探索过、甚至没有去过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的森林地区”([17],IX页),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东北地区的探索更是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地区作进一步考察,以丰富和完善该地区的动物群研究。
1913年,苏柯仁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考察,至1915年,共考察4次(图1),历时约3个月:

图1 苏柯仁东北考察示意图(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国家自然资源部)截取地图加以标示)
(1)1913年春末夏初,从天津出发到达开原,由开原进入吉林省。考察了吉林西部的森林地区和上松花江盆地,包括榆树岔(位于吉林朝阳城东南20到35英里的森林地带,其中朝阳城位于吉林-沈阳的边界上,距沈阳东北150英里处)、烟筒砬子(在靠近辉发河和松花江交汇处,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南100英里处)等地。
(2)1914春天,再次从天津出发,走水路,途经旅顺港和大连港,到达丹东,乘船从鸭绿江下游而上,最后沿其支流浑江而行,考察了周边地域,包括两岸距离河口120、150及180英里处的一些地方,此外还对邻国朝鲜进行了简单探察。
(3)1914年秋末初冬,前往吉林北部的森林进行生物考察。主要集中于黑龙江一面坡周围的森林区(位于哈尔滨及宁古塔间的中东铁路附近)。
(4)1915年夏末秋初,对松花江的下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包括三姓县(今称依兰县)往下约120英里,距离黑龙江省和阿穆尔河汇合处约30英里;还有靠近松花江吉林河畔的富锦县附近。(15)罗桂环亦对苏柯仁此次的考察路线进行了简要介绍,参见文献[7],247—248页。([18],III- IV页;[27],75- 85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苏柯仁最后一次考察中,当他到达哈尔滨后,最先沿着松花江到达了与阿穆尔河的交汇处,想要探索阿穆尔河沿岸周围地区,但受俄罗斯政局影响(16)据苏柯仁描述,当时有大量奥地利及德国囚犯逃出俄罗斯阿穆尔省的拘留营,对当地居民构成威胁,而这些逃犯极有可能会伪装成考察的博物学家,进入中国境内,再由此伪造护照成为英国或法国国民。因此,当时在俄罗斯阿穆尔河一带禁止携带步枪、散弹枪及照相机,且每位到达此处的人都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苏柯仁也不例外,当他到达附近时被认作是间谍被捕,最终通过与哈尔滨领事处取得联系,经身份证明后才得以获释。参见文献[27],第84—85页。不得不放弃该计划。
从上述考察行程可以看出,苏柯仁的采集地点从南到北,他表示这些地方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或野外收藏家进行过探索,均为生物学上未经探索之地。([18],III、IV页) 在这几次考察中,他研究动物的出没地和习性,观察鸟类迁徙,同时收集各种不同物种的标本。此外,还考察了动物群,并与之前在华北、蒙古南部所考察的动物群进行了比较。他将收集到的标本寄往美国国家博物馆,由不同专家进行鉴定。其中主要有米勒、霍利斯特(Ned Hollister, 1876—1924)帮助鉴定了哺乳动物;雷莱(J. H. Riley,1873—1941)、里士满(C. W. Richmond,1868—1932)对鸟类进行了鉴定;宾尔(Barton Appler Bean,1860—1947)、斯特尼格(Leonhard Hess Stejneger,1851—1943)、考德尔(Andrew Nelson Caudell,1872—1936)等动物学家分别对收集到的鱼类、爬行类以及昆虫类的标本进行了鉴定。([17],II- III页)
3 考察成果及影响
3.1 发现新物种
在东北地区的考察中,苏柯仁发现的新物种并不多。其中有两种新的哺乳类动物,分别为新种姬鼠和新种蝙蝠。(17)据罗桂环所述,苏柯仁所获得的新种姬鼠,后来未被认可。参见文献 [7],第248页。姬鼠为其1913年7月6日在吉林省获取,由米勒进行鉴定,被命名为Apodemuspraetor。米勒撰写的《东亚的两种新鼠类》(Two New Murine Rodents from Eastern Asia)一文对此进行了介绍,发表在史密森学会学报上[19]。新种蝙蝠于1914年秋在吉林北部的森林中发现,标本送往美国国家博物馆,经米勒初步鉴定后,苏柯仁又做了进一步检查,将此命名为Murinahuttonifuscus,并于1922年在美国的哺乳动物学杂志上发表《满洲的新种蝙蝠》(On a New Bat from Manchuria)[20]一文,对该新种蝙蝠做了描述说明。
此外,他还发现了两种新的鱼类,均在鸭绿江捕获。其中一种是小型鰕虎鱼,由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金斯堡(Isaac Ginsburg,1886—1975)鉴定,用苏柯仁的名字命名为Rhinogobiussowerbyi。[21]另一种为鲶鱼,由他和宾尔一起做了鉴定,并将其命名为Pseudobagrusemarginatus。1921年,苏柯仁撰写《满洲南部鸭绿江中的新种鲶鱼》(On a New Silurid Fish from the Yalu River,South Manchuria)[22]一文,对新种鲶鱼做了描述说明,发表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学报上。
3.2 东北地区的动物地理区划
苏柯仁此次的考察研究,除收集动物标本和发现新物种外,还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对“满洲”地区的动物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满洲”地区的动物亚区并非如前人斯克莱特(Philip Lutley Sclater,1829—1913)(18)斯克莱特,英国动物学家、鸟类学家。1901年获取牛津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确定了世界主要的动物地理区域,1860—1902年担任伦敦动物学学会秘书。所说,属于古北界的一个独特动物亚区,事实上是由许多其他动物亚区汇集而成,所包含的动物均属于不同的动物亚区。([18],XIV页)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苏柯仁所谓的“满洲”地区,并非只是当时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大省,俄罗斯的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也包括在内。他指出该地区“西面与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蒙古东部和中国直隶省(河北)接壤;南面边界为辽东湾、朝鲜湾以及渤海湾;北面与阿穆尔盆地北部边界相连;东面是鞑靼海峡和日本海;东南面是朝鲜。([17],V页)苏柯仁的这种划分,或许是受到了他所参考的相关著作的影响。(19)苏柯仁在其相关研究中主要参考了施伦克的《1854—1856在阿穆尔地区的旅行和研究》(Reisen und Forschungen im Amurland,1854—1856)、斯特尼格(Leonhard Stejneger,1851—1943)的《日本及邻近地区爬虫学》(Herpetology of Japan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施密特(Peter Schmidt,1872—1949)的《俄罗斯帝国东海的鱼类》(Pisces of the Eastern Seas of the Russian Empire)、伯格(L.S.Berg,1876—1950)的《阿穆尔鱼类学》(Ichthyologia Amurensis)以及科马洛夫(V.L.Kamarov,1869—1945)的《满洲植物志》(Flora Manchuria)这五大著作,奠定了其研究基础。参见文献 [18],第VI—VII页。这些书籍的作者多为俄罗斯动物学家,考察之处多是中俄边境一带和日本周围,其中主要包括了阿穆尔地区、滨海边疆区、日本海等地区。
苏柯仁通过举例分析(20)苏柯仁在研究中列举大量案例,例如介绍说明了鸟类(榛鸡、雀鸟、海鸥等)、鱼类(鲤鱼、鱥鱼、淡水鳕鱼等)、冷血脊椎动物(胎生蜥蜴、蝰蛇、林蛙等)等诸多在“满洲”发现的物种与欧洲物种相联系,分布范围涉及“满洲”、西伯利亚、欧洲。参见文献 [18],第XI—XIV页。,表明“满洲”动物群“与中国、西伯利亚、北美和日本的野生动物群有关”([18],XIV页),这一地区不存在所谓的“满洲”动物亚区,所包含的动物应被分配到不同的相邻亚区。此外,他还表示在处理“满洲”地区的动物时需注意这些亚区,并进一步做了详细总结:
(1)北极动物亚区:西伯利亚的北部和东北部海岸及冻土地带。其中鸟类有夏季飞来的候鸟、多种野禽,以及若干燕雀类;哺乳动物类有:北极狐,北极熊、海象、海豹及一些鲸类。
(2)西伯利亚动物亚区:西伯利亚的中部及南部、蒙古北部、阿穆尔盆地、滨海边疆州,黑龙江,吉林,乌苏里河流域,朝鲜东北部。主要动物有:马鹿、驼鹿(或称狍)、麝鹿、麋鹿、驯鹿、野猪、棕熊、狼獾、白鼬、狼、狐狸、水田鼠、野兔、榛鸡、黑公鸡、黑啄木鸟、西伯利亚松鸦、蝰蛇、胎生蜥蜴、林蛙等。
(3)蒙古动物亚区:戈壁沙漠、蒙古东部、满洲西部、鄂尔多斯沙漠、新疆以及中亚沙漠。主要动物包括野驴、野马、羚羊、兔狲、沙狐、狼、三趾跳鼠、沙漠仓鼠(Phodopus)、双峰驼、棕蛇(Elaphedione)、沙蜥(Phrynocephalusfrontalis)、沙鸡、蒙古云雀等动物。
(4)华北动物亚区:南蒙古草地、甘肃、陕西北部、山西、河南、直隶(河北)、山东、奉天(辽宁)、辽河盆地,以及满洲的西南部和南部,可能还包括朝鲜西北部。代表动物有:马鹿(Cervusmandarinus)、豹(Felisfontanieri)、山羊、栗鼠(Sciurotamiasdavidianus)、鼹鼠(Myospalax)、仓鼠(Cricetulus)、鼠兔(Ochotona)、花背蟾蜍(Buforaddei)、多种鸟及爬虫。
(5)西藏动物亚区:西藏及中国西部高原。
(6)日本动物亚区:库页岛、千岛群岛、日本岛屿,可能包括朝鲜南部。([18],XVI- XX页)
总体而言,苏柯仁认为,对地理、地貌、植被及气候的准确了解是完成动物地理区划的关键。但动物地理区划是人为的,得以正确划分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某些物种在受到环境压力和其他物种施压的情况下,被迫跨越自然界线,进入并不适宜的区域,这一情形加大了博物学家正确确定动物区系的困难程度。另外,他还表示,这些动物地理区划只是暂时的,并非固定不变,且对区域边界的界定也不能十分明确具体。([18],XVI—XVII、XX页)
苏柯仁通过实地考察及结合前人研究,除了对动物地理区划做出上述整体性分析外,还在具体介绍各类动物的过程中,对它们所属地理区域进行了简要说明。他对东北地区动物地理分布的研究论述大多记载于其系列著作《博物学家在满洲》中。极具意义的是,这一系列著作成为我国动物地理研究初期的工作成果(21)关于动物地理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初,中国国内学者还较少注意,至四五十年代左右才逐渐被重视起来。1956年,为配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全国自然区划”工作计划,动物地理区划研究的相关工作正式开始。郑作新和张荣祖等学者负责工作成果的整理撰写,于195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与中国昆虫地理区划(初稿)》一书,参见文献[23]。,即《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与中国昆虫地理区划(初稿)》一书[23]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是,因为苏柯仁并未对东北地区进行完整考察,其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论述说明是在参考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缺少考证。所以,该书在参考其著作的过程中,对他的一些结论提出了质疑。
例如,书中指出“据苏柯仁,在黑龙江流域还有北极狐(Vulpeslagopus)、雪羊(Oviscanadensisnivicola)等,但恐不可靠”([23],5页)。经作者查阅发现,苏柯仁对北极狐的介绍说明并不多,他曾写道:“施伦克记录了在阿穆尔(Amur)发现的白狐或北极狐”,“它(北极狐)的范围似乎延伸到整个西伯利亚北部,向东延伸到阿拉斯加,向北到达北极点十度以内。很难说它向南延伸了多远,但施伦克在阿穆尔的记录提供了一些线索”([18],44页)。雪羊与北极狐情况类似,对雪羊所属地区的说明同样来自施伦克的考察研究,他写道:“施伦克记录了一只野羊……,它来自阿穆尔地区,无疑为雪羊(O.nivicola)”(22)苏柯仁对雪羊的研究论述,参见文献 [18],第121—123页。([18],121页)。苏柯仁并未在考察中亲自发现北极狐和雪羊,同时也没有明确表明北极狐、雪羊出现在黑龙江或是阿穆尔河一带。另外,他所提到的关于施伦克在Amur发现了北极狐和雪羊,其中的“Amur”很可能指阿穆尔地区,并不一定特指阿穆尔河流域。
综上来看,苏柯仁只在东北局部地区进行了考察,对这一地区动物地理分布研究参考了大量前人著作,因此其研究成果中不少结论的正确性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但是,他对未经考察的生物、不能确定的结论,并不会给出肯定回答,可见他对科研认真及严谨的态度。此外,中国学者在参阅其成果过程中,偶尔会有翻译不准的情况,进而导致对其中一些内容有所误解。总体而言,苏柯仁的研究成果是当时我国动物区划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对我国该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有力促进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
3.3 东北地区的自然志
1919年,受第一次大战影响,苏柯仁回到英国。同年5月26日,他在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结合地图、照片等资料,对东北地区的考察做了演讲,介绍了该地的地理环境、考察经历以及人文、政治等有关内容。
演讲结束后,荣赫鹏、卡特利(Oswald Cattley,1850—1922)、巴德利(John Frederick Baddeley,1854—1940)等人发表评论,对他的演讲内容表示肯定和赞扬。学会会长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1843—1929)(23)霍尔迪奇,英国地理学家。曾于1902年参与了由阿根廷和智利政府发起的调查安第斯山脉边界的科迪莱拉山系一事,以确定安第斯山脉的边界。1917—1919年担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此外,还于1917—1918年出任英国地理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主席。称这次演讲是该学会在“本季度听到的最好的演讲之一”([27],92页),并认为他“是一位在科学界享有盛誉的博物学家”。([27],89页)由此可见,苏柯仁对东北地区的考察在英国地理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4)此次演讲的内容被整理成《满洲的探险》(The Exploration of Manchuria)一文,于8月刊登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上。参见文献 [27],73—92页。
苏柯仁发现,东北地区的科学考察受到当时帝国殖民扩张版图的影响,相关的博物学著作几乎都是用俄语或德语出版,而用英文出版的相对较少。不仅如此,在已有的出版物中,大多面向的是“生物学家的一个有限圈子”,并非“大众中对科学进步和发现感兴趣的人们”([18],II页)。据此,他希望出版一部对博物学家的研究有所帮助,同时也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英文书籍。因此,在英国期间,苏柯仁整理了东北考察时的笔记资料,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博物学家在满洲》([28],32页),1920年在英国率先出版。其远亲理查·雷恩·索尔比(Richard Raine Sowerby,生卒年不详)(25)苏柯仁晚年定居美国华盛顿期间曾与其进行了大量通信。他依据《苏柯仁传奇》(The Sowerby Saga)前三卷内容以及信件中的有关信息写作了《中国的苏柯仁》(Sowerby of China: Arthur De Carle Sowerby)一书,于1956年出版。参见文献 [28]。曾评价说:“这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籍”,“在(英国)科学界很受欢迎”([28],32页)。1921年,苏柯仁回到上海,随之其五卷本《博物学家在满洲》相继由天津出版社再版。
著作第一卷主要介绍了其四次生物考察和收集过程中的个人经历、考察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以及风土人情等。后四卷则分别针对东北地区的哺乳类、鸟类、鱼类和爬行类、昆虫等种类的动物进行了描述说明。其中,苏柯仁对哺乳类和鸟类动物关注颇多,共记录描述了113种哺乳动物和458种鸟类。除动物外,在最后一卷他还对“满洲”植物群做了简要论述。
书中收录的动植物不仅是其考察所收集的,还结合了他人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合和总结,较为全面地对东北地区(26)还包括俄罗斯的阿穆尔省和滨海边疆区在内。的动植物群进行了概述。例如,针对鸟类部分,苏柯仁主要利用雷莱所列的一份鸟类名单,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结合不同鸟类的习性等特征,对458种鸟类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参照和遵循权威鸟类学者哈特尔特(Ernst Hartert,1859—1933)的著作《古北界动物区系中的鸟类》(DieVögelderpaläarktischenFauna),采取通俗易懂的名称,给出了新的鸟类学名。之后,万卓志(G. D. Wilder,1869—1946)(27)万卓志,1894年来华,在直隶通州传教。1910年前往北京,担任京都汇文大学堂神科教习。1925年北京博物学会成立,被选为该会的首任会长。他长期在中国开展鸟类研究,曾与胡本德合著《中国东北部的鸟类》(Birds of Northeastern China)一书,由北京博物研究所出版。参见文献 [29]。和胡本德(H. W. Hubbard,1887—1975)两人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杂志》上发表了《直隶鸟类名录》[30]一文,对东亚鸟类也做了新的命名。苏柯仁发现,其中与他所论述不一致的命名共计126个。对此,他在书中进行了补充修订。他表示,在这些新的鸟类命名被哈特尔特这样的权威鸟类学家采用之前,决定先单独将不一致的名称列出,以供中国鸟类学的研究者参考。([25],XV页)
从当时各种新闻报道来看,该书在中国再版后,很快受到当时相关学者和普通大众的欢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报刊《自然界》翻译并转载了这部著作中的部分内容[31- 33];《中国杂志》刊载了该著作各卷书评,其中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1862—1931)评价著作第一卷,“旨在以一种十分受欢迎,且又十分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满洲地区的自然历史”[34],亦有评价表示该书“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生物学家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35],“这几卷书不仅阅读有趣,而且是所考察地区(东北)的权威参考著作”[36]。
此外,苏柯仁在《字林西报》、《中国杂志》等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与此次考察有关的独立文章,如《博物学家在满洲》、《朴实的满洲精神》、《满洲》等[16,37- 38],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可见,苏柯仁对东北地区的考察以及研究成果,不仅增强了英文世界和中国对于东北地区自然情况的进一步认识,也显示了20世纪初博物学更加面向大众的发展特征。
4 结 语
苏柯仁迈入博物学领域绝非偶然。首先,来自家族科学研究的传统以及开放的成长环境,使其从小对自然便有着无限热爱与向往。其次,19世纪末西方博物学探险的热潮,以及幼时对中国丰富自然资源和多样自然环境的美好记忆,使他最终踏上了前往中国进行博物考察的道路。他参与贝德福德伯爵东亚探险队和克拉克探险队在华的两次博物学考察,则为其博物学的考察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博物馆的扩建以及向大众的大量开放,博物学在大众中普遍流行起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掀起了西人来华探险考察的高潮。苏柯仁在与克拉克探险队的考察结束后,便直接受雇于克拉克。此后,他在中国的考察因独特的雇佣形式,不仅灵活性较高,同时也享有国际机构提供的考察及研究便利,并与美国国家博物馆之间形成了长期互利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柯仁在1913—1915年期间,对当时欧美国家探索较少的东北地区进行了考察,并将成果用英文进行发表,使其成果得到了英国学界的认可,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苏柯仁这次考察所形成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中国也进行了出版与发表。其中,尤其以他在《博物学家在满洲》系列著作中对东北地区动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研究影响较大。20世纪初,关于动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研究,中国国内学者还较少注意,直至1956年才开始了系统的动物地理区划相关工作。由于起步较晚,并不具备展开相关研究的实际条件,所以当时主要工作任务是将有关资料加以综合,整理分析,总结以往动物区系调查的成果([23],1页)。而苏柯仁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对我国动物学的发展建设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我国相关报刊还翻译与转载了其《博物学家在满洲》中的不少内容,有效地促进了东北地区博物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这些均有力推动了中国生物学的进步与发展。
作为20世纪初的著名博物学家,苏柯仁与他之前在华考察的西方博物学家相比(如谭卫道、郇和、韩伯禄、威尔逊等),考察形式和研究方式基本一致:都是在中国各地大量收集生物标本,发现新物种,以及对所发现物种进行描述、分类、命名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但在家族背景、成长环境、对中国的热爱以及私人雇用形式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苏柯仁在华博物学考察极具特征:首先,他以对自然的热爱和个人探索兴趣为其博物考察的出发点,远离了当时西方商业和政治权力驱使下的目的性考察;其次,他在中国长大,能说流利的中文,因而在考察过程中占有很大优势;再次,他的考察较具灵活性,可结合其自身情况选择所要考察的地点。除此之外,家庭和成长环境使他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些都使苏柯仁成为西方来华博物学家的一个独特案例,对此进行考察,将有助于丰富与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西方博物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了解与认识。
致 谢感谢外审专家的宝贵修改建议。承史密森档案馆Deborah Shapiro给与的热情帮助,获取到苏柯仁的自传、有关文章等珍贵资料,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