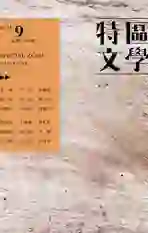诛心环
2021-09-26葛辉
一
早上起来,富传伟给母亲打电话,寒暄了几句,没想到一直顺着琐事聊下去。从隔床新到的病人到陈医生再到廉护士,接着聊了医院食堂的伙食,中间夹着杂七杂八的事情,村里的事和城里的事,然后又聊到了出租車价格,接下去聊到了开电动黑车的黑瘦老头儿。母亲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但他老伴儿不给他做饭,然后又聊到排队做放疗的人都学奸了,来得越来越早,想抢第一越来越难之类。
继父查出食道癌,查出时已是晚期,病灶长度10厘米,因离贲门太近,无法手术,医生建议保守治疗,说也许这是最好的选择。他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给当年实习时的老师和一些卫校时的同学,他们多数支持不手术,说手术不过是徒增痛苦,勉强延长存活期而已,而且,他的病情确实不适合手术。
几天前,他去医院看望继父。见陈医生,她说,这种事,摊上了就这样,好话谁都会说,但没用,不妨有话直说。目前病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层楼的病人都一样,预后都不好,对于家属来说,要嘱咐的无非两件事:一是早做准备,二是注意临终关怀。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他和母亲说想请几天假陪床,尽点孝道。母亲说没必要的,目前只是每天放疗和输液,还没做化疗,反应也不明显。每天输完液,带着他出去转转,在外面吃晚饭,回来和同楼层的病友闲聊天,是个闲人的活儿。
“还不是时候。”母亲那时说,“到时候,有你应该干的事儿,目前还是我来吧,你还是忙你的。”
就是借了这句话,他回到徐城,接着准备手上的事宜,虽然知道继父身体凶险的情况,但仍然装作不知。须知人对于未知的恐惧总是习惯自我欺骗,他有时候会想,一切可能都是假的,也许会有什么转机,医院也不是完全不会出错的,何况医生还说,或许有一丝可能。
母亲在电话那边喋喋不休,终于说到继父的情况了,说他早上吃了半碗粥,到底还是开口吃饭了。
“不应该给他输脂肪乳的,医生本来说,以他的情况,可以不输,但我觉得他吃不下饭,营养跟不上,硬让医生加的。这不,换成小袋之后,就开始饿了。”
“大袋太费时间。”他说着,把电话开到免提,穿衣服。
“就是,一输就是一天,输完了天都黑了。”
“是啊。”
母亲接着说起头天饭店里的饭菜,说炸虾仁做得不好,比别处的小,又硬,像水煮花生。
他们不在医院吃晚饭,输完液,母亲会推着继父出去走走,在外面找个小饭馆。继父喜欢吃馆子里做的蒸鸡蛋糕,每次能吃一小碗,有时还能喝一点疙瘩汤。
他穿完衣服,发现母亲似乎一直在回避着一件事。
“原来30床的大爷呢?”
电话里传来风声,母亲停了一会儿,她说正在出门,要去排号了,然后去打饭。
“我叔呢?”
“他在门口抽烟。”
“烟还有吧。”
“这个你不用管。”
母亲接下来说要去领号了,然后挂掉了电话。
富传伟穿好衣服,洗脸,走到客厅里,周玲已经在厨房忙着。粥锅里冒着热气,切菜板叭叭作响,女儿富咏还未起床,但他一眼就看出来,她早就醒了,只是闭着眼装睡。
想到六十公里外的老家县城医院里,肿瘤科每天都在死人,他觉得这个小屋子里洋溢的气氛真好。
二
火车驶入隧道,车厢里迅即漆黑一片。随后,车厢顶灯打开,柔光冲淡了眼前的黑暗,视觉渐渐适应,他看到了坐在他对面的姑娘。
脚步声,过道中来去的布料摩擦声,还有不远处的人在小声地对话,像是在说天气或者牛羊。手机铃声响起,有人起身接了个电话,说话的声音很小,慢慢远去。火车轮碰撞铁轨,发出咔嗒嗒的声音,车厢晃动着,一切都很真实,但又变得魔幻。可能睡了一小会儿,所以有点恍惚,觉得一切都不现实起来。他在心里问了自己一次,这是在哪儿,要去哪儿,去干什么?
他回答自己的问题,在火车上,去徐城,去徐城大学讲课。
给学生们讲什么来着?
他伸手拍了拍膝上的包,心里踏实起来,那里面有做好的笔记,U盘里存着课件。这时他想起,课都是讲熟了的,可以说是倒背如流,甚至,最后的十分钟,留给学生们提问的时间里他们会问什么他都知道,他对此胸有成竹。
任何一件事重复地做,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
隧道很长,火车已在里面开行了至少三分钟,他只记得进入隧道之前窗外是山,山上有一簇簇的山楂树,矮矮的一团团。绿色的叶子中透出红色的果子来,很多都是野树,长在山坡上的松树中间。山沟里有些民房,蓝色或红色的铁皮瓦,上面有圆形的、红白相间的、转动的通气口。道路上有几辆拉家具的农用三轮在缓慢行走,还有一些电动车载着红红绿绿的女人,一根电线杆上不停地闪着光,火车开近了才看清,是一只不停转动的驱鸟器。
中间有一瞬间,车窗外闪过一片盆地,有大片的农田,农田间有一条小河。
火车在山间行驶,隧道穿山而过。
像是穿过大山的食道。
他觉得喉咙一阵发紧,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随手拿起水杯。手指碰到水杯时,感觉稍微有点异样,杯子的质感似乎比往常光滑了一点。在旅行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觉,这种事情也算是正常。他打开杯子,喝了一口水,想起了家事,想起母亲。然而也就是那么一个念头,因为对面的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就盯着面前的桌面一直看。
他想,或许她看到了什么,也许,桌子上有一块污渍让她想到了什么。想到这儿的时候,自己的眼睛也往桌面上瞟过去,一时间愣住了,他的双眼盯住了自己的左手,确切地说,应该是盯住了自己左手的无名指。那是一根普通的手指,很直,呈圆柱形,或许有点像圆锥,但不明显。指节若隐若现,指甲剪得很短,贴着指背,指甲根部的白色月牙儿很明显,像是一只盯着他看的眼睛。
然后是指节褶皱的皮肤,很细的纹路,像是包浆的文物。
他的眼光停在指根处,那是一枚有花纹的戒指,大得有点夸张,是银的。
他愣住了,心轻轻地往下一沉。自己平时并不戴这东西,但这次出来时心绪不宁,竟然把它给戴出来了。
不知道对面的女孩儿是不是在看着他的手指,看着这枚戒指。
纯银的戒面四周是唐草花纹,中间是方形的戒面,正中间刻的是繁体的“龙”字,花纹里嵌着一点黑色的银锈。他把右手向左手收拢过去,慢慢地抚摸着戒指,然后用右手捂住左手,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姑娘。她转过头,看着车窗。
车窗外是一片漆黑,像是夜,又比夜还黑,像是掉进了墨的海。
姑娘在把车窗当成镜子。她笑了笑,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下睫毛,把手拿开,动了动嘴唇,嘴唇嘟起来,看起来确实可爱了很多。
他的右手背一痒,低头看时,那上面立了一只蚊子,黑白相间的腿像稳定器支架样立着,透明的翅膀随着车厢的震动轻轻地抖动着,黑白相间的肚子正在上下晃动。
“有蚊子。”他说。
姑娘沒有理他,她拿出手机,正在准备自拍。
火车声突然变小,一道白光照进来,晃得他眼前一白,再恢复时,看到女孩儿收起手机,也不知道她的自拍是否成功。窗外青山绿树,蓝天白云,艳如手机或电脑图片,手上的蚊子早就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只留下一个米粒大小的包。
很痒,他用戴戒指的左手狠狠地对着右手背挠了几下。
群山之后是一片平原,阳光明媚了起来,车厢里的冷气显得可有可无。有时,会有一点微微的凉风吹过来,但来无影去无踪,大多数时间里,周身外都是黏黏腻腻的热气,有点闷。
车厢里开始弥漫开酒味儿和香肠味儿,一股黄瓜味儿飘过来,显得既格格不入,又不管不顾。人们说话的声音小了,但也不是真安静,应该是车轮碰铁轨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之前过了一处铁路桥,是在两座山之间,钢架桥,火车在桥上开了十分钟左右。从车窗向外远看下去,离地足有二三十米高,有一种离地飞行的感觉。车窗外,天很蓝,下面是一片遥远的草地,不远处有水塘,羊群像是一块块撕碎了的白吉饼。还有一些黄白花、棕红色和黑白花的牛,像是一些切碎的羊杂。
车轮碰铁轨的声音就一直这样持续,略有变化,但还是吵人。火车开行在两座山之间,声音回荡。
很快,火车冲出山谷,又上了一座桥,转过一座山时,山坡后露出金光闪闪的螺髻。然后,巨大的佛头从山后显露出来,仿佛就在眼前,盯着他看。佛像面容慈祥,气度雍容,正是大日如来佛,山那边应该有一座寺院。
父亲病后,他和陈医生在佛光寺见过面。之前觉得是碰巧,但后来他再想起来,就觉得像是冥冥之中。和这次在火车上碰到的这位姑娘一样,都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必然。
不是有人说嘛,所有的偶然,其实都是必然。
他和陈医生在寺里聊天,说了说他继父的病情。陈医生要进伽蓝殿上香,他在外面等了一会,抽了一支烟,然后掀开门帘进去,看到陈医生跪在最右的蒲团上,嘴里念念有词。心想难怪她一直不出来,也许人家和佛祖有话要说。又退出来,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然后,他进了药师殿,跪在蒲团上拜了三拜,出来时陈医生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走进大雄宝殿,在十八罗汉面前转了一圈,看着罗汉的面容,发现有一张脸酷似他的爷爷。他在那张脸前站了一会儿,久久地望着塑像,想着这张脸若是笑起来是什么模样,但想象不出。爷爷生前有时会笑,但大多数时他都是沉默的,他高兴与否,都是通过奶奶来传达。奶奶说,你爷爷高兴了,他就认为他高兴了;奶奶说你爷爷生气了,他就知道,自己有事情做错了。
罗汉像脚底下,踩着一只小老虎,它的面目也不怎么狰狞,像是一只大猫。
父亲在遥远的故乡,变成一串号码。母亲口中的父亲是个恶人,父亲的名字每次在母亲口中出现,都是和脏话连在一起的。
偶尔,他会给父亲打电话,说说家乡的事情,问一些同学的消息。他那时想,故乡啊,就只剩下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号码了。
青狮白象,文殊普贤,他在两位菩萨面前认真地拜了拜,心里念着阿弥陀佛,然后起身,在后门处瞻仰观音菩萨。出殿走出不远,就看到陈医生正在千佛塔下转圈儿。
从佛光寺出来,到修车店去取车,车还在升降机上悬着,修车师傅用卫生纸擦着手上的油污。机油如线,从车底流出,流进下面接着的有大漏斗的机油桶。
“还没完?”
“有个急活儿,耽误了。”
他对陈医生说:“这事儿闹的,不如我请你吃饭。”
陈医生点点头,说别了,不如回寺里吃素斋。
他点头说好,吃完饭我再送您回去。转过头,对修车师傅说保养完了把车开到阴凉处放着,别晒得像烤箱似的。
“医生们得了癌症怎么办?”
“我们?”陈医生看了看他说:“他们我不知道,我反正不治。”
“听好多人都在说,不插管,不开刀。”
“插管也好,开刀也好,无非是续命,可是生活质量没了,只是等死。不过,这也是个人选择问题。”
“看你对寺里很熟,常来吗?”
“常来。”
“来拜佛?”
陈医生点点头,说:“不光是拜佛,也来忏悔。”
富传伟点点头,说了一声谢谢。医生见惯生死,医学操作总不能百分百挽回人命,心生愧疚也是人之常情。
想这事的时候,火车开过那座山,佛像完全显露出来,随后又被山挡住,并没有看到佛像脚下,也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寺院。
他心想,还是会有的吧,不然,空山里建这么一座佛,还金光闪闪的,有什么意思呢?
从回忆里出来,现实在车厢里来回晃动,他按了按膝上的包,心里想着次日的公开课。讲课的事能把他从任何一种思绪里拉出来,拉到现实中,告诉他目前所处的情况。
他转头看了看身后的过道,过道空空的,只能看到几只从座椅里伸出来的脚。推小车的乘务员从车厢一头出现,穿白衣服,系紫色的围裙,戴紫色贝雷帽。
在经过他身边时,他招了招手,花了四十五元买了一份盒饭,打开,看了对面的女孩儿一眼,正好碰上她看他的目光。
“你买贵了。”她说,“我男朋友说,一会儿卖不出去的时候,二十几块就能买到。”
他点点头,说是啊,可是这会儿后悔也晚了。
他打开盒饭的塑料盖子,里面是一点米饭、一点炒青菜。像是油菜,也像是小白菜。两只鸡翅根、一点西红柿炒蛋、半只白煮鸡蛋。他看着这盘饭,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青菜,觉得味道和寺里做出来的差不多。
寺里的饭堂是止语的,不准说话,他和陈医生面对面吃饭,偶尔抬头,也只能看到她的头顶。吃完饭后,把碗筷送到后厨,自己洗净,放到架子上去。出来,他小声问陈医生,在哪儿结账?陈医生摇了摇手。他以为是说不用他花钱,就想坚持付账。陈医生把食指放到唇间小声地嘘了一声。他才明白,刚刚他忘记了止语。
走到外面,看到做飯的胖僧正在树荫下练罗汉拳,他就走过去,问吃饭在哪儿结账。胖僧收起架式,双手合十说了一句施主您请自便。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就回头接着练拳去了。
“自便是啥意思?”他问。
“就是你愿意给钱,就往功德箱里捐点,你不愿意给钱就算了。”
“那我还是不给钱了。”他说,“回头我请你吃饭就是。”
两人信步走进弥陀殿,他想到或许应该拜一拜,因为阿弥陀佛是西方接引佛,任谁以后都要碰到的。何况继父正病着。
拜完之后,他看到陈医生走到佛像前,在功德箱那儿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绿色的钞票,折了两折,扔进了功德箱,然后,直起腰,往后走在那面墙前面站住,看着墙上的一个个小牌位。
“原来就几个,稀稀落落的,现在也满了。”
她接着说:“我经常来这里看看的。”
“我捐的不是饭钱,是香火钱。”
说完,她指着其中一个牌位说:“这是我的孩子。”
三
确定这次出行后,富传伟给母亲打了电话,问继父的病情。那时一个疗程的放疗已经结束,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溃疡面不可见,部分食道弹性差,建议进流食。
母亲说,继父还好,每天能吃一小碗小米粥。近日放疗反应出现了,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坐在床上来回晃,因为这个,医生开的口服化疗药也停了。
他说,要不把这次公开课停了,毕竟这种事情,主办方应该理解。母亲说大可不必,这种病,两三个月也是他,拖个一年半载也是他。再说,确实不用照顾。他说那好,但出门之前,一定要回家看看,问母亲有什么需要的,可以给她带去。她说不用,家里什么都有,东西和钱都不缺。
“其实,你也不用回来的,怪麻烦。”
“不麻烦。”他说,“我这次出门,要去四个地方,得半个月左右……”
本想说先去看看,以免出现什么情况,将来被村里人指点,但话到嘴边,觉得不应该说。
“那你来时打电话吧。”母亲说完,和继父说话:“传伟要来。”
他在电话里听到继父的声音,不大,但能听清。
“来干嘛?别让他来。”
母亲说了什么,声音不大,没听清,随后电话被挂断了。
出发前他去看继父,他精神尚可,坐在屋子正中的沙发上看电视剧,是抗日的片子,说不上名字。
母亲说,继父喜欢看打鬼子的戏,像《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这一类的。
他坐到继父身边,问他感觉身体如何,继父说,就那样了,这回怕是完蛋了。
“村里多少人得这种病了,哪有一个好的?”
继父看了一眼富传伟,接着看电视,一边看一边说:“我心里明白着呢,这病,都不用上医院查,我自己就知道,就是这个病。”
“不是说还没确诊吗,至少,还没做胃镜,也没做活检。”
“做那玩意儿干啥?花钱又遭罪的。”
“要不,我和传强带你去济南查查,咱不住院,就看看人家有啥办法……”
继父摇手,说:“没用,白花那些钱,比咱有钱的、上北京的、上台湾的、上国外的,白瞎,都一样。”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电视画面暂停,留下一张变形狰狞的脸。
“美国那么发达,那儿的人就不死吗?”
富传伟转过头,看母亲。
“和你说了吧,劝不动,说了多少回了,就是不干。”
继父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就是命!”
说完,他又按了遥控器,电视里画面动起来,狰狞的面容笑起来。
一场战争就要打响,士兵们士气高涨、雄纠纠气昂昂,继父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就是喝酒哇。”母亲说,“就这也没耽误喝酒。”
“我告诉你!”继父几乎是咆哮着,“听着,我就是死,也是喝酒喝死的,不是病死的。”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好好好,你是喝死的。”母亲和富传伟对视一眼,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他来徐城那年二十岁,却不能确定那年和继父是不是第一次见面。他觉得小时候见过他。随着时间推移,之前记忆里的那个男人越来越不真实,渐渐被面前的这个人代替了。
打从他见到继父,他就一直喝酒,原来喝啤酒,三孔牌,中午两瓶,晚上两瓶。他来之后改喝白酒,三井小刀、二锅头、老村长、散酒……中午四两,晚上四两。他的病与喝酒不无关系,因为他喝酒很少吃菜,晚上喝酒时也不吃主食。
自从查出病,哪怕是住院期间,午饭和晚饭依然必须要喝一点,只是没有之前喝得多,一两二两的。
七岁时,父亲在铁路上班,不常回家。母亲在家养猪,那时家住在一处山坡上,是三间砖房,院子里还有一座小土房,一间半,租给了一些卖血的外地人。
有天晚上,他在家写作业,母亲和一个男人聊天,她们给他出了一道题。
“‘日’字加一筆,能写出九个字,是哪九个?”
他在纸上写出九个“日”字,每个上面加一笔。
由、甲、申、白、田、旧、目、旦。
最后一个,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这时,那个男人说:“今天这灯泡不怎么亮呢。”
母亲笑笑,说:“是呀,电压不稳呢。”
说完,母亲拍拍他的头说:“傻孩子,叔叔在提醒你呢。”
他记得,当时还是没听明白是啥意思。
于是,母亲抢过他手中的笔,在最后一个日字上加了一笔,写出了一个“电”字。
他想到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和母亲说话的男人的样子,他时常怀疑,那个人是不是面前的这个看电视的人呢?
四
“您生活一定很幸福吧,我看您一直在摸那个戒指。”
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女孩儿。她看着他,一只手拿着手机,手机屏幕亮着,另一只手按在桌面上。
“怎么看出来的?”
她把手机放到桌上,用手指理了理嘴边的头发。
“戴无名指,不是结婚戒指吗?”
他看着她,微微地笑了一笑,心说我这个岁数,大多数的人不都结婚了吗,这和幸福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多大了?”
“十六。”女孩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关掉屏幕。
“还在念书吗?”他接着问道,“在哪个学校?”
“在卫校。”
“卫校好,未来可以当医生。”他说,“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的,不管到啥时候,大夫都有饭吃。”他把手抬起来,小心地用小指挠了挠头皮。他很小心,因为头发上打了啫喱膏,必须把指甲小心地伸到头发的缝隙中。
对面的女孩儿苦笑着,说:“那么难,有几个能考上的。”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说,“卫校毕业得上大专,大专毕业要工作三年才可以考助理医师资格证,很难的。”
“那你怎么打算?”
“我考自考了,已经过了三门了。”
他点点头:“那不错。”
“实在不行就去考公务员。”她说,“我舅的战友在卫生局,是副局长。”
“那也不错。”
“可是我不愿意去,我表姐说卫生局科员太累,我要是考公务员,想考个轻松一点的岗位,就是,冷门一点儿的。我同学说,图书馆就不错。”她说完,抬了抬眼皮,飞速地瞟了他一眼,眼珠轻轻地一转,眼神闪烁起来。
“叔叔,我手机没电了,你有充电宝没有?”
“哦。”他低头拿起膝上的包,打开,翻找起来。
“我不确定带没带,平时我不怎么用充电宝的。”
她说:“我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男朋友的?”他本来就是开个玩笑,但女孩儿的表情认真起来,她说是呀,他一会儿要来接我,我告诉他我在这趟车上。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指上的戒指,他想,也许可以给这个孩子讲一讲戒指的故事。
或者,说一说别的,比如,在一千公里外的医院里,有一位女医生,让人觉得难以接近,眼神里透出一种野生动物才有的警惕。可是,一旦和她交上朋友,她就会变得很健谈。她和所有女孩子一样,都年轻过,也和一部分女孩子一样,爱过、幸福过、恨过、失望过、痛苦过、绝望过,也高兴过。她可能曾经向一个人献出所有,像在执行某种必然执行的仪式。但仪式过后,一切就结束了,她被扔在一边,像是手术中用过的,被扔在一边,被遗忘的、沾满鲜血的橡胶手套。过了一些年,她长大了,靠自己的努力做了医生,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偶尔会去寺庙里去看看,去看看仪式过后的残留,那个未曾出世的孩子。她有过几种爱情,其中至少有一种爱情是轰轰烈烈的、奋不顾身的,但也有一种爱情是平静如水的,是凑和的,是柴米油盐的,是一日三餐,公婆孩子的,是所有人的,也是自己的。
火车又开进了隧道,很短,大概在里面行进了二十秒到三十秒,刚刚进去随后又出来了。一条大河映入眼帘,是非常宽的一条大河,河水是白的,流得很急,水面银光闪闪,像是有人在上面撒了一把白胡椒粉。
他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
应该去打点水了。
周玲打电话过来,问了一些情况,富传伟告诉她,一切正常。
车载广播播放了一段轻松的音乐,然后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
“列车将要到达圆环城车站,停车两分……”
“到圆环城了?”
“我现在能看到中行大楼了。”
“还得三个钟头儿。”
“没事儿,天黑之前就到酒店了。”
他接着问女儿富咏的情况,听不听话,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之类。
周玲说都没事,你在外面注意安全。他点点头,说又不是第一次出门,然后嘱咐她在家也要早睡,不要熬夜,别忘了颈椎牵引。
大河过后是一片肥沃地农田,土地被开垦成一片片整齐的方格子,翠色欲滴。不远处是一片楼房,楼房的上空弥漫着白色的雾气,中行大楼鹤立鸡群,像一只突然伸出的手。
“我说,你知道吗?”周玲说,“宁楠好像跑了。”
富传伟微微一笑,说:“和老邢?”
“应该是,老邢老婆回来了。”
“从加拿大?不是说她在那边有人吗?”
“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听宁海燕说的,她说老邢亲口告诉她的。”
“就是说,老邢老婆回来,老邢就不能和宁楠在一起了呗。”
“是吧,老邢之前说离了,其实根本没办手续,他老婆不是移民加拿大了嘛,本来以为移民成功,就自动离婚的。没想到根本不是,移民是一码事,离婚是另一码事。”
“那现在怎么弄呢?”
“还能怎么弄?既然要回来,肯定是在那边混得不行呗。现在老邢要离,人家不离了。”
富传伟点点头,说了一声哦,周玲接着说:“没办法了,估计老邢也知道这回不好弄了,直接和宁楠一商量,兩个人跑了。”
“老邢没事儿,孩子上大学了,宁楠不行啊。”
“都这个时候了,还顾得了那么多?你不懂女人的,女人一旦认准了一件事,天塌下来都挡不住的。”
“那倒是。”
宁楠是周玲的同事,特别好的朋友,人特好,热情大方,能安排一切事。他们一起出去玩,不管干什么,只要宁楠在,一切都会安排得井井有条,让人感觉特别安心。
他见过老邢一次,是个闷葫芦,不怎么说话。那次他们一起吃烤串,宁楠和他一起来的,他不怎么说话,别人和他说话,他回答一句,然后就只是坐着,看着大家笑。
没感觉他比宋昊好,在富传伟眼里,他比宋昊差远了。
闲聊了几句,他挂掉电话,发现女孩儿一直在看着他。
“想听听这个戒指的故事吗?”
“好哇!”女孩儿双肘支到桌子上,手里捧着手机,快速地回了个信息,然后把手机放下,一双眼睛盯着他。
其实,有什么好讲的呢?不论怎么讲,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故事,不止说起来无聊,听起来更让人瞌睡。
一个女孩儿,家里兄妹四五个,或者五六个,其中有一个到两个兄弟,一个到两三个姐妹。自小父母忙里忙外,只管吃饭穿衣,其它方面少有照顾。偶尔能吃一点好的,新衣服要先给兄弟。在父母的眼里,女儿早晚要嫁到别家去,给别人做饭,给别人洗衣,和这个家庭不再有关系。要离开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家庭对她们就不再有义务,她们对这个家庭也不负太多的责任。对于长辈来讲,女孩儿在这个家也只是暂时替别人豢养着罢了,像是长大了就要上市的鸡鸭猪羊或者到了节令就要收获的果实。
女孩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恩惠。有人请她看电影,请她吃瓜子,给她带糖块,借来自行车载她上班,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和他是朋友,让她在所有人眼里都显得光鲜。毕竟,别人有的,她也将要有了。
怀孕,结婚,很快孩子出生了。
老人常说,女人结婚,等于翻一回身,重新做一回人。
女孩儿这时才明白,翻一回身,有时候要看运气,翻得好了,重新做一回人,翻不好,想做人都做不成。
男人其实不懂爱情,也不懂女人,好多的事情不只会对她做,只要时机合适,他们会对任何女孩儿做。自己只是把内心的一点小小的感动当成了爱情。
很普通的一天,这个世界上无数成长为女人的女孩儿感受到了爱情的那一天,像是完成一个必然的宿命一样,她们又变回了女孩儿。家长里短,锅碗瓢勺,邻里关系,三姑六婆和花前月下的对比显露出来,毫无意外的,她感觉,上一回没活好,要再活一回。于是,已经是母亲的她抛弃了七岁和五岁的两个儿子,和另一个男人离开了自己的第二个家,走了。
他讲完,戒指已经从左手无名指上脱下来,拿在右手。
“其实故事是我编的。”富传伟说,“每一个戒指都有一个故事,哪个故事都比这个精彩。”
女孩儿点点头,撇撇嘴,没说话。
她猛地把充电线拔下来,把充电宝重重地放到他的面前。
“他可好了!”她说完,扭过头去,看着车窗外,不再理他。
五
火车进站,富传伟走出车站,应该有人来接他的,杨院长说会安排人来的,会在出站口等。
可是,出站口没人,他检票出站后只扫了一眼就知道,这里面没有等他的人。
他站在出站口旁边,吸了一支烟,看到一辆黑色商务轿车从路口开进车站,一行人跳下车,前面的人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远远地向出站口跑过来。
他的视线缓缓地在站前的街道上扫视,全国的车站大概差不多。他想起多年前第一次从东北坐火车到徐城,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乡,一晃,时间过去二十一个年头了。
是啊,那是2000年,那年,他二十岁。
二十岁离家,在外二十年,这二十年间,家乡变了。他上次回家是在去年,走在家乡的街上,发现经过了棚户区改造,那片他出生的土地已经面目全非。
路口的铁皮屋商店没了,沿街的店铺没了,道口烧鸡店没了,活鸡活鱼猪血肠没了,清真牛羊肉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百货大楼和对面的家乐福超市、苏宁家电。
那几个穿黑西装白衬衫的人穿过栏杆,走上站前的小广场。
他看着他们,在家二十年,在外二十年,家乡变了,不再是家乡。徐城变了,徐城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家乡。
他的两个父亲,一个是二十岁之前的父亲,一个是二十岁之后的父亲,这两个父亲形成了两块拼图,都不完整,但缺一不可。
他想到一句话,他在上课时常说的。
“每个人最终都将成为历史。”
不自觉的,他心里难过起来。
他想,课该怎么讲呢,讲讲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女孩儿,她逃了学,正在去见男网友的路上;讲讲陈医生和她堕胎的孩子;讲讲宁楠和老邢,讲讲他们未来也许会幸福,但也会变成继母和继父。
他的目光在街边的一家店铺那儿停住了,那是一家很小的门脸儿,店门口有一口大锅,很小的招牌,上面并排写着羊汤、馄饨、火烧、大饼、羊肉泡馍。
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他看到那张纸上的一排大大的黑体字。
欢迎富传伟教授。
他想起来,十九年前,是个冬天,下着大雪。他从火车上下来,走到出站口,雪花很大,漫天飞舞,人群中升腾着热气,每个人身上都有白色的雪片。他走出出站口,站台上有个瘦小的身影,手里拿着一块用香烟包装拆开的硬纸板,上面写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富抟伟。
这人,把字都写错了。
继父见了他,点了点头,那可能是他和继父第一次见面,也可能是第二次。他觉得这个男人有点眼熟,但又觉得很陌生,他背着手走在前面,他背着行李跟在身后,继父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就这样一直出了站台。
“你穿得太少了。”他说,“这边冷。”
说着话,他走到积雪的公路边,他跟着他,感觉积雪是软的,在脚下吱吱作响。
他伸手,在口袋里掏了掏,拿出了那只银戒指。
“他们给我的,你看你得意不?”
他看着面前摊开的手掌,手心里是一枚粗大的戒指,戒面四周是唐草花纹,中间是方形的戒面,正中间刻的是繁体的“龙”字。花纹闪亮,是崭新的。
他问他:“冷吧?”富传伟摇摇头。
“走,去吃碗羊肉泡馍吧。”
继父说着,把手里的纸板一扔,钻进了街边一间房屋。
(责任编辑:廖晨)
葛辉,男,1980年生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现居德州,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0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省级期刊发表短篇小说二十余万字,有小说入选齐鲁文学大展2013年及2019年小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