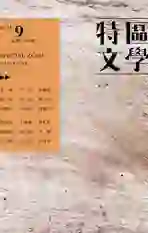上午十一点
2021-09-26谢小灵
黄昏时,我家的房子成为山的剪影的一部分,后来直接沦为夜晚的一部分。榕树略长一些的枝条拍在河水上,一种少女在玉米地嬉戏的妩媚感油然而生。万物在变化中糅合着无以名状的宁静,大叶榕树散发出清澈的阴凉和香味,抵挡火辣太阳。儿童和少年像鱼在水中,瘦小的身子浸在河里。身体的寒意刺激着我们,伙伴们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棋子跳入了棋盘。风刮过来,大家在河岸和水面之间跳跃、扑腾、下沉又浮起,循环往复的快乐经久不衰。在榕树下的小河里,少年们人仰马翻地嬉戏,发出暴风雨般的笑声。
傍晚,天空仍旧很热。在河岸附近的小角落,我默默地拍水,不想弄出太大声响。弟弟把自己做成堤坝,花费大量的时间挡水,由此获得强烈的喜悦。他压根不想见到我这位哥哥,不想和我同时在流水中,感受同一种脱离约束带来的自在享受,感受小河缓缓流动所赋予的一种超越身心的稀缺快乐。弟弟把我看成一个累赘。他从不和我一起钓鱼摸虾,也不理会这对我产生的不愉快的影响,即便他知道我需要他带给我一些光明,以弥补我漫无边际的黑洞。在家里,他端着高人一头的架势,从不掩饰他对我的嫌弃,甚至对准我的耳朵再三表明这种厌恶。
我和弟弟没有密切的情谊。父母每天都给我不加掩饰的指责。弟弟比我小两岁,他在家里挨打受骂的次数却少我一半。然而,爷爷奶奶给出的零花钱里面有他一份也同样有我一份,他因此受到打击,特意寻找别的办法彰显他在家中的优越感。弟弟拿起一把梳子,实际上我不记得用没用过这把脏兮兮的梳子。他说,这上面的头发你看不见吗?都是你留下的,你用过就不晓得洗一洗吗?谁看见这梳子会愿意跟你交往啊,脏得要命!
我的存在对他就是一种伤害,就像穷人和富人,不平等才是他们相处的前提。他越过父母的意见,单方宣布他不是我的手足。我只能用沉默来应对。我沉闷、冷静、不轻易发作的性格,使他暗暗地感到我不可战胜的气场。弟弟不接受我的沉默,他总想要打碎它。他随意打断我的叙述,在他眼里我是没有话语权的;他在外人面前扬言,说他是如何厌恶我;家里来了同学,弟弟要我走开消失,最好站出来说我跟他没有关系、我是我母亲捡来的—否则怎么全家眼睛都是好的,就我一个人看不见呢。他恶狠狠地对我说:“阳光将这一片大地照耀得发亮发光、发紫发烫,你知道吗?你知道苍茫的意境吗?你知道天堂的颜色吗?”
每次填表,弟弟不喜欢填写“家庭成员”一栏,尤其不想写上我。他希望他的出生像一个未解之謎,或者他其实是外人莫名其妙的私生子,在村头臭水沟被我们发神经的父亲捡到了。说起这无中生有的事,他煞有介事:“不然的话,我和你们哪能有这么大的差异。”
现在我和弟弟都已经长大,他上了大学,我也来到广州读特殊教育学校。弟弟不想我也有在广州上学的荣耀。在上学的同时,我还在附近的按摩店打一份工。我挣薪水并没有能改善我和弟弟的关系。弟弟想逃离这个家庭,妈妈却把弟弟优越的成绩视作家族的骄傲,指望他在大学开始令人刮目相看的奋斗,进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没想到他全盘接受纨绔子弟的信条,游戏人生让他恶行累累。
有一天,一些动静从他的房间传过来。我偷偷地模糊看见,他在房间里先是练习一种拉丁舞的动作,接着对着小镜子表演吐烟圈。他瞥见我的偷窥,深感冒犯。他对我的抗拒加倍,我从此失去了与他一同吃饭的资格。
最令弟弟沮丧的就是他的长相。他虽有张瓜子脸,但不怎么周正。我却长得越来越像个城里人。上大学后弟弟的长相江河日下,远离他对自己容貌的基本要求。他对长相又抱有执着的期待,希望别人眼中看到的是他理想的外貌,并得到美男子应有的礼遇。弟弟终于尝到了“女大十八变”的滋味。他有一颗酷似龙王的头颅,八字眼、八字眉、八字嘴,瘦高的身躯像极了旧时的柴火。村里一些小孩往往见到他便大哭起来。他对此的反应是:“村里的人连同他们的孩子都是没有眼光的。谁厌恶我就是谁的错。”
我常想跟一个迎面而来的人说说话,尽管不知道他是谁、在哪里,我确信有这么一个人,但始终没找到这个人。村里老人家说我谦逊老实,实则我的内心天马行空。我和天生的盲人不同,我曾经知道也见过阳光和蓝天的颜色。我的理想是去旅游。他们说,一个瞎子出去旅游能做什么?我说,透透气,空气对弱视力的人也有意义。我不费力气就分得清空气中的波长,而别人是分不清楚的。我的想法饱含矛盾,只有我理解其中的和谐统一之处。
很多年前,妈妈生日那天,爸爸给妈妈的礼物没有到来,我却来了—如果怀上我算礼物的话。当时的妈妈是高兴的,不像现在她的说法:“你是来讨债的。”
我得到按摩店的工作、开始自食其力的事实也改变不了母亲对我的歧视。我知道我的出生使她对命运感到灰心丧气。她在家随意发飙、抱怨,错误永远是他人的。她指责我,说我像我的父亲。我很不平,不是你先选择爸爸在先的吗?妈妈不回复,直接将她的人生上升到悲剧的高度。
在妈妈眼里,我一直有变废为宝的义务。妈妈希望我做一个算命卜卦的先生,起码是四邻八舍的奇人。如果我因瞎眼而有了一点神秘的气质,就可改变我给她带来的晦气。有次我答应成为一个算命先生,她第一次露出苦笑,生活忽然有了生机。弟弟考上了大学,我的前景将如她所愿,这似乎让妈妈的精神得到了短暂的恢复。悲惨的巨浪曾经一次又一次袭击了这位外乡来的母亲,但深渊中的幻影始终在鼓励着她。她设想自己是神秘的算命先生的母亲,一种超越常人的特殊感油然而生。如果我和弟弟能有些在我们村庄独一无二的异相,也算是对她人生的一种变相弥补,妈妈或许又会迎来一生中的好时光。她坐在家里唯一一把圆靠背的椅子上,感觉圆圆的靠背似结结实实的胳膊,把她搂住了。
那几天,她身上丢失多年的善良与热情又回来了。她开始关心邻居,过度热情地打招呼,甚至偷偷拿回来造假化妆厂的伪劣化妆品送给邻居的女儿,说女人18岁就要开始保护自己的皮肤。
发现我是低视力后,妈妈很少抱我。小时候,我很厌烦她给我喂饭的方式,她总是嚼碎以后再给我,每次我都推开她送过来的二手食物。当时妈妈还不知道我是一个盲人,她会搂着我,到处走动,哄我吃,当我是宝。我大了一些,学着帮家人做家务,我帮爷爷倒中药时,先是对不准碗口,让中药洒了一地;端到他面前时又抖了两抖,爷爷的裤子出现一大片湿斑。慢慢地,爷爷发现桌上的脏乱跟我总脱不了关系。开始他还不相信,大声呵斥,你是瞎子吗?呵斥了十几天,大家都相信了我原本就是一个瞎子。我哭了好久,在痛哭以后,我睡了长长一觉,醒来觉得头有平时两倍重。
与此有关系的是桂林舅舅的到来。舅舅结婚十年还没有生男孩,他想要我当他的儿子。舅舅说,没有自己的儿子,老了谁煮饭给你吃啊,你到女儿家不就是一个外人来访?舅舅年轻的时候,妈妈很怕他,因为他对妈妈用尽了恶语咒骂。他讨厌妹妹,并且写在日记上。现在舅舅亲切地喊妈妈为“甜妹”,带来好多桂林特产,劝说妹妹把儿子过继给他:“都是一家人啊。”妈妈对他提及旧事:“哥哥,你以前和现在,不像是一个人。”舅舅理直气壮地解释:“又不是当着面骂,你装作不知道就行了。”妈妈没有把我送出去。舅舅走的时候,又恢复了给我的第一眼感觉,冷酷、势利。后来妈妈发现我真的是瞎子,忽然觉得有火焰在脑中流动。她把我重重地扔在地上,尖叫起来,好像我是一条蛇在她面前扭动:“为什么你不跟你舅舅去桂林?”
我的父母在一间小店认识。妈妈是小店售货员。她爱欣赏黄昏的光线像金子一样流过山坡,远方的景色是她的向往。一天,爸爸从炎热的大太阳底下钻出来,小跑着,手里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对妈妈说:“有没有这样的矿泉水?”“你把瓶子留下,我明天帮你找。”他俩对视,有说不完的话。于是就有了明天,有了更多振奋人心的明天。妈妈觉得他对自己好,爸爸觉得她愿意和自己说话、长得比周围人好看。从那以后爸爸开始帮妈妈送早餐,他的军营里经常有加餐,很多战友都知道了他帮女朋友打饭。
四个小杯子随意地放在精致小盘上面。妈妈问爸爸:“你那个杯子是哪里的?”爸爸说:“这些都是我们老家的小茶盅,以后带你到我们家喝茶。”爸爸的广东籍贯也是妈妈看上他的原因之一。爸爸说,广州东站的火车开往全国各地,他们就专门去东站谈恋爱。广州东站不全是熙熙攘攘的,前面有一片很安静的长方形小树林。从西口出来以后,就可以去宜家看北欧家具。爸爸买两杯奶茶,有一点装模作样地自我陶醉。
妈妈喜欢被爸爸粗糙的手抚摸,像逃荒的人喝到大碗鸡汤。几天后妈妈离开商店,把全部家当塞进拉杆箱,准备嫁到广东了。她的嘴角显得稚气十足。
父母在结婚前差点分手。爸爸给妈妈拍了一张好看的照片,不慎遗失了。冷战了十天后,妈妈还是想和爸爸和好,对妈妈来说,把这样一个男人从眼前抹掉,就像在黑沉沉的天气中把雨水辨别出来一样难。她去敲爸爸的宿舍门。爸爸把门开到一半,准备迎接着女友敌意的目光。没想到,她说:“我的身份证落在你那里。”爸爸表現得有些懒散,这种懒散好像刺激了她,她转向窗户,侧脸藏起了目光。她好像看着远处,继续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落在你这儿了。”爸爸没有恢复清醒,穿好袜子准备动手找身份证。妈妈的目光早已离开了屋子,对着远处的山,好像一个画家准备写生。她平静的后脑勺好像给爸爸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她准备和我坐下来喝一杯酒?这种感觉爸爸还没有说出来,妈妈就突然说:“我的身份证在你这里,所以说这是怪你。”她笑了起来,爸爸也笑了起来。
少女时期的妈妈的亲吻真实又纯洁。发生关系到底是从心灵相交开始还是身体交好开始?她不确定。她也不相信一段关系可以永恒。在某天下午,热恋中的妈妈急切地要抛掉她的贞洁,像她多年看重它一样强烈。在某天黄昏,天气闷热,他们更加吸引彼此。爸爸说妈妈像是他的孩子。他了解她,他爱她,他们之间没有陌生感。有那么一分钟,妈妈的手离开了他的背,在空中随意画着三角形、四边形,数不尽的图案。妈妈文雅地说:“你的身体长满青苔,滑溜溜的。”爸爸说:“我教你怎么说广东话。”他说粗话,像个村里人。他们躺在凉席上,对彼此浮想联翩。当时还没有人建高楼,抬眼只看到树的影子。他们成为对方的水域,也成为对方的小鱼。他们尽心尽力探索彼此的宇宙,仿佛对方城池里的每条街道、每栋房子、每个角落,凡是道路能达到的,凡是尘埃能达到的,身体也是所向披靡、无所不至。妈妈和爸爸都享受到搂抱之好、亲吻之好、互相渗入之好。
微光唤起了人对某种滋味的回忆。
妈妈说,父亲是一个有爱却不耐烦的丈夫。妈妈懂得大自然的美好,妈妈知道眼前和远方有梦幻般的存在。一开始,妈妈外乡人的背景、时而梦幻的神情和南方口音似乎使她在乡下人中显得鹤立鸡群。那个是某某带来的女人,本地女人往往如此称呼这个桂林女人,好像她是一个千里迢迢赶过来的、背负重大使命的女人。她和她们一同绣花,不同的是,妈妈会站起来看看五月份的原野,看看雨天的空心菜点染绿油油的大地。更多村里的女人对她的特殊地位是不服的。我妈妈容貌姣好,但村里无人赞美过她的长相。时间久了,爸爸慢慢地受到影响,对妈妈也怠慢了。
漏洞终于出现了。我舅舅来到村里,那些女人很开心:“她弟弟像个要饭的。”这是妈妈特殊地位垮台的开始。妈妈爱田野也爱阅读,但这再不能成为爸爸把她宝贝一般护在怀里的理由。他不再和妈妈分享对山林的热爱,不再一起散步:“散步做什么,给人家笑话,不如去买菜呢。”他发泄压抑已久的失望。他开始在家里偷偷训斥妈妈的各种不是,比如,她还不会潮汕话,他把自己的桂林之行看作绝望之旅。这对妈妈是双重打击。他开始当着兄弟的面,后来当着自己父母的面,大声训斥、打骂她。有时,爸爸还会理直气壮地痛打我们兄弟,直到棍子裂开。爸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让妈妈和我们兄弟进去,每次都要爷爷过来发很大的脾气,才不情愿地开门。龃龉多了,妈妈逐渐讨厌这个男人,她只想看到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撕碎。
爸爸殴打妈妈、爸爸出轨、爸爸失去意识这互为因果,没有人留意到先后,三件事情几乎是同时在我爸爸身上出现。失去意识是爸爸第一次死去。父亲第一次死是死在无意识之后,还是死在自己清醒之前,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我五岁那年的一天,爸爸耷拉着脑袋被部队的两个战士送回了家,两人对爷爷奶奶说,你们的儿子因公受伤,演练时手榴弹提前爆炸,头部受伤。爸爸以废人的状态转业回乡了。
好在爸爸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是清醒的。有一年年底,家里人忙着做粿,烧香拜老爷,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他去镇上买张饭桌。这天傍晚,爸爸回来了,一脸兴奋,买来了三张方桌和两张床。爸爸很得意:“那女老板说这床质量好,要我买下。”妈妈发火了:“女老板说屎尿好吃,你也吃。”爸爸的回答更快:“我愿意,我愿意!”妈妈的脸黑了:“她算老几啊,要你去死你也去啊!”爸爸扑了上来:“就是死都愿意,她把我拉上床了!”
我从爸爸几次矛盾的叙述中勉强还原了他的外遇。那天爸爸来到家具店,看见老板娘,丰腴的身材,肤质细腻,爸爸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女老板拉扯了他一下,爸爸怔住了,那天买家具的人就只有爸爸一个,老板娘一个眼神,他就扑了上去。后来,反正爸爸买来了桌子和床。家里是不需要这么多桌子的,也没人让他买床。爸爸说家里将有新人来。“你老实说,发生了什么?”每一天妈妈问,爸爸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有时他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使这件事彻底成了一个无头案子。“那个女人把我往身边拉,把我往床上拉,她要我看床,我后来跑了,她跑了,我追上去。”“她买了粿条给我吃,我第一次听到女人这样唱歌,她专门唱歌给我听,有一句歌词是,哎呀我的小傻瓜,你就是欠我一顿打。我默默地听,记住了她百灵鸟一般的声音。”那一天整个村里都知道了,爸爸打妈妈时候说出来:“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她的皮肤好光洁哦,嫩嫩的。”这一句话刺痛了妈妈的心,妈妈咬住嘴唇,眼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种复仇神情。妈妈斥责他伤害自己,父亲只是不断地抠耳朵,有时候摸一下鼻子,再摸一下头,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事后我想,一切都是爸爸脑子那一大块淤血的错,那一块淤血阻隔了他对这件事的悲伤感觉。母亲说不知道自己前世作了什么孽。妈妈那时还不能深刻地了解什么是命中注定、什么是逆来顺受,她不知足,放任自己的悲伤肆虐,她一次次昏倒,又一次次精神恍惚。她把自己像撕破的帆一样扔在床上,有时又像卷胶纸袋一样把自己蜷缩成一个不规则的破烂、一个林中迷路的人。她在家里的几个房间绕来绕去,像一根被风吹乱的杂草。她端碗时发出惊人的声响。几天过去了,妈妈还没有走出这种情绪,把自己折磨到全家都不敢靠近她。我在那几天走路都蹑手蹑脚。
有时候爸爸心情好一些,一边打着妈妈,一边说出似是而非的道理:“你想要老公,就要知道老公会带来应有的坏处。只要老公的好处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种菜种瓜果,你会有青青的山脉、绿油油的菜地,也会被虫子和一些可怕的东西折磨。”爸爸说,无需多讲,懂的人一对眼就懂。
爸爸的外遇出轨是他主动张扬出来的,夸耀的成分更大。那个女人的出现,到底是有爸爸的吹嘘成分还是真有其事?不管怎样,他或真或假的恋情打击了妈妈。
爸爸越被人家追着问越来劲,干脆笑着坐在沙发上,抓起我的手臂用力地晃着,头也摇着,表情像是吃了鸡腿一样欢喜。他张开嘴直视着我,我知道我应像一只捕猎的鸟一样的衔住他的目光。我尽力表现出精准控场的能力,屏蔽掉羞怯与担心。不然,我就又要受皮肉之苦。我只需要看爸爸的手指头的方向,就知道他何时会找出我的错误、附赠痛打。
那天不到11点,太阳明亮,我在学校,课间有人来到我们教室,牵着我和弟弟的手,拉我们回家。那人走得很快,我的腿不停地大力迈开向前,都很难赶上他。回到家里,见妈妈坐在家里的角落,她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安静。爸爸躺在床上,用我们没有见过的厚厚的黄布蒙住了头。大人叫我们跪下来。不知多久,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了。我没有听懂。抬进来一口棺材,棺材周围蒙着红色的布,黄色的布铺在中间。爸爸的鬓角摩擦棺材板的声音有点沉闷,又有点清晰。寿衣是蓝色的,很新。之前他穿着时髦的时候,总像披着羊皮的狼。爸爸不虚荣,但也不够自信,他永远对自己的外表心不在焉,头都不梳好就冲出去。我经常留意到梳子上剩下的头发,那些头发残存被主人抛弃的不知所措,还在热情地粘在梳子的各处。可如今,他配上这种绸缎的衣服,却有了一种文明、高贵的气象。
大伯和叔叔几个人用10厘米的钉子一个又一个对准孔眼敲打,钉好了棺材。四周摆放了几十根蜡烛。他们把爸爸往棺材里放的时候,动作持续而稳定。我看不见父亲的脸,也看不见大伯和叔叔的脸,他们仿佛有一种执着的冷漠。钉子敲打了很久,盖棺材的时候,人们把我带出了那间屋子。我听见了声音,但更多像是我的耳朵发出了一种声音,疲惫又冗长,起落有节奏,仿佛还有一种安抚人的宁静力量。那时我尚未感到悲伤,开始怀念我父亲粗糙的大手,他的那种触摸按摩对肌肉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安慰。我似乎是第二次遇到这样明晃晃的太阳。我胸口感到一阵燥热,好像太阳是我穿过的第一件衣服,一件炽热的衣服。我听见了爸爸的左边额头擦过棺材板的滋滋声。我每次想起木材的敲打声,就会想到当时的情景。爸爸的脸上仿佛仍回旋着一丝呼吸。我幻想着他伸出手从棺材里抱我。他仿佛还有一条命,仅仅一次死亡不会终结他的人生。我能明显感到爸爸对于棺材的尺度有一些微微的不满,他厌恶棺材两张板子不结实或者钉子不牢靠,火气攒到一定程度,爸爸就会跳起来。我不合时宜地想象,爸爸将举起来大手打我,他依旧搞得清楚是非对错,他把那只大手打到我脸上了,他的胳膊肘好像也有微弱的碰撞棺材板的聲音。我的爸爸死在那年冬天,地面上天天在刮风,风打着空气的耳光。
他就是安安静静地睡在他的棺材里,他的全职工作就是平躺着,在一片黄色的软绵的厚厚的布下面。布匹看上去光滑、柔软。父亲的躯干有着冷漠的气质,他的冷漠和他平常的暴躁脾气有一种奇怪的对比。人已经死去了,死了以后冰凉的身体还有一些柔软,村里人说这种柔软表明他心没有恐惧。他躺在租来的冰柜里,四周满是火苗跳动的蜡烛,一缕缕的蜡烛气味构成了一个仪式。父亲在乐声中走到了村口,人们跪在那里哭泣,活人只能跪着哭。送葬的队伍从村子这边开始行进,他们选好了一条路线,两支乐队一支在棺材的前面,一支在棺材的后面,乐队演奏的歌有两支:《世上只有妈妈好》《敢问路在何方》。前面乐队的一个人拿着爆竹,每到一处就点一通;后面有个蓝衣服的女人一直在哭。近亲穿着白衣服,远亲穿着便装,带着小白色的花朵。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女人围成一圈跪拜和哭泣,我的眼里,一切在阴影里逶迤穿行。在仪式要往山里火葬的时候,有人例行公事地喊了一声,有谁要跟着去的啊?我说我想去。小孩子去做什么,没人理会我。我再坚持,爸爸可能要爬出来,举起木棒,向我劈来。
车开远了,逐渐模糊,最后成了一个小圆点,消失。我眼前有一串光圈,像腰上所系的草绳的颜色。我打开了一扇看不见的门,泪水就像洪水一样汩汩流出,但是并没有滔天的声音。我像一个坚守阵地的人却把阵地私自出卖,解放了我关在内心已久的话语、敌人以及泪水。家里其他人都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我咬着牙为爸爸做一点体面伪装。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走上坡的路,其他人已经飞快地下坡,把身体所有的废气彻底排出。
爸爸入殓时,妈妈为什么没有哭?眼泪流干了还是她装不出来?如果父亲死在头被炸伤之后,如果说父亲那时已经失忆,那他所做的那件出轨的事,如何伤得了母亲的心?妈妈不是真的恨他。妈妈产生了一种悲伤到来的喜悦,绝望也带来更加深的满足。随着爸爸的死,他带给妈妈的伤害也被埋葬,妈妈是否终于如愿以偿?妈妈总说自己的命不好,嫁错了人,连生孩子也懊悔。她从桂林来到了揭阳,妈妈讲的潮汕话还是像外国人讲的中国话。妈妈从绝望中找到一丝安慰,如果爸爸有过对自己不忠的事情,是不会这样毒打我们的。
我记得祈祷的招魂的仪式在某天中午举行,几个人在那里挥舞着手里的工具。这种仪式除了让我感觉到一种不能确信的滑稽的效果,丝毫不能对我产生安慰。我同时认为这是对爸爸的一种打搅。招魂的仪式持续在黑暗中进行,一个活人变为非人带来的不适感逐渐消解,爷爷脸色苍白,爷爷的影子也是脸色苍白;奶奶的影子苍白,奶奶的脸看起来相当糟糕。仪式中,我和弟弟还得到红鸡蛋。
父亲在雨天会待我亲切一些。他有一次讲述他外婆的故事,手拍着我的脸,还揉了一下。粗糙、甜蜜的痛感。爸爸说自己当年去当兵,是因为学习不好,脾气暴躁。他对我们的暴躁像是他肉体的需要,而不是他精神的需要。
爸爸去世后一周左右,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爸爸睁开眼睛一次,他清晰地叫了一句妈妈的名字,还低声说了一声,没有家具店老板娘这个人。爸爸穿着刚认识妈妈时的军服。在梦里,爸爸含情脉脉,皮肤红润,有一张很年轻的脸。妈妈对我说:“哦,是吗?你是当算命先生的料。”不知多少天后,梦有了续集:父亲又穿着军服,对爷爷说,爹爹,我回来了。
我眼睛看得見的时候,已经感觉妈妈的细纹开始爬到鬓角,时常忧伤。她皮肉下垂,骨头收缩,牙缝开裂。妈妈已经提前过上老年生活。人的孤独是从老年开始的。
我也想念弟弟。遥远的那天早上,我和弟弟六点就起床,从村外搭公交车去到汕头玩。我们成为当天第一个到小公园的人,为了来看爷爷记忆中的小火车。当时爷爷可能才几岁,天刚蒙蒙发亮,在他前面一辆小火车高声鸣笛,然后白雾炸开。爷爷兴奋无比,感觉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那个坐在前面的火车司机。他还记得火车司机紧紧盯着前方由铁轨组成的长长的路。火车一拐弯落入更深的城市中去了,犹如太阳落入树林那头。他身上穿着蓝色的制服,还戴着帽子和手套,旁边放着绿色的水壶。这一身打扮深深印在他年幼的记忆里。火车的声音显得深沉。没有人理会他,哪怕他这时喊救命,也不会有人跑过来。每个人都很悠闲,一望无际的陌生人就像一望无际的麦田。他坐在小公园,脸蹭在自己的大衣里。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把腿伸直,在最后一个和煦的夜晚。
(责任编辑:王思雨)
谢小灵,广东珠海人,广东诗歌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珠海金湾区作协主席,《金土地》杂志编辑,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教师,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