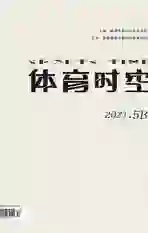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及其现代矫正价值
2021-09-17张宏治
张宏治
中图分类号:G85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21)05-009-02
摘 要 儒家通过射箭这一技艺确立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是“礼让”。“礼让”原则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相呼应,是“道”的直接体现。它通过个体主体性的建立,使个体能够诚实面对现实生活,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生存关系,以此达到幸福。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的普遍异化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礼让”原则重建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 中华传统体育精神 存在 克己复礼 主体性 异化
春秋末年,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礼让”确立。“礼让”原则根源于中国的“天道”传统,它带着诚实的态度立足此岸世界,为个人在世界中与他人如何交往,如何面对自身的感性生命以及如何实现天人合一提供了根本遵循。现代工业文明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对存在的遗忘。面对这种异化困境,“礼让”原则展现出强大的道德主动性,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交往提供了精神支撑。
一、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
西周时期,贵族教育的理念和体系已比较完备。其中,“六艺”在“官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春秋末年,孔子开创“私学”,打破阶级壁垒,将礼乐教化带到了平民生活中,“六艺”随之成为君子感悟“性命”与“天道”的途径。孔子将这六种技能纳入儒家道统之中,从那时起,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术”的关系焕然一新。“术”不再是体悟“道”的遮蔽,恰恰相反,“术”是达“道”的自然法门。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基石和主干,其道统的“此岸性”常常要求一种诚恳敬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思想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统一于现实的生命活动。所谓“文通武备”,一个人若想成为一名君子,不仅要知“礼乐”,更要通“射御”。子曰:“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在儒家传统中,礼乐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身的根本,它让君子懂得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并给自己以合理的定位,这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诚实地面对现实和自身。君子六艺中的“射”,指的是射箭,“御”指的是驾驭马车,二者关乎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协调,是中华传统体育的文化哲学的重要起源之一。如果说“礼乐”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那么射箭作为一种典型竞技性的体育运动,它在孔子那里被赋予了超出一味争胜的道德修行意义。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与人争胜,但射箭是一个例外,即使是比赛射箭,君子依旧谦让温和。儒家文化讲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其仁爱的道德要求往往排斥争强好胜。但儒家的入世情怀又要求一名君子必须诚实地面对眼前生活与身边实有,正是在这种道德与现实的矛盾与张力的境遇中,儒家对于体育精神的看法得以发生和展开。弓箭本身是古战场的杀伐之器,比赛本身是零和博弈,这些现实往往与儒家的核心理念相背离,而孔子恰恰要面对和解决这种矛盾。孔子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继承先贤的思想,借助“让”这一道德理念建立一种参与者必须遵循的道德规则或“射礼”。作为一种竞技比赛,射箭必然要产生胜负,这种必然性是使射箭比赛得以存在的根本,胜负双方必须承认结果。另一方面,虽然胜负是必然的,但比赛双方对待对手的态度也是必然的。无论输赢,双方都能以一种“让”的态度对待对方,那么,一种“人性”的必然性就得以确立。胜方不骄,败方不馁,给予对方以充分的尊重,自身的品德得以完善。许倬云说:“这种构想,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重叠。个人的部分从‘修己’领会到自然的人性,个人既不能孤立,也不应当孤立。”[1]我们看到,第一种必然性与第二种必然性存在本质差异,即人在第一种差异面前只看到了自身的得失,在第二种必然性面前却能看到他人的存在,也只有在看到他人时,他本身的存在才不再停留在抽象的状态中。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孔子赞同周武王散军郊射的做法,否定了单纯以彰显力量为目标的射穿箭靶的粗暴方式。在丛林法则下,人与人是弱肉强食的关系,生存的压力导致互为仇敌,禽兽争斗比的是獠牙是否尖锐、体量是否庞大,这是一种纯粹野蛮的“尚力”的生存方式。面对这种恃强凌弱的兽性倾向,儒家坚持以“礼”纾难,在野蛮的动物性与文明的人性之间寻求平衡。与“尚力”不同,“射不主皮”讲求“尚武”。中华文明的始祖在创字时,赋予了“武”字以脚趾加戈的原始杀伐意义,经过文明的演进,止戈为武的涵义突破了人性的缺陷,赋予了“武”字以辩证的天道思想。在止戈为武的尚武精神中,暴力是有秩序的,它不仅能高扬个人的主体性,让人性中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得以宣泄,而且能使暴力規则化,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和谐稳定。乔凤杰指出:“儒家对武术道德的主要影响,乃是为武术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与古代社会保持一致的体制结构,为武术习练者提供了用以统制其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2]。儒家运用文明的“礼”给野蛮的暴力立法,划定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界限,以此保护人性不受外界条件的干扰,人性的独立保证了竞争在合乎理性的状态下进行。
二、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的现代矫正价值
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是现代性,现代性的支柱则是“资本”。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进行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客观规律,构建了科学的现代史观[3]。对于资本,马克思有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第二种判断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从原始积累到向全世界扩张,都是其自身运行逻辑的产物。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唯一目的和方向就是“增殖”,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被活劳动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通过反噬活劳动,从而占有其剩余劳动。资本通过这种对人的活劳动的占有不断扩张,它支撑起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将社会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觉服从资本增殖的逻辑,把对物质数量和质量的感受当作对现实生活的本质感受,物质生产取代人际关系的生产,社会生活的情感层面和物质层面发生颠倒,物质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卢卡奇指出:“人既不实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已经存在并且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作用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5]。个体与他人的感性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也发生扭曲,传统的人际关系发生分裂,人将物质作为与他人交往的“一般等价物”,一切与人有关的活动必须用物质加以衡量,非理性逻辑被冠以理性的框架。当社会运作受阻时,应归因于没有遵守资本逻辑,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资本最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对立力量。在这种情形下,浪漫主义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是不合乎现实的。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应立足于生存维度,用传统的人本主义精神矫正物质对个体自主性以及个体与他人关系的扭曲。
现代社会的物化性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决不能以单纯的伦理道德观念衡量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从个人生存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做过剖析:“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个体的全面发展,即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这一目标无非是个体价值和幸福的实现。马克思没有将希望寄托在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身上,他承认自由个性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但这种现实的自由个性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能力体系高度发达。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种哲学理论做出高度评价:“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7]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异化的辩证法,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个性的实现和异化同在一个历史发展线上。马克思将解决物化的办法设定在物化自身的对立统一中,通过社会生产解决社会生产本身带来的问题。与马克思解决物化的方法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精神强调挖掘人自身的主体性,为克服现代性危机奠定坚实的心性基石。
主体性的丧失是现代性物化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丧失导致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非理性化,要想获得生存幸福,人必须在“明心复性”的基础上重建主体性。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扎根于中国人对于“天命”与“人性”的一贯性关系的理解,重建人的主体性需要理解这一原则背后的本体论原理。“天”作为独立于一切存有的实体,通过“气”与“理”化生万物,人按这种内在的、至善的“生生”本性打开其“超越性”维度。“天命”不在人的生存之外,它与人的感性生活高度一致,人的主体性通过“率性”得到发扬。立足于现实,不同的人应因材因时,根据个体先天禀赋,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主体性的回归。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是儒家将这一原理纳入现实体育生活的根本遵循,其实质是为人在体育生活中找到主体性基石,为人打通体育与道之间的联系。
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对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把控。“礼让”的理论依据可以表述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讲的是尽心竭力,“让”讲的是推己及人,前者合乎礼法,后者心存他人。人的生存要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个体私利总要和他人利益产生冲突,人应按照本性中的“恕道”行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有禀赋的人自觉以本性行事,践行“让”,禀赋差的人能自觉按照“礼”的教化面对他者,就能使人类社会走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大道。
参考文献:
[1]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2]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唐爱军.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現代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03):23-31.
[4][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