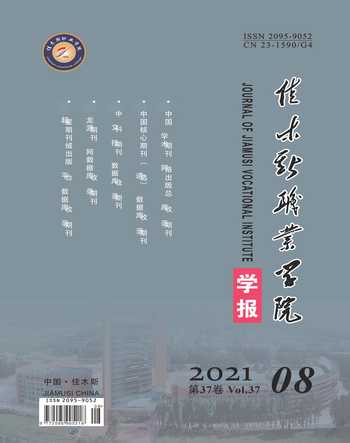《家》中黑人女主人公抗争历程的叙事分析
2021-09-10赵玉存
赵玉存
摘 要:托妮·莫里森的《家》在聚焦黑人男性弗兰克的同时,呈现了黑人女主人公茜艰难的抗争历程。本文结合作品中呈现的叙事技巧,分析文本中的聚焦转换、人物对话以及循环叙事策略,将有助于探析黑人女主人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抗争意识的觉醒、自我救赎的实现。
关键词:黑人女性;抗爭历程;自我救赎;《家》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8-00-02
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十部小说《家》,在叙事中书写了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女性在多重压迫下的生存困境,呈现了女性同盟力量对女性抗争意识觉醒的重大作用,展现了女主人公为冲破束缚、寻求自我、实现自我救赎的艰难抗争历程。
一、控制聚焦转换呈现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
《家》第三章,通过弗兰克回忆叙事的内部聚焦引出茜悲惨人生的缘由。根据弗兰克的叙述,受到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种族主义者强行闯入黑人的生活领域,致使弗兰克全家连同众多黑人在“戴或不戴警徽但总是拿着枪的人”[1]的威胁下,被迫离开了得克萨斯州。在救世主堂外排队领餐时,有身孕的母亲无意中听到了排在她前面的女人的名字“伊茜德拉”(Ycidra),便认定那是“世上最甜美的东西”[1],并以此为腹中的孩子取名。但除了母亲,其他人都叫她茜。因担心茜会死于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母亲生下她后等了九天才敢为她起名。虽然茜没被死神吞噬,但生在路上这件事似乎预示了她未来要以无根的状态过飘荡的生活。
《家》第四章,叙述者通过将叙事视角聚焦于茜,讲述了她从出生到成年的悲惨经历,呈现了其艰难的人生历程。出生后,茜成为祖母丽诺尔怨恨聚焦的对象,甚至洛特斯小镇里的“每一个大人都能对她呼来喝去”[1],原因是“正经的女人生孩子,都是在家里,躺在床上,由一群经验丰富又虔诚的女人们接生”[1],而茜却是在家人逃亡的路上出生的。年幼时,封闭隔离的小镇环境无法为茜的身份构建提供有利的空间,使其对最初的自我毫无信心,“觉得自己一文不值”[1]。在这期间,只有哥哥弗兰克给予了她疼爱与关怀。但弗兰克的过度保护使她不知如何应对险恶的人心和复杂的社会,致使茜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弗兰克参军后不久,渴望得到爱与安全的茜,在不清楚男友普林斯(Prince)背景的情况下,便与之结了婚。但普林斯对茜的爱只是为了得到祖母丽诺尔的车。在满足了自己的物质需求后,他便将茜抛弃在亚特兰大。为了生存,茜接受了为白人医生做助手的工作。
《家》第五章,叙述者没有聚焦茜之后的生活,转而以弗兰克为焦点展开叙事,讲述了弗兰克从朝鲜战场退役归来后,在北方的颓废生活。直至第十二章,叙述者才通过白人医生家的另一位女佣——莎拉(Sarah)的视角道出了对茜的叙述戛然而止的原因。茜在成为白人医生助手之后,沦为其研制药物、器械的实验品和牺牲品。在白人医生的药物麻醉下,茜失去了意识,成为任意处置和实验的对象。
《家》第八章,叙述者通过丽诺尔的视角从侧面描写了茜被任意打骂、沦为祖母出气筒的厄运。深受男权思想影响的丽诺尔非但不同情婚姻受骗的茜,反而将车被骗走的原因归咎于她,甚至指名道姓地辱骂她为“小偷、傻子”。对家庭不闻不问的父母以及尖嘴薄舌的祖母并没有承担起为茜营造健康成长环境的责任,反而使茜的生活更痛苦。在多重聚焦的转换下,茜悲惨生存困境的图景渐趋完整。叙事者通过控制叙事聚焦的转换,不仅交代了茜悲剧人生的源由,而且为记述茜日后踏上走出精神困境、实现自我认同的艰难抗争之旅做了铺垫。
二、人物对话展现女主人公抗争意识的觉醒
《家》通过设置茜与女性个体之间、茜与女性集体之间以及茜与男性之间的对话,将主人公抗争意识觉醒的过程自然地体现出来。
第一,与女性个体间的对话促进了茜女性意识的觉醒。当茜在亚特兰大走投无路时,她向邻居塞尔玛寻求帮助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其逐渐清晰的自我感。
塞尔玛:你该不会知道他(普林斯)跑哪去了吧?
茜:不知道。
塞尔玛:想知道吗? 茜:不想。
塞尔玛:谢天谢地。 茜:我需要一份工作。
塞尔玛:别告诉我你不在波比那干了。
茜:我没辞,但我需要更好的,薪水多点的。我现在没有小费,必须在餐馆吃。
塞尔玛:波比那的饭菜最棒,你上哪也找不到更好的。茜:可我需要一份正经工作,能存下钱的。而且我不会回洛特斯[1]。
茜的话语逻辑清晰,目标明确,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份薪水多点且能存下钱的工作;茜的思想态度坚定,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都不愿再回洛特斯小镇;茜的主体意识很强,她的回答中“我”出现六次。此外,“不知道”“不想”这两个简短回答,也体现其坚定意志。
第二,黑人女性集体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了茜自我认知的提升,加强其自我认同。当茜和弗兰克返回洛特斯小镇后,小镇黑人妇女的严厉话语使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骨子里的狭隘和自卑。
A:你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惦记。
B:你又不是给这种魔鬼医生拉车的骡子。
C:谁跟你说你是垃圾的?
茜:我怎么会知道他(白人医生)想干什么?
D:不幸可不会发警报。你得警醒着点儿,不然它就闯进屋子里来了[1]。
小镇黑人妇女们轰炸式的言语实则是对茜的关心和激励。当茜被弗兰克带回洛特斯小镇后,茜与妇女间的对话不仅使茜重新定位自我身份,而且感受到来自女同胞的帮助,得到抗争的动力。在小镇妇女的帮助下,茜实现了心智上的成熟和精神上的成长。
第三,茜与弗兰克间的对话更突出茜作为黑人女性在经历创伤与挫折后树立的独立人格,她不再怯弱,而是变得更加成熟、更有主见,并敢于表现自己。
弗兰克:我很抱歉,茜,我真的替你难过。
茜:别抱歉。
弗兰克:好了,丫头,别哭。
茜:为什么不哭?我要是想哭,一定是因为难过。何必非要打起精神来?我应该难过。这件事本来就够惨的了,我不会因为真相让人觉得痛苦就假装它不存在[1]。
对话展现茜被破坏性实验剥夺生育能力后对弗兰克安慰话语的应答,通过“为什么不哭?”“何必非要打起精神?”这两个简洁有力的设问体现了茜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三、循环叙事策略体现女主人公自我救赎
《家》突破传统线性叙事小说的结构,通过从“房子”到“家”的上升式意象循环、洛特斯小镇的地点循环,以及马场埋尸的情节循环,搭建起密切相连而又前后呼应的叙事模式,既给人留足悬念又体现了茜自我救赎实现的轨迹。第一个是从小说开篇的孤寂冷清的房子到结尾充满爱与温暖的家的上升式意象循环叙事。这一循环叙事结构突出主人公的核心目标:家。开篇小诗通过一系列发问为小说情节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使后续情节围绕“寻家”“回家”展开描写。在小说的结尾,莫里森同样采用诗歌的形式与开篇小诗呼应,使“房子”与“家”的意象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故事发展,茜对于“家”的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扉页上的房子,在茜看来,只是暗影幢幢的房子,缺失爱与光明,不能称之为“家”。在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过上有‘爱’的生活,爱自己、爱親人才能使冰冷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2]。故事的结尾,茜说的话意味着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重新开启了新生活。第二个是洛特斯小镇地点循环叙事。从描写主人公眼中枯燥乏味的洛特斯小镇到落笔在充满爱与关怀的洛特斯小镇,体现了带有浓郁黑人文化传统的小镇是黑人女性走出精神困境、实现自我救赎的归宿。起初,冷漠无情的家庭环境使茜对洛特斯小镇充满心理阴影;历经磨难后,充满欢声笑语的洛特斯小镇友好地接纳并治愈了茜。通过和小镇女性一起生活,共同缝制百纳被,茜逐渐缔结了和妇女们的情谊,摆脱了自卑,改变了对小镇的看法。在社群的帮助下,茜进入了积极乐观、团结友爱的黑人大家庭,完成了种族的自我认同。第三个是从弗兰克兄妹在马场看见白人埋尸到二人去马场重新埋尸的情节循环叙事。马场埋尸的情节循环叙事不仅“具有强烈的重建和重生的象征意义”[3],而且体现了茜与弗兰克直面过去、合力应对种族主义的决心。童年时,茜和弗兰克遇到活埋黑人事件,年幼的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成年后,在弗兰克的带领下,茜前往马场在月桂树下与弗兰克合力重埋尸骨。年幼时茜躲在弗兰克身后等待庇护,但成年后的茜经历磨难有了面对未知的胆魄。面对种族主义的迫害,茜选择勇敢站出来。
四、结语
在《家》中,莫里森描述了黑人女主人公从迷失到觉醒、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艰难抗争历程。聚焦点的转换体现了在父权制文化和种族主义的压迫下,茜艰难的生存困境;人物对话的设置,体现了茜逐渐觉醒的女性抗争意识;故事开篇和结尾的循环叙事结构呈现了茜抗争历程的起点与终点,体现了她自我救赎实现的轨迹。莫里森通过描述黑人女性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压迫下的生存遭遇及抗争历程,道出了黑人女性唯有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才能冲破精神枷锁,获得心灵救赎。
参考文献:
[1]托尼·莫里森.家[M].刘昱含,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
[2]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3(1):111-119.
[3]项玉宏.托尼·莫里森新作《家》的叙事策略[J].江淮论坛,2014(1):182-187.
(责任编辑:张咏梅)